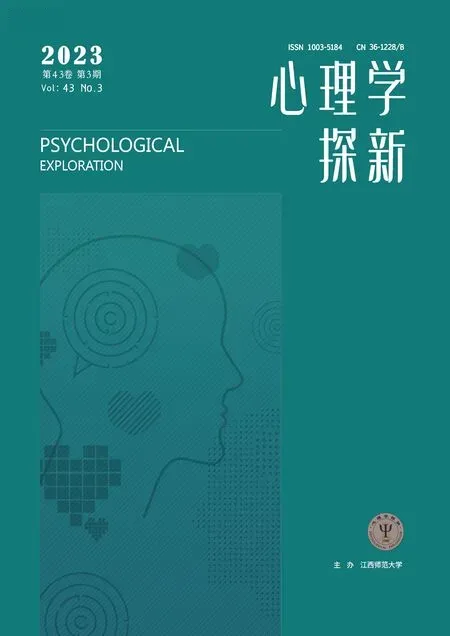物以类聚还是近墨者黑?同伴对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影响
2023-02-27张天羽王堃炎刘明东王晓娟沙晶莹张向葵
张天羽,王堃炎,刘明东,王晓娟,沙晶莹,张向葵
(1.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长春 130024;2.鞍山师范学院应用技术学院,鞍山 114000;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北京 100038)
1 引言
饮食失调(Eating disorder)也称进食障碍,是一种由不正常的饮食习惯或一组以异常进食行为为主的精神障碍(Berkman,Lohr,& Bulik,2007)。其临床型主要表现为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亚临床型主要表现为节食和贪食。现如今,在“以瘦为美”的社会风气下,苗条、骨感俨然成为一种潮流,人们会自觉接受有关身材管理信息的洗礼,并试图通过节食或贪食后催吐来迎合时代的审美偏好。然而,饮食失调会带来诸多负面的健康结果,如物质滥用、抑郁症状、过早衰亡等(Crow et al.,2008;Eichen et al.,2012;Ferreiro et al.,2014;王玉洁 等,2021)。因此,关注饮食失调的心理发生机制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导致饮食失调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身体不满意(Body dissatisfaction)是个体对身体的负面认知、情感体验和伴随性的行为调控(Carlson Jones,2004;Stice,2002;陈红,2006;王玉慧 等,2016),如错误审视身材、过度关心体重、不良进食行为等(Bibiloniet et al.,2013;Withnell &Bodell,2023)。研究表明,在非临床型的群体中,身体不满意和紊乱的饮食模式密切相关,并且这种紊乱的饮食模式极易发展成临床型的饮食失调(Bucchianeri et al.,2013;Gorrell et al.,2019)。此外,作为消极身体意象的典型情绪表现,身体不满意会让人们对自身身体持偏执的负面评价,从而容易引发如低自尊、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Jacobi et al.,2004;史攀 等,2020)。鉴于此,同样有必要识别诱发身体不满意的关键因素,从整体上帮助个体形成积极健康的身体观。
纵观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发展阶段,在青少年时期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在经历青春期生理变化的个体对其身体胖瘦的波动最为敏感。已有研究发现,41.6%的青少年整体上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满意,更有50.83%的女孩认为自己“超重了”(陈红,2006)。值得注意的是,由身体不满意引起的饮食失调在青少年群体中也十分常见(Taylor et al.,2006),如Bun等(2012)对6980名新西兰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15.8%男孩和32.5%女孩认为自己过胖,并通过体育运动、使用药物、贪食后催吐等方式来修正自己的体型。国内一项对1147名青少年的调查研究也发现,青春期女孩普遍存在对苗条身材的强迫观念,主要表现为过于关注体重问题,其中,在初中女生中,有13.8%尝试通过节食来抑制体重增长,而34.1%的女生选择过度运动的方法来保持或减轻体重,尽管许多人的体重都处于正常范围内(陈秋燕 等,2007)。与此同时,一旦青少年减肥失败,渴求的“瘦理想”愿望就会被压抑,使得心理资源骤减,引发情绪动荡及不良的心理状态,可能会通过食物来寻求安慰和满足感,容易对食物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进而导致他们过度进食或贪食(Sun et al.,2020)。然而,青少年时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期,更是身体迅速发育的高峰期,上述不良行为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严重的消极影响,也为个体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状况埋下隐患,应引起足够重视。
三重影响模型(The tripartite influence model)指出,媒体、家庭与同伴是青少年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最初影响源(Thompson et al.,1999)。相比于媒体和父母,同伴的作用更为凸显,因为“社会比较”的负面效应主要集中在同伴(Boyce et al.,2008)。青少年会依据某种标准自主选择同伴,同时又会与其同伴的态度和行为变得愈发相似,这种动态过程被称为同质性现象。众多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与其同伴会在诸多内化和外化行为上表现出同质性现象,如偏差行为、攻击行为,网络成瘾等(Haynie,Doogan,& Soller,2014;Rulison,Gest,& Loken,2013)。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作为潜在的风险行为,很可能也会表现出同质性现象。由此提出研究假设1: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上具有同质性。
为进一步剥离同质性现象的机制,探寻同质性发生的原因,Kandel(2017)提出同质性假说(Homophily hypothesis),它又分为两个过程:“选择效应”和“影响效应”。有关选择效应,即在行为特点、价值取向、经济地位、兴趣爱好等方面相似的人更容易相互选择,成为朋友。正是源于这种惺惺相惜,会强化彼此行为属性上的相似性(Hamm,2000)。相似性吸引理论(Similarity attraction theory)指出个体倾向选择与自己在态度、行为等方面相似的人群建立友谊,即因为相似性而产生了人际关系的吸引。不仅在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特征会出现相似性吸引(McPherson,Smith-Lovin,& Cook,2001),而且在人格特质、态度以及问题行为等多个领域也会出现相似性吸引(Jeon &Goodson,2015;Montoya &Horton,2012)。一项对 651 名青少年饮食失调的研究中发现:青春期女孩的同伴团体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行为上具有相似性(Kirsch et al.,2016)。同样,Simone等(2018)也发现青少年与那些有着相似的不健康体重控制模式的人建立友谊的可能性较大。由此基于上述理论及实证研究提出研究假设2: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上的同质性源于选择效应,即青少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身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方面相似的人做朋友。
关于影响效应,是指一个人在某种状态下的认知、表情、姿态、动作会感染周围的人,进而通过近距离的人际关系(如家人和亲密朋友)对远距离的人际关系(如同伴的同伴或朋友的朋友)产生影响(张镇,郭博达,2016)。这种“殊途同归”很可能使得一个人的行为模式受他人影响而趋近相同。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的核心是模仿学习,并强调普遍性和诱因对模仿的重要性。在同伴交往背景下,个体可能通过建模、奖励和惩罚,以及替代强化(观察学习)等方式来改变自身行为。由此可推论,倘若朝夕相处的同伴严格控制体重,同时又因身材姣好而在人际关系中颇受欢迎,很可能诱发个体发生模仿学习。如Crandall(1988)发现年轻女性的贪食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亲密的朋友愈发相似,这种结果主要源于社会化过程。相似的是,另一项研究也表明,青春期女孩容易把节食当作一种集体活动,为了满足群体归属感,同伴团体成员会从事节食以避免“与众不同”(Carey,Donaghue,& Broderick,2011)。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3: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上同质性的原因源于影响效应,即青少年与其同伴容易通过观察、模仿等相互影响的社会化过程致使彼此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方面表现出相似性。
探究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上的同质性及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明晰同质性,有助于根据青少年的友谊网络识别饮食失调高危团体;另一方面,探究作用机制,可以指导青少年构建良好的同伴交往环境及促进同伴间的积极相互影响。团体领域的研究可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来解决,通过两次及以上测量来捕捉个体属性和网络关系的动态变化,在控制结构网络效应和额外变量的基础上分离出个体属性对网络关系动态变化的影响和网络关系对个体属性动态变化的影响两个过程(Snijders et al.,2010)。该方法在自然环境中测量同伴团体,能够确保研究的生态效度(马绍奇,焦璨,张敏强,2011)。目前,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青少年欺负、抑郁、校园欺凌、亲社会行为等多个研究领域(Van Rijsewijk et al.,2016;Veenstra &Huitsing,2021),能够有效揭示青少年发展过程中与他人关系的变化及相应行为的变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同质性假说,结合相似性吸引理论及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通过横向及纵向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讨青少年与其同伴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相似性及原因,继而考察同伴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基于“物以类聚”,还是“近墨者黑”,以期为科学引导青少年慎重交友、健康交往以及人格健全发展提供一定的心理学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长春市某中学随机选取24个独立的班级进行三个时间点的测量,共有932名青少年参与测试,由于辍学、转学、生病或数据不完整等原因,T2、T3分别流失被试42、23人,考虑到样本量在纵向追踪研究中的重要性,当前研究对样本流失率进行了分析,经检验,T1时间点的流失被试与继续参与测试的被试在身体不满意、节食、贪食上均无显著差异(ts<1.96,ps>0.05),表明本研究中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在保留的867名被试中,400人(46.1%)为男性,467人(53.9%)为女性,其中269人(31%)为初一,281人(32.4%)为初二,317人(36.6%)为初三,基线时的平均年龄为14.5岁,标准差为0.95。
2.2 研究工具
(1)同伴关系网
事先根据各班班主任提供的班级名单确定班级规模,主试指导学生在关系数据测量处填写班级中比较亲密、要好的朋友的名字,并根据与其亲密要好关系的程度按照顺序填写(例如:在下方的1 _ _ 上填写与你最亲密的好友的名字,2 _ _上填写与你第二亲密的好友的名字,以此类推)。但只填写班级内部好友的名字。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 6为每个班级构建社会网络关系矩阵。
(2)身体不满意
采用Garner等(1983)编制的进食障碍量表(Eating Disorders Inventory,EDI)中的身体不满意分量表(EDI-BB)测量个体的身体不满意水平(如,“我对我的体型不满意”),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薇,王建平,2005)。共有9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6代表“总是”,总分越高,则表示身体不满意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身体不满意分量表三次测量的Cronbach’sα分别是0.83、0.82、0.88。
(3)限制性饮食
采用Van strien等(1986)编制的荷兰饮食行为问卷(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DEBQ)的限制性饮食分量表测量个体认知层面的限制性程度(如,“如果你的体重增加了,你会吃得比平时少吗?”)。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刘雪纯 等,2023),共包含10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5代表“总是”,总分越高,代表个体限制性饮食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三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5、0.87、0.83。
(4)贪食
采用Garner等(1983)编制的进食障碍量表(Eating Disorders Inventory,EDI)中的贪食分量表(EDI-B)测量个体的贪食水平(如,“当情绪低落我会吃东西”),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薇,王建平,2005)。共有7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法,1代表“从不”,6代表“总是”,总分越高,则表示贪食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贪食分量表三次测量的Cronbach’sα分别是0.86、0.85、0.79。
2.3 研究程序
为保证被试进入新班级后,充分结识新同学、选择新同伴,又尚未完全受到同伴影响,因此第一次测量在秋季学期开学后一个月进行,随后每间隔3个月追踪测量一次,共进行基线水平、T2、T3三次测量。在每次数据收集前,所有被试都获得了知情同意。调查由受过培训的研究生助理进行。参与者被要求在教室里填写纸笔问卷,涉及人口统计学项目、同伴关系网、荷兰饮食行为问卷和进食障碍量表。所有问卷在统一指导语下进行团体施测,并当场回收。参与者可以随时退出研究。完成调查后,参与者将获得一份学习文具或者学分作为参与补偿。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4.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借助Ucinet 6转换同伴矩阵图及形成班级关系网络。运用Stocnet 1.8中拟合指数随机图P2模块和SIENA程序进行横向及纵向社会网络分析。所得同质性结果及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均纳入到CMA 2.0进行元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所有变量在未旋转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三波数据中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分别为5个,且首个因子分别解释了总变异的22.6%、26.3%、26.1%,均低于临界值 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青少年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及同伴关系的描述性分析
对三个时间点的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情况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个时间点的身体不满意水平差异不显著(F(2,1732)=3.26,p=0.086),节食水平差异不显著(F(2,1732)=2.89,p=0.117),贪食水平不显著(F(2,1732)=2.73,p=0.132)。由此可知,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在三波测量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却相对稳定。就平均值来看,在T2中,身体不满意略有下降,节食、贪食略微升高,而在T3中,身体不满意略有提升,节食、贪食持续增加,结果见表1。

表1 青少年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与关系变量的描述性分析(M±SD)
另外,对青少年同伴关系进行描述性分析(见表1),结果显示,同伴的关系数量在三个波次的测量中呈动态变化的趋势,具体而言,相比于T1,T2的关系数量略有下降,而T3中又有所上升,相应的网络的密度的变化趋势也是先减后增。图1为某班三个时间点关系网的变化,其中,每个蓝色的正方形带代表一名学生,数字为该同学的序号(编码),从它发出的箭头代表着青少年对同伴的提名,指向它的箭头代表着个体接收到同伴的提名。从其关系及结构来看,不难发现班级网络由松散到聚合。

图1 某班级三波次同伴关系网
3.3 青少年与其同伴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的同质性分析
采用Stocnet软件中的P2模块对24个班级依次进行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横向社会网络分析,再将每个班级同质性的结果纳入元分析(见表2),由此获得比单个网络更可靠的效应估计。根据Robins等(2007)所提出的:参数的绝对值超过该参数标准误的2倍,则意味着结果显著的原理。可以发现,在身体不满意、节食水平上,青少年与其同伴存在着同质性。而在贪食水平上,同质性参数为0.06,标准误为0.04,不满足于参数绝对值大于标准误2倍的标准,结果不显著,说明在贪食上,青少年与其同伴不存在同质性。

表2 青少年与其同伴饮食失调同质性的元分析
3.4 身体不满意、节食同质性原因的纵向社会网络分析
鉴于在贪食上,青少年与其同伴不存在同质性,故不再对其同质性原因进行探讨,但需要对所有班级进行身体不满意、节食同质性原因的纵向社会网络分析。采用Stocnet软件中的SIENA模块做数据处理,再将所有结果纳入元分析。结果见表3,在身体不满意水平上,选择效应参数为0.03,标准误为0.04,不满足于参数绝对值大于标准误2倍的标准(Robins et al.,2007),故选择效应不显著,而影响效应参数为0.114,标准误为0.039,满足标准,影响效应显著。在节食水平上,选择效应参数为0.008,标准误为0.007,选择效应不显著,而影响效应参数为0.179,标准误为0.031,参数明显大于标准误2倍,因此,影响效应显著。

表3 身体不满意、节食同质性原因的元分析
4 讨论
4.1 青少年身体不满意、饮食失调及同伴关系的变化趋势
研究发现,在三个时间点的测量期间,青少年的身体不满意、节食、贪食虽然存在着一定的波动,却相对稳定。从各时间点的平均值来看,T2阶段,身体不满意略有下降,节食、贪食略微升高,T3阶段,身体不满意略有提升,节食、贪食持续增加。可能的原因是,身体不满意包括特质和状态两个方面(Colautti et al.,2011),研究表明,除人格特质、外表相关因素和社会文化影响外,身体不满意也与环境因素密切相关,因此会呈现出时而上升或下降的波动状态。反观节食、贪食方面,一方面,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发育迅速,心理发育迟缓的阶段,这些变化容易导致他们情绪持续波动,依据情绪调控模型,消极情绪可能会诱发青少年的饮食失调,如通过贪食和补偿性行为调节和对抗苦恼、恐惧、愤怒等心理感受(Kenny et al.,2022)。另一方面,处在身体发育黄金期的青少年会频繁地接受来自家长的“投喂”,在某种程度上很可能引发贪食,随之体重增加,再次诱发情绪困扰,从而导致那些身体感知敏感的青少年容易以节食来修正身体的变化。
在对青少年同伴关系的分析中,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发现,T1阶段,I(某同学)提名了J、K、L。T2阶段,I提名的顺序改变为K、L、J。T3阶段。I则提名了M、N、P,不再提名之前的同伴,这种变化趋势在低年级尤为明显,说明青少年的同伴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同伴关系的程度逐渐变化,或增强、或弱化;二是原来的同伴关系解散了,而创建了新的关系。这种表现可能是同伴关系网数量及密度不断变化的重要原因。
4.2 青少年身体不满意与饮食失调的同质性
通过横向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讨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相似性。结果发现,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节食上存在着同质性,在贪食上不具有同质性,部分支持研究假设1。这与一些已有研究的发现保持一致(Meyer &Waller,2001),可以为进一步探讨同质性原因提供数据支撑。然而,该结果也与少量已有研究结果相矛盾,如Crandall(1988)发现年轻女性的贪食水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亲密的朋友愈发相似。对于这种不一致的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外表对于社会接受度的谈论即同伴间关于“与理想身材一致有利于实现社会接纳”的谈论,以及肥胖谈论会加速青少年同伴团体间形成相同或相似的消极身体意象观(Wang et al.,2020),这种身体不满意会引发低自尊,进而促使青少年从事节食行为,从而导致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节食方面具有同质性。反观贪食方面,贪食行为可能与个体的饮食习惯和BMI水平有关,且这种行为本身与内化的“瘦理想”相悖离,在某种程度上受社会或团体规范的影响较小,从而导致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贪食方面不具有同质性(Marks,De Foe,& Collett,2020)。
4.3 青少年身体不满意与饮食失调同质性的作用机制
在验证了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节食相似性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采用纵向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考察了这种相似性的原因。遗憾的是,结果并未发现选择效应,不支持研究假设2,表示身体不满意和节食方面的相似性并不能作为青少年选择同伴的依据,或者说,友谊并不是围绕相似的身体不满意或节食水平而建立的,未验证相似性吸引理论,可能的解释是身体不满意和节食的相似性并不是青少年结识友谊的主要标准,相反,友谊的形成可能与性格、兴趣爱好、社会经济地位、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关(张云运,2022)。
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是基于影响效应,支持了研究假设3。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Paxton等(1991)发现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在身体意象问题和节食上会变的相似,其结果主要源于同伴间的社会化效应,即通过观察、模仿、强化、说服等相互影响的过程,诱发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身体不满意和节食方面表现出一致或相似的现象。这一结果与社会学习理论观点一致,可能的解释有,第一,同伴的消极身体意象和节食行为会促使青少年对自身身体进行审视,进而发生观察学习(张天羽,张向葵,2019);第二,青少年热衷于同伴间的外貌比较,以此来获得对自己身体外貌的整体评价(Barnhart et al.,2022),然而,经常性地上行比较,即与身体匀称、相貌姣好的同伴对比,尤其被比较对象在群体中还颇受欢迎,就会强化其“身材好等于受欢迎”的错误信念,进而产生身体不满意和节食行为(Myers &Crowther,2009)。最后,同伴间的肥胖谈论以及对自身节食计划或行动无心插柳的宣扬,均会导致青少年“瘦理想”内化,并把节食作为修正身材外貌的重要途径(Compeau &Ambwani,2013)。
4.4 研究价值与不足
本研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技术探讨在真实情景下,青少年与其同伴在友谊上的动态变化及行为属性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次印证了同伴是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强有力预测因素。同时,研究结果也很好地揭示了同伴对青少年身体不满意、身体失调的作用机制,对于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方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育工作者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同伴的作用,帮助青少年意识到同伴交往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潜在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心理健康工作人员可通过识别与干预团体中“危险人物”的身体满意度和饮食行为,帮助并引导青少年合理规避他人身体不满意和不良饮食行为的负面影响。
尽管本研究在班级网中系统地探讨了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选择和影响的过程,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无论是身体不满意,还是饮食失调,都是基于被试自我报告的,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青少年可能有意遮蔽自身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其他方法,如他评报告,以便更客观地考察变量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同伴影响和选择效应并非完全独立,可能存在着重叠效应,后续研究应当注意区分,并深度挖掘两者的交互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向和纵向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运动Stocnet软件中的P2模型进行青少年与其同伴饮食失调同质性分析,并基于随机行动模型(SIENA)对其同质性的原因进行选择和影响效应的检验,最终发现:青少年与其同伴在节食、身体不满意上具有同质性,在贪食上不具有同质性。造成节食、身体不满意同质性的原因是基于同伴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