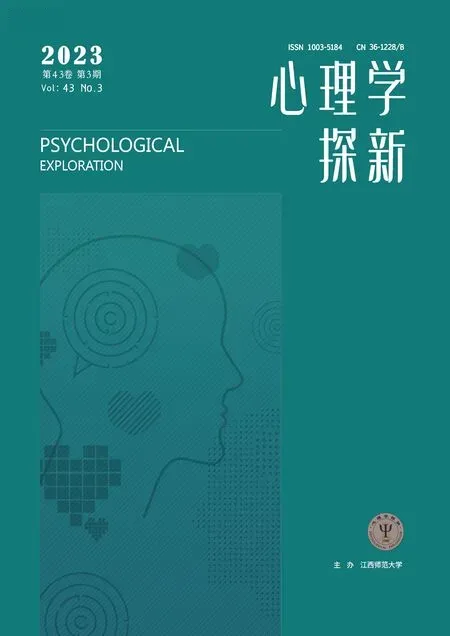眼睛注视方向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面孔情绪识别的影响
2023-02-27林云强叶嘉城赵顶位
林云强,叶嘉城,2,潘 彧,3,赵顶位
(1.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杭州 311231;2.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温州 325014;3.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系,上海 200062)
1 引言
面孔情绪作为社会情感和语言交流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情绪识别在个体社会交往能力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Axe &Evans,2012)。de Haan和Nelson(1997)的研究发现1周岁左右的婴儿就具有识别高兴、愤怒等基本面孔情绪的能力。社会交往障碍作为自闭症谱系障碍个体(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核心症状之一(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已有的证据表明在ASD群体当中存在普遍的、跨文化的面孔情绪识别困难(Fridenson-Hayo et al.,2016),这种困难被研究者们视为ASD个体社会交往障碍的重要表现(Harms,Martin,& Wallace,2010),具体可以表现为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的下降以及面孔识别正确反应时的增加(肖帅萍 等,2017)。
面孔情绪的识别依赖于许多面孔信息,其中眼睛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表达和理解情绪的重要依据,而眼睛注视方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交线索,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欲望和意图,并可能与环境中的重要社会事件相呼应(Ristic et al.,2005)。普通个体在面孔情绪识别过程中存在视线接触效应(Eye Contact Effect),眼睛正视相较于斜视能促进随即进行的面孔情绪加工认知过程(Senju &Johnson,2009)。Adams和Kleck(2003)的研究表明普通成年群体在进行面孔情绪识别时会一起加工眼睛注视方向这一信息。在识别高兴和愤怒情绪时,相比于其他的眼睛注视方向,正视的眼睛注视方向可以帮助个体更快地识别面孔情绪(Adams &Kleck,2003)。Bindman,Burton和Langton(2008)的研究同样发现,普通个体在识别高兴和悲伤情绪时,面孔眼睛注视方向为正视的反应时较注视方向为侧视的反应时短。
然而,荆伟和王庭照(2019)的研究发现在各类有关ASD个体的性别识别(Pellicano &Macrae,2009)、面孔记忆(Zaki &Johnson,2013)、高危婴儿的前瞻研究(Nele,Ellen,Petra,& Herbert,2015)等各类行为研究及生物和脑电研究中,ASD个体并没有在面孔加工任务中表现出视线接触效应。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DSM-5)将ASD儿童所表现出的视线加工障碍已作为诊断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个关键特征(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可以得到确认的是,ASD群体中确实存在普遍的视线加工异常。进一步的眼动研究证据显示,在特定情境下的面孔情绪识别任务中ASD个体对眼睛方向缺乏敏感性。例如,在观察厌恶情绪时,普通儿童在正向凝视条件下表现出对于眼部区域更长时间的注视行为,而ASD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对于眼部区域注视的增加(Bagherzadeh-Azbari et al.,2022)。因此,ASD个体的面孔情绪识别过程可能受到视线加工障碍的影响。
也有研究证据并不支持ASD个体的面孔情绪识别过程受到了视线加工障碍的影响,并且有研究提出面部情绪识别困难可能是ASD个体对于眼部定向不足的结果。例如,贺超颖,陈靓影和张坤等(2019)发现,眼睛注视方向会对ASD儿童的视线加工产生了正向影响,且呈现不同面孔类型时有不同的注视偏好。而Nuske,Vivanti和Dissanayake(2014)发现ASD儿童在识别面孔情绪时对眼部区域的注视会减少,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ASD个体在面孔加工过程中对眼部注视不足的情况会逐渐显现(荆伟,刘仔琴,2018)。元分析研究也揭示了ASD儿童相比普通儿童表现出明显的眼部区域注视缺陷(郝艳斌 等,2018)。这种眼部定向区域的注视减少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ASD个体面孔情绪信息获取的不充分。还有研究指出这种对眼睛注视减少的现象,可能是ASD个体调整眼睛感知到的威胁知觉的一种自我调节方式(Tanaka &Sung,2016)。
综上研究说明,ASD儿童在面孔认识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视线加工障碍或缺乏对眼部的关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眼睛注视方向产生情感反应(如威胁知觉)。由此可见,关于ASD儿童眼部线索的加工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目前还尚不清楚ASD儿童在进行面孔情绪识别任务的过程中是否会整合眼睛注视方向这一视觉线索。因此,研究拟通过面孔情绪识别任务,探讨眼睛注视方向对ASD儿童情绪识别的影响和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过程中的视线加工特征,并提出三点假设:(1)眼睛注视方向会对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产生影响;(2)面孔情绪类型会对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产生影响;(3)ASD儿童在不同眼睛注视方向下的面孔情绪识别的表现与普通儿童的面孔情绪表现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参加实验的对象选自某省的特殊教育学校和融合教育学校,其中有17名ASD儿童与17名普通儿童,每组男生15人,女生2人。每位参与实验的ASD儿童都具有省内专科医院出示的诊断书,或符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诊断标准,并排除共患其他类型的精神病性障碍或癫痫等。实验前,运用瑞文智力测验(Combined Raven’s Test,CRT)和毕保德图画词汇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PPVT)对两组儿童的言语理解能力和推理能力进行了测试,ASD儿童和普通儿童在心理发展水平上无显著差异,符合实验匹配的要求(见表1)。

表1 ASD儿童与普通儿童的PPVT和CRT得分及年龄
2.2 刺激材料
面孔图片采集自38名在校大学生(女25名,男13名),每人拍摄6张具有不同眼睛注视方向的中性情绪照片。拍摄完毕后由2位研究人员对图片进行筛选,删除眼睛注视方向和面孔情绪不符的照片。筛选依据如下:(1)对于眼睛注视方向,以眼睛中心为坐标轴原点,左水平方向为0°。当眼睛注视方向正视时,瞳孔应位于眼睛中心;正上注视时,则瞳孔位于眼睛中心正上方(90°±5°);左水平注视时,则瞳孔位于眼睛中心左水平方向(0°±5°);左上注视时,则瞳孔位于眼睛中心左上方向(45°±5°);右水平注视时,则瞳孔位于眼睛中心右水平方向(180°±5°);右上注视时,则瞳孔位于眼睛中心右上方向(135°±5°)。(2)对于中性表情,剔除闭眼,歪嘴(张嘴),皱眉等非中性表情特征图片,获得初选图片214张。随后:
(1)使用Adobe PhotoShop CS6对图片进行标准化处理,做到大小、明暗、空间频率、对比度等参数的统一,图片皆为彩色。

(3)将高兴和愤怒的图片再一次进行标准化处理,图片背景设置为白色并请80名学生对面孔情绪图片进行一致性评定,认同度达到90%以上的图片方可采纳,最终得到正式实验图片共180张(见图1)。

图1 实验刺激界面样式
2.3 实验程序
所有儿童被试均安排在相同、舒适的环境中完成实验。实验程序由E-Prime2.0编制完成,儿童坐在离显示器前约60cm的凳子上,调整到最佳实验状态。然后由主试将实验的基本步骤通过口述为主,文字为辅的方式进行告知。
2.3.1 练习实验
练习实验中的面孔图片皆为完整面孔图片,且眼神注视方向为正视,一共10张。在儿童充分理解实验要求的前提下,进行10次练习,具体程序见图2。在提示语之后,刺激界面呈现之前会提醒儿童注意屏幕变化,按键反应后自动转入空白页,空白页持续时间1000ms,所呈现的刺激界面随机出现,由被试识别情绪类型后,口头说出情绪名称,再由主试快速按下相应按钮。如果正确率达到或超过85%,即可开始正式实验。

图2 实验刺激材料呈现流程
2.3.2 正式实验
正式实验中的面孔图片分为6(眼神注视方向:正视、正上注视、左水平注视、左上注视、右水平注视、右上注视)× 3(情绪类型:高兴、中性、愤怒)个水平,每种水平下有10张图片。具体实验程序同练习实验,被试共需识别图片180张,实验中每识别完60张图片休息3-5分钟,并给予适当强化物奖励,从练习实验到正式实验平均用时约为30分钟。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主要选取儿童对面孔情绪识别的正确率值和正确反应时值进行处理,通过软件SPSS 22.0整理数据,未发现缺失值。对于反应时数据,剔除的极端值(平均数加减三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使用平均数值填充,最后再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检验。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分别以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和正确反应时(见表2)为因变量,以被试类型、眼睛注视方向和面孔情绪类型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表2 儿童对不同面孔情绪类型与眼睛注视方向的面孔情绪识别的正确率和反应时(M±SD)
3.1 正确率

图3 ASD儿童和普通儿童对不同情绪类型面孔识别的交互效应
3.2 正确反应时

图4 ASD儿童和普通儿童对不同眼睛注视方向面孔识别的交互效应
4 分析与讨论
4.1 ASD儿童在不同眼睛注视方向下对面孔情绪的识别能力偏低
有关儿童情绪识别正确率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被试类型对情绪识别正确率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ASD儿童的识别正确率显著低于普通儿童,表明ASD儿童在不同眼睛注视下对不同基本面孔情绪的整体识别能力偏低,与普通儿童相比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与诸多研究结论一致。Eack,Mazefsky和Minshew(2015)的研究表明普通成年人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要显著优于ASD成人。林云强和童叶莹(2016)的研究同样发现ASD儿童情绪识别能力与智力障碍儿童和普通儿童存在显著差异。然而,也有研究者发现ASD个体在情绪识别任务的表现与普通群体并无差异(Evers,Kerkhof,Steyaert,Noens,& Wagemans,2014),还有研究者提出,ASD个体中是仅有部分人在情绪识别方面是有困难的(Nuske,Vivanti,& Dissanayake,2013),以上差异可能来源于各种实验相关因素,包括参与者的特征,比例年龄、智力因素及共病等。例如,Nagy等(2021)发现,ASD的儿童对于面部情绪的识别受到任务时间的影响:在非限时实验条件下,ASD儿童对于面部情绪识别的正确率与对照组一致,而在限时的实验条件下,ASD儿童对于愤怒和惊讶情绪的识别正确率则要显著低于对照组。
对于正确率指标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注视方向并未对儿童面孔情绪识别结果产生影响。而来自反应时指标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注视方向与被试类别的交互效应显著而被试类别主效应不显著。结合以上结果可知,在非正视条件下,ASD儿童与TD儿童具有相近的反应时,但是面孔情绪的识别正确率却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并不能为视线加工障碍所解释。一方面,ASD儿童对于面孔情绪识别正确率的下降可能是面部(尤其是眼部)区域注视不足从而导致面部情绪信息获取不足引起的结果。来自ASD儿童面孔表情定向的眼动证据表明,在限时条件下,ASD儿童对于面部区域以及眼部区域的总注视时间要显著低于TD儿童(林云强 等,2022)。另一方面,Nagy等(2021)认为ASD个体使用了非典型的情绪处理机制导致ASD个体在情绪处理方面更为困难且费力。有研究证据表明ASD个体在完成情绪识别任务时,梭状回和杏仁核的活动减少,而楔前叶活动的增多(Wang et al.,2004)。Harms等(2010)认为这分别意味着面孔注视的减少和注意力负荷的增加。
4.2 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受情绪类型影响
在儿童情绪识别正确率方面,被试类型与情绪类型交互效应显著。首先,ASD儿童识别高兴情绪的效果显著优于中性和愤怒情绪,ASD儿童的情绪识别受到了情绪类型的影响,ASD儿童存在对积极情绪的识别优势。Wong,Beidel,Sarver和Sims(2012)的研究印证了这种ASD个体在识别消极情绪方面存在困难的事实。林云强和童叶莹(2016)在研究面孔偏转方向对ASD儿童情绪察觉的影响中也发现,在眼睛注视方向为正视的情况下,ASD儿童对高兴情绪的识别正确率高于愤怒情绪,在面孔情绪识别过程中存在正性情绪突显效应。来自脑磁图(MEG)的证据显示:与愤怒面孔相比,ASD儿童对于高兴面孔的神经活动增加,这表明ASD儿童对于愤怒情绪的反应不明显或不成熟(Leung et al.,2019)。
其次,与普通儿童相比,ASD儿童表现出识别中性情绪和愤怒情绪的障碍,ASD儿童识别中性和愤怒情绪的正确率显著低于普通儿童,而对于高兴情绪的识别与普通儿童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结果与Song,Kawabe,Hakoda和Du(2012)的研究结果一致,ASD儿童在识别高兴情绪上与普通儿童具备相同的优势。肖帅萍等(2017)的研究结果则有所不同,虽然ASD儿童对于高兴情绪识别更具优势,但是与普通儿童相比对于积极情绪的识别仍存在损伤。尽管各个研究还存在着部分不一致的结果与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相比于消极情绪,ASD儿童对于积极情绪的识别能力更佳。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ASD儿童能较好识别愤怒情绪(White,Maddox,& Panneton,2015),这种差异可能和不同研究所选取的被试年龄有关,如White等人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为平均年龄15岁的青少年ASD个体。此外,Ketelaars,In T Velt,Mol,Swaab和van Rijn(2016)研究结果表明ASD个体识别高兴、生气、害怕等面孔情绪的能力和普通个体相当,仅在低强度情绪识别上表现出困难,这种差异可能来自实验所选被试,该研究所选取的被试均为女性。
4.3 ASD儿童在进行面孔情绪识别过程中可能存在视线加工障碍,缺少对眼部线索的关注
在儿童情绪识别的反应时指标方面,被试类型与眼睛注视方向交互相互显著,结果显示ASD儿童对面孔情绪识别正确反应时不受眼睛注视方向影响,而眼睛注视方向对普通儿童面孔情绪识别的反应时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普通儿童在识别眼睛注视方向为正视的情绪面孔时较斜视面孔要更快,这表明普通儿童在识别面孔情绪时存在视线接触效应。但是,ASD儿童在识别面孔情绪过程中没能将注视方向这一眼部线索进行有效整合,存在一定的视线接触障碍,可能源于其杏仁核方面的损伤(Senju &Johnson,2009)。ASD儿童有研究表明普通个体在对高兴、愤怒、恐惧等情绪进行加工、识别、归因等任务时,杏仁核发挥了重要作用(Morgan,Nordahl,& Schumann,2013)。
荆伟和王庭照(2019)基于视线加工双通路理论的启示提出,ASD儿童的视线加工障碍可能是由于视线加工皮下通路先天功能异常而皮层通路后天发展异常所致。由于视线接触效应主要涉及皮下通路对正视视线的快速无意识反应能力,而ASD个体存在皮下通路功能异常,直视视线不能有效激活皮下通路,因而在各类面孔认知加工任务中均不能表现出视线接触效应。此外,视线接触障碍的产生还可能于其他脑区异常有关,Kleinhans等(2010)选取了高功能ASD个体和智力相匹配的普通个体作为被试,在要求被试们完成一项情绪匹配任务时发现,与普通个体相比,ASD个体的左侧前额叶激活显著降低,而枕叶激活显著提高。Kim等(2015)的研究同样发现ASD个体在受到面孔情绪刺激时,与认知相关的社交大脑的各个区域激活显著降低。
然而,眼睛注视方向为什么不影响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还有另一种解释,即眼睛回避假说(The eye avoidance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眼神接触对于ASD个体而言是具有社会威胁的,直接的眼神接触会导致杏仁核过度兴奋和对社会性刺激的高生理唤醒(Tanaka &Sung,2016),因此,ASD个体产生对眼部区域的回避,这种推论得到了来自有关ASD个体的眼动证据的支持,眼动研究证实了ASD儿童在观察面孔区域时存在着特异的视觉注视模式,即缺少对眼部区域的注视(Hadjikhani et al.,2017;Neumann,Spezio,Piven,& Adolphs,2006;Nuske,Vivanti,& Dissanayake,2014)。基于眼睛回避假说,ASD儿童在面孔情绪识别过程中缺乏眼部线索的关注,其对于面孔情绪的加工可能主要依赖非眼部区域,如嘴部,而非缺少视线加工能力。因此,在不同眼睛注视下,ASD儿童并没有在正确率和正确反应时等指标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5 结论
(1)ASD儿童对不同眼睛注视方向下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偏低,与心理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普通儿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2)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加工过程受情绪类型的影响,表现为在高兴情绪下优于中性情绪优于愤怒情绪。
(3)ASD儿童在面孔情绪识别的加工过程中可能存在视线加工障碍或缺少对眼部线索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