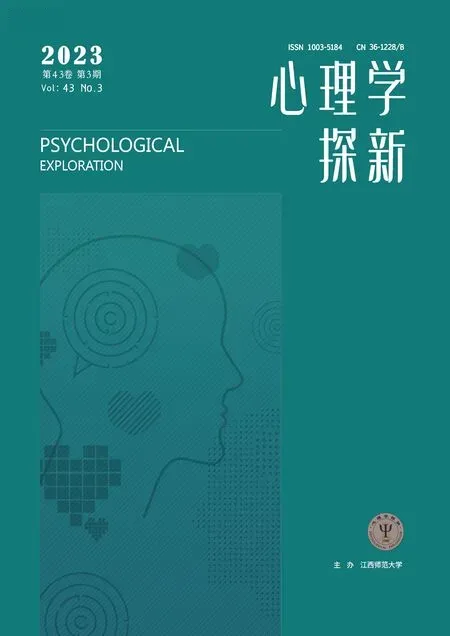精于西学为何执着守旧?
——“狂儒”辜鸿铭的心理传记学分析
2023-02-27高峰强韩耀杰付若冰
高峰强,宋 雪,韩耀杰,付若冰,田 梅,王 鹏
(1.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358;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3.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济南 250014)
1 引言
众多中国历史名人当中,辜鸿铭(1857-1928)可谓是“中西结合”的一名“文化混血儿”。因其曾留学西洋,精通英、德、法等多种语言却在西学东渐潮流中“顽固守旧”而被国人称为“清末怪杰”。19世纪晚期,如严复、容闳等有深厚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多选择“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而同样留洋归国的辜鸿铭却逆流而行,毕生致力于守护和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精神,提出“只有孔孟之道才可以救中国”。在其他留洋知识分子致力于翻译西方著作时,辜鸿铭却选择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等经典文学巨作翻译为外文,在当时的西方获得了“中国泰戈尔”的美誉(Chunmei,2011),直到今天,其经典译作仍被学者们参考研究。
然而,作为一名国学大师,辜鸿铭身后的评价却总是充满矛盾和疑惑。人们难以否认的是,他对中国封建传统有着近乎痴狂的个人偏爱,以至于有时对其糟粕也表现出一种不加选择的赞美和维护。在解放女性的时代,他钟爱三寸金莲,支持纳妾;在破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时代,他称赞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纯朴而高贵”。一直以来,辜鸿铭的矛盾、偏激、执拗与古怪吸引着学者们去解释与诠释他(胡春霞,2014;孟凡周,2010;钟慧琳,2009),但以往研究大多都是在意识层面对其个人经历进行描述,以尽可能地引发人们的理解。近年来,研究发现辜鸿铭本人也曾出于自我防御策略对自身经历进行隐瞒(程巍,2017),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在更深层面上结合心理学理论,分析其行为深层的心理动机,才能真正回答他为什么“精于西学而执着守旧”的悬疑性问题。
与本研究的需求相对应,心理传记学是立足于“问题主义中心”式的,探索个体独立性的一种特则研究,是对“人性”问题的直接关注(马皑,宋业臻,2019;郑剑虹,2014)。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心理传记学对那些颇富争议的天才巨擘尤为感兴趣,例如有精神疾病迹象的世界国际象棋冠军Bobby Fischer(Ponterotto &Reynolds,2013),豪爽大气却也傲慢无礼的一代大儒熊十力(丁雪 等,2020),以及不婚的旷世奇才牛顿(王鹏 等,2021)等,本研究的传主辜鸿铭先生也是一位这样古怪而又杰出的人物。近年来,由于社会的发展使得大众对辜鸿铭的评价渐渐趋于客观,满足心理传记分析的基本要求(舒跃育,2018),因而本文采用心理传记学方法,对辜鸿铭的人格特质与保守主义成因进行尝试性解读。
2 方法
2.1 伦理原则
研究遵循心理学家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Ponterotto &Reynolds,2017),研究资料均来自公开可查询的读物。研究以尊重、移情和负责的态度与方式对传主人格与观念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说明,旨在帮助大众更好地透视人类存世的多样性与无限的发展潜能。
2.2 资料筛选与理论选择
研究使用资料包括传记、信函集、传主作品以及相关文献与报纸,资料筛选时通过寻找 “凸显性指标”与“原型情景”来定位有特别心理意义之处(舒跃育,王栋,2012;舒跃育,杨玲,2008;郑剑虹,黄希庭,2013)。理论选择时遵循“手套”原则,即寻找与辜鸿铭生涯贴合力高的心理学理论对悬疑性问题进行解释(威廉·托德·舒尔茨,2011)。
2.3 传记撰写与有效性考察
撰写传记并参照“优秀心理传记作品标志”进行检阅修订(威廉·托德·舒尔茨,2011),使用Runyan(1988)准法庭程序对研究进行准确性评价,确保研究严谨性。
3 结果
3.1 童年经历形成“慢生命史策略”
1911年,辜鸿铭在寄给骆任廷爵士的信中曾提到,自己花了20年时间才翻译出令其完全满意的《中庸》译本,然而在那个时代,辜鸿铭的所耗费的心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生活上,辜鸿铭中晚年的日子也非常困顿,从表1也可以更为感性和直观地看出当时的辜鸿铭处于一种物质资源极为稀缺的状态。

表1 辜鸿铭的私人信函
除此之外,辜鸿铭的信件中还有很多请求朋友帮忙安排职业、寻找出版社的内容,为什么辜鸿铭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坚持自己的翻译与写作事业?为什么辜鸿铭始终难以放下傲骨和气节?欲探讨辜鸿铭的人格成因,还要从其早期经历着手。
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他的父亲辜紫云是当时橡胶园的主管。辜曾在演讲中提到自己童年时期的生活“无非就是爬爬椰子树,在灌木丛旁的河流里游游泳,期间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些马来语的歌曲”(孔庆茂,2015,p.102)。孔庆茂先生也在评传中这样描写辜鸿铭的童年:“不用说,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不过在他心目中,只知道这连片的橡胶园、幢幢别墅洋房,知道层层叠叠、翠蔓拂缀的热带丛林…… ”(孔庆茂,2015,p.23)。
实际上,心理学历来重视个体发展敏感时期的相关经历对人格与能力形成的影响。例如,生命史理论提出,个体生命早期的经验能够为其提供“生存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线索,为了更有效地适应环境,个体会在无意识当中调整生命发展的策略与节奏(Ellis et al.,2009)。在恶劣环境成长起来的个体对未来环境的预期是不稳定的,因而采用快策略,强调短期的回报与机会主义。相反,成长于良好环境的个体对未来环境的预期是稳定、充足的,因而采用慢策略,视野更为长远,具有更强的延迟满足能力(徐斐,孙时进,2019;Griskevicius et al.,2013;Griskevicius et al.,2011;White et al.,2013)。
辜鸿铭的童年安逸愉快,而他后来的行为表现也支持了他慢生命史策略的观点。一方面,辜鸿铭视野长远,延迟满足能力强。他不仅在缺乏积极反馈的条件下坚持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且在清末时期就有预见性地点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须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来吸收消化现代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辜鸿铭在生活与工作中表现出“机会主义”的极端对立面。例如在洋务运动问题上,辜鸿铭就被张之洞批评“知经而不知权”,他从不趋炎附势,在张之洞帐下做了十八年的幕僚,职位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位置上。在中国的局势进一步严峻之后,辜鸿铭更是表现出了适应困难。当辜鸿铭在物质资源丰富的环境下成长为一个“慢策略者”之后,所处的环境却渐渐变得危机重重,这从个人发展历程而言颇具戏剧性与悲剧色彩。
3.2 青少年时期的自卑与“优越情结”
辜鸿铭童年的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他锲而不舍的人格基础,但仅从童年生存环境断定个体之后的发展路径也不甚恰当。在辜鸿铭的成长历程当中,青少年时期的留学经历同样存在着反映辜鸿铭人格发展变化的原型情景与凸显性指标。
与严复、容闳等人不同,辜鸿铭开始留学是在青少年时期,在这样一个自我同一性与自我概念发展的关键敏感阶段,辜鸿铭经历了什么?1921年,辜鸿铭在“中英学社”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到了自己在苏格兰的“社交生活”,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辜鸿铭主要讲述的却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位曾于中国通商口岸居住过的苏格兰女士:“这位女士在回到自己苏格兰的家乡后,遭到了当地中产阶级的鄙视,即使她租赁了豪华宽敞的别墅,并且买了昂贵的家具,过着贵妇般的生活,当地人也不再视其为高贵的夫人,而是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最终,她被所有人排斥,不得不离开了爱丁堡(辜鸿铭,2018,p.106)。”
实际上,辜鸿铭从不直接提及自己的种族歧视经历,而总是以这样隐晦的方式来暗示自身可能的遭遇。另外,他还曾叙述过自己在留洋时期因“辫子”而引起的尴尬经历,但实际上关于这段经历的描述有很多不一致或完全不同的版本,而它们却都源于辜鸿铭本人的叙述(见表2)。

表2 辜鸿铭对“辫子的故事”的不同叙述
三种版本中的一些描述显得幽默又热情,而一些描述却涉及与性别有关的侮辱。由于客观限制,现有研究并不清楚究竟哪一个版本最接近事实,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涉及了辜鸿铭自身叙述的矛盾,符合“失误”或“扭曲”的凸显性指标(舒跃育,王栋,2012;威廉·托德·舒尔茨,2011)——无论遗忘还是扭曲,都能说明关于辫子的经历涉及了辜鸿铭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性别误会与一定程度上的尴尬与受辱,而这种经历又恰好发生在辜鸿铭自我同一性与自我概念的发展时期。
种族歧视与“辫子”带来的性别误会不可避免地会让个体产生“自卑感”。而实际上,辜鸿铭确实在这样一个发展自我独立性的阶段,发现身在异国、言语不通的自己甚至难以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情:“还有一次,两位年长的未婚女士有一天邀请他共进晚餐,在喝下了多杯姜汁啤酒之后,他便想去卫生间,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结果,晚宴还未结束时,人们就把他送回了家,他啜泣不已,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我想去卫生间’(辜鸿铭,2018,p.104)。”
综上,可以合理推测,留学时期的辜鸿铭遭受了自卑的痛苦体验,但为什么后来人们所认识到的辜鸿铭却如此好骂善辩?阿德勒认为,自卑是一种推动个体心灵活动的人格动力,为了克服自卑感,一些个体会用先天的“侵犯驱力”来寻求补偿,从而促使个体更加“男性化”。他认为任何形式的、不受禁令约束的攻击、敏捷、能力、权力,以及勇敢、侵犯都是男性气质的表现。此外,个体需要通过“追求优越”来克服自卑,如果追求过度,则会产生“优越情结”(阿尔弗雷德·阿德勒,2019)。
与此对应,辜鸿铭确实存在部分上述人格表现。例如,曾有评传对辜鸿铭的“骂”进行过概括性的描述:“他骂慈禧太后‘万寿无疆,百姓遭殃’,骂袁世凯‘贱种’,骂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出洋看洋画耳’……(孔庆茂,2015,p.15)”此外,即使是对跟自己关系紧密的朋友骆任廷爵士,辜鸿也难以掩饰自己的“攻击”倾向,他在同爵士的信件中经常提前预告或者在之后解释一下自己的“失礼”:“我知道,写这样一封信函给您,或许意味着要和您唇枪舌剑一番,甚至反目成仇,然而,我必须要有思考的自由……(辜鸿铭,2018,p.44)”最后,作为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辜鸿铭的“合理化”也颇为出名,即个体编造出一个似乎合理但实际上站不住脚的解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19),辜鸿铭曾以三三得九固不能改来论证数千年前孔子教人之法能行于今日,这种“不允许”自己的观点被驳倒的执拗也能够作为辜鸿铭“优越情结”的佐证。
3.3 青年时期的创伤性事件
虽然辜鸿铭后来成为了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在刚刚回国时就是一个坚定的“中国人”,相反,在政治身份上他甚至是一个“大英子民”,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享受自己作为“大英子民”的利益。在生理身份上,一些研究也对辜鸿铭是否其养父布朗先生的私生子这一问题存疑(程巍,2019;Clunas,2020)。在回到中国后,辜鸿铭还写过一首名为《过去的好时光不再有》的离别诗,这表现出当时的他正处在一种对归属的混乱状态:
思绪纷纷,与对异国的四季
它的白天与黑夜还有他处的天空的回忆
痛苦地交织……这些我童年熟悉的面孔
如今,我浪游归来,已习惯异国景象的双眼
却觉得他们如同异域之人,我回过头,思绪飞回那片已隔重洋的土地
和多年前的那些景致与面孔(程巍,2019)。
事实上,在写下这首诗时,辜鸿铭的父母和养父都已去世了。那么在这样一种对归属的迷茫状态下,是什么让辜鸿铭产生了如此深刻的执念,让他为宣扬传统文化的事业奋斗终生?据辜鸿铭描述,自己重新变成一个中国人的原因是与马建忠的一次偶遇,在这次会面中,马建忠对自己大为赏识:“‘但这太不可思议了’,他说,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该满足在洋人的办公室当小职员的……尽管你丢掉了自己本有的民族身份,成了一个欧洲人,但欧洲人,英国人,永远不会把你视为他们中的一员(程巍,2017)。”
而最近的研究发现,辜鸿铭的这段自述存在着明显不实与捏造的成分,让辜鸿铭重新变成一个中国人的真正原因更可能是他的躯体受辱经历(程巍,2017)。研究者依据辜鸿铭在上海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演讲中的多次跑题,对此进行了推测(见表3)。

表3 多家报纸对辜鸿铭“跑题”的报道
心理传记学格外重视传主的“重复性行为线索”(舒跃育,王栋,2012;威廉·托德·舒尔茨,2011),即为什么辜鸿铭在演讲中多次 “跑题”,解读这样一些与上下文不连贯的“孤立”内容,他在执迷于什么?同青少年时期的种族歧视一样,辜鸿铭对这次创伤性事件同样也采取了隐晦宣泄的方式,甚至用被证实不会存在的“同马建忠的会面”来掩盖,以至于几乎所有辜鸿铭的传记都描写其走上民族主义道路的“诱因”是他同马建忠的会面,直到近些年研究才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可见辜鸿铭对此是讳莫如深的。
3.4 孤独感与“逃避自由”
虽然辜鸿铭乖张怪诞的言谈与形象常常伴随着幽默色彩,但他在大多数时候总还是一个孤独而不受认可的人。面对外界的误解与诋毁,辜鸿铭尝试在“概化他人”与“重要他人”之间划清界限:“我会在乎什么美名或者骂名吗?在这关键的时刻,我渴望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贴近并在乎那些靠近我、在乎我的人们(辜鸿铭,2018,p.13)……”
这是辜鸿铭1891年同骆任廷爵士通信中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他以一种反问的形式叙述自身的不屑,这种关乎过分强调的否认常常让人生疑,辜鸿铭真的不在乎吗?需要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生来具有对尊重的需要(亚伯拉罕·马斯洛,2013),这一点在之后的信件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在1916年7月与骆任廷爵士的书信中,辜鸿铭附上了汪凤瀛为他写的六十岁寿辰的祝寿辞,希望骆任廷爵士能帮他把这篇祝寿辞翻译成英文,并刊登在英文报纸上。在同年8月6日的信件中,辜鸿铭再次提到了这件事,此时辜鸿铭已经“降格以求”,自行将文稿翻译成英文了,他再次请求骆任廷帮忙在报纸上刊登祝寿辞。11天之后,辜鸿铭再次写信,此时辜鸿铭的愿望已经达成,在这个时候辜鸿铭才以委婉的方式向骆任廷解释,自己确实渴望被认同(见表4)。

表4 辜鸿铭多次请求骆任廷爵士将自己的祝寿辞刊登在报纸上
辜鸿铭终生都是一个将自己的伤疤藏起来的人,无论是留洋时期的种族歧视,还是回国后的受辱经历,辜鸿铭都以遗忘、否认、歪曲与欺骗的形式将其掩盖起来,毕竟他所处的环境抱有如此多的恶意。在1906年6月同骆任廷爵士的通信当中,辜鸿铭第一次赤裸裸地表达自己的孤独:“我这一辈子都只能凭借一己之力来孤军奋战。作为一个被欧洲化了的中国人,我自然无法获得来自本国同胞或是外国同仁的丝毫同情。从来没有一个人,哪怕是伸把手,来帮我走出困境,我所面对的只有永不停休的辩论和针锋相对的争斗。在上海祥和欢庆的气氛中,您或许并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孤独(辜鸿铭,2018,p.36)。”
关于此,弗洛姆的社会精神分析论曾经进行了关于孤独感的探讨。他提出,个体的孤独无助感与会与“自由”相伴产生,当社会解除了传统的束缚而寻求个人的独立性时,个体就会产生“个体化”。而个体化的过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益增多;另一方面,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为个体提供积极的个体化所需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个体又失去了那些能够为他提供安全感的纽带,这时自由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相伴产生的不安全感与孤独感会促使个体逃避自由(埃里希·弗洛姆,2002;郭永玉,2022)。
在封建制度中,个体的行为和思想上都会受到伦理道德的束缚,因而能够满足个体逃避自由的需求。而辜鸿铭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情感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自由的逃避。例如,辜鸿铭倾心于中国封建制度下忠诚而牢固的君臣父子关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人要各自安于自己的名分。因此,辜鸿铭对于忠君之人也一概持褒扬态度,他对于义和团反洋教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是重义尊王的精神体现。慈禧死后,辜鸿铭曾作《已故皇太后》一文致《字林西报》,表示对该报挖苦慈禧的不满,他写道:“她智识的杰出,来自于品德的高尚、灵魂的伟大(辜鸿铭,1996,p.394)”。在文化上,辜鸿铭则认为中国的道德文化与社会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他提出:“在中国,如果你攻击并消除臣民对于皇帝的尊崇,建立起没有皇帝的共和国,那就破坏了民众道德所依赖的整体框架(辜鸿铭,2018,p.133)。”
除了“保皇”,大众对辜鸿铭更深的偏见来源于他对于裹足、纳妾的赞美。辜鸿铭把“妾”解释为“立女”,意为站在男人身边作为扶手的女人,他赞美中国妇道的“三从四德”,提出“三从”是一种无私的牺牲和“无我”的精神,认为裹足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辜鸿铭为什么如此偏爱裹足与纳妾?孔庆茂提出,这是辜鸿铭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体现,是对中国礼教的情感。而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如果说辜鸿铭逃避自由而偏爱封建制度以谋求归属感,那么其妻子和妾室则将自由交给了辜鸿铭,使其获得了一种倾斜、忠诚而牢靠的人际关系,即从女性忘我的过度奉献中获得与孤独感相抗衡的安全感与归属感。
4 讨论与结论
辜鸿铭总是以“古怪”著称于世的,他的奇谈怪论、逸闻趣事,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广为流传,死后更加扑朔迷离。身为一个喝洋墨水长大的人,辜鸿铭为何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此痴迷?除了一些存在于他自身意识内的原因之外,是否还有一些无意识中的、情感驱动的原因令他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动机,以至于使他逆时代潮流并坚持终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使用了多种心理理论分别对其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诠释,得出以下结论:
在童年时期,辜鸿铭安逸、优渥的经历令他形成了“慢生命史策略”,为他执拗且坚守的人格奠定了早期基础。在青少年时期,处在自我同一独立性发展关键时期的辜鸿铭在留学期间经历了自卑的痛苦体验,而对自卑的过度补偿使其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优越情结”。在青年时期,创伤性的受辱事件推动辜鸿铭从角色混乱的混血儿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最后,辜鸿铭对中国封建文化不加选择的偏爱部分源自于不可抑制的孤独感促成了其对自由的逃避。
在理论贡献上,本研究也可为心理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比如,在本研究中可以提出的疑问是,为什么同样怀揣报国梦想留学西洋,辜鸿铭和严复等人归国后做出的选择如此不同?为什么只有辜鸿铭在遭遇了种族歧视之后产生了人格上的“优越情结”?本文分析认为原因包含两点:(1)首先,严复、容闳等人开始留学均为成年以后,而辜鸿铭开始留学是在10岁或14岁,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年龄差,留洋期间的种族歧视环境才得以在更大程度上影响辜的人格,促进“优越情结”的产生,使其在人格上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2)其次,相比于严复、容闳、詹天佑等“组队留洋”的知识分子,辜鸿铭在同伴支持上的缺乏可能更为严重,因而会产生更强烈的、对自我认可、对归属的需求,这也助推了辜鸿铭对封建传统的情感和热忱。反映在对心理理论的启示上,阿德勒提出,自卑带来的追求优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其会激励个体产生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其可能会使个体产生“优越情结”。然而,已有理论并不明晰是否产生“优越情结”取决于哪些因素,辜鸿铭的例子则启示了,受歧视或遭遇自卑体验的年龄,以及个体在自卑经历中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可能会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在实践意义上,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来帮助人们辩证地看待“留学低龄化”可能带来的心理发展问题,以及童年环境对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意义。
研究虽然得到了有意义的结果,但也有以下几点局限:(1)首先,本研究仅从无意识的角度阐述了辜鸿铭保守主义人格的成因,而实际上,辜鸿铭幼年时所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导师卡莱尔文化保守主义观以及辜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等都对其人格和保守主义思想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影响(胡春霞,2014;孟凡周,2010;钟慧琳,2009),由于这并不是当前心理传记学方法能完全解释的,因而本研究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未来研究可结合文化学、社会学等进行进一步阐释。(2)其次,虽然本研究使用“生命史理论”、“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以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对辜鸿铭的人格和思想成因进行了较为贴合的解读,但是研究依然可能有“偶然”和“巧合”的成分存在,依然需要以严谨的态度看待心理学理论对个案生命的诠释。(3)最后,虽然作者尽力以一种客观的视角与立场展开阐析,但个人观念的融入可能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