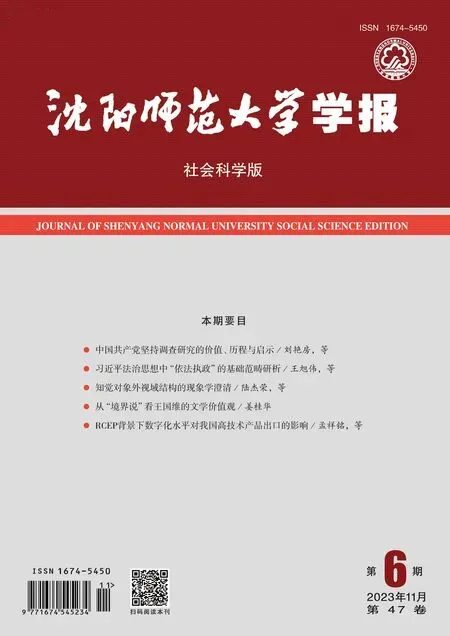从“境界说”看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观
2023-02-25姜桂华
姜桂华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王国维的“境界说”大致形成于1905 年至1908 年之间,由《人间词话》集中呈现。由于《人间词话》用印象式、感悟式、点评式这种传统的诗话词话形式结构成篇,在形态上、结构上、话语方式上不具备典型的理论性、系统性,在观点的表达上具有某种朦胧性,导致很多研究者在深表遗憾的基础上不断做着替王国维重建理论体系、订正理论观点和深挖理论来源的工作。应该说,这些研究者的努力是有意义的,它证明“境界说”及《人间词话》在由非理论形态的传统诗学走向理论形态的现代诗学过程中,确有特殊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学界也有必要反思:过多纠缠于“境界说”理论形态的建构、理论来源的挖掘并试图极力厘清中、西影响的界限,对于理解“境界说”、理解《人间词话》,乃至理解王国维的文学观及其意义,是不是也会导致某种程度的遮蔽?因为任何经典文论的意蕴解析和意义发掘,都需要后世学人结合学术本身的发展,以及学术与时代的有效关联,有意识地不断变换观照角度、研究方法和阐释方向,让经典本就具备的巨大的阐释空间真正敞开,不断向后人、向新的时代释放新的价值。基于此,本文尝试打破王国维研究领域惯有的“理论形态”“理论来源”等执念,从文学批评价值取向的角度阐释王国维的“境界说”,致力于理解其中蕴含的文学价值观。
一、“境界”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蕴含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概念、高频词汇,主要用于词这种文体的评价和论说,但实际上王国维对它的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一本书或一种文体。同时,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王国维有时还会以“意境”一词表达与“境界”基本相同的意指①在“境界说”研究领域,有些学者认为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与“意境”含义不同,主张将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本文侧重点在于考察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忽略两个词的微弱差别不会影响整体判断,故在基本同义的层面上理解二词。。比如,《宋元戏曲考》中就有这样的表述:“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1]389可以说,在王国维那里,“境界”是用来评价以词为主的一切抒情性文学作品(也包括戏曲等叙事类作品)的价值标准。
《人间词话》首刊本第一则即开宗明义将“境界”树为高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2]3也就是说,判断词作优秀与否只看“境界”有无即可,有“境界”则优,无“境界”则劣。从宏观的时代视野看,五代、北宋词就是有“境界”的优秀作品的典范。而且,王国维对自己确立的“境界”标准是颇为自得的,他说:“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2]7他同意严羽对盛唐诗玲珑透彻、含蓄蕴藉等特点的形容,并把五代、北宋词拿来与之相提并论,却不同意用“兴趣”或“神韵”来概括这些好作品。类似的言论还有:“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2]46可见,“境界”于王国维,并不是无意或偶一用之的闲聊文学的随机用语,而是用心凝练而成的,蕴含确定、独特而深刻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评价文学优劣的价值标准。
那么,评价文学,“境界”何以能“探其本”,而“兴趣”“神韵”“气质”等何以“不过道其面目”呢?这确实是耐人寻味的问题,现当代文论领域很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探析。咀嚼、辨析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言论,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境界”的蕴含具有启发和镜鉴意义。20 世纪40 年代,朱光潜曾在《诗论》中表示自己倾向于以“境界”言诗:“从前诗话家常拈出一两个字来称呼诗的这种独立自足的小天地。严沧浪所说的‘兴趣’,王渔洋所说的‘神韵’,袁简斋所说的‘性灵’都只能得其片面。王静安标举‘境界’,似较赅括,这里就采用它。”[3]186之所以认为以“境界”说诗全面,而以其他词语说诗片面,因为朱光潜是从诗与人生世相关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他认为诗“是从混整的悠久而流动的人生世相中摄取来的一刹那,一片段”,由于艺术家灌注生命给它、赋予完整的形象给它,所以它拥有了“在刹那中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千,在有限中寓无限”[3]186的特质,这样的特质,只有“境界”一词能够准确表达。将诗与人的生活相关联,将诗的意义提升至更广、更深、更高的人生追求层面,朱光潜对“境界”的理解极富启发性。叶嘉莹指出:“沧浪之所谓‘兴趣’,似偏重在感受作用本身之感发的活动;阮亭之所谓‘神韵’似偏重由感兴而引起的言外之情趣;至于静安之所谓‘境界’,则似偏重在所引发之感受在作品中具体之呈现。”[4]279这是将文学的基本特征定位在“感受”或曰“兴发感动”上来理解“境界”与其他表述的不同。认为用“兴趣”“神韵”“境界”谈论诗词,都是重视文学感受性这种审美特征的表现,只不过“兴趣”侧重于关注创作主体的感发活动,“神韵”侧重于考察欣赏主体联类无穷回味不尽的状态,“境界”则侧重于探析作品中感受的具体呈现。这种沿着作家、读者、作品三个维度区分三种表述的做法,足够清晰细致,但未能回答“本”与“面目”的问题。因为对于文学来说,作家、作品、读者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从某一角度出发片面强调某一因素的绝对重要性是违反文学规律的,这也正是欧美“新批评”所谓的“意图谬误”和“感受谬误”站不住脚的原因。好在叶嘉莹没有搁置“本”与“面目”的问题,她认为,从所标举词语的义界看,“兴趣”“神韵”较空灵,“境界”较质实,从对诗歌质素的体认看,“则沧浪及阮亭所标举的,都只是对于这种感发作用模糊的体会,所以除了以极玄妙的禅家之妙悟为说外,仅能以一些缪悠恍惚的意象为喻,读者既对其真正之意旨难以掌握,因此他们二人的诗说,遂都滋生了很多流弊;至于静安先生,则其所体悟者,不仅较之前二人更为真切质实,而且对其所标举之‘境界’,也有较明白而富于反省思考的诠释”[4]279。也就是说,以“兴趣”“神韵”等论诗词失之玄虚,而王国维以“境界”论诗词则相对切实、明确、有理论意味。应该说,叶嘉莹的比较符合几种表述的基本情况,但似乎还是局限在几个词语的表达特点和表达效果角度进行思考,且分析也有较强的感受性。写有《王国维诗学研究》的佛雏对“本末”问题也有论及,他认为,严沧浪的“兴趣”、王渔洋的“神韵”、沈德潜的“格调”、袁简斋的“性灵”等,“仅仅涉及‘境界’的外围或某一侧面”,而“境界”则是“诗的一根枢轴”,围绕这根“枢轴”,王国维“就境界的主客体及其对待关系,境界的辩证结构及其内在的矛盾运动,境界的特性与发展规律,以至境界作为艺术鉴赏的标准,等等,即涉及诗的本体、创作、鉴赏、发展四大方面,作出比较严格的分析,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诗论体系”[5]171。这是从诗学理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将“境界”定在核心概念的位置。毋庸置疑,从分析较严格、体系较完整的角度将王国维的诗学贡献突显出来,与中国传统诗论区别开来,是有意义的,但佛雏仅从“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入”与“出”、“渐”与“顿”、“隔”与“不隔”四种“对待关系”分析了“境界”的构造过程,未能很好地阐释王国维以“境界”为核心的诗学本体论、创作论、鉴赏论、发展论的清晰面目,以及确切内容和几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透彻揭示出王国维“境界说”高出前辈和同代侪辈诗论的奥妙所在,亦属遗憾。
与以上学者大多从诗学内部理解问题不同,李泽厚则是从时代性质的角度,在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等冲突意识下理解王国维的“境界说”,认为正是对“近代主题”的敏感和苦思冥想,王国维才提出“建构一个超利害忘物我的艺术本体世界(‘境界’)”,这“就比严羽(沧浪)、王士祯(渔洋)以禅悟为基础的‘兴趣’‘神韵’的美学理论,要在哲学层次上高出一头”[6]404。他说:“我认为,这‘境界’的特点在于,它不只是作家的胸怀、气质、情感、性灵,也不只是作品的风味、神韵、兴趣,同时它也不只是情景问题。它是通过情景问题,强调了对象化、客观化的艺术本体世界中所透露出来的人生,亦即人生境界的展示。”[6]402这是将“境界”定位在从哲学高度思考、感受和表现人生,在本体的高度上形成与近代困苦现实相对照的层面上来理解,突出了它的根本意义和包蕴性:创作主体层面的气质等问题,作品层面的神韵、兴趣等问题,创作过程中物我、情景关系等问题,都是“境界”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李泽厚拈出“本体”二字和“人生”二字理解“境界”,从将文学提升至人类终极关怀的根本位置这一角度理解王国维,是在不同高度、广度、深度上分清了“境界”与“兴趣”“神韵”等的差异,也就是从对文学重要价值认识的角度回答了王国维的“本末”问题。只不过李泽厚当年着力于建构人类学本体论(主体性实践论)的哲学和美学,没有从文学价值观的角度对“境界说”做进一步的阐释。后来夏中义以“生命感悟”[7]30-31、刘锋杰以“生命之敞亮”[8]对“境界说”进行阐释,都有可贵的启发意义,只是他们的探索也未明确触及文学价值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哲学领域出现了价值论研究热,与此相应,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丰富的价值论话语,一些学者尝试对文学价值观做出较严格的学理界定。像“文学价值观是参与文学活动的人,以自身的文学‘需求系统’为标准,对文学的客观属性及它与人的价值关系的认识整合而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对文学意义和对文学活动进行价值评价的思维框架”[9]7这样的表述一时比较多见。从将文学价值观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来说,这些既追求个人思考的独创性又遵循价值理解的共通性的探究是可贵的、必须的,但是,从将文学价值观作为考察一个时代或一个作家、批评家、理论家等文学观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机械地套用僵硬的定义。其实,通俗地理解,文学价值观就是对文学有没有价值、文学有怎样的价值、文学为什么有价值、什么样的文学有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文学价值观的研究,相对于过去文论界过于重视文学本质论来说,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文学研究在观念、思维、范式等方面的革新。从价值观的角度阐释文学,既与从属性论、特征论角度阐释文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又与后二者有一定的区别。以文学价值观为抓手研究文学观,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属性论的抽象性和特征论的局部性并将二者协调起来,使文学观的研究与建构在高屋建瓴与具体有形、严谨周密与开放活跃之间达成平衡。
纵观王国维所说的“境界”,作为其诗学审美理想和最高标准,恰好蕴含着对文学有无价值、有何价值、为何有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和回答,所以从文学价值观的角度对“境界”所蕴含的内容和意义展开研究,既符合王国维学说的本意,又能够对他那看似零散的片段言说进行整合以见其内在逻辑。
二、“境界”与文学价值的三维
关于“境界说”,学界有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它代表王国维学术兴趣由哲学转向文学后的观点,与热衷哲学研究的前期观点划然有别。本文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如果说从中西互识互鉴、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角度看,以“境界说”为代表的文学观,从内容到表达,确实比以《〈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前期文学观更成熟、更有个人风格和中国特色。但是,如果从对文学超功利的神圣、独立价值的强调和呼吁看,王国维的主张始终如一。也就是说,王国维前后期对文学价值的揭示和张扬是可以互释、通释的。鉴于学界对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论基本采取从前期言论简单概括为超功利说,进而作为常识来传播的状况,这里尝试打通前后期界限对其做较细致的分析,以使其丰富内容和逻辑层次较清晰地浮出历史地表。
文学有什么价值?中国自古代至近代,基本上是在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框架内回答这个问题,像曹丕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0]61的层面上论文,刘勰在“原道”“征圣”“宗经”的轨道上说“文之为德也,大矣”[11]2。即便有老庄—钟嵘—司空图—严羽—王士祯—袁枚一脉,言无用之用、言感荡心灵、言韵外之致、言兴趣、言神韵、言性灵,但或点到为止或玄妙神秘,不成规模、少见逻辑。至王国维,对文学“无用之用”价值的揭示和论说,达到了切实、充分、透彻、逻辑较谨严的程度,即使放在今天看,其观点和文字仍散发着相当诱人的魅力。
(一)“所见者真,所知者深”[2]36:文学以真启人的价值
王国维认为,从世俗功利的角度看,文学无用;从超世俗利害关系的角度看,文学有大用。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超越实用功利,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探究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引导人们思考、醒悟自己人之为人的生存境况。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之所以将李煜、冯延巳、苏轼、欧阳修、秦观、辛弃疾等人的词树为有“境界”的典范,就是看重它们具有这样的蕴涵;同理,之所以将温庭筠、吴文英、姜夔等人的词视为无“境界”的典型,也是嫌它们缺少这样的蕴涵。王国维认为,“大家之作”之所以有“境界”,之所以“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2]36,是因为“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是从能够深刻洞见、揭示人生和宇宙真相的角度为“境界”赋予内涵。类似的论说还有“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2]10“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2]11“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2]12“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2]21等,这些以“大”“深”“远”为主旨的论说,指的是优秀作品所生成的“境界”,虽由具体景、情、事来表现,却能够超越一物一景一人一事一情,具有更深刻、更广远的概括意义,能够引起更多人产生共鸣,感悟宇宙人生真相,从而将人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生存蒙昧中提拉出来。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营造的“境界”多次被王国维标举,并说其与“最得风人深致”的《蒹葭》“意颇近之”,与《节南山》中的“诗人之忧生”之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似之”;冯延巳“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所营造的“境界”则被认为与陶渊明《饮酒》第20首中的“忧世”之叹“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亦“似之”[2]16-17。这些被誉为“忧生”“忧世”的作品,揭示了茫茫宇宙中渺小的生命个体无路可走、无处可去、无家可归的迷茫感、孤寂感、失落感,触及的正是“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这个关乎生命存在的终极之问、千古之问,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典型表现。
在超越实用功利、探寻存在真相的意义上论述文学独立而神圣的价值,可以说是王国维一生始终未变的情结。1904 年,王国维就说过:“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则哲学家与美术家之事业,虽千载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发明之真理与其所表之之记号之尚存,则人类之知识感情由此而得其满足慰藉者,曾无以异于昔;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12]120从超越世俗利益、超越时空局限等角度强调文学不同于实业、政治等的独立、神圣价值,铿锵有力。1906 年又说:“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12]51而且,王国维虽指出文学与哲学的区别是一直观的、顿悟的,一思考的、合理的,但实际上在论述价值时,他对文学的理解是综合的,即文学是直观而思考、顿悟而合理的。他说:“今天吾国文学上之最可宝贵者,孰过于周、秦以前之古典乎?《系辞》上、下传实与《孟子》《戴记》等为儒家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纯粹之哲学也。今不解其思想,而但玩其文辞,则其文学上之价值已失其大半。此外周、秦诸子,亦何莫不然……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今舍其哲学,而徒研究其文学,欲其完全解释,安可得也!”[12]53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文学最初是一体的,至二者分离归属不同领域后,哲学中也许难觅文学踪影,而优秀的文学中仍有哲学之魂,文学其实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哲学,寻味、体验、以生动独特的方式表现人的生存境遇、生命状态,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分。
正是因为重视文学超功利的探索宇宙人生真义的精神价值,王国维才一再表示反感那些混淆视听的伪文学。《文学小言》中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绝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1]24又说:“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的文学同。”[1]25所谓“的文学”,就是以吃喝等实用利益为目的的文学,“文绣的文学”,就是以博取名声为目的的文学。王国维所批判的是一切作为功名利禄手段、工具的文学和文学观,因为这样的文学及文学观与真正的人生意义的探索、寻味,相距天壤。同样是因为重视文学超功利的探索宇宙人生真义的精神价值,王国维还说过这样的话:“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2]60客观地说,感事、怀古的作品,也并不都拘泥一人一事,从具体人事写起而达至揭橥宇宙人生普遍意蕴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甚至有些祝寿作品也蕴含着一些难得的人生境遇、人生意义的发现。王国维不仅掌握这个道理和事实,而且自己也不乏感事、怀古之作。这里,他宁可给人留下“矫枉过正”和“片面”的话柄,将“感事”“怀古”“寿词”之作一律看低,就是要以极端的形式强调文学超功利的,独立、神圣的,探索宇宙人生一般意义的价值。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13]134-135,并且用宁可赴死也不以停止真理探索为条件求取苟活的人生选择,向世人示范了思考、求索、揭示宇宙人生真相的神圣。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也以一死和诸多激扬文字向后世证明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悔和“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意义。关于王国维自杀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说法,窃以为,以死亡昭示对某种真相、真理的坚持,也许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种。这样理解他的死亡,与理解他在“省察人生”的意义上定位“境界”、阐释文学,似可形成一种互文性。文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穿越表象和假象,洞悉真相,深刻地认识人、认识世界,不是教人顾影自怜、怨天尤人,而是探寻人之为人的状态和意义,让人认识到不做他人的盲从者,不做命运的低眉者,不做功名、利禄和欲望奴役者的重要性。
(二)“优美”与“宏壮”:文学以美悦人、以情动人的价值
从人类终极关怀的高度理解文学价值,除了感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王国维还看重文学的审美价值、情感力量。他认为,文学的价值还在于能使人超越被功名、利禄、欲望等束缚的不自由状态,收获丰富的精神世界、良好的情感状态、超俗的人生趣味,也就是说,文学所具有的感染人、温暖人的价值犹如一束光,能够引领人的精神由匍匐爬行到展翅飞翔。
早在1903 年,王国维就强调审美活动对人的重要意义:“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12]46这里所说的“美”是广义的,指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自然美与艺术美。到1907 年,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更加突出艺术的价值,认为“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12]137。即艺术美比自然美更容易把人从各种利害关系笼罩中抽离出来,使之进入高尚纯洁之域,体验纯粹之快乐。他生动地形容艺术使人达至的审美自由状态:“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着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12]137由昏暗到光明,由漂泊到安宁,由迷茫到欣喜,由束缚到自由,艺术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可以说被王国维形容到了无以复加的美好程度。这里谈审美价值字面上虽然不是单指文学,实际上则主要指文学,因为整篇文章是指向《红楼梦》的。至《人间词话》,对审美价值的张扬就独指文学了,像对“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宝帘闲挂小银钩”“绿杨楼外出秋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等词句所营造的“境界”的标举,突出的就是它们带给人的和谐、静谧又充满盎然生趣的纯粹审美快乐。
然而,文学中不只有宁静的优美,因为生活中其实很少风平浪静。王国维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说:“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2]44这里所说的“难工”“易巧”,与其说关乎表达技巧,不如说关乎文学的言情属性和感人价值。王国维之所以对温庭筠、韦庄、姜夔等词评价不高,就是因为它们只在“精艳绝人”“富力精工”,甚至“格韵高绝”上下功夫,缺乏真情、实感、深意,不能发挥感动人、引领人的作用。“画屏金鹧鸪”“弦上黄莺语”之所以没有“境界”,除了不自然、不生动,主要原因在于不感人,可谓语不关情,象不带意;冯延巳的“和泪试严妆”之所以有“境界”,恰恰主要因为其言情既丰满,又自然、巧妙:一个受相思之苦折磨的深情人,强忍悲伤装扮自己,时刻盼君归的日常,活脱脱地推至读者面前,其孤寂痛苦、其思念哀伤、其忍痛律己、其热情不灭……种种情感以鲜活淋漓之态扑面而来,谁能不为之动容?同理,之所以认为“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2]24,而“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2]25,也是因为苏轼的咏杨花词体物入微、情真意切,“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很好地体现了“一切景语皆情语”[2]45这一诗学真谛。生命独自飘零,无人怜惜、无处依托,随时化作尘土、随时卷入流水,何等孤寂、何等哀愁、何等憾恨、何等无奈!作者就是杨花,杨花就是作者,人人都是杨花,人人都是作者,情感的潮水在杨花—作者—读者之间奔涌回环。而姜夔咏梅花的两首作品,除了堆叠的词语、繁复却关联松散的意象外,寻不到感人情愫。尽管学界为姜夔词叫好的声音也时有出现,但从文学情感本性和价值的角度看,王国维因“白石有格而无情”[2]29对其做出的无“境界”评价,是站得住脚的。可以说,《人间词话》中被高度评价为有“境界”的作家作品,主要皆因真切、自然、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动人的情感。
从以美悦人、以情动人两个角度理解文学的审美价值,与王国维将“境界”划分为“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相一致,也与其将美划分为“优美”和“宏壮”(另称“壮美”)相一致。也就是说,“无我之境”以“优美”之形态让读者产生和谐、宁静、温馨、舒展的审美体验;“有我之境”则以“壮美”之形态让读者经历与作品情感同频共振到观照作品情感、反观自我情感的审美体验。比喻来说,优美感似波澜不惊的湖面,而壮美感如由汹涌澎湃的海上逐渐来到波澜不惊的湖面。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2]4-5,不仅适合分析作者的创作状态,也适合分析读者的审美体验。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理解“境界”,可以让我们澄清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在王国维那里,“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没有高低之别,二者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在使人获得审美体验,将人从名缰利锁、生活之欲中解放出来,暂时体会纯粹的思悟之乐、纯粹的感怀之乐,久之则使人在精神健全、情感饱满、趣味超俗这一点上,二者无异。只是文学因其对人生高悬理想之烛、饱含悲悯之情,往往更敏感于愁苦,而致“宏壮”的“有我之境”更多,“优美”的“无我之境”较少而已。
(三)“万不可作儇薄语”[2]63:文学以善导人的价值
这里所说的文学“善”的价值,不仅指狭义的在道德层面引导人向善的伦理价值,也包括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因为高调张扬文学超实用功利的独立、神圣价值,王国维往往被误解为轻视甚至否认文学社会性的向善价值。其实,王国维并不否认文学在富国强民、国泰民安,以及厚人论、美教化等方面发挥善的作用。只是他不认可庸俗社会学,认为文学不必直接“载道”,不是直接作用于政治、经济、道德,主张文学通过以真醒人、以美悦人、以情动人的方式健全人的精神世界,撑起人的精神高度,进而改变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世界。他的文学观与西方那些绝对不关世事的“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等是不同的;与明中叶至清中叶以徐渭、汤显祖、李渔、袁枚等为代表的,以自然人性论为哲学基础,以放纵情欲、宣泄本能等为内容,以俗、艳、险、怪、谑、骇为审美趣味的文学观也是泾渭分明的。早在1903 年,王国维就说:“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12]46-47这足以表明,他是重视包括文学在内或说以文学为主的美育,与德育和智育的紧密关系的。王国维的“境界说”其实就是以真为核心的真善美内在统一的文学价值论。它向人们昭示:文学正是因其在超越功名、利禄、欲望的层面上求真、动情,才能在预防人类精神荒芜、疗愈国民情感疾病方面发挥作用,进而收获兴邦兴国的“善”。这其实与同时期梁启超因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而倡扬发挥其作用,以便通过“新小说”达到“新人心”“新人格”即“新民”的目的,进而完成“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14]3等大任,是大同小异的。
王国维张扬文学独立、神圣的价值,确实有康德、叔本华等西方思想,以及老庄一脉中国传统文学观影响的原因,但是,为中国近代社会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寻找出路,才是其根本原因。对于当时国家不重视精神培养,只是急功近利地从西方输入物质文明以期救国的举措,他颇有不满,指出:“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指不重视),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12]49其心急如焚、语重心长,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动。针对“今之人士之大半,殆舍官以外无他好焉”[12]68的社会状况,他直言:“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12]48以看似偏激的言辞,指出艰难时世里从政治家到教育家到国民轻视文艺、轻视精神培养的急功近利观念与做法的危害。其实,王国维并不是绝对否定物质和政治,而是说在重视物质的同时也应重视精神,在重视政治的同时也应重视文学,因为文学的作用更广远,精神的培养更需久久为功。面对晚清、民国乱世中挣扎的,空虚麻木、萎靡不振的一些国民,尤其是以吸毒麻痹自己的可怜人,王国维写道:“今试问中国之国民,曷为而独为鸦片的国民乎?夫中国之衰弱极矣,然就国民之资格言之,固无以劣于他国民。谓知识之缺乏欤?则受新教育而罹此癖者,吾见亦夥矣。谓道德之腐败欤?则有此癖者不尽恶人,而他国民之道德,亦未必大胜于我国也,要之,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于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于感情上而已。”[12]123而“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不可……使有解文学之能力,爱文学之嗜好,则其所以慰空虚之苦痛而防卑劣之嗜好者,其益固已多矣”[12]125。这些结合时代语境、社会状况思考文艺价值的铿锵论说还有很多,王国维就是希望并且坚信,只要全社会都不急功近利,都重视美育、重视精神,真正的文学就能发挥改变中国人精神状态,进而改变生存状态、改变国家面貌和社会面貌的作用。应该说,这种对文学价值和功能的论说,确实有过于理想的成分,但是观其主旨并不虚妄,因为他懂得这种改变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
正是因为不轻视文学向“善”的社会价值,王国维才反对将文学拘囿在象牙塔里搞“阳春白雪”。《人间词话》中,有多则涉及姜夔词的评语,中心意思是格调虽高,却无“境界”,而主要原因在于“隔”和“无情”。与谁“隔”?对什么”无情”?具体地说,是谈创作主体与写作对象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考察创作主体作为人与人间万事万物有无血肉关联。真正的文学是作家在生活中摸爬滚打感慨万千之后再与生活拉开距离进行审美观照的结果,所谓“痛定思痛”。这样的文学,既是有热气的,又是有高度的;既是亲切的,又是有启发的。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2]37一个与写作对象、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没有血肉联系的作家,与一个深陷在生活的泥淖中不能观照生活、思考生活的作家,都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姜夔的词,在王国维看来,于“入”与“出”二事“皆未梦见”[2]38,所以他说:“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2]64指出姜夔词的“高”,并不是具有真正明朗、宽广、高洁的品格和“境界”,因为它与真切的生活感知、真实的情感状态和深切的人类命运关怀缺少联系,而是徒具用辞藻堆叠出的格调,这种“高”即便是再清再雅的“阳春白雪”,终因不来自社会人生,亦不将人引向社会人生,而意义有限。同理,王国维反对将文学收编于私人场所用做迎来送往的工具,反对将文学囤聚于宫闱闺房之内在镜面画屏之间搞无病呻吟、炫技玩巧,反对将文学作为酒足饭饱后游戏人生的戏谑物,也都是因为不轻视文学向善的社会价值。他最看重作家的赤诚、真挚、忠实,最讨厌作家以轻佻、不严肃、不尊重、无所谓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写作,认为:“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2]64他甚至从是否“游词”的角度,为一些所谓“艳词”“淫词”“鄙词”进行正名,认为只要从真情实感出发,“读之者但觉其亲切感人”或“但觉其精力弥满”[2]38,不给人轻浮、油滑、拿人生做儿戏之感,就不是“游词”,就无害;只要它们不是通过玩文学而将人引向玩人生,反倒是以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直言,引导人认真地对待社会人生,就不仅无害,而且有益。所以,他才说“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要之,王国维不可能轻视文学社会性的向“善”价值,因为他坚信:“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12]156尽管从学理上讲,这种将作品品格等同于作家人格的观点存在不全面、不科学的问题,但是,它恰恰证明了王国维对文学与道德关系的重视,对文学应具有促进道德提升和社会良性发展等价值的重视。
三、结语
丹麦文论家勃兰兑斯说过:“批评是人类心灵路程上的指路牌,批评沿路种植了树篱,点燃了火把,批评披荆斩棘,开辟新路。”[15]350确实,与文学理论的厚重、严谨、科学、系统等相比,文学批评的明快、鲜活、有力往往更具方向性和启发性,这可能源自批评既与文学现实、社会现实保持生动的联系,又与批评主体的文学价值观密切相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与其说是理论著作,毋宁说是批评著作,王国维之所以能对诸多作家作品做出态度明确的价值判断,就是因其心中有成熟的文学价值观。王国维的文学价值观可以概况为“一核三维”:“一核”,即一个核心观点,王国维认为文学本身具有关怀人类生存根本问题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不依赖其他事物的独立的、重要的、神圣的,是其他事物无法取代的;“三维”,即王国维主要从引人洞见宇宙人生真相、形塑人的情感和精神、导人进入社会性生存三个维度论述了文学的价值。王国维的“境界说”蕴涵丰富,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本文从文学价值观角度所作的阐释只是进入“境界说”研究的一种尝试,期待这种阐释对“境界说”研究、王国维研究,以及新时代的文学价值观研究等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