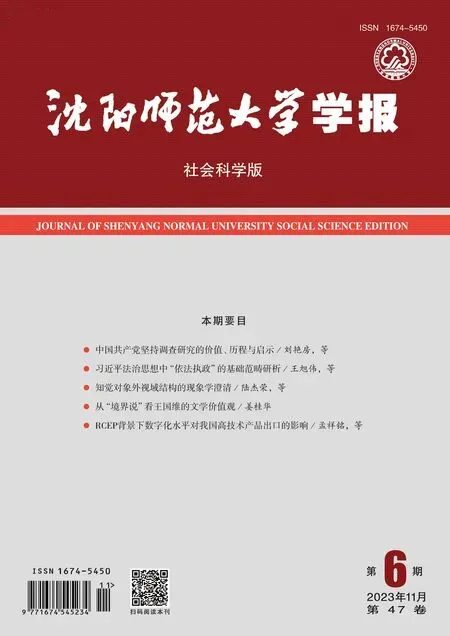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分析
——以《檀香刑》日译本为例
2023-02-25鲁畅,杨洋
鲁 畅,杨 洋
(沈阳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檀香刑》是莫言潜心完成的一部长篇力作,获得了中国首届“21 世纪鼎钧文学奖”,并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檀香刑》日译本于2003 年首次在日本出版发行,之后两次再版发行。《檀香刑》日译本之所以能长时间生存于日本文学市场,成为日本读者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窗口,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译者吉田富夫在翻译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分析已经成功译向日本的《檀香刑》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阐明高质量译本的产生过程,对于推动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翻译适应选择论内涵
翻译适应选择论这一理论概念于2001 年首次由胡庚申提出,随后又著书《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出版发行。此书的问世,标志着该理论被正式确立。胡庚申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与思想,将其作为构建该理论的哲学依据,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综观研究,探讨了“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相关机理、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方法做出了新的描述和解释。该理论将翻译本质解释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指出翻译活动由适应与选择两个阶段构成,并且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力求实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该理论具有跨学科性,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
(一)翻译生态环境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来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才有可能取得译作的成功。具体而言,翻译生态环境是指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包括翻译的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在内的相互关联的、互动的整体[1]40。总之,翻译生态环境是译者和译文生存的总体环境,既是制约译者进行适应与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体,也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
(二)适应与选择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译者的适应阶段和译者的选择阶段。译者的适应阶段是指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译者的选择阶段是指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的“选择”+ 对译本最终行文的“选择”。翻译过程中的两大步骤——“适应”与“选择”,又都是以“译者为中心”主导的[1]180。也就是说,“适应”和“选择”这两大步骤都是以“译者”为中心而完成的。翻译适应论的翻译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作出适应性选择转换[2]。
具体而言,在适应阶段译者应充分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在内互联互动的翻译生态环境。例如,如果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原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译者必须适应该文学作品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这也要求译者在文学翻译方面有一定的经验和造诣,否则译者将极有可能被以文学作品为要素的翻译生态环境淘汰,如出现读者不愿意读、出版社不出版、审稿者不通过等情况。在选择阶段,译者的选择是在不同维度上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三个维度是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同时,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视角来看,译者不论是采用异化还是归化,直译或是意译,译文不论是使用正式表达还是委婉表达,均可以看作是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所作出的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1]125。
(三)三维转换
翻译不是一项简单的“语言对号入座”的工作,而是一种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胡庚申在翻译适应选择论中将翻译方法表述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之下,译者相对地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133。
具体而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从语言形式、风格等不同的层次和方面进行选择转换。译者对原文风格和语言特点要有敏感的认识,译者应在不破坏原作文意的情况下,根据目标语社会的表达习惯,将原作的语言信息转换成恰当的译文表达。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要求译者要有跨文化意识,要注意克服由文化差异造成的阅读交际障碍,重点关注文化内涵的传递。此外,译者还要将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维上,即需要译者重点关注原作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维度往往是相互交织、整合的关系,强调对某一维度或要素的描述,并不意味其他维度或要素在翻译过程中不起作用。
二、《檀香刑》日译本中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一)译者的适应
译者为了自身的职业发展与译本的长久存续,就必须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其中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从内部翻译生态环境来说,译者要适应个人能力及个人需要;从外部翻译生态环境来说,译者要适应目标语社会、目标语读者、原文本等。
1.译者对个人能力的适应
胡庚申指出,译者只有选择了与自己的能力相适应或相接近的作品去翻译才会容易取得成功[1]105。吉田富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著名的日本籍学者和专家,师从中国文学研究者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两位名家,1958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3 年取得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十分热爱中国文学与中华文化。他从1997 年至今26 年间持续向日本读者译介莫言的文学作品,也是唯一应邀出席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的日本籍译者,是莫言及其文学作品在日本最重要的传播者之一。吉田富夫具备较高的中日双语、双文化能力及丰富的莫言作品翻译经验,这使得他能够准确理解莫言《檀香刑》作品中的感情和主旨,胜任《檀香刑》的日译工作。从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来看,充分体现了译者个人能力对内部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2.译者对个人需要的适应
吉田富夫曾自述他非常喜欢读莫言的早期作品《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等。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吉田富夫凭借着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喜爱,开始执笔翻译一些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吉田富夫在访谈中曾说过他和莫言有许多类似的经历,两人都生长于农村,当阅读莫言的故事时总能想起自己的广岛县老家,莫言书中的母亲形象也让他忆起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等[3]。吉田富夫之所以选择莫言的《檀香刑》进行翻译,一是因为他本人具备较高水平的中日双语、双文化能力,以及文学素养、文学作品的翻译经验等译者必备的素质;二是因为他对莫言及其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三是吉田富夫自身职业发展的需要,体现了译者对内部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3.译者对日本读者和社会需要的适应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译作总量在日本开始呈急速增长趋势,中国文学再次迎来日本社会与读者的关注高峰,被日本读者接受并引起共鸣。此时,日本读者乃至日本社会都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并试图透过中国文学作品窥探中国社会现状,了解真实的中国民间社会。吉田富夫选择翻译莫言的乡土文学作品《檀香刑》,就是为了满足日本读者、日本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需求,即译者对外部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4.译者对《檀香刑》原作的适应
莫言笔下的《檀香刑》饱满生动,写活了高密东北乡民间百姓的人物形象,讲述了中国被列强侵占的那段时期百姓们的反抗和主人公之间的爱恨情仇。由于中日两国在语言、文化、社会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吉田富夫考虑日本读者对译文阅读理解和接受的程度,开始尝试在两种语言的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如莫言在创作《檀香刑》时,将山东省地方传统戏剧“茂腔”移植到作品中并改名为“猫腔”,充满韵律感和文学色彩。另外,作品中使用大量的地域方言,十分贴近中国北方的现实生活。对此,译者为了让日本读者能够理解这部具有浓郁中国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并获得与中国读者同样的阅读感受,在翻译时将原作中的“猫腔”转换成日本人熟悉的“五七调”,并在翻译方言时加入日本广岛地区的方言,这种翻译方法使得日本读者能够顺畅阅读并理解原作的文化。正是基于吉田富夫对翻译生态环境的多维度适应,才造就了其如今成功的译者身份。
(二)译者的选择
为翻译出优质的译作,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译者的选择作出要求,即需要译者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基础上,做到“三维转换”,即侧重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上进行选择转换,从而实现语言信息的通达、文化内涵的传递、交际意图的体现。
1.译者语言维的选择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在语言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1]176。中日两国隔海相望,历来交往密切,但两国都有独立的语言系统。因此,译者要适应中日两国语言的差异,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才能将原著作的语言信息有效地传递给目标语读者,从而使译文具有可读性。
例1:“猴子,真他娘的有两下子!”[4]396
译文:「猿よ。まったくたいした腕じゃ!」[5]205
这里的“有两下子”,是原作中一名叫朱八的人说的话。这句话是朱八对乞丐侯小七的称赞。朱八一行人乘着夜色,想救出死牢里的孙丙,便派侯小七先行去打探情报和地形,小七不负众望带回了有效的信息,所以朱八用“有两下子”来表扬他。“有两下子”用于非正式场合,在中国方言中用来形容某个人有点本领。译者在理解该方言内涵的基础上,选择将其意译成“まったくたいした腕じゃ”。日语中“まったく”是副词,意为“本当に,実に”修饰后面的内容。“たいした腕”表示赞赏某人有了不起的本领或者能力。可以说,译者选择的语言准确译出了原文“有两下子”的方言内涵,在日文的生态环境下生动地描写出侯小七的聪明伶俐,有效地实现了原作语言信息的选择转换。
例2:“与其让一些二把刀三脚猫杀他,还不如让俺杀他。”[4]60
译文:「生半可な二流のやからに殺されるより、わしに殺されるほうがましというもの。 」[6]98
原文中的“二把刀三脚猫”这一带有数字词语的表达具有暧昧的语言效果。这里的“二把刀”并非意味着某个人真的拿着两把刀,“三脚猫”也不是指长了三只脚的猫。实际上,该例句中“二把刀三脚猫”的数字表达是指对知识掌握不足、技艺不精的人,比喻对各种技艺仅仅略知皮毛的人。在翻译这类词语时,如果不了解其语言生态环境,就很难准确译出原作的精髓。译者选择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将其译成“生半可な二流のやから”。在日语中此句的含义恰好可以表达出对技艺一知半解的二流之辈之意。译者采用的意译策略使得该译文准确地向读者传达了原文“二把刀三脚猫”中所蕴含的语言信息。由此,译者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例3:“有几个花花绿绿的人,在众人前面那个用砖头堆垒起来的台子上……”[4]329
译文:「派手な原色の衣裳の人間が数人、みんなの前の煉瓦を積み上げた台の上で…」[5]96
“花花绿绿”是莫言在原作中采用AABB式叠词的形式,描述了马桑镇里几位唱猫腔的男人的着装打扮。在日语中,很难找到与“花花绿绿”相对应的语言表达,同时原文中的“花花绿绿”实际上是指这些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有各种颜色,扮相风格也十分奇特。在理解该叠词的语言内涵后,译者选择将“花花绿绿”意译成“派手な原色の衣裳”。日语中的“派手”一词具有穿着打扮、样式、色调等花哨鲜艳之意,译者选择此译词,准确地向日本读者传达了原文的语言含义,最终实现了语言维的选择转换。
2.译者文化维的选择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在传递原作文化内涵时所做的选择。翻译活动不仅涉及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涉及不同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的传播。因此,翻译选择适应论要求译者积极向读者传达原作的文化内涵,需要译者从文化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例4:“钱大老爷派人送来了贺礼:一对银脖锁,每个一两重。”[4]185
原文中“银脖锁”是钱丁送给孙丙夫妇孩子的一份礼物。明清时期,中国人常在儿童的脖子上挂上这样的银制饰品。自古以来中国人认为只要给孩子们戴上它,就能避灾祛病,“锁”住生命,也称之为“长命锁”,所以很多孩子一出生就戴上这个饰品直到成年。然而,在日本没有“银脖锁”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如何翻译日本社会没有的物品,译者选择了异化直译附加注音、注释的翻译方法,直译并注,附加“病魔の侵入を防ぐとされる幼児の首飾り”的注释。译者通过注释向日本读者说明了“银脖锁”的具体用途,让日本读者能够感受到中国人对新生儿的关爱和期盼,从而实现了文化内涵的传递,保持了原作与译作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
例5:“前边就是娘娘庙,急来抱佛脚,有病乱投医……”[4]14
“娘娘庙”是孙眉娘为关在死牢的父亲祈求平安所去的地方。译者了解中国和日本不同的历史文化,因此在翻译时采用了异化直译附加注音注释的方法,直译并注音再附加“子授けの女神を祀ったやしろ”的解释。译者通过注释向日本读者解释了“娘娘庙”的主要作用即“子授け”,并让读者感受到孙眉娘对父亲的担心和慌张的状态。这种译法准确传达了“娘娘庙”这一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因而也实现了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选择转换。
例6:“皇太后说了,‘行行出状元’,咱家是状元,儿子也得成状元。”[4]359
“状元”是在中国科举制度、科举文化下的社会产物。中国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废除。在科举考试中,当考生通过县级考试、省会组织的考试、国家首都组织的考试、最后通过皇帝面试时会被称为“进士”。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第一名才能被称为“状元”。能考取状元实属不易,可谓是各方面均十分出众的人才。原作皇太后话语中“状元”一词是对赵甲在刑场上行刑技艺的赞许,认为他的行刑技艺可以称其为该领域的状元。理解中国科举文化,了解状元的社会地位,译者采用直译附加注音后注释“科举试验の一位合格者=第一人者”的翻译策略,既体现了赵甲技艺之高,又向日本读者直观地传达了“状元”这一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从而实现了译者对原作文化内涵的选择转换。
3.译者交际维的选择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是指译者把重点放在交际意图的传递上,没有交际功能的信息没有任何价值[7]。因此,除了语言信息的传递和文化内涵的传递,翻译适应选择论要求译者还必须关注原著的交际意图能否在译文中得到体现。为向读者传达原作的交际意图,需要译者从交际维度方面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1)区分人物独白
原著《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组成,这三部分均使用了不同的叙事方式。其中猪肚部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以超脱故事人物身份的角度,客观、直白地向读者讲述了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故事,但在该部分中仍夹杂着第一人称视角的人物内心独白。莫言在原作中并没有使用特殊的符号或者注释将一人称人物自述的内心独白和三人称客观讲述的内容加以区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自然可以快速进行区分,但是,对于日本读者来说,准确地在客观叙述中辨别出人物自述的内心独白可谓是困难重重,这种情况下原作的交际意图就不能够充分地被日本读者接收,继而很有可能导致交际意图传递的失败。
例7:“她的心中顿时一阵冰凉,情绪低落到极点。不算,刚才祝祷时俺的心不诚,这次不算数。”[4]152
译文:「心がたちまち冷え、 気分はどん底に沈んだ。(なしだ。さっきお祈りしたとき、うちは本気じゃなかったから、今のはなしだ)」[6]240
例8:“眉娘知道自己败了,彻底地败了。自己生了一张娘娘的脸,但长了一双丫鬟的脚。”[4]157
译文:「自分が負けた、とことん負けたことを眉娘は知った。 (うちは皇后さまの顔を持ちながら、腰元の足をしているのだ)」[6]246
从上述例句可见,译者掌握了原作的叙事方法,在译文中采用增加“()”符号的方法,对人物独白和内心活动做出了明显标注。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人物独白和心理活动内容,译者在日译本中只使用了“()”符号进行区分,并通过“()”符号,使读者可以轻易区分出原作在“猪肚部”章节中出现的与第三人称叙述内容不同的第一人称人物的独白和内心活动。可以说,这样的翻译处理让读者能够直观感受到人物独白,减少了阅读障碍,从而顺利实现了原著交际意图的传递。
(2)再现故事舞台
《檀香刑》讲述的是一部爱恨情仇与人情冷暖交织的故事。山东省高密县的县衙门便是这部民间故事上演的重要舞台。在《檀香刑》译本后记中,译者指出:“また、小説の重要な舞台の一つが県の役所たる県衙門ですが。”[5]408此外,《檀香刑》原作中在各章节均频频出现高密县衙门内的场所,如“西花厅”“东花厅”“三堂”等。特别是第15 章第3 节,朱八、孙眉娘一行人在黑夜解救死牢里的孙丙时,更是提及了衙门内的诸多场所,并向读者展示了这一行人在县衙门内的一条动态的营救线路。莫言在描写主人公们营救孙丙情景时的语言节奏十分紧凑,似乎有一种力量将读者带到这场营救行动中,给人一种亲临现场般的阅读体验。莫言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檀香刑》呈现出了这种戏剧性叙事效果。
例9:“她进了大门,沿着笔直的甬道,穿过了那个曾经斗过须的跨院,越过仪门,进入六房办公的院落,然后从大堂东侧的回廊绕了过去。”[4]173
译文:「表門を入った眉娘は、 真っ直ぐな通路を歩いてついこの間髯くらベのあった中庭を拔けると、を過ぎてが執務している一画に入り、ついで回廊を通って大堂の東側を拔けた。 」[6]272
例10:“俺们弯着腰出了死牢,趁着外边的乱乎劲儿,跑到了狱神庙后边的夹道上。迎面一群衙役提着水从仪门内跑出来。”[4]404
译文:「腰をかがめて牢を出た一行は、外の騒ぎに紛れて駆け、獄神廟の通路まりつきました。水を提げた下役人たちが、の中からこっちへ向けて飛び出して来ます。 」[5]218
以上描写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日本读者来说,他们对文中的县衙门是陌生的,虽有译文和注释指引,但依旧很难联想出县衙内建筑的样子、布局与主人公们走的是县衙内的哪条路。日本读者仅凭干枯的译文文字并不能产生同中国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难免会在阅读过程中出现交际障碍甚至交际失败。基于此,译者选择在译本的上、下册中分别插入《檀香刑》原作中不存在的县衙门地图。如此一来,读者可以对照译本里的县衙门地图进行阅读,亲身感受原作里的情景。同时,通过译者在地图上所作的注释,读者可以了解县衙门内的建筑及其具体功能,可以说,译者选择“文字(译文)+ 地图(视觉)”这一翻译策略,从交际维度方面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成功地将原作的交际意图反映到日本读者的脑海中,实现了交际维度上的翻译选择。
(3)简化或具体化原作内容
译者为实现交际维的选择转换,除了在译本中加入“()”符号及县衙门的地图外,还对原作的语言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文字处理,即将原作的复杂表述简化,将其中隐藏的语言信息和交际意图具体化,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作的交际意图。
例11:“他一躬到底,二躬到底,三躬也到底……”[4]32
译文:「深々と三度お辞儀をくり返し…」[6]54
这里原文描写的是送赵甲回家的车夫的动作。当赵甲给车夫一张价值很高的银票时,精疲力竭的车夫突然打起精神,极其夸张地向赵甲鞠了三个躬,这既是车夫对赵甲的感谢,也是故意向赵甲献媚。例11 中的重要信息分别是“一、二、三次”和“鞠躬”。译者对原文这一动作描写在翻译时选择进行简化处理,抓住原文的主要意图,将其译成“深々と三度お辞儀をくり返し”。简化后的译文又很好地反映出车夫的感激之情和夸张的鞠躬动作,日本读者通过“深々と”和“三度”这样简洁的译文既获得了原文的重要信息,也快速地理解了原作的交际意图。译者将原文的复杂表述进行译文简化,选择符合日本读者习惯的表达,有效地完成了交际维度的翻译选择。
例12:“谢夫人救命之恩,如果有来世,就让俺给夫人当牛做马吧!”[4]408
译文:「奥方さまに命をお助けいただいたご恩は、来世で牛馬となってお返し申します! 」[5]224
原作为一个对话场面描写,是孙眉娘对钱丁妻子说的话。孙眉娘在救父时被士兵发现无处可逃,钱丁妻子不计前嫌救了孙眉娘。在中国的话语中“当牛做马”是一种隐喻表达,意思是像牛、马一样被人驱使,甘愿听从别人的话。这里从字面上看,是孙眉娘把自己比作了牛和马,但其真正的交际意图是向钱夫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以及要报恩的诚意和决心。译者在理解原作交际意图的基础上,将这一表达译为“来世で牛馬となってお返し申します”在“牛馬となって”后加“お返し申します”,向读者传达了孙眉娘的交际意图。译者将原作隐藏的语言信息和交际意图进行具体化的翻译,实现了交际意图的传递。
三、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檀香刑》日译本之所以在日本能够取得成功,深得读者青睐,主要依赖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进行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适应了包括个人需要、能力在内的内部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包括日本社会与读者的需要、《檀香刑》原作在内的外部翻译生态环境。在语言维上,译者倾向使用意译的翻译方法来实现原作语言信息和内涵的传达;在文化维上,译者倾向于使用直译附加注音注释的翻译策略向日本读者传递中国文化内涵,并通过直译保留了汉字外形,一定程度上唤起了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助推了两国文化的深入交流;在交际维上,译者通过在译文中添加符号“()”标注人物自述的独白内容,通过插入县衙门地图来降低读者阅读理解的难度,避免日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疑惑。简化和具体化原作语言,使得译文表达更加简洁直观,交际意图更加具体明确。在倡导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当下,译者应该具备主动地多维度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翻译意识,并在翻译过程中使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努力实现三维转换。译者的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关键,译者要维护原语与译入语的生态平衡,从而翻译出高质量的译本,借此向海外树立中国文化大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