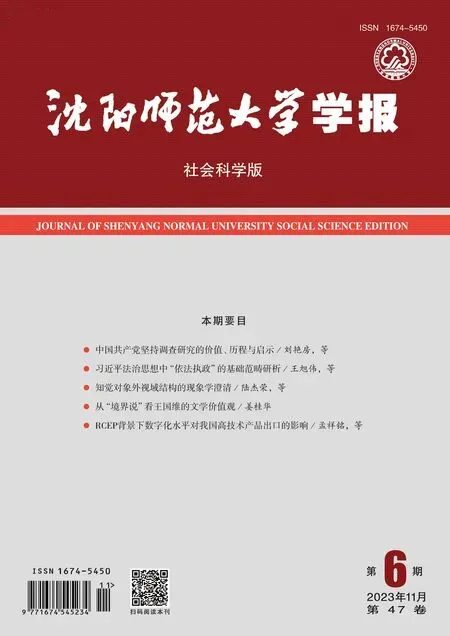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史诗理论视域下的《奥德赛》
2023-02-25李希梦
马 新,李希梦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其著作《诗学》从哲学高度提炼了希腊艺术精神,成为西方美学的开山杰作。《诗学》主要讨论悲剧和史诗两种文类。亚里士多德以浓重的笔墨探讨了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创作经验,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悲剧理论,奠定了美学史上悲剧观的基础。随后,亚里士多德将关注点转向了史诗。《诗学》以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为例证,对史诗特征展开分析,开创了史诗理论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奥德赛》史诗的摹仿
柏拉图认为,“摹仿远离真相……只触及摹仿对象的影像”[1]617,诗人都是虚无影像的摹仿者,他们无法把握真相,从而使诗歌远离现实和真理且对城邦公民具有强大的腐蚀性。因此,柏拉图将诗人逐出了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在柏拉图的摹仿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赋予艺术世界的摹仿以自主性与创造力,成为影响西方世界最为深远的文艺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系统地论述了摹仿在诗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拉近了诗歌与真理的距离,赋予诗人更多的主体性。他主动为诗人和诗歌辩护,认为诗歌是诗人创造性的劳动。他肯定了摹仿作为人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的意义,指出“诗人画出一个人的特殊面貌,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2]57,强调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美学指导。特别是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强调诗歌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作用,指出“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摹仿”[2]17。他认为,史诗、悲剧、戏剧等艺术形式的创作过程皆是摹仿,但它们的摹仿并非毫无差别。史诗是一种“用叙述体和‘韵文’来摹仿的艺术”[2]83,因而,在摹仿媒介、摹仿对象和摹仿方式上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在《诗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指出摹仿媒介的首要性,以“只用语言、不入乐的散文或不入乐的‘韵文’”[2]17来阐释语言作为诗的摹仿媒介的存在。在这里,韵文指向格律文,即单一诗格或混用诗格的体裁。按照艾布拉姆斯(Meyer Howard Abrams)给出的定义,史诗是“长篇叙事体诗歌,主题庄重、风格典雅,集中描写以自身行动决定整个部落、民族或人类命运的英雄或近似神明的人物”[3]97。因史诗摹仿的对象多是决定民族命运、半神半人的英雄,所以英雄格,即六音步扬抑抑格成了经典史诗常为采用的格律。荷马史诗均采用这种英雄格律进行摹仿。在《奥德赛》中,共有12 000 多行诗句,每行诗句有6 个音步,每个音步由3 个音节按“扬抑抑”的顺序排列,即“扬抑抑格”,而最后一个音步是2 个音节,为“扬抑格”。因英雄格是最庄重、最有分量的格律,故用作荷马史诗的摹仿媒介最为适用,一方面,它朗朗上口、易于吟诵;另一方面,它节奏感强,有利于史诗情节的穿插及场景的变幻,受到亚里士多德及荷马等游吟诗人的推崇。
在摹仿对象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史诗应与悲剧一样,摹仿“行动中的人”[2]20。这里的人指好人,也指坏人,因为他们具有鲜明的品格或性格。荷马所摹仿的人物比一般人好,《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萨卡的国王奥德修斯便是一位能力非凡的希腊英雄,他有勇有谋、重情重义,具有超越常人的高尚品格。同样是描述“行动中的人”,史诗与悲剧在摹仿人物的行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因其应一览而尽的长度限制只能摹仿演员在舞台上正在表演的事,而史诗因其叙述体的特点则可以摹仿多件正在发生的事,也就是摹仿对象的多个行动。荷马便摹仿了奥德修斯归家历程的多个行动,详略得当地将10 年的苦难历程浓缩为41 天的海上冒险。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也未按部就班地叙述10 年的特洛伊战争,而是从最后一天的“阿克琉斯之怒”展开,将摹仿对象的多个行动穿插点缀其中。由此,史诗在摹仿对象的行动方面更具优势,能够借助“容量”呈现人物的多面性格,体现恢宏的整体气势,引领读者接纳情节上的突转与穿插。
此外,史诗的摹仿方式多变。亚里士多德强调,史诗诗人在简短的序诗之后,应立即请其他具有“特殊性格”的人物出场,尽量减少使用诗人自己的身份,这样才能被称为合格的摹仿者。在《奥德赛》中,荷马主要运用第三人称缪斯女神的叙事视角将故事展开。他在开篇使用自己的身份以序诗的形式介绍了史诗的主题之后,便借女神之口将事件的缘由娓娓道来,将自己彻底置身事外。在第9 章法伊阿基亚人的宫殿里,荷马又借盲人歌者之口讲述了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中使用的木马计策及众英雄的悲壮事迹,并在盲歌者吟唱后切换视角,以奥德修斯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亲口将10 年的历险经历向众人诉说。可以说,多种摹仿方式的运用令诗人并非线性地记录、摹仿历史,而是依照可然律和必然律进行“创造”,将史诗故事呈现于读者面前,从而达到摹仿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美学效果。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通过梳理史诗理论阐述了摹仿说的实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摹仿是进行再创造和再表现的活动,文学作品的真正价值便存在于其被表现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赋予了诗人主体性,肯定了诗人的创造性和诗歌的教育意义,为文艺作品的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令读者获得了对现实更加深刻的洞悉。以《奥德赛》为代表的史诗借助英雄格律摹仿媒介,运用多种摹仿方式,对近似神明的英雄人物进行摹仿,完美契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史诗理论,展现了荷马之于《诗学》史诗研究的实践性价值,对后世史诗的发展和研究影响深远。
二、《奥德赛》史诗的情节特征
《奥德赛》史诗的情节特征主要体现在结构布局和情节成分两个方面。在谋篇布局中,亚里士多德重视情节各部分的比例,指出好的情节需要完整、精密的构思且具备内在的逻辑联系。在《诗学》里,亚里士多德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有机整体论”思想,认为史诗诗人不仅要编织戏剧化的情节,还要使史诗的情节成分紧密联系,从而缔造一种完整性的审美。在他看来,一部优秀的史诗应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且具备复杂的情节成分,例如突转、发现与苦难历程等,这些也是悲剧乃至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本质属性。
(一)结构布局:有机整体论
亚里士多德针对史诗的有机整体论明确指出,史诗应如悲剧的情节一样,“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环绕着一个整一的行动,有头、有身、有尾,这样它才能像一个完整的活东西,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赋予的快感”[2]83。史诗摹仿的行动应具有开端、发展和结局,三个部分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按照情节内部的逻辑关系严密组织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奥德赛》的情节虽然繁杂但却完整统一,兼具以上三个部分。情节的“头”能引起后面事件的自然发生,《奥德赛》开篇便是奥林匹斯众神会议宣布助力奥德修斯返回家园,从而引出了接下来一系列的情节事件。“身”则承前启后,串联起头和尾,使情节完整统一。奥德修斯漂泊海上,历经了一系列的苦难事件,但他在重重阻挠下仍不放弃,成功化解了一切艰难险阻。“尾”则按照必然律或自然地承接前事,终结所有情节。经历了10 年的海上流浪,奥德修斯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终于顺利归家。正如研究学者保罗·泰勒(Paul A.Taylor)所述,“主人公的行为导致的后果完全出乎意料,但从前因后果来看又是合理的”[4]。《奥德赛》以神谕始、以神谕终,头尾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合结构。
史诗的有机整体论还体现在情节的整一性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2]35。情节具有整一性是指所有的情节都须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中心事件处于核心地位且能表现主人公行动的整一性。荷马在创作史诗《奥德赛》时,并没有事无巨细地将奥德修斯所有的遇险经历平铺直叙,而是详略得当地环绕着一个整一性的行动来精雕细琢,从头至尾对“奥德修斯归家”这一主线行动进行摹仿,将无关事件进行选择性删除,从而使关键情节得以展开。众神会议后,奥德修斯返归之旅缓缓拉开序幕,接下来的情节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奥德修斯之子特勒马科斯在女神雅典娜的召唤下出海探寻父亲的踪迹;二是女神卡鲁普索遵照神谕释放了被其囚禁7 年的奥德修斯,而奥德修斯在归家之路上不幸遭到海神波塞冬的报复,遭遇风暴流落到法伊阿基亚人的领土,随后在国王的帮助下得以返乡。与此同时,特勒马科斯也从海外归来,父子相认,全家在20 年后得以团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便是整一的情节核心,“奥德修斯归家”这一主线将各个场景片段编织起来,避免了情节繁杂给人带来的眼花缭乱和材料堆砌之感。
史诗的情节也须有适宜的长度。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时间长短应以一览而尽为佳,便于观众记忆情节和酝酿情感,以使其美学价值发挥到极致;而史诗具有独特的叙述体优势,可同时描绘众多正在发生的事件,由此史诗的分量得以增加,显示出雄浑壮阔之感。“就长度而论,情节只要有条不紊,则越长越美;一般地说,长度的限制只要能容许事件相继出现,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能由逆境转入顺境,或由顺境转入逆境,就算适当了。”[2]36荷马在《奥德赛》中运用了插叙和倒叙的手法使情节得以丰富和变化,由此成就了亚里士多德“情节论”中推崇的完美史诗。正如史诗研究学者约翰·凯文·纽曼(John Kevin Newman)所述,“荷马充分利用预测和回忆的方式总结了整个故事,但只讲述了其中的一部分”[5]48。荷马集中笔墨叙述了奥德修斯归家前41 天的海上漂泊历程,其余的大部分情节均以穿插的形式作为奥德修斯的回忆在法伊阿基亚人的宫殿里借主人公之口娓娓道来。《奥德赛》实现了在集中摹仿奥德修斯返乡的整体行动的前提下,清楚交代了所有情节的始末。其中,尤以“冥界篇”最为典型,这一卷将希腊众英雄的事迹兼收并蓄,体现了荷马史诗叙事的高度凝练。且史诗穿插的形式有利于奥德修斯归家主线的展开,避免了悲剧容易出现的单调问题,这样的情节安排紧凑有序、张弛有度,符合《诗学》中的情节长度论。
荷马在情节的结构布局上实现了对以往史诗的超越,进行了自我革新。《奥德赛》通过移步换景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在叙事中挣脱了时间的限制,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画卷中展示了恢宏壮阔的人神世界。
(二)情节成分的灵魂:突转与发现
在史诗情节层面的特征中,除了情节的结构布局,《诗学》还指出史诗的情节应该包含三个“复杂的行动”[2]42,即情节的突转、发现和苦难场景。亚里士多德将史诗情节分为简单情节与复杂情节,并指出复杂情节通过突转或发现,抑或通过二者来达到结局。在第24 章,亚里士多德认为《奥德赛》是复杂史诗兼“性格”史诗。所以,《奥德赛》不仅在情节上包含以上三种成分,且荷马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运用这些成分最好的诗人。
若情节乃史诗之灵魂,那么突转与发现便是情节之灵魂,二者联手使简单的情节复杂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面”[2]43,而发现是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2]43。这两个成分相互作用,使个体的命运发生转折。严格来说,《奥德赛》中每一个事件的产生与发展、每一个矛盾的激发和化解都包含着突转与发现,正是突转与发现的交织使得这部史诗环环相扣、紧凑严谨,极具美学价值,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情节类型,因为突转与发现的同时性可最大程度地引起读者的怜悯和恐惧之情,从而使心灵受到净化。例如,读者对误入独目巨人洞穴的奥德修斯感到怜悯,更因其在洞穴内九死一生的遭遇而深感恐惧。值得一提的是,突转与发现也需遵循情节的整一性,关乎《奥德赛》的整体情节,涉及奥德修斯命运的逆转过程。在史诗的结尾,奥德修斯归家后陆续被奴仆、儿子、乳母、妻子,以及伊萨卡的所有人发现其真实身份,发现的过程充满了神秘色彩,层层递进、逐步深入。自此情节形势发生了逆转,奥德修斯将真实身份公之于众,他重新站在道德、权力与武力的制高点,成功将所有求婚者斩杀,实现了史诗情节的完美突转与发现。
除了突转与发现,苦难场景也是史诗摹仿复杂行动的因素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苦难是“毁灭或痛苦的行动,例如死亡、剧烈的痛苦、伤害和这类的事件”[2]44。奥德修斯为履行诺言帮助斯巴达的国王墨涅拉奥斯夺回被帕里斯掳走的王后海伦,抛下了自己的王国、心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远征特洛伊,这本身就是苦难历程的开始。在战争局势僵持不下之际,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献上木马计策终结了10 年的特洛伊战争,为希腊联军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战争结束后,希腊众英雄纷纷归家,然而奥德修斯的苦难还未终结。他又在海上颠沛流离了整整10 年才得以返乡,经历了漂泊、生存和复仇的苦难。长期远离故园、颠簸于未知世界是漂泊之苦,漂泊历程中的艰难险阻是生存之苦,归家后的屠戮是复仇之苦。这一切皆因众神之王宙斯掌管人间祸福和人类的生杀大权,奥德修斯知晓一切却也无法违背命运。在《奥德赛》中,命运才是世间的主宰,凌驾于人类之上。在命运的统率下,奥德修斯归返途中的所有行动和事件完成了表层与深层的统一。《奥德赛》体现了古希腊时代的命运决定论及理念论等思想,在情节的结构布局与成分方面为史诗理论做出了较为完美的阐释。
三、《奥德赛》史诗的人物特征
情节在史诗中的核心地位无可撼动,第二位的便是性格。史诗摹仿的是高尚人物的行动,而史诗人物的命运是由其性格所致。史诗摹仿的主人公具有独特的品格或性格,这些“英雄人物”出身高贵、声名显赫,在苦难面前意志坚定,具有超越常人的卓越性。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不吝笔墨地对奥德修斯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立体化描绘,“神样的”奥德修斯的形象在两部史诗中一脉相承。首先,奥德修斯聪明、睿智且富有谋略。奥德修斯以智慧名扬天下,诸神多次称赞其聪颖机敏、精于谋略。千钧一发之际,他仍能冷静分析形势想出万全之策应对,在诸多危难中渡过难关,比如谎称自己名为“无人”在羊群的掩护下逃离巨人境、将自己缚于桅杆摆脱塞壬歌声的诱惑、喝下魔药征服女神基尔凯救出同伴等。在听闻囚禁自己7 年的女神卡鲁普索决定放自己回乡时,奥德修斯并没有表现出激动和迫不及待等人之常情,而是沉着冷静地分析局势、以退为进,既不想贸然犯险也不愿错失良机。他对卡鲁普索说:“女神,你或许别有他图而非为归返……我无意顺从你的心意乘筏船离开,如果你不能对我发一个重誓,这不是在给我安排什么不幸的灾难。”[6]92在被监禁的7 年中,奥德修斯没有在流逝的光阴中失去理智或沉湎安乐享受的温柔乡,他要求卡鲁普索发重誓以防不测,确认无虞后才踏上了返乡之路。人神力量虽不可相提并论,但奥德修斯凭借自己的智慧在海上的颠沛流离中化解了无数的苦难。即使在时隔20 年后终于回到家乡伊萨卡,他也未急于表明身份,而是扮成乞丐去试探众人的反应,看清众人的真实面目后才与大家相认。
其次,奥德修斯意志坚定、执着勇敢。尽管前途未卜,奥德修斯能否顺利归家始终是一个未知数,但他从未言弃,金银财富、美女佳人和永生的诱惑都不能动摇他的信念,归家的目标一直支撑着他熬过艰难的时光。“我仍然每天怀念我的故土,渴望返回家园,见到归返那一天。即使有哪位神明在酒色的海上打击我,我仍会无畏,胸中有一颗坚定的心灵。”[6]94正是因为奥德修斯高尚的品格才使他受到了神的垂怜和眷顾。自始至终,雅典娜尽心尽力地为他奔走呼告,不仅在众神会议上请求众神之王宙斯放其归家,还为他清除了许多障碍,鼓励他的儿子外出历练寻父,直至奥德修斯踏上伊萨卡的土地仍然在为其出谋划策。《奥德赛》不仅是人与神的较量、人与自然的对抗、男人与女人的斗争,更是人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追寻自我的过程。然而,史诗的主人公并非十全十美,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局限性。奥德修斯对财产和名誉十分看重,离开伊利昂到达伊斯马洛斯后,面对无辜的基科尼亚人,他攻破城池、屠杀居民、虏获女子、劫掠财物。他生性猜忌多疑,甚至不相信妻子佩涅罗佩的忠贞,不仅在冥府中急切地询问母亲妻子是否改嫁,归家后还用计策试探妻子的真心。此外,奥德修斯已具备“早期奴隶主”[7]的特点。在杀死求婚者后,他又处死了所有不忠的奴隶,视人命如草芥。
史诗摹仿的是行动中的人,他们往往不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诗学》中指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2]48。亚里士多德借“过失说”强调人之所以遭受苦难、陷于厄运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而不是因为自身的罪恶或邪恶。由于人物不够强大,他们的弱点和过失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会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折磨。他们的错误往往与他们的道德品行无关,正是光辉的人物却因无意犯错而铸成悲剧才让读者不禁扼腕叹息。奥德修斯无意犯错的原因就在于特洛伊战争后,他率领众将归家途中误入海神波塞冬之子独目巨怪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中,为逃出生天刺瞎了波吕斐摩斯的眼睛,惹怒了其父波塞冬。自此,奥德修斯被迫挣扎辗转于浩渺的海洋。在漂泊期间,奥德修斯之所以多次身陷囹圄多是其同伴的愚莽狂妄所致。奥德修斯的灾祸并非咎由自取,而是从天而降的厄运,一方面,读者会因英雄人物陷入厄运而产生怜悯与同情,并在这样的情感中感悟人性的纯善,故而生发出崇高之感;另一方面,读者意识到英雄也并非完人,他们与平常人一样有着过失和弱点,他们自身的悲剧又带有几分感同身受。正因为主人公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反而和普通人相似,史诗才更加惊心动魄,快感油然而生。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阐释史诗应塑造高尚但伴有“过失”的人物特征的意义所在。
四、结语
荷马史诗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参照,它完美契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史诗理论,对后世史诗的发展和研究影响深远。《奥德赛》中呈现出的诗人摹仿的创造力、情节的整一性、人物性格的多样性,极大程度地诠释了《诗学》对史诗研究的理论价值。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站在了悲剧与史诗的交点,厘清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与不同,肯定了艺术作为摹仿现实世界手段的真实性,称颂了诗人的创造性与诗歌的美学价值,为后世叙事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借助对《诗学》与《奥德赛》的平行研究,有利于对史诗渊源的探析及发展脉络的把握,理解荷马史诗在摹仿功效、情节构建、人物塑造和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诸多特征。不难看到,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相互激发、互为影响,其间的互动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沉淀与更新,有待当代学者继续加以研究与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