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附与涌现概念下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 *
2023-02-24黄翔
黄 翔
社会科学试图对人类社会现象(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心理等)及其运作机制通过科学的研究给出合理的理解。自19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各研究方向(如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在学界成为专门的学科之后,对社会科学的哲学思考便一直被两类难题困扰。一类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另一类是社会本体论问题。第一类问题追问我们是否能够把对社会的研究看成是科学?如果能够,我们要以怎样的标准使得对社会的研究成为科学?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的合法性,它吸引了大量科学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投入研究。研究此难题的基本策略是在方法论上寻找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关联之处,并以寻找到的某种方法论标准来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辩护。换言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常常与方法论问题纠缠在一起。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对科学方法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别,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常常随之而产生变化(Agassi,2011;Turner,2007)。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以库恩(Thomas Kuhn)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转向产生之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有逐步被消解的趋势。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引发了许多学者认识到即使自然科学各个学科也未必共有相同的方法,各学科都可以拥有在其他学科未必能适用的独特方法(Roth,2011;Wray,2017)。从这种方法论层面上的多元主义视角出发,社会科学不一定与自然科学共有相同的方法。社会科学完全可以在拥有自己的方法或方法论规则而仍不失为成为合格的科学学科。因而,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便转化为确认哪些是适用于或更为有效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在辨识、对比和评价这些方法的异同和应用时的有效性时,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发现其中许多相关争论最终会落脚于社会科学哲学的另一类难题,即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本体论问题上。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社会本体论问题很大程度上展现在20世纪中期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争论以及该争论所引发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反思上。简单地说,整体主义坚持社会性(sociality)由某种共有的或集体的隐含规范构成。这种规范之所以是隐含的是因为它们并不一定被明晰地表达出来,因而当它们因果地引起某些符合规范的行动时,行动主体在当下行动中并不一定会意识到它们的作用。作为整体主义的代表,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坚持对社会行为的经验研究(如统计学研究等)可以得出社会事实所遵循的因果定律,尽管因果定律想要表达的社会实在并非被经验研究所直接通达。社会实在由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性约束构成,而规范性约束只有内在化为某种“集体意识”才能因果地引发人们的行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认为不存在不可还原为个体的社会性实体,在方法论层面上坚持个人行为和个人意向状态是说明所有社会现象的基础。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学理论常被当作是个体主义的典范,他的许多表述支持方法论个人主义,但他的理论远比单纯的个体主义复杂。按照这种对韦伯的简单化理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对有意义的行动的说明应该同时是因果充分的和解释充分的,即在正确说明引起行动的原因的同时,也需要正确地解释行为中所具有的意向性内容。韦伯并不要求社会科学建立某种普遍性的理解方法。理解只是对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给出充分的因果解释。对他人可分辨的行动类型的理解最终来自认知主体对被称为理想类型的行为的精确理解。由于理想类型的概念引入了认知主体的认知因素,建立于其上的韦伯的社会学很自然地带入个体主义方法论,并反对预设任何涂尔干式的共有的隐含规范。
方法论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议题,但在20世纪下半叶却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哲学究有一个可被称为“总体合法化”(global legitimation)的显著特点,即各种立场的辩护者大都试图通过厘清某些基础性本体论概念及其与相应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来总体性地为社会科学奠基,并在揭示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的同时,提出社会科学未来发展的规范性要求。①其他一些立场与争论如实在论、批判理论、实用主义等无疑都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的“总体合法化”特征的形成。因篇幅关系对此将不展开讨论。例如,无论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来调和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尝试,还是温奇(Peter Winch,1926—1997)使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资源来为解释主义和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作辩护,我们都不难从中看出总体合法化的特征。然而,在20世纪下半叶,对总体合法化的追求开始降温,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的多元主义立场逐渐被更多的学者接受。造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一些理论概念的引入和澄清,不少理论困惑得以消解,并最终形成了当今社会本体论问题域的变化与重组。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是“随附”和“涌现”。这个两个概念的介入使得经典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理解这个改变的过程和造成改变的理由,是把握当代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并预期其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本文第一部分简单地介绍随附性概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多重可实现性概念;第二部分在梳理随附概念被如何引入到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后,探讨该概念如何被用来重整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的各种版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突破方法论集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传统二分所带来的困境提供了可能;第三部分探讨涌现概念如何影响当代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
一、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
“随附性”(supervenience)在逻辑层面上表达了位于不同层级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即一个或一组高层级的属性A随附于一个或一组低层级的属性B,当且仅当属性A不会发生变化,除非属性B发生变化。换言之,属性A如果发生变化,那么属性B一定发生了变化。这个形式关系在20世纪70年后被戴维斯和金在权等学者引入到心灵哲学之后,变成心灵哲学中处理身心二元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工具(Davidson,1970;Kim,1984)。它的基本想法是与心灵相关的高层级属性随附于与物质相关的低层级属性,换言之,各种心灵和认知状态如感觉、情绪、记忆、注意力等如果发生任何变化,都意味着其所随附的与物质相关的属性,即大脑、身体和身体行动的物理、化学、神经等属性,也一定发生了变化。然而,相反的蕴含关系并不成立:即与物质相关的属性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心灵和认知属性一定发生变化。这个相反的蕴含关系的不成立意味着心灵和认知状态的多重可实现性,即同一种心灵和认知状态可以相应于不同的与物质相关的属性,或由不同的物理属性来实现。举例来说,看到面前有一盏亮着的灯这样一个视觉经验随附于与该经验相关的视神经系统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属性,是因为如下事实:当这个视觉经验发生变化时,例如面前的灯光灭掉了,那么,看到眼前的灯亮着和灯光灭掉时的视神经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状态一定会有所不同。然而,看到眼前的灯亮着这个视觉经验可以由视神经的不同物理、化学和生物状态来实现,例如,我昨天、一个小时以前看到的亮着的灯实际上是由与现在不同的(昨天的和一个小时以前的)视神经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态来实现的。
运用这种以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的方式来理解心灵对物质的依赖关系起码有两点好处:首先,在理解心灵和认知现象时,我们不必一定将所有的心灵和认知属性都还原为物理属性。比如,我们可以谈论和反思昨天、一个小时以前以及现在所拥有的眼前一盏亮着的灯的视觉经验是同一种视觉经验,而不必关注实现它们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其次,我们可以避免将心灵理解为某种超自然的形而上实体,因为同一类经验的不同各例原则上都可以找到之相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状态。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物理主义的还原论立场和二元论立场之间找到中立空间,例如,一些学者可以辩护某种非还原论的物理主义。
随附关系不仅可以处理身心二元关系,在更一般性的意义上它表达了高层级与低层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常常被应用在心灵哲学以外的领域。例如,在元伦理学领域中,随附关系可用来理解规范的道德属性与道德无关的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Miller,2014,49)。在社会科学哲学中,随附关系也很自然地被用来处理宏观/微观和集体/个体关系之间的二元关系。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宏观或集体属性以如下方式依赖于微观或个体属性:宏观或集体属性的任何变化都意味着微观或个体属性有所变化;同时,同一种宏观或集体属性也具有多重可实现性,即可以由不同的微观或个体属性来实现。例如,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由特定的队员、教练和相关工作人员组成,从组队、到训练、到参赛、到夺冠,都是由这些个体成员行动来完成的。同时,不同时代的中国女排又是由不同个体成员及其行动构成,换言之,作为一个抽象的类型概念的中国女排,经历过各种高峰、低谷、荣誉、困难,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员多重实现的。
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概念的引入,给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带来一种新的概念分析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澄清隐含在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中的一些含混之处,避免对整个争论的过于简单化理解,开拓了反思社会科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新天地。随附和多重可实现性概念带给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是帮助我们区分以下三组对立的六个立场:本体论集体主义vs.本体论个体主义;方法论集体主义vs.方法论个体主义;说明集体主义vs.说明个体主义。
二、集体主义vs.个体主义
在具体分梳各个立场之前,我们需要先解释一些“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异同。“整体主义”(holism)一般是指人类能动者的某些属性和技能只有在与他人产生互动或社会性关系中才能获得,与“整体主义”相对的是“原子主义”(atomism),是指人类能动者可以独立地获得其属性和能力。人类的一些先天或天生(innate)属性和能力是在这种意义上的原子主义式的,如吃喝、睡觉、哭笑等。从原子主义的立场出发,社会属性与能力是个体属性与能力的叠加和组合之后形成的。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之所以被看成是整体主义的,是因为在他的理论中,使得社会事实得以产生的人类的属性与能力如与他人合作、社会分工、通过宗教仪式而形成集体共识或集体表征、外在于个人意向又对个人的行为产生规范性影响的社会事实等,都不是个体属性和能力的叠加结果。而“集体主义”(collectivism)一词则是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相对应的,前者认为社会属性无法还原为个体属性,后者坚持社会属性最终能够被个体属性说明。在一些文献中,“整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词相互混用,未做仔细区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学者还未具备很严格的概念工具来清晰地界定这两个词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上运用的界限。当随附性概念以及我们下面要看的三组二元概念产生后,“整体主义”一词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运用明显地被更为精确地表达和替代。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组概念:
本体论集体主义(Ontological Collectivism,OC):在本体论层面上,存在着不可还原为个体的社会性实体。
本体论个体主义(Ontological Individualism,OI):在本体论层面上,不存在任何不可还原为个体的实体,换言之,唯一存在的是个体实体。
这一组概念中最为重要的概念是“还原”。反还原论立场的支持者,如涂尔干,就认为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无法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即个体的结构和功能,就像生命体如小猫的结构和功能,无法还原为它的爪子、毛发及其化学元素的结构和功能。还原概念在20世纪科学哲学中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义。例如,根据十分著名的内格尔(Ernest Nagel)的定义,理论A可以还原的理论B,当A中的词汇可以被B中的词汇定义,同时A中的定律可以从B中的定律中推出(Nagel,1961,345-366;Suppe,1974,55)。无论从涂尔干的还原概念还是科学哲学中的还原概念出发,反还原论立场(即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无法完全还原到个体的结构和功能)和整体主义立场(即存在着超出个体属性和能力的叠加的社会性属性和能力),很自然地会被看成是一种本体论集体主义OC(即存在着某种不可还原为个体的社会性实体,如集体表征、社会事实等)。
OC所要面临的困难是要解释不可还原为个体实体的社会性实体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存在的。个体实体的存在是没有争议的,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交流甚至操纵来感受和证实我们自己和他人的存在。然而,社会性实体如民族、国家、军队、大学、居委会等,尽管经常出现在人们的语言交流和文字记载中,我们也似乎毫不费力地理解这些社会性概念,但当这些社会性概念脱离了个体成员,它们还剩下哪些不可还原为个体的实体?一所大学如果脱离了在其中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则只剩下校园的占地、操场、建筑等可物理实体。在其中我们很难找到能够形成涂尔干所说的具有外在性和规范性的社会事实的实体。而且,这些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社会性实体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影响个体行为的?
本体论个体主义OI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承认个体实体是唯一存在的实体,那么从个体实体出发,如何产生出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属性?反还原论论据试图指出许多社会性结构和功能无法还原为个体的属性或并不是个体属性的叠加。此时,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概念便为OI提供了一种无需依赖还原概念却可处理社会属性和个体属性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简单来说,OI的支持者可以坚持社会属性随附于个体属性,即当社会属性发生变化时,一定会产生个体属性的变化,而个体属性的变化并不一定意味社会属性的变化。例如,当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时准备应试的青年学子的人生规划;而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年代,也有不少才华横溢的青年绝意仕进,却无法影响整个科学制度运作。同时,一个社会性属性可由不同的个体属性多重实现。例如,科举制度可以运作于不同朝代甚至不同地域如古代朝鲜和古代越南。总之,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的概念的引入极大地提高了OI的可行性。
与OC和OI密切相关,在方法论层面上展开的另一组概念,即方法论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MC)和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MI)。我们无法像对待OC和OI那样,直接地给出MC和MI的直接定义,这是因为方法论个体主义MI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鲁本(David-Hillel Ruben)曾经指出:“方法论个体主义从来就没有足够清晰和精确地表达过,以至于难以对其进行合适的评价”(Ruben,1985,13)。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最初由波普尔(Karl Popper)的学生沃特金斯(J. W. N. Watkins)提出,一方面捍卫波普尔在《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的个体主义,另一方面将波普尔的个体主义概念中政治性维度从哲学维度中区分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①“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词由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于1908年提出,其目的是区分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与政治领域中的个体主义,参见Udehn(2001,104)。这部著作同时还介绍了熊彼特和波普尔外其他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先驱,如密尔、狄尔泰、西美尔、韦伯、门格尔、冯·米塞斯、哈耶克,等等。他所给出的MI的定义是这样的:
是人决定了历史,尽管人也被历史决定。这个事实的和形而上的断言具有如下方法论上的意涵:大尺度的社会现象如通货膨胀、政治革命等,应该以个体的境况、倾向和信念来说明。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个体主义”。(Watkins,1955,179-180)
沃特金斯对MI的这个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个定义是以本体论个体主义OI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预设了个体实体是唯一存在的实体,不存在独立于个体实体的社会实体。因此,是个体的人决定了历史,尽管不同个体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社会现象会影响个体人的生活。在沃特金斯看来,这种MI所反对的是被称作“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的立场:
从这种观点出发,个体的社会性行为应该用他们所在的文化-制度结构中的位置,加上支配系统运作的定律来说明…这就是所谓的“方法论整体主义”。(Watkins,1995,179-180)
在另一篇文章中,沃特金斯使用的是“社会学整体主义”(Sociological Holism)一词:
如果方法论个体主义意味着人类被当作在历史中唯一可移动的能动者,而且如果社会学整体主义意味着某些超人类能动者或超人类因素被假定在历史中运作,那么,这两种立场穷尽所有可能。(Watkins,1957,106)
不难看出,作为沃特金斯的MI的对立面,无论是“方法论整体主义”还是“社会学整体主义”都预设了本体论集体主义OC。
沃特金斯的MI定义的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所谓方法论层面上的个体主义,是在说明(explanation)这个维度上展开的。也就是说,方法论层面上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争论围绕着说明社会现象的说明因素是个体还是集体这个问题展开。在这里,我们需要对“说明”一词做一点说明。从一般性的直觉来说,说明是指对我们感到困惑、好奇或想知道的事物予以解说之后获得对该事物的理解(understanding)的过程。例如,我们向朋友说明为什么会约会迟到,老师向孩子说明如何使用三角尺画出特定的角度,牧师用《圣经》说明人类的起源,等等。通过说明,人们因获得理解而感到认知上的满足,这是人类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理认知过程。说明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之一,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说明自然和社会现象。科学哲学界中最为著名的科学说明理论是亨普尔(Carl G. Hempel)提出的覆盖律理论(the covering law theory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根据这个理论,科学说明与日常说明的根本区别在于,说明项(explanans)与被说明项(explanandum)之间的关系是论证关系,而且作为论证前提的说明项中具有科学定律(Hempel,1948)。例如,科学理论对地震的说明与神话通过神祗的愤怒的地震的说明,都可以给人以理解上的满足感,但前者与后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的说明项中含有各种科学定律尤其是物理学定律,这些定律与其他条件和描述语句一起,可以演绎地推出描述特定地震的语句。亨普尔的覆盖律理论的优点是给出了科学说明了一个十分清晰的、可以被形式逻辑刻画的定义,因此成为日后科学哲学在讨论科学说明问题的理论起点。亨普尔的理论也曾受到一系列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许多学科包括社会科学中的说明并不经常使用科学定律,另一些学者坚持科学说明的说明力来自将说明对象统合到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之中的能力,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科学说明的更为一般性特征是解释产生被说明项因果机制。在此,我们不必介入这些说明理论之间的争论细节,只需认识到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有着不同种类的说明方式,如定律说明、统合说明、因果说明、机制说明等。回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沃特金斯所说的方法论是MI要求在社会科学的说明中,能够最终对社会现象予以说明的说明项的应该是个体属性如个体行为或个体意向状态。
从本体论预设和说明维度这两个特征出发,我们可以对沃特金斯所理解的MI给出如下定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MI):由于个体是唯一存在的实体,只有个体行为和个体意向状态才能充分地说明社会现象。
而沃特金斯所说的“方法论整体主义”或“社会学整体主义”与MI相对,学界更多地称之“方法论集体主义”(Methodological Collectivism),可被定义如下:
方法论集体主义(MC):由于一些社会现象由超个体的社会实体引起,个体行为和个体意向状态无法充分地说明这些社会现象。
MI与MC的二分有其合理的地方。一方面,它清晰地展示了超个体实体的本体论预设所带来的方法论层面上的后果。另一方面,一些沃特金斯所辩护的MI的确可以很好地说明一些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以理性个体为建模基础的当代经济学。然而,这个二分也有过于简单化之嫌。沃特金斯把密尔、韦伯、波普尔等人的社会理论归为MI,把黑格尔、涂尔干、帕森斯等人的社会理论归为MC。沃特金斯的MI和MC的区分更像是一份对波普尔式的社会理论在方法论、本体论甚至政治层面上的规范性要求的宣言,而难以成为分析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合适的概念工具。
卢克斯(Steven Lukes)指出造成上述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沃特金斯对MI和MC的刻画实际上同时涉及了本体论和说明两个维度,而这两个维度本应该分别来讨论(Lukes,1968)。一旦从本体论维度分离开来,在说明维度上我们可以区分如下两种立场:
说明个体主义(Explanatory Individualism,EI):只有个体行为和个体意向状态才能充分地说明社会现象。
说明集体主义(Explanatory Collectivism,EC):个体行为和个体意向状态无法充分地说明这些社会现象。
不难看出,El和EC可以分别从MI和MC中推出,即MI的坚持者一定是说明个体主义者,MC的坚持者一定是说明集体主义者。但是,反之则不必然,即从EI中推不出MI,从EC中也推不出MC。这就使得如下立场得以可能:我们可以坚持本体论个人主义OI的同时也坚持说明集体主义EC。换言之,我们可以在承认不存在超个体的社会实体的同时,坚持一些社会属性无法被个体属性充分说明。这是一种未能被沃特金斯的MI和MC二分捕捉的立场,它的优势是在避免不必要的形而上学负担的同时,能够处理那些不由个体属性叠加而成的社会属性,因此,被越来越多的当今社会本体论学者接受。
更为一般性地,卢克斯的EI和EC的二分,为我们理解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分析工具。沃特金斯的MI和MC的二分,只允许我们区分以下两种极端立场:
整体主义(Holism):本体论上坚持OC,方法论上坚持MC,说明维度上坚持EC,即OC&MC&EC。
原子主义(Atomism):本体论上坚持OI,方法论上坚持MI,说明维度上坚持EI,即OI&MI&EI。
然而,这种简单化的二分却忽略了一种建立在随附性和多重可实现性之上的、 由本体论个体主义与说明集体主义的组合。我们姑且称之为“一元论集体主义”:
一元论集体主义(Monistic Collectivism,MoC):本体论上坚持OI,说明维度上坚持EC,即OI&EC。
这里的“一元论”是指在本体论上只承认一种实体即个体实体的存在,而反对个体实体和超个体实体同时存在的二元论。MoC的基本思想是,尽管在本体论坚持不存在超个体实体,但在说明层面上,社会属性仍然可以成为社会现象的合法的说明项中成分,因为存在这样一些社会现象,对其理解无法只用个体属性来说明,而是需要依赖社会属性来说明。MoC很难被归在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二分以及MI与MC二分所给出的任何一类中。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新的问题:OI&EC是如何可能的?即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一元论即反对存在超个体实体的情况下,如何会出现一些社会现象,它们不能单用个体属性来理解,而需要社会属性来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逐渐形成的共识是:一些社会属性不是个体属性的叠加,而是从个体属性中涌现出来,因而,对拥有这些涌现出来的社会属性的社会现象,无法只使用个体属性来进行说明,而需要依赖涌现出来的社会属性。
三、涌 现
很显然,在这里“涌现”(emergence)是个关键性概念。涂尔干曾坚持集体表征不是个体表征的普遍化或叠加后的产物,而从个体表征、个体行为和个体之间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这就像作为生命体的小猫不是其躯干、血肉和毛发的叠加,而是从这些构成部分中涌现出来的。涌现出来的生命现象,无法被构成部分的属性说明和预测(unexplainable and unpredictable),因而是一个全新的(novel)、不可还原(irreducible)为其构成部分的现象。涂尔干的涌现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看成是一种为超个体实体辩护的OC立场。然而,一旦我们采用卢克斯的策略,将本体论、方法论与说明层面区分开来,就会发现涌现概念不必只在本体论层面上而是可以在说明层面上展开。
“涌现”一词据说是由英国哲学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在其《生命与心灵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Lewes,1875,vol. 2,412)。刘易斯与其他一些哲学家推动一个被称为“英国涌现主义”(British Emergentism)的思想传统。①英国涌现主义者还包括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贝因(Alexander Bain,1810—1877),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1859—1938),摩尔根(Lloyd Morgan,1852—1936),布罗德(Charlie Dunbar Broad,1887—1971)等,参见McLaughlin(1992)。该传统坚持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非还原的等级关系,其中高等学科中的定律可从基础学科中涌现出来,例如,化学定律从物理学现象中涌现出来,生物学定律从物理和化学现象中涌现出来,心理学定律从生物学现象中涌现出来,等等。自从“涌现”一词被提出后,涌现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在不同领域来说明不同的现象。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复杂性系统理论用此概念来说明有规律的机械化(mechanistic)现象如何从分子之间的无序运动中产生,生物的有机(organic)现象如何从物理的机械化现象中产生,社会现象如何从生物的有机和心理现象中产生(例如,Bertalanffy,1968,55;Miller,1978,28-29,1036-1038;Prigogine and Stengers,1984,160-170;Gell-Mann,1994,99-100;Kauffman 2000,chap. 6)。在物理和生物层面,涌现出来的高层级属性仍然可以用物理主义的方式来理解,坚持各层级的属性都可以被因果关系充分地说明。而在心理和社会层面,对涌现概念的使用常常是为了避免物理主义还原论即原子主义所坚持的OI&MI&EI,坚持心理和社会属性因其意向性和目的性的特征无法充分地仅被物理和化学的因果规律来说明,尽管绝大多数的学者在本体论层面上并不反对唯物论。
在心理学方面,活跃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英国涌现主义,坚持生命与心灵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识和意向性从物质实在中涌现出来并且随附于后者。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格式塔心理学也使用涌现概念来坚持心理现象应该整体地理解,而不应被拆分为其物理构成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在美国实用主义阵营中,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在《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第六章中反对心灵状态或意识可以被物质性的心灵材料(mind-stuff)充分说明。杜威(John Dewey,1859—1951)著名的经验观坚持经验是有机能动者与环境的互动和主动参与后涌现出的结果。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强调了心灵的社会维度的涌现过程及其对行为的因果作用。在20世纪下半叶的心灵哲学领域中,涌现概念和随附性概念常常被一起用来反对将心灵属性看作是没有因果效力的次现象的立场(如Beckermann,et al., 1992;Kim,1984/1993;Humphreys,et al.,1997)。在认知科学领域中,涌现概念被用来质疑以使用内在表征模型来说明智能行为的经典认知科学进路。例如,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进路试图模拟低层级的神经网络的平行互动如何涌现出高层级认知及其引发的智能行为的过程(Bechtel and Richardson,2010,chap. 9)。联结主义的涌现概念为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进路提供了理论支持,后者坚持认知能力是认知主体的大脑和身体与环境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结果(Clark,1997,chap. 6;Varela,Thompson and Rosch,1991/2016,chap. 5&6)。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们曾提到涂尔干就提出过涌现的概念。其实,孔德就已经提出过类似于涌现的观点,如“社会不能被分解为个体,就像集合平面不能分解为线,或线不能分解为点”;又如“在近期复杂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简单的无机科学所运用的分解方法是完全非理性的,而且无法得出任何结果”(Sawyer,2005,38-39)。孔德的思想不仅影响着法国社会科学界,包括作为其后辈的涂尔干,在英国也影响着与其有书信交流的密尔,以及其他涌现主义者。在英语学界中第一个将涌现概念用于社会研究中的是美国昆虫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他不满之前的英国涌现主义者们将涌现概念仅用于生物和心灵现象,将其早期对社会性昆虫特别是蚂蚁的研究延展到社会,坚持社会性结构涌现于个体之间的各类合作,而不是个体的行为叠加总和(Wheeler,1928)。20世纪上半叶使用涌现概念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是帕森斯。他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层次是不可还原为物理科学的“单位行动”(unit act)和“行动系统”(action system),而且,“只有在单位行动之间的关系复杂到一定水平之后,行动系统的属性才能涌现出来”(Parsons,1949,739)。
20世纪下半叶对涌现概念很大程度上围绕着“微观—宏观关系”(the micro-macro relation)问题展开(Bouvier,2011)。这个问题试图从微观对象的个体与作为宏观对象的集体之间的关联方式出发来理解社会现象的基本特征。涌现概念使得社会团体、群体行为、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等这些社会现象不再需要超个体的实体支持。换言之,涌现概念支持了MoC所坚持的本体论个体主义OI,然而,涌现概念并不直接支持MoC所坚持的说明集体主义EC。这是因为尽管涌现概念常常被用来替代还原论理解个体或微观属性与集体或宏观属性之间的关系,因而的确为说明集体主义EC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还原论者也可以因不同理由仍然使用某种涌现概念来理解个体属性与宏观属性之间的关系。例如,上面提到的认知科学中的联结主义理论基本上持还原论立场。联结主义试图模拟宏观的智能行为如何从微观的神经元之间的网络互动中涌现出来的过程,而建模中的变量是微观单位及其互动,宏观层面上的智能行为则是模拟的结果。换言之,宏观层面上的智能行为在本体论层面可还原为微观单位互动结果,在说明层面上完全被微观变量说明。不难看出这预设了还原论的涌现概念。按照这种概念,现出的高层级的属性被理解为是由于低层级属性的某种特定组合后产生的结果。例如,水所具有的属性如透明性,并不是水的组成元素即氢和氧的属性,而是氢分子和氧分子在特定条件下化合构成的水分子聚合后所涌现出的现象。水的透明性这个属性对于氢分子和氧分子来说并没有任何因果影响力,却最终可以被氢分子和氧分子的化合过程来说明。联结主义也坚持高层级的智能行为是在低层级的神经元网络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涌现出的结果,高层级智能行为无法因果地影响相关神经元本身的属性,却最终由神经元之间的互动过程来说明。联结主义所给出的平行分布式网络就对这个互动过程的模拟,并通过模拟给出对高层级智能行为的说明。
与联结主义类似,在社会科学中,占据经济学研究主流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常常会使用这种预设了还原论的涌现概念来理解社会属性与个体属性之间的关系。它的基本想法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由个体成员及其之间的互动构成,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不同组织方式会涌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持有预设还原论的涌现概念的著名的社会学研究包括霍曼斯(George Casper Homans,1910—1989)的行为社会学理论,在其中霍曼斯坚持在社会交换行为中涌现出的社会属性最终应该用心理学资源来说明(Homans,1964,229);另一个著名的研究是科尔曼(James Samuel Coleman,1926—1995)的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试图从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个体行动为出发点来分析整个系统的行为。个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在系统层面上涌现出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之所以是涌现出来的,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组织运作的结果,无法从个体的愿望和预测中推出,也不是个体行动的叠加。例如,市场泡沫就是从微观个体行为中涌现出来的一种宏观经济现象。科尔曼同意涌现出来的社会系统现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但在说明层面上最终依赖个体之间的合理互动(Coleman,1990,19-20)。
MoC并不否认方法论个体主义所坚持的预设了还原论的涌现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微观-宏观关系,因为的确有一些社会现象可以用此概念来说明。例如,商品的价格就可以被看成是从希望最大化个体利益的理性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现象。在本体论层面上,商品价格及其属性不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以及影响消费者理性操纵能力的因果效力,在说明层面上却可以被理性消费者之间的群体互动关系来说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宏观社会现象的商品价格随附于个体消费者的愿望及其之间的互动。然而,MoC所要坚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宏观社会现象都能被方法论个体主义和预设了还原论的涌现概念来说明,这是因为有一些涌现出来宏观社会属性尽管随附于微观个体属性却无法还原为后者。这里有两个理由:一是一些涌现出来的宏观社会属性不仅随附于微观个体属性,也由不同的微观个体属性多重可实现,而宏观社会属性的多重可实现性使得它难以还原为个体属性;二是宏观社会属性一旦对个体行为拥有因果效力,则难以还原为个体属性。
我们先看第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建立在多重可实现性的概念上。我们在第一部分曾提到这概念,它的基本想法是,一个高层级的社会现象可由低层级的个体属性多重实现。例如,复旦大学是由不同时代的师生和管理人员多重实现的:它在1905年由马相伯在吴淞创办的“复旦公学”中的师生和管理人员首次实现,民国中期由教育家李登辉校长所带领的师生和管理人员实现,解放初期由陈望道校长所带领师生和管理人员实现,改革开放之初由苏步青校长所带领的师生和管理人员实现。总之,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师生和管理人员个体多重实现的,可谓“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师生”。福多(Jerry Fodor)曾论证,如果高层级属性随附于底层级属性并且可由低层级属性多重实现,那么,在原则上高层级属性还原低层级属性并不总是可以达成的。这是因为高层级属性还原为低层级属性要满足如下条件:高层级属性之间形成律则性(lawlike)关系和变化,多重实现这些高层级属性的低层级属性的相应殊型(token)之间也发生同样的律则性关系和变化。但这个条件并不总能被满足。例如,李登辉校长提出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训作为复旦的教育精神,仍然激励着当代复旦大学的师生。然而,我们无法断言李校长当初提出这个校训那一年的师生和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殊型,对当下复旦大学的师生和管理人员所组成的殊型具有精神激励的作用。如果福多提出的条件无法被满足,那么,高层级属性无法还原为它们所随附的低层级属性(Fodor,1974)。
复旦校训的例子也同样支持了宏观社会属性无法还原为个体属性的另一个理由:一些社会属性拥有独立于它所随附的个体属性的因果力,即因果引发其他个体属性的能力。在复旦校训的例子中,李登辉校长提出的校训在几十年后仍然因果地影响今天的师生们学习和生活。如果社会属性的确具有独立于其所随附的个体属性的因果力,那么,我们将有理由坚持社会属性不必还原为个体属性。然而,学界对于社会属性的因果力是有所争议的。在心灵哲学领域中,随附性概念提出之后,一些学者坚持只有心灵属性所随附的物理属性才拥有引发心灵主体认知活动的因果力,而心灵属性看起来所具有的因果力其实是一种次现象(epiphenomenal),而低层级的物理属性是因果完整的(如Kim,1993,19-21;Papineau,1993,16;Yablo,1992,246)。坚持心灵属性具有独立于其所随附的物理属性的非还原论者需要证明低层级的物理属性在哪种意义上是因果不完整的。霍尔干(Terence Horgan)利用高层级属性的多重可实现性提出了一种论证:由于高层级心灵属性在低层级的物理属性中是多重可实现的,高层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低层级的物理层面上未必总能找到相应的因果关系(Horgan,1994)。索耶尔(Robert Keith Sawyer)将霍尔干的论证延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以复旦校训为例。李登辉校长为全校提倡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学习和生活态度,这是一种社会属性,我们可以作用“S”来表示。S所随附的是当年李校长提出校训时所参与的各种人员的行动与互动,可以用“I”来表示。经过一些历史曲折,该校训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成为激励和指导全校师生的精神原则。我们可以把今天对校训的接受用“S*”来表示,“S*”所随附的是受到该校训激励的今天的师生和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用“I*”来表示。不难看成,在高层级的社会属性层面上,当年李校长提出的校训S因果地引起今天对校训的接受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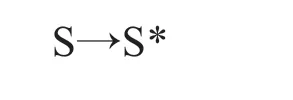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该校训也因果地引起了S*所随附的受到校训鼓舞的师生及其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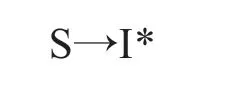
然而,我们无法在S所随附的个体行动I与S*所随附的个体行合I*之间找到因果关系。换言之,高层级的社会因果属性S→S*无法还原为在低层级的个体属性I和I*之间的因果属性(Sawyer,2005,70-71)。
以上两个理由,即基于多重可实现性的反还原论和社会属性的因果力的存在,为MoC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MoC中一个著名的进路是“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该进路坚持社会属性对个体行为具有因果作用,同时也坚持社会属性从个体属性中涌现出来(如Bhaskar,1979;Archer,1995;Collier,1989;Lawson,1997,2019等)。批判实在论在兴起初期,由于坚持不可还原为个体属性的社会属性的实在论,被一些学者质疑有同时承诺个体实体和社会实体的二元论之嫌,从而无法被看成为一种MoC立场。例如,批判实在论的创始人之一巴斯卡(Roy Bhaskar)的理论就被质疑是否能够兼容其所同时预设的社会实在论与本体论一元论(King,1999,270-278)。对于这个质疑,多数批判实在论者会选择寻找批判实在论与MoC相兼容的策略。例如,艾切尔(Margaret S. Archer)坚称批判实在论“所要捍卫的并不是哲学二元论而是分析二元论的有用性”(Archer,1995,180)。艾切尔的意思是,批判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仍然是一元论OI,坚持只存在个体实体,但由于涌现出来的社会现象过于复杂,在分析层面上难以仅用个体属性充分地说明社会现象,因而需要预设社会属性作为独立的分析或说明单位。当然,MoC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坚持实在论,而可以在实在论问题上保持中立,只坚持OI和EC,即在本体论层面上坚持个体是唯一存在的实体的同时,在说明层面上坚持社会属性具有独立的说明力和因果地引起社会性行为的能力(Kontopoulus,1993,Sawyer,2005)。
对于涌现的运作机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扎赫勒(Julie Zahle)区分了三类理论:一是建立在整体-部分关系上的理论,二是建立在随附关系上的理论,三是建立在涌现现象的历时性发生过程之上的理论(Zahle,2017)。以整体-部分关系为出发点的理论也是多种多样的。温萨特(William Wimsatt)认为涌现产生于高层次属性的不可叠加性(nonaggregativity),即不是低层次属性以各种关系叠加而成(Wimsatt,1997)。贝切特(William Bechtel)和理查森(Robert C. Richardson)用可分解性(decomposability)和可定域性(localizability)来理解涌现。一个可分解系统中每一组成部分都按其内在原则行动,因而组成部分的属性可以不依赖其他组成部分属性来理解,而系统整体的属性也由其组成部分的属性来决定。一个不可分解系统很可能产生涌现属性。一个系统是可定域的,当其功能性分解与其物理组成部分相应,并且每一个系统属性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应的子系统。一个系统是不可定域的,当该系统属性无法找到与其相应的物理组合或子系统而是分布于系统之内。涌现属性同样可能从不可定域的系统中产生(Bechtel and Richardson,2010,23-27)。坚持实在论的艾德-瓦斯(Dave Elder-Vass)则使用社会属性的因果能力来理解涌现。在他看来,涌现出来的社会属性是社会实体因其组成部分即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因果力。例如,国家所具有的发动战争或向人民的经济活动课税的能力,或者由群体授权某一个体代表该群体作出决定的能力等(Elder-Vass,2010,152-157)。建立在随附关系上的涌现理论认为涌现的社会属性随附而非还原于个体属性,并且可由个体属性多重实现。例如,索耶尔坚持社会定律随附于个体定律之上(Sawyer,2005)。又如,孔托波罗斯(Kyriakos Kontopoulos)关注宏观结构随附于它的微观组成部分,因而涌现出来的宏观现象具有某种自主性的特征(Kontopoulos,1993)。建立在涌现现象的历史发生过程的涌现理论的例子包括艾切尔的形态发生(morphogenesis)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涌现理论如果想要反映真实的社会现象,就需要理解当下的社会结构如何从过去的个体行动中涌现出来的具体过程(Archer,1995)。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模拟个体能动者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互动,产生或涌现出宏观层面上的复杂行为样态或行为规律,从而形成人造社会的过程(Epstein and Axtell,1996;Epstein,2006;Gilbert,1995)。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涌现概念所要直接反对只是一种特定的哲学立场,即物理主义还原论,该立场坚持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也应该在说明层面上还原为个体的物理属性。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明个体主义EI。①物理主义还原论作为一种极端的哲学立场,尽管是一种唯物主义还原论(即坚持所有存在的实体最终都随附于物理实体),但唯物主义还原论不必仅接受物理主义还原论。我们所看到的本体论个体主义OI的各种立场包括MoC都可以与唯物主义还原论兼容。而不同种类的涌现概念其实可以同社会科学哲学的各种立场相兼容:整体主义、原子主义、还原论、实在论、个体主义方法论,等等。然而,涌现概念仍然为20世纪的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了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首先,它让我们看到社会科学哲学各种立场都缺乏先验理由的支持。采用哪种立场更为合适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要看我们想要理解的社会现象的具体情况而定。其次,涌现概念也让我们看到方法论集体主义MC和方法论个体主义MI的二分即其所预设的整体主义和原子主义的二分都过于简单。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科学哲学家逐渐看到他们不必在上述二分中作出选择,而是可以接受MoC。MoC在随附和涌现的概念帮助下,可以建立非还原的唯物主义立场之上,坚持社会属性随附于个体属性(包括个体的物理属性)之上,但不必还原为后者,因此,社会属性所具有的因果力,不必还原为作用于个体属性之间的因果力(Sawyer,2005,98)。
四、结 语
总之,20世纪的社会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或宏观和微观的二分争论展开。从心灵哲学领域中引入的随附概念以及从复杂性理论中(再)引入的涌现的概念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界提供了打破一系列传统二分的有用工具,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还原论与二元论的极端立场之间开辟出各种中间进路。学者们在承认社会属性的自主的说明力的同时也能坚持一元论的唯物主义立场,从而不必承担不必要的形而上学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