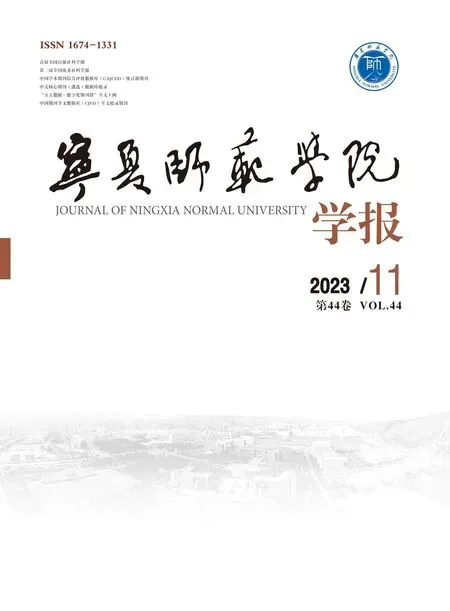语文知识课程价值演变的学术史考察
——兼议工具性质观存在的必然性
2023-02-23解光穆
解光穆
(宁夏师范学院 教师发展研究中心,宁夏 固原 756099)
与基础教育阶段其他课程相比,语文课程赖以安身立命的语文知识确有着诸多独特之处,如自身的母语性质,使得语文知识就可自然或半自然“习得”,而无须如其他课程的知识那样主要靠“学得”;再如这门课程涉及语言学、文章学、文学等众多学科且在每个学科内又有着复杂组成,这就使得语文知识数量众多且关系复杂,“语文里讲的,除选文的内容部分外,都是语文知识”[1],这与其他课程主要以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学习为主有着极大不同;还如语文知识主要是体现于实际使用中,因而就使得语文程序性知识的学习与运用显得颇为复杂,这与其他课程中程序性知识理解运用相对便捷也有着很大不同。因此,从语文课程学术史角度来考察语文知识的价值功能,对认识为何要有语文知识、应有哪些语文课程、怎样教语文知识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一、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研究的学术考察
晚清北洋政府时期,语文课程实际上又有着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五四运动前,语文课程以文言文为课程对象的阶段;一是五四运动后,白话文进入语文课程并与文言文并存的阶段。
(一)1904年到1919年
这一时期,在从古代传统“泛语文”“大语文”课程形态向独立设置的现代语文课程转型中,语文课程表现出对传统训诂、小学等文言基础知识系统传授的继承[2],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也就得到充分肯定。其中庾冰在1912年就从语文表达形式与思想内容关系认识入手,提出“以内容与形式组织而成文,二者不可偏废”,主张语文课程应注重在“形式上教授之”;在他看来语文“形式虽千端万绪,其大要不外文体文法文词三大项”,因而“初学作文,只求与此三者得‘条直’二字之评语”[3]。这表明在庾冰的语文课程观中,语文课程要指向于语文表达形式;而指向于语文表达形式的语文课程,就要把“文体文法文词”作为主要课程对象。1914年,徐特立提出语文课程的根本目的,即“使儿童知普通言语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章,而养其表达思想之能力,兼启发其知德者也”。在他看来,“表达思想之能力”属于语文形式方面,“启发其知德者”属于思想内容方面,二者虽密切交织,但就其独立设科目的看,这门课程“主要目的则在形式方面”。[4]语文课程怎样才能“使儿童知普通言语及日常须知之文字、文章”呢?徐特立认为要加强对文字与文章的形式知识的教学与训练,也就是“文字即形声训诂,文章即文法修辞”[5]。这些阐释,清晰表明了徐特立的语文课程目标观与语文知识价值观,培养学生掌握文字文章能力,是这门课程的根本目标;而要达此目标,“形声训诂”与“文法修辞”等方面语文知识的传授与训练就是不可或缺的。1915年,以小学语文教师身份的姚铭恩发表了《小学作文教授法》一文,提出在作文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两大要素中,学生虽也存在着“内容上之组织难”问题,但更多表现在“形式上之组织尤难”上。基于此判断,他明确提出:“国文教授,以修炼形式方面为主目的,则作文之教授,自当注意于形式上之修炼。”[6]为此,他列举出了作文在表达形式方面的多个具体方法,体现出对写作知识的重视与探索。随后,孙本文也从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角度,强调语文课程应以指导学生对语文形式的学习与掌握为主:“嵬集知识发表思想之能力,几为向日教国文者出全力以谋之鹄的。读文作文,非不准是励进。若乃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固宜重形式而轻实质矣。”[7]从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区别中,他强调了“读文作文”能力才是语文课程“之鹄的”,而“启发智德,则有各科学在,似非国文教授之主鹄”,鲜明表现出以语文表达形式为课程本体、以语文表达形式知识为重要课程对象的观点。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对语文课程本体认识和语文知识课程价值认识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开启了语文课程建设“知识化”进程。从庾冰、徐特立、姚铭恩等对语文知识特别是写作知识的论述中,我们即可明显看出这一时期已开始把语文知识纳入语文课程内容体系之中,这就深远影响到其未来的改革发展。二是语文知识体系构建被纳入语文学者的学术研究领域。姚铭恩对写作知识的系统表述与教法阐释,表明当时学者已开始了对写作知识内部组成的系统探索与概括总结,反映出语文知识体系得到了初步构建。三是推动了语文课程的转型发展。我国古代语文课程在注重语文教育的“教化”功能发挥中,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与训练呈现出片段性、零散性与体悟性等不足。语文独立设科后,学者开始对语文知识进行的思考与建构,就促使学术界“深入到对语文课程知识价值、语文课程知识本质的审思”[8]。四是存在着偏重文章知识的不足。姚铭恩等对语文知识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章领域,而对语言、文学等语文知识关注不多。
(二)1920年到1928年
从五四运动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段时期,对语文课程建设有着重要影响的就是白话文成为重要课程对象,并在言文一致语言政策下引起了语文学者对语文知识的新探索与新建构。1922年,周予同认为语文课程之所以独立设科,就是为了促使学生掌握语文运用的知识与方法,文法学随之也就成为“中学国文中最重要的科目”[9]。把研究语言组织方式、内部结构及实际具体运用等表达形式方面的专门知识视为“最重要的科目”,反映出周予同对语文知识在语文课程中基础性地位的清晰认识。1924年,沈仲九认为白话文进入国文课程后改变了教师“只教学生熟读”的呆板教法,使得他们开始注重方法上的指导。“对于法则和方法,比以前注重得多;什么语法文法,什么作文法,什么小说作法、诗歌作法、戏曲作法,什么修词学,都列入正功课了。”[10]1925年,沈仲九明确提出语文课程必须注重加强对学生进行语文知识(法则)的传授与训练。为形象说明这一问题,他以书法家写字为例,说明学生学语文与书法家在成名前练字是一致的,学生学习语文特别是初学语文时,“不能不把怎样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等分析地练习。练习熟了,自然能意到笔随,得心应手,不必再分析地留意于‘词’‘句’……”正是有此认识,沈仲九就辩证指出:“国文教授的目的,自然在使学生能够以直观力得到‘文’的形式内容的合一;但是教授的入手,仍免不了把内容形式分析地来注意。”[11]怎样才能实现“把内容形式分析地来注意”呢?就应在国文课程特别是国文教材中注重对语言法则(文法)知识的选择与呈现,“形成以文章和法则互为经纬,两相融合,于文章中发见法则,将法则运用到文章上”[12]。
相较于五四运动前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的认识,这一时期沈仲九等对这一问题的阐释表现出了一些新特征。一是进一步肯定了语文知识在语文课程中的核心地位[13],突显出其基础性课程价值——文法学是“中学国文中最重要的科目”。二是强调了语文知识的学习要知行合一,即要把语文知识转化为语文能力。三是提出语文教材要体现出语文知识,即“形成以文章和法则互为经纬,两相融合”的教材体系。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研究的学术考察
在这一时期,对语文知识体系建设研究成就最大、贡献最著的当属宋文瀚、王森然、夏丏尊、叶圣陶、周谷城、蒋伯潜等著名学者。鉴于篇幅所限与叶圣陶等对语文课程建设的历史贡献为学术界所熟知,故笔者对这一时期的学术考察主要以宋文瀚、夏丏尊两位先贤为主。
1931年,宋文瀚在把语文课程定位于是一门“技能的学科”基础上,并结合语文教材编写对语文知识体系建设作了全面论述。一是分析了语文知识的复杂性,突显出语文知识运用的重要性。在与其他课程目标、知识传授等的比较中,宋文瀚认为别的课程大都“重在知识的传授”,语文课程却“重在传授知识的文字的运用的训练”。正因为如此,“别的学科在使学者明瞭,国文科则于明瞭而外,尚须使学者能运用”[14]。这一精要论述说明,与其他课程知识传递重在“知”相比,语文课程中的语文知识却要在“知”的基础上更要“行”。譬如学习汉语词序在语句构成中的灵活性、组合性等知识时,更重要的是学习者要在实际语文运用中能恰当自如地使用诸如“不很好”“很不好”与“你喝大杯”“你大杯喝”以及“一台电脑多少钱”“多少钱一台电脑”等语序组合。二是分析了语文知识的技能性特征,突显出语文知识的能动性作用。在语文课程是一门“技能的学科”定位下,体现语文课程学科特征与内在要求的语文知识教学,要求学生在反复运用或长期使用中认识语文知识、掌握语文知识、使用语文知识,从而达到“练习愈多,成效愈大”[15]。三是提出了语文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设想。在《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文末,宋文瀚以“附录”形式集中列举了记叙文阅读法(题目与作者、旨趣、内容、时间、表现方法等程序性阅读知识),描写文阅读法(题目和作者、动机、对象、表现技巧等程序性阅读知识),说明文阅读法(题目和作者、思想方法的讨论、组织方面的讨论、说明方法等程序性阅读知识),论说文阅读法(题目和作者、思想方法讨论、组织方面讨论、辩论法讨论等程序性阅读知识),小说阅读法(小说篇名与作家、背景与结构、人物、格式、价值等程序性阅读知识)。[16]他总结出的文章、文学作品阅读理解的程序性知识,反映出这位虽不被后世熟知的语文教育家在语文课程本体论、知识观方面的精深研究与深刻见解。[17]
在推动语文知识体系建设中,夏丏尊更是作出了显著贡献。一是阐释了语文知识具有的核心地位与重要价值。夏丏尊认为“文字的内容是各个不同的,同是传记,因所传的人物而不同,同是评论,有关于政治的,有关于学术的……”[18],但从独立设科根本目的看,语文课程却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各各不同”文字在语言表达形式与方法上的相同性与规律性,“就整篇的文字说,有所谓章法、段落、结构等等的法则,就每一句话说,有所谓句子的构成及彼此结合的方式,就每句中所用的词儿说,也有各种的方法和习惯。”[19]在这里,整篇作品的章法、段落、结构等法则与无数句子的内部构成及彼此组合的方式以及对词汇使用的各种方法与习惯,就是我们常说的语文知识。对这些语文知识,夏丏尊指出:“这种都是形式上的情形,和文字的内容差不多无关。我以为在国文科里所应该学习的就是这些方面。”[20]就是说,作品的篇章结构、衔接过渡、首尾安排与语段安排、句式选择以及遣词用字等这些与“文字的内容差不多无关”的,才是体现语文表达形式使用规律的,即语文知识。二是强调了语文知识具有的启智育德等功能。夏丏尊认为,对语文知识的学习除可以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外,还具有开阔视野、充实精神、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等多重作用。对此种种功能,他阐释说:“他也许不能用古文来写作,却能看得懂普通的旧典籍;他不必一定会作诗、作赋、作词、作小说、作剧本,却能知道什么是诗、是赋、是词、是小说、是剧本,加以鉴赏……”[21]夏丏尊对语文知识众多功能的认识,对破除狭隘语文知识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有些语文知识虽属纯观念性的,但学生是否具有这些知识却对语文能力提高有着重要影响。[22]三是明确了语文课程以语文表达形式知识为本位的课程观。在肯定思想内容与表达形式相统一的基础上,夏丏尊主张要把对语文表达形式知识的学习与运用作为主责主业:“我们学习国文所当注重的,并不是事情、道理、东西或感情的本身,应该是各种表现方式和法则”,即“应该着眼在文字的形式上”[23]。正是在强调语文课程要以语言形式为本体,并在聚焦主体中来促使学生学习语文知识、把握运用语文知识,后世学者评价说,“他的形式观既有技道相融的充实之美,又有悦目愉情的自洽之美、主体力量的张扬之美”[24]。四是构建以文章读写为主体的语文知识体系。在《国文百八课》等教材中,夏丏尊与叶圣陶坚持文本(选)与语文知识的有机勾连与相互配合,较完整呈现出了文字知识、语言知识、语用知识、文体知识和文学知识等,反映出对语文知识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25]
此外,蒋伯潜、周谷城等也表达了各自对语文知识价值的真知灼见。其中蒋伯潜对当时一些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专门组织学生讨论“问题与主义”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就内容而论,则限于问题与主义;就教法而论,则完全偏重内容,忽略了文章底形式与技术”[26]。周谷城也对当时中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混淆词性、不讲句法、不分章节等现象予以批评,认为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就在于教师没有把国文课程看作是“文字技术的学科”,而是“把国文看成纯粹灌输学术思想的科目”,随之就“丧失了训练语言文字技术的效用”[27]。
综合来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语文知识价值认识与实践建构具有的重要课程意义有如下三方面。一是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有着较广泛共识。如就这一时期广受好评的《国文百八课》《开明国文讲义》等教材特别是专门普及语文知识的畅销书《文心》等来看,肯定语文知识能动作用是有着广泛社会共识的。二是建立起初步的语文知识课程体系。这一时期语文知识建设形成了包括文字(演变、语音及六书等)、文法(包括词性与词位、句式与段落、语体文法与文言文法等)、修辞(文章结构组织与体制、遣词方式与词格类别、藻词法和文体等)、文章(体裁与作法、辩论方式、证据与判断、反驳方法等)与文学史、辞书韵书等。客观看,这些知识虽大多为陈述性知识,但却为语文知识体系建设奠定了必要基础。三是语法知识还未成为语文知识的重点。与新中国成立后语文知识建设主要集中于语法领域有所不同,这一时期虽有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等著作出版,但这些语法研究成果(知识)被直接纳入语文课程内容却并不多。这说明,如何认识语法知识课程价值将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与解决的问题。四是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的认识事实上是与语文课程的学科定位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并使得语文知识课程价值显现。
三、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研究的学术考察
纵向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末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研究,可发现其有着两大发展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学者们对语文知识价值的积极阐发与构建;一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语文知识“有用论”与“无用论”的交锋对峙。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对语文知识建设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学者主要有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吴天石等众多知名学者,其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是“八字宪法”的明确提出。1962年,吴天石提出语文知识“就是字、 词、句、篇章,还有和文章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语法、 修辞、逻辑等基础知识”;同时“语法、修辞、逻辑是包含在文章中的,离开文章就谈不上语法、修辞、逻辑”[28]。这表明,吴天石在对语文表达形式作为语文课程本位判断基础上,对语文知识的基础地位与能动作用有着充分认识与肯定,并把语文知识与其他课程在对象内容方面区别了开来。吴天石对语文知识范围与对象的论述,随之就被概括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而成为语文教育的“八字宪法”,并使得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中明确要求语文教材应通过“编写成短文”形式,以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与掌握。[29]今天看来,这一教学大纲在坚持以语文表达形式为本位,使得“‘语文知识’和‘语文运用’”实现了统一[30],成为语文知识建设历程中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对语法知识作用的高度重视。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一时期对汉语语法研究与教学达到了空前高度。其中张志公从写作能力形成与提高角度,肯定了语法知识的积极作用:作文“要写得好,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在“很多条件之中”的一条“是起码的,就是要写得通顺、明白”。而“写作是否通顺、明白”,又主要决定于“词用得对不对”“次序摆得对不对”等。怎样实现词用得对、次序摆得对呢?其一“从多读、勤写之中,我们能够慢慢地摸到那些规矩”;其二是“在多读、勤写的同时再有系统地学学那些规矩,不光靠在读写之中去摸”。正是在此基础上,张志公就明确提出:“学习语法的用处就在这里,因为语法正是讲那些规矩的。”[31]这一论述表明,包括语法知识在内的语文知识是一客观存在,在语文课程中学习与掌握的语文知识实际上是人们对实有语文知识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对这些抽象与概括的规律予以认识与把握,就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语文运用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三是对语文知识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夏丏尊的认识一样,吕叔湘也指出:“语文知识中的词汇、语法和修辞,都能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譬如比较同义词、近义词的不同点,可以提高学生的辨别能力、分析能力;语法中的句法,特别是复杂的句子,如何去分析清楚,也可以培养思维能力。”[32]正是在此认识基础上,吕叔湘就明确反对取消语文知识:“有的教师认为语文知识对写作没有作用,主张取消。这只能说明过去我们讲语文知识的时候,照顾系统性多了点,照顾实用不够,决不能说明语文知识对培养学生的读写能力无用。”[33]这就深刻阐明了语文知识不存在有用无用问题,而只是在传授与训练时存在着科学性、实用性强不强的问题。四是对语文知识的具体建构。张传宗在阐释应以语言作为语文课程本位时,以初中说明文教学为例来阐述为何要进行语文知识教学、如何进行语文知识教学:初一年级应在小学基础上,“主要学会语言的通顺”,初二年级应“主要学会不同性质和表达作用的语言”,初三年级应“主要学习语言的优美”[34]。从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相结合角度,对初中三个年级说明文的语文知识有着系统设计,反映出论者对语文知识体系的深刻把握。
与肯定语文知识价值与重视语文知识学习观点相反,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语文知识“无用论”开始登场。在语文知识“无用论”者看来,由于语文课程基本取向不是引导学生研究语言而是学习语言,因而就不应把注意力过多放在语文知识传授上,甚至可直接取消语文知识教学。与之相似,语感论者也认为语文教学应重点培养学生语感,而不是对语文知识的学习与掌握。[35]自然,由于语文知识特别是语法知识在学习训练中存在机械训练等问题,再加之语法体系自身也存在不尽完善及学派林立现状,也有学者就极力主张“淡化语法”[36]。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出现的语文知识“有用论”与“无用论”相互对峙,我们应看到:第一,不论语文知识是“有用”还是“无用”,事实上都与论者对语文课程本位观、性质观等问题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从语文课程根本性质、基本目标出发,“有用论”者必然就要突出语文知识的价值功能并主张促进知识与能力的融合。第二,持有语文知识“有用论”的学者主要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众多知名学者,这与“无用论”者多系“临时研究”或只对语文课程有着感性认识的学者明显不同,这需引起后人深思。第三,在20世纪末出现的“语文教育世纪大讨论”影响下,语文知识“无用论”曾一度时间占据了上风,并直接影响到21世纪拉开帷幕的语文新课程改革。
四、新课程改革以来语文知识课程价值研究的学术考察
考察21世纪的语文知识学术研究流变史,即可发现,语文知识“有用论”与“无用论”在对峙明显态势下,呈现出从“无用论”占据上风再到“有用论”占据上风这一演变轨迹,即从世纪之初明确提出淡化语文知识而使得语文教材较少有语文知识编排,到最新“部编本”语文教材中语言知识表现出“回暖”趋势。[37]
20世纪末在由文学刊物发起且主要由文学研究者、社会工作者主导,而语言学家、语文教育者基本失声的“语文教育世纪大讨论”影响下,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在一度时间内受到极大质疑,“双基训练”被严厉批判。在此背景之下,语文知识“无用论”者全面展开了对“有用论”者的批判。一是从语文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不同出发,有学者认为传统语文课程在关注理性知识时,使得对文本的学习异化成为肢解课文、证明语文知识客观存在的过程,其结果近期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的丧失,远期则是学生人文底蕴的流失。[38]二是从语文知识点多面广的分散性、复杂性等特征出发,有学者提出语文知识系统要实现系统建构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淡化就成为一种发展必然。[39]三是从语文教材编写出发,有学者主张语文程序性知识不宜过多地进入到教材内容体系中。[40]
同时,针对人文性质观、语文知识“无用论”等观点导致的“泛人文性”“泛文化性”等倾向,不少语文学者坚决维护语文知识“有用论”,并对其价值与实现等问题进行了新探索、新阐释。首先,对“去知识化”现象的批判。李海林对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去知识化”七种“自我放逐”现象进行归纳与批判的基础上,认为在对旧有语文知识系统的批判中,却“并不必然地导致‘语文课不学知识’‘语文课不需要知识’的命题”的出现。[41]这是睿智之见,因为反思或批判旧有语文知识体系与传授方式,实际上应更多考虑的是学习哪些新知识、采取哪些新方式,而不是不要语文知识传递与训练的问题。其次,对“三老”语文知识观的维护与发展。针对一些学者对“三老”语文课程性质观与知识观的简单指责与粗暴批判,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维护与发展。如有学者认为叶圣陶语文知识观的基本点表现在三方面:“学‘活知识’”,“‘活学’知识”与“‘教活’知识”[42]。笔者也对张志公语文知识课程价值观的当代意义进行了阐发[43], 并以张志公对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内在关系论述为基础,对这一重要课程问题的处理进行了“再论”[44]。再次,对语文知识研究视域的新开拓。其中刘大为分析论证了“语识”知识概念[45],韩雪屏对语文课程的知识内容有着系统论述[46],王荣生对语文知识从宏观认识到微观建设都提出了不少独特之见[47]。这些新探索,对深化语文知识价值认识与现实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最后,对加快建构语文知识体系的新探索。在近年研究中,语文知识“无用论”趋于偃旗息鼓,代之而起的是怎样建设语文知识体系的问题。对此,学者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面对种类庞杂、数量庞大的语文知识,必须从有利于促进听说读写能力形成与提高的高度来精挑细选与优化组合,即韩雪屏强调的应在廓清语文基础知识范围、层次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有适当难度和有组织的语文知识。[48]为此,近年来不少学者基于言语、语用等多个视角探讨了语文知识体系建设问题,如朱于国、姜向荣提出了建设语文课程知识谱系的基本设想[49],反映出语文知识建设的新成就。
从语文独立设科后的语文知识学术历史流变中,我们即可发现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与价值实现有着不少共识,这对我们以深刻启迪。第一,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的核心要素。从民国初期徐特立、姚铭恩等的论述看,肯定语文知识课程价值并予以积极建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如有些学者认为这一问题出现于民国中期后或出现于新中国成立后或出现于改革开放后。语文知识问题实际上是语文课程在独立设科之后就随之出现的一核心问题。这就充分说明,语文知识作为语文课程安身立命之根本,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且成为语文学者必须面对、要解说、要解决的重大课程认识与实践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在语文课程研究中主张搁置起来或认为性质问题只是“皇帝的新装”的假命题或伪问题等观点[50],就需要重新加以讨论。第二,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的关键问题。从前文中可看出,肯定语文知识具有积极课程价值并予以实践转化是曲折向前的学术“主流”,主张淡化乃至取消语文知识的观点则是“支流”。这说明,如没有必须与必要的语文知识进入到语文课程内容体系之中,这门课程就实难作为一门学科课程而真正“独立存在”。肯定语文知识建设在语文课程建设中的关键性作用,又是与语文课程要坚持以语言文字为本位,并使课程目标任务主要集中于语言形式方面的认识密切相关的。对此可直接提供佐证的就是持工具性质观的学者,大多都肯定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而持非工具性质观的学者,大多否定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此中缘由,即叶圣陶指出的“文法告诉我们语言的习惯,使我们知道如何是合式,如何是不合式。修辞学告诉我们运用语言的方式,使我们知道如何是有效,如何便没有效”[51]。第三,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行为取向的具体体现。基于语文课程重在使学生学习掌握语文使用而不重在认识语文这一基本判断,不少学者对语文知识课程价值实现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必须以有用与能用、好用为语文知识的建设方向与实施准则。这也就是叶圣陶强调自己不太赞同“语文知识”这一概念,因为“把语法、逻辑、修辞之类称作‘知识’,好像只要讲得出来就行,容易忽略实际运用”。但由于“现在大家既然用惯了‘知识’这个词,那么就得把这个词的意义扩大,把能力也包括在内”[52]。先贤的这一论述,实则极清晰地表明语文知识课程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在于要指向于语文知识的实际运用,并服务于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与提高。而要促进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实际运用,显然就需要在对语文这一“工具”的反复历练中来认识和掌握这一工具。第四,语文知识是语文学者共同关注的重大课程问题,应在百年学术流变中高度评价以“三老”为代表的语文先贤作出的开创性贡献。由于传统语文教育长时期存在着“对知识的忽视”现象[53],并影响到语文课程实施,因而就成为这门课程实质性建设中的重要任务。正因如此,从民国时起为改变“国文课用现成教科书的少,多数是教师自己选文章,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只有白文(而且都是古文),没有注释,更没有附加的语文知识”[54]现状,以徐特立、夏丏尊等先贤特别是以“三老”为代表,开始了对语文知识体系建设的不懈努力。今天看来,已有语文知识体系虽存在着有待商榷与有待完善之处,但其基本原则、主要方向却是需要充分肯定的。要看到,正是在语文知识的实质性建设中,才使得语文课程的工具属性、工具目标得以突显,这是由于“只有把语文课程视为一门指向于引导学生学习认识、掌握运用语文或语文形式这一‘技能的学科’基础上,才能在课程根本对象的选择与确立中将其与其他课程区别开来”[55]。第五,语文知识价值认识与价值实现有着曲折复杂的学术流变,影响和制约着语文课程建设步伐。有学者从百年语文教材中语文知识编排情况发现,语文知识在教材编排中呈现出“有无、繁简、多少”的波浪曲线变化。[56]要看到,这种“波浪曲线变化”实际上也历史或现实地表现在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与语文课堂教学之中,同时也历史或现实地表现在语文知识的学术研究之中。可能正因为如此,在语文知识学术研究的百年流变中就存在这一现象:越是学养深厚的著名语文学者,就越加重视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并积极致力于实践建构;越是初涉这门学科领域的年青学者与教师,却愈加表现出“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忽视轻视语文知识的课程价值。第六,语文知识的科学化建设依然面临着艰巨任务。从语文知识百年学术流变中可看出,虽然对这一重要课程问题在认识上求得共识面临着明显挑战,但更大挑战还在于语文知识的实践构建上。因为我们面对与破解的是这一复杂局面:“汉字恒有之,语言要素恒难之;语文技能恒有之,语文知识恒难之;点滴语文知识可有之,系统语文知识恒难之;争论起伏恒有之,求而同之恒难之。”[57]以此观之,现阶段以学习任务群来促进语文知识的传递与训练,已成为重要途径与具体抓手。[58]但学习任务群在有助于促进语文知识向语文能力转化之时,也存在着语文知识学习系统性、层级性不够等问题。这表明,在百年语文知识建设学术探索基础上,要真正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还需与明确语文课程性质、课程目标任务等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并探索如何统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