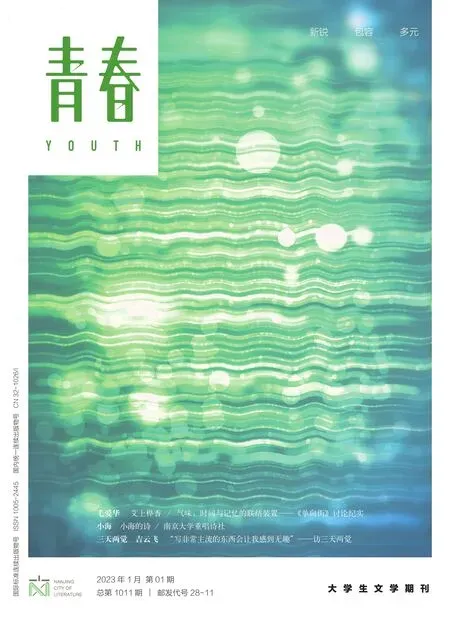水仙宫前
2023-02-22苏州大学张煜棪
苏州大学 张煜棪
小姑在黑堂屋里点蚊香的时候,合璧从阳台上转身来看,文竹长野了,满地罗网,照得幽旺,引来的火被一口吹灭,她的手背上才生出第一块红色的瘙痒。她听着昆虫翅膀扑簌簌坠入影里而后翕动的声响,把自己挠肿了,皮肉上爬出一道道白屑子,蚊香的白烟也就攀上来了,在不远处黑洞洞地兴灭。
合璧忍着痒,捂住左耳,大地上的虫翅升起,死气殆去了,她用右耳回溯,听到了虫鸣满室。她唯一能肯定的是,暗处有什么动人心魄的东西。合璧渐渐看到了花盆的一角,三两片前朝青瓦浮在水中,叠出了一只小船,文竹就从黑水河似的地方探出来,洇开一摊潮绿。她突然想到高考第一天的早上,起了一点雾,太阳破开的时候,语文卷子刚发下来,白亮一片,看不清字,就听到一对鸟儿飞来,互相啄颈,影子映在她的考卷上,逐头衔尾,一阴一阳缠出两条鱼。
也就是那时候,合璧好像听到哥哥不见了,那天是五月初五。大人们夜游行船,遥遥重重地嘱咐小姑在岸上看好一群孩子。小姑自己也是孩子,却有做长辈的架势,立在满树大红灯笼下,电影明星似的轻轻挥手点头,身后龙威狮影,舞个不停,她一张东方面孔在香灰里淡淡拂动。直到班里传闻成绩平平的小姑上了北大,合璧才肯相信小姑真是美国人。顾香侬实为Shannon Koo,特意拼成这样,因为广东华侨听上去正宗地道些。当年小姑的父亲留洋回来,带着与合璧一般大的顾香侬认祖归宗,说她母亲是血脉纯正的白人女子,名字翻译过来,中间是有一点的。合璧记不住是露西还是琳达,不过每回中央六套播译制片,她就鲜嘎嘎地拉着人胡说,这是我小姑她妈妈,讲话时舌头会卷的。可顾香侬生了一张中国人的脸。洋孩子不信水鬼,但被大人一讲,心中也要毛毛的,于是隐入舞龙舞狮的人群里,心中“abandon abandon”(放弃)地来回念,仿佛护身神咒,邪不侵体。
哥哥要去河边看龙舟,合璧怕闹,天上的锣鼓太吵了,夏虫不停叫,便捂住耳朵躲到一棵老柳树下,发现树根围出一汪水,红烛花下黑亮,有两条金鱼在里头游来游去,婴孩脚掌大,肥幼骇人。她趴着看了好久,胳膊腿都是泥,呼呼哇哇地惊叹,忽而想到哥哥说过的一个故事。他们的某位先祖是唐高宗的后妃,一位姓聂的娘娘,在正史上并无记载,却被厚葬在一座叫水仙宫的宫观之中。两个盗墓贼不知怎么就发现了水仙宫,一打开古墓,就被一缕烟迷了眼,费了好大劲,总算是摸瞎升了棺,却只见两条金鱼在手电筒的光束里游。故事到了这里,哥哥刹住,任凭她怎么缠闹都不讲了,毕竟故弄玄虚这种特权,在讲故事以外的地方很少能用得上。现在她用一双泥花花的小手虚虚地拢住了这两条金鱼,相信了一切讲不完的故事都是真的,鱼尾巴拍起的水打在脸上,也不敢碰,怕化出一个血窟窿,有数不尽的盗墓贼举着手电筒钻出来,五官七窍金光乱撞。
小姑来喊她一起找人的时候,一条金鱼忽然不动了,就这么浅浅一捧水,它竟无限地下沉,惊得合璧跳起来,撞落了柳枝上挂的红纸,水潭被一口封住。小姑急道,不要玩了,你哥哥不见了,大家都在找。见合璧还在捞那张红纸,一声不吭,顾香侬揪住她的肩膀,狠狠掰过来,用两只巴掌牢牢箍住她的脸,又说了一遍,你哥哥不见了。合璧被唬住了,看着小姑的红嘴唇开合,中国人的嘴,洋人的唾沫,许久不喝水也会有一股苦腥气吗?直到小姑重复了三四遍,在她脑门上拍了一记,合璧才醒过来,哆嗦半天,哭着说她的右耳听不见了。顾香侬也愣住了,但很快就一把放开她,不争气的东西,转身朝河边跑去。
合璧哭着在树根下刨,哪有什么金鱼,只剩一捧死水,红纸上的字糊了,李×萍和吴××的姻缘也泡烂了。她的右耳里开始有了响动,满天烟火,道士唱念,水里有人叫她的名字,金鱼在黑亮的水里翻涌,顾香侬告诉她,你哥哥不见了。
那晚河面上漂了几张粽叶,灯笼纸破了,龙舟湿漉漉散在岸上,船洞挂了些黑魆魆的藻,团团散散,像水鬼的脚印。她的左耳听到大人们喊着哥哥的名字,大名小名,一直喊,一直喊,叫魂一样,到后来,她的右耳也听到了哥哥的名字,陌生得不知道是谁。
天快亮的时候,一家人赶去吴江,找那个老阿爹。老人家被敲门吵醒,不大痛快,听了来事就开始犯难,但遭不住哀求,也只好请他们进来。
合璧听不清,捂住右耳问,哥哥能找得回来吗?
高考那天,合璧试卷上现出的鱼影,让她想到连同李×萍和吴××的姻缘一起消失的那两条金鱼,还有远在天上又或深在地下的先祖。她放下笔,向先祖发愿,如果哥哥能回来,我考不上大学也可以。
她想聂娘娘已然听到了她的心愿。
高考失利后,她右耳的癔症严重了,只能听到一个小时前的事,偶尔会听到顾香侬在北方的湖边“abandon abandon”地念,感到鬼气缠身。家里人不晓得她的心事,要她好好休养,再复读备考。有时她觉得他们不是不懂,是不肯承认她的思念,让它沦为一种衰败演绎。一旦后代有了过于精密的自我,那种幽微的、阴燃的、包罗万象的能量,使活人也有一股恐怖谷的味道。婆婆要带她去找老阿爹看虚病,疫情过去不方便,电话打过去,是他女儿接的,连衣钵一同接了,这下才晓得,那天早上他们前脚刚走,老阿爹就坐在阴阳鱼下没了,手肘撑在开关上,那盏小灯就在暗屋中一直跳。
合璧背靠着阳台的栏杆,有时希望它松动,人就会像金鱼凭空沉入黑洞一样坠落。她眼看着蚊香的白烟从文竹背后攀上来,笼住整间屋子,像要来抱住她,还有她的全部命运。
她忽然记起文竹的花盆是哥哥搭的,光脚翻去邻居家偷青瓦,被拎了半天耳朵。他想种的其实是垂丝茉莉,春日里,太阳要上来的时候,帘幕留一点缝,青瓦船上就垂下星星点点的玉坠子,哥哥说这叫“满船清梦压星河”,而合璧高中快毕业了才知道,作者并不是唐朝一位叫温如的女诗人。可惜当年等到春分,两人才发现落错了种,那时顾香侬回国了,借住的老屋要完璧归赵,两人将错就错,也没有重种。五月初五哥哥走后,顾香侬的父亲难以面对他们,虽然顾香侬也是孩子,到底算是长辈,没有把人看好。合璧的母亲说,家里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了,要让合璧读个好初中,房子虽老,却是好学区,你看,离高中也不大远。顾香侬的父亲心中明了,都是顾家人,房子仍借给他们住,直到合璧高中毕业,只是香侬也要嫁妆的,一来二去,商量着把合璧的户口迁过来。
顾香侬与顾合璧已经很久不说话了,到了人人恨不得将元宇宙塞进口袋、脱口而出的年代,她们是两团最远的星云,避之不及,仿佛永远留在五月初五那夜,各自隐入龙腾狮影背后,两张东方面孔在飞尘、烟火、香灰的风眼里念念有词,“abandon abandon”地念,又舍不得抛离,磐石一样死死对着,直到古河水也改道。等到要处理中国籍身份名下的房产时,顾香侬装作才想起合璧,南下了这一趟。疫情出境不便,六个月的期限一到,两本护照的人就浮出了水面。法理上,顾香侬不过一缕幽魂,Shannon Koo 才是堂堂正正的活人。等过户办完,她又要北上回京,要对着国旗承认顾香侬这一身份的瓦解,于是她买过的票、看过的戏、吃过的饭、开过的路都成了野史与幻影。香侬当然舍不得自己消失,但她更舍不得外宾的便利。
下午合璧从方医生那儿回来,取道三元坊,绕回书院巷,买了中学时两人常吃的蛋饼,塌了许多甜酱,算作示好,结果先是未想到顾香侬要控糖,后又不曾料到医院有人确诊,合璧一下子变作密接,两人齐齐隔离在这老屋里,硬是碰在一起,要挨过四十八小时。顾香侬一进门,就看见了这盆文竹,摆在老屋的天元,无人打理,却长满四野。她莫名其妙找话说,天时地利的景物,不合时宜地卖弄,她说文竹的花语是eternity,怕合璧听不懂似的,又补了一句,就是永恒。Shannon Koo 已不再被困于abandon,开始想eternity,合璧心下笑了笑,竟有种获胜的凄凉,上了北大就是不一样,单词终于从A 背到了E。
当时这盆文竹还没有夜晚那股慑服人心的力量,顾香侬躲着碎枝丫走了两圈,直跺脚,好不容易满抽屉翻出一盘蚊香,外缘一圈幽碧的霉点,太阳下山时被映成一只翠玉镯。她一边掰一边说,才三月,蚊子就多得嘞,叮得人手脚痒。一听到她的乡音,合璧又看到了那只夜光游水母。
合璧往阳台走,不知道外面封得如何了,右耳边始终有人讲话,咳嗽的、掩饰咳嗽的、忍住咳嗽的,心跳乖乖起伏,捂住就消散了去,而左耳则听见护城河两岸的早樱摇落,河面上浮了一层香膏腻脂,吞吐着北寺塔的金影。一片花瓣落在塔尖,天就暗了,灯罩下是清淡的雾,合璧忽感到自己就跟这北寺塔一样,一半在高墙中立住,一半做了影子沉入水底。她回头看到顾香侬蹲在文竹影里,点起了蚊香,她的控糖是有效果的,鹅黄色一条细弯弯的月亮,风动中隐现,如经幡挂在猛洞河上,在满地昆虫翅膀之间,不晓得是哪朝哪代的回魂夜。
合璧的心被黏住了,原来此生所有的念想、胡想、肖想、狂想、非分之想、应分之想、无稽之想、滑稽之想,不论在何时何地打开无穷尽的一扇扇门,都会像蚊香的白烟一样,顺着文竹的碧绿经脉,又将一道道地回到这间老堂屋里厢来。
活人的一生就是鬼打墙。
顾香侬摸黑进去洗澡,也不开灯,浴室的水声黑洞洞地砸,天罗地网,合璧的右耳成夜地听着这水声乱弹,像金鱼尾巴的水甩在脸上,满身都是擦不掉的红疹子。
春分后的第一天,天亮就早了一点,蚊香烧完了,合璧闻到了春天的闷青味,躺不住,就爬起来了。因为熬了整夜不敢翻身,腰背痛了好久,全身麻滋滋地痒。顾香侬还在睡,合璧昨夜好像听见她在做梦,分不清是哪只耳朵听到的,又或是她自己在做梦。她在床边歪了会儿,手机推送了新闻,古城区早上新增一例阳性确诊,胡某,男,25 岁。她还来不及心跳,堆了整夜没看的微信又响了起来。
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朋友们转身回到各自的日常。她悄悄把新闻又翻出来看,胡某,男,25 岁,流调后,活动轨迹整理如下:……
方士医生的周日下午被分成两半,一点半到三点半是胡某的时间,三点半到五点半是合璧的时间。合璧从未见过胡某,却与他隔空说过许多话。方医生的号不好挂,托关系都排不上队,但到了她这里,这段时间正好就空了出来。那位患者的故事不谈,她的离奇康复一口气成全了两个奇迹,合璧的阿婆由衷感激。问诊室里摆了一座盆景,精雕细琢的一株蓬莱松,就是人们讲起工笔花鸟会最先想起的那种姿态。有次讲着讲着,她忽然发现多了一道影子,幽弱青绿,是蓬莱松还未被剪去的新枝叶,映得方士写着隐疾暗梦的档案本如一面金褐色的屏风。原来一切竟是真的,只是出走的每一步都被精准地还原归零。她再来的时候,惊觉自己的秘密被勘破了,影子已不在了。钱换时间的地方讲求秩序,活物、死物、人物、器物、玩物、景物、文物都不许撒野。
第一次在方医生对面坐下,合璧兜了好久的天气晴朗,其余的讲不出口,只好盯着那盆蓬莱松,直到想起沉默都是计费的,硬掏也要掏点什么出来讲讲。她想到远方有战事,却不晓得打到什么地步了,好像那股惴惴不安的感觉过去了,倾城之恋变得不合时宜,蝴蝶翅膀扇得再凶,日常生活也不得不发生。兴许是讲到了外国的事情,她想起了同学们刚知道顾香侬是Shannon Koo 的那阵子,真从一张汉人脸上看出点洋味儿来了。女生们默契地轮流找Shannon 上厕所、谈心事,暗暗攀比。合璧觉得她们都病了,教语文的黄老师也病了。黄老师很清高,有儒雅的老做派,爱写竖排繁体板书。可是只有合璧记得,开学第一天点名,一个同学名字生僻,他念了姓便读不出来,就背着手“啊”了一声,垂眼会心的模样,说其实父母不该给孩子取太难读的名字,有如此这般的不妙,转而介绍自己怎么从《辞海》里给女儿翻出了“小茶”二字,起得太好了。黄老师从不批评人,然而心中有铁律般的亲疏,顾香侬人凭籍贵,自然被收编做了爱徒,得以登上每次考试的优秀作文集锦,被他评点作序、广为传颂。同样是写,香侬们写是现实主义,合璧们写是毫无新意;香侬们写是破而后立,合璧们写是离经叛道;香侬们写的叫作诗一般的论文,合璧们写的则是不懂学术规范。好事占尽的香侬们还打出了“缓慢写作”的旗号,集锦要出得慢一些,可那本集锦哪有别的快慢挤得进去。那回平均分特别高,黄老师将其归功于此,普通人与自己创造的历史变得无关。
讲到这里,合璧突然滞住了,似乎想起什么,方医生只当她意犹未尽又时间感太好,知道这回就到这儿了,但少女的身体端坐,郑重地道,方医生,我有个不情之请。这个词一旦用上了,就到了必讲无疑的地步,好像押上身家性命来考验对方的体面。方士惶恐,仍请她放心说。她问,为了前一位病人的隐私,我能不能和他的时间对调。方士突然笑了,在椅子上动了动,又强坐定,反问她为什么。她说,我的右耳能听到他在这里说过的话。方士翻开那本金屏风一样的档案本,只有几页对折成了两半。她循着方士的食指,看到病人信息那一栏,“胡是,男,25 周岁”,下面是他本人签字的一封极短的授权书,紧接着是大段大段默好的独白,与合璧今日所言丝毫不差,最末写着——
我的左耳能听到你在这里要说的话。普通人与自己创造的历史怎么会无关呢?我们的一切基于一种共时性。
当晚合璧一沾枕头就睡熟了,梦到自己睡在黑水下,有位仙人来到她身边,看不清脸,白衣带在她面上飘拂。
仙人推醒她,两人一起循声往上看,原来在水面之上,日夜下着端午这天的雨水。履舄交错,把水花踩成五月初五的烟火。趿金齿屐踩过水塘的人,踏踏响,走在夏日青山间,又在脚底下画了流云样,用鎏金铜齿钉住离散的团云,屐头也偷偷彩绘了凤头,屏住脚趾的时候看不见,但走起路来,翎羽凌风扶摇,人将要腾入云中去。只是盯住这双大脚琢磨一阵,好奇怪,果然是个士人想学女子穿凤头鞋,庭中过把瘾。走累了,人往丝瓜藤上搭一把手,看远处的塔寺,如环形气泡。穿赤舄的,在深宫看梅老去,烘手待煮茶。有喜延唐制的,白蕉衫下短靴一双,临窗切井水冰镇过的熟瓜。至于那些皮的、布的、丝的金莲们,在纱帐间消暑,人在气泡外欢喜地融化,有一些听闻而后悄悄化用的情结,取来妆镜不看,想象扰扰绿云从摘下的钗钏里滑淌出来,如两丛荔枝叶散落一般。
第二回她在蓬莱松边一坐下,就有种放任坠落的轻快,想到幼时窗前那一大排天门冬,哥哥常躲在阴头里讲故事,燥了就掰一些天门冬,去了心煮水喝,两个人一起呸呸呸地吐舌头。方士依二人许可,将两份档案合二为一:胡是,男,25 周岁;顾合璧,女,19 周岁。活像一块墓碑。在胡是的半块时间里,他听还未到场的合璧说故事,方士一一写下他的提问与回应,记在左边,在合璧的半块时间里,她又和早已离场的胡是谈心,由方士尽数补在右半页。方医生说话的机会不多,分上下两场才能听完整本,专业意见倒显得像朱批,浮在一边,后来几乎不表。
合璧问胡是,左耳能听到未来是不是很“方便”?
胡是说,不听生死,不听赌彩。
胡是问合璧,右耳能听到过去是什么感觉?
合璧说,听得了生死,听不成赌彩——又问他,你能听到多远的未来?
胡是说,海枯石烂。
她没料到是这样俗气的答案。
但他又说,海真的会枯,石真的会烂,你能想象那种分贝并不是零的死寂吗?一切分子或是原子之类的东西,都陷入无序逃离,到了我耳朵里,是已经成为流亡史的被游历过的未来。
合璧惊叹,是经常有人会这么问你吗?你都排练好了这个回答。
胡是说,因为我比你更早听到了你的心声。
方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合璧静默了一会儿,忽然闷闷地问,那是你先听到了我,还是我先听到了你呢?
胡是说,一旦思考这个问题,就纠缠不清了,你知道暗物质吗?我觉得那就是生物体思考时的能量,但当人去思考它的时候,它就被介入,成了不能思考的对象——人永远无法思考外物;思考可以参与,但不能抽身事外。
合璧无奈,一听就知道,我们说话仿佛两种文体。
胡是笑笑,突然问,你能听到多久的过去呢?
合璧说,我不知道这是我听到的,还是“听”到的——有一个双引号,你知道吗?
胡是说,我知道。
合璧说,小时候哥哥告诉我,我们有一位先祖姓聂,是唐高宗的才人,在正史上是没有她的名字的,却连武则天都很敬重她。因为她除了早上的几个时辰醒着,其他时候一直在做梦。有时候,她告诉侍女,她梦中飞到外面做侠女,每天阳神出体,从大明宫里偷一块砖,一直衔着飞回家乡,十几年下来,她就造出了一座水仙宫。不知哪一年,天花病传了进来,家家闭户,得了天花病的人,都躲进了水仙宫,直到有人发现墙砖上竟有皇家标记,层层上报,事情才败露,于是聂才人就说出了实情。古人在传说中通常都很单纯的,或者说接受度太高了,大家轻而易举地全信了。聂才人说,事到如今,只有把我自己变成砖还给你们了,说罢就断了气。传说李治和武则天都亲眼见到聂才人咽了气,衣服瞬间空瘪了,从下摆滑出了两条金鱼,在地上干游了一会儿,就变成一块砖,上面刻着一条阴阳鱼。也是传说,李治和武后都大为震撼,派人千里迢迢将这块砖送回了聂才人的故乡,添进了水仙宫中,又兴建地宫,为聂才人留了一座衣冠冢。
胡是问,那水仙宫现在何处?
合璧说,找不到了,我哥哥说,有两个盗墓贼根据传说的线索找到了水仙宫,捞了点金银财宝去了南洋,后来好像辗转又去旧金山淘金了。我怎么记得这么清?
合璧感到外物层层剥落,脆生生地塌陷,重重叠叠听不到尽头,她等着,可她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哥哥,她应当铺张地讲讲五月初五的夜晚,讲那晚被锣鼓淹没的呼救,讲柳树下沉入水底消失的一条金鱼,讲她如何从中理解到自己的破碎,还有她不能自成一块合璧。她要告诉胡是,哥哥被带走了。于是胡是就应当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找我?她就会等在那个节点,告诉他,所有人都在想他,每一天都在想他,而她还从未体会过被人思念的感觉,该轮到她了吧,她已受足了惩罚。
可胡是没有再问下去。
方士从蓬莱松后递来一张纸巾,合璧抬头,从未见过这种神态,好像丹炉上缠了三尺白绫,方士解释,他是照胡是说的,掐准时间这样做的,她那一点可怜的眼泪就咽了回去。
合璧与胡是约好,下周要见一面,胡是想听她说水仙宫的故事,盗墓贼在墓里看到了什么,结果一个到早了,一个留晚了,仿佛化作彼此弦动的残余。胡是不听小我生死,没有躲过自己的疾病,却成全了她。合璧的右耳是无尽悼亡,每日忙着面对消亡,对真正的废墟视而不见,她不要听什么宇宙中的星尘聚散,世俗肉身才是浓艳壮烈的,世上没有比同一个基站、同一种疾病、同一份文件更铁证如山的亲密了,总要有什么一碰天就要塌下来的东西,才能圆满他们的秘密,昭告他们是天生一块合璧。
老堂屋的蚊香散尽了,她痒到心肺里去,找出一盘新的来,学着顾香侬掰去一圈霉点,看它们散在地上,在日光下颤巍巍地泛翠。点上的时候,烟香迷了眼,火光乱摇,让合璧记起好多年前,哥哥爱看武侠小说,成天琢磨掌中虚气,她悄悄吹灭蜡烛,让他误以为自己真的得了,哥哥还给她传授经验,你成不了是因为你总想让火灭了,要想象周围那看不见的无所不在的东西,覆盖了它,不是它灭了,它一直在,只是人看不见了。她就笑着鼓掌。
她吹灭火星子,想着这一点罪过也能被一并原谅吧。
不多时,白烟又把老堂屋笼住了,只有一缕烟始终不散,昏昏绕绕地被勾入顾香侬的卧室,仿佛晚清绣像插画中的仙宫。合璧循着烟路摸进去,房内不见太阳,白烟逃进来,才有了一些光,像月色收敛,覆成雪霜,清亮无形,如远山笛鼓。在烟雾中,合璧看到顾香侬婴儿般蜷着身子,在暗红的褥子里熟睡,呼吸起落都成了房子的节律,宛若一颗跳动的黑暗之心,迷信着夜晚歌谣的力量。她趴在床前,端详这张东方面孔的酣眠,已整整一天一夜了,似乎房子里就是这么古怪,分好阴阳,有人睡不着,就有人睡不醒,分不清是die down(消亡)和骀荡。合璧拢住左耳,好像有人说话,是顾香侬说了整夜的梦话,说着在妈妈子宫里一片柔红色的光。
妈妈要告诉你什么叫史诗,你的祖先来自古老而遥远的东方,在来到旧金山之前,他们是一对夫妻,也是探险家,爬过昆仑建木,见过秦岭妖瘴,最险的一回,你可能想不到,是误入了一座唐朝娘娘的墓穴,两人九死一生逃了出来,结果掉进了河里,变成了两条金鱼,一直游,一直游,游到了南洋,又花了好多年,才变回了人。
顾香侬忽然翻了个身,惊得合璧放下了捂耳朵的手,一下就听到了她要醒的嗡哝。白烟覆住了顾香侬的梦,合璧知道她真要醒了,不知哪里藏身,情急之下爬进了床底,像沉入黑水河。她听到顾香侬坐了起来,趿上鞋,推了一条门缝,白烟和绿影也就流入了床下。她左右探看,发现眼前的墙皮破了,露出一块砖,砖身画着一条阴阳鱼,逐头衔尾,她忍不住摸了摸,两条金鱼就落入了合璧的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