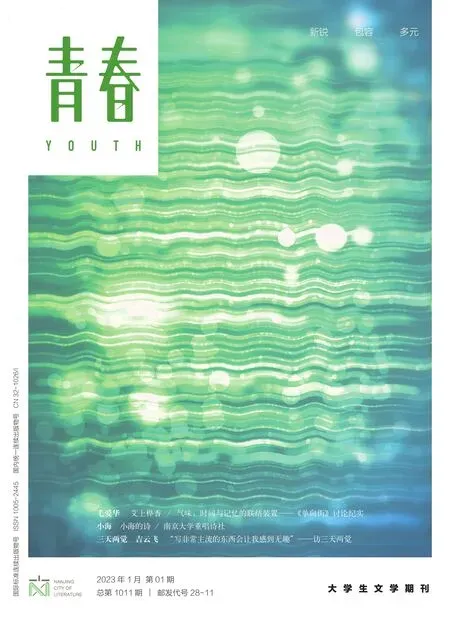小青鸟
2023-02-22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黄靓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黄靓
一个深夜,我从梦中醒来,床前泊着月光,如银色的海,而惘然的心是一叶小舟,在旷阔之上漫无边际地漂游。过去的十九年,我浑浑噩噩生长,吃不够,睡不够,从未有过这样的静夜思。
这是入学的第二周,军训接近尾声,正课即将开始,新人新事奔涌叠加,时间的每一处罅隙都跃动着欣喜,而与此同时,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也在暗自生长。起初没人肯承认自己想家。怎么可能想家呢?自由、鲜活、未知,正是摆脱高考重压的我们所渴望的生活。怎么可能想家呢?
每晚的睡前神聊,从八卦教官、比较社团、讨论不同专业、赞美或吐槽食堂饭菜,逐渐转移到讲解各自的家乡及过往,并在此话题流连不去。宿舍六个人,小潘是苏北本地人,悦悦和我分属苏南、苏中,其他三人则分别来自云南、山东和西藏,因此宿舍微信群名为“祖国大好河山”。女生们的想法千奇百怪,难得一致,只在一点获得共鸣,就是离家之后,渐渐对“家”有了清晰的概念。
“我的家乡是个县城,老,旧,但不邋遢。一年四季鲜花盛开,游客不多也不少,日子很安逸。”段亦尘是哈尼族,人长得黑而瘦,声音却很沉静,像萦绕在明月周围的彩云,又像雨林中不断冒出的菌菇。我们躺在黑暗里,听她描绘远在滇南的建水。小火车缓缓穿行,山上长满绿油油的茶树,清风送来古塔的铃声,精巧的洋房映衬着厚重的合院。老街经过修旧如旧的维护,古朴与时尚并存,银匠埋头打造花样繁复的饰品,凿着,锤着,拉丝,绕圈,掐花,仿佛在细细地雕琢时光。
有舍友和我一样,跟随旅行团去过云南的“昆大丽香”,在走马观花的游览中,建水是个可有可无的景点。段亦尘从小到大未出过小城,却认定那是世上最好的地方。我们笑她是井底之蛙,她不为所动,在她看来,没有比天空的颜色、风的温度、水的声音,还有花开草长更重要的事了。
思乡的魔盒就此打开。徐娇讲烟台的晚上,是铿锵爽利的快板专场。她家是种植大户,课余时间她基本都在农场干活,骑三轮车,开拖拉机,摘苹果,种白菜,捆大葱,施肥,打扫鸡兔窝棚,什么都干,除此之外还常跟村里的武师练拳脚。
与好说好动的山东小嫚不同,悦悦是典型的江南美人,苍白柔弱,窗帘上的蜘蛛都有可能引发一场晕厥。她们那里教育内卷严重,她从幼儿园开始即在各类辅导班中奔走,考试成绩从未低于年级前十,钢琴、舞蹈拿到最高级位,围棋、外语也多次获奖,代价是小小年纪便患上神经衰弱。
小潘未满十八岁,在我们中年龄最小,在家却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这在苏北不算稀奇。她极聪明,只是不肯用功,初中时请人帮忙申请了游戏账号,就此沉迷手游。军训宝贵的休息时间,大家瘫倒在地,只有她掏出隐藏的手机分秒必争地打游戏,并因队友太菜而开视频与其对骂。“我才不想那个家呢。”她对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充满愤恨,轮到她讲述的夜晚,说了许多与外婆、外公共同生活的童年趣事。
卓娅的家最远,西藏阿里,离天最近的地方。开学当天,一身朋克装的她顶着“奶奶灰”短发,涂着“烂番茄色”口红,左右耳朵各戴三个耳钉出现,颠覆了我们头脑中约定俗成的西藏女孩形象。相处后才发现,她热情善良,单纯得近乎“呆”。她向我们展示藏区生活,与游客眼中的诗情画意不同,一代代藏人辗转于冬夏牧场,日常充斥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和与恶劣气候无休止的对抗,求学、求医格外艰辛。她向往繁华舒适的都市生活,但知道自己的心永远属于高原。
一向后知后觉的我,挨到最后才讲,是因为感到家乡普普通通,没山没海,有限的经历更是平淡无奇,除了上学还是上学,没什么好说的。然而在那晚的静夜思中,一些本以为模糊的往事贝壳般呈现于记忆的沙滩,星星点点,微小而特别。
我初中就读的学校,学风严谨刻板,只要有点滴空余,诸如因下雨取消体育课,或者副科老师请假,主科老师便竞相占课,绝不给人松懈的机会,就连晚自习,也常出现几科老师各据一方答疑解惑的场景。他们对时间如此锱铢必较,却肯花一整天带我们去乡下挖山芋。秋日的田野广阔明朗,蓝天白云下,水鸟蹁跹,湖塘泛着金光,那是师生们唯一一次无拘无束的游玩,也是我首次领略到苏中平原的美。
高中时光缓慢又迅疾。缓慢是由于昏天黑地,似乎只有深夜凌晨而没有白天,迅疾则是我没来得及多想便结束了。高考完最后一次去学校,仅仅相隔几天,却恍如隔世。通往宿舍楼的水杉树依旧静默挺拔,报告厅旁几树石榴花开得明艳如火,大操场中有几个班在上体育课,教学楼里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唯独毕业班所在的那排教室冷冷清清。我在其中一间找到语文老师,她正指挥几个学弟、学妹打扫卫生,地上到处是毕业生抛撒的试卷和书本,黑板成了心情墙,画满龙飞凤舞的线条。我把辅导材料还给她,向她道谢,也道别。她站在围栏边目送我,从五楼到一楼,每走到楼层转角,都能看到那个不断挥手的娇小又坚定的身影。高中三年,她每学期都会给每位同学写信,不谈大道理,只讲小事情,还常在考试周给大家发棒棒糖。印象最深的是高二分班前夜,她给大家放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当甜美的高音二重唱《今宵微风吹拂》在教室响起,阳光、雨露、月色、花香同时来到每个人的心中,化解着无处安放的躁动和忧郁。
时间带着人飞跑,身后风景成了明信片,我们交换阅读,惊叹连连。六个不同星球的生物,落到同一个暗黑营地,必须斩妖除魔,才能重生——这是小潘的说法。开学前大家递交了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的调查问卷,以为住在一起的将是性情相似的人,然而实际却如此千差万别。离奇“算法”使人费解,或许这正是世界的玄机。
宿舍朝向西北,对着校园的湖,远处有大片空地,稀稀拉拉长着一些植物,相邻学院的扩建工程似乎总在休眠状态,塔吊高悬,静物般隐藏着张力。再远处横着高速公路的立交桥,傍晚时从窗口望去,浑圆的落日悬在天际,桥上车来车往,落日一点一点被夜色吞噬,流溢出无可名状的沉寂之美。
从秋到冬,再从春到夏,卓娅坐在窗前看落日的次数越来越多,像极了圣-埃克苏佩里笔下悲伤的小王子。她在大一下学期谈恋爱,大二下学期分手,度过跌宕起伏的一年。我们忍耐着,看她高调秀恩爱,留长发,穿长裙,为那个男生省吃俭用买礼物,争吵猜疑,淋雨哭泣。她本以为一切如高原景物般具备清晰的轮廓,不含糊不苟且,没想到在感情中迷失了方向。从前那个充满热力的小太阳,变成一株湿答答的滴水观音,一度卑微得让全宿舍的人都抬不起头。她的分手夜是全宿舍的狂欢节,徐娇专门下楼买可乐和薯片,砰砰砰,嘭嘭嘭,漫天爆米花飞舞,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太软弱,被小潘换成霉霉的Last Christmas(《去年圣诞》),我们以围巾结成长裙,在夜灯旁跳锅庄,直到把卓娅逗笑。
除去这段不成功的经历——成不成功已不重要,作为卓娅恋爱的见证者,我们真切感受到她历劫后的成长。全宿舍只有段亦尘处于持续的恋爱进行时。虽然徐娇动辄“我也是有老公的人”,她最初微信名为“彭于晏老婆”,被辅导员在班会上不点名批评:“个别同学,认知停留在初中水平,盲目追星,网名粗俗……”于是她改为“晏晏家那口子”,仍然被批,最后改成“彭&徐”,可能觉得已无可救药,辅导员不再管她。在大家眼里,小潘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孩子,我虽没有恋爱经验,却是理论家,解答婚恋问题时头头是道,而悦悦从入学开始就不改“学霸”秉性,学习外的时间还要跟水土不服作斗争,从胃肠失调到皮肤过敏,根本无暇顾及其他。段亦尘男友是她的高中同学,他上了北大,她考到这所幼师学院,从隐蔽的早恋,到落差极大的异地恋,充斥着种种不确定,但她并没有很焦虑,最起码在我们面前没有过多表现。“顺其自然吧,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就行了。”她有一颗与实际年龄不相称的佛心。
有关焦虑,悦悦最有发言权。第一年高考,她考完第一场就崩溃了,心悸,发抖,出汗,控制不住地哭泣,甚至不愿睁开眼睛。复读一年,她担心噩梦重演。再次高考前,从前的竞争对手特地请假回来带她去爬山,那个微胖的女孩当年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被一所985 录取,学了生物。在清风吹拂的山顶,她告诉她高考并不可怖,大学也绝非万事无忧,进大学后自己拼尽全力只勉强达到及格线,有两门课程还差点挂科,无奈之下抛开矜持,常跟同学交流,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断调整自我,寻找出路。
她们的人生尚浅,还谈不上“相逢一笑泯恩仇”,却因坦诚而多了前所未有的心气相通,那一刻,悦悦感到某种释怀。极目远眺,飞鸟在天际轻盈掠过。她认定那是传递信息的青鸟,很难说清它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却是她晦暗青春里最为鲜明的记忆。
“你们相信青鸟的存在吗?”一次夜聊,悦悦问大家。睡前的昏沉中,我仿佛看到她穷究不舍的眼睛。盐城的风吹粗了她的皮肤,跟家人视频时,她妈妈对她用了“壮实”一词。她喜欢所学专业,还额外完成自考项目,摒弃外来的压力后,她从学习上获得了真正的快乐。
装睡是不可能的。我含糊地表示许多诗词里都有青鸟的踪迹。卓娅尤其愿意相信,因为高原人一向珍惜各种生命体之间的联络。而徐娇认为是迷信,她不喜欢带有缥缈色彩的东西。段亦尘则把它定义为一种意念,并从哲学和医学两方面进行解释。
“我玩过一个游戏,龙族凭借青鸟的智慧化解危机,并寻找到最适合族群生存的星球。且不说游戏投映现实,平行宇宙里存在一切可能。”小潘说了一番老气横秋的话。
春学期一开始,我们就在宿舍上网课,看老师在空荡荡的教室对着桌椅讲话。每次打饭宿舍只能派出一个人,拎着饭菜艰苦地上下楼。浴室不开,洗澡在宿舍解决。快递、外卖一概停止。每天核酸,各类填报琐碎而繁杂。书桌紧邻窗台,因此我常对着那个湖发呆。它的大名叫“学子湖”,呈弯月状,周围绿荫环绕,像通透的翡翠,更像通往无垠宇宙的神秘海。
草木不管疫情,自顾自生长。封校多日,西校区的树上挂满青藤,水泥路也长出杂草,于是出现了蛇。保卫科挂起警示牌,起先集中力量对草木进行大规模修剪,接着四处投药,结果湖里漂起死鱼,中毒的老鼠步履蹒跚地出现在阳光下,抽搐着死去。
我一度认为它不会好了,曾经的“相看两不厌”变成如今的“相顾空泪垂”,疫情起伏,想来实在使人丧气。可是有一天,湖边响起机器的轰鸣声,一群人在那儿忙忙碌碌,两天后,水被抽干,露出幽深的湖底,填山造海的人们继续忙碌,清污,建造,修补,打扫,持续两周,最后往里面注水,一场奇迹般的工程这才宣告结束。
接连几天雨,气温骤降。中午轮到我打饭,特意提前下楼,先到湖边游荡。我有点愧对湖,因为曾对它失去过信心,而脱胎换骨后的它仿佛并不介意。湖水在寒风中显得格外洁净,新砌的护坡也展示着朴实的造型,波光粼粼中,依稀有鱼游动。我走近几步,想看得清楚些,忽然听见有人喊我。
“同学,同学!”几步远的柳树下,站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黑发齐肩,系着红围巾,抱着书,应该是刚下课。她取下口罩,冲我热诚地笑着。
我也向她致意。她走过来,简单地聊了几句,临走时,把围巾系在我脖子上,关照我早春气候变化无常,注意头颈保暖。
懵懂着去打饭,回宿舍后大家猛夸新围巾,于是我讲起湖边际遇,并劝大家别颓废,那个老师说很快就要恢复线下上课了,琴房、舞蹈室、图书馆、体育场也将正常开放,我可以去琴房找她还围巾,她每周六都在那里给钢琴调音。在舍友们的哄笑和提醒中,我这才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原来她以为我心理出了问题,于是不动声色地进行劝慰。再次望向窗外,湖在那里,不远也不近,静默地流淌着温情。
大二一个很普通的晚上,连着几天,气温都很高,出现了蚊子。卓娅痴迷于新入手的花露水,喷得太多,导致整个宿舍弥漫在浓烈的香味中。徐娇在上铺连打几个喷嚏,表示忍无可忍,段亦尘说闻到了夏天的味道。我没吭声,但下一秒,耳机里就响起了《夏天的风》。手机播放的是未知电台的歌,播到哪首都是随意的,歌声传出的瞬间我呆住了,一下子就明白了电影里经常因美丽的巧合就对某个人心动的感觉。正是这些看似偶然的点滴,使我们感知外界,并与万物产生关联。
转眼来到大三,专业理论进入最后阶段,过后便是各种实践与考试。同学中,有人即将结束学业踏上社会,有人继续在本专业考本读研,也有人打算改变专业开启新的人生方向。学校请来一位早已退休的特级教师给我们讲课,四个学前教育班的同学,把偌大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
老教师从教五十余年,从普通教育开始,到后来解决特殊儿童的教育难题,在漫长的教、学、研过程中潜心摸索,使一个又一个几乎被放弃的孩子获得正常的人生。课程快结束时,有同学问,如果试过多种方法,仍不见成效怎么办。
“投入全部的真诚,重复和坚持。”老教师回答。
她一头花白的短发,背也略显佝偻,眼睛却让我想到清澈的湖水。身后黑板上,挂着她逐一讲过的图片,蒙特梭利,三维立体,全息音乐环境,图画法……有几张还在轻轻摇晃,仿佛提醒大家注意它们的精彩。她和它们一样,散发着从容的气息;她在我们身边,带有真切的关怀,因而更加坚定和纯粹。
窗外是学校的植物园,正值丰沛浓烈的深秋,松树结着松塔,硕果累累,槭树科植物绚烂多彩,如激情飞扬的大幅油画。阳光洒满教室,照着一排排桌椅,一级级台阶,一个个身影。流金岁月,我们感悟着,质疑着,探寻着,发现着,如同世间青鸟,从未停止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