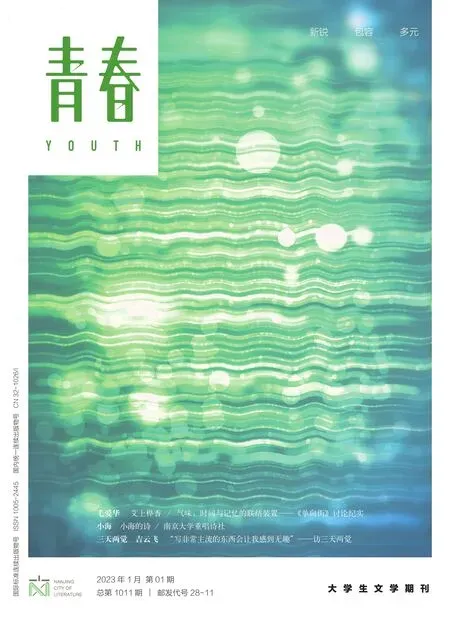艾上桦香
2023-02-22北京师范大学鲁院班毛爱华
北京师范大学(鲁院班)毛爱华
1
刚听说,她已经走了。
也就是去年秋天,她还在给我们做面条。
那是一个清凉的秋日,银杏已泛黄。京城处处弥漫着哀婉的绚烂。京郊一个大房子里,她站在厨房的灶台旁,低头忙活,很是投入。她很少转身看我们,好像,那个时空里,只有她一个人。大部分时间,她很少说话,似乎觉得没有什么需要说的,又似乎一切都已经在心底深处内化了,不至外求。但是一遇到她感兴趣的话题,一开腔,她又滔滔不绝,停不下来。我总觉得,她和别的阿姨不同。事实上,我甚至不觉得她是一个阿姨,而是一个少女。把她归入“阿姨”的行列,仅仅因为她的年龄。她身上有一种疏离感,但又不是要故意疏离谁,那只是她自带的气质罢了。不管她说话还是不说话,仿佛都和这个世界保持遥远的距离。
她的家中堆满了书,各种颜色,各种厚度,各种题材。玄关处、楼梯上、地板上、茶几上,七零八落地躺着。书的精神,像蔓藤一样,张牙舞爪,深入房子的各个角落,连厕所、厨房都不放过。橱柜里、洗衣机上面,鞋柜上也难逃一劫。
第一次进她家,我还以为到了一个旧书店。她穿着一件白色吊带裙,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站在书的海洋中,让我错以为自己闯入了一个电影镜头。那一瞬,我感觉我迷失了。她太虚幻,仿佛不属于这个真实的世界。我迷迷瞪瞪地走近她,在离她几米远处站住,悄悄打量她。
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五官,只见她的黑发垂在白皙的手臂上。她的手里捧着一本《百年孤独》,看起来却似乎一点都不孤独。她慢慢地翻着,好像并没有觉察到我的靠近。她也并不是在读那本书,而是像在寻找什么。好像是在寻找一段记忆,一个标签,或者一张照片。
“吓住了吧?你还敢说你爱读书吗?”秀秀在我耳旁低语,我觉得耳朵痒痒,笑出声来。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有些错愕,好像看到了让她惊奇的景致。她定在那里,手抖动着,眉头微微锁着,嘴角又淡淡地笑着。
“阿姨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问秀秀。
“因为你像她呗,她也许是看到了自己的过去。”
“这么说来,我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将来?”
“知道我为什么爱你了吧?”
“为什么?”
“你像我妈,却比我妈还亲。”
“阿姨比我好看多了!”
“等你也到了她这个年龄,也会一样好看的。就像一本书一样好看!妈,这是白桦,我老跟您提的,我的死党兼塑料花闺蜜!”
“我知道。”她接了一句,又低下头去继续翻书。
“您怎么知道的?”
“我们俩见过!”她又一个抬头,抿嘴笑了笑。我突然瞪大眼睛,心里像被什么戳了一下,因为我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她。
“妈,您胡说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带白桦来这个家,您怎么可能见过她?”
“前世见过!”她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严肃的,丝毫没有玩笑的意思。我心里一惊,把秀秀拉到一边:“别打扰阿姨看书了吧?”
“不打扰,我等你很久了!”她像是长了顺风耳,能将我对秀秀的耳语听得一清二楚。我又一次为之一振。
她放下书,朝我和秀秀走来,走到我跟前的时候,她抬起右手,搭在我的左肩上。然后,她看着我,用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眼神,好像是在欣赏,又好像是在探究,好像是在肯定,又好像是在质疑。我仿佛是一个飘在时空里的猜测,她在找答案,却又不是真的想要答案。看了一个我无法测量的时间后,秀秀一声“妈,您干吗呢,把人都看化了”,她才如梦初醒般,将手臂垂下,继而走向厨房。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叨着:“我给你们做面条!做面条,做,面条!”
继而,我就听见她小碎步跑向厨房的声音,而后是水龙头的流水声和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我和秀秀坐在饭厅的餐椅上,看着落地窗的外面。我只要一个侧脸就能看见她纤细的背影。吊带裙裹在身上,黑发垂至腰间,小腿肚裸露着,发着瓷光白。脚上粉色的凉拖鞋的后跟已经磨破,露出里面的白色质地,和那吊带裙裙尾的破口一样,给我一种撕裂的感受。那是一种优美的残缺,残缺的优美。她摆弄着手中的蔬菜,身体的动作配合手的动作,左右慢动时,又生出几分少女的曼妙。那一刻,我觉得她奇美又静谧,从容又青春。
“看到了吧?我是我妈和书的小三,书是她的一切,我是那一切中的某个断面或者空洞,哈哈哈。”秀秀夸张地笑着,无所谓地说着,我却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几分自嘲,从她的笑里看出了几分哀怨。
“你知道我怕什么吗?”秀秀突然停下笑,朝我投来一个犀利的眼神。
“怕什么?”我反问
“怕你也变成她那样!”
“阿姨究竟什么样?她这样不好吗?”
“看着是挺好!处起来就不好了!”
“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那种不被需要!你存不存在对她似乎毫无影响!你来或不来,她觉得都一样!”
“你又不是她,怎么知道她怎么想!”
“这几年,她从来不主动打电话给我,好像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这个世界上只有书,无穷无尽的书。除了书以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什么了。至于我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她,我无法清楚地定义自己。”
“这世上,有几个人能清楚地定义自己呢?也许,她只是以为你不需要她,或者她不想让你觉得她是个弱者,需要别人随时的关心。”我顿了一下,呼出一口气,“也许,那是一种只有她自己能承受的孤独,她不想把孤独分享给你,让你跟着孤独。”
“你看,我就说你像她吧,说起孤独这个词,你们的表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真怀疑,你才是她亲生的!”
“你懂什么叫性格对撞吗?”
“不知道!”
“一种性格的人往往会促成截然不同性格的人的产生。”
“你看你看,你一说起这些所谓的高大上的深刻的东西,就和她一个调调!”
“好吧,说些别的,阿姨穿这么少不冷吗?”
“不知道,我问过,她却说‘我冷不冷,我自己不知道吗?还需要你问’,这是她的原话。”
“哦!”
我和秀秀一边聊着,一边看着窗外。近深秋了,一株柿子树,光秃秃的,毫无艳色。干枯的枝丫在风里轻微地晃动着,像是冬眠前的垂死挣扎。柿子树旁一株银杏,黄灿灿地迎着日光,像凡 · 高笔下的向日葵一样散着温暖。我正在想,银杏树的存在究竟让柿子树作何感想。它会因为它更加孤独吗?还是会因为它更加绝望,抑或是感激它给它枯竭的身体一些肉体无法共享的仅限于视觉上的灿烂。柿子树真的需要银杏的布施吗?我正想着,就听见厨房传来一声活泼的召唤:“面好了,桦桦,来吃!”
继而,我就看见她端着一大盆面笑眯眯地朝餐桌走来。餐桌上摆满了书本,她将盆底置入书堆里,慢慢地旋转出一块空地。什锦蛤蜊面的香气从餐桌上生起,灌满整个大厅,钻入我的鼻腔。那是一种杂芜又浓郁的香气,里头杂糅了海鲜蔬菜和菌菇的精华。餐桌上也堆着许多书,面条盆像一个孤儿,闯入书的领地,怯生生,又怜惜惜的。要不是那香气实在迷人,那一盆面大概会汗颜自己的孤立。秀秀将桌上的书往边上挪了挪,确保餐盆有更大的领地。秀秀的手刚碰到一本咖啡色书本的书脊时,她便一声大叫:“别碰那书!”说是大叫,不如说是怒吼,从骨头缝里挤出来的怒吼。她的脸上冒出青筋,像一条条水蛭突然爬上了白皙的面盘。她眼里顿时生出泪水,很快就滚落到脸颊。
秀秀吓了一跳,把手收回。被吓一跳的还有餐盆里的蛤蜊。它们连壳带肉,在汤里颤抖了好一会儿。她定在那里许久,我和秀秀也定在那里,不敢轻举妄动。做了好几个吞咽动作后,泪水已经将她的脸颊洗过一遍,她才像如梦初醒般匆匆忙去抢秀秀手中的书。那急迫的样子,好像晚一秒钟就要天下大乱似的。
她将诗集捧在怀里,径直走向大厅中央的沙发,坐了下来,发呆了好一会儿。她脸上刚刚暗去的笑容再次浮现,泪光中闪现出孩子般的天真。只是因为刚才那乍起的刺激,她的脸上出现了老人们都有的表情。她从一个少女突然变成了庸常中的阿姨的样子。脸上的皮肤像吊带裙的裙摆一样起了褶皱。
我没有细看那诗集,也并不知道作者是谁。后来,还是听秀秀说,那个诗人叫西枫,是她早年的学生。西枫在他30 岁的时候走了,留下的唯一的诗集,她视若珍宝。诗集的序正是她写的。秀秀也说不清楚,她为什么会那么紧张那本诗集,好像那是一个伤疤的结痂,又好像是一个缄默的承诺。在秀秀那里,那本诗集更像是一个插满引线的烟花筒,随便触碰一下,都可能引发她的爆发甚至毁灭。
“来吃面啊,妈!”秀秀喊“妈”的时候总是很生硬,好像那是从她胸腔里勉强挤出来的声音。我总觉得,她和她之间隔着什么东西。也许,就是那本诗集。
她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后,在秀秀的反复催促下才又向餐桌走来。她一坐下,就开始拿起筷子捞面条,往小碗里装。她脸上的笑容打开了些,嘴角浮现两个梨涡。我看着她,又好像看见一个怀春的年轻姑娘,刚刚读完心上人的来信。
我接过她递给我的小瓷碗,开始吃了起来。我不敢吃得太猛,生怕汤汁溅出来,溅到餐桌其他的书上,又惹来她一声大吼。不知道为什么,看她吼,我并不害怕,只是有点心疼,好像生怕一个孩子突然被踩了玩偶,伤心地哭起来。
“桦桦,你别这么拘着!吃面条要有吃面条的样子。你这么小心翼翼地,又不是吃提拉米苏。吃面条应该像写小说,大快朵颐,唾沫飞溅,吃提拉米苏才是读诗,用勺子慢条斯理地拨弄,总要弄出一些非凡的调性。”她说着,拿起筷子,大口地吃起来,吸溜吸溜地。“在我们老家,不管是什么宴席,红喜事、白喜事、百日宴、生日宴,都必然要吃这碗面,看着不过是一碗普普通通的面,里面揉进了许多好东西。猪脆骨、蛤蜊干、贝柱、木耳、蛋皮等。这面就像一本书。读书的人只看到书出来的样子,却不知道,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做多少预备、酝酿、耕耘、提炼。”
“是!阿姨,您刚刚花了整整一个小时。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好吃,功夫下得细致入微。”我也放开了些,可依然不敢太彻底,我总是吃几口,就将瓷碗往自己的跟前挪一挪。
“还拘着呢!”她突然伸出手,将离我的瓷碗最近的几本书,扔到地上,“你这孩子,不就是书嘛!跟吃饭相比,书有什么要紧的!”
“可是阿姨,我看您明明爱书如命!”
“那是错觉,书哪有命重要!”
“妈,你平时可不这么说,怎么对白桦就不一样了!好像她才是您亲生的!”
“你是你,她是她。你从来不看书,我当然希望你爱书。她就不一样了!”
“她咋就不一样了?”
“她也是个书虫子!书虫子自然有书虫子的好,可是书虫子就没有书虫子的恼吗?不管爱什么,爱过了,都是病!吃面吧!味道不错吧?给我打个分吧?千万不要说100 分,那肯定是骗我的,我宁愿要真实的50 分,也不要伪善的100 分。”
“90 分吧,阿姨!”
“这么说还有可提升的空间了?说说看!”
“如果五香粉少放一些,木耳再泡开些,蛋皮再薄一些,葱花在出锅后再放,就该离100 分无限接近了!”
“你也是?”她放下筷子,瞪着眼看着我,一脸的惊讶。
“是的阿姨,我想我们应该是老乡。有着一样的乡愁!”
“你老家也是平顺?”
“正是……”
2
老乡见老乡,相见不恨晚。那以后,我常常去她家。开始的时候秀秀带着去,后来,秀秀不去,我一个人去。我去,做两件事,吃她做的蛤蜊面,听她讲的故事。我也说不上来,那些故事到底是真实的发生还是真的是故事。看她讲的时候那般真切的样子,我感觉那是真实的,可那些故事的情节那般离奇,我又觉得是虚构的。
她只讲一个人的故事,西枫的故事。她只讲西枫,但我很清楚,那是她和西枫的故事。两个人的故事,她用一个人来演绎。她讲了又讲,每一次讲的内容大都一样,但每一次讲总会增添一些和上次不一样的小细节。好像她在画一幅画,框架打好,一次次往里面填充颜料和内容。讲得越多,细节越多,画面就越饱满。
“西枫是我的学生,28 岁的时候来读我的博士,他是那么有才华……”讲到这里,她必然要笑一笑。眼睛眯起来,梨涡跑出来。“他又是那么俊朗,笑起来一口白牙。”讲到这里,她的眼睛必然发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光芒,带有痴迷的穿透的力量。
她一直讲,我一直听,讲到最后。其实没有最后。每次都以为是最后,可还是会有新的开始。“他走了,30 岁那年,年纪轻轻的。如果,如果!”她总是在讲到如果的时候,就停下,眼里的光芒暗去,笑容收起,嘴角下拉,露出苦涩和纠结。我从不追问如果后面的事情,事实上,我每次都只是听,极少发问。就算问,也是为了给她的故事,一些起承转合的帮助。
就这样,断断续续讲了一年多后,疫情开始了,我们就极少见面了。直到去年秋天,秀秀又喊我,说她特别想见我,我才又去了。
她似乎老了许多,头发不再垂着,还戴上了帽子。人越发清瘦了,但依然很白净。她还是给我们做面条,可是好像味道也差了许多。蛤蜊里能吃出沙子,青菜已经煮成了黄色。面条更是不再筋道了。
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希望我再来,尽快再来一次。我点点头答应了。可是也就是一个月后,我想再去的时候,听说她的小区被封控了。后来,我只能在和秀秀的网聊中听到她只言片语的消息。因为疫情,秀秀也很少去看她。再后来,我就听说,她去世了。发现她的是小区打扫卫生的阿姨,从落地窗外面往里看,看见她仰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手里捧着一本咖啡色的书……
秀秀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体检报告,才知道她已经胃癌晚期。但是她的死因却不是胃癌,而是因为服用了大量的“安定”。
3
我和秀秀约在觅桦咖啡吧见面。一见我,她就泪如泉涌。一边哭一边控诉:“以后,我就只剩你了,她走了,她真的走了,她给你写了一封信,却没有给我写信。你才是她亲生的吗?你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她的私生女之类的,你不会是我同母异父的姐姐吧?”
“也许是哦,那不正好吗?闺蜜成了亲姐姐,岂不是赚到了吗?”
“也是哦!”秀秀破涕而笑,递给我一个信封,“你现在就拆开,我要看看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让我回家一个人先看好吗?看完,我再跟你说!”
“不行,你现在就看,我太好奇了,她会跟你说什么,她可是我亲妈呀!她给你留了一个上了锁的信封不让我看,这叫什么事儿呀!”
“那我去卫生间看可以吗?咱俩折中一下!”
“好!”秀秀一点头,我就急忙走向卫生间。等我拆开信,看完了,我就径直走出了咖啡厅,因为我无法带着内心的涌动去面对满心期待的秀秀。
信不长,却让我仿佛遇见了一个永生。
“我不是真的爱书,我只是爱西枫。他临走前说,他在一本别人的诗集中发表了一首写给我的情诗,让我慢慢找!那首诗的名字叫《艾上桦香》,可是我读遍了国内所有诗人的诗集,也没有找到。你帮我找到它好吗!”
一个星期后,在她的墓前,我将一根火柴划亮。《艾上桦香》在她的凝视中化为灰烬。
《艾上桦香》在我的诗集中,我原本以为,他是写给我的。
在我这里,他叫春城,和我一样,来自平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