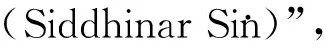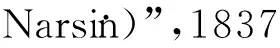清代汉文文献所见廓尔喀官职考述*
2023-02-20孙琦
孙 琦
自1789年第一次廓尔喀之役后,清朝对廓尔喀(1)廓尔喀即今尼泊尔。1769年,尼泊尔境内的廓尔喀吞并巴勒布各部落,统一了尼泊尔,建立了廓尔喀王国。清代官方档案最早涉及尼泊尔时,多用“巴勒布”称呼。直到1791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爆发后,清廷才了解到巴勒布部落早已被廓尔喀吞并,遂统一称谓“廓尔喀”。的认识逐渐加深,并与之频繁交往,尤其是自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结束后,廓尔喀王开始向清朝俯首称臣,并承诺“五年遣使入贡一次”,(2)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廓尔喀正式纳入清朝宗藩体系之中。1792—1906年,每值例贡,廓尔喀都会派遣使团来华朝贡,中廓宗藩关系正常运行。正是由于中廓之间频繁往来交流,清代汉文文献中出现了诸多廓尔喀官职译名。以往由于缺乏相关的廓尔喀语(3)廓尔喀语为16—20世纪初廓尔喀人使用的语言,亦为清朝与廓尔喀往来公文中的官方语言。本文廓尔喀语的转写,依照尼泊尔国家档案馆的转写方式,即梵语转写方式。原始档案,鲜有学者对其逐一考证,大部分是直接利用清代一些官员对这些廓尔喀官职的描述。然而,这些官员都是以清廷的官秩品级来套用廓尔喀官职,过于局限,从而造成某些错误判断。本文利用多语种文献,尤其是参考了廓尔喀语原始档案,对出现在清代汉文文献中的廓尔喀官职逐一考述,以纠正过往的一些错误认识,进一步说明其职能及其在中廓交往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一、噶南
“噶南”一词首见于1856年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定日商议停战合约的廓尔喀官员“噶南足打毕噶然玛兴塔巴”。(4)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996页。笔者查阅廓尔喀语文献,发现此人被冠以“Karnel”(5)“General Gagat Shamsare’s letter”,No.66,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名号。《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Karnel”为“首席将领、上校”。(6)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尼泊尔学者皆记此人为“上校足打毕噶然玛兴塔巴(Col.Jodh Bikram Thapa)”。(7)参见Vijay Kumar Manandhar,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Adroit Publishers Delhi,2004,p.274.Prem.R.Uprety,Nepal-Tibet Relations 1850-1930,Years of Hopes,Challenges and Frustrations,published by Puga Nara,Kathmandu,1980,p.79.据此,笔者认为“噶南”当为廓尔喀语“Karnel”之音译。另据1884年出使廓尔喀的赵咸中所记,“至次年(光绪十年甲申)正月初间,派来二大酋,一国王之犹子,官名噶南(同我国亲王)”。(8)吴丰培编:《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07页。由此看来,足打毕噶然玛兴塔巴的身份为王室成员,而真正的官职为“噶南”。
在1856年第三次廓尔喀之役结束后,噶南足打毕噶然玛兴塔巴开始充任“廓尔喀驻拉萨代表”一职。据1856年驻藏大臣赫特贺奏道:“至来使噶南本系该逆派赴藏中管束巴勒布之头人,现已令其赴后藏行寓谒见,由奴才赫特贺再行剀切晓谕之后,即饬赴前藏任事。”(9)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1000页。这位驻藏噶南后来还为廓尔喀国王及官员请赏,“经该番总噶箕令驻藏噶南投递夷禀,冀邀恩赏”。清廷也照旧例给予恩赏。
二、噶箕
“噶箕”,廓尔喀语为“kājī”。(10)此处应该注意的是,英文著作中也有称呼噶箕为“Kazi”的,乃“j”音变为“z”的缘故。《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kājī”为“中世纪尼泊尔的主要行政长官,相当于部长”。(11)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自1792年中廓议定“五年一贡”制度,历届廓尔喀来华朝贡使团的正使均为“噶箕”。1842年,驻藏大臣孟保记:来华朝贡的“噶箕”为“二品官,辖文武官”。(12)吴丰培编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拉巴平措、卢秀璋、陈家琎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3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1884年,出使廓尔喀的赵咸中认为“噶箕”等同于清朝侍郎。(13)吴丰培编:《川藏游踪汇编》,第307页。在清代,侍郎为“二品官”,这与孟保所记相同,或为当时清廷官员的共识。然而,在一封廓尔喀政府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廓尔喀语信件中,直接称呼拉萨四位噶布伦为“Lhāsākā cār Kāji(拉萨四噶箕)”。(14)“Various disputes in Tibet”,No.30,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并且,在廓尔喀送给西藏地方政府四位噶布伦的廓尔喀语礼品清单中,也全部记为“Lhāsākā cār Kāji(拉萨四噶箕)”(15)见“Documents relating to presents sent to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Nepalese mission”,Part3,Serial No.63(53),Royal Nepal Army Head-quarters,Kathmandu.。而对清朝官员则直译(中堂)、Darī(大人)”。显然,在廓尔喀看来,噶布伦职位等同于“噶箕”。据《清史稿·职官四》记载:“前藏唐古特三品噶布伦四人。掌综理藏务。”(1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职官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407页。若非用清朝官秩品级界定“噶箕”一职,三品官似乎更为合适。

自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后,廓尔喀每五年向清朝遣使进贡,历届廓尔喀使团正使均为“噶箕”。这些“噶箕”经过廓尔喀王精挑细选,一般都为世家子弟,且身居高位。他们肩负着两国邦交的重要使命,来到中国必须小心谨慎,妥善处理与清廷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安全提供保护。
三、噶布党(噶巴丹)
清代汉文文献中出现的“噶布党”或“噶巴丹”皆为廓尔喀语“Kaptān”之不同音译。《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Kaptān”为“上尉”。(21)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驻藏大臣有泰认为噶巴丹“如内地千总”。(22)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435页。“噶布党”一词首见于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当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兵临廓尔喀都城阳布时,廓尔喀王派遣“大头人噶布党普都尔帮哩、噶箕朗穆几尔帮哩、达萨尔乃尔兴,并上次进京之小头人巴拉巴都尔哈瓦斯四名,带同从人二十余名……具禀恳降”。(23)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744页。这是最早出现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关于廓尔喀“噶布党”的记载,也可见此时“噶布党”的职能为廓尔喀的军事将领。然而,在1856年第三次廓尔喀之役结束后,“噶布党”接替“噶南”,开始充任廓尔喀驻藏代表,主要职能是维护廓尔喀在拉萨的商业利益,并时刻向廓尔喀政府传送拉萨的情报。据一封时间为1863年7月的廓尔喀语信件显示,当时任廓尔喀驻拉萨的代表为“噶布党钱德拉巴纳噶尔科且底里(KaptānBāna Kārkiī)”。信件内容涉及了1862—1863年瞻对发生的工布郎吉叛乱事件。(24)“Kaptān Bāna Kārki ī’s letter”,No.103,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噶布党钱德拉巴纳噶尔科且底里于同年9月卸任驻拉萨代表一职,他的继任者噶布党吉特曼森哈斯瓦拉且底里(Jitmān Sinha Silavaī)到达拉萨。噶布党吉特曼森哈斯瓦拉且底里在任期间,廓藏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他的主要任务便是在拉萨搜集情报,并时常向廓尔喀政府报告。如1971年2月15日他向廓尔喀政府发送的一封情报,内容涉及清廷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在拉萨的活动信息。(25)“Kaptān Jitmān Sinha Silava ī’s letter”,No.42,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不久,他又向廓尔喀政府报告称,在拉萨的一名中国士兵向廓尔喀驻拉萨领事馆开枪射击,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事后,驻藏大臣向他表示已经严惩了那些放枪的中国士兵。(26)“Various disputes in Tibet”,No.30,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1793年3月,廓尔喀驻拉萨的几名官员遭到虐待,尽管西藏地方政府向廓尔喀官员道歉,但是,廓尔喀政府并不满意,仍然于1874年初撤走了噶布党吉特曼森哈斯瓦拉且底里。(27)Vijay Kumar Manandhar,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Adroit Publishers Delhi,2004,p.291.然而,到了1875年,双方关系有所缓和,廓尔喀政府又委派噶布党返回拉萨,继续出任驻拉萨代表。(28)Leo E.Rose,Nepal:Strategy For Survial,Berkely:Ui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p.123.
清代最后一任廓尔喀驻拉萨代表为噶布党且底巴哈都热卡底热且底热(Jit Bahadur Khatri Chhetri),此人于1901年被廓尔喀政府任命为“噶布党”,驻守在拉萨。(29)Vijay Kumar Manandhar,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p.312.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多次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与噶布党且底巴哈都热卡底热且底热的交往,如1904年4月8日记载:“巳刻正廓尔喀头目噶巴丹(如内地千总)。且底巴哈都热(四十三岁),名卡底热且底热(如世家,非世家不应书此六字)。的者(如字识)。玛朗的扒底(四十岁)。并苏必达热(乃管兵者)。朴底玛朗他巴(四十七岁)。俱来见,其噶巴丹人甚精明,面貌身材皆好。因唐古忒去英国交战,实属无理取闹,请驻藏大臣一切含容,莫要见罪,要极力保护。伊果敢王现有信字到藏,故来回明,因令其译出汉字呈递,伊等遵谕而去。”(30)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35页。这是有泰到藏以来第一次会见廓尔喀噶布党,初始印象颇佳。当时,正值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地方,英军在荣赫鹏的率领下,已经进入西藏,并开始向江孜推进。之前,十三世达赖喇嘛遣使前往廓尔喀求援,请求廓尔喀现任总理钱德拉·夏姆谢尔(Chandra Shamsher)派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前来调解。而钱德拉·夏姆谢尔则让噶布党且底巴哈都热卡底热且底热将信件带来,即有泰日记中提到“伊果敢王现有信字到藏”。钱德拉·夏姆谢尔在信中回复十三世达赖喇嘛说,现在派遣任何廓尔喀人前往西藏“已经为时过晚”,如果达赖喇嘛愿意,可以委派廓尔喀驻拉萨代表噶布党与英人进行调节工作。另外,钱德拉·夏姆谢尔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保证说,英人“并不觊觎西藏的领土”,因此不用担心。最后,钱德拉·夏姆谢尔还谈及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准备逃离拉萨的消息,并劝他不要这样做,出逃拉萨就等于抛弃了自己的人民。(31)Leo E.Rose,Nepal:Strategy For Survial,p.158.同年4月11日,有泰又记道:“廓尔喀噶巴丹将其国果敢王致达赖信件译出,于昨日送来,颇有道理,惜达赖不信,实无如何。今日赴噶厦处说之,其办事人亦以达赖为不是,应许必将其言代达,未知肯听与否?因噶巴丹人甚明白且恭顺,赏其银牌、哈达、袍褂料,颇知感激。”(32)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36页。显然,有泰颇为赞同廓尔喀总理钱德拉·夏姆谢尔的言语。从这两次会面也可以看出,有泰对噶布党的初始印象极佳,认为“噶巴丹人甚明白且恭顺”,因此还赏赐了“银牌、哈达、袍褂料”。
1904年7月下旬,荣赫鹏率领英军到达曲水宗。朱绣《六十年大事记》记载,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请有泰同赴曲水议阻,有泰不允”。(33)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吴均校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19页。有泰在日记中记载,“十二日(1904年7月24日),……达赖忽来文,已议论三日矣,令李光宇译出,明日再看”;(34)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64页。第二天又记道,“十三日(7月25日),早同鹤孙谈,洋人已到曲水,止在一过河,则藏内大不得了矣……晚饭后过少韩处一谈,竹君在座,适谈间,噶布伦等来回公事,因传见,乃请即刻赴曲水,先挡洋人,告以非见实在公事,实在藏内可信之人不能前往,其三大寺喇嘛仍哓哓置辩,因拍桌申饬之,旋令其下去。复找鹤孙来谈,刘巡捕、李光宇来回,仍是求快往,或派人先止住不过河,其心如焚,可谓急时抱佛脚矣,一笑”。(35)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64—465页。显然,朱绣所说的“亲请”应该只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信和噶布伦来请。此外,廓尔喀噶布党似乎也是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委托来请有泰前往曲水阻截英人,因为同年7月31日,有泰记道:“噶必丹来禀见,所说无非请余到曲水,可挡住洋人,未免发笑。”(36)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66页。有泰不但没有前去议阻,反而派人前往曲水欢迎英军,并“拟给英大员荣赫鹏照会”称:“贵大臣风霜辛苦,远道驰驱。该藏番蠢愚顽梗,不听开导。本大臣实觉怀惭。”(37)江潮编录:《藏印往来照会》,黄维忠、季垣垣点校,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1页。有泰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拉萨,待有泰与英人荣赫鹏等会晤时,“达赖亦不知去向”。(38)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69页。此后,有泰与英人开始议复和谈条约。噶布党且底巴哈都热卡底热且底热在中英双方的和谈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对促成1904年9月7日英国与西藏地方的《拉萨条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廓尔喀驻藏代表的特殊身份,他可以与英国军官荣赫鹏和中国驻藏大臣有泰会面洽谈。有泰于8月15日在日记中记道:“噶必丹忽来,不过请早为议结为是,泛而又泛之语,因未见。”(39)有泰:《有泰日记》,康欣平整理,第470页。显然,在中英谈判期间,廓尔喀噶布党会影响有泰对英方的态度。而英方荣赫鹏也希望获得廓尔喀驻藏代表的支持来解决争端,因为他发现廓尔喀噶布党是一个“更重要的关键性人物”,后者的“代表身份举足轻重”。(40)Vijay Kumar Manandhar,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Nepal-China Relations Up to 1955 A.D.,Vol.I,p.312.实际上,正是在英方荣赫鹏的利诱下,噶布党开始沦为其侵藏爪牙,并设法煽动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催促后者签下《拉萨条约》,从而为英国牟取了更多在藏利益。
综上所述,“噶布党”在清代的角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为廓尔喀的军事将领,出现在三次廓尔喀之役。后期则充任廓尔喀驻藏代表,其主要职责为调解廓藏商民纠纷,维护廓尔喀在藏利益。此外,噶布党还负责为廓尔喀政府探听西藏地方的情报,尤其是在上述廓藏双方发生纠纷时,他们时刻向廓尔喀政府汇报有关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官员的态度与动向,起到了监听西藏地方的恶劣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中国西藏地方的安全与稳定。殊为可憎的是,在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地方之际,廓尔喀更是充当英帝国主义的帮凶,先是廓兵导引英军入藏,后又委派其驻藏噶布党煽动驻藏大臣有泰及西藏地方官员,催促后者尽快与英方签订《拉萨条约》,这严重损害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和西藏地方的利益。
四、苏巴
“苏巴”,廓尔喀语为“Subbā”。《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Subbā”为“政府高级行政长官,也指廓尔喀国内林布族的头人”。(41)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据19世纪初实地考察廓尔喀的弗朗西斯·布坎南·汉密尔顿记载,苏巴是一位负责税收、司法和警务的官员,在税收方面,“事实上,他负责他所管辖地区的全部皇家税收。有时候,他也委派几名下属官员福孜达尔(Fouzdar)以他的名义征收一些分支地区的税收,有时也把税收交给几名伊杂热达尔(Izaradar)打理。而福孜达尔之下的土地收入,由乔杜里斯(Chaudhuris)或德萨利(Desali)以及上述低级官员征收。这些办事机构的官员不是世袭的,也没有固定的薪金支付体系。有时津贴按土地发放,有时按租金的百分比提成,有时按月偿付薪水。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巴决定的。但是,他和他手下的每一名官员,都以库尔查(Khurchah)的名义,尽可能的从他的部下那里榨取一切”;(42)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An accont of kingdom of Nepal,p.84.在司法方面,“自廓尔喀建立稳定政权后,通常在各地设立一名苏巴取代当地的王公(Raja),至少在形式上而言,这些苏巴行使和先前王公一样的职权。但是,在没有廓尔喀宫廷命令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对任何人实施五种酷刑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当人们为不公正的待遇而怨声载道时,苏巴就有核查的权力。王公在自己的小片领地上不敢忽视正义,因为臣民的情感是他唯一可仰仗的资源”;(43)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An accont of kingdom of Nepal,p.84.在警务方面,苏巴在他的统治之下可以拥有一些武装人员,但并非正规军。(44)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An accont of kingdom of Nepal,pp.84-85.由此可见,苏巴是一位地方高级行政长官,负责地方的税收、司法和警务。不过,据一封署名为苏巴噶鲁森哈斯瓦尔(Subbā Kāār)的廓尔喀语信件显示,在1855年廓尔喀发动第三次侵藏战争时,苏巴噶鲁森哈斯瓦尔奉命在廓尔喀各部落征集士兵,并带领士兵前赴西藏作战。(45)“Subbā Kālu Svār to Upadhyaya”,No.66,National Archives of Nepal,Kathmandu.看来,苏巴也充任征集士兵、带兵作战的高级军官角色。

其中1852年的苏巴毕木兴拉纳在华遭遇最具代表性。1852年8月,廓尔喀使团离开加德满都,按时抵达北京,受到了友好接待。但是该使团的旅程并不愉快。首先,使团正使噶箕行至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时病死;接着,副使萨尔达尔也遭到同样的厄运,在使团返程时病逝。由于正副使的死亡,使团暂时由苏巴毕木兴拉纳领导。在使团从北京返程时,中国的太平军叛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以致毕木兴拉纳等人被迫要绕道返回拉萨。根据廓尔喀政府的说法,在返程途中,贡使遭受到了各种虐待和羞辱,尤其是在西藏东部的康区。然而,当时英国驻廓尔喀代表拉姆塞(Major G.Ramsay)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在致英属印度政府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我不得不认为,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使这个廓尔喀宫廷处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廓尔喀使团受到的虐待,从而希望派遣一支军队穿越雪山前往西藏。关于这一点,各种谣言满天飞——或说廓尔喀首席萨尔达尔在中国被谋杀;或说中国皇帝拒绝接受廓尔喀的贡物,并说正如藏格巴都尔带着礼物前往英国朝拜维多利亚女王,他也应该亲自来北京表贡。我完全怀疑这些报告,因为我看到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信,描述了中国北京招待廓尔喀贡使的情形。这封信是中国皇帝寄给廓尔喀总理的,由接任正使的中尉毕木兴拉纳传递。这名中尉报告了副使萨尔达尔和其他一些贡使的死亡情况,并说使团目前面临巨大的艰辛与困难,从而不得不暂时停留在几个地方并且不得不走一些弯路以避免遭到敌视中国政府的反叛者(笔者:太平军)袭击。”(49)“Mission to China”,Foreign Department Secret,26 May 1854,No.50,National Archives of India,New Delhi.此处,拉姆塞称毕木兴拉纳为“中尉”,可能“苏巴”等同于“中尉”职衔。另据苏巴毕木兴拉纳的报告信所说,“抵达北京后,将表贡呈递给中国皇帝,后者给了我们更多的赏物。从北京返程回国途中,萨尔达尔、苏毕达尔等人不幸病逝”。(50)“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Poka No.64,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Kathmandu.显然,廓尔喀官员的死亡是自然原因所致。然而,在此之前,廓尔喀总理藏格巴都尔一度将他们的死亡归罪于西藏康巴人。(51)Leo E.Rose,Nepal:Strategy For Survial,p.108.可是,藏格巴都尔最终还是夸大了1852年廓尔喀贡使在中国受虐待的事实,以作为1855年发动侵藏战争的借口。而苏巴毕木兴拉纳作为廓尔喀使团中幸存的高级官员,他的报告也为反驳藏格巴都尔的无稽之谈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五、萨尔达尔
“萨尔达尔”,廓尔喀语为“Sardār”,《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Sardār”为“位于噶箕之下、苏巴之上的高级行政长官”。(52)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此词常随“噶箕”出现在清代汉文文献中。历次来华朝贡的使团副使均为“萨尔达尔”,可见地位仅次于噶箕。1842年,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萨尔达尔毕热拔达热噶热格带领廓尔喀使团来华表贡。驻藏大臣孟保记此“萨尔达尔”系“廓尔喀管兵大头人”、“三品武官”。(53)吴丰培编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拉巴平措、卢秀璋、陈家琎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3辑,第223页。弗朗西斯·布坎南·汉密尔顿记载:“萨尔达尔为军事长官,经常被分配到该国(指廓尔喀)不同地区实施管辖。无论他们在哪里任职,事务的管辖权都要大于苏巴。尤其是刑事管辖权更为广泛,因为他们不必向法院提交申请就可以判处他人死刑,而苏巴想要处决一名罪犯,就必须得到法院的许可。有时,在各大部落任职的萨尔达尔与四大乔特里亚和四大噶箕组成十二人大议会,协助廓尔喀王治理国家。这些身居高位的萨尔达尔,与廓尔喀其他高官一样,不时还会得到升迁的机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萨尔达尔一般会被分配到各部落驻守,并有权管辖当地的所有苏巴和民事官员,虽然他们的身份是一名真正的军官,除了婆罗门,只有这样的人才配授予重要职位。”(54)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An accont of kingdom of Nepal,p.87.

六、达萨尔
“我(笔者注: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祖父拉纳巴都尔萨野(Raa Bahādur Sāh)之时,十年十二年之间通用银钱,见其市价减少,该铸钱头人达萨尔ār)就未铸钱,以致短少银钱。彼时唐古特廓尔喀(Gorkhā)两相争闹,酿成大事,将从前旧章尽行改坏,所有在藏贸易巴勒布(Nepālī)三十二家及头人等难以在彼居住,两相争闹有应得之罪。巴勒布地方即系唐古特地方,唐古特地方即系巴勒布地方,从前亦系两相和睦,我大皇帝亦不能灭此旧章。所有贸易三十二家亦系照例原有之事,至济咙聂拉木(Kuti)之处贸易,番民均系照例规在贸易。从前一切事物例规改坏,再我们从前议的话,现在照依。刻下头人达萨尔未曾铸造银元,是以银钱短少,我们廓尔喀与唐古特多年相好,若照从前旧例来往通行,一切事情大有好处。”(60)尼泊尔国家档案馆藏:《尼泊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表贡文书》(Nepāl Sarkārle Cina Sarkārlāī Saugāt pathaudā ko ptra),信件号:44。由此可见,“达萨尔”为廓尔喀管铸银钱的官员且在廓尔喀与西藏地方的银钱贸易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1816年,廓尔喀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野“所差达萨尔巴凌角行抵西藏”,言称“披楞仗势发兵临境,只离阳布两天路程,若不救护”,廓尔喀“实在不能抵敌”。(6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846页。此为廓尔喀求援清廷,从中可见达萨尔偶尔也会出任求援使者之职。
七、苏毕达尔和杂玛达尔
苏毕达尔,为廓尔喀语“Subedār”的音译,杂玛达尔为廓尔喀语“Jmādār”的音译。
在廓尔喀派往中国的使团中都会包含几名“苏毕达尔”和“杂玛达尔”。如1842年廓尔喀使团中的苏毕达尔苏热敦邦折、苏毕达尔哈拉哈兴卡底、苏毕达尔薄处八卡底”和“杂玛达尔的比巴萨尔达邦折、杂玛达尔咱哈毕卡底、杂玛达尔莺达兴卡底”等。驻藏大臣孟保记“苏毕达尔”系“廓尔喀管兵头人”、“四品官”;记“杂玛达热”系“廓尔喀管兵头人”、“五品官”。(62)吴丰培编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拉巴平措、卢秀璋、陈家琎主编:《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3辑,第217—223页。据弗朗西斯·布坎南·汉密尔顿记载:“苏毕达尔在一支连队担任指挥军官……每支连队除了军官和乐队还有五六个班,每个班由20—25名士兵组成,由一名杂玛达尔指挥。”(63)Francis Buchanan Hamilton,An accont of kingdom of Nepal,pp.88-89.与驻藏大臣孟保的形容相比,亲自前往廓尔喀考察的弗朗西斯·布坎南·汉密尔顿则描述得更为直观具体。“苏毕达尔”似乎更倾向于现在的连长,统领由100多人组成的连队。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在与廓尔喀谈判被俘后,曾描述“数日来,各廓尔喀苏毕达尔(跛Rb)身边都带领百名兵丁看守”。(64)丹增班觉:《多仁班智达传》(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752页。《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Subedār”为“统领100名士兵的军官”,(65)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颇为中肯。“杂玛达尔”的职位低于“苏必达尔”而高于普通士兵,(66)Nepāl Rājakoya Prajāān,Nepālī因此更倾向于班长,统领20—25名士兵。
1792年第二次廓尔喀之役时,廓尔喀曾派苏必达依喇巴忻喀瓦特等人来营,呈送礼品,并禀称:“如蒙大皇帝施恩赦宥,从此永为天朝属下,阖部落部长头目以及番民人等,皆归王化,渥受天恩。”在廓尔喀承诺此后“永遵天朝王法,与廓尔喀和好,再不敢侵犯边界”的情况下,福康安答应对方的撤兵请求。(6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3册,第759页。再据《卫藏通志》记载,奉上谕,福康安等奏廓尔喀遣头目苏必达巴依喇巴兴、喀瓦斯等,来营呈送牛羊、酒米、果品、糖食等物,备犒官兵。(68)《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合刊》,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4页。苏必达为“Subedār”的不同音译,此处为清代汉文文献最早对苏毕达尔的记载,由上亦可知苏必达依喇巴忻喀瓦特为统领100多人的军官,只不过是廓尔喀一个小头目而已。
八、喀尔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