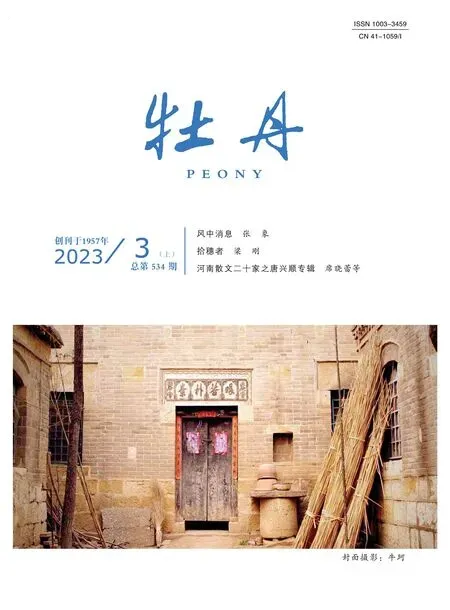风中消息
2023-02-20张象
张象
白色的风,岭南烟雨,七里香的花朵,黑色的大海,以及一望无际的漫长生活,这些都不能使我悲伤。可是妈妈,我现在很冷。家里乱得像蚁穴,我的嘴巴发出萧萧的叹息,来自易水的风,染红了我的旌旗。
搬到这里,已经半年多了。
妈妈,你知道的,换座城市从头开始,这样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是妈妈,请别为我担心。我在你走之后的第三年,和一个南方姑娘结了婚,她的名字叫陈细妹。细妹不高,有一点儿胖,她笑起来像波浪形的风,裹着水草的味道,清爽干净,是你喜欢的“庄户人家”模样。婚后第二年,你的孙子麦迪出生了。他长得白白胖胖,大概算是可爱的小孩。我在写字楼里拼命工作,细妹在出租屋里努力带娃。我们没有外援。我没有房子,细妹和我登记,户口本是从家里偷出来的。自己带孩子,真的辛苦。妈妈,我才知道你的辛苦。
时间在窗外飞过,有时骑着神气的白马,有时踩着肮脏的塑料袋。
麦迪一天天长大,眉目间,一些东西在变化。他依稀长出了父亲的隐忍,母亲的倔强。他越来越像我们。但是长大,意味着他上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却无法在北京落户,无力在北京买房。这座城市再好,终究不属于我们。我们只是卑微的外乡人,蚂蚁般路过坚固的北京城。妈妈,其实我不如蚂蚁,也不如水里的鱼,不如扑腾着翅膀飞过天空的灰白鸽子。它们不为世俗所累,简单而快乐。无论世事轮转,王朝更迭,它们都只遵从内心的抉择,去留随意,迁徙自由。
我们来到了深圳。妈妈,半年多之前,我们放弃了北京的一切,我辞掉你认为体面的工作,告别了北京长达十年的朋友,来到深圳这座陌生的城市。我们原想,这里有政策,大学毕业即可落户,只要落了户,即使暂时买不起房,上学总会容易一些。另外,我来深圳是受邀创业,作为公司高管,如果运气好一些,在麦迪上小学之前买得上房呢?是的,我们正是冲着这一点来的。
这次南迁,细妹比我更积极一些。这里,距她老家只有一省之遥。跟北京一年四季的干燥少雨比起来,岭南的树木葱茏、雨水绵绵,对她来说更为亲切。
但是妈妈,现在我感觉冷。我冷不是因为天气,您知道的,深圳的夏天,热得像一场大汗淋漓的梦魇。我冷也不是因为工作,创业的日子总是辛苦,通宵达旦,没日没夜,发不动工资,甚至大起大落,血本无归,那都是有可能的,在深圳,这样的现象不算什么。我冷,也不是因为细妹,不是因为麦迪,我们很好,虽然我们刚刚吵了架,虽然这兔崽子哭着说同意他妈换个老公。
我冷是因为我自己啊。妈妈。
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是个明净的秋天。天空蓝得清澈,白云垂得很低,仿佛无数枚蒲公英散落天际,又被风聚在一起。绵柔的海风从西湾红树林的方向吹来,一浪一浪,忽东忽西,似沾满咸腥的手,在殷红的落日下,放肆地撩人头发。人间到处是高楼,灯红酒绿的巷陌之间,一切都异常鲜活。
工作的事很快落实,在工商部门做完股权变更,我们就租了一套两居室。
说是两居室,其实只有40多平方米,客厅短短的,白墙上残留着上个租户留下的身高图表,造型是小鹿的卡通形状,麦迪很是喜欢。主卧有飘窗和大床,还有白色衣柜,一张斑驳的写字桌,桌上供着半旧不旧的佛陀:肉髻,垂耳,盘腿而坐,举着右手,双目半睁,像是在跟人打招呼。佛陀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台米色空调。次卧如一条竹筏,窄小得只能存放杂物。
虽然旧了点儿,小了点儿,好歹也算“家电齐全”。令我们欣慰的是,小区位于公司附近,繁华地段,自有配套幼儿园。小区内部,小桥流水,假山喷泉,还有翠绿的杧果树,像菠萝的棕榈树,金红色的荔枝,高大的椰子树,散发着清香的七里香白花,加上还算殷勤的24小时保安,综合对比,这家算是性价比最为合适的。小区环境的幽雅和便捷,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们身处斗室的局促和不安。
政策确实不错,我们全家的户口都迁到了深圳。妈妈,你看,你的后代都成了深圳人。可是妈妈,做文明的深圳人,压力可真大啊。
麦迪新学校适应以后,细妹也出去,找了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工作倒是轻松,但工资也就四千出头。我一月工资两万,扣掉保险和税,到手一万六,房租加水电煤、物业费,一个月至少五千,麦迪每月上学,杂七杂八费用五千,我们一家三口,买米买菜买细妹喜欢的水果花卉麦迪喜欢的宠物零食,加起来又得五千。也就是说,我和细妹辛辛苦苦干一月,减去必要开支,就只能存五千,一年下来,也就能攒个五六万。这样算下来,奔波一年,我们创造的价值,除了养活我们自己,最多也就能买深圳的一平方米房产,以一个四十平方米的小房子为例,我们需要奋斗四十年。当然,这还得是在房子不涨价、货币不贬值、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的前提下。问题是,谁能保证房子不涨价、货币不贬值、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任何意外呢?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农村户口,迁出来容易迁回去难。而且迁回去意味着失败,那就更看不到未来。然而在深圳,麦迪要受稍好一点儿的教育,单有户口还不行,好些的学区房,哪怕比四十平方米都小的房子,也得买上一套。所以我别无他法,只能指着创业成功。
人世间的失败五花八门,成功却只有一种。为了唯一被认可的所谓成功,我透支了太多。一次又一次降低底线,一次又一次含泪妥协,最忙的时候,我恨不能把自己撕成两半,一半扔出去应酬,一半留在公司工作。应酬也是工作。我指的是,应酬之后,我依然有许许多多不得不做的案头工作。
但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份工作。从来没有。
可是妈妈,为了生活,我别无选择。就像烈日下的民工,他们奔波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就像夜幕中的姑娘,她们流连在暧昧的酒吧门口。就像多年前一位年轻的矿工,他每天钻到几百米深的地底下,变成耗子,舔着干裂的嘴唇,蜷在黑暗里,匍匐在煤层间,摸索,开采,打磨。那都不是因为热爱,那只是为了生活,为了他挚爱的家人们啊,妈妈。
我曾为了一个大单,陪客户喝到吐血。我曾为了一个项目,给客户改了30 天方案。我曾因为提案一天没有吃饭。我曾连续工作45 小时没有合眼。然而妈妈,这些都有什么用呢?如果努力就能得到,吃苦就能成功,当年的矿工,你那年轻的丈夫,我正当壮年的父亲,就不会扔下我们独自离开。
细妹又怀了孩子。妈妈,你高兴有第二个孙子吗?国家已经放开了三胎,可细妹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不过,她还是意外怀孕了。惊喜吗?并不。这世界,有时就像个苦瓜味儿的玩笑。玩笑之后紧跟着诅咒。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深夜,四壁无人,静得仿佛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我埋着头在电脑前苦思冥想,时不时在黑色键盘上敲打几下,马蹄声达达,在暗夜的深谷间回荡。空调没有开,窗户没有开,后半夜,我的头上渗出了疲乏的细汗。我腾出手,擦汗,手指触碰到头上的包,那包肿胀如山,像孕妇的腹部一样高高地隆起。几个月了,它难倒了所有医生,各大医院跑遍,没有人能使它痊愈。有时候我很想拿一把刀,把它像钉子户一样夷为平地,可是妈妈,我没做到,我不能跟黑社会一样野蛮粗暴。我是文明人。文明的深圳人。我在深夜擦汗的时候,发现头上的山丘里,居然爬出来一条虫子。一条蠕动的虫子!
我敢确定,它绝对不是从什么花草树木之类的外界空降到我头上的。它清清楚楚是由里向外钻出来的,就像婴儿大哭着钻出母体一般。起初,它只是山丘浅表的一阵痒,一阵试探性的摸索和蠕动之后,忽然之间,一股针扎般的刺痛,从我的头皮里迅疾升起。紧接着,我感觉到,一条毛手毛脚、细手细脚、多手多脚的虫子,在越来越浓的刺鼻的血腥味儿之中,扶摇直上,从我的脑袋里破头而出。它钻出山丘,扭动身子,伸了个懒腰,仿佛一名酒后初醒的醉汉,蹒跚着站稳脚跟。它在我茂密的黑发里蹿来蹿去,似乎那压根不是我的头发,而是它的花园。
停下工作,我岔开食指和拇指,趁其不备,一把将它捏到手里。众多的白炽灯下,出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只蚂蚁。一只两粒头皮屑那么大的蚂蚁!
蚂蚁天线般的触角动个不停,一会儿伸展开,一会儿折回去,就像在做广播体操。它的脑袋上口器明显,六条长腿拱卫着细胸,孕妇般的大肚子,与周身一样,都是和黑夜一般的颜色。我感到一阵恶心,第一反应是把它捏死。
但我没有把它捏死。我看到了它孕妇般的肚子。我把它扔了。我就那么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它像颗篮球形状的梦一般高高举起,用力一扔,它就落到了一米开外的垃圾桶里。
第二天回家,我把这个篮球形状的梦讲给细妹听。
细妹辅导完麦迪功课,收拾着碗筷,正为肚子里的不速之客发愁。我的想法是把他打掉。我喜欢孩子,但我不想让我们本就晦暗不明的生活再横生枝节。然而细妹不同意。细妹说,佛像在侧,我就说这样的话,简直大逆不道,罪过罪过,需要念一百句“阿弥陀佛”方能抵消。但我看佛像盘腿端坐,双目半合,不悲不喜,依然像平常一样举着右手,没有半点儿要加罪于我的意思。
细妹说,我的梦神神道道,听得人恐惧。我倒不恐惧。但是从那以后,我总是失眠,食欲减退,有时无缘无故就感到痛不欲生,总觉得脑子里不太对劲。
过了几天,一个碧绿的清晨,细妹忙,我顺路送麦迪。麦迪哭哭啼啼不愿上学,我好说歹说,连蒙带骗,一点儿用没有,这才佩服起细妹来。我没细妹的耐心和温柔,眼看上班要迟到,我却和儿子胶着在路边的香樟树下,一时着急,扳转麦迪的屁股,不由分说就是两下。
打孩子我是第一次,力度没拿捏好。这个身高刚刚超过一米的男子汉,在我的魔掌下哇哇大哭。他委屈地撅着小嘴,像个弃儿般站在路边。太阳的光辉盛不下他的泪水,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又小又薄,显得格外孤独和无助。络绎不绝的行人从我们身边掠过,一个男性家长冲着我会心地眨了眨眼,旋又匆匆远去。头顶茂密的树冠上,小鸟叽叽喳喳叫得正欢,我看见麦迪苍白的小脸,眉头紧锁,悲伤像被快镜头的爬山虎一样攻占了,我的心揪了一下。
头顶再次奇痒无比,接着就是刺痛。我大惊失色,顾不上麦迪,用刚打过他的手在头发里一阵乱摸,终于捏到一只蚂蚁。这蚂蚁仿佛不是上次那只,因为颜色不同。上次那只通体乌黑,是夜的颜色。而这一只发蓝发绿,是早晨的颜色。
然而,这不是上次那只吗?两粒头皮屑大小,天线般的触角动来动去,六条长腿拱卫着细胸,孕妇般的大肚子,蹬着腿,蹬着脚,在我手里,就像婴童似的不安分地扭动。我被它扭得意乱神迷,心里像吞了一只蟑螂一样恐惧。恍惚间,我想起我以前学过的生物课本,课本里说:蚂蚁都是群居动物。
我就掐着蚂蚁的脖子,把它送到麦迪面前。麦迪还是哭,对我视而不见。我说:麦迪,别哭了,你看,爸爸给你抓了什么?他抹了抹眼睛,看着我,不说话。我说:你看,一只蚂蚁哦!来,送给你,这次爸爸不管你,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想把它弄死,扔到水里,拿火烧,都没问题……麦迪止住哭,一只手还护着屁股,另一只手摸了摸我的手,吹了吹,又拿开,左看看,右看看,忽然指着我的手说:爸爸,你是在逗我吗?哪里有什么蚂蚁?我只看见你的手更红更大了!
我鼻子一酸,说这不是大,是肿。他怯生生地说:爸爸,那你,疼不疼?我不敢看他,一把抱起他小小的身子,飞快地向幼儿园奔去。
送完麦迪,一路小跑到公司,办公室里白天也开灯,我把捏了一路的那个东西,放在掌心,小心翼翼地展览给人看,同事却都笑我,说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一个和我较熟的男同事,开玩笑说:麦总你肯定又没休息好,现在还在梦里吧?另一个女同事,是做设计的,长得要比陈细妹好看,她十分殷勤地给我冲了杯奶茶,凑我耳边说:麦总,您最近压力大,晚上回去就别太加班了嘛!“加班”两个字,她咬得特别重,我欲说还休,只有无奈的苦笑。
是醒还是梦?是真相还是幻觉?可是,我看得见。这只蚂蚁我看得见。它在我头上,在我掌心,在我眼里,留下的痒和痛,留下的昆虫特有的气味,留下的触角接触肌肤的悸动,以及细脚爬过掌心的酥麻,那都是千真万确的啊。
我把它扔在我办公室的地上,趁它还没走几步,踏上去,狠狠踩了一会儿。
妈妈,我踩死了它。这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恐惧。
生物课本上说,蚂蚁都是群居动物,要是一窝蚂蚁在我体内驻扎,那我还有活路吗?我只能先下手为强。
到了周六,五点以后太阳不很灼人,我便答应麦迪,暂时放下工作,陪他们娘俩去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卧着一大片绿汪汪的湖,水上荷叶蒲扇般大,一朵朵睡莲,红瓣黄蕊,开得正好。微风吹皱湖面,水鸟箭一般射过,金鱼、鸭子都比赛逃命,张皇失措,比箭还快地四散而去。
这是个不大的公园,进门有座雕塑:红色的大扇子,上面写着三个金色大字。游人并不多,三五成群,带着玩具,基本都是周末带孩子放风筝的。麦迪没有风筝,就在绿地上扔飞机,我和细妹坐在草坡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视线一刻不敢离开孩子。草坡上的音响里,正在播放一首英文歌,仔细一听,原来是Queen的《波希米亚狂想曲》。
风大起来,蓝色的泡沫飞机,飞到天上,却被树梢拽住了脚。那是一棵体态丰盈的荔枝树,荔枝正红,飞机卡在树叶间,怎么摇都下不来。麦迪跑来,一脸歉意地向我们求助。细妹看了看两米开外,让麦迪自己想办法。麦迪顺着细妹的目光望去,目光定格在老太太手里的拐杖上。一个戴着墨镜的老太太,正在草坪上席地而坐晒太阳。麦迪眼睛转了转,跑到我身旁,亲昵地抓我手臂,央我帮他。我知道细妹想锻炼他,就拒了。麦迪只好自己硬着头皮走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房东打来的电话。
忽然之间,像被谁打开了机关,我的头皮一阵发痒,蠕动,刺痛,毛手毛脚……
“群居”“蚁穴”“驻扎”……这些字眼又在我眼前乱飞,世界天昏地暗,日月开始旋转,我一个踉跄,差点儿滑倒在地。麦迪回来说:爸爸,你没事吧?
我说我没事,急忙稳住脚步,帮麦迪。麦迪捡起飞机,举着拐杖,向老奶奶奔去。我把刚与拐杖分离的手插进浓发,小东西跑得飞快,偶尔驻足,一条腿还在我头上打着节拍,像人在晃腿。我张开拇指和食指,左右包抄,穷追不舍,直到麦迪把拐杖还到了老奶奶手里,这才满头大汗地抓住了它。
我把它捏在手里,心里恨得要死。我给细妹看,细妹仰脖喝完最后一口矿泉水,拎个空瓶子瞪着我说:哪里?哪里有什么?
天旋地转,我的崩溃一触即发。妈妈,我的崩溃一触即发。我的崩溃,我的崩,崩,崩溃……一触即发!
蚊子渐多,夕阳西下。我翻转手,看见这只扭动着身体、很不服气的蚂蚁,闪动着黄昏般的光泽。我把细妹手中的空瓶子夺来,又还她,让她帮我把盖儿拧开。我把黄昏色的蚂蚁迅速地关进了瓶子。
打车赶到医院,皮肤科已下班。我挂了急诊。急诊大夫是位满脸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听完我的离奇遭遇,表情严肃,用戴着手套的右手,按了按我头顶上的大包。又拧开矿泉水瓶,像看演出一样伸了伸脖子,旋即把盖子拧紧。
我说大夫,咋样?大夫一脸凝重,操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先生,根据我的经验,您这病已经蛮严重了。我像看到了救星,迫不及待地问:什么病?他顿了顿,像在选妃子一样选词汇,犹豫片刻说:这样,您下次来的时候呢,记得要带上家属!我一冷,说啊,这就要交代后事了吗?他也擦了把汗,说不是,到时你别找我——去精神科,挂胡主任的号!
妈妈,我很绝望。我又想起了爸爸离开我们的那个夜晚,那个时候,同样疼痛的绝望,也曾像海水一样把我淹没。
我把瓶子带回了家,不顾细妹的反对。
晚上,他们在主卧看鱼,吃水果,吃零食,我从厨房冰箱拿出冻硬的瓶子。然而我一拧开,黄昏颜色的蚂蚁嗖地爬了出来。它掉头向下,沿着瓶身爬行,看上去又冷又硬,似已逡巡许久,早就在瓶颈处等待我的接驾。我张开拇指和食指,抓了一次,没抓到。它的身体就像冰溜子一样滑,我一抓,它就滑到了地上。我蹲下来,两手合围,像捧沙子一样把它从地上捧起。它在我手中,身上彻骨冰冷,凝结成汽,比绝望更深的寒意,像一道闪电一般,从我的双手传遍全身。我浑身颤抖,如遭电击。
妈妈,我很冷。
白色的风,岭南烟雨,七里香的花朵,黑色的大海,以及一望无际的漫长生活,这些都不能使我悲伤。可是妈妈,我现在很冷。
我被困住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把蚂蚁打入冷宫,五个小时,它仍没死。它只在我眼里,别人都看不见。放在镜子前,镜子里一无所有。我给它拍照,手机里一片空白。
我拿火烧,拿烟烫,怎么都不能使这只冰冷坚硬的蚂蚁停止呼吸。我忍无可忍,我气急败坏,我把它丢进了惊涛拍岸的马桶,然后摁下冲水按钮……
惊魂甫定,我瘫坐在客厅的袖珍沙发上,手脚冰冷。在发给房东的微信里,我委婉表达了公司(也许)再过五天发工资,希望房租可以再宽限几天的美好愿望。房东没有回复。也许他已经进入了甜美的梦乡。梦里一定有海,有阳光,有沙滩,有不需要交房租的住宅,以及人人能上的学校……
我抬起左腕,看了看手表,时针刚刚指向十点。我打开房门走进主卧,屋里有一股杧果混合卤鸡爪的味道,细妹头朝里,穿着裙子趴在床上,手捧着手机,正在追剧。麦迪和她头挨着头,短袖短裤都还没脱,几乎和她一模一样的姿势,正用平板看动画片。我已经不抖了,但特别累,就像刚刚爬完了30 层的楼梯。
我坐在床沿上。麦迪一双小脚丫对着我,悠闲地一晃一晃。我发现床上新换了床单,散发着洗衣液和太阳味的床单,恰是蚂蚁图案,而颜色,跟黄昏一模一样……嗡的一声,我的脑袋涌进了千军万马。
睡吧,我累了。我跟细妹说。
细妹翻身坐起,放下手机,眼带笑意地凑过来说:终于忙完了?咱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个怎么办嘛?她摸了摸肚子。我叹了口气说,反正你又不听我的。她笑了,笑容像波浪形的风,裹着水草的味道,清爽干净地说:这么说,你同意了?我说今天不想聊这个话题,我真的累了,我想睡觉。细妹说,推推推,往什么时候推?推到肚子大了,你想后悔都来不及!我不理她,拍了拍麦迪的小脚丫,我说:关上平板,睡觉了。麦迪不听,卧室里依旧充斥着“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就到……”我独自挣扎在崩溃的河岸边,冷风拍打我的脸。
我强打起精神跟麦迪说:我再说一次,关上平板,赶紧睡,明天还要上学呢!麦迪却对我反唇相讥:爸爸,你傻了呀,明天是星期日,不用去上学!我想起来,他说的对,只好摆出独裁者的威严命令他:不上学也赶紧睡,早睡早起身体好!
这时细妹推了我一下,意在催我回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就那么一推,力气也不是很大,我就啪地摔到了地上。麦迪看着动画片,眼都不眨,但却高兴得拍手大笑,一边笑还一边换着声调唱:“爸爸摔了个屁股蹲儿!爸爸摔了个屁股蹲儿!!爸爸摔了个屁股蹲儿……”
我的愤怒长成野马,野马脱缰,策反双手,麦迪的平板电脑被高高举起,重重摔下,天真无邪的玻璃,啪的一声,四分五裂。麦迪愣了一下,小脚丫不再晃动,他坐起来,纯真的脸上长出玻璃,四条晶莹剔透的玻璃,在他脸上顺流而下。猫头鹰的笑声,此起彼伏,在房间里酿成陈醋。
就在今晚。妈妈,就在今晚,我在深圳租来的夜里,和细妹吵了架,而麦迪,你那四岁的孙子,站在他妈妈那边。家里乱得像蚁穴,而我像个事不关己的看客,眼睁睁看着他们打包起行李,手牵着手,路过小鹿形状的身高图表,夺门而去。我只坐在绝望里,四壁战火纷飞,我像被马桶带走的蚂蚁一样无能为力。
我累了,妈妈。我真的累了。
天气很热,但是我真的很冷。屋里的灯,灭了,月光斜斜照进来,像群蚁一样游走。而我的脑袋里,又一只蚂蚁蠢蠢欲动。这一望无际的无穷无尽的潮水般的永不止息的蚂蚁啊,什么时候才能从我的脑海里彻底走开?
蚂蚁正在蠕动。
它来得这样迅疾,这样坚定,我已经隐约听到了它的咆哮声。
这是一只和以前不一样的蚂蚁。
月光那么白那么凉濒死的写字桌驮着犯困的佛陀佛旁众生环绕来不及休憩的杧果皮和截肢的鸡骨头窃窃私语金鱼们泡在眼泪里但却还在哭哭声尖厉而刺耳仿佛凌晨三点碾碎旧梦的车佛对面吊在墙上的空调不怀好意咋咋呼呼地吹着冷气我的牙齿咯咯作响浑身上下散发着死一样的冰凉。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家里乱得像蚁穴,我的嘴巴发出萧萧的叹息,来自易水的风,染红了我的旌旗。妈妈,请别为我哭泣,今夜,我已做好了打算。
我要在它摧毁我之前先摧毁它。我要把盘踞在我头顶的蚁穴一举消灭。我要学着做一个暴君。我要用我儿子的小刀,把这钉子户般的蚁穴夷为平地。
我像个幽灵一般,站在白色衣柜翻出来的镜子前,颤抖着把手放到头上。月光鱼贯而入,凉凉地在屋中横冲直撞,四散飘逸,看客一般注视着屋里的一切。我用小刀拨开头发,鼓鼓的红红的蚁穴露了出来,蚁穴上已经没有头发,像一座寸草不生的沙丘。小刀如临大敌,一步步逼近,前后左右,找着角度。
近了。近了。更近了。
再有一步。再有一步,我就可以做到。
成功唾手可得,我的内心充满了悲壮的欢喜。然而,忽然之间,我看见镜子里,我的头上高高鼓起的包,尚未等我动手,便已擅自裂开。像一件被人撕开的粉色袍子,从我脑袋四周,渐次褪下。
嗵的一声,袍子落地。
我警醒地抬起头来,手持钢刀。然而并没有蚂蚁。连蚂蚁身上的刚毛都没看到一根。我很失望,不知发生了什么。
我感到体内生出粉身碎骨的疼痛,小刀把持不住,轰然坠地,发出声响。
与此同时,在衣柜的镜子里,一只巨型蚂蚁出现,和我一般大小,呆立床前。而我的躯体,茫茫然不知所踪。
这只巨型蚂蚁,长着尖利的口器,但是眼神空洞,下边的两只脚,像人一样站在地上,最上边的双手高高举起,仿佛做着投降的姿势,而中间的两只手,它用来抱着肚子。它抱着肚子的样子,让我想起我的细妹,她正怀着我的骨肉,却带着我的另一个骨肉,痛哭流涕,离家出走在炎热的深圳夏夜。
镜子里,这只蚂蚁有着彩虹般的颜色,浑身晶莹剔透,酷似一大串蚂蚁形状的彩灯,若在夜空闪烁,一定无比绚烂。
看着地上呼呼大睡的小刀,我因这突然发生的意外而目瞪口呆,犹豫了好几秒,才想起今夜的目标是和蚂蚁死战。
我心里念了一百句“阿弥陀佛”,强行收敛心神,打算重拾利器,摆脱幻象,将刀子像死神一样准确地刺入蚂蚁的胸膛。
然而我找不到自己的双手。更准确地说,我找不到我自己。
整个卧室,月色如洗,我只看到镜子里,一只彩虹色的巨大蚂蚁,腆着肚子,噔噔噔地退到飘窗边上,穿过玻璃,挥动翅膀,像只大鸟一般飞上了天。它的全身都散发着光,像一道绚烂的彩虹,连夜空惨淡,都被它染成了五颜六色的好看。
蚂蚁越飞越高,越飞越高,直到消失不见时,夜空中忽然落英缤纷,梵音袅袅,慈悲如礼花绽放,一个巨大的佛的背影横亘天际。我听到了熟悉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