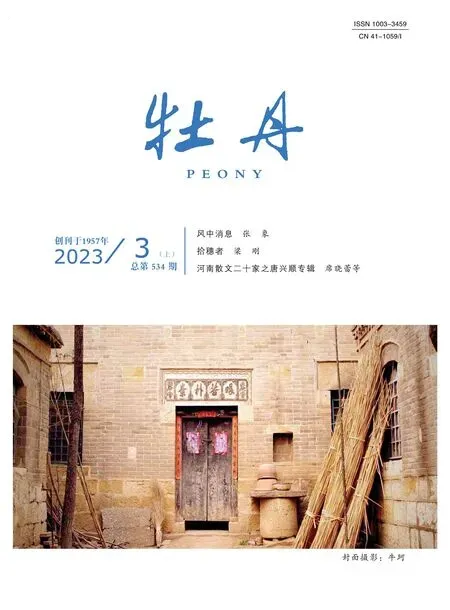犄角
2023-02-20冯耀民
冯耀民
一边是卖金银首饰,一边是卖服装。卖服装的一面墙与卖金银首饰的一面墙相接,但凸出了两尺来宽,形成了一个犄角。
犄角外是人行道。人行道外是街道。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棵棵粗大,树冠高过四五层楼。离犄角三四米是十字街。
犄角掩映在浓绿的法国梧桐下,居闹市,却清幽、安适。
他就在这犄角擦鞋。一口长方形木箱,一把藤条圈椅,两只矮板凳,是他做事的工具。圈椅有些年代了,靠背的藤条磨得光亮,左边的半圈也许坏了,用一块蓝布包着。木箱是三层,黑漆斑驳不堪,也是许久以前的物件。矮板凳的木头面磨得照见人影儿,尺把长,四条腿呈“外八字”,疑心是否坐得稳。来顾客了,顾客坐圈椅,脚搭一只矮板凳。他坐另一只矮板凳,给顾客擦鞋。没有顾客,他就坐圈椅,背靠圈椅,仰着面,抱着双臂,伸长腿,脚搭板凳,打盹。圈椅靠着犄角。他就靠在犄角。一棵法国梧桐正对着犄角,枝叶遮着犄角,遮着人行道。晴好天,细碎的阳光银子似的落在他脸上身上。
有时,也见他抱着双臂,在人行道上踱步。就在犄角左右四五步的范围。“擦鞋吧。”“擦不擦鞋?”之类招揽生意的话,没听见他说过。
他长得胖,肚子像扣了个大脸盆。中等个子,背负着大肚子,走路蹒跚。脸胖得肉往下坠。面色灰黑,像钻了烟囱没洗干净。平头,有很多白发。拧着眉头,眉心舒展不开。我知道那是岁月使肌肉失去了弹性,就算熟睡,那眉心的几道杠杠也不得舒展。
这个犄角,我天天都能看见。因为我上班经过时,还没走过十字街,远远地就能看到。以前,我站在十字街等红绿灯,看的是犄角的最上方,它与蓝天相接,养眼。自从看见他在犄角擦鞋,我自觉不自觉地看向了犄角最下方。除了下雨天,我上班都能看见他。
我第一次看见他在犄角擦鞋是秋天。法国梧桐叶色青黄,稀稀疏疏地飘落。他在给顾客擦鞋。低着头,弓着背。因为肚子大,身子向前倾斜很多,屁股撅起老高,他几乎没有坐着矮板凳。黄昏时,夕阳从远处投来一束光,照在对面高楼上的玻璃墙上。一团红红的光,反射到犄角上,像挂着一盏红光灯泡,给有些昏暗的犄角以光亮。我走过他身旁,我看他,他一点儿也没察觉,他正专心给顾客擦鞋。擦得好吃力。
在小城,像这样在街上露天擦鞋,我很久没有看到了。以前,人多的街头、巷子,会有一个男性老人或男性中年人,撑一把土黄色大伞,摆上工具,给人们修鞋,顺带擦鞋。不几时,街上有了专门擦鞋的。繁华的街道,相隔不远就会有一个擦鞋的。汽车站进出街道旁的人行道上,更是不讲距离,一溜擦鞋的。男的女的都有。女的以大妈居多。她们擦鞋手脚麻利,兴头高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小城开了第一家擦鞋店,挂起了擦鞋招牌。接着,就有了第二家,第三家……擦鞋这份工作,跟其它生意一样就有了门面,不再是地摊。莫说街上,就是车站,地摊擦鞋的也销声匿迹了。当然,擦鞋店也修补鞋子,街头巷尾自然也没有了撑起大伞修鞋的老大爷。修鞋、擦鞋这种低微的营生,也成了规范、体面的职业。还是全国连锁。比如我住在学府路的“XX 擦鞋”店就是全国连锁店,擦的是品牌。
擦鞋全部转入店内,人行道似乎宽敞了些。擦鞋有了门面,美化了市容。
我以为他在犄角的营生不会长久。
几场秋雨后,法国梧桐叶焦黄了,打了卷儿,在枝头颤动。晴天、阴天还是见他在犄角擦鞋或打盹。也许,他在这犄角占用的地盘不大,也不影响行人行走的缘故,使他没有被撵走吧。
两三个月了吧。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照顾他一次生意。有几次,我走近犄角,脚步慢下来,想坐到圈椅上,让他给我擦鞋。可是,看他腆着个大肚子的吃力劲儿,就又走过去了。因为总感觉他比临产的孕妇坐在凳子上洗衣服还艰难。
他应该是认得我了。我也觉着他认得我了。是他的眼睛和神情告诉我的。我从穿风衣到穿上羊绒大衣了。法国梧桐叶也纷纷披离。环卫工早上打扫干净了,很快又满地都是。我上班下班会看到他拿着一把竹子扎的扫帚扫犄角周围的落叶。扫帚小,扫把不长,他需要弓身很多。他似乎扫一下,就要直一下腰。我下班了,踏着落叶走向犄角。在我看向他,他也看向我时,他箍着的眉头上扬了一下,箍紧的眉心似乎舒展了一点,眼睛也亮了一下。也随即看向了落叶,继续扫着落叶。从这次偶然目光相遇后,当再次相互看见时,他眼神挺温和的。只是我没见他笑过。也没听到过他的声音。因为没有一次见他和路人聊天。也许我没看到他遇见熟人。
他是喝茶的。地上近一尺高的玻璃杯,那是个老物件,里面泡有茶叶。他家应该就在老城区,从离这里不远处的巷子进去,只有老城区的老人们才会保管着一些老物件。
他应该没有挣到多少钱。虽然这里人流量还可以,但找他擦鞋的不多,我多数看到他坐在圈椅里打盹,也没见他玩智能手机。晴天、阴天,没顾客就打盹。双臂抱在胸前,仰着面,很安详。行人从他身边经过,鞋跟的嗒嗒声,他也不受影响。这个犄角就是他的世界,其他与他无关。
冬天来了,他穿着盖过膝盖的深蓝色羽绒服,戴着黑色的绒帽,穿着高帮的雪地鞋。犄角虽然能挡风,但这作用不大。冬天,他的脸瘦了,赘肉没有了。
下雪了,纷纷扬扬的。早上上班时没见到他。中午下班时,看到了他。他用那把破扫帚把犄角四周的雪扫干净了。没有顾客,他卧在圈椅里打盹。雪不大但还没停歇,有雪片落在他身上。不光我看他,也有行人看他。只是下午下班时,没见着他。
小城下了一场大雪,从半夜时下起,下了一天多。积雪尺把厚。腊月是小城最冷的时候天晴了,出太阳了,他又来了。
正月,想他应该在家玩。可街上店铺开业了,他也在这犄角摆好了他的工具,像往常一样擦鞋、打盹。
觉着他又瘦了些,精神头也差了些,眼睛有些凹陷。肚子似乎消了点儿,从侧面看去,倾斜度平了些。他看见我,眼神闪了一下,有些许笑意。
您这么早就来做事了。我笑着对他说。
嗯。他应答,眼睛里的笑意没散。
原以为我这样问,他会像其他老人一样打开话匣,会多说一些话。可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神情严肃地喝着茶,没有多说话的意思。一时间,我也不知再说什么好。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没想到,就这一句话,一个字,就没有了。其实盘旋在我心里的话是很多的。他的寡言,他的严肃,使话无法说出来。我甚至觉着是不是我一直没有照他做生意而使他不愿和我多说一句话。可我又觉着不像。因为找他擦鞋的人不多,他好像不在乎。因为他照样天天来,也没有吆喝生意。
可是看见他,成了我的习惯。走到这个范围,我的视线总会第一时间落到犄角。
法国梧桐叶嫩绿的时候,一天下午,我远远看见一个小女孩和他在人行道上打羽毛球。小女孩八九岁的样子,穿件火红色的外套。天晴得好,没有明显的风。法国梧桐树上芽叶稀疏,不足以把枝头掩盖,在斜阳的辉映下浓淡有致,娇嫩得如同小女孩的脸。小女孩仰着头,挥着羽毛球拍,打过去一个球,咯咯笑着:“爷爷!接好!”他也笑着,眼睛笑成了弯月。后来几个黄昏,小女孩也来陪他打过几次羽毛球。他的笑,像欢欣的轻音乐萦绕在脸上。
春天很快过去,进入梅雨季。出了梅雨季,也没见到他。直到九月开学,我还是没有看见他,犄角显得空荡,落寞。
犄角斜对面的人行道旁,有个二十几年的配钥匙摊儿。我在那儿配过几次钥匙,配钥匙老人认识我。想他应该知道擦鞋老人的事,黄昏下班了,就去问他。
伯伯,那位擦鞋的伯伯咋没来了?
两个月前死了。
得的啥病?
唉,他得了肝病,等查出来,晚了。
什么时候查出来的?
去年秋天。他还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去年他咋没去住院治,却来擦鞋?
治了也不起作用,他不去住院,在家吃药。
我再次望向犄角。仿佛看见他弓着背、腆着大肚子、臀部翘起的情景。犄角上的一枝法国梧桐,叶子泛着淡淡的黄。夕阳余晖从对面高楼上的玻璃墙上反射过来,给犄角上的树叶、墙壁,涂上了金粉,好看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