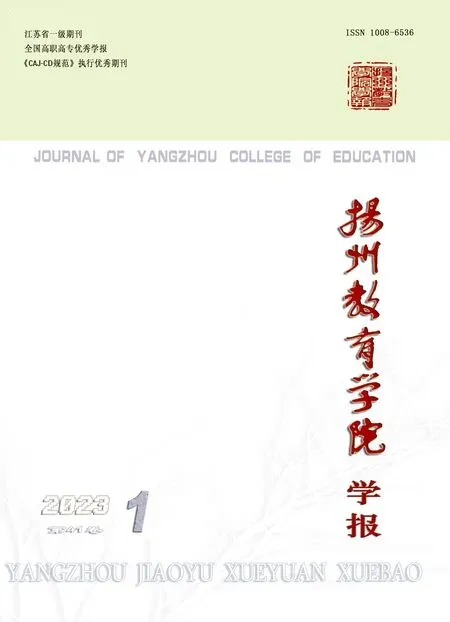论毕飞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的创伤叙事
2023-02-20余梦成
余 梦 成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语,最初是指外力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后逐渐延伸至精神层面。“创伤”并不单纯指身体或心理所遭遇的伤害与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已经从实指逐渐演化为多方面的叙事过程。而书写创伤并非只是描绘个体在社会进程中所遭遇的疼痛体验,也不只是为了描绘一种社会现象,其目的在于以个体的创伤记忆反映群体的精神困境,进而达到对民族文化记忆、人类生存现状、文明发展阶段的反思和自省。
《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最独特的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94年,小说突破了早期的先锋叙事手法,以克制的激情叙事、成熟的语言、丰富的生活经验缓缓诉说着青年红豆的“创伤事件”,深入探索人的命运和文化内蕴,呈现出“哀而不伤、怨而不恨”的特点。学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并不多,目前研究主要围绕小说的伦理内涵、权力叙事、悲剧意蕴、女性书写等方面展开,尚未关注到其中“创伤事件”的书写。
一、记忆、身份:性格与命运的探索
对命运的好奇、探索、书写一直是古今中外作家钟爱的主题,他们将个体生命的发展过程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人的生存、死亡、灾难等主题嵌置到命运的魂环里,以此探索世界、人物深处的隐秘性。
毕飞宇自述他的写作动机主要是“出于对命运和性格的好奇”[1],但与荣格的“性格决定命运”相反,毕飞宇认为,人的性格是由他的命运所决定的,“命运才是性格”[2],这表明他从程式化的“性格即命运”中逃离出来,克服人物性格与命运的模式化、概念化写作,构建了自我独特的命运观。因此在《雨天的棉花糖》中,他赋予红豆独特的性格,以此承载其无法承受而又不可剥离的“命运创伤”。
命运的性格化叙事让红豆从小就具有与常人不一样的特征,带有更多女性化的精神气质。少年时期是假丫头片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拒绝了父亲为他制作的木质手枪、弹弓等一系列具有原始意味的进攻武器,只希望做一个干净的女孩,在安静中成长为姑娘。但随着年龄的变化和身体的成长,红豆从小如花似玉的面貌以及尚未发育完全的身体让他从大龙那儿获得了“上甘岭”的称号,而这称号在某种程度上设定了他后来的人生路径和成长命运,“一个人的绰号有时带有极其刻毒的隐喻性质。小女孩一样的红豆背上了‘上甘岭’这个硝烟弥漫的绰号,最终真的走上了战场”[3]150。
与“命运即性格”相契合,“性别角色错位”塑造了红豆的主体形象,弱化了一切属于他身份的男性特征,从小就已经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与发展路径。“说到底红豆还是不该做男人的,如果他是女人,一切或许会简单起来。上帝没有让红豆做成女人,是他的失误之一。”[3]163如果说红豆从小就具备“刚健有为”的男性气概,他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烈士,成为家庭的骄傲。但命运总是魔幻的,它规定了红豆性格的养成,在“命运——性格的逆向思维中,红豆成为了生命荒原的飘零者,受到了来自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绝对伤害。而这伤害,决定了他悲剧的宿命”[4]121。因此,对于红豆而言,他的悲剧“不属于性格悲剧,而是被钦定的命运悲剧”[4]122。
“命运”不仅影响红豆一生的经历,也困扰着“我”对生命的思考。“生命是讨价还价不得的,无法交换与更改。说到底生命绝对不可能顺应某种旨意降临你。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样的生命却又由不得你。生命最初的意义或许只是一个极其被动的无奈,一个你无法预约、不可挽留、同时也不能回避与趋走的不期而遇,你只要是你了,你就只能是你,就一辈子被‘你’所钳制、所藩篱、所追捕。交换或更改的方式只有一个:死亡。红豆,你没法不是你。”[3]163因此,对红豆来说,最好的方式只有忍耐,忍耐现存的生活方式,忍耐“他者”异样的眼光,忍耐内心的“疼痛”以及忍耐自己。
毕飞宇将生命的思考放置在命运的安排下,以“命运创伤”的叙事形式影响着红豆的成长发展。如“我”所坚信的,“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3]150。红豆五年级时就钟爱那伤春悲秋的二胡弦乐,在他五年级时,买回了那把他反复揉搓心中尘事的二胡,将每一首曲子都拉得横秋老气、哀婉凄迷。以至于“老太太们听着红豆的琴声时常背着红豆的母亲议论:‘这孩子,命不那么硬。’话里头有了担忧”[3]152。“命运创伤”虽不会直接而强烈地对身体带来巨大的表面危机,但却因它潜在不可见、长期遗留、无法解决的特征对个体带来更大的精神伤害,儿时的细节或许已经从某些方面预示了红豆最终凄迷的结局,性格忧郁内敛,女性特质鲜明,这恰恰是引发并造成红豆“战争创伤”的重要一面。
二、梦魇、幻觉:战争创伤的疼痛
战争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伤痛,其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的创伤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和父亲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坚毅的性格,但更多的是为其带来无法磨灭的创伤印记。作为战争的亲历者,战时场景在他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将其带入到梦魇之中,长期承受着战争创伤的疼痛体验。
红豆的父亲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归来后就变成了英雄,残酷的战争塑造了他英勇光辉的形象,“那只不存在的手掌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3]157。但“身体之残是战争对个体造成的仅次于死亡的威胁,在战斗中侥幸活下来的士兵,虽未付出生命的代价,却在残缺身体的重新接受中饱受心理的煎熬和世俗的眼光”[5]。他时常会想到那些战斗中的情景,饱受心灵的挤压,只能借酒消愁,“在酩酊中追忆起一个又一个至死不渝的英雄们”[3]160。他将“创伤记忆”发泄于家庭之中,在吸烟与酗酒中伴随着红豆的成长。
当然,对待创伤的酷刑,并非所有人都会采取逃避的方式,有时创伤的痛苦记忆会使个体采用更加残忍的方式去面对,直面创伤并接受创伤的多重折磨才是结束伤痛最好的办法。对父亲而言,他也要将儿子红豆培养成“英雄”,以更为痛苦的方式去面对他内心最不愿意揭开的“疤痕”。于是他从小就给红豆制作带有原始进攻意味的武器,并将红豆送进了部队,等待百炼成钢。而当红豆“死而复生”时,他的“殊荣”就此坍塌,长期遗留的“战争创伤”从心灵深处慢慢浮出,渴望儿子成为“烈士”的“英雄”,无法接受这样“荒诞”的现实,大声发出“为什么不死”“为什么回家”这极其荒谬的质询。幻想在现实的尘雾中破灭,勾起了他反复回避的经历,于是“从红豆生还的那天起开始风蚀。越来越深刻的变化显现于他的发愣之中。他时常站立于碎瓦片之间,如古代的圣贤先哲寻视破碎裂痕中间的考古意义”[3]175,也间接地造成了红豆最终的悲剧。
红豆在战争中,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枪林弹雨”,也没有受到严重的身体外伤,更多的是精神的压抑、心灵的扭曲、等死的恐惧。他们长时间地坐在坑道里,等待着来自上级的“命令”,在等待中饱受压迫和摧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战争,也不知道死亡何时来临,他们“所有的忍耐、接受、焦虑、恐怖,都成为打仗的附属物,吸附在战争的隐体下面”[3]175。于是在残酷的战场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精神化身“蛇”,带有恐惧面具的一条条柔软的躯体。在冯至那里,“我的寂寞是一条蛇,冰冷地没有言语”[6],而在毕飞宇、在红豆这里,“我的恐惧是一条蛇,柔软地没有躯体”。长期的精神忍耐让红豆在战争中迷失自己,在恐惧中变成俘虏“003289”,最后又在“烈士”的称号中复活回家。但是他脱离战场以后,并未从战争的阴影中逃离,创伤的后延性使得“战争创伤”一直延续至幸存者生命的发展轨迹中,让红豆陷入另一场更可怕的战争。红豆的参战经历在其心间留下了严重的创伤后遗症,回来后经常进入到战争的梦魇中,参战经历的复现、空间场域的撞击、强烈的恐惧、现实与梦魇的交错,使他找不到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其人格不断分裂,最终在虚幻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红豆“战争创伤”的印记不仅来自亲身经历,还有父亲的“残肢断臂”。当所有人都在为父亲是“英雄”而振臂高呼时,红豆看见的只是凭空高出的背部与空荡荡的袖管。当父亲在逃避与发泄他那无法抹除的战争印记时,童年时代的儿子只能默默忍受,在心灵痛苦与家庭压抑的氛围中背着自己与父亲的“名号”慢慢长大,这时期的“疼痛”比任何时候都来得真切与长久。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红豆的内心早已负载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印记,因此当他直面战争时,才会更加恐惧,更加想要逃避。
战争对个体具有极强的塑造性,但并非所有都是“英雄化”书写。对于红豆与父亲而言,战争带给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负面的“创伤记忆”。残酷的战争让他们都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心理创伤,导致他们患有“创伤神经症”,而“创伤神经症在于受害人对精神创伤的‘固着’。受害人总是停留在某个时间点,永远无法走出过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7]。因此红豆与父亲最终都没能走出战争创伤的阴影。父亲表面看似光环加身,但本质上也饱受战争的肉体摧残与心灵剧痛,只有通过抽烟酗酒、打砸破坏等方式发泄情绪,以及采用更极端的方式——让红豆成为自己的“化身”,再次进入战场,成为“烈士”。而不幸的是,红豆在面对战争时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而是在恐惧中幸存下来,回家后无法获得家人、朋友的认同,成为“他者”口中的“汉奸”“逃兵”,在惶惑中抑郁而逝。
三、焦虑、困境:文化创伤的哲思
当然,“创伤不仅仅包括经历过死亡,还包括了死亡而幸存了下来而自己却不理解。受伤者由于闪回不断困扰的不是其经历死亡的不可理解,而是其幸存的不可理解”[8]。红豆悲剧的核心并不在于命运与战争,而是在身份的定位中缺失“自我”,无法获得“他者”的认同。“人类在追求知识和情感的过程中,总是隐含着对‘他者’的渴望”[9],当“自我”在“他者”中无法获得身份定位时,极容易导致存在的虚无主义,进而陷入到焦虑、困境的泥沼中无法脱身,而这主要是由社会“文化”导致的。“‘文化创伤’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害体验,它不只是涉及个体的认同,而且涉及群体认同。它不是群体每个成员都会亲身经历的,但是它会影响整个群体。它标志着某一群体身份的丧失。”[10]11-12在强大的文化伦理的奴役下,红豆没有成为真正的“烈士”比他成为“烈士”更加令人恐怖。“认同危机进一步将红豆推入深渊,绝望的红豆最终精神失常,只希望能通过杀掉过去那个不被社会接纳的自己来‘重生’。”[11]小说中的“文化创伤”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父权压迫”。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是以宗法氏族社会的‘大同世界’为理想建构起来的社会境界,社会组织结构长久地笼罩在父系家长制的阴影之下,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最深层”[12]。父权压迫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成长,红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从小就期望摆脱父亲为他安排的道路,但父亲始终是权力的中心,他最终还是走上了参军的道路,而这也正是其悲剧的核心。父亲的战争经历,让他渴望将红豆培养成另外一个“三班长”,用“烈士”的血和荣誉祭奠未亡的自己,治愈内心的创伤。在红豆的身上,始终笼罩着父权的影响,家庭中他承担着父亲“癫狂”的脾气,战争中他想象并回忆着父亲的战争经历,临死前他依旧没能得到父亲的认同。可以说,正是因为“父权压迫”以及得不到父亲的认同,红豆才有这样“疼痛”的经历。《雨天的棉花糖》将“父权”设置为红豆悲剧的深层根源之一,描绘了“‘死’而复生的红豆无法摆脱心灵的困境,特别是处于以父亲为象征的社会优势的男性价值心理的压迫,由疯而死”的过程[13],解构了父系氏族以来的家长制“父权”的压迫。对于父亲被划定为“右派”,从小缺失父爱的毕飞宇而言,将“父权”放置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予以表现,既是对父亲的渴望,也是对“父权”的消解,对文化意识的重新思考与建构。
其次是“中心文化”观的影响。长期以来的文化模式,使得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无法摆脱“中心文化”的思想,处于“选择性集体失忆”状态中,红豆所遭遇的不理解,就是这一文化的表现。抗战一直塑造的是“英勇无畏、无惧牺牲”的个体形象,而很少有人关注到战争中个体的心理表现,经历战争后的士兵内心的创伤以及战争带来的各种应激综合反应。《雨天的棉花糖》将视点深入到个体参战前的成长经历,战争中的行为表现以及战争后的心理反应,塑造了一个有别于“中心”的“边缘”军人形象,深入描绘了他们内心所遭受的痛苦,将灵魂中的“脆弱”面暴露在阳光下,以唤起人们对“边缘现象”“边缘文化”的重新思考。姜广平等人注意到毕飞宇“小说中的人物软弱的特点,他们的头上好像永远有一层力量在挤压着他们,在残酷地折磨着他们时”[14],其实毕飞宇早已意识到每个人心中的软弱与“疼痛”,而他不过是 “把那门窗打开,让人看见”,将覆盖在人物内心最深处的薄膜揭开,建立了有别于“中心主义”的文化思考,从边缘探索人物的心灵。
“文化创伤与心理创伤不同,这种创伤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所以,文化创伤必然指向一种社会责任和政治行动。”[10]130作为从文革的叙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作家,毕飞宇的视域从未脱离现实,他的创作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学性想象。《雨天的棉花糖》取自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事件,这使得小说所采用的“创伤”叙事更为贴近生活,而“创伤的特质在于,它基于真实而残酷的事实,更存在于对该事实的反复体味中”[15]。在长期的“集体性失语”中,毕飞宇一直将目光下沉到普通人身上,通过描写他们的遭遇指向现实中的文化现象,就是文革长期以来的文化控制对个体身心的双重压制与破坏,是一种“政治的创伤”“集体的创伤”。而他将这一现象描绘出来,并非是简单地唤醒人们的记忆,而是用一种满怀社会责任的文学者的态度,去重新思考这些文化现象,“建构文化创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弄清楚形成文化创伤的根源所在,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对于灾难过后、后创伤时代的人类生活应该如何应对提出有效方案”[10]130。
红豆自杀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灵魂的拯救与创伤的疗救。但显然,这次救赎失败了,红豆尚未死亡,这也说明了其“创伤”的“不可修复性”。他进入了另一个比死亡更加残酷的地狱——“疯人院”,在那里,红豆经历了更加“疼痛”的“创伤”,加速了他想要改变自己的进程,当他回家以后,终于以“死亡”完成了自我的更改与救赎,与那个时代彻底决裂,用恐惧(精神的回归)唤醒人类心灵沉睡的信仰,在“渴望拉二胡与不停摔二胡之间黯淡消瘦下去。气息越来越弱”[3]194。
四、结语
《雨天的棉花糖中》在视角的变换与转接中,将不同的文化人生相互比照、共同彰显,突出红豆人生经历的凄迷。毕飞宇将“命运创伤”“战争创伤”“文化创伤”联结在一起,共同构建了红豆悲剧的来源,一定意义上还原与重塑了历史现场。但“创伤的目的不仅是对现实的复原,更重要的是对造成创伤后果的行为及其背后根源的反思”[16]。毕飞宇在冷静叙述事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解构了长期以来影响并束缚人们的文化思想,更多地将其目光投射至引起创伤的文化根源上,通过还原历史进行深度反思。因此,《雨天的棉花糖》表面是写红豆的悲剧命运以及战争的创伤,但实质上,他已经将目光落到经历抗战后的人物身上,通过解构人物内心的“疼痛”与矛盾,重新建构了一种有别于“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毕飞宇长期的“创伤书写”“边缘叙事”,视域更加宏阔也更深入,更具文化哲思,建构了其独特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