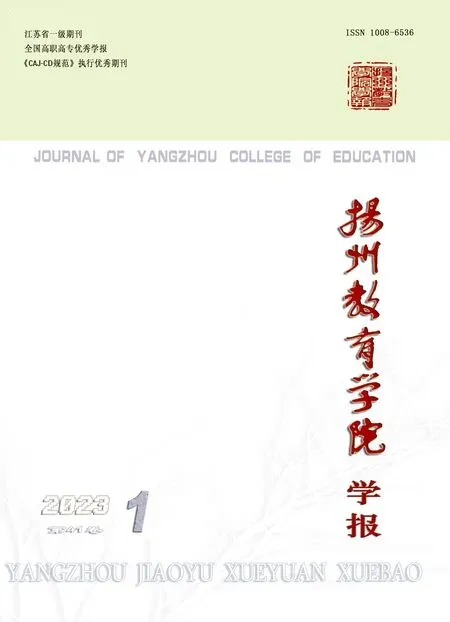论毕飞宇小说中的生育书写
2023-02-20王天怡
王 天 怡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毕飞宇在作品中对女性有着突出的关注。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建造了一个复杂的权力世界,再现了女性残酷的现实生存图景。通过对生育的书写,毕飞宇营造出女性与权力二者之间不断撕扯牵拉的互动张力,意在表现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生命的苦痛和生存的挣扎。毕飞宇通过生育书写,展现了女性在封建思想、男权话语、现实权势等多重权力关系之下所呈现出的欲望压抑、女性失语等生存困境,同时也对女性如何寻求突破、找寻自我价值给予了可能性的展示或寄望。
一、毕飞宇生育书写的具象呈现
(一)性爱中的身体
在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小说中,性爱是表现婚姻生活的重要片段。然而,在传统宗法制文化中形成的生育文化,影响了两性生活的样态,男人通常成为婚姻和生育文化的主导者,成为性的占有者、征服者和主动者。
《玉米》系列小说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发展相对滞后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乡村,传统生育文化对性爱的影响更加突出。如作者对王连方夫妇夫妻生活的多处描写中,完全消弭了其中的温情因素,性爱呈现出程序化的僵硬感。事实上,在《玉米》系列中,冰冷的两性场景比比皆是:无论是在外有权的王连方和郭家兴,还是普通丈夫有庆,在性爱中都具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甚至时常伴随“巴掌”等暴力行为,而妻子在性爱中往往采取沉默或迎合的姿态。
通过夫妻性爱这一个横截面,读者得以窥见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弱势地位,面对凌驾于女人之上的夫权,部分女性压抑着自己在性爱中的需求,在被迫工具化的过程中,女性自身的欲望无从表达更无从索取,很多时候只能将之深深藏匿于内心。久而久之,她们也就习惯了沉默和屈从的状态,并在潜意识中完成了一种自我的物化。
当然,这种物化并不能完全消泯女性对自我价值的渴求与探索,经由身体,往往也会伴随着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部分重塑,即便有时候这种重塑的力量是模糊的、混沌的,近乎本能和盲目。女性在性爱中的这一“反向”或“逆动”的过程通常正是毕飞宇要着力表现的模糊而充满张力感的地带。作为作家,他并不愿意用太多既成的道德定见去评判她们,同时也并不像具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女性主义作家,或具有彻底的反权威、去中心的解构主义立场那样,赋予身体、欲望以某种绝对化的诗意或彰显一种纯粹游牧化、解域化的感性生成的力量。毕飞宇笔下的女性对身体价值的探索相对而言是沉静而低调的,同时也更具有现实色彩,它们往往与现实的权利纷争交缠在一起,与世俗的机心甚至功利的计较和算计混杂在一起,有一种泥沙俱下的浑浊感。
在毕飞宇的小说中,大部分女性的确处于较为艰难的生存境遇中,因此不得不被迫沉默、被迫扭曲。但作家并未抹杀女性作为人的欲望,毕飞宇仍然为女性身体的欲望留下了合理性的地盘。小说《玉米》中的年轻女性玉米,在情窦初开的年纪便在两性亲密接触时释放出了欲望的因子。而在《青衣》中,毕飞宇也用了“舒张”“铺展”“恣意”这样的词来描述主人公筱燕秋与丈夫进行夫妻生活时的姿态。从这样的描述中,能看到女性的身体实际上也承载着欲望。尽管女性的欲望更多的是被隐藏起来的,或者说是不被世俗所允许的,在男性欲望的高调出击和近乎天然的合法化面前,女性欲望的领地只是一片缩小、隐匿、喑哑的存在,但那也是女性生命的一片自留地,潜藏着开凿新的生存空间或架构新的生命格局的可能性,并非空无,亦非荒野。
(二)受孕的身体
毕飞宇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对女性生育状态下身体的描写。当女性身体发生变化,女性的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也会随之产生一系列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身体是始终在场的。在此,身体绝非单纯的生理事实,往往也是意义的生发点。对于女性而言,生育邀请着女性全身心地参与其中,并在这种参与中不自觉地进行着从身体到心理的重塑。毕飞宇敏锐地把握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他利用鲜活且反差极大的夸张性语言,为生育状态下的女性身体蒙上了一层奇幻的面纱,“玉秀巨大的肚子十分骇人的鼓在玉米地面前,被阳光照出了刺眼的反光”[1]181。作家强调着肚子的巨大与骇人,直观地呈现着正在孕育新生命的躯体,营造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也在无比真实的场景感中展露出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然而,外界伦理规范道德又使得这个生命的到来是如此地不合时宜,巨大的肚子与周遭的一切显得那么格格不入。这种突兀感和生命力共存的状态,使得整幅画面具有了强大的张力。
在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毕飞宇也对女性生育时所散发出的强大生命力有着细微的描写。作家用“绵延温暖的奶香”“浓郁绵软的乳汁芬芳”等形容,为女性哺乳的场景打上了一层柔光,使得整幅画面具有了圣母一般的美好与圣洁。毕飞宇借小孩旺旺的视角肯定了女性生育的价值,女性的身体不仅仅承担着生育的生理使命,同时也承载了女性作为人而具有的温情和怜爱。当然,女性主体对生育的态度无法通过个体案例得出确定结论,生育于女性而言是需要被放在具体语境之下被阐释的。但显然,毕飞宇并未抹杀女性身体在生育过程中所具有的自我能动性的意义,而是在着力发掘平凡女性在生育时所面临的外部影响和内部更新。
在毕飞宇笔下,处于生育过程中的女性身体呈现出和谐与矛盾共存的特质。透过受孕的身体,既能看到女性身体在作为生命伟大创造者时所展现出来的自然人性的光辉,同时也能感受到个体价值、社会角色之间难以完美契合的冲突与悖论。女性生育过程中的身体同时承载着生理功能与社会身份,它是自然生命与社会文化权力的交界,因此通常也是和谐与矛盾共生的复杂地带。
二、生育背后的权力世界
毕飞宇曾这样表达过对权力的关注:“权力,或者说极权,一直是我关注的东西。”[2]何谓权力,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对此概念进行过这样的阐释:“权力是一个过程经由不断的斗争与对立、转化、加强或倒置力的关系;(权力)是这些力的关系在彼此间找到的支持,于是形成一个锁链一个系统,或是相反的,是这些力的关系的歧义与矛盾,使得它们彼此孤立。”[3]福柯在此强调的重点是,权力不是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权力是各种力量关系相互运作的复合体。小说人物的命运也在各种复杂权力关系的推动下铺展开来。
(一)男权凝视
对于长期浸淫在“生男有用、生女无用”封建生育文化中的人来说,重男轻女的观念是极难去除的。在《玉米》系列小说中,表现“生男执念”的描写比比皆是。主人公玉米的母亲施桂芳已经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却仍然坚持不懈地期盼着能诞下一个男胎。提起自己曾经流产的三胎,施桂芳“每次说这句话都要带上虚设往事般侥幸的心情,就好像只要保住其中一个,她就能一劳永逸了”[1]2。“一劳永逸”这个词精准地展现出了施桂芳的内心,对于施桂芳而言生育是一种劳动,而生出儿子才意味着使命的终结。施桂芳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生育机器,用子宫盲选着那些“不是丫头的种子”,赌注式地产下一个个孩子以期上天能赐予她一个男婴,至此才迎来她价值的巅峰,同时却也是其自身生命(作为女人甚或作为母亲)的落潮。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玉米,不仅见证了父母一定要生男孩的疯狂,也感受到了生出男孩后母亲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因此,重男轻女的理念也潜移默化地在玉米的心里生根发芽。玉米无比认同男权社会 “重男轻女”的价值判断标准,母凭子贵,她能借由儿子获得权力的分割。而一旦这个希望落空,生育对于玉米而言则失去了意义,其婚姻的价值也就此大打折扣。
事实上男权对女性生育的影响并不全然都是直接或外在强制的,而是更多地根植于女性对权力的潜意识认同。正是女性对权力的崇拜与认同,她们主动或被动地习惯了男权凝视下的一切规则,自然而然地汇入主流话语之中,成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接受者、参与者,甚至是积极生产者与同谋。
(二)俗世权力
在民众的日常社会关系和普通生活中,权力通常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特权。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中,读者能清楚地看到一套权力等级体系。当然,权力的高位与低位只是相对的概念,权力是流动的。一旦低位者获得权力,仍然会从权力的受虐者转而变为施暴者。
凯特·米利特认为:“支配地位和权力在性活动中具有重大作用。”[4]掌握权力的高位者等同于在生育活动中位居高位。在小说《青衣》中,筱燕秋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交换条件献给老板来获得上台表演的机会。权力渗透进性爱,进一步改变了性爱的性质,将性爱变成了商品或交易的工具。当权力已然操控到内心时,权力支配等于性支配是必然的结果。
在小说《玉米》中,变味的权力之性的猖狂弥漫,几乎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凭借支书身份,王连方可以任意地在全村的女人中挑拣选择,在权力与性的交织中,王连方仿若立于金字塔顶端,享受着其中随心所欲、无人阻挡的快乐。在毕飞宇笔下的世俗社会里,权势和地位所带来的特权是被人们基本认同的。权力的低位者被动地屈从,充当被占有和征服的对象。在毕飞宇的小说世界中,无论男女,都被囊括在这套权力层级体系内,每个人都是权力发生作用的一环。毕飞宇并不意在突出两性权力对立,而是指出了现世的权势,亦即人们所处社会地位所形成的环环相扣的权力秩序,是如何通过身体关系施加于身处权力低位的弱势群体之上的。
在王家庄,世俗权力成为凌驾在家族关系、性别关系之上的决定一切的价值标准,全面异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与日常生活。例如,当王连方由于触犯军婚失去权力后,转变成为权力的低位者,其女儿便遭到了村民的报复。毕飞宇在描写施暴场景时,用的动词“摁、顶、塞”,无一不带有强烈的力量性和侵占的属性。施暴者要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以同样的方式还回去。生存在这套权力运行机制下的人们,或是对权力规则深信不疑,或是以一己之力无法打破规则,因此他们都在等待着自己拥有权力手柄的那一天,将以往遭受过的屈辱、痛苦报复性地施加给新的权力低位者,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如此,权力体系的内在结构得以不断巩固、加强,直至成为权力的死结,无以化解。
毕飞宇看似在其小说中突出表现的是女性在各种权力关系中被侵占被欺压的困境,但实际上作家是在借着写女性的外壳写人性。权力关系的形成需要施加者和承受者,而女性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作为普遍的承受者身份而存在的。生育书写所聚焦的权力关系是复杂且模糊的。权力之间相互影响,又综合地对个体发生作用。在大多数时候,毕飞宇作品中所描写的权力都指向一种琐碎化的、日常化的权力。这些权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进入到平凡人生活之中,对个体日常的行为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作家的着眼处不是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而是处在权力关系之下的人们是如何被影响又如何自处的。
三、权力困境中的女性突围
权力关系虽然无可避免地包含了主导与屈从、宰制与被动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铁板一块,或只是单极化的效应,而是一种处于动态平衡中,由诸多微观权力交错互动,呈现出充满诸多不稳定因素的网状结构。毕飞宇注重表现人性,他以平等包容的眼光看待人的行为,也包括弱势者的尝试与抗争。在权力关系的动态拉扯中,他总是极力避免将女性置于完全静态的屈从主体的位置。
(一)自我赋义
伊格尔顿曾说:“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5]在《玉米》小说中,主人公玉米的抗争之路也从身体开始。当玉米与飞行员彭国梁感情失败后,玉米选择用十分极端的方式来完结自己的处女之身。玉米在对自我的掌握中终于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通过这样极端的对自己身体的处理方式,她宣泄了内心激烈的情感,也是对自我尊严的重掌和对既有权力的抵抗。尽管这种方式里有挥之不去的无奈甚至是自虐的意味,但不管怎样,她从宿命论的悲哀者一跃成为自我命运的主人,她不再处处被动,而是成为了自我生活世界的行动者和创建者。
处女之身原本就是男权对女性身体凝视的结果,是“他者”给予女性的一种特殊的身份标识,因此女性身体的自我掌控,既是对男性权力控制的一次反抗,也是一次清醒的自我确认。正如学者王韬所言:“女性真正的觉醒正在于女性向着自己身体的还原,女性只有破除掉身上一切男权话语的文化积淀,只剩下作为本原性的身体存在,并从自我本原性的身体存在出发时,才能彻底地捍卫自己女性话语的纯洁性。”[6]
这种具有自我赋权意义的身体不仅是爱欲的身体,还包括作为母亲的身体。从女孩走向母亲,生育意味着生理意义上的身份转变,而精神层面的角色转变则来源于女性内心母性意识的唤醒。母性对于女性生育而言,是主体内部最原生朴素的一种生育驱动力。小说《玉米》中,玉米和柳粉香对待肚中不符合大众伦理道德的孩子都产生了爱怜之情。事实上,这也是女性在生育权上从失语状态中挣扎苏醒过来的自然母性的复苏,是作为独立个体意识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把握和认同。以往,男权文化控制了女性“为谁生”“生什么”的生育文化规则,而一旦女性源于自身母性,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养育孩子便是对生育权的重新掌握,生育不再是被给予的义务,而是基于女性自身主体选择的自我文化价值的赋予。
透过小说文本不难看到作者隐含的态度。毕飞宇看到了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无奈一面,但同时并不否认女性主体的生育愿望。毕飞宇意识到生育承载了社会的多重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毕飞宇似乎在引导女性向内探求,他希望女性对自我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让生育成为更自由、更自主的选择。
(二)权力争夺
作为男性作家的毕飞宇在书写女性方面的可贵之处之一便是,他并不是一味地站在男性的角度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生存境遇,而是将女性放在政治、经济、权力的社会语境下,关注她们身处的生长状态。
在小说《玉米》中,成长中的玉米经由一系列打击逐渐习得了自己身处的这套权力规则,并将自己所仅能倚仗的身体与生育转化为了权力依附的筹码,玉米秉承着“不管怎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的准则寻找权力依靠[1]75。从玉米婚后愈发极端的争权行为中,可以看到她对于权力的狂热。她就如同每一个平凡人一般,在苦难中寻求出路,在飘零中寻求傍身之所。玉米对权力渴望的背后,是她对于“要更好地活着”的一种质朴渴望,尽管这种渴望也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
性往往是女性受到掌控与压迫的焦点,但同时也是女性抗争的空间。玉米利用性和生育进行权力争夺,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权力空间的一种解构。女性不再完全处于被动支配的地位,生育是女性用以斗争的资本与工具。从无意识到自我选择,是女性处于男权、夫权、父权等多重压力围困的社会语境下,主体意识向前试探的一步。不过对于玉米而言,这向前的一步还是相对有限的,最终,作为女性的玉米还是没有通过权力依附的方式突破男权的压抑,继续扮演着被损害和扭曲的角色。
正如福柯所言:“我所谓的反抗(身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它并不先于它所反对的权力。它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7]毕飞宇小说中的女性与权力便是如此共生的关系,无论权力对女性如何挤压都无法完全掌控女性的身体,在权力关系的控制中,女性自始至终都在生育活动中保留有一部分的话语权。
毕飞宇曾在接受访谈时谈及写作时的性别意识,自陈只是对性别特质进行还原,而并不会过于在意性别区分问题。他说:“性别在我这里从来就不是问题。……即使我写她的性行为、怀孕、例假等非常女性的特征,我也不会十分在意她的性别,因为她是那样的。”[8]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性别作为人物本身属性的一部分而存在,并非是突出表现的部分。毕飞宇通过女性的尝试与抗争,所要表现的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权力互动关系中,人的困境、尊严和勇气。
(三)生命力的彰显
品味毕飞宇的语言,其实不难发现毕飞宇在生育书写中刻意的冷静节制。他乐于当一个呈现者,将自己观察到的世界以较为客观冷静的方式摆在大家面前。他参与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又似乎能够游离出来,与这个世界进行平等直接的对话。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毕飞宇似乎更喜欢将景色环境与生育活动联系在一起进行大篇幅的描写。如小说《玉米》中,在玉米办喜事那天恰好是夏忙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大地丰乳肥臀,洋溢着排卵期的孕育热情。……它们是水做的新媳妇,它们闭着眼睛,脸上的红润潮起潮落”[1]74。毕飞宇在这一段大地景色的描写中,对夏耕的繁忙景象做了极尽的渲染,洋溢而出的是对大地强大生命力的向往和赞美。柏拉图曾经这样阐释女人和大地的关系:“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方面,不是女人为大地做了榜样,而是大地为女人做了榜样。”[9]女性与大地的孕育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一脉相承的。毕飞宇将等待播种的土地比作排卵期的女人,看似是写大地,实际上是在写女性,这种地母般的旺盛生命力实则也是毕飞宇笔下女性角色身上最突出的魅力。
具有强旺的生命力几乎是毕飞宇笔下人物的共性。毕飞宇笔下的这些女性们,生活在男权话语、普世权力、封建道德等多重权力话语的包围中,在各种桎梏之下,她们处境艰难。但她们也一直处于努力生长和内部更新的状态。尽管在现实层面,这种生长更新是有限度的,她们无法彻底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但其权力抗争和自我赋权的行动力仍然能给予人们一种不断尝试、突破困境的勇气和启示。透过女性的生存之境,可以反映出人类的某种悲剧性宿命,但从一种类似于地母精神般的生命力量中,不难发现一种从未停止生长的新的可能性的存在,或许,这便是女性符号在社会存在中最基本的,同时也最具原生性的意义所在。
尽管作家自陈,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急切地追求着这样一个答案,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沉稳的状态。毕飞宇无意让人们去克服人性的弱点去走一条模板化的成功之路,他认可一切经历的合理性。毕飞宇在小说世界中渴望看到人们回归本真的自我,尽管他们的行为越出了大众道德的界限,但毕飞宇无意对此进行批判。毕飞宇的态度是自由而包容的,人性并不总是美好的,人性的罪恶同样是人身上的一部分,这才是人性的真实。毕飞宇关注的不是“伦理的人”,而是“感性的人”,这种态度是一种对个体经验的肯定,对世俗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人性的肯定。
四、结语
毕飞宇曾说:“需要强调的是,我‘久久望着’的其实还是人的命运,准确地说,我们的命运,我们心灵的命运,我们尊严的命运,我们婚姻的命运,我们性的命运。”[10]正是借由“生育”这个人类生存的切口,毕飞宇向人们展示了个体生命的存在状况,并在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追问中直抵人性深处,探索和思考人之生存的种种可能。这样的尝试,或许本身也是文学介入现实的一次小小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