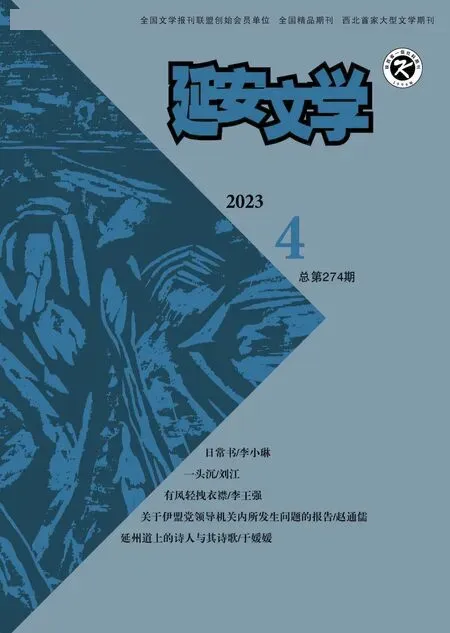西地平线上的落日和星空(外一篇)
2023-02-19孟澄海
孟澄海
太阳还没有落山。
或者说,这里本来没有山,黑戈壁上只隆起着饕餮般的沙丘。太阳就悬浮在一层青灰的烟尘之上,光线呈现出暗红或苍黄颜色,沉落之前,犹若祭坛上浑圆的铜鼓,喑哑、悲凉、凝重……
那时候,我已来到居延海边。
风吹过来,我感到身上已没了祁连山雪花的冰凉,而是一种令人心烦的干燥与闷热。能看见风的背影,卷着沙尘在远方奔跑,鬼魅般飘起又落下。几十只骆驼站在风中一动不动,恍若褐色山崖。居延海就在风的背景下展开,湛蓝或澄碧,雪浪涟漪,一圈一圈由里向外荡漾。火星一样荒凉的巴丹吉林沙漠,却环抱着这么一个水泊,令人想起审美的悲壮和崇高。《圣经》上说,神灵无处不在。神有意造海,水就来了。其实,在时光远方,神就是自然造化,掌握着秩序规律。人类足迹尚未抵达这里的岁月,神给这里安排了天堂般的环境:泽乡水国,芳草野花,锦鲤银鸥……
很静,我站在岸上,弯腰掬起一捧水,轻轻靠近嘴唇,清凉,甘洌,依然有黑河源头的气息和味道。水湄边,是干净柔软的黄沙,被水浸润过,泛出盐碱的斑渍,泪痕一般。周围长满芦苇,璎珞般的穗子在风里摇摆,苇花四散飘扬。夕阳余晖,牵着细密的光线,穿过芦苇荡,将金箔一样的光点洒向水面,与粼粼水融合在一起,如梦似幻。天鹅飞起,白鹭落下,归家的路已被暮色占领,但羽毛和翅膀依然明亮,晕染着落霞的色彩。
我的四周黄沙漫漫,死亡般的孤独无处不在,而这一刻,突然感到居延海就像一颗硕大的冰蓝露珠,悬挂在灵魂深处,湿婉,细腻,深情脉脉。
落日下,万灵归于阒寂,海水渐趋深沉。从我站立的角度望过去,波心里还有云朵的倒影,缓缓游弋着,若隐若现,似真似幻,以默言的梦境告白天空。我脚下长着零星的荒草,草间是蚂蚁的家园,洞穴密布,营垒森严。我发现一群蚁正抬着蚁王的尸骸,整齐有序地向它们的墓地走去。生灵都有人类不可知晓的秘密,也许在居延海尚未出现的年代,蚂蚁就在此地创建了王国,它们加冕与丧葬的礼仪持续了亿万斯年。也许,在它们的记忆中,这浩渺辽阔的水域,只不过是前尘往事里的一滴泪水。
书上说,居延海是黑河的闾尾湖。闾尾一词出自《庄子》,意思是水的归宿。那个洞悉天地宇宙奥秘的哲人,认为万物运动的最高境界为自由自在,逍遥快乐。黑河古称弱水,发源于祁连山,流经青海、张掖、酒泉,最后穿过茫茫戈壁荒原,魂归漠野,最后汇聚成波光潋滟的巨大海子。《山海经》记载,昆仑山由弱水之渊环绕,山上有昆仑悬圃,西王母就住在那里。中国许多神话传说都与此水有关。最叫人产生联想的还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对林黛玉的那句爱情表白: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一条沧桑孤独的内陆河与爱情扯上瓜葛,至少也增添了几分婉约柔美的色调。
这是我第二次沿着黑河西行,乘车旅游,走走停停,或拜访古迹,或体验风光,时间安排宽裕,心情自然闲适轻松。记得第一次去额济纳看金秋胡杨,行色匆匆,一路上似乎见到除了戈壁荒漠,就是黄沙白草,所有的风景都笼罩着蛮荒苍凉的色彩。那时候,正是青春在身,满脑子都浮现着边塞诗的意象: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西风里的流云,流云下的古堡和驿站。跟几个写诗的朋友坐在黑河岸边的古渡上,看着太阳穿过胡杨林,慢慢接近西地平线。纷纷扬扬的胡杨叶片,从树冠飘落,带着橙黄或暗红的梦幻,覆盖了我们的惆怅和忧伤……
三十年过去,诗化的激情逐渐淡化,人间烟火堆积于心,有了一种沧桑厚重。向西远去的头一个夜晚,我伏案读帕斯的太阳石。帕斯自称这是时间之诗。他受阿兹特克太阳历史影响,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时间,一种是线性的,即充满暴力的人类历史;另一种是非线性的,恰似宗教的神圣节日,已被人类丢失。古代墨西哥人的金星历让帕斯着迷:金星既是启明星,又是长庚星,具有死亡和复活双重品格;它每隔584 天在同一位置与太阳重合。帕斯想探寻像金星那样切入宇宙时空的永恒瞬间,《太阳石》因而采用584 行,首尾6行重复,构成环形结构。读完帕斯的长诗,我感到那些玄奥的意象背后还有看不见的东西,旋转的时空隐含神秘的内聚力。
2019 年秋日的某个傍晚,我从金塔县城出来,走进了黑河东岸的一片荒原。这里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不见人烟。视野里除了石头和蓬蒿,只有空空荡荡的黄昏暗影。黑河无声无息,仿佛应了某个神灵的召唤,流向地老天荒的远方。我斜躺在岸边的一个沙丘上,抽烟或小憩,让身体像沙蜴一样舒展开,尽情享受漠风的吹拂。也就在那个时刻,我看见了帕斯诗中的金星。她悬浮在祁连山偏西的天空上,饱满灿烂,在山岚的映衬下,周围氤氲了一个淡蓝的光圈,现出几分孤绝的神秘。如果按照帕斯的说法,沿着金星闪亮的光线前行,就可抵达时光永恒的彼岸。我的猜想是,也许金星能让时间倒流,使消逝的历史现场重新回到当下,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纷纷复活,穿过我们好奇的眼瞳……大地之上,天穹之下,大漠戈壁空空荡荡,死寂如夐古的梦魇。
事实上,我在金星微光斜照的地方,只发现了一处烽燧。当地朋友告诉我,那个烽燧就是汉代的肩水金关遗址。汉武帝时代,设置河西四郡,为了巩固边陲,连通西域,在黑河沿岸修筑了许多关城驿站,而肩水金关便是其中之一。阙楼早已坍塌,瓮城不见踪影,歌榭舞台被雨打风吹落去,就连烽燧上的黄土也年复一年剥蚀消减,成为光阴的记忆。曾经滞留于此的戍边将士、商贾驼队、诗朋词侣、墨客高僧……都凋零于无边的旷野之中,葬于风,埋于雪,然后消弭、飘散于虚空。
在戈壁,死亡是焦黑的,更悠久的死亡是白炽的,茫茫白砂,是时间风化的尸骨。许多世代过去了,许多地质年代已经迷茫。烽火依旧。死亡能够禁止一切,已知,未知,历史以及未来,记忆或者猜想,禁止鸟群从上空飞过,禁止月色暗示潮水……烽火台独立西风,但不仅仅指向天空。它伤痕累累,一年里总要将身上的灰尘放弃一次,如同一棵树,根系向下,令枝蔓拥有向上的力与渴望。而那最后一片叶子,最后一朵花,在飘落之前正努力写下对时间的告白。
而在时间幽深寒凉的黑夜里,有一种神秘的物质深埋地下,它们是书写着汉字的简易木牍,宛若灿烂的星斗在另一个遥远的时空里静悄悄旋转,等待着与人类相遇。
1930 年,由中国、瑞典的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肩水金关的烽燧周围出土汉简近1 千枚。1973 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掘汉简1 万多枚。内蒙古居延地区一次性发掘出土如此多汉简,这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世界,人们把居延汉简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并称为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居延汉简,内容均为两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辖区内的屯戍文字,它出自当时中下属士吏之手,非为艺术而书,是一种本色的呈现。试想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驻边扎寨的将士们显然不可能像书斋里的文人雅士,悠闲地推敲着一笔一画,一切皆随意潇洒。于是我们看到居延汉简的轻松自如,恣意率真,信手写来,其飞动的线条和纵横开张的间架造型都是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感情流露。当然,军卒书写时也许还不知书法是何物,更谈不上士大夫阶层浓郁的文化气息。但他们无心拈来的书迹却正是书家日夜追求的童年纯真。汉之拙朴自然,汉之雄浑狂野,都蕴含在文字书写的点横撇捺之中,凸显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
河汉横亘天穹,星月的光辉默默映照人间。从酒泉到额济纳,我发现黑河两岸的秦关汉城或沉没,或倾圯,只剩下孤独死寂的废墟。废墟和古渡的傍晚,羊群正穿过碎石的河道,尘土飞扬,去向不明。玄奘渡河西行,鸠摩罗什去往中土,都要穿越此地的西风流云、星光月色,如今一切都成烟云,空留黑河浩大的水势,如诵经声。居延海边的黑水城已成千年遗址。岸边的佛塔依旧守护着神灵渐弱的呼吸。我不知从祁连山黑河源头到居延海,从此岸到彼岸,已有多少故事像河水远远流逝。今夜,在这远离城市的荒凉地方,在这西地平线上的一个叫居延海的蓝色水泊岸上,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河汉无声,鸟翼稀薄,云朵向群星疯狂地生长,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我成为某个人,某间点着油灯的陋室,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放大了胆子,住进了星光的呼吸里……
天马飞过山河大地
过敦煌,朋友们都去了莫高窟。
二千多年的朝圣路,依旧人来车往,悬壁上的佛端坐西风流云之间,吸引着凡尘目光。但人心已经不古,物质至上的时代,站立仰望或伏身跪拜,灵魂再也无法抵达三危山顶的莹莹白雪。
我踽踽独行,来到了一处水洼地。
当地人把这里称作寿昌水库,其实它就是一个海子,古称渥洼池,水浅,澜静,鱼翔,鸟飞,幽蓝纯净得像一个梦境。几千年来,那个梦境里泊着天光云影,还有芦花与红叶,还有上古时遗留的星月呼吸……
岸上长满了草,野花斟满霜花,摇一下滴落露珠,再摇一下便招来白翅黑斑的蝴蝶,它们和周围的童山秃岭构成强烈对比。秋天里,生与死,繁盛与衰败,在此地都有另类的美学意义。
坐在一棵胡杨树下面,头顶上罩着金黄的树冠,身边翻飞着金黄的落叶,脚下跳跃着金黄的夕晖光斑,我恍惚置身于一座金黄的神殿之中,心绪顷刻平静了下来。对胡杨而言,时间即是虚空,她不在乎生老病死,与沙漠戈壁对晤千年,一旦衰朽,依然独立西风,将铮铮铁骨指向苍穹,向人世传达神的隐语。
暮色降临。有牧人赶着几匹骆驼走过渥洼池,弦月下,雾岚与月色交融,掩映着骆驼高大的身躯,剪影般若隐若现。远处的鸣沙山与月牙泉已陷入暮霭,更远处的祁连雪峰只剩下钢蓝的轮廓,头颅深埋星空,孤独如我。
突然想起暴利长,那个活在历史传说中的河南人。
地方史志上说,汉武帝元狩三年,生活在河南新野县的小吏暴利长,因犯罪罹刑,被当地官府充军发配至西北边陲敦煌,到渥洼池畔开荒屯田。那些日子,暴利长时常去水边放马,他发现来自祁连山上的一群野马,每天黄昏都飞奔到渥洼池边饮水。一天,他在野马群中看见了一匹与众不同的骏马。这匹马鬃毛披拂,骨骼挺拔,枣红毛色,跑起来四蹄飒踏生风,周身闪耀着光芒,宛如一团燃烧的火焰。
暴利长为了捕获这匹野马,就用泥土捏塑了一个假人,让它手持马笼头和缰绳立在水旁。时间久了,野马对假人习以为常,失去了警惕,暴利长便代替假人,亲自手持套索立于水旁,趁马不备时将其套住。他闻知汉武帝酷爱良骥,便把此马说得神乎其神,并诡称它是从渥洼池水中跃出的马,后来托人将马献给了武帝。汉武帝本是个十分爱马的人,之前,曾通过祭司占卜,在卦辞中得到了“天马当从西北来”的神谕,于是派人到西域乌孙国去探寻天马。这次,当听说眼前的这匹马从池水中跃出,且能腾云驾雾,日行千里,自然喜出望外,认定此马便是太一天神所赐,立刻命众臣齐聚皇宫,稽首拜贺,并展开木简,亲笔写下了《天马歌》,歌曰:
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
读《汉书·武帝纪》,有这样的记载,“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班固是严谨的史学家,他生活在东汉,彼时,武帝的茂陵早长出白草黄花,他只根据前人的说法,小心翼翼写下了一句话,记下了马出渥洼池的具体时间。至于那个暴利长以后去了何方,落脚哪里,我翻遍所有史书,均语焉不详,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史书阙如,倒是民间故事一直没有泯灭,传说武帝自得到天马后,龙颜大悦,降旨赦免了暴利长的罪过,并赐给他养老的俸禄,不久,他便骑着一匹白骆驼离开敦煌,东归洛阳。
暴利长做梦也没料到,由自己编织的一个美丽谎言会改变后半生命运,使他重回桑梓,安度晚年。更不会料到,他垦荒牧马的地方,那个幽蓝清澈的渥洼池,会走进煌煌史册,千百年来被文人骚客反复叙述、咏唱,成为充满神秘色彩的天马故乡。
没有风,渥洼池的四周一片阒寂。黄昏的月牙如蓝菊花瓣,漂浮在水面上。历史的天空下,时间就是一个水滴,一片水泊,从不同角度折射着时空岁月,如梦似幻,迷离渺茫。我恍惚走进了博尔赫斯笔下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于时间迷宫里盘桓、逗留,眼前忽而是明月青天、霜冷长河,忽而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乍见烽火狼烟、鸣镝啾啾的战场,又闻丝绸之路上幽怨的琵琶羌笛……
我相信,在狂野拙朴、胸襟浩荡的汉朝,那一匹凌空翱翔的天马,就是一个时代的隐喻。
事实上,马出渥洼的故事流传开来之时,汉朝与匈奴的战争已经结束,那个逐水而居、弯弓射雕的游牧民族,在留下一曲“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的一曲悲歌后,便消失在茫茫朔漠,从此音讯杳无,去向不明。之后,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长安西望,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若珍珠般串联在一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魔幻的电影场景:天空湛蓝,白云朵朵,一匹马展开宽大的羽翼,迎着万里长风,自由自在飘弋、翱翔、腾跃……马嘶嘶而鸣,叫声震动山河大地。马的翅膀下掠过西北的雪山、荒原、沙漠、绿洲,以及废墟、老城、石窟、寺庙、村庄、汉墓群、古战场。那时候,马的眼睛深沉如夜,所有的梦幻往事和夐古岁月都在那海子般的瞳孔里沉淀,并发出光芒。在辽阔浩瀚的苍穹之上,马的视野里铺展开血管似的驿道,那上面点缀着丝绸、茶叶、琥珀、玳瑁、香料、佛经、儒典,还有商贾和驼队,诗人与僧侣……这就是丝绸之路,一条连接了东西方物质、财富、精神、信仰的文明大通道。蚕以心血结茧,吐出雪白的丝,然后再由人织出丝绸,它本来是一种生活物品,柔软,美艳,色泽斑斓,穿着于身,便可显出人的身份地位,代表了优雅高贵,精致富丽的江南生活方式。然而,当十九世纪的李希霍芬把这种商品写进《丝绸之路》后,它便从物质层面转化为一种精神与气象,成了拓荒、西进、光荣、牺牲、开放和胸襟的代名词。
天马行空,在文人笔下如同一个雄奇意象。罡风浩荡、壮怀激烈的时代,突然闪现于梦境,于是就有了天马的影子,它带有神性和灵气,或者说就是一首大气磅礴的边塞诗。有汉一代,武帝刘彻雄才大略,眼界阔大,他的胸襟与气度,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文人的表述,这种时代精神体现出“奋迅”“骋驰”“奔扬”“驰骛”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快速、骤急。据《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载,汉代宫廷盛行赛马,而汉武帝极为热衷这项游戏,经常下旨让百官举行“驰逐”活动。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和陶俑中,有不少赛马的形象:骏马飞驰,互相追逐,骑手则抖缰扬鞭,躬身伏于马背,做出与马飞行的动作。《淮南子·说林》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同时喜欢骑马狩猎,亲手射杀黑熊和野猪,他挽弓纵马,追逐野兽的放犷行为,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汉书·陈汤传》记述西汉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的,而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
双翼凌空、扶摇而上霄壤的天马,象征了一个时代的青春力量。卫青、霍去病、李广、赵破奴、张骞……一长串载入青史的名字,都有着天马的品性与精神,他们智慧、勇毅、蓬勃、狂狷、豪迈,舍家别土,西行远征。为了大汉的社稷江山,敢于校场点兵,长河饮马,血染黄沙。黄钟大吕的汉朝,主旋律昂扬向上,阳刚之气充塞天宇,龙马精神元气淋漓,不闻靡靡之音,不见颓废之态,每一个热血男儿都有机会张扬自己的才情与魄力,奔赴西部苍茫大地,或纵骑驰骋于烽火狼烟之中,或行走于驼队商旅之间。那个时代,青春拥抱着雪山荒原,弱水河畔,芦花飞扬,西部的长河落日间,一直回荡着青春少年的英雄浩歌。
多年前,我旅行至武威,在凉州博物馆见到了“马踏飞燕”的青铜雕塑。据当地朋友讲,这件文物出土于雷台汉墓,是一个张姓将军的陪葬品。那个早晨,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窗上照进来,落到了铜奔马身上,光与影或明或暗,游弋变幻,铜奔马仿佛有了微微动感。我仔细观察,发现这匹马躯干壮实饱满,四肢修长,匀称轻捷,三蹄腾空、飞驰向前,一蹄踩踏着飞燕翅膀,而燕子吃惊地回过头来张望,燕子与奔马同时显出一种凌空飞翔的姿势,动作轻盈、迅捷,力量和速度,激情与梦幻,凝固于青铜造型之中,大气磅礴,美轮美奂。
朋友告诉我,雷台汉墓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有一个马俑胸前有铭文记载:“守张掖长张君”之墓,而从墓葬发现的银制印章,由于深埋地下,印文锈蚀剥落,漫漶不清,仅可隐约辨识“将军章”几个字,专家、学者各述己见,聚讼纷云,有人认为是破羌将军、武威太守张江;有人认为是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武威太守张奂;也有人认为是张奂的小儿子武威太守张猛;还有人提出是宣威侯、破羌将军张绣或汉阳太守张贡。近年又出现新的观点,说长眠于此的很可能是前凉国王张骏以及中国道教祖师张道陵。
其实,在我看来,墓主人为谁已不重要,二千多年岁月,陵阙坍塌,棺椁腐朽,肉体早化作一抔尘埃,即使考证出结果,其姓名称谓也不过是冰凉的符号而已。我想到的是,张姓将军驻守武威,戎马一生,当肉身陨落之后,身边的故旧部下定然为他举行盛大葬礼,金银玉石、绫罗绸缎并不稀罕,最要紧的是陪葬一匹青铜宝马,让它背负将军的灵魂,在来生继续飞行于浩瀚蓝天……
渥洼池的天马展翅飞翔,从大汉飞到了盛唐。
唐开盛世,骏马立下了赫赫之功。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太宗李世民亲自出战,陷阵摧敌,追亡逐北,他先后参加了六次战役,骑乘过六匹战马,它们的名字分别是:飒露紫、卷毛騧、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李世民登基后,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园,于贞观十年下诏,将六匹马的英姿琢刻于石屏之上,镶嵌在昭陵北阙。同时亲题赞辞,记载马名、肤色、乘用时间、所负箭疮等等。从此后,昭陵六骏闻名天下。
唐朝定鼎,天下一统。贞观年间,唐太宗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合达到了顶峰。当时有西域二十多国的君主及其代表集聚长安,奉太宗为“天可汗”。从此,由长安向西,可自由横穿整个欧亚大陆,直驱地中海东岸的安都奥克,全长约七千多公里的驿路古道,商旅逶迆,马帮骆队络绎不绝。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七至八世纪的长安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被称为“世界性首都”。如同汉武帝一样,唐太宗也酷爱良马,他虽然没有把“昭陵六骏”命名为天马,但那些马同样具有天马的气质和精神。李白在他的《天马歌》中写道: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
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
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
诗人笔下,这匹长着虎文龙骨、绿鬓飘扬的天马,所指即是蓬勃的时代气象: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诗人通过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新的美感。它涵盖了盛唐文人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开阔的眼界,自由活跃的思想,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激奋昂扬的气概,展现了一个强大民族鼎盛时代的整体精神风貌。
弦月西沉,夜色弥漫开来,渥洼池水气氤氲,一片迷濛浑沌。我抬起头,看见天狼星座刚刚从西地平线升起。
敦煌已是万家灯火,我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