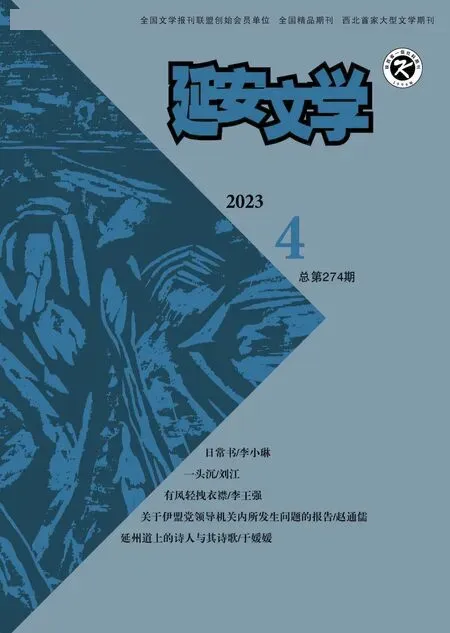摇曳的蒲公英
2023-02-19张伟东
张伟东
1
午后的阳光,透过镂空的碎花细纱窗帘斜照进来,给发廊的地面涂上一层金色的光斑。
虹姐格外亲热地拉了一下我的手,将我摁在美发椅上。椅子的中轴安有一个液压装置,底座边缘有个脚踏板。虹姐的高跟鞋踩住脚踏板,咯噔咯噔几下,就将美发椅调到了适合她操作的高度。
我长得又黑又瘦,脸上还花花搭搭地挂了几个雀斑。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我都进入青春期好几年了,胸脯看上去还是像飞机场一样溜平,没怎么发育。我太在意自己的身材和长相了,老觉得自己丑,心里不免生出几分自卑。这发廊里面的镜子实在太亮,晃得我一点自信都没有了,我怯怯地低垂下脑袋。
虹姐看着很年轻,那是她保养得好,年过四十了,身板儿一点没走样。漂染成酒红色的靡撩卷发被她挽成一个别致的发髻别在脑后,露出一截象牙般白皙的脖颈,很有几分成熟女人的韵味。她静静地站在我身后,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用心端详着镜子里面的我,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拿手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让我仰脸瞧着镜子里的自己。她手里掐着一把“匠士”剪刀,咔嚓咔嚓地开始精心修剪我凌乱的头发。
虹姐简直就是一个魔术师,还不到半个钟头,镜子里的我,就明显有了变化。原来参差不齐的头发,让她修剪得特别有型:里面的那一层有点短,外面的略长,向里勾着,垂在额前的刘海儿,自然地偏向一边,露出我自以为清秀的眉眼来。
接下来,虹姐开始给我化妆。先拿洗面奶给我洗脸,洗好后用毛巾吸干,第一层用的紧肤水,轻轻地拍打,吸收了之后再抹乳液。虹姐的手指细巧而柔美。她极有耐性地拿她的纤纤玉指,在我两边的脸颊上画着圈圈。按摩了一会儿,给我用了打底霜。她说我脸上有斑,所以,底霜要打得厚一点才行。打完底霜,开始扑粉。我的皮肤有点干,虹姐就给我用了湿粉,只扑了薄薄一层。她说我的眉毛其实挺好看的,先拿刮眉刀简单地修了修,然后帮我画了眼线,涂了眼影。虹姐说我嘴大,皮肤黄,要把唇线画得稍微往里一点,唇彩给我用了暖色系的番茄红,她说这样能够提亮肤色。一番捯饬,再看镜中人,我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还是原来那个土不拉叽的李小敏么?简直是判若两人呀!
在虹姐发廊的那些日子,我不光学会了如何打扮自己,还学会了给客人做耳烛。耳烛是挺有意思的手艺活儿,是把一根空心的蜡烛插入客人的耳朵眼里点燃了,通过热气上升形成真空负压,把客人耳朵眼里的耳屎、鼻窦和大脑里藏着的有害物质给吸出来,这样不但可以去除耳垢,而且还能起到排毒和治疗失眠的作用。虹姐嘱咐我说,毛手毛脚的人干不了这个活儿,万一操作不当,熔化开的蜡油子不小心滴进了客人的外耳道或者是鼓膜上面,容易把客人烧成聋子。所以,每次给客人做耳烛的时候,我都是小心翼翼的。
有天晚上,发廊里进来一个满脸横肉的老男人。他要求做耳烛,虹姐就安排我过去伺候他。在一个小单间里,耳烛做到一半的时候,老男人嗷地一声叫,反手就一记耳光,将我打倒在地上。接着他一通嚷嚷,把虹姐喊过来。他向虹姐告我的状,说我笨手笨脚的,把他耳膜给烫坏了。虹姐拿一个袖珍手电筒,往他耳朵眼里照了照,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小敏,你咋就这么不小心呢?虹姐边说边给我递眼色,示意我给客人赔礼道歉。我委屈地说,虹姐,这事儿真不赖我,耳烛做得好好的,他突然就伸手摸我,还扒我的衣服,吓得我手一抖,才烫着了他。那老男人死不承认他摸了我,硬说我活儿不地道,把他耳膜给烧穿孔了,嚷嚷赔钱。虹姐问他赔多少?老男人伸出一个巴掌。虹姐说,五百?老男人说,五千,少一个子儿都不好使!虹姐抿嘴笑了笑,软声软语地说,不好使呀,那你等着啊,我这就找个好使的过来跟你说话。
虹姐转身拿起电话,拨通了,里面有个男人喂了一声,虹啊,啥事儿?虹姐捂着话筒说,遇上碰瓷儿的了,你抓紧过来处理一下。好的虹,你别怕,我马上就到!说完,那边电话就撂了。这边老男人继续摆出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哼了一声说,不拿出个五七六千的来,天王老子过来也不好使!
过了一刻钟的工夫,一辆“城市猎人”越野车,驰到发廊门口,吱嘎一声就刹住车。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从车上跳下来,回手“砰”地一声关上车门,震得窗玻璃嗡嗡直响。中年男人梳着个大背头,有一张麻子脸。进屋后,虹姐把他拉到一边,耳语了一番。麻脸男回过身来,从腋下夹着的公文包里拽出五百块钱,摔到老男人脸上。
老男人睖睁地看着麻脸男说,你他妈谁呀你,就这点钱,打发要饭的呢?这当儿,我瞄见麻脸男右手朝自己后腰里摸。他麻利地从衣摆下拔出一把手枪,黑洞洞的枪管顶在老男人脑门子上。吓得老男人两条腿打哆嗦,差一点就跪在地上。麻脸男警告说,再不滚,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老男人立马就怂了,揣起五百块钱,转身跑路了。
事后,虹姐责怪我说,小敏啊,你做人也太本分了,不适合在发廊里工作。我倔犟地说,我来你这儿是学手艺的,又不是来卖身的。我这一句话,把虹姐顶生气了。她撇嘴说,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干服务行业,就是伺候人的活儿!我噘嘴说,来的时候,李洋也没跟我说清楚,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你这儿了。虹姐忿忿地说,既然你这么不懂事,那明天就不用上班了!
我以为虹姐只是说了句气话而已,没想到她真的做了辞退我的打算。第二天,傍午的时候,虹姐起床了,她没梳头,也没洗脸,就先给李洋拨了一个电话过去,叫他来发廊一趟,把我领走。
2
李洋不是啥大人物,就是一家职业中介所的小老板。我跟李洋非亲非故,认识他其实也没几天。
一天早上,我去他的中介所里找活儿。推开门的时候,里面乱哄哄一片,挤一屋子人。靠里面的墙角摆着一张老板台,桌面上并排摆放着两部电话机,还有一摞登记表。李洋坐在一把老旧的大班椅上,身子前倾,趴在老板台上,手里捏着一支碳素笔,一边询问求职人,一边登记,间歇还要接打电话,忙得一头雾水。
当时,我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紧靠门后的一把塑料凳上。李洋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一直等到快中午了,求职的人都散尽了,才轮到我过去登记信息。李洋把他手里的碳素笔递我,然后推给我一张登记表。我把填好的表格递给他,他扫了一眼,看到姓名栏里写的是李小敏,原籍吉林省公主岭市,他亮起眼睛看着我说,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咱俩是老乡啊!
李洋的年纪,看着也就是四十出头的样子。我说,叔,您也是公主岭人啊?
他套近乎说,嗯嗯,咱俩不光是老乡,还都姓李,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此刻,我心里想的是,在家靠父母,可父母我早就指望不上了;出门靠朋友,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我人生地不熟的,两眼一抹黑,能遇见李洋这么一位同姓老乡还真是缘分,所以,我得攥住这棵稻草。
李洋问,你都会干些啥?我答,啥也不会干。他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啥也不会干,我怎么给你找活儿呀?
我说,我高中刚毕业,父母离异了,没人管我,大学也上不了。我出来呢,就是想自食其力,可我没啥手艺,所以,我说我啥也不会干,这么说有毛病么?
没毛病,没毛病。李洋嘴里打着哈哈,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拽出一沓用工单位信息表,翻了半天,最后把一根手指戳在一张表格上,抬头说,学美发挺好的,你可以过去试一试。
那张表格的左上角有一张名片,拿曲别针别着。李洋把名片抽出来,递我手里时,我闻到了名片上散发出来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名片正面印着“虹姐发廊”,反面是小字,印着服务项目:美容、美发、洗头、按摩、刮痧、耳烛,地址是春城大道156 号。我把名片揣进衣服兜里,然后掏钱给李洋。凡是来他这里找活儿的,中介费五十,成了不退,不成退三十。李洋有点不好意思接这个钱,客气着说,都是老乡,中介费就免了吧?
我说,咱都是背井离乡的人,谁出来打拼都不容易,再说,这五十块钱你也不白拿。
李洋愣愣地说,李小敏,你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我方向感不好,出门老是转向,麻烦你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
李洋笑了笑说,没问题,谁让咱俩是老乡呢,我开车送你过去。李洋自己有一台轿车,也不是什么豪车,就是一辆七成新的白色捷达,就停在旅馆的楼下。他的中介所开在旅馆的三楼,是租借旅馆里的一间办公室。那天,李洋开车把我送去了虹姐发廊。临走,李洋还不忘回头,嘱咐虹姐多照应着我点。
3
一次耳烛事故,我就被虹姐炒了鱿鱼。李洋过来把我接走了。回去路上,李洋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瞥我。见我低头一声不吭,他明知故问,怎么了?在发廊里干得不顺心呀?
我抹搭眼皮,嘟嘴说,顺什么心呀顺心?那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儿,明里打着美容美发的幌子,暗里做的是皮肉生意,你好意思把我介绍到那种地方去,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李洋说,李小敏,我开的是职业介绍所,又不是私家侦探所,我哪能对用人单位了解得那么清楚呢?我要真知道虹姐发廊是那种地方,我肯定就不会送你过去了。
李洋把车开到了旅馆的楼下,扫了一眼腕表说,都中午了,我们去对面的迎宾楼吃顿便饭吧。见我没吭气,他说,放心吧,不用你掏钱,我请你。
李洋找好了泊车位,我就下了车。他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他。那是一家新开业的迎宾楼,门口还架着拿鼓风机吹起来的彩虹桥,红地毯两边排满了花篮。一楼是餐厅,二楼以上是客房。餐厅里分中餐厅和快餐部,中餐厅只接待客人的预订,快餐部有独立的门脸,接待散客。李洋把我领进了快餐部,找靠墙角的一张小方桌,我们俩面对面坐下了。李洋将服务员递过来的菜单子托手里翻了翻,问我吃什么。我说,随便。李洋笑了笑说,没有随便这道菜。我说,我不挑食,你点啥我就吃啥。
李洋点了一盘地三鲜,两碗大米饭。那顿饭吃得虽然简单了些,但是却格外地香,即便过去了二十几年,依旧让我记忆犹新。吃完那顿饭,我跟在李洋的屁股后头,打迎宾楼里面出来的时候,在正门口遇上了迎宾楼的王经理。李洋跟王经理认识,就微笑着迎上去,握住人家的手,寒暄了两句。原来,迎宾楼里的服务员和服务生都是通过李洋给介绍过去的。李洋随口问了王经理一句,您这里的服务员招够了吗?王经理说,还差两个名额呢。李洋朝我招了一下手,示意我跟王经理打招呼。我嘴角上还黏着大米饭粒子呢,抬起衣袖子抹抹嘴,走过去,问了声,经理好!
李洋向王经理推荐我说,她叫李小敏,是我吉林的一个小老乡,迎宾楼里要是还缺人手的话,您就安排个差事给她干吧,乡下姑娘,勤快,能吃苦,还不挑活儿。
4
半个月后,我就顺利地上岗了。我被分配到迎宾楼的快餐部,负责四个台位的卫生和服务,工作时间是早九点到晚九点。可能是因为我在迎宾楼上班的缘故,也可能是图近便,李洋时不常就会跑到快餐部来吃午饭。他每次来,都会问我,在这里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顺不顺心啊?不管李洋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兴许他就是随口那么一问,却让我心里生起一股莫名的暖意。
李洋不只是自己来迎宾楼吃饭,隔三差五也带社会上的朋友过来消费。有一次,我瞄见他跟一个穿警服的中年男人一起过来的。穿警服的男人身材高大威猛,狮眉虎眼,梳着大背头,脸上的大麻子疙疙瘩瘩的。这人瞅着有点眼熟,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他是谁。李洋和穿警服的男人脚前脚后走进来,但是他们没到快餐部就餐,而是去了中餐厅。我猜他们是提前往迎宾楼的吧台打了电话,在中餐厅预订了小单间,好方便谈事儿。
后厨有个叫姜华的矮胖子,他是迎宾楼厨师长的大徒弟,快三十了,还没有结婚。有事没事的,他总喜欢和我搭讪。他总听我管李洋叫叔,就以为李洋是我亲叔呢。那天,姜华在背后捅咕了我一下,诡秘着一对小眼睛问,李小敏,知道你叔身边穿警服的男人是谁么?
我问,咋的,那个人你认识?姜华说,不光我认识,很多人都认识他。我问,他是干啥的?姜华小声说,他姓桑,叫桑军,外号桑麻子,是咱们这个辖区派出所的所长,他屁股后头还别着一把手枪呢!
姜华一说手枪,我呼啦一下就想起来了。没错,这个人,我在虹姐发廊里见过的。当时我给客人做耳烛,惹出乱子,虹姐就是给他打了个电话,叫他过来平事儿。只不过那天他穿便衣,今天着警服,我就有点恍惚了。
没两天,李洋突然跑过来跟我说,他盘下了迎宾楼对过的那家旅馆,然后又雇了个帮手,专门替他打理中介所的事务。他偷偷地问我,想不想一个人打两份工。我说,那当然想了,钱多了又不咬手。于是,我和李洋私下里约定,早上七点钟,我起来先过他那边去,帮他洗客房的布草,是用洗衣机洗,也不是很累,我就欣然同意了。迎宾楼这边,我每天是早上九点钟上班,所以,往后我每天必须早起,七点之前过李洋那边去,洗上两个小时的布草,九点钟返回迎宾楼上班刚刚好。两边跑,虽然辛苦了点,但是可以多拿一份工资。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从初中到高中,一直没有间断过。晚上,临睡觉之前,我都要写一写日记。我把进城以来遇到的人和经历的事儿也都写进日记里了。李洋算是我在这座城市里遇见的第一个关心过我,给过我帮助的男人,所以,我把他写进了我的日记里。那天,我把日记本带在身上,干活的时候感觉不太方便,便临时把日记本放到吧台下面的一个抽屉里了。晚上将要下班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去拿,结果拉开抽屉,翻找了半天,发现日记本不翼而飞了。日记本里详细记录了我的过去,里头藏着我不能言说的一些隐私和秘密。当时我心里急得像着了火一样,问遍了身边所有的同事,没一个人看到过我的日记本。领班的跟我说,你到后厨去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见。
跑进厨房的时候,我刚好撞见姜华蹲在地上收拾鱼呢。除了姜华,后厨里没有别人。出于礼貌,我问他,姜师傅,你看见一个日记本没有?
脑膜炎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发热、头痛、颈强、谵妄或精神症状、嗜睡、乏力、癫痫和呕吐。但仅25%的成人有典型的临床表现,大多数患者临床表现不典型,成人的细菌性脑膜炎表现越来越不典型[4],荷兰一项全国范围的研究表明,696 例社区获得性成人细菌性脑膜炎中,44%的患者出现典型三联征,95%的患者至少出现头痛、发热、颈强直和意识改变4 种症状中的两项[5]。患者的年龄、潜在疾病、免疫功能和是否应用抗生素往往决定就诊时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姜华没言语,干咳了一声,拿手指指墙角。那边立着个堆放锅碗瓢盆的不锈钢架子。我一眼就发现自己的日记本,在架子的顶头放着呢。我几步过去,把日记本拿手里,翻开扉页一瞅,页脚上沾着一个油腻腻的大手指印子,心头便猛地一紧,我知道,有人翻看过我的日记了。我感觉愤怒,也感觉委屈,眼泪一颗接一颗地从脸颊上滑落下来。我哭得噎住了,出不来声音,身体倚靠在不锈钢架子上止不住地抖。背对着姜华,我在那里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我的那本日记。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用黑色碳素笔写日记,最后那一页只写了半页。可我现在却看到,空白的部分被人填上了新的字迹,分明是刚刚写上去的,而且还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一段歪歪扭扭的小字:
小敏,没经过你的同意,翻看了你的日记,非常抱歉!放心,只有我一个人看了你的日记。我没有恶意,我只是去吧台抽屉里翻找工具,结果发现里面有个日记本,我以为是账本,出于好奇心,我就翻开看了看,让我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你。我想对你说,不管多沉重的包袱,我都愿意和你一起背,我想成为那个一辈子为你遮风挡雨的男人……
——姜华
我擦干眼泪,默默地把日记本收起来,头也不回地转身就离开了。回到寝室里,我躺下了,却怎么也睡不着,感觉浑身疼。到了后半夜,我就莫名其妙地发起烧来了。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就七点钟了,可我没有力气爬起来。那边旅馆里的布草攒了一大堆,李洋见我没过去洗,他就跑到迎宾楼这边来,看看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听迎宾楼领班的说我今天没上班,请了病假,李洋又忙不迭地跑到寝室里来探望我。他进来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输液呢。李洋过来摸了摸我的前额,说烧得这么厉害啊,我送你去医院吧?我说,用不着去医院,麻麻烦烦的,感冒发烧又不是啥大病,打两瓶点滴,吃几片退烧药,躺床上歇两天就好了。
李洋转身出去,到街角的超市买回一大堆水果,放到我的床头上。他回来时,发现姜华在我的寝室里,上一瓶药水点完了,姜华正在帮我换下一瓶。李洋不光买了水果回来,还顺便给我打了午饭,往床头柜子上放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有一盒饺子放在那里。李洋没有多问,放下手里的东西,朝我微微一笑,叮嘱我多注意休息,他说他旅馆那边生意挺忙的,有时间再过来看我。我打着吊瓶,不方便下床,就叫姜华送李洋。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一直是姜华在身边照顾我。我不想平白无故接受人家的照顾,我不让姜华过来,可我挡不住他。姜华忙过了饭口,就给我送饭过来,饭菜都是他亲手做的,有时候是红烧肉,有时候是排骨,有时候是鱼,不重样,还给我买了一堆感冒药和发烧药。李洋每天也抽空过来看我一次。他每次来,都能碰上姜华在场。第四天,我的烧就退下去了,体温恢复了正常,病也好彻底了。早上,我过旅馆那边洗布草的时候,李洋过来套我话说,小敏,我看那个姓姜的小胖子,对你挺上心啊?他是不是想和你处对象呀?我一边忙活,一边说,叔,你可别瞎说,人家有对象。李洋撇嘴说,他要是真有对象的话,就不可能对你那么上心了。
5
精明的李洋,把旅馆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每天换下的布草也越来越多了,我一个人也有点洗不动了,主要是有些床单子上经常会带着血渍,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后来,李洋把洗布草的活,外包给了一家专门承揽为酒店和宾馆洗布草的洗涤公司,人家每天定时开着面包车过来,把布草拉回去,公司里有洗涤车间,都是大型的工业机器,用化学原料暴力蒸白,不管那些布草脏成了什么样子,只要从机器里滚一遍出来,看着都是扎眼的白。
李洋的旅馆和中介生意打理不过来,好长时间没空过来看我。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迎宾楼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小变故。厨师长和餐饮部的经理,也不知道是因为啥事,两个人闹翻了。厨师长不打算在迎宾楼干下去了,私下里计划带上姜华和另外几个徒弟撤出去。姜华是他的大徒弟,自然是师傅去哪,他就跟着去哪。姜华建议我也辞掉迎宾楼的工作,说服务员吃的是青春饭,不能干一辈子,要长远打算,就得学门手艺。我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的,真的是为了我好。姜华认识一个三星级酒店里的白案师傅。那天晚上,他偷偷地把我领去了那家酒店,找到了那位白案师傅,把我推荐给他当徒弟。那个白案师傅姓吴,快六十岁的人了,长得精瘦精瘦的,一对鹰眼,瞅人的时候黄眼珠放光,贼得发亮,我都不敢正眼看他。
离开迎宾楼之后,姜华准备跟着他师傅去青岛包灶房。临走前,他还过来看我,给我留了一个那边的电话号码,最后还撂下一句话,说让我跟着吴师傅在这边好好学,等手艺学成了,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去青岛那边找他。
这家酒店的后厨房很宽绰,光面食间就三个。第一面食间是我和面的地方。每天晚上九点,别人下班以后,我要在这里发面,平均每天大概要用掉一百五十斤面粉。发面时,泡打粉和酵母按比例混合,兑温水,加面粉,简单揉一下,早晨四点半我要第一个起来,到面食间,把发好的面反复揉。五点半,吴师傅准时过来,带着我把面做成包子、馒头、花卷、豆沙包之类的面点坯子,下一道工序是把做好的面点坯子端到第二个面食间里,摞到笼屉上蒸。这里还有一口超大的蒸饭锅,一次可以蒸下一袋子米。上午九点钟前后,早餐时间基本就结束了。之后,我就要准备中午的米饭了,洗好了米,放好水就通知锅炉房给蒸汽。这时候,我就要站在一个小凳子上,拿一把铁锹插进蒸锅里不停地搅,直到搅不动为止,然后盖严实盖子,再等十分钟,通知锅炉房停汽,米饭就蒸好了。差不多十点钟左右,我又要从第二面食间转到第三面食间。这会儿,吴师傅已经准备好了饺子面,饺子馅,还有各种饼的面。我的任务就是给师傅打下手,有点饺子的,我就擀皮儿,有点饼的,我就看饼铛。
中午的伙食饭,通常都是在午后一点半吃。吃伙食饭对我来说,倒是一件比较享受的事情,不但可以在餐厅里坐着,还可以有机会接触其他同事。在面食间里,面对我一个人的时候,吴师傅总是板着一张老脸,只有大伙儿凑一起吃饭的间隙,看到同事之间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吴师傅的脸上才会露出一点笑容。吃饭的时间也就两刻钟不到,大家就稀稀拉拉地散去了。大厨房里留下两个人值班,吴师傅也回寝室休息去了,面食间里就只剩我一个人。我得先把第一面食间里的卫生打扫干净,面盆洗出来,准备晚上发面用。然后转身去第二面食间,把十几口大蒸屉刷出来。瞅一眼那口蒸饭锅,里面没有剩饭了,锅边上有个把手,摇一摇,锅就歪向一边,加水、刷锅、淘米、焖饭,忙活忙活,就下午四点多了。吴师傅过来了,我跟着他到第三面食间,把中午做过的活计,再重复一遍。八点半钟,开始吃晚上的伙食饭。九点以后,除了我,其他员工都可以下班休息了。而我要返回第一面食间里去发面,通常要忙活到夜里十点多,我才可以回宿舍里冲个澡,躺下歇息。有时候不想睡觉,我也可以溜达出酒店,到外面买点私人用品啥的。如果时间不是太晚,我也会想着给姜华挂个电话过去,在电话里跟他聊会儿天儿,排遣一下寂寞,消磨掉无聊透顶的时光。
6
吴师傅是个精明的老头儿。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真心教我什么东西,对我这个徒弟,他一点都不上心,而且还处处提防着我。譬如我发现,每次拌馅儿的时候,他都是躲进一个小黑屋子里,把门关死,不让我进去,我就看不见那些馅子里都放了哪些调料。所以,我想给姜华打个电话,让他跟吴师傅说说,多教我点白案手艺。
那天晚上,不知道啥原因,就感觉自己心里边七上八下的,都没顾得上发面,我就急三火四地跑到酒店外边,出了门,往右一拐,有个带话吧的小超市,我惦记着给姜华拨个电话过去,想告诉他我现在的想法。拨头一遍,说是空号,我以为是我脑子糊涂记错号了,就把写有姜华电话号码的一张纸条从衣服兜里翻出来,对照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又重新摁了一遍数字键,结果还说是空号。这个电话号码,前些天还能打通的,我还和姜华在电话里聊了半天呢,现在怎么突然就变成空号了呢?是不是姜华在那边有啥事儿了?还是他处对象了?如果他有了新的女朋友,那我将来还有必要跑去青岛投奔他吗?
从超市里走出来,我胡思乱想着返回酒店的面食间里,就感觉脑子里晕乎乎的,两条腿也发飘,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一样。我拿起面盆,放好酵母粉,本来该加温水把酵母化开的,一不留神就倒了一小盆开水进去,马上又反应过来,再加凉水,稀里糊涂地就把面发上了。等我忙活完了,回寝室都快十一点半了。时间太晚了,我也懒得洗澡,上床就睡下了。凌晨四点半,放枕头边的闹钟把我给吵醒了。睁开眼,我把窗帘拉开一个角,瞅了瞅,外头的天还是黑的。我穿好衣服下床,迷迷瞪瞪地走进面食间里,去揉头天晚上发的面,揉了几下,手感不对,心头一紧,呀,面没发!我当时脑袋就大了。一定是昨天晚上我拿开水烫的,酵母失效了,这可怎么办啊?就在我手足无措的节骨眼儿上,吴师傅过来了,发现面没发,他当时就火了。他的两只鹰眼朝我直放光,光里有无数根麦芒似的针尖在不停地蜇我。眼瞅着酒店开早餐的时间就要到了。是我前期工作没做好,害得吴师傅抓瞎了。吴师傅桄榔桄榔地敲着面案子,逼问我咋办?我说,这样吧,我去外面的早餐店挨家走走,我自己掏钱,把能用的面点都买回来,先应应急吧。
吴师傅瞪眼瞧着我,连打了好几个唉声。外头的天,麻麻亮了,我嘴里喷着哈气,穿梭在大街小巷上,凡是亮着灯的早点铺子,我都进去了,见到包子、馒头、馅饼、油条、油炸糕我都包圆了买。一直倒腾到七点半,吴师傅见我顺脸淌汗,身上穿的小棉袄也都让汗水给塌透了,冒出的热气像蒸笼似的。早餐这一关,好歹算是应付过去了。吴师傅气消了之后,把我叫到他跟前,心平气和地说,让我离开他。我当时有些惊讶,我说师傅,你是不是看不上我?吴师傅又打了个唉声,说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年纪大了,想告老还乡了。然后,我就发现他眼角湿了。我问他,师傅,你怎么哭啦?是不是我不争气,让您失望了?吴师傅抹了一把眼泪,跟我说,上个月酒店员工去体检,他查出了癌症,晚期了,没得救了,他不想死在城里头,他惦记回乡下去死,他说叶落要归根,叫我别跟着他了。
那天下午,我打好行李包,出了酒店大门,抬头望了望城市的上空,阳光锥子似的刺眼,天气却格外地冷,小风一吹,我湿透的棉袄感觉硬梆梆的,像战士身上的铠甲。我站在十字街头,转了个圈儿,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我想了想,抱着一线希望,又跑进了那家带话吧的小超市。我心里默默地祈祷,这次能拨通姜华的电话。我拨了三遍,也可能是五遍,还是空号,我挂掉电话,拎起身边的行李包就往出走。那个超市门口的台阶很高,我脚下一晃,踩空了,脑子里嗡一声,眼前一黑,瞬间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7
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的一张病床上。
那间病房里,总共有四张床位。其它三张床位上也都躺着病人,他们都拿被子捂着,看不见人长啥模样,但是能听得见病痛折磨使他们发出来的哼哼声,每个床位的边上都立着点滴用的吊杆,都在输液,身边有家属围着。我吃力地挺了挺脖子,骨碌着暗淡的眼珠,四下里撒眸了一圈,病房里找不见一个我认识的人,我就问给我扎针的大夫,我说我是怎么到医院里来的?大夫说,你从超市门口的台阶上栽下来,摔晕过去了,是超市老板拨了120 急救电话,把你送到这儿来的。大夫说我身子骨太虚弱了,需要人照顾,让我想办法通知一下家里人。我撩了一下眼皮儿,有气无力地说,我没有家人。大夫说没有家人,朋友也行,总不能把你撂在这啊!我想了半天,想到了李洋。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也只能给他打个电话了。
电话是大夫替我打的。李洋听说我躺在医院里,电话里也没多问,开车就过来了。看见李洋,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他先是安慰了我两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大夫,询问我的身体情况。大夫说没什么大碍,就是血糖太低了,回去后需要多注意休息和补充营养才行。输完液,就可以出院了。李洋在医院大楼里奔前跑后,替我垫付了医药费,最后又跑去窗口,为我办理了出院手续。
返回旅馆的路上,李洋一边开车,一边埋怨我,怪我离开迎宾楼没跟他吱一声,害得他担心,找了好些天,也没有我的下落。我跟他说,咱俩就是萍水相逢,你已经很照顾我了。你盘下那么大一家旅馆,生意忙不过来,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所以就没有联系你。
回到旅馆,在走廊里,我遇见了虹姐,这让我感到十分地意外。虹姐着一身藏青色的职业装,上衣是小开领,贴身的衬衫,翻到外面的领口雪白,头发高高地绾起来,举手投足间透着职业女性的成熟。我和她打了声招呼,她看我时,脸上浮动着一丝温暖的笑意,看来,虹姐是把过去的事情抛在脑后,她已经不再生我的气了。为了让我休息得好一点,李洋吩咐楼层服务员,为我单独开了一间客房。掩了门,我就问他,虹姐怎么会来你这儿?你和她到底啥关系?李洋吞吞吐吐的,不想跟我说实话。我嘟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俩关系不一般,以前你还说,你不了解虹姐发廊是什么样的地方,现在你们却在共同经营着这家旅馆,你们不是好人,是骗子!
说着说着,我居然委屈得跟个孩子似的,趴在客房里的那张大床上,呜呜地哭起来了,而且哭得很大声,大到隔壁房间里的客人都听到了。李洋生怕我误会他,不得不跟我说出了实情。原来,这家旅馆是他和那个叫桑军的派出所所长合伙盘下来的。可是,国家法律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是不得经商的,所以,旅馆执照上的法定代表人写的是李洋,而实际上,桑军才是隐形的大股东。到了年终岁尾,桑军是要从旅馆这边分走一大半红利的。李洋和虹姐之间的关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暧昧。李洋说,虹姐是桑军的姘头,是桑军信不过他,才把虹姐安插在他身边,从中把持着旅馆的经营大权。有桑军在背后撑腰做保护伞,虹姐在李洋的旅馆里开了按摩中心。按摩中心里的女孩子,岁数都不大,小的也就十七八,大的也超不过二十五六岁,都是来自乡下的姑娘。
我身体养好以后,李洋就怂恿我跟虹姐学了按摩。李洋教化我说,行业无贵贱,学按摩跟学揉面是一样一样的。可我也不是傻透腔的姑娘,慢慢地就回过味儿来。过去他们对我千般好,原来都是无利不起早。等到时机成熟了,就拉你下水,把你培养成他们生意上的招牌。我私底下问了这里的一些姐妹,她们刚刚进城的时候,也都和我一样,曾经在酒店里做过服务员之类的工作,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虹姐,不不,确切地说,应该是虹姐认识了她们。虹姐真是个不寻常的女人,物色姑娘,就像海东青捕捉无家可归的小兔子一般十拿九稳,总能在你遇到难处或是你走投无路的裉劲儿上雪中送炭。现在,被虹姐拉拢过来的姑娘,全都脱胎换骨了,变成了一棵棵摇钱树。白天,按摩中心里十分冷清,基本上没什么客人。只有到了晚上,招牌上的霓虹灯一亮起来,这里可就热闹了。进来的有年轻小伙儿,也有半大老头子;有夹包做买卖的生意人,也有建筑工地上灰头土脸的农民工。按摩中心格局十分地紧凑,有一条很深的走廊,廊道里的光线昏暗暧昧,两侧是一间紧挨着一间的简陋小隔断,里边空间狭小,只容得下一张窄床和一把椅子。小单间,没有门,也没有窗,为客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只落着个软塌塌的粗布帘儿。漂亮又会来事儿的姑娘,把客人拉到小单间里,躺一张窄床上,为客人捶捶胳膊、捏捏腿,轻轻松松就把钱赚到手了。按摩服务,姑娘们和虹姐五五分账,要是有特服,就三七分,姑娘七,虹姐三。这里的姑娘都是夜猫子,昼伏夜出,晚上接客通常到后半夜三点钟左右才消停下来。
8
从旅馆大门里出来,顺着一条笔直的柏油路往西走大约两公里,再往南一拐,就是正在兴建当中的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建在一座大山脚下的缓坡上,没破土动工之前,这里就是一片寂寥的荒野。一年前有工程队过来,拿红砖砌起了隔离墙,开始大兴土木,只几个月的工夫,荒野上就耸起参差错落的楼茬子。去年入冬后停工了几个月,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发区里的各项工程又开始上马了,施工现场整天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又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了。
每到晚上,总会有那么一两拨工友,在露天的烧烤摊上撸完肉串,喝完啤酒之后,就勾肩搭背地跑到按摩中心来找乐子。我认识他们当中的老王和老马。因为他俩常来,来了也不要求特服,就是正常按摩,十块钱四十五分钟,松松筋骨、解解乏就走了。我对老马的印象特别好,因为他每次过来都找我,每次来也都没有过分的要求。记得老马初次来的时候,身上脏兮兮的,衣服领子里面全是灰土,我问他是干啥活儿的。他说他就在附近的工地上干活儿,瓦工。我问他工地上的活儿是不是很辛苦。老马说,干啥活儿不辛苦,活命呗!
老马喜欢聊天儿。他跟我讲,他乡下的老婆前些年得癌症死了,丢下个闺女给他。闺女现在上大学了,正是用钱的时候,家里地少,不够种,他就跟着老王一块出来打工,为的就是给自己闺女多攒点学费。我说,那你还跑到这种地方来花钱。老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悄默声地告诉我,其实他不想来,是老王每次都摽着他来。我说,你们这些农民工,撇家舍业出来挣点钱多不易,咋就喜欢来这种地方呢?老马说,像我和老王这样年岁大些的还好说,工地上还有精强力壮的汉子呢,他们背井离乡出来找活路,在外头一干就是一年半载的,哪熬得住啊?实在憋得不行了,才出来跑个马,没办法的事儿啊,哑巴畜生还有个发情期呢,何况大活人哪!
老马最后一次来我这儿,是那年中秋节的晚上。他花钱在外面请老王喝酒,喝到后半夜,老王突然间来了兴致,说啥非要请老马过来按摩。那天晚上,旅馆的客人非常多,楼上楼下的客房全住满了。老马和老王进来的时候,除了我之外,按摩中心里的其他姐妹没一个闲着的,都在坐台服务。我把老马拽我屋里,问他想咋按,他往窄木床上一趴,哼唧着说,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老王瞟了虹姐好几眼,问她,还有没有年龄小一点的姑娘了?虹姐仰脖儿优雅地吐了个烟圈儿,拿眼睛勾搭老王说,年龄小的没经验,你说是不是?老王的眼神像把尺子似的,上上下下打量虹姐,之后也没有反对什么。虹姐就把老王拉到了我隔壁那一间屋里。老王上了床,脸朝下趴着,虹姐跨在他的大腿弯儿上。按了差不多一刻钟的时候,虹姐心里长草,跟老王说,大哥,做个特服吧,别的姑娘一次三百,你给我二百就行。老王磕巴着说,不,不上当。虹姐一边抡拳捶打老王的后脊梁,一边哝哝地说,你这么大个男人,咋这么小气呢?连二百块钱都舍不得在女人身上花,真没劲!老王哼了一声说,二百块钱,够我请老马在外边喝两顿酒了!
虹姐把嘴凑近老王的耳根说,二百块钱吃了喝了,还不是香香嘴,臭臭屁股,有啥好么?不是老妹子说你,做男人,你就得学会逛窑子吃豆腐渣,该省的省,该花的花。老王结结巴巴地说,关键你,你也不是小姑娘啊!在你身上花二百块钱,不,不值当!
就在老王和虹姐打情骂俏的节骨眼儿上,突然有一队便衣警察从旅馆的后门撞进来,开始逐个查房。我和虹姐这两间屋子里有小暗门,都连着地下车库。警察撞门进来的时候,老马和老王已经顺着小暗门跑路了。因为有桑军罩着,平日里轻易没有人过来查房。若是赶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桑军都会提前给虹姐挂个电话过来,让暂时消停几天,等风头过去了,再开门营业。然而,这次偏偏是例外,这次是由省公安厅治安局牵头,秘密进行的一次跨区异地扫黄打非专项行动,压根就没与地方公安派出所通气。旅馆和按摩中心被扫黄组的民警抓了现行。当晚,李洋和虹姐就被警察连推带搡地押上了警车。他俩被刑事拘留了,关进了看守所,听说性质挺严重的,一时半会儿怕是出不来了。这次事件的结果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桑军因充当涉黄服务场所的保护伞和变相参与经商,丢了公职不说,最后也被判了有期徒刑。经历过这样一场暴风骤雨的洗礼之后,我也准备和这座城市说再见了。
9
那天早上,我去按摩中心的那间小屋子里收拾我的私人物品。整理好行李箱,转身准备出屋的时候,我发现门旁的挂钩上吊着一件男人的上衣。那是一件旧得不像样子的迷彩服,上面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我随手摘下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翻过来掉过去地瞅。没错,这是老马的上衣。警察突击查房的那个晚上,老马逃得唐突,没来得及把衣服摘下来穿走。我已经做了去青岛的打算,想在离开之前,把衣服给老马送过去,也好顺便跟他道个别。
走进那片开发区,我围着工地踅摸了好几圈。奇怪的是,这里异常的安静,既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也抓不到一个人影儿,只看见成群的麻雀在低空飞来飞去。那些还没封顶的半截子楼房,高的高,矮的矮,像是一座座无主的荒坟。
忽然间,我觉得背后有人,回身一瞅,居然是老王。老王脸色暗淡,怔怔地问,你咋找到这儿来了呢?我说,我给老马送衣服来了。我把手里的衣服朝他扬了扬。
老王沉郁地说,你来晚了!
什么来晚了?我睁大了眼睛问他。
老王十分难过地说,三天前,老马出了意外。垒砖的时候,他脚底下踩空了,从三十米的高空摔了下去……人炼了,骨灰匣子,昨个让他闺女捧回老家去了……
我瞪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朝老王扬了扬手里的衣服。老王眼圈一红,就哽咽了。他递过来一个打火机,哀戚戚地对我说,就地烧了吧。
我松手,老马的上衣轻若鸿毛一样,落在了光秃秃的水泥地面上。蹲下去烧衣服的时候,我发现水泥地面裂开了一条缝儿。缝隙里面挤挤挨挨地生出几朵婆婆丁来,茎端顶着三五朵卑微的小花,单纯的鹅黄色,像绣在水泥地面上的一朵朵雏菊。另一株花葶上,白色的冠毛结成一朵蓬松的绒球,如一把撑开的小伞。我折下小伞举到空中,轻轻地拿指尖触摸了一下,白色的小伞摇曳着飘散在风里,像极了我迷茫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