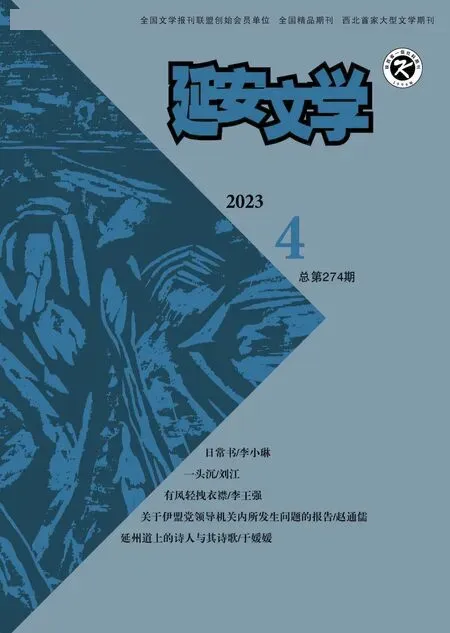焰火烂漫
2023-02-19程相崧
程相崧
1
程金贵早早起了床,洗刷完,点上燃气灶,烧上水,准备下点儿面条。蓝色的火苗儿舔着锅底,烤得锅里的水发出“吱吱”的响声。他小心翼翼地切了点儿葱花、姜末,又切了一个西红柿。他觉得刀“铛铛”地声音有点儿响,小孙女儿还睡着,他怕吵醒她。他在炒锅里淋了点儿油,将葱花姜末迅速往里一放,香味儿瞬间便在空气中翻滚起来。这边儿爆好锅,那边儿水也开了。他把面条儿下进锅里,倒下葱姜西红柿炒出的汤汁儿,便打了两个鸡蛋,在那儿等着。他平时做饭,都是打一个鸡蛋,到时捞到孙女儿碗里,也够她一天的营养了。
今天,因为自己有重要事情,要耗费体力,还要耗费脑力,他就给自己打了一个,补一补,也算提前犒劳一下。面条儿是他之前擀的,冻在冰箱里,为的是吃时方便。小孙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间紧,有时候现擀来不及。小孙女儿就爱吃他擀的面条,从商店里买的挂面她不吃,他也不想让她吃。据说,那些挂面用的面粉都把营养提取出去了,做的时候还放了胶,放了防腐剂。他盯着汤锅,等面条在水里翻了几滚儿,觉得熟得差不多了,便把鸡蛋打了下去。他熄了火,把面条给小孙女儿捞出来一些,盛在她的小碗儿里,没有加汤。汤加早了,等孩子起来时,就不好吃了。
他给小孙女儿盛了一碗,也给自己盛了一碗,端到餐厅里,晾着,便到卧室去叫醒孩子。
他的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一卫,86 平米,住他祖孙俩也绰绰有余了。他刚刚搬进来时,对客厅啦,卧室啦,餐厅啦这样的说法本能地有些抵触。从前,在农村住着时,就是一个小院儿。一个过道门儿,门楼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走进去之后,就是几间正房,几间偏房。正房叫啥哩?叫堂屋,堂屋的中间一间,正对着房门的,一般也就叫做中堂了。中堂里一般挂幅字画,摆张条几,讲究些的,还会有张八仙桌、几把椅子。逢年过节,家里来了亲戚朋友,都要让进中堂里坐,泡上茶,抽上烟,把一年的酸甜苦辣说道说道。这中堂的作用,大约也就相当于城里人的客厅了。
那厢房哩?在农村,如果东厢房做了厨房,那么西厢房则一般住着年轻人,或者充当着仓库。城里人也有厨房和仓库,不同的是厨房虽然讲究,却总要小些,而仓库就不叫仓库,变成了储藏室。粮库、水库,还是“库”大气不是?这名字一变,就带了许多的小家子气。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从前,秋天庄稼收获了,人们喊着:农具入库,歇一个冬天,等着过年,真是美滋滋的日子啊。庄稼人农具多,小的铁锨、木锨、抓钩、锄头,大的板车、水泵、犁子、耧车,那时候都能入到库里。现在怎么办?往储藏室里塞不下,只好扔了,只好当破烂儿卖掉。
这些都还好说,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是餐厅这个说法。金贵老汉记得,在农村的时候,尤其是像他这样的爷们儿家,都是端了饭碗到院子门口去吃,到村口的歪脖子树下去吃,那算啥?算集体食堂吗?
他瞎琢磨着,来到那个朝阳的单间,那个名叫卧室的屋子,小孙女儿还没有醒来。云儿,云儿,他故意粗声大嗓地唤着,鞋子重重地踏着地板,想要尽其所能地吵醒她。小云果然翻了一个身儿,但没有起,也没有吭声,而是又伸展着胳膊,仿佛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睡去了。他心里明白,其实云儿并没有睡着,她只是懒得起,有些赖床。他便爬到床上,用嘴巴往她耳朵眼儿里哈气儿。他猜的没错儿,孩子果然没有睡着,痒得“咯咯”笑了起来。他往她腚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说赶紧了,该起床了,爷爷送走了你,还有正经事儿呢。
他跟孙女儿住的这个小区,算是一个回迁小区,住的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小区在城边儿上,孩子上学倒也方便,骑着电动三轮,不到十分钟就能到。小云在那边自己穿衣服的时候,他就端起来自己的那碗面条儿,三下两下便扒拉完了。小孙女儿已经会穿衣服,就是有时候鞋带儿还系不太好。小云洗了脸,刷了牙,在饭桌前吃饭的时候,金贵老汉就收拾好了孩子的书包和水杯这些该带着的东西。他收拾好小孙女的东西,就走到衣柜上镶嵌的那面大镜子前,照了照。那衣柜是女人嫁给他的时候带来的嫁妆,女人年轻的时候,每次出门,都要到这镜子前照一照。他盯着镜子里那个人,心里对自己说,如果我是老板,我会不会招聘个老家伙给我干活儿呢?他这样想着,先是自己摇了摇头。他盯着那一张满是皱纹的脸,那脸跟上面的一头黑发似乎有些不相称。那一头黑发,是他前几天拿定了主意去应聘这个职位的时候去外面理发店染的,花了三十块钱。刚才,小孙女儿还没起床的时候,他还特别仔细地刮了胡子,没有了胡子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下巴看上去有些怪怪的。
今天,程金贵计划好了,要出趟远门。那个地方原本不远,就在他原来的小村。现在,小村的地被征收了,他们被安置到了县城,离那地方就远了。那地方的土地被征收之后,虽然离城还那么远,却也就不能算作农村了,只能算作郊区,或者按照文件上的说法,叫做化工园区。那化工园区干些啥,当地人不知道,只看到院墙拉起来了,高高的像监狱,院墙里修了些高烟囱,架了些铁管子。他今天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园区里的一个厂。
据说,那个园区以后会发展得很大,那个地方,以后也会变得很繁华。大到什么程度,繁华到什么程度,他想不出。因为,现在园区里企业还不多,建成的几个也还只是个雏形,有的只是个空架子,有的刚刚投入生产,所以,从县城到那里,就还没有开通专门的公交线路。跟从前一样,二十里的路程,打出租车,得几十块钱;骑电动三轮,就得大半个小时。
2
程金贵把小孙女儿送到学校之后,便开着三轮车,往农村老家的方向,或者说向那个厂子的方向开去。他坐在车上,觉得自己有些好笑,因为他竟然感觉自己呼吸有些困难,心脏也跳得厉害。他这辈子,并不是没见过世面。年轻时在唐山当了五年的兵,复员之后又在县运输队帮忙开车,后来回到村里,还干过一届支书。这辈子,除了没参加过高考,啥没干过?今天,去一个厂子应聘一个小小的门卫,竟然紧张成这个样吗?那张招聘门卫的启事,他是在接送小孙女的时候,在一个电线杆上看到的。一开始,他没注意,后来看到地址,心里就是一热。因为,那地址栏里分明注着:原程庄。程庄就是他原来的庄儿啊!就是他领着一家老小过活的庄啊!就是他当过支书的庄啊!虽然地图上没有了,却还是没有被人忘记。
他的眼眶竟然莫名地一热。
从前,他是单知道他原来的那个庄用钢皮围上了,里面长满了荒草,现在才知道,原来有人在那里建了个厂。他又将那招聘启事看了一遍,那上面说,招聘保安两名,主要工作是出入登记、日常安全、防火防盗等,待遇面议。他想了想那厂子离县城的距离,觉得虽然不近,有了电三轮,却也可以。来回几十分钟,一早一晚的,接送孩子并不耽误。如果晚上需要在厂子里值班,把孩子接到那里去住也可以。唯一的,他中午没法回来,孩子只能在学校里吃。这其实跟从前差不多。从前,他每天也都不闲着,在外面打些零工,扛扛蒜袋子,剥剥蒜皮儿,中午也没法儿给小云做饭。
有一件事儿,他一直有些忐忑,那就是自己的年龄。人家招聘启事上并没有年龄限制,可他觉得,自己可能的确有些太老了。六十八岁,奔七十的人了,还能不能做好一个保安呢?他觉得,如果放到前些年,他刚刚六十挂零的时候,一定行的。那时候,身体虽然跟现在差别不大,他却还绷着一股子劲儿。他六十四岁那年,儿子争气,弄了个塑料大棚,种了葡萄、草莓、蓝莓这些水果,一年也弄个一二十万,不差钱儿。他心里也就渐渐松懈下来。那感觉,仿佛自己已经退居二线,以后的生活就是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了。谁能想到,地被征了之后,儿子竟然染上了好赌的毛病。输尽了赔偿款不说,连从前的积蓄,也输了个一干二净。那些日子,村里人有了钱,又没事儿做,整天聚在一起赌博。儿子输了钱,不甘心,就偷偷借了高利贷。因为这,儿子欠了多少外债,他不知道,他知道的是,很快,那些追高利贷的人就整天上门要债了。他想要报警,还没来得及,儿子就用一瓶农药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儿子死后,儿媳就走了,撇下个女娃儿,当时才四岁哩。他在儿子死了、儿媳跑了之后,紧了紧手脸,心里想,这辈子余下的时光,恐怕要好好重新规划一下了。现在,儿子跟儿媳的大结婚照还在房间里挂着,他每回看见都要在心里问一句,现在啥世道哩?没情没意吗?
他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紧张得额头上就有些冒汗。小孙女跟他一起下楼,似乎发觉了爷爷今天有些怪怪的。她盯着爷爷看了几眼,问:“爷爷,你今天有情况?”
“没有。”
“爷爷,中午还接我不哩?”
“你自己在学校吃。”
程金贵骑在三轮车上,心里盘算着,现在小孙女六岁,他六十八岁,自己还能供她几年。过些年,等到她十六岁上高中,他就七十八岁了。她二十六岁大学毕业,能养活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个年近九十岁的耄耋老人了。他想到这里的时候,莫名地就有些伤感,心里说,自己能活到那个岁数吗?他这样骑了一段儿,心里又给自己打气说:你行,你一定行的。你没看见村里的程巨渊那个老家伙,八十多岁了还骑自行车去地里割草哩?你看看你,现在这三轮车不是骑得飞快吗?不是跟个小伙子也没有多大区别吗?你剩下这几十年,一定要好好活;只要好好活,早着哩!
他一出城,心里就有些恍惚,认不得了,实在是认不得了。道路很宽,车辆也不多,他分不清是省道还是国道。他只能凭借一两个参照物——一个残存的破旧水塔,一棵拧着身子往空中长的古树——来辨别这里是李庄,那里是王庄,那边是赵庄。这样走了一段,他感觉程庄近了,奇迹般的,凭着感觉,没有凭借任何参照,他来到了从前的程庄,来到那个刚刚建成的厂子前。那厂子比他想象的还要大些。
他到了厂子里,应聘的不多,除了他之外,已经有四个人在那里等着了。他下了车子,知道自己来得还不晚。他下车跟那几个人打了个招呼,问了问,大部分都是附近庄上的。两个年轻些的,四十来岁,因为家里负担重,没有出远门打工;另外两个,比他还要老些。这种情况,让他心里有了底。
他们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便有人领着到了一个办公大楼前,上了楼,到了二楼的走廊上。在走廊的尽头,有一个会议室。领着他们的那人先让一个进去,其他人在外面等。轮到他进去的时候,发现那里面已经有几个领导模样的人端坐着了。他往那里一站,那些人的目光便刀子一样砍过来,仿佛把他砍掉了一半儿。
他耸了耸身子。
“姓名。”
“程金贵。”
“多大了?”
“六十六岁。”
“你身份证是六十八。”
“那是虚岁。”
“吸烟不哩?”
“不吸。”
那些人拿着他的材料,翻看着,小声地讨论着。
“你想一个月多少钱?”
“一千八,不……一千五也行。”
他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急切地想要应聘上这个工作。他原想说,一千四也行的,想了想还得给他的小孙女儿交学费,加上其它花销,每月一千五已经够拮据的了。
那些人没有马上就答复,又问了些啥,就让他走了。
程金贵骑着三轮车往县城回的时候,心里有些悲哀。他想,老了老了,真是做不动啥活儿了。若不然,他怎么会为了挣一千来块钱,一天到晚熬在这里哩?在蒜干厂里给人扛蒜袋,一天就能挣个百十块,一个月下来,至少也有三千块钱的进账。那活儿来钱,可也累啊。一天下来,腿也疼,腰也疼,背也疼,常常疼得整晚上睡不着。
有些外村的人看他这样拼命,就劝他,老哥哥,上头赔了你那么多,顿顿羊肉汤泡馍,吃到死也吃不完,你拼上老命干啥哩?他不能说儿子赌钱的事儿,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着。他这么大岁数,有时候烦了,真不想活了,可他不是一个独人儿,他还有小孙女儿小云哩。小云今年才六岁,这辈子还长着哩,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哩。现在趁着还做得动,多少做些,省着花。
他在回家的路上,不禁又想起儿子来了。那年,上头下了文件要收回村里土地的时候,儿子刚刚弄起来塑料大棚,葡萄、草莓、蓝莓种得正起劲儿。儿子是好样儿的,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回到村里,没给当爹的丢脸。儿子的大棚干了没两年,不仅收回了成本,还小赚了一笔,如果他能活着,等着大把大把的票子往家挣哩。
他实在想不到,这样好好一个儿子,后来能迷上赌钱。儿子欠下外债之后,每天晚上那些人都会来要钱,气势汹汹的。后来,儿子就跑了,一个多月没有音信。他再次见到儿子,已经是在一百里外的一个出租屋里。儿子静静地躺在地上,手边扔着一瓶喝光了的农药。
他走上前去,辨别出那张苍白的脸的确是自己的儿子时,跺了跺脚,往那张脸上狠狠吐了口唾沫。那一刻,他不知道为什么那样恨眼前躺着的那个年轻人,那样恨那个身材模样都跟自己有些相像的可恶家伙。这个可恶的家伙,程金贵心里想,他把一个家全部扔给这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多不地道哩?他多狡猾哩?
“你作死。”他骂了一句。
程金贵骂完儿子,晕晕乎乎地走出小屋,脑袋还在打转。他跟从前比,甚至变得有些轻松,如释重负。那天,他简单处理了儿子的后事,骑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开着。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一边开车,一边嘴里骂骂咧咧:你个短命的娃儿,你可把我害死了!你把你爹坑坏了!
现在,他还没有安葬儿子,儿子的骨灰仍旧在家里放着,放在那个小罐子里,黑黑的小罐子。他早就觉得,这么长时间,自己该给儿子好好地安个家,找个窝的。他明白,这是他这做父亲的责任。他也去许多公墓看过,问过价格,选过位置,可是,每次临走的时候,他都不忍心,不舍得把娃儿孤零零地留在那儿。从前,村里人的骨殖都是埋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如果还能那样,多好?他每天干活儿,干累了,就可以跟儿子坐在一起,说说话儿。
现在,儿子还是在他原来的卧室里。从前一个活蹦乱跳的年轻人,变成了那长方形盒子里的一捧粉末儿。那盒子很好看,外面雕刻着牡丹、芍药等百花图案。在盒子上方的墙上,挂着儿子的大幅照片,黑白的。儿子的眼睛很亮,眼珠黑白分明。每天,他都会上上下下打量几遍。
3
程金贵到那个厂子上班之后,才发现厂子里的一片空地上有一棵桑树。他不知道那片地方是不是他们家从前的责任田,但那桑树跟从前他家责任田里的那一棵一模一样。
他记得,那时候多好啊。女人还没有得病,不但没有得病,还那么年轻。他、女人、儿子,三个人在玉米地里干活儿。玉米那样茂盛,又宽又厚的叶子大刀一样,玉米林子密不透风。三个人在玉米地里割草,热了,累了,就钻出玉米地,坐在桑树底下歇一歇。桑树下有风,桑树那么大,婆娑出一地的阴凉。玉米高了的时候,树上的桑葚也熟了,紫了,黑了,紫黑紫黑的。儿子就爬到桑树上,够桑葚吃。桑葚个头儿那样大,吃到嘴巴里那样润,那样油,那样酸,又那样甜。儿子那样贪吃,每回都吃得醉倒在桑树底下。
在他的记忆中,儿子从蹒跚学步起,就在那块地里活动了。那年,儿子刚会走路,跟着他娘到地里来。程金贵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年地里种的是瓜,西瓜、甜瓜、菜瓜。刚刚栽种瓜苗的时候,儿子跟着到地里来。别人家那样小的孩子,在地里疯跑,常常踩坏了刚刚栽种的瓜苗儿。他也有一样的担心。可是,那天儿子到了地里,颠颠地跑来跑去,却不往瓜苗上踩,似乎知道护着瓜苗,爱惜着瓜苗哩。他跟女人在地头上看着,笑得合不拢嘴。他在心里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娃儿长大后纵使出息不了,至少也是个好样儿的庄稼人。
那年,儿子一个春夏跟着大人,全在那块瓜地里。五月里,菜瓜做了纽儿。菜瓜总是比甜瓜开花早些,做下纽儿就能吃,不跟甜瓜一样,也不苦。那一次,他在地这头侍弄着西瓜秧,远远就看见儿子在地那头摘了一个菜瓜纽儿,坐在畦埂子上,在那里偷吃哩。他就喊了女人,两个在这头边看边笑。
儿子小学初中成绩还好,高中就不行了,没考上大学,去了外地打工。那时候,女人是那样健康,宽宽的肩膀,大大的腚盘儿,一顿饭都能喝三碗汤。谁能料到,人没活到六十,就早早地走了哩?儿子从外面回来,在自家那块责任田里埋了他娘,就不走了,在地里建了大棚,开始种葡萄。儿子喜欢葡萄,喜欢草莓,也喜欢蓝莓。儿子说,过几年,他还要在塑料大棚里种蜜柚,种火龙果。儿子说,有娘在那儿看着,他种啥都能种成。他种星星能结星星,种月亮也能结月亮……
当然,村里各家地里的坟还是迁走了。每个坟头补贴五百,然后在县里统一批给的公共墓地里安排一个位置。程金贵在那厂子里没干几天,就到公共墓地里给女人烧了一回纸。一来,他把自己找到新工作的事儿跟女人说了说;二来,这年的清明节也快到了。他跟人打听了,清明节厂子里不放假。清明节上坟的多,上坟就烧纸,他们保卫科到时候要加大力度,加强巡逻,谨防烟火。
程金贵到厂子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保卫科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严防烟火。厂子里生产啥虽然没人说,可不准吸烟、不准见到明火,却是三令五申并挂牌警示的。这样,清明节不放假,还要加班加点,加强巡逻,他倒也是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他早早地去看了女人一趟,买了几样好吃的,烧了两卷纸钱,撒了一瓶白干。他蹲在那里,想到了好多事儿,心也随着通红的焰火一跳一跳的。从女人的墓地回来之后,他心里还难受得要命。那公共墓地寸土寸金,不像从前在自家责任田里,爱堆个多大的坟头就堆个多大的坟头。那里只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水泥框儿,里面刚好放了装着骨灰的罐子,外面摆一个牌位,显得有些寒酸。他看到女人这样的归宿,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儿。
当然,你如果想给亡人一个好一点儿的环境,也可以花大价钱买商业墓地。一千、两千到数万元不等,任你挑,就像活人在这个那个小区里挑房子一样。程金贵知道,这些天,单是程庄的人,就有好些已经重新买了墓地,打算在清明节这天请来和尚、道士、乐器班儿,热热闹闹让又经历了一场劫难的他们找到个平安的归宿。村里人都得到了数额不等的赔偿款,只要有这份孝心,现在做这个事情,从财力上来说都还不难。程金贵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盘算了盘算,从心里打消了这种念头。
这些年,国家重视传统文化,清明节也成了法定节日,小孙女小云清明节这天要放假。放了假,他不能回家陪她,就只能把她接到厂子里来。这样,清明节的前天傍晚,他便跟厂子里告了一个晚上的假,到学校里来接孙女。
“爷爷,清明节放了假干什么?”孙女一出校门,就缠着爷爷问。
“宝贝孙女,爷爷这两天忙。明天一早,你就跟爷爷一块儿去厂子里值班呀。”
“好好!”孙女高兴得不行。
从在厂子里上班之后,金贵陪孙女的时间就少了,他从心里感觉有些对不住孙女儿。这天晚上,他想领着孩子去吃点儿好的。小云平常最喜欢吃火锅,但他觉得那东西死贵,还不实惠,便很少带她去。他看孩子这样懂事儿,便想犒劳她一下,用三轮车带着小云,到了小区附近新开的一家火锅店。爷孙两个到了火锅店,找了个位置坐下。这家火锅店刚装修不久,电磁炉火锅桌,红色的靠背椅,环境显得优雅而高档。爷爷爱吃辣,孙女不能吃辣,就要了个鸳鸯锅。爷爷领着孙女,去选了两包肉片,几样蔬菜。小孙女吃着吃着,忽然跟爷爷说:
“你看看,那火苗多好看。”
爷爷顺着孩子的手指望去,原来在火锅店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些仿真火盆。那下面其实是黑色的塑料盆子,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布条儿,里面肯定是有小灯泡,还有小电扇啥的。总之,那布条飘摇着,抖动着,红彤彤的,就像燃烧着的火苗。
“爷爷,好看不?”
“好看。”
程金贵看着那些几乎能够以假乱真的火盆,一开始觉得挺有意思。那焰火那样红,那样艳,比真的还要好看,这样的装饰倒跟火锅店的氛围十分融洽。他看了一会儿,问店里的服务员:“你们这些火盆怪好,是从哪儿买的哩?”
“你说这装饰火盆?经济园里就有,叫吊式仿真焰火,也叫电子挂式布焰火,二十块钱就能买一个。”服务员笑笑说。
“爷爷给你买一个好不好?”程金贵说。
小孙女没想到爷爷这样慷慨,惊讶地望了爷爷一会儿,高兴得拍起手来。
4
小云从床上起来,头件事儿就是找那个布焰火。
那焰火盆儿,是昨天他们从火锅店出来,到经济园里一家灯具店买的。那店里啥好玩儿的都有,万圣节的南瓜灯,圣诞节的小彩灯,爷爷都没买,爷爷只买了这样一个焰火盆儿。那盆儿刚刚买来的时候,还没有接上电源,布条子是死的,灯是暗的,风也一动不动。
“爷爷,我想让火着起来。”小孙女说。
“这事儿简单。”
程金贵拿着那个黑色的塑料铁锅,端详着。锅里面有两个聚光灯,几个出气孔,还有两根电线。店里的人说,因为这种灯往往是商店里用作装饰,成组地买,需要串联在一起,也就没安装单个的电源,如果想让孩子拿着玩儿,回家安装一个电池就行。他在路上就想,上哪儿弄个电源去呢?他一开始想买一个,后来就想起老伴儿活着的时候,经常听的那个小收音机。那小收音机自从女人走了,就一直没动过,放着也没用,正好现在可以利用一下。从前,女人身体没病,能干活儿的时候,自然没时间听收音机。后来,病下了,儿子就给他娘买了那收音机。他拿定了主意,就领着孙女回了家,回家之后,又有些犹豫,心想,女人活着时候的东西,现在,为了给孙女修玩具,把它拆了,好不好哩?他想了下,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女人最疼这个孙女,就算女人活着,她也一准同意的。
程金贵想到这儿,拿来螺丝刀和钳子,小心翼翼卸开外壳,里面五脏六腑就都露出来了。
“电池,那就是电池。”孙女指着一个蓝色的圆滚滚的东西说。
程金贵点了点头,开始卸电池。他找到了输入和输出的电线,这两根电线,自然要剪断,并且要尽可能留得长一些。这个不难。电池是用胶粘在收音机壳上的,要弄下来就费点儿劲儿了。他没想到这么难弄,后悔没花上几块钱从外面买一个。他找了一把给孩子削铅笔的小刀,在胶上来回划拉了几下,不行。他又扔了小刀,用螺丝刀往下撬。他撬了一阵,觉得电池有些动弹了,却还是拿不下来。他觉得真是比垒屋时撬石头还难。
从前,这样的活儿都是儿子做。家里灯泡坏了,电视机坏了,孩子的电子玩具坏了,都是儿子拿螺丝刀修理。儿子上学时物理学得好,爱捣鼓小东西。他想着儿子,好不容易把那电池撬了下来。他心里一阵欢喜,小孙女儿也高兴地拍着手。他又拿出那个黑色的铁锅,试图将电池按到里面。这个做起来简单多了。他接上了线头,两个圆形的聚光灯就亮了起来,风也一下子吹了起来,扬动布条,红色的焰火也就燃烧起来。
“爷爷好棒。”小女孩拍着手说。
程金贵给小孙女端上早饭,一人一碗豆沫汤,外加一根油条,一个鸡蛋。这样的早饭,无疑在这个家里显得有点儿丰盛。小孙女有滋有味地吃着,吃完之后,那边爷爷也已经把三轮车收拾好了。小孙女自己把碗筷收拾好,端到水管前冲洗冲洗,把那个布火焰抱在怀里,要下楼。
“你等等。”金贵说,“那灯我拿。”
“爷爷,我干啥事儿?”
“你到屋里去,把桌子上那个瓦罐儿抱出来。”金贵说着。
小孙女一愣,她听爷爷说了,那瓦罐里盛的是爹。她对爹有些模糊的印象。爹那样一个大活人,那时候似乎整天把自己抱在怀里,亲着,闹着。忽然有一天,这大活人就没了,她到处找都找不到。爷爷说,爹变小了,爹钻进了这个瓦罐儿。她就惊奇得不行,心说爹是孙悟空吗?可以变大变小,可以钻到瓦罐里去?爷爷不让她再问,也不让她碰那瓦罐,更不让她打开那罐子盖儿。那个罐子一直以来就放在客厅里的一张桌子上,那桌子上摆着几个相框,还请了一尊菩萨。爷爷没事儿了就给菩萨上三炷香,在那儿祭拜祭拜。
那个罐子,爷爷从不让她动,今天给了特权,她自然不敢怠慢。她走到方桌前,轻轻抱起了那罐子。她把罐子从桌上抱下来,抱在怀里,还笑了一下,心想爹真轻,爹变得真轻。
这一老一小下了楼,往二十里外的厂子里去。
这天依照农历的时令是清明节,如果依照阳历,却也巧得很,又是植树节。他们开着三轮车往城外去,走到城边上,就要经过一个花鸟宠物市场。他们走到那里,发现路边一辆接着一辆,排满了卖树卖花的大车小车。杨树柳树、桃树杏树、月季芍药,应有尽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常见的室内花木。橡皮树啦,虎皮兰啦,滴水观音啦,等等。花农站在车子一旁招揽着生意,一些打算买花买树的人凑上前去,讨价还价。程金贵把车开到那儿,找了个地方,慢慢地停下了。他把车子锁在那里,领着小云往前走。
“爷爷,咱要干啥?”
“买一棵树。”老头回头望了望孙女儿。
“爷爷,咱要买棵啥树?”
“咱买一棵松树,或者柏树。”
“为啥买松树或者柏树?为什么不买桃儿?爷爷,我爱吃桃儿。”
爷爷没吭声,背着手往前走。孙女说得对,整个市场上,卖桃树的,杏树的,柿子树的,石榴树的,多得很,就是没看见卖松柏的。现在,城市里有院子的少,大都住了楼房。个别有院子的都爱种个果树,不仅能吃到时鲜的果子,枣啊杏的,听起来也吉利。谁会往家里种棵松树或者柏树呢?程金贵领着孙女儿,找了好一阵,终于看见一个卖松树的,塔松。
他挑了一棵最小的,讨价还价,买了下来,放在三轮车上。然后,让小孙女上了车子。他开着车出了花木市场,走了一段,又靠路边停了下来。
“爷爷,你还想买啥?”
“你在这儿等着,爷爷去买瓶酒。”
程金贵跑进路边的商店,不一会儿,便提了一瓶子二锅头出来。小孙女望着爷爷,不知道今天为啥这老头儿犯了酒瘾。在她记忆中,爷爷不常喝酒,但每喝必醉,一醉就说话糊涂,没完没了。她不知道,今天爷爷如果喝醉了,会说出些啥糊涂话。
程金贵领着小孙女到了厂子,先让孩子抱着那个瓦罐子,放到他值班室的床底下。他又一手拿着那个布焰火,一手提着酒瓶子,把它们跟那罐子放到一起。松树,老人没有动,还让它在车子上。老人收拾好了这些,先是在厂子里巡视了一番,接着,又领着小孙女,沿着厂子的院墙,到厂子外面巡逻了一圈儿。这样巡逻一通下来,也就花去了一两个小时。或许是村里老人们的坟都让晚辈迁走了的缘故,今天,虽然是清明节,但到这儿附近来烧纸的却不多。他回来,让孙女儿抱着瓦罐,自己提着酒瓶子,又放到三轮车上。
他开着三轮车,到了厂子里那棵大桑树底下,停了下来。这厂子里进行了简单的绿化,但这棵大桑树肯定不是后来栽上的,而是原来的树保留了下来。他早就看好了,在离桑树不远的一个地方,原来栽着一棵松树。那松树没有栽成,死了。他拿着一把铁锨,走到那枯死的松树前,开始刨那棵已经干死的松树。小孙女觉得有意思,站在一边看着。他卖力地刨了一阵,围着松树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坑。那树不小,但因为死了很久,根早就朽了,摇晃了摇晃,就拔了下来。老头把枯死的松树扔在一边,又用铁锨把坑往下挖了挖。
“妮儿,抱着那瓦罐,慢慢下去,把它放到坑底。”
小云听了他的话,到车里抱起了罐子,回来盯着他,却没有动。
他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小孙女瞪大了眼睛,把罐子搂得更紧了。
“爷爷,为什么把爹……”
“你个傻娃儿,这叫树葬,咱就把你爹埋在这儿,日后你想你爹了,就来看看这棵树。”
“这树就是爹变的吗,这树就是爹吗?”
程金贵想了想,说:“差不多。”
小女孩想了想,显得有些高兴。爹从前是一个黑黑的罐子,现在,爹变成了一棵树,以后还会变成啥?她觉得,虽然树也不好,可总比从前那个罐子强多了,也好看多了。小女孩沿着坑沿儿,小心翼翼地下了坑。她蹲下身子,把瓦罐放在脚下,抬起脸来望着爷爷。
“你跟我学,我说啥,你说啥……”
“行。”
一想爹娘把儿养,得儿一尺五寸长。
白天把儿背身上,夜晚把儿放身旁。
喂儿抱断一双膀,喂儿熬坏眼一双。
倘若儿女有病患,忙请医生开处方。
百家锁儿锁颈项,指望百年寿岁长
……
女孩儿自然不知道,爷爷教她唱的是一首丧歌,是在爹娘的葬礼上,年轻人给老人唱的,名字叫《十悲伤》。小女孩儿跟着爷爷唱完了丧歌,从坑里爬上来,仿佛胜利完成了一项任务,笑嘻嘻地看着爷爷。
程金贵让小孙女往后站站,便开始往坑里填了几锨头土。他手紧紧地攥着锨杠,一看那拿锨的姿势,就知道这是一个干活的老手,是个老把式。土把地下的瓦罐埋没了之后,他便拿起那棵树,放在坑里,让孙女扶着,他一下下往坑里填土。
这样,不一会儿,松树便栽好了,直直地站在那里,那样好看。爷爷干完了活儿,仿佛想要犒劳一下自己,拿起那一瓶二锅头,拧开了盖子。小孙女以为他会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喝下,让她没想到的是,爷爷竟然浇水一样,把一瓶酒全部撒到了那棵树下。
5
这时候,远处大门口来了一辆车,黑色奥迪,油光锃亮,不用看车牌就知道是王厂长的车。王厂长的车缓缓开来,在金贵身边平稳地停下了。金贵低头朝里看了一下,司机小李不在车上,今天开车的是厂长自己。当初应聘的时候,上头有规定,说见了领导和重要客人要敬礼。程金贵退后一步,立定站好,“啪”地给厂长敬了个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的军礼。
王厂长今天似乎心情不错,将车子在金贵身边“嘎”地停住了。他不仅停住了车,还从车上下来,问金贵身边这娃儿是谁,多大了,上了几年级。小云看见生人,有些腼腆,躲到了金贵身后,金贵一一答了。王厂长问了这些,又问安全情况,问可有人祭奠老人烧纸,有的话批评阻止了没有。王厂长又特别交代,安全生产无小事儿,化工厂非同小可,一个火星就能引起一场事故。你虽然只是个保安,可在这时候,你的责任比我厂长还要大哩。你要严厉阻止,但是一点,阻止时也要有理有据,注意方式方法,实在不行就报警。
程金贵点头答应着。
王厂长这样说着,就看见了一旁刚刚栽好的那棵松树。他指了指那棵松树,问:“老程,这是咋回事儿?你在干啥?”
“这树枯了,我补一棵。”老头说着,用脚踢了踢脚下的枯树。
王厂长往树走了两步,上下端详着,又跑回来上下看着程金贵。他开始笑了,说:“老程,你真是好样儿的。当初我留你,还有人提意见,说你年龄大。现在看来,留下你真是对了。这棵小树,枯了,是枯了,没有栽活。这事儿绿化科都没看到,我都没看到,你老程却看到了。看到也没啥!别人看到就看到了,也跟没看到差不多。你不但看到了,还买了棵树补上,用的还是自己的钱,连个招呼都没跟厂子里打。今天,如果不是我恰巧碰上,恰巧看到了这一幕,你说说,老程,你会不会把这事儿告诉我哩?你会不会哩?你不用说话,我知道你不会。你不会告诉我,你就是这样一个人!老程,通过这件小事儿,我认识了你!人说以厂为家,你这才是以厂为家啊。”
王厂长激动地说着这番话,还不时拍拍金贵的肩膀。
程金贵站在那里,盯着松树,盯着那绿油油的钢针一样尖利的松叶。
王厂长钻进车里,往前边开去了,开到办公区去了。王厂长坐在驾驶室里,发动车子的时候,情绪还是那样激动,脸还是红扑扑的。
程金贵领着小孙女儿,走到值班室,指了指床底下,跟小孙女说:“妮儿,你端着那布焰火,端到那棵松树底下去。”
“爷爷,为啥?”
“今天是清明节,你爹刚入了土,咋能那么冷冷清清,没点儿焰火哩?”
王厂长上了楼,来到办公室,拉开了百叶窗帘。他心里还有些激动,朝远处眺望着,寻找着那棵新栽的松树,寻找着那祖孙俩。他看到了他们,他们一高一矮,站在那桑树的不远处,站在那新栽的松树旁边。他看着看着,忽然在他们脚下看到一个火盆,一个里面烧着纸的火盆儿。那火焰是那样红,那样亮,欢快地跳动着,像是一个什么奇怪的活物儿。他先是一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之,他听到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喊着:着火了,着火了!他从百叶窗里看到,一群人冲下楼,喊叫着,正朝程金贵和那女孩在的地方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