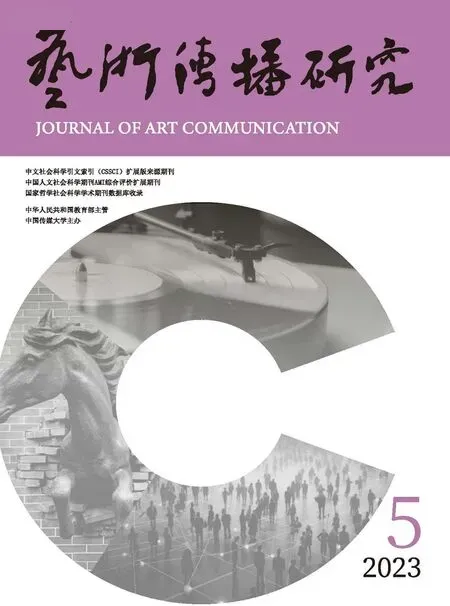中国本土唱片在发端期产生赝品的前因后果
2023-02-17柴俊为
柴俊为
2023年是中国本土唱片诞生120周年。1903年3月18日,在上海“金谷香西餐馆”(1)位于四马路(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一个房间里,诞生了第一张中国本土唱片的母盘——费雷德·盖茨伯格率领的英国留声机公司(the Gramophone &Typewriter Ltd.,简称G&T)录音团队,接下来在中国总共录制了470张母盘。这些母盘被运往德国汉诺威的工厂制成唱片,首版以“克莱姆峰”(Gramophone,现又译“留声机”)品牌上市销售。因此,国内馆藏目录对这批唱片多记有“德商”字样。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批唱片作为首批在中国本土录制的戏曲音乐唱片,目前看来,绝大多数可能是“赝品”,即“伪托”——其署名的表演者并非其实际的表演者。现有证据确凿可以甄别的,涉及小叫天、汪桂芬、孙菊仙、周春奎、汪笑侬、白文奎、小连生、三麻子(王洪寿)、小子和、郭秀华、刘永春、林步青等人物。
显然,这既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英国留声机公司远东之行的初衷。该公司这一次旅行录音,除在中国采录之外,还在印度、日本、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录制了大量的民族音乐唱片,而就目前关于这些国家的唱片的研究看,尚未见类似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单单在中国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呢?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少有学者关注。诚然,有的研究关注到了伪托当时个别名伶,特别是谭鑫培、孙菊仙等人的唱片,但仍把绝大部分“克莱姆峰”的唱片默认为真品,以为“盖茨伯格和徐乾麟所录制的录音,是第一次收录当时上海的著名演员和歌女”(2)[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的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王维江、吕澍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7页。,很少认识到冒名顶替、以假乱真曾是当时洋行所生产的唱片的一个系统性缺陷。这个缺陷既缘于西方商人的傲慢,亦缘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买办阶层的所作所为;而得到国际著名品牌“克莱姆峰”的背书,正是这一缺陷得以扩散的关键。
一、重新解读“上海之行”
盖茨伯格1942年在纽约出版的回忆录《音乐走四方》(TheMusicGoesRound)数十年来多次再版,其中,关于他在上海和香港的回忆的段落以及他的部分日记,为研究东方唱片史的学者较多地引用。不过,这些史料里有两个问题似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第一是盖茨伯格对他所录制的中国戏剧(曲)音乐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对此,今天的读者当然可以用“文化差异”这个理由来解读,然而只要比较该书中对印度、日本甚至缅甸的戏剧音乐的描述,就会发现原因可能不完全如此。固然,盖茨伯格在该书中对印度和日本的某些音乐也表现出相当的不适应——比如关于印度音乐,他曾表示“我的音乐训练的根基被动摇了”,(3)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54.而面对“狂言”这一日本的艺术体裁,他居然直说“对我来讲,听起来就像驴叫”,(4)同上书,第61页。不过,这种负面评论在书中相对来说依然是局部的、特定的;他在这部回忆录中对印度、日本的音乐和唱片业的发展也都有总结性的反思。而谈到上海和香港,他的评价全部是负面的、刻薄的,比如“中国人演唱时用尽全力咆哮”,“他们的音乐理念是巨大的碰撞和轰鸣”,“她们的声音犹如小猫的哀鸣”,(5)同上书,第63页。除此之外似乎别无话说。对于一名有着相当音乐修养的作者来说,这样的评价差异背后,除了文化因素外应当还有其他的原因,譬如对其他民族的精神世界缺少理解的意愿,又如他所遇见的演员的水平、修养及其所继承的风格是否真的代表了中国戏剧戏曲的最高水准。
第二个问题或许更为关键,即盖茨伯格团队在上海录音时,其采录程序及酬劳制度均异于在其他国家的惯例。
这次远东之行,录音团队在各地的工作程序本来是差不多的:每到一地,均由当地的中间人(主要是英裔人士)带领,寻找合适的艺人、剧团,然后观摩其表演,随后制定录音计划,再进行采录。在加尔各答,由于该公司当地分支机构的英裔印度职员对印度音乐毫无兴趣,盖茨伯格还专门找了当地的警察陪同去“哈里森路的各种重要娱乐场所和剧院”,又去当地富豪家参加晚宴,观看少女表演的歌舞(“Nautch”),然后,选了一位著名的歌手古拉·扬(Goura Jan)来录音,她每晚的出场费是300卢比。此后,又约到了当时有“最好的(印度)古典歌手”之称的扬基·拜伊(Janki Bai),录音费高达3000卢比。(6)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p.55-57.团队在印度大约花了6周时间,录制了500多个母版。在日本的时间更长——盖茨伯格是“1903年新年的那一周”(7)同上书,第59页。到达横滨湾的,而他的日记显示,直到2月13日他还在为日本艺妓录音。采录小组在东京一开始就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参观剧院和茶楼,并进行试音。盖茨伯格回忆说,他们“拟定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民族音乐录制清单”(8)同上。,最后录制了600张各种类型的日本传统音乐唱片,支付的费用高低不等,每段在5美元到30美元之间,一般是20美元。后来,该团队离开中国后到达缅甸,也是先观摩了名为“ZAT”的当地杂剧演出,然后录制了40张成套的唱片。
对比之下,盖茨伯格在中国上海的工作则颇有异样,这主要表现在两点:速度快和价格低。在日程方面,1903年3月16日,他们与英商“谋得利洋行”(The important music-house of Moutrie &Co.(9)同上书,第62页。)的中间人见面,商定由他去安排演员;次日,在洋行为他们安排的西菜馆布置录音设备;第三天即开始录音,仅用9天时间就完成了325张唱片的录制——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说,“效率”高得有些惊人。在酬劳方面,竟然不分剧种、不分演员优劣,一律每段4美元,这个价格也低于团队在日本、印度所出的最低价。
这部回忆录没有记载团队到达上海的日期,也没有记载在上海观摩演出、挑选演员的详情。其中的一则日记表明,他对前来录音的演员及其带来的节目并不了解,以至于第一天只录了10段,不得不中止:
3月18日,星期三。我们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大约来了15个中国人,包括伴奏乐队。中国人演唱时用尽全力咆哮,每晚只能唱两首曲子,然后嗓子就沙哑了……
第一天,在制作了10张唱片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喧嚣让我的头脑麻痹,无法思考。(10)同上。
抛开一些明显带有傲慢和偏见的修辞不谈,这里很引人注意的一个信息点是:谋得利洋行安排的演员演唱,使盖茨伯格大为意外,不得不停止录音以解决技术问题。假设盖茨伯格事先对演员和演出有所了解,接触过后来姓名被写在片心上的名伶,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如果亲自与名伶的管事(类似经纪人)进行过谈判,他也会知道4美元一段的价格是请不到名角的。两年之后,名伶陆续应邀参加录音的价格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1)参见柴俊为:《中国戏曲唱片赝品概述》,载傅谨主编《京剧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第八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21年版,第589页。
必须指出,“谋得利洋行”主营“注重乐器洋琴,话匣仅系一种副业”(12)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下),《时事新报》1928年7月30日第14版。。用现在的话说,它主要的身份是一家外贸乐器行,虽与音乐有关系,但并不是生产和销售“音乐录音”的公司,何况当时的中国也不存在专业的录音公司。那么,为什么盖茨伯格会认为它是一家“重要的音乐室”呢?这,应该就涉及了该录音团队在上海被“安排”(arrangement)的关键环节。而由这次“安排”所形成的录制销售模式,直接影响了之后十余年的中国唱片业。
二、圆盘唱片到来前的中国留声机市场
从商业角度考察,可以发现这次“安排”的快速完成与当时中国蜡筒留声机的销售模式有直接关系。现有的许多记述表明,在圆盘唱片录音来到上海之前,中国已经有留声机销售——笔者最近发现的一篇1928年的报道说得更详细:
话匣又名留声机器,三十年前已有之,其时有法人那泼者首先在吾国发售,假南顺泰为发行所,惟所制造之机器殊为草率,如钟表有发条,推之能动而已,传声者系蜡筒……(13)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按“三十年前已有之”,则最迟1898年就有了。我们看到,目前残存的戏曲蜡筒实物虽由不同的洋行、商号录制,但很多是百代公司出品的空白蜡筒,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法人那泼者首先在吾国发售”的说法。当然,盖茨伯格到上海时,销售蜡筒留声机的已远不只有法国商人。在欧美,留声机一开始主要是作为商用的听写机销售的,在家庭娱乐方面的价值开发得比较晚。早期的蜡筒不能批量复制,所以最初并没有真正的“唱片商品”可以供应。对一般的艺术消费者而言,既然没有音乐内容提供,留声机就难以推广。欧美的商业录音活动始于1889年,最早开发这项业务的是爱迪生公司,但该公司仅坚持了8个月即退出,直到1895年左右才重回录音生产。与爱迪生公司差不多同时且能够持续开展商业录音业务的是哥伦比亚公司,后者堪称世界商业录音的奠基者之一(14)参见Tim Brooks,“Columbia Recordsinthe 1890s:Founding the Record Industry,”ARSC Journal,(1978):6-7.。该公司除了供家庭娱乐之外,还着力推广一项风靡了多年的点唱机业务。遗憾的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当时没有出现这样敢于冒险的先驱者,为了销售留声机,洋行经营者开发了一项“只赚不赔”的小生意:
……其时尚未发明今日复印流传之方法,如欲购买,将机器之价格及所需蜡筒之多寡,预先订定价目后,方由该公司雇清音前来收音,其价值颇廉,如雇清音来唱一日,代价三元左右,而一日至少可收至十余筒,每一蜡筒仅值小银元二三角而已。然每售一筒必须收音一次,亦太费事矣。(15)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清音”又称“堂名”,源于昆曲清唱,但到了清末的上海,已沦为一种半业余的打唱班,专应婚丧嫁娶上门清唱,另外商号开张、节日祭神等活动亦多请清音班凑热闹。清音班只应清唱、演奏,不能化妆登台,营业特性正合留声机灌音,但其中不少人的艺术水准相当平庸。
从为数不多的现存戏曲蜡筒可以看出,经营这种灌音业务的不只一家。但这种为销售留声机所录制的蜡筒,也很难说是正规的“音乐产品”,它更像一种代客加工服务。这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开创的那种有品牌、有版权、有目录(相对标准化)且能够小批量复制的商业录音还是有根本的区别。不过,这种“代客录音”业务,恰好为盖茨伯格的上海之行(以及此后中国商业唱片的发展)准备了一个“便利”条件和一个“陷阱”。
所谓“便利”条件,就是聚集了一个以清音班为主的灌音圈子。我们在现存的蜡筒和不同品牌的赝品唱片里,会听到一些相同的嗓音,并且经常反复灌制同一个唱段。在盖茨伯格录制的唱片里,有一张写作《一支令·前段》(16)模版号E1513,目录号G.C.12506。,署名“周春奎”,另一张写作《三支令·后段》(17)模版号E1514,目录号G.C.12507。,署名“孙菊仙”,实际是同一人所唱。此人的特点是一嘴的南方字音。这两张合起来是一段戏,即京剧《天水关》中诸葛亮“派将”,给魏延、马岱分别下了一支令箭,又给关兴和张苞下了一支令箭,俗称“三支令”。此人大概很得意自己这段演唱,1905年又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了一遍,用的名字是“裘处”,表明是票友身份;同年,他又用这段在胜利公司分别灌了一张10英寸和一张12英寸片——10英寸片一人到底,署名“白文奎”;12英寸片比较完整,加上了魏延、马岱“接令”的配唱,署名“杨处、小金红、马飞珠”(18)模版号、目录号9167。。次年,海因里希·布蒙(Heinrich Bumb)到上海,此演员又出现在“拨加(Beka)唱片”的录音现场,演唱中仍有这一段,复以“裘处”署名(19)笔者怀疑此人即为裘姓票友,胜利公司署“杨处”可能是笔误。。像这样的事情绝非孤例,甚至一些知名的演员也加入过这个圈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冯二狗。冯二狗是名旦小子和(冯子和)的兄长,其丑角的声价虽然在林步青、姜善珍、何家声等名丑之下,不过早年有嗓,能唱,除本工以外,在《十八扯》等戏里学老生、小生均有是处,尤其学孙菊仙“几可乱真”(20)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李名正整理,载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辑),上海艺术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页。,胜利唱片有他学孙菊仙的《雪杯圆》。此外,他还能唱苏滩、本滩、小热昏等,均有唱片存世。因此,他可称是早期录音圈的大忙人,大量的唱片里都有他的声音。劳弗(Berthold Laufer)代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NH)1901年9月在上海录制(21)1901年9月至1902年,德国人类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劳弗代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来中国考察,在上海和北京录制了一批戏曲、曲艺及民间音乐蜡筒,其中有400个蜡筒目前保存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统音乐档案馆。的现存蜡筒中也有他的节目,比如梆子《翠屏山》中的潘老丈(22)Collected by Berthold Laufer,China,Shanghai and Peking,1901-1902,SCY2895,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海和尚(23)同上,SCY2914-2915,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南无调《和尚采鲜花》(24)同上,SCY2921,https://media.dlib.indiana.edu/media_objects/3f462n38f.等。以他为代表可见,这批演员当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灌音经验。
所谓“陷阱”,就是用这批演员来冒充名伶。当时,与美国的自动点唱机业务有点类似,中国乃至亚洲其他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人工点唱机”——留声机小贩:
唱机形式……一种是装置喇叭的,声浪较响,便于大处静听;一种是用橡皮带头,一组分支好几副……每人纳了相当(的)听费,他就会给你一副塞入耳内,开唱时你就能听到蜡筒上所放出的戏曲声音来了。这一类大都是走江湖的所置,专走乡村小镇的处所,欣赏的孩童居多。(25)丁慕琴:《唱片漫谈》,《大美电台周报》第3期(1946年1月24日),第3页。
而这些留声机小贩播放的蜡筒,其内容几乎都在假冒当红的名角:
当时人们对这新出现的玩意儿,不免带些好奇的心理,其所以能够吸引人们的兴趣,就在于这些摊桌上除设置有留声机(备有五六根橡皮管供人塞在两耳收听的听筒)一座外,还陈列着许多灌有京剧名角所唱的蜡筒,每一纸壳上都有标签,写明汪桂芬的《文昭关》,小叫天的《卖马》,或孙菊仙的《硃砂痣》等。人们虽明知俱是假,好在每听一次只要化八文钱,能过一次戏瘾,也就不在乎了。(26)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李名正整理,载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辑),上海艺术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页。
综上可见,在盖茨伯格到来之前,上海的一些洋行及其买办人员已经制造了一套“录音造假模式”。
三、南顺泰洋行、谋得利洋行与徐乾麟
盖茨伯格要想不跌入这个赝品陷阱,除非有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他自己要了解当时在当地留声机销售领域中的这套运作“底细”。另一方面,遇到的合作者要有见识、有资源、有基本的商业道德——这就需要合作方能认识到圆盘唱片的前景,把眼光放长远,不做那种“三元钱”成本、“卖一制一”的作坊式生意,还必须掌握梨园界的资源,能约到且愿意去约真正的名家。遗憾的是,这些条件都不具备——盖茨伯格的合作者是英商谋得利公司。
《时事新报》的文章说,“西人在华营话匣业者,以南顺泰为最早,其次即谋得利琴行”(27)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南顺泰洋行位于新开河浜,是一家德商,它和谋得利都跟徐乾麟有关系。徐乾麟从1882年起即担任谋得利洋行的华人买办,同时又是南顺泰的执事(28)佚名:《英美租界公堂会讯案》,《申报》1901年4月7日第3版。。上海的这套留声机经营模式,他显然是熟悉的。
盖茨伯格在当年3月16日的日记中说:“我们与一位河南路的买办(中间人)George Jailing[他的中文名字叫Shing Chong(音译)]作了安排,由他来组织艺术家。”(29)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62.这里的“George Jailing”是否是徐乾麟,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毕竟这两个名字都与徐乾麟常用的英文名C.L.Zeen不符。不过,作为谋得利洋行唯一的华人买办,在这种与华人及中国文化相关的业务中,徐乾麟是决策的主导者,这一点在学界是无异议的。
国外的一些学者把徐乾麟,以及后来协助胜利公司录音的“Yuen Sing Foong 先生”误认为是“京剧爱好者”“票友”,以为他们“在上海的娱乐圈有广泛的人脉”(30)Christina Lubinski and Andreas Steen,“Traveling Entrepreneurs,Traveling Sounds:The Early Gramophone Business in India and China,”Itinerario:European Journal of Qverseas History 41,no.2(2017):282.,通过他们“才能为物克多公司争取到中国最好的人才”(31)同上文,第287页。,笔者不知其有何依据。《时事新报》的文章坦言,“该行买办徐乾麟先生与伶界素无往来”(32)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要知道,清音班与戏班的性质不同。清音自古就是半业余性质的演出团体,营业方式是“开门接生意”,上海的有些清音班干脆设于沿街,有人上门来约就去唱。因此,请他们去录清唱几乎没有门槛。而专业演员的主业是戏院(当时叫茶园)演出,虽然观客上园子看戏也没有戏票资金之外的门槛,但是请他们(特别是名角)外出应堂会或参加票房清唱等活动,包括后来的录音活动,则必须有人脉,另外还得“懂行”。在盖茨伯格录音的几年以后,百代公司在北京由谭派名票乔荩臣作买办,高亭公司聘罗亮生为顾问,蓓开公司聘用剧评家梅花馆主等,都是这个道理。另外,徐乾麟等人明显也不是“京剧爱好者”或“票友”。盖茨伯格的日记说,他的一位朋友来参观录音,问唱的是否属于情歌,买办回答“不是,他是在唱自己的祖母”(No,he is singing about his grandmother)。(33)F.W.Gaisberg,The Music Goes Round(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42),p.63.笔者查阅“克莱姆峰”上海唱片的全部目录,未发现哪一段的内容与“祖母”有关,而在传统戏曲里也几乎找不到有“哀歌”祖母的唱段,所以这段记载极有可能反映了买办自己因听不懂而信口开河。罗亮生曾直言:“该行华人经理徐乾麟认为对唱片录音何必要顶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即堂名)的人来唱,写上名角的名字,既便当又省费,而且一样可以行销。”(34)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李名正整理,载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辑),上海艺术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页。这种灌片理念足见此类买办对戏曲艺术是没有感情的。像上述《三支令》的例子,一个人唱同一出戏,竟可以分别假冒“孙菊仙”和“白文奎”两位名角;在1905年乔治·切尼的录音中,他们又把真的孙菊仙和清音班所唱的录音同时署为“孙菊仙”;谋得利主持的后三次录音中,有一名清音老生现存近90段录音,先后或同时被署以“双处”“时慧宝”“马昆山”“马处”等四五个名字(35)柴俊为:《双处及其唱片真伪考辨》,《中国京剧》2023年第8期。……这些随心所欲的做法,充分显示徐乾麟和他的下属是戏曲的外行,京剧爱好者必不至于如此荒唐,至少也可以做得略微像样一些。
笔者梳理这些细节主要是想说明,无论盖茨伯格是否愿意,以谋得利洋行当时的人脉资源和业务知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帮盖茨伯格约来真正的名角录制300多张母盘。盖茨伯格在上海之所以录得快、价格又低,就是因为谋得利“安排”了清音班唱蜡筒的熟手们。何况徐乾麟也向《时事新报》坦承“最初所制蜡片(36)所谓“蜡片”,当指录音使用的母盘。最初,一个母盘只能复制一个模版,1902年以后,新技术使得一个录音母盘已可以复制多个模版,唱片的产量因此大幅提高。,即雇当地清音所唱”。(37)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然而,盖茨伯格未必有兴趣了解其中底细,谋得利也未必明确告诉他这些人都是用来冒充名角的。当时,西方的留声机业正处于法律大战的漩涡,公司方面如果了解真相,应该也不太可能冒这样的侵权风险。
四、“谋得利-克莱姆峰模式”
尽管盖茨伯格的上海之行掉入“赝品陷阱”,在中国唱片业发展史上留下了较为不堪的一幕,但就当时的市场反应而言,这些赝品的销售情况居然不错。虽然音乐内容的艺术品质一言难尽,但是产品的可选性、耐用性、便捷性、新鲜感相比之前的“可录式”蜡筒都大幅提升了,所以吸引力不言而喻。据说,470个华语模版一共压制了36 000张唱片,除了在中国销售,海外的巴黎、布鲁塞尔、苏门答腊等地也都有经销商询问订货。(38)[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的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王维江、吕澍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销售上的成功很快引来了投资竞争。1906年1月,拨加(Beka)公司的旅行录音小组刚到香港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
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刚刚完成了最新的录音——据说有1 000段,支付了50 000美元的费用。 “物克多”“克莱姆峰”以及“新乐风”(Zonophon-Records)和“高亭”在(香港地区)……都有代表。(39)John Want,“The Great Beka Expedition,1905-6,”The Talking Machine Review,No.41(1976):729-733.
从文献价值方面看,“克莱姆峰”的赝品也确有意义,不过只是一种“歪打正着”的意义: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京剧、梆子等所谓“乱弹”剧种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平庸”演员与著名演员之间除了艺术修养与技巧水平的差别之外,还有一种因从民间艺术、广场艺术逐渐向城市戏剧、剧场艺术发展而形成的历史性差异。早期比较原始、粗糙的艺术风格和戏路常常保存在一些底层演员甚至票友的身上;而这些早期唱片与名演员的交集更少,这种历史的陈旧风貌也就保留得更多——这个问题容笔者另做专题研究时详述。但显然,这并不能抵消“克莱姆峰”唱片在中国唱片历史发展中的显著负面影响。
不讲商业诚信,欺骗消费者,侵犯名演员权益……这些问题自不待言,“克莱姆峰”唱片最根本的问题是,把原先流行在中国洋行间的那种“卖一制一”的小作坊式欺诈给工业化、国际化了。这种“商业欺诈”在这样的跨国企业及其著名品牌的背书下迅速扩张,十余年间,争相加入中国市场的欧美唱片企业除了百代公司之外,哥伦比亚(Columbia)、胜利(Victor)、高亭(利喴,Oden)、拨加(Beka)等公司或多或少都在中国生产过赝品。(40)柴俊为:《中国戏曲唱片赝品概述》,载傅谨主编《京剧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第八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21年版,第585-598页。可以说,当时中国的唱片录制一时间形成了一种“谋得利-克莱姆峰模式”。
民国以降,不少研究者因不明底细,往往把此类赝品误解为特定的“高仿”。比如在关于孙菊仙唱片真伪的争议中,剧评家们纷纷猜测是学孙菊仙较有成就的冯二狗、双处、时慧宝、吕月樵等假冒孙菊仙。这种思路可能引导当代学者产生了更深的误解:
一开始,胜利和谋得利公司(或者说买办徐乾麟)试图利用他(按:指谭鑫培)的名字获利。他们请了几个学了谭派唱腔的票友来上海的录音棚录音,然后贴上“谭鑫培唱×××”的标签……(41)[德]史通文:《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的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王维江、吕澍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实际上,当时除百代公司完全拒绝“谋得利-克莱姆峰模式”之外,同业其他公司几乎都采用了这个模式。在现存的大量唱片中,我们既可以发现同一个人的录音写成两三个甚至更多名角的名字的情况,又可以发现同一名角分别被几人假冒的情况,所以很可能根本无所谓假冒者是不是学了“×派唱腔”的。一个比较夸张的例子是,1907年录音的利喴苏滩唱片,其中署名林步青、张筱棣、周凤林的均为女子苏滩之叶菊荪一人所唱,仅笔者所见即多达48面,实际当远远不止(42)这批唱片的目录及考证依据,参见柴俊为:《中国戏曲唱片赝品概述》,载傅谨主编《京剧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第八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第594-596页。——造假已经造到连男声、女声都不在乎的地步,遑论流派风格。
这种冒充名角的做法形成一种行业痼疾之后,至少造成了两大不良后果。
第一,错失历史机遇。举个极端的例子,当时京剧界的三大代表人物汪(桂芬)、谭(鑫培)、孙(菊仙)之中,汪寿命最短,于1908年6月10日去世。据目前所知,汪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是1907年9月的福寿堂义演。此次义演由田际云、李毓臣、乔荩臣等发起,“汪桂芬头一个赞成”(43)佚名:《记汪桂芬在福寿堂演义务戏事》(一),《顺天时报》1907年9月6日第5版。,他第一天唱了《取成都》,第二天唱了《群英会》,第三天的《战长沙》即未参演。从时间上看,如果早一点采取“百代模式”(44)柴俊为:《中国戏曲唱片赝品概述》,载傅谨主编《京剧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第八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21年版,第586-587页。,哥伦比亚、胜利、拨加都有机会填补“后三鼎甲”的声音缺失。遗憾的是,这三家公司第一次到中国,都是紧随盖茨伯格的足迹,从香港(或广州)到上海,而没有到京城的计划。当然,汪桂芬的例子包含了假设,毕竟就个例而言,即使后续有更多的公司按照“百代模式”诚实经营,以汪桂芬的怪脾气,他仍然可能不去录音。但是,从概率上讲,由于绝大多数公司沿袭了“谋得利-克莱姆峰模式”,中国唱片业在其最初的十年里失去的就肯定不止一个“汪桂芬”。
第二,浪费颇多资源。中国唱片业起步的十年,有大量的资金和母版重复消耗在低质量的演唱上。如前文所述,以清音班为主的那个“录音圈”人数有限,录制的重复率极高。在中国唱片资源最稀缺的那些年灌制唱片最多的,不是当时的名伶,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半业余演唱者。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这一模式在得到市场反馈和资本加持后,很快产生了新的“变异”。1904至1905年在上海录音的哥伦比亚公司,花了数月的时间才录了1 000个模版,录制速度明显降低。我们在存世不多的相关唱片实物中看到,它们虽然还是以清音(堂名)演唱为主的赝品,但是也有林步青(《打宁波会馆》《跑马赋》等)、时慧宝(《教子》《琼林宴》)、刘永春(《铡美案》)、汪笑侬(《瓜种兰因》《党人碑》)、三麻子(《举鼎观画》)等名伶的真品。也就是说,在“克莱姆峰”之后,其他厂家在造假的基础上,也开始尽财力、人力所及,邀请一些名角录音了。很快,这一“变异”也传到了谋得利。紧跟哥伦比亚公司来华的胜利(Victor,时称物克多)公司与“克莱姆峰”为关联企业,所以其录音师乔治·切尼到上海之后也找谋得利代理(45)哥伦比亚公司在美国跟胜利公司是死对头,后者的总裁曾用诡计挖走前者生产圆盘唱片的子公司“环球唱片”。后者又与“克莱姆峰”是关联企业,1904年以后,双方制定协议:“克莱姆峰”品牌专注于印度及远东其他地区业务,中国区的业务归胜利公司。因此,“克莱姆峰”的部分华语唱片此后以“物克多”品牌再版销售。约请名角的新举措一定程度上也是老对手相互竞争的结果。:
谋得利第一次请名伶收音时,因该行买办徐乾麟先生与伶界素无往来,颇感困难。后有金谷香西菜馆西崽某某与小连生(即潘月樵)交好,经其介绍,得与徐乾麟相识,小连生乃为徐君在伶界中竭力宣传,又拉拢同业前往清唱,故第一次得度收音成功,小连生之力居多也。(46)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
必须指出,此文为谋得利、徐乾麟辩护的立场鲜明,叙述中时空倒错、夸大其词等问题在所难免,但其提到的第一次为物克多录音时邀请名角却是事实。我们现在在充斥着大量赝品的当年的唱片中,可以找到汪笑侬、林步青以及真小桂芬(张桂芬),包括后来争议不止的孙菊仙等少数名家的部分真品。
不能否认,这一“变异”客观上对后来中国唱片的逐步转型和文献保存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虽然现存的1905年唱片中能确认的名角非常有限,但是此后约请名角的数量渐渐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哥伦比亚和物克多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录音中,真品数量都比最初有较大的提升。然而糟糕的是,这种“鱼龙混杂”的出版行为,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无解的文献难题。
这种难题在“克莱姆峰”的唱片里已经存在。从现存的唱片来看,该品牌的唱片并非全是“当地清音所唱”,(47)退庵:《话匣与伶人之关系》(上),《时事新报》1928年7月29日第14版。其中有十来张是女声,除“林黛玉”之外,片心署名都有“妓女”字样。当时,在茶楼、书场有大量的妓女卖唱,她们在蜡筒时代就已步入“录音圈”,比如“劳弗蜡筒”中即有大量的妓女演唱录音——这应该是出于国外录音团队要求兼录男女声的要求,然而他们或许不完全了解:中国戏曲的声音性别,并不取决于演员的生理性别。“克莱姆峰”的这些“妓女”唱片现在很难断定真伪,毕竟除了没有公认的真品可供比对之外,这些卖唱女子也不像名伶那样有剧评、传记等旁证可以参考,甚至都无法用演唱水准去衡量——即使唱得很糟,也可能是真品,因为妓女唱曲并非专业,跟名伶不同,其唱工高低跟名气没有必然的联系。
另外,罗亮生曾指认徐乾麟经手的谋得利录音包括筱荣祥等人的演唱:
那次录音所邀的角色中如冯二狗,他学孙菊仙几乎可以乱真。其他如筱荣祥、孙瑞堂以及在堂名唱老生名的阿狗(忘其姓)等也都是以唱工出名的。(48)罗亮生:《戏曲唱片史话》,李名正整理,载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1辑),上海艺术研究所1986年印制,第99页。
罗亮生先生的口述并没有指明是哪一次录音。从上下文的表面意思来看,似乎是指胜利唱片的那次。胜利公司的三次录音,现在未见到完整目录,已发现的唱片中并无筱荣祥,唯有“克莱姆峰”唱片中有11张,其中《洪羊洞》一片还有1905年再版的胜利版(49)目录号6836。。也就是说,罗先生说的“那次录音”很可能就是1903年盖茨伯格的录音;然而,“克莱姆峰”的唱片又没有冯二狗、孙瑞堂的名字,因此也可能是把徐乾麟主导的多次录音混为一谈了。当然,还有一种更极端的可能性,即他们也被用来冒充名伶,无法辨识了。(50)根据目前掌握的造假规律看,似乎不太可能。名演员被用来造假的例子极为特殊,容另文详述。
等到名角加入之后,这类文献难题就更多、更复杂了。比如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孙菊仙唱片真伪”争议就是一桩离奇的学术公案。双方当事人在世时,一个声明“我孙某人从不灌片”,一个指认“我给你灌过唱片”,不对簿公堂,只打口水仗。究其症结,就在于谋得利在“克莱姆峰”和“胜利”两个品牌上都伪造过孙菊仙唱片,所以即使有真品,在争论时也难以取信众人。如此一来,在中国最大的戏曲剧种——京剧的鼎盛时代,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后三鼎甲”中,汪桂芬唱片均属赝品,孙菊仙唱片真伪争论不休,近一个世纪来只有谭鑫培的“七张半”百代唱片堪称确凿可信的声音资料。
如今,还有当时的大量唱片处于“死无对证”的状态。近些年,笔者根据公认的百代唱片真品,结合史料文献等旁证,逐步辨析了一些标署名角如孙菊仙、刘永春、“小桂芬”、双处、林步青等的唱片的真伪。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文献数字化的普及,使早期唱片的真伪研究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性;特别是近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可望为验证唱片、推进相关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但是,接触早期唱片文献越多,研究越深入,也越容易发现有许多早期声音文献是“无解”的,可供比对、参考的资料更少——涉及梆子、粤剧、潮剧等剧种。若没有可靠的资料作为参照,人工智能恐怕也回天乏术。这不能不说是“谋得利-克莱姆峰模式”留在中国声音文化史上的巨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