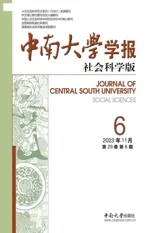中国式道德现代化:意识与规范的秩序性契合
2023-02-13舒高磊
舒高磊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现代化进程使人们的道德心理、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变化,促使伦理文明产生了新形态。西方式道德现代化进程虽然伴随着正义、德性等向善追求,但是始终不能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中国式道德现代化则提供了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方案,其所蕴含的道德逻辑既注重解决现代性矛盾,也着眼于建构现代化秩序。中国式道德现代化遵循唯物史观调节“意识-规范”的结合效度:缓解了自由化、个体性的道德意识对集体秩序的冲击,避免了制度化、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对个人生活的忽视。这种自由意识与公共规范互相调适的过程,是自我至善追求与公共至善目标的互动过程,也是中国式道德现代化的历史主题和未来旨向。
一、在革命战争中解放主体德性:意识自觉-摆脱传统规范依附
我国现代化历程可追溯至洋务运动时期,政治革命、文化运动以及列强侵扰使传统封建秩序深陷危机,原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难以适应现代化转型的需要,逐渐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自魏源等启蒙学者掀起“西学东渐”浪潮,多种思潮跟随着中国传统经济卷入世界市场的步伐渗透进来,猛烈冲击着传统规范的伦理根基;辛亥革命虽然破除了封建制度枷锁,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传统伦理关系,国民内心仍残留着传统的规范道德,因而伦理革命就要肩负起唤醒民族自觉的重任;新文化运动将群众的自我解放意识与集体向善精神结合起来,以“民主”“科学”为武器批判集权秩序及其统治工具,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礼教的纲常旧俗,传播自由开化的人道精神。尽管近代伦理革命不能直接促成民族独立,但却打破了民众依附传统规范的思维惯性,为创造新经济关系、建构新政治制度凝聚了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健全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及‘集体主义’的人生观(反对个人主义;各个人当择一宗旨,结为团体,服从其分配工作以达共同目的,亦即自己之目的……决不应以为共产主义便真是‘过激主义’—— 蔑视一切个人私德)”[1],饱含着以无产阶级新道德取代传统旧道德的愿景。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通过伦理革命激发国民的“自觉智能”,以主动进取的“日新之德”塑造民众新的生活态度、新的人格品性,并以此粉碎传统宗法秩序及其道义根基。封建伦理同集权政治互为表里,将礼教伪装成愚弄民众的专制工具,使其沦为奴隶的而非自主的、退隐的而非进取的、虚伪的而非实际的、想象的而非科学的驭民手段[2](90-95),成为依赖绝对命令、苟安生存逆境、承认因袭合理的无端羁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不具备独立人格、自主权利和变革精神,仍然坚持对统治权威的人身依附和信仰崇拜,使道德文化领域的惰性心理、奴性意识越来越阻碍现代化发展进程。其实,道德精神本应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转型,“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3](145),但在那些怠惰、庸碌、遁世、颓败风气的浸染下,绝大多数国民早已习惯于臣服而缺乏价值期待。当他们将统治阶级规范视为必然尊奉的绝对纲领时,新道德观念自然就难以被接受,破旧立新的革命活动也便失去了群众参与的情感基础。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政治律令、文化霸权愈发挤压人们的生活空间,麻木滞重的社会气象不断消解着国民的解放热忱,“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2](213)。如果全社会都缺乏革命精神、创新活力,那么传统伦理就开始面临转型困境或断裂危机。
在近代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博弈中,马克思主义伦理观促使民族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成为改造国民性的有利思想武器。五四运动延续着辛亥革命以来的思想开化进程,使私德与公意逐渐由对抗走向融合,道德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也不再专属于统治阶级,而是逐渐下沉到普罗大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看法,维护个人权益并不排斥尊重集体秩序,公共生活也要以肯定个体价值为前提,“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的机会……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3](327)。掌握了这种公与私的辩证联系,既可以避免社会的普遍规范抹煞个体的自觉性,还能通过丰富个体的善性来杜绝其利己主义倾向。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通过倡导社群情感、公德精神来扭转私德堕落的局面,通过向国民灌输团结互助的权利观、义务感,抛弃私有制度中的个人主义旧道德,创造富有同情心、公共性的集体主义新道德。马克思主义伦理观解决了社会转型中的道德缺位问题,超越了资产阶级人道原则的狭隘性和封建主义价值观念的局限性,为新生活革命提供了符合现代化标准的伦理支撑,使更多有志民众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中转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将无产阶级伦理精神付诸工农实践,通过明确道德现象的阶级立场和价值基础,使社会主义道德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合法地位。统治阶级擅长将自身的价值准则设置成具有公共形式和普遍效力的社群规范,假借所谓的“绝对真理”来攫取特殊利益,并维持其集权统治。但经验世界并没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永恒标准,不同社会或组织的道德呈现必然有所差别,那些标榜“超验善恶观”的初民幻想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所以,道德意识形态的阶级真相不能被遮蔽,“新旧社会制度更迭的过渡时间,必然有相异的道德观念之争(旧礼教与新思潮之争),其实是阶级斗争反映到社会心理里来罢了”[4]。可见道德文化的阶级属性始终是社会革命、人性解放的重要方面,“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5](870)。无论是颓败的封建枷锁还是逐利的资本逻辑,都充斥着不同阶级间的价值对抗,既不能彻底扫除陈规陋俗的思想沉渣,也不能粉碎肆意剥削的权力工具;而社会主义道德则拒绝压抑和物化人性,推崇“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愿景,预示着对新型人际关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新民主主义道德革命与无产阶级工农实践密切配合,不断锤炼着新的人格、塑造着新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启蒙与文化改造相结合,清算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情感留恋,以新伦理革命破除封建的、资本的意识形态迷障。道德意识形态植根于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不偏不倚的道德理想在阶级社会中没有生存的土壤,那么社会形态更迭就意味着道德规范体系变革,因而在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浪潮中,固守传统道德规范只会让人继续经受腐朽文化遗存的思想浸染。“封建制度下的地方主义、个人主义、宗族关系、迷信、不能集中等天生成的弱点很多,通通是不革命的,应加以改造。”[6](50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构新型文化秩序,倡导“自觉至、个性张”等现代精神,鼓励国民主动自救并积极创造享有尊严的新生活:一方面,将德性解放作为精神气质转型的基本前提,促进无产阶级自觉反思旧文化形态、重塑新文明风尚,彻底打破肤浅凡庸的宗法桎梏、狭隘自限的礼教束缚,将原来的思想藩篱、生活牢笼改造成道德清朗的人性邦国;另一方面,通过完善宣传机制、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组织公德普及活动来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通过改革婚姻制度、传播人道理念、鼓励参政议政来提升军民的文明程度,激发他们共建和谐秩序的热情。
中国共产党将道德建设寓于教育事业中,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荣辱观念,在革命根据地的新型阶级关系中蔚然成风。为实现“行动的纪律化——反对无政府的倾向……生活的集体化——反对个人主义”[6](82),共产党人不仅在苏维埃教育事业中传播共产主义道德知识,培育民众的集体互助情感、遵纪守法意识、克己奉公理念、团结友爱精神,争取中间阶级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觉悟;还坚决批判伪善主义、反对宗法教义,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谬误,纠正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忽视客观规律的认知偏差,避免出现动机不纯、意志不坚的偏颇倾向。共产党人强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7],通过道德模范赋予共产主义伦理以可观可感的现实形象,发挥英模榜样、事业先锋、群众领袖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引领作用,激发无产阶级工农群众革命自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社会主义文艺站在人民解放的立场歌颂善、批判恶,弘扬集体权益高于私人利益的伦理精神,鼓励民众做满怀道德情操、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的纯粹的人;同时批判那些自诩为“超越了功利原则”却又抱着自私狭隘思想的伪善者,及其超阶级的抽象、普世的人性观念,为革命根据地军民的道德生活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
新民主主义道德体现着民族解放的政治伦理,营造了胸怀正义精神且担当忠诚、服务人民群众而不谋私利的文化氛围,是共产主义理想的生动实践、集体主义价值的真实弘扬,激发了无产阶级爱国自救的道德热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特别注重通过教育党员、整训军队的方式推进道德建设:既要求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对照党章律令及时进行检查和纠偏,引领党员争做德性优良、政治坚强、思想先进、生活高洁的模范革命家,不因私心而丧失党性原则、忽视科学真理、逾越集体规范;还借助军队整训将纪律条例内化为战士的自觉意识,以民主作风肃清封建堕落的思想残余、生活旧习,通过健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条例规范,将革命队伍团结在科学社会主义价值准则下。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道德不是“精神个人主义”的纯粹自我实现,而是充分体现了集体主义的群众史观:彻底克服本位思想和自利倾向,将私人感情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集体意识、忘我精神,既要求个人实践遵循集体规范以促成自我完善,也注重激发群众的主体创造力以发挥首创精神。
二、在国家建设中形塑道德制度:意识善为-遵循集体规范原则
新民主主义道德精神在新中国的文化秩序中得以延续,是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需求,不是脱离人民群众和国家实情的超阶级想象。这种经由实践孕育和检验的道德文化秩序,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集体主义属性,体现了国家意志(象征着集体和谐的公共规范)与人民权益(象征着个体向善的自由意识)互促共进的价值关联,两者之间不再有难以调和的矛盾。既然无产阶级道德最终指向人的解放,那么无产阶级政权就必定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社会主义伦理秩序的至高准则。新中国成立后的道德现代化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道德实践,既要祛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的遗留糟粕,还要配合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建造新的道德体系和新的精神文明秩序。
当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自律精神时,共产主义道德就是人民群众克服艰难困苦的制胜力量。在共产主义道德理念的指引下,民众逐渐由自为谋生转变为自觉地争取解放。为了帮助群众认清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道德缺陷,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宣传人性觉悟、思想解放,“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1060)。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共产党人运用诉苦运动等多种形式配合道德建设,揭露传统社会的剥削事实与没落前景,明确了封建主义宗法道德、资本主义强权道德同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差异。这些道德意识层面的自我反思帮助工农群众丢掉了“宿命论”的惯性思维,使他们逐渐摆脱阶级压迫、解放自我本性,积极争取有权利、有意义、有价值的新生活。共产党人超越唯心史观的认知局限,强调任何阶级都有代表各自价值利益、善恶观念的道德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推进道德意识形态的破旧立新,根据国家政权的建设要求完善道德文化制度,探索由新民主主义道德转向社会主义道德的历史可能性。道德天然具有规范依附性和社群归属性,那么建构道德制度就要首先确认国民的群体特征,在新政治制度、新劳动关系中改造其道德认知,增进其民族归属感与国家认同感。建构道德制度既要尊重国民的个体诉求,也需强调国家的集体属性:一方面,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的文化政策,“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8],明确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以行业准则、组织条例等形式摆脱传统道德窠臼,倡导奉献、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培养团结互助、遵纪守法、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道德制度不以抽象的善恶、荣辱作为价值标准,“我们讲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9],这些涉及具体道德实践的科学意识形态,彰显着感性世界中人们追求自我解放的伦理精神,是对人民群众的自然本性和现世幸福观的尊重,使他们以饱满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投身社会主义国家建设。
中国共产党促进道德文化风貌的气象更新,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移风易俗,培育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道德文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自尊自强的精神写照,蕴含着勇毅拼搏、坚忍不拔、勤劳实干、朴素节俭、不畏艰险、锐意进取、探索创新、实事求是、不谋私利、服务人民的道德品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凝聚民心、顺应民意的优良传统。共产党人重申社会主义纪律规范的权威性,通过强化纪检监察、加强舆论监督来纠正党员的作风问题,杜绝官僚命令思维、骄傲自满情绪、意志薄弱倾向、堕落腐化现象、庸俗涣散习气,谨防贪污浪费、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投机倒把、假公济私、贪图享乐、盗骗国家资财等错误行为,遵循“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推进“三反”“五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道德模范既彰显着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国革命道德,还蕴含着共产主义人道观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诸如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等等。所以,共产党人注重发挥英模典范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将这些先进形象、向善精神作为道德宣传的鲜活素材,教育群众树立科学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以及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共产党加强道德教育事业的机制革新,将爱家、爱公社与爱国、爱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塑造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共同向善的伦理格局。共产党人在社会文化事业中完善道德教育机制,弘扬互助精神、劳动热情、团结意识与勤俭美德。社会公德要求全体国民在普遍交往的公共生活中,遵守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基本规范,这种集体属性的道德准则需要广泛地宣传普及,使国民彻底根除小农观念、本位主义等狭隘思想,养成理性健康的公共生活习惯,构建和谐有序的新型人际关系。职业道德是国民在职业劳动中所应践行的道德规范(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具体规定了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纪律意识、作风态度等内容,切实增强了人们遵循职业准则的义务感。家庭美德是在家庭生活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提倡自主自愿、志同道合的恋爱婚姻原则,注重扶老携幼、讲究敦亲睦邻、严格家教家风,通过培养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实现幸福美满的生活。
国家建设时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道德精神向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历史转型,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发展诉求来构建新的道德规范体系,通过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来塑造新的道德文化风貌。这种转型过程还将近代中华民族蒙难蒙辱的政治阴影转化为人民群众昂扬拼搏的奋进动力,激发了他们自尊自信的主体觉悟和能动意志,使同心同德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和鲜亮底色。社会主义道德超越了封建主义的“舟民论”、资产阶级的人道学说,遵循群众史观将人民伦理奉为至上法则,强调“克勤克俭,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则是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是无产阶级的美德,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兴盛繁荣的重要保证,是革命和建设前途的希望所在”[10]。这种道德精神使人不局限于暂时的生活苦乐、道路曲折或利益得失,避免那些罔顾集体规范、国家利益和群众幸福生活的私利化倾向,以全人类解放的长远眼光和伟大气魄克服了狭隘的自顾心理,不仅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还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擎举集体主义的精神旗帜,携手掀起创优争先的建设热潮。
三、在改革开放中整顿价值空间:意识反思-构筑公共规范体系
改革开放为国家道德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对群众道德生活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新时期道德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主体觉悟和创新精神,衍生出更为强调自我价值的多样态、差异化的伦理意识,超越原有的道德规定。另一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社会关系变动致使道德文化领域呈现复杂的局面,比如市场经济带来的拜金思想肆意滋长、公德理念被扭曲异化、宗法迷信沉渣泛起,等等。这一局势导致某些因过分崇尚物质富足、偏重资本利益而忽视互助精神、奉献意识、集体观念、国家权威的非道德现象产生。与此同时,波谲云诡的世界形势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也产生了新的冲击: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通过文化扩张、思想渗透等形式乘隙而入。面对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环境,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疏解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难题,“恢复和发扬发愤图强、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舍己为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的社会风尚”[11](212-213),引领党政军民同心共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使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基层道德治理,缓解社会秩序转型期出现的现代性矛盾,标定国家道德规范、国民道德意识的价值尺度。伴随着国民对精神生活现代化的主体性反思,其道德实践逐渐向多维度、纵深化延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人们逐渐冲破精神滞重、思想教条的桎梏。但国民意识的初步释放并未获得全然清朗的价值观空间,像“潘晓来信”所反映的社会心态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还有那些曲解“思想解放”而挟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错误思潮,也假借拨乱反正的旗号寓政治主张于道德话语中。共产党人明确澄清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意识形态原则,“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11](562)。他们还同损公肥私的丑恶现象、危害集体的坏人坏事作斗争,拒绝道德战线的自由放任、涣散软弱和精神污染,避免道德理想产生动摇、义利观出现本末倒置等问题的产生。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制定行规守则、乡规民约等具体化道德规范,组织“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文明活动,开展“青年文明号”“文明城镇”“道德模范”等系列表彰活动,来纠正歪风陋习、惩治违法乱纪、弘扬传统美德、维护团结秩序、培育文明新风,努力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事业的健康发展局面。
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发展协同推进,在兼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完备的情况下,建构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道德规范体系。就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而言,因为思想文化的转型源自社会结构的变革,所以新道德秩序的形塑过程难免会落后于新经济关系的建构,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要求加强道德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精神面貌,需要两手共抓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在此基础上促进国家善治。就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而言,只有将道德文化与法律制度结合起来进行国家治理,才能维护国家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12],将精神文明范畴的德治同政治文明领域的法治结合起来,使社会利益关系既能接受法律制度的强制性约束,也要遵循道德规范的倡导性引领。就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反作用而言,道德建设为现代化强国战略提供精神支撑与价值动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13],将遵循现实规范与追求崇高价值结合起来,鼓励那些争取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道德观念,增强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公民道德建设是凝聚价值共识、培育和谐秩序的伦理工程,深刻影响着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文明程度。人民群众是道德现代化的实践主体和受益对象,在主动营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氛围的同时,自觉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公民道德建设不仅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汇聚家庭、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投入德育事业;还要坚持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公平相协调、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联结、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相配合等基本原则。与此同时,通过争创先进典型、普及文艺传媒等道德实践,引领人民群众充实精神生活、提升道德境界、塑造美好心灵,养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团结互助、锐意进取的良好道德风貌[14]。这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拓展道德实践的场域,创新道德宣教的方式,以价值共识的凝聚作用和思想难题的疏解功能,将道德规范渗透进日常生活诸领域,培育公民的理性平和、自尊自信的积极心态。
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发挥道德文化的支撑效用,铸就全体国民都能认同的思想道德根基,促进国家公共生活的秩序向善。“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5],健全道德规范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伦理依据。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属性,涵盖着物质资料基础、政治权利结构、精神生活追求等多重要素,特别是在道德秩序方面具有内在规定性: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构互助友爱、平等和睦、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体系。为了建立这种引领全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既要外在地强化道德监督机制和失德惩戒准则,严肃整治灰色文化市场、严格取缔非法牟利产业、严厉查禁淫秽丑恶商品,防止邪念败坏道德风气、腐蚀人心善意;还要净化精神世界、激发道德潜能,加强道德教育事业的价值引领和文化服务职能,挖掘道德自律的规范意义,像诚信建设就要争取使“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成为公民普遍恪守的信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其蕴含的伦理精神,转化为人民群众所能感知、认同和践行的生活规范,通过厘清伦理标准来构筑社会道德防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彰显了政治与伦理相融合的辩证原则,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相互贯通、相辅相成,通过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教育、实践推广等途径融入国民精神生活的全过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中,道德建设旨在解决那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价值矛盾,扭转那些把腐朽当神奇、把庸俗当高尚、把谬误当真理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社会风气,避免公民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格格不入、与现代文明风尚互不协调。“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16],必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和谐的道德文化氛围。
四、在新时代完善德治格局:意识向善-凝聚核心规范(价值)观念
持续推进道德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求:国家伦理意义的丰富、民族的赓续,都要求道德文化继续发挥价值凝聚功能,“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17](158)。与此同时,解决现代性道德矛盾需要合理应对复杂的文化态势,需要调和国民对伦理生活的高质量、宽领域诉求同道德服务供给不充分、道德资源配置不平衡间的矛盾。然而在道德现代化进程中,“意识-规范”的矛盾相对突出:当人们极度向往甚至盲目奔赴非限定空间时,就容易因崇尚自由而无视那些象征着集体规则的道德纲领;反之,人们对公共规范产生单向度的迷恋或绝对化的偏执时,就会机械地创造那些缺乏价值动力和人格基础的纯粹概念图式。解决这种两难困境,既需要内在地培育国民崇尚美德的向善意识,还需要外在地建构社会主义价值规范体系。所以,新时代德治格局注重调适“意识-规范”的契合关系,使个体的私德与集体的公德、应然道德理想与实然道德经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在中国式道德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善其意识”与“善其规范”的深度融合,为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道德根基。
兼顾个人品德与社会公德,使个体私德善其意识与集体公德善其规范相结合,“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18]。道德现代化连接起国家公共精神与国民主体觉悟,道德要素因其所处的领域、所涉及的关系不同而存在公私区别:私德多是个人修养中独善其身的德性操守,依托自我本能而对环境应激做出反馈;公德更多是公共领域中相善其群的价值准则,强调认同、遵从集体规范的自律性与责任感,因而在某些现实生活场景中,私德更偏重能动性意识、公德则偏重公共性规范。私德与公德既有差异性也存在相通性,共同构成塑造理想化人格的德性根基:私德是公德的构成要素与个性展现,集合起来汇聚形成公共伦理秩序;公德给私德发展引领方向、规划空间,以具备普遍规制效力、公共判决功能的道德纲领作为私德评价的衡量标准,因此,提升公德能弥补私德之不足、培育私德可以弥补公德之缺损。只是私德意识因具有主观的实现欲望而存在更显著的自由倾向,那么当人的自由本性面临道德规范的价值限定时,就容易出现“意识-规范”不可兼得的两难情况。
因为无论在公共空间还是私人领域,道德都蕴含着公民履行向善义务的责任感,所以不能使公德脱离人格基础而成为绝对他律性的制度纲领,也不能只将私德视为纯粹自律性的价值觉悟。因此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必须处理好公德与私德的辩证关系,既要强调“养大德方可成大业”,还要重视“养小德才能成大德”。与此同时,公德和私德虽然有大小之辨,但是都能启发国民对诚信、友善等道德要素的主体认知,使国家道德建设既承认多样化道德生活的合理性,也通过普遍认同的伦理精神增进价值凝聚力。新时代道德治理重申“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19](324),既赋予这些道德要素以公共规范的权威,也给予个体意识以自觉向善的空间。公德与私德相结合的实践机制,不仅避免了私德无限地扩展为全社会道德之源而超越公德的现象,也避免了公德均质地凌驾于个体权利之上而忽视私德的问题。
兼顾主观道德信念与客观伦理生活,使应然道德理想与实然道德经验相结合,前者发挥共识意义、导育作用来引领社会风尚,后者观照生活具象、回归现实关怀。崇高的道德理想与朴素的道德事实相依相融,避免了应然价值之魂与实然经验之根的任意缺席,这样既能以道德理想促进道德实践积极追求向善生活,也能以道德实践推动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情感。新时代道德秩序注重调整应然道德理想与实然道德经验之间非对称的偏移关系,强调“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20],要将社会主义道德知识和伦理精神具象化为实践行动,避免产生人民生活诉求与国家道德期待之间的脱节或断裂状态。如此这样,就可以通过激发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振奋道德精神、升华道德境界,来弘扬趋善避恶、扬善弃恶、扶正祛邪的实践风气,不至于因知行分离而产生道德理想的抽象化或伦理经验的庸俗化倾向。当然也必须认识到,理想信念与经验事实并非完全契合,两者间存在可供调适的空间。因此,道德理想与道德实践之间是难以实现对等转化的,如果要实现,还需要价值主体对客观道德情境和道德知识进行创新性的理解。
道德理想因内在蕴含着群体愿望而更具公意属性,既体现了“行有所凭”的道德规律,又包含着“行能至圣”的道德信仰,使道德治理的形式和内容都烙刻上崇高的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通过对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坚守,使国民对科学的道德理想虔诚而执着。道德实践是彰显个体价值意识的行动反馈,通过回归伦理知识来检验道德理想的合现实性,保障道德理想不会脱离实践而演变成纯粹抽象的概念形态。新时代道德治理不能仅仅依靠单向度的理论说教或灌输,而要更加强调“生活实践展现道德愿景、道德理想观照经验事实”的逻辑原则,将那些衍生于经验生活的典型模范、文艺作品复归现实,引导人们既在培育道德风尚中尊崇伦理精神,又在陶冶道德情操中规范伦理生活。这体现了理想与现实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使那些对爱国主义情怀、民族复兴梦想的善性追求,最终指向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实践。
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道德与法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融合补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18](145-146)。现代法治文明并不意味着道德被边缘化,诸多法律制度正是由道德规范演变而来,这种道德-法律的转制逻辑也是道德现代化的鲜明特征,道德能够追问法律制度的正义性根源,遵循特定价值标准审视法治过程的合伦理性,在崇德向善意义上支撑着法治实践。因而道德与法律虽然存在着较为严格的责任界限,却表现出相互补益的历史必然逻辑,正所谓“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19](133)。其实遵守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要求,而法律实施自然也彰显伦理精神,这种道德滋养法治、法治彰显德性的国家治理方略,使道德和法律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存在着密切关联的融合空间。
德治蕴含着通达真理规律、遵守秩序法则的内在要求,使人改变对传统刑律的纯粹形式认知,一方面将那些获得普遍认可的道德理念上升为公共约束性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还将法制条款内化为公民自觉遵行的价值准则。当然,还需要以法治手段来解决道德生活中的秩序性矛盾,以刚性约束机制和惩恶整治等兜底性举措,塑造公民对道德准则的敬畏意识,“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19](117),辅以征信机制等规章建设、法律宣传等普法教育来带动全社会向上向善。只是法律制度并不追问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管理经验行为的过程机制存在着局限性、滞后性问题,难以更深层次地涉及某些内在思想领域,因此要发挥道德治理的预防性补位效用来弥补法治的缺憾,从思想根源上消除人们道德失范的潜在动机,使人的心灵秩序能够主动自觉地对照并遵循规则。所以法治建设也承载着惩恶扬善功能,使法律制度及其施治过程都能彰显人文关怀、弘扬美德义行,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合理融入良法善治格局,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更具道义基础的和谐环境。
五、余论
中国式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方案,“既奠立于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也厚植于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从而既经得起历史尺度的衡量,也经得起道德尺度的评价”[21],既彰显了党领导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的合伦理性,还内蕴着调适自由意识与公共规范的演进脉络。中国式道德现代化从革命战争时期唤醒国民的意识自觉,使其摆脱对传统规范的政治依附和道德愚忠;到国家建设时期形塑道德制度,遵循集体认同的规范化原则,培育共建共享的善为意识;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整顿道德空间,构筑公共规范体系、维护和谐精神秩序,使价值反思与文化转型互促共进;随着新时代道德治理格局的优化完善,尊重意识、崇尚规范成为国民自信自强的伦理文明新风尚。这种由“唤醒意识-建构规范”转向“尊重意识-崇尚规范”的道德逻辑,始终印刻着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向,将意识与规范的互动关系由紧张状态调适为秩序性契合,避免落入自律至善或普适意义的道德现代化转型困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德性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