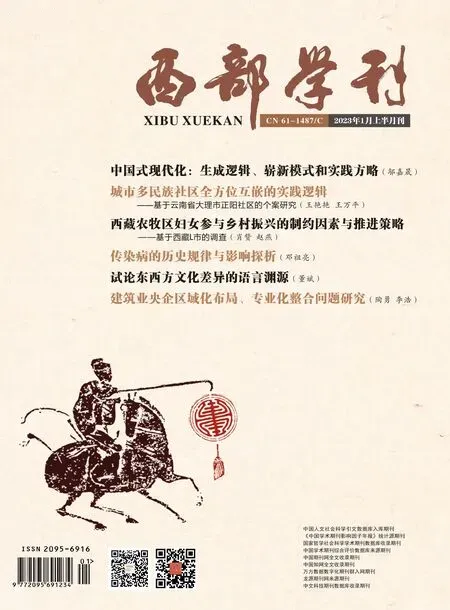哲学阐释学与传统译论的渊源
——兼论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2023-02-10张济韬
张济韬
哲学阐释学的创立为人文学科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阐释学应使人文学科从受自然学科影响的方法论思想中解放出来,回归“理解”。就翻译学而言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译论与哲学阐释学的割裂?本文将从哲学阐释学理论出发,以译者的主体性为引线,阐明其作为桥梁的双重意义。它不仅是连接主体间的桥梁,也是阐释活动中连接“理解—解释—应用”结构的桥梁,因为哲学阐释学与传统译论本就互补。
一、文学翻译作为阐释艺术的不可穷尽性
“翻译不啻于一种西西弗斯的苦役”[1],即便这句话所含的隐喻表面上简洁至此,但是对于不同的受众群体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对于不从事翻译或翻译研究的人来说,这句话可能听起来莫名其妙。首先,“西西弗斯的苦役”这一源于希腊神话典故的用语对试图理解他的人提出了前提要求。在希腊神话中,一个国王因为触怒众神被惩罚日夜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但是每当他就快要完成时,巨石则在神的意志下滚落回去。因此他必须长此往复这项苦役,成为了周而往复的荒谬人生的象征。那么“苦役”是否在表达翻译工作者在工作当中的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工作之烦劳?
对于一般性的翻译工作,译者往往只需找到他者文化和自我文化中相应的指称关系,保证基本的行文流畅,然而文学文本并非如此。作为艺术性的产物,它所代表的是人类思维活动中最具有“能产性”(Produktivität)的一部分。文学本身就是不可衡量的多种要素的结合,诗性的本质特征包括了艺术作品的无尽挖掘性。而在功能翻译理论下,译文必须符合一定的预定目的。那么文学文本翻译的目的何在?是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使之能够便于理解,抑或是保留并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还是在于使作品本身通过内容与表现形式相结合而自成一体的美学价值得到展现?译者面对或复杂或抽象的文学表达不断尝试得出译本,却发现寓于表现形式中的诗性早已破坏殆尽。译者的妥协反而是普遍现象,翻译扎根于译者主体无尽的取舍之中。正是翻译的这种“无限靠近却永远无法抵达的”特质,使其蕴含了无穷的研究价值。“翻译是西西弗斯的苦役”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苦”,而在于表达译者在阅读文本时、在理解的无尽往复循环和不断的斟词酌句中,越来越接近“完本”却最终只能停留在“善本”的遗憾。
从古典时期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再到越来越细分的翻译现象,传统的译学研究对于翻译实践在认知层面上有着巨大贡献。其就作为方法论而言,指导了译者在翻译实践时进行规划和策略的制订。然而进行文学翻译分析时,问题的复杂性单靠个别或数个理论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且缺乏一种统领性的理论支撑。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创作,却被作为一种技术范畴看待,亟需一种人文的视角拓宽其视域。由此,哲学阐释学就应运而生。
二、阐释者的主体性与哲学阐释学之渊源
阐释学问题自古典时期便已有之。柏拉图在《伊安篇》中如此论述:“吟游诗人伊安在对荷马的诗作进行传唱时对于度的把握,正是伊安的传诵和荷马的诗作之间应存的对应关系。吟游诗人的目标应在于令人信服地如此营造他的吟唱,以至听众们能够被感染,以期引发它在内化和吟唱原诗时所感受到的同样的效果。”[2]由此可见,阐释学思想与文学翻译的本质不谋而合。吟游诗人伊安在荷马的诗作与再创作之间徘徊,在作品与听众之间搭起桥梁。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翻译即阐释,译者与吟游诗人的角色别无二致。
尽管阐释学渊源悠久,但无论是古典阐释学,还是施莱尔·马赫创立的一般阐释学都未能达到一种普遍的高度。他认为之前的阐释技艺学是局限于神学文本或古典文献的语文学解读,仅仅是“数门专科阐释学”[3]75。施莱尔·马赫的一般阐释学不无启发性,但他认为“当艺术作品本身进入流通,它就失去了天然性和原始性。也就是说每个作品的一部分可理解性源于它最原始的特定语境”[3]78。可见其对艺术作品的所谓最原始、最本真的意义的推崇。然而艺术作品的意义同样在于作品和每个受众的交流对话,它在每个独特的、个体的理解中都会产生不同的意义。正所谓我们在艺术作品当中看到我们自身,主体性的特殊地位在施莱尔·马赫的理论中被掩盖了。哲学阐释学得以发展离不开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们经过长时间的论述将“理解”奠基为存在哲学的本体论核心。海德格尔将“理解”视作是与“生存情态”同宗同源的存在结构,它们共同构成了“此在”(即人)的存在基础。“每个人都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着名为理解的活动,却不必要清晰地意识到其本身的存在。”[4]理解活动的涵盖范围从最简单的手部捉取动作延伸到深入加工极其复杂的理论联系。因而“此在”才可以学会打开窗户、用锤子钉钉子乃至读懂哲学家晦涩的著作。可见,理解远远超出了我们简单所说的人的能力的范畴,而是作为一种相当普遍和一般的存在一直伴随着人的生命、思考以及行为。
如果说在海德格尔那里主体性只是稍得凸显,那么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则在“前理解”这一基本思路之上阐明了人文学科中历史意识研究的必要性。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在开头部分花了极大笔墨进行了词源学考究,论证了艺术创作的历史性。通过对一系列概念如康德哲学中的鉴赏力、判断力以及美学素质的培育、经历、象征和比喻等进行批判性分析,得出个体的理解视域深刻地融入在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等周边因素当中。在此基础之上,伽达默尔为启蒙时期被贬义化的“偏见”一词(Vorurteil)平反,认为其从德语构词法也可以解读为“前判断”。它的指称本质上是“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来自他人的权威性成见”。这符合启蒙时期反对宗教权威的总基调,即“正确、毫无偏见且理性的阐释文本”[5]272。这意味着理性拥有了阐释的最终决断权。然而纯粹理性终究是一种理想状态,人的情智与理智同宗同源。所谓“正确”必然是一定时期和范围内社会共识的体现,人总是在这样的“前理解”中得以理解。“偏见”所代表的真意和“前理解”其实相差无几,正是理解活动中最积极和能产的要素。启蒙时期将理性和“偏见”对立起来,实则二者无法离开对方。
个体的理解是历史性的,那么整个社群乃至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其中各种人文要素相互关联。如果“理解的历史性”聚焦于个体层面,那么伽达默尔提出的与其近似的“效果历史”原则则是宏观的。不同于以往客观主义对于某一特定历史对象进行研究,“效果历史”注重的是它在整个历史中的影响,影响“现在”的决定性因素正是“过去”。它指明人文学科中的一切文化现象是相互关联的,人文社科类研究在相互身上都能找到自己的倒影。因而翻译总是有其“效果历史”的根源,人文学科体现为整体观与历史观的结合。
那么以“前理解”出发看待翻译问题,就不难理解译者的主体性何以成为整个翻译问题的关键因素。译者是戴着镣铐的舞者,以伽达默尔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游戏空间”[5]124(Spielraum)来对着这句话进行解读:翻译是“阐释游戏”,这种游戏的本质就在于阐释是在穿梭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由规则性和定性因素所划量出来的“游戏空间”。首先,文本本身释放出一个理解空间,这个空间是隐性的内容和显性的语言文字的共存体,这个空间作为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体表现为译者的活动范围。其次,译者本身的理解视域由其效果历史意识所决定,它自身所拥有的理解空间由其个人经历、能力以及翻译的任务性等因素所决定,但这只能说明译者的“镣铐”从何而来,却未能阐明译者如何“起舞”。
如果理解只是单纯地对过去的重复、模仿,那么创新性又从何而来?如果翻译的原则仅仅局限于对原作的忠实,往往生产出拙劣的译作。译者主体性能动性的一面伽达默尔用“能产性”进行了替代。如果将能动性单纯地意会为直觉性的创新,则难免会与“理解的历史性”的本体地位冲突,以致于回到先验哲学的范畴中,背离哲学阐释学的主脉。“能产性”则不与“理解的历史性”相悖。历史意识一方面由“效果历史”所决定,但同时也可以审视其阐释语境,从而构成了所产生的历史效果。为了进一步阐发这方面的思考,伽达默尔引入了“视域”这一概念。“视域约束于思维的有限性,体现了视野拓展的发展规律。”[5]307在理解过程中,基于“前理解”而生成“不同的理解”是理解的规律性体现,哲学阐释学因此超越了“比作者更好地理解”。它不再单单是指向阐释主体的“过往”,而代表了一种源于过去、指向未来的循环。
“视域融合”为理解的创造性因素提供了一种解释。创作过程是艺术性的,是灵感和积淀的共通作用。以哲学阐释学的视角来看,灵感的迸发与作者的认知积累密切相关。创造性的成果往往建立在深厚的积累上,而非单纯创造性的尝试。认知的扩展不是对过往知识的单纯叠加,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主动性创造。在阐释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会有新的东西得到阐发。翻译是译者在原文文本基础上的“视域融合”过程。尽管译者的目的似乎是到达所谓的文本视域,但是他无法到达,而是有所阐发。译者在诸多视域融合中的选择性创作,便是带着“镣铐的起舞”,也是其“创造性的叛逆”。
哲学阐释学要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创作者的主体性身上,分析其在独特的“前理解”上做出的判断,但如果将错综复杂和包罗万象的语言现象单纯地归于“理解”的一般性,则欠缺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做出的判断仍然需要具体的描述。
三、走向互补——哲学阐释学与传统译论的渊源
事实上伽达默尔针对具体的阐释情景同样有着深入的探讨。他将前人的“理解(Verstehen)—解释(Auslegung)—应用(Anwendung)”的模版视为“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以避免“理解”脱离其本体位置。“应用”同“理解”和“解释”一样是属于阐释过程的组成部分。“应用”是与“理解”和“解释”所绑定的某种特定阐释情景,因此也是一种一般性的存在。伽达默尔列举了神学阐释与法学阐释的两个例子。一场布道首先要对《圣经》的内涵进行理解并阐发,以在这一具体的情景实现“应用”,即通过某种表现形式达到针对听众的传教效果。在审判时对于法律条例进行的解读同样也是针对各式各样的个例,兼顾先前的案例和适度原则才得以进行的。翻译(暂且不论机械翻译)则是以译者为重要媒介,从一个社会群体所共同的语言实体转换到另一群体的语言实体的阐释情景。
艺术的表现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表现为越来越多样化,但语言仍是翻译这一特定阐释活动的媒介。与语言学关系紧密的传统译论尽管具有局限性,比如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这使得作者和原著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崇拜对象,译者和读者都成为不敢越雷池的被动接受者[6]。但是其作为翻译中无穷尽的语言现象所进行的分类努力,不仅提供了“前理解”,而其本身就属于整个阐释过程的一部分。无论是“目的论”“等值论”“文本类型学”乃至归化和异化等范畴对于翻译研究是永远不能够缺席的。对于翻译问题,哲学阐释学和传统译学各代表了其一半的答案。尽管伽达默尔声称需要将人文学科从方法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5]23,但阐释学追求的“真理”与其应用的“方法”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译者的主体性不仅是主体间性的桥梁,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它也是连接“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桥梁。每个阐释主体历史性的理解决定了它独特的主体性判断,也因此会产生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产生不同的翻译方法。
在具体层面,要了解译者在变化万千的思绪中如何做出的主体性决策,则需要了解译者、贴近译者、聆听他的故事。或从他的个人生平出发、通过收集史料置身于他的年代,乃至与他进行亲自对话。因为译者的效果历史意识贯穿着整个创作,其任务便是要通过阐释反省将效果历史对于现在的影响彰显出来[7]。但若驻足于此,又会陷入类似于施莱尔·马赫所推崇的“心理学方法”的渊薮,且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也难以尽述。一切理解总是与特定的阐释的情景相伴,传统译论以认知的形式把“翻译”这一特定的阐释情境中的各种现象与方法尽可能地加以限定。因此,译者主体性分析归根结底就是要分析其心路历程,分析其在怎样的效果历史的意识下做出了怎样的翻译决定,同时在既成的翻译决定和现象中验证译者的效果历史意识。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分析不应束缚于任何一种固定的理论视角,否则只能得到部分的答案,多学科、多理论融会贯通是人文学科研究理应遵循的思路。
以此出发看待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注重两点:一是要建立译语文化汉学者和译者进行沟通,二是要不断加强本土译者的跨文化能力。正如先前所言,完全陌生的东西对于理解来说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对于德国受众来说无疑是一种陌生的异域文化,本土译者外译的作品取得的反响程度绝大多数比不上外国译者的译作。德国的汉学者和译者能够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不仅在于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对深入地了解,更在于能够将异域文化的可接受性变强,找到异域语言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共通点。这是母语者与生俱来的优势。而作为中国的译者,则更应该拓宽自己的视野,以自身为起点,但也不失与母语者的比较,找到恰当的切入点,尊重差异,取得“共鸣”,以量取胜更要以质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