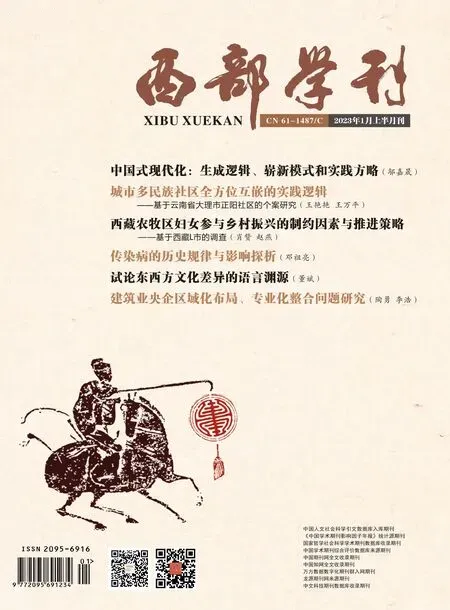赤子之心与孩童之心
——老子与李贽二心之解析
2023-02-10张洁
张 洁
在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提到“赤子”或“婴儿”的地方共有五处:“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怕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老子在书中多次提及赤子或婴儿是希望人们能够返璞归真,时刻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婴儿的天真无邪、淳朴自然不免让人联想到自然成长的孩童,“孩童之心”是真心、是本心,是人的心灵最自然地发散流溢出的状态。不论是“夫童心者,真心也”,还是“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都体现出“孩童之心”在李贽理想人格和价值准则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拥有“孩童之心”,就是保持未被污染的本真之心。本文将阐释“赤子之心”与“孩童之心”的思想内涵,并力图从二心的复归与深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比较,以求得出二心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
一、何谓“赤子之心”?
“赤子”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康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孔颖达疏:“子生赤色,故言赤子。”天生赤色,故曰赤子,可见“赤子”即为刚出生的婴儿。与婴儿语义相近的还有“孩”“孺子”,等等。春秋时期战火不熄,动荡不止,诸侯兼并,民众流离失所。混乱的社会环境、尖锐的社会矛盾,给民众带来数不清的灾难。在这个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时期,奴隶主贵族式微,封建因素蓬勃发展,老子提出“赤子之心”,希望人们回归到朴素自然的状态中,意图缓解人们之间的争夺与杀戮。
为何“赤子之心”被老子所提倡,其背后根本原因是老子认为“赤子之心”之中有着一种“大德”,天地大德曰之生,“德”正是从“道”中所来,是形而上本体永恒之“道”在人世间的切实体现。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拥有深厚道德之人,就好比初生的婴孩,毒虫、雄鸟、猛兽都不会主动去伤害他,整日大声啼哭,但嗓子不会沙哑,这都是因为他精神状态饱满、和气淳厚的缘故,这也是“含德”的缘故。同样讲“德”的还有“常德不离”。如果“道”作为老子哲学体系的根本原则,那么“德”就是无形无体、恍忽幽深的“道”内化于万物的显现。初生的“赤子”或“婴儿”体现了“含德之厚”这种理想的完满状态。因为其保持着这种完满状态,所以“赤子”无知无欲,如王弼注:“无争欲之心,故终日出声而不嘎也。”正因为自身圆满无所欲求,无所求之即无所夺之,无所夺则不犯万物,所以蛇虫鼠蚁、飞禽走兽都不会“损其全”,“益生曰详,心使气曰强”要求人不能有纵欲贪生、心使气强的做法,事物过于壮盛了就一定会衰败。从这里可以联系到老子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因此最接近于“道”,最近于道的水的特征就是利万物而“不争”。最善的人选择居住最卑微恶劣的地方,而心胸却保持深不可测的沉静。“心,善渊”的“渊”字,亦有保持沉静之义。心如果不争、不动,不支配气,就不会破坏和顺的状态,否则有心强求“谓之不道”,不合乎道就会灭亡,那么就不能如“赤子之心”一般得道而活。赤子是“含德之厚”的存在,而“赤子之心”也必须谓之有道。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是老子以及道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道”作用于万事万物的一种自然状态。“朴”有质朴、素朴之意,是一种未经干扰的原始状态。“朴散则为器”,与“朴”相背的就是人为的雕琢。王弼注:“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真朴已散,成为万物之器。”“器”与“道”相对应,形而下者谓之器,是真朴这种状态被打破后的产物。“婴儿”与“朴”正是有着这种天然去雕饰的初生状态,一种浑然天成、未加修饰的自然本真。“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贪欲滋长,那我就要用“道”的真朴来镇住它,这样就不会产生贪欲之心了。在“朴”的状态下,人性的欲望不会过分滋长,这样状态下的人性是真的、自然的,始终保持本真的状态,宛如初生的“婴儿”。无法否认的是,婴儿会成长为大人,人性的私欲也会从无到有,那么最为重要的无非要善于保持这种自然的状态。“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鉴,能无疵乎?”精神和形体合一,聚结精气以致柔和温顺,那么人心灵深处明澈如镜、深邃灵妙。“婴儿”能保持其“朴”的状态,在于“抱一”与“专气”。身体与精神合而为一,自然之气聚合,始终保持这种本能状态。老子认为,像“婴儿”或“赤子”这种其心保持质朴、专一的状态才是人应当追求的。
二、孰是“孩童之心”?
李贽所处的晚明时代,封建制度逐步走向衰落,而统治阶级为了加强统治,使得经济、政治、思想上的禁锢加剧。但是随着新经济萌芽的开始,刺激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家,李贽就是其中之一。李贽提出“孩童之心”的思想,希望人们保有自然之童心,童心也就是“孩童之心”,孩童的心是纯真无暇、自然而然的。李贽关于“孩童之心”的主张主要集中在《童心说》中。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也就是“真心”,孩童的心是纯洁、天真无邪的,是一种纯任自然的状态,是心的自然之性。李贽这里的“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道家的“真”,有自然之意,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雕琢。“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真”受于天,是自然的不可更易的,“真”中含有的自然之序,反对任何阻碍精神形体自由之事物。李贽提倡的“真”,在此基础上更强调人发于内心之真情实感的现实表达。与“真”相对的也就是“假”,“真”即“绝假纯真”。“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如果一切以闻见道理为主,那么说的话就变成了刻意为之,而不是内心的真实表达。人一旦以虚假为本,所知所行无不虚假,人人虚假则难以辩真。“真心”与“假心”相对应,表现的是真自我、真性情,一旦“童心”被障,取代“真心”“真言”的就变成了“假心”“假言”。
“本心”是朴素、原始、未受社会世俗气息沾染的纯净孩童之心。李贽认为“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这里提到的“本心”是禅宗术语,禅宗的佛性论以“心”为本体。高僧慧能云:“若识本心,即是解脱。”人要保持“本心”的清净无染,摒除俗世的纷扰、诱惑,坚守本性,这样才能明心见性、成圣成佛。慧能认为任何人都有佛性,“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但世人往往贪恋尘世的纷扰,容易失去本心、迷失心智,所以佛性的保持就在于内心的清净无染。“孩童之心”在父母未生之前是空无的,在降生之后也未曾沾染外物,是纯净无瑕的,所以“童心”具有“本心”的特征。李贽认为“孩童之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之所以失去清净的本体,原因在于“童心”被“障”。“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造成“童心”被障的是“闻见道理”。如果后天得来的感性闻见和理性道理一旦入主人的心灵,“童心”也就壅塞了,说出的话言不由衷,写出的文章并非真情实感。这里的“障”字出自禅宗“理障”这一概念,解释为当下解脱的障碍,它也是禅宗的核心思想。真正的解脱只能通过自心自性的体悟实现,并不是通过语言和闻见这些外在的形式达到,这与李贽“童心说”中关于“童心被障”的看法不谋而合。“童心”是断绝虚假的根源,成为圣贤的根本,而“本心”更是获得佛性的关键。李贽的“孩童之心”是他对佛家“本心”的借鉴与运用,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李贽在《藏书》中写道:“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李贽的“童心”包括人的私心,并且这种私心是人皆有之的,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人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私”是“人之心也”,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私欲是人们在日常生产活动中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的来源和动力,李贽从百姓日用的角度,肯定了私心的合理性:“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且亲身体验百姓的劳苦生活和倾听广大劳动人民肺腑之言。李贽认为“人必有私”,肯定劳苦人民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拥有自己合理的私人利益是天经地义的,同时批判了专制统治者以仁义道德为借口剥削人民的事实。
三、“心”之复归与深化
(一)“赤子之心”与“孩童之心”的复归
老子的“赤子之心”和李贽的“孩童之心”虽然年代相隔久远,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共通之处。李贽受老子思想由来已久,曾作《老子解》。李贽的“孩童之心”思想深受老子“赤子之心”的影响,赤子的“复归于朴”与孩童的“真心”都崇尚一种浑然天成、未加修饰的原始自然状态。“朴”的状态因欲望而打破与“闻见道理”导致的童心被“障”都突显了“二心”的失落;老子的“复归于婴儿”以及李贽对“天下之至文”的追求与呼喊都体现出“二心”回归的必然,而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二心”的复归。
首先,“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的复归意味着二心的失落。老子“赤子之心”的失落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统治者“强为”,干预的越多越刺激人们欲求的疯长,从而导致“赤子之心”的失落,而心的失落又加剧了民众的罪恶、社会的混乱。在个人层面因“闻见道理”入主心灵,“童心”因被其所替代而丧失,“童心”丧失,一切皆假,不是出自“童心”的话,即使再动听,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只有发自“童心”的作品,才能成为“天下之至文”,但因为“假人”“假事”,尤其是“假文”的盛行,又进一步加剧了“孩童之心”的丧失,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其次,“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都是老子和李贽对其理想人格的追求,是通往理想人格所需的内在的道德与性情修养。“复归于婴儿”“圣人皆孩之”因为婴儿是含德之厚、无欲无知、自然圆满的存在,因此得道要“复归于婴儿”,得道成圣即是保持赤子的本性,复归于赤子纯真自然的状态,圣人不为外物所累,顺乎自然,这种状态也正是老子最为推崇、追求的理想状态。“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在李贽看来,圣人们不读书时,童心自然存而不失,纵使多读书,他们也能守护童心,“童心”在此成为评判的标准,圣人也就是童心未失的人。“二心”的复归是达到圣人理想人格的内在途径,是原初理想状态的复位与回归。
最后,“赤子之心”与“孩童之心”都具有存在、失落与回归的运动过程,但二心在复归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别。老子“赤子之心”复归的终点在于消解人的欲望,并使之抽离喧闹的世俗,让掩盖在欲望与世俗下的人性得以显现,从而复归人自然之本性,复归于“赤子”,最后复归于最高之境界——“道”。“孩童之心”在复归的同时考虑了生存的现实性,在圆满的理想状态与残酷的现实之间拉扯,在复归与生存之间找到平衡的出口。因此,老子的“赤子之心”是李贽“孩童之心”复归的方向与终点,而“孩童之心”是“赤子之心”在现实的土壤里得到的发展与延伸。
(二)“孩童之心”对“赤子之心”的深化
随着时间的流逝,婴儿总会长成孩童,“孩童之心”在保留原初“赤子之心”的同时紧扣时代发展。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回归到“小国寡民”的状态,不追求知识和利益,老百姓各得其所,自然而然地生活,这是针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环境,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提出的主张。老子认为是“赤子之心”的丢弃,导致人私心私欲的泛滥,因此希望人民无欲无为,老死不相往来,从而在复杂的现实斗争中远离纷扰、保全自己。
李贽所处的时期市民阶级壮大,他的社会经历使其从市民阶级的角度出发,肯定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李贽的“孩童之心”里不仅有“真心”也有“私心”,与老子的“赤子之心”不同的是他肯定了私心存在于人本性中的正当性,把“赤子之心”的出世拉入到“孩童之心”的入世。李贽的“私心”也体现了对人自身的关注,他在《焚书》里写道:“士为贵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癖;不知为己,惟务为人……”,做人贵在做自己,要肯为自己的“孩童之心”去斗争以此感到自我安适,而不是去一味地迁就他人。这与老子“赤子之心”里强调“不争”的观点也是不同的。李贽对“赤子之心”思想进行了深化,“孩童之心”在保持“赤子之心”本真与质朴的同时,从自身的生存与幸福出发着眼于人本身的发展,顺从自然之本性,在浮华喧嚣中秉持自己内心的纯真与自由。
李贽对“赤子之心”的发展还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他把“赤子之心”的自然本真运用到文学领域,把是否拥有“童心”看作是创作的关键,强调作者的原初自然之心,如追求“自然之为美”的“化工”境界。“致虚极,守静笃”,但老子的“赤子之心”更向往摆脱外在的束缚和纷扰、致虚守静的理想生活。与老子平淡不争的心境不同,李贽在保留其心的情况下对“童心”的维护更为激进。屈原在《九章·惜诵》里“发愤以抒情”,李贽依据其观点,提出了“发愤而作”:“不愤不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呻吟也,虽作,何观乎?”他所说的愤是一种怨愤激昂的情感表达,要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甚至“发狂大叫,流涕痛哭,不能自止”。创作不仅要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更要将这种情感强烈地表现出来。李贽在文学上这种情感的强烈喷发和具有时代性的观点是对老子“赤子之心”的内在发展与深化。
四、结语
“赤子之心”和“孩童之心”是老子、李贽在各自时代背景下提出的理论观点,虽相距甚远但仍有异曲同工之妙,归结为二心的复归与深化。赤子终会长成孩童,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二心都是在人生漫长历程中摆脱生存困境、迈向理想人格、呼唤理想家园的重要途径。老子的“赤子之心”向往与原初世界合二为一,是其理想之追求,李贽的“赤子之心”珍视人间之烟火,是其现实之央浼。李贽的“孩童之心”是老子“赤子之心”自然而然的发散与流变,“赤子之心”与之同时也是“孩童之心”的指向与归宿,二者相互交织,互为表里,以成就天地之大心,道德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