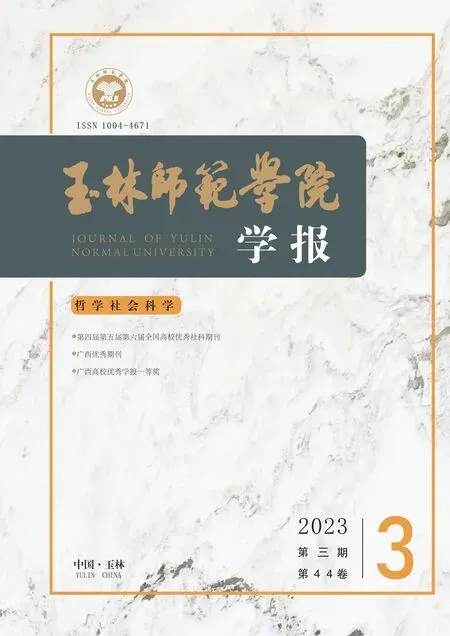从律令制之引进看日本民族的学习意识
2023-02-09陈志雄
陈志雄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01)
8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正处在唐朝的鼎盛时期,是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与西面的阿拉伯帝国一并成为世界之两极。当时的唐朝无论是在经济实力方面,还是在典章制度、文化教育方面,其发展水平都远超东亚各国,可谓闻名遐迩、举世瞩目。与此同时,由于国家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开放包容,使得周边国家得以近距离与唐朝接触,乃至深度与之展开交往、融合。此时,众多国家的使节、客商、学者、僧侣、医生、工匠纷至沓来,云集长安,都希望能从唐朝取回治国、富国、强国的真经宝典。而当他们踏上这片热土时,看到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合理完备的制度设计、繁荣灿烂的文化形态,亦无不为之惊叹、为之赞美。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对周边国家绽放出夺目的光芒,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与唐朝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通过派遣使者深入学习唐朝的先进文明成果,是日本奈良朝与平安朝前期的外交政策之核心。其中,唐代律令制传入日本以后,经过不断整合,实现了在日本的本土化,这是一场适应自身特点、有自主意识的改新。《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有记载,由中国归来的留学生惠日上奏天皇曰:“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此后的两三百年,日本一直致力于对这句话做出自己的探索与表达。日本在引进、吸收、借鉴唐朝律令制的过程中,充分意识到国家的政治统治形态不仅具有时代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后者构成日本学习唐朝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因而采取循序渐进的学习借鉴模式。而直到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才对中国的律令制度加以全面接受,进而对国内的贵族官僚制、田制等加以改革,使得日本逐渐确立起完备的封建国家体制,对此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律令制引进的国内背景
日本在大化改新前,世袭的氏姓贵族占据统治地位,包括奴隶、隶农、农奴这些被奴役的劳动者(即部民),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中央及地方豪族各自拥有自己的私地和私民,并加以肆意驱使、压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在公元626 年,从春季到秋季,阴雨连绵,农业出现了大歉收,民有倒悬之忧,老弱转乎沟壑,出现了路有饿殍、人相食的恶劣现象。公元644年,本来就不稳定的社会又遭遇了谣言蛊惑——说只要在东国的富士川沿河一带祭祀一种“常世虫”,就可以致富长寿。于是民众竞相捐钱祭虫,酗酒歌舞,引发了大骚动。
显然,这种部民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皇室与中央豪族、中央各大豪族之间、中央与地方豪族之间、各地方豪族之间,不断相互倾轧争战,国无安宁之日,也就无法一致去应对外来的危机。日本国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
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为挽救时局,以儒家“尊君”思想为旗帜,于645年发动宫廷政变,打倒了独断专权的大豪族苏我氏,顺利发起大化改新运动。大化改新后的新政权,采取收回私地私民以为公地公民的办法,将土地由朝廷以国家的名义授给农民耕作,农民则承担相应的赋役义务。而原来的氏姓豪族变为由朝廷所任命的各级官僚。如此,在政治体制上,国家由原来的氏姓贵族世袭统治,变为以天皇制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开启了日本文明的新时代。在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以唐律为蓝本,建立日本自己的律令制度,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借鉴和建立律令的过程,既是选择方向、推动变革的过程,又起到用法制巩固改革成果的作用。
此外,日本在母系社会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天皇的母亲——“国母”的亲戚掌握政治实权的“摄关政治”。为了争得天皇“监护人”一职,氏族内部、家庭内部反复上演着激烈的斗争。为了维持天皇监护人的地位,必须让女儿进宫(身为后妃)生下皇子,保持着天皇外戚的身份。随着官职世袭化,阶层身份固定化的推进,决定人生的更多是家世,而不是个人的能力与奋斗。据统计,“《源氏物语》中有一百二十几处使用了‘宿世’这一词汇来表示前世的报应及果报。在当时的故事、汉语日记中也屡屡可见‘宿因’‘宿缘’等说法”①苅部直、片冈龙编,郭连友、李斌瑛等译:《日本思想史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这种宿业观决定了中层以下贵族的身份意识,为他们一辈子的不得志提供了依据。
二、律令制的引进
从5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国力日益强大,在东亚的影响力空前,随之导致的是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衰退,丧失了其存在感。公元562年,日本原来在朝鲜半岛所占领的任那被新罗吞并,这让视任那为禁脔的日本国内上下倍感危机四伏。之后日本的历代统治者都力图恢复,但却迟迟未能实现,其所一贯奉行的“大陆政策”有破灭之可能。在这种由中国及其周边国家所带来的压力下,日本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必须要改革,以寻求新出路。于是以壮士断腕之悲情,积极向中国唐朝学习。可以看到,日本一方面是低姿态地来向唐朝求教学习,但另一方面它是从未放弃与唐朝争夺朝鲜半岛的战略,并把唐朝作为赶超的对象。唐朝是师是敌,这其中的百般滋味,可能日本自己也永远理不清、道不明。是永远的危机感与积极突围的心态,让日本树立起了强烈的学习意识,以求保持自身。
在与唐朝的交往过程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当属遣唐使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唐代文化闻名遐迩,吸引着周边国家派遣使团前来学习,尤其是日本国。公元7世纪初至9 世纪末,日本派遣大规模使团赴唐学习,汲取唐代先进文化,并将中华文明带回日本,不仅使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天文历算以至衣食住行、风俗娱乐等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这场持续了两百余年的文化往来,对推动中日文化的交流互鉴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②丁雨琪:《论日本遣唐使团在唐代文明传播中的作用》,《唐都学刊》2022年第6期,第38页。。遣唐使团人员不仅为唐律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舆论、思想的准备,而且他们其中的一些人也亲自参加了日本律令的制定工作,积极向天皇朝廷上奏,提出中肯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唐律在日本的生根发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吉备真备,在唐专心学业17年,建筑、历法和刑律方面都大有建树,是努力吸收唐朝文化、促进日本自身发展的一代遣唐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曾任东宫学士,为皇太子(后来的孝谦天皇)讲授《礼记》和《汉书》,后官至右大臣,对日本朝廷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据统计,“日本派遣遣唐使,从舒明天皇二年(630)八月派遣犬上三田耜开始,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九月停派止,前后共19次(其中3次未能成行或中途而返,3次为迎送唐使),历时264年”①刘俊文、池田温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法制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其中,从文武天皇到孝谦天皇的将近60年间,正值大唐盛世,唐朝政治制度臻于完备,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日本共有4次派遣,这是最精审的一个学习阶段。日本开始深入去探索唐制之精神,而不满足于形式主义的模仿。及至光仁天皇到仁明天皇的约80年间,共向唐朝派遣了3次。但是此时的唐朝饱受安史之乱的颠沛之苦,内部政局动荡,体制紊乱,社会凋敝。因此,遣唐使每次缩短了在唐时间,任务转为在唐广泛游学,请教疑难问题,出现了一批“请益生”和“请益僧”,以期真正消化之前所学到的知识。可见,日本其学习之心如饥似渴,但并非是不顾自身与他方的实际状况,而表现出饥不择食,泛泛而学的姿态。
尽管日本引进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但当政贵族会根据当时日本的时间、地点、契机制定了“格”“式”,使得律令制度脱胎换骨,此外还制定了符合本国社会状况的法制、政治体系。日本当政者广泛引进律令制等唐朝的各项制度,并效法唐朝整顿法制,构建社会制度,但其中有一项制度始终没有被引进,那就是关于选官用官的科举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氏族势力太过强盛,造成负责律令政治的官僚基本上都采取世袭制,由各个氏族来分担政务,所以来自大洋西岸的科举制根本就没有可供生存的土壤。
杨鸿烈指出:“日本法律虽完全以中国法律为根据,但日本原来‘法律’一字之意义盖与中国毫无关系,日本文字中‘诺里’(ノリ)即指法律而言,其第一意义为‘大声宣告’,继则为‘宣告者即为现在有统治权之人’。”②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3页。在日本,最高统治权在天皇(或幕府将军)。如此,自本自根从日本语境中产生的“法律”之概念就是指“天皇之命令”,天皇就是“法律”之意义的全部所在。中国显然不可与此同日而语了。因此,从对日本之“法律”一词的语义分析来看,可以洞察出《唐律》传入日本之后,所可能发生的转变及其效应,它必然会与天皇制紧密相关联。
再者,从大化改新开始,日本极大地接受了中国文明的影响,但仅就法律与制度这一层面来看,日本所重视吸收的有:中央与地方的组织架构、颁田制度、租税征收制度以及军队编制等等,唯独不在此列的是关于最高法典的修纂问题。我们知道,最高法典关乎一个国家国体与政体的安排,是对国家政治之最根本的问题作出规定的大法。显然,日本大力引进律令制,但对国家法典问题却丝毫不加问津,其一切事务的中心目的都在于:巩固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维护天皇的绝对权威与统治地位。也就是说,其顶层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理念的追求始终固若磐石,使得日本的国家体例有一个坚固的枢轴,举国上下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对于诸如颁田制、租税制这类次一级的体制,则给出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广开思路,不断改新进步。这种改新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作为中心的天皇制。
总体上,日本是将唐制之复杂变为简单。李唐地大物博,礼乐文明雍雍熙熙,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盛;然日本以岛国之故,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国力税收根本就无法承担起如此隆盛的礼乐制度之运作,所以在这方面模仿唐制时,日本就大胆地去删繁就简,以求自适。这种高度理性下的“节用”与“敬事”之原则在当代日本民众的生活习惯中依然可见,如出门在外产生的果皮垃圾会自己打包起来带回家,扔到自家的垃圾桶里;如在日常消费中践行着极简的生活理念。这是可以让很多国家感到自惭形秽的。在这方面,推行律令政治的贵族们从上往下以垂范天下,民知敬从,自然能化民成俗。
又如,奈良时代佛教如日中天,寺院兴建等佛教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上开始广泛崇信佛教。出于对佛教生命观和慈悲情怀的考虑,日本的立法者会在刑罚处分上较《唐律》减轻一至两等,并且犯罪连坐的适用范围极其狭小。“日本采用《唐律》,其文句虽相同但多加以斟酌改订,如中国极重之罪为‘十恶’,而日本则省为‘八虐’,且大体上《日本律》较《唐律》之处刑皆为减轻”①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94页。。我们知道,佛教在日本的兴盛是由于上层统治者主动加以倡导而致的,因此这种在刑罚制定上对佛教理念的自觉关照,可以看成是日本统治者一个以身作则的适当表达,透露出国家政治开明的消息。其在立法中,不断斟酌国情而有所取舍之苦心,令人肃然起敬。
三、律令制与神道皇权观念
据《日本书纪》与《古事记》记载:天照大神是统治天国高天原(诸神所居之处)的祖神,也是日本神道教的最高神,他的孙子琼琼杵尊奉命降临苇原中国(日本国),负责治理这个国度,实现了天照大神的一次授权,标志着日本国神系王权的开始,历代天皇作为统治者均是琼琼杵尊的直系子孙,如此也就形成了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的传说。②有学者指出:“天照大神……作为主权神的角色是自然而然、无可争辩的,并且控制天地的‘主权’是可以交接的,或者说是上一代主权神的授意,哪怕是天照大神在与其弟弟速须佐之男命的交战中失败后,这种主导地位依然没有消失。之后在天之岩户神话中,天照大神消失后天地一片昏暗,众神想方设法将其从天石屋中请出的情节,表明天照大神对高天原和苇原中国的重要性。这种主权的授意类似中国古代的君权神授,从伊邪纳岐命开始,过渡到天照大神控制高天原与苇原中国,再到神武天皇作为正式的地上王权持有者,权力的更迭链条环环相扣,完整且连续。”(参见王刚《中日祖先的建构——以黄帝和天照大神为中心》,山东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30页。)
日本历代中央王权(包括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皇权和以将军执权为核心的幕府政权)都把神道目为自身政权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宣扬神是王的祖神,王是现世神,王权是神权的自然延伸。对神权与王权之紧密联系的特别强调,并不断去巩固这种关系,这种意图的发展必然让当政者去傍上了律令——即具备权威性与固定性的律令条文。
如前所述,公元645年,日本朝廷发生了宫廷政变,政变的直接结果是削弱了氏姓贵族奴隶主的保守势力,确立了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中心思想,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这场政变,让当局对稳固政权这一问题充满了强烈意识,于是不断去寻求一个有效的办法,甚至出现中央率领群臣集体向神祇宣誓的现象。为确保皇权统治的稳固,朝廷开始着手律令制度的创建,力图用法律来确立天皇的绝对权威。从天智七年(668)到天智十年(671),由天皇授命,中臣镰足为首,完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令书的编纂,即《近江朝廷令》,此后又有《净御原朝廷令》《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面世,以及相继又编订了格、式和律令的注释本。
统治者在制定律令时,不遗余力地去规定王与神、王权与神权之不可分割的关系,使得王是“神之苗裔”“王权神授”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弥漫开来。包括后来中世纪出现的武士法,其中关于神道的规定,也是完全出于这种思路的考量。并且,律令制还规定祭祀优先于政事,祭政一致。法令明确规定:天皇掌握祭祀权,立神祇官而为人所敬,坚守祭祀传统,维护神社形象,保障神社财产利益等。这样就把祭祀祖神纳入到日常的政务活动中来,使得追溯政权合法性的活动得到了可靠的凭依。
通过这种律令条文形式的规定,使得缥缈悠远的神话传说得到理性力量的确证,可以让它走得更远、影响更广。律令与皇权、神道(这两者都是最原始、最传统意义上的至高至上之主体)在这里首次得以相提并论。将神道与王权的关系纳入到法令内部来加以解释,这无形中就突出了法治思维,强调法的崇高地位,强化了社会民众对法的尊奉,淡化了原始神道中的崇拜信仰,而更加突出了“天皇即是神”的理念,这对后世的社会治理产生了不言而喻的影响。再者,通过律令规定,将国家的基本政治诉求与祭祀交融在一起,甚至可以说祭祀即是国之大事,即是政事。这对天皇制的维持,乃至于一直延续到当代日本,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说,“律令的制定过程既是皇权加强的过程,也是原始信仰向神道转化的过程”③刘岳兵编:《日本的宗教与历史思想》,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也就是说,通过引进学习唐朝律令制,日本大大加快了自身的文明进程,并且为纲纪社会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四、日本的学习意识
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学习意识。朝鲜、越南与我国壤境相接,鸡犬之声相闻,然其对中国文化之精神的吸收毕竟有限。日本与我相隔茫茫大海,在航海技术不发达阶段,彼此交通往来,颇非易事。然而,日本还是克服一切困难,不畏百般周折,汲汲以求,承接中华文化如饥食渴饮。圣德太子深慕中国之灿烂文化,于是有三番五次特派“遣唐使”之举,其一腔炽热之情,不能不让人为之动容。见大唐法制事业突飞猛进,日本则急起直追,中日两国一同铸就了东亚法制史上一道所未曾有的奇观。
日本之学习,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制化学习。吴震在探讨儒学“日本化”时指出,儒学东传,经过一番“日本化”改造而融入日本文化传统当中,被用来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实现“臣民一体”“道德齐一”。同时,在这种“日本化”的背后应当存在着“日本性”的问题,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传统究竟何在的问题。①吴震:《当中国儒学遭遇“日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58页。内藤湖南也曾指出:“从日本人的立场来看,日本文化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萌发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的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②内藤湖南著,刘克申译:《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0页。对“日本性”的追问,是日本在向外学习以发展自身过程中所孜孜以求的一个关切。从律令制的引进及其在日本的发展来看,日本始终都在深思:我能不能通过学习他人来重塑自身,同时又能保持自性。
日本偏居一隅,四面是白茫茫的汪洋,如果不学习只会陷入愚昧之地。故日本有强烈的学习意识,向外学习成为了民族的常态,这是民族不断开拓进步的一个机制。然而,在此过程中,如何能够保持自身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塑造自性,成为需要去不断探讨的问题,这种意识已经满满地灌注在日本民族之忧患观意识中,成为国民一致向前奋斗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