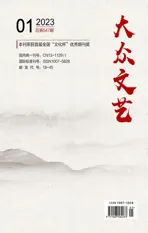传统艺术音乐的非革命性
——以本雅明的技术复制理论为依据
2023-02-08肖子秋
肖子秋
(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91)
革命,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议题,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法忽视的议题。然而,在20世纪初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历史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对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不再抱有希望,甚至对革命本身也转持悲观态度。在马尔库塞于60年代重拾革命信念、重新选定革命主体,并通过学生运动进行实践尝试之前,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本雅明已经提出“将艺术作为革命的武器”的观点,着眼于大众的积极作用,建立起了一套新的革命理论。
《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Das Kunstwerk in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rt,以下简称《作品》)是本雅明的代表作,其中综合了他的艺术革命思想、“奥拉”(aura①)概念、技术理论等重要思想,是阐述其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文本。在此文中本雅明认为,电影艺术是实现其革命理想的最佳艺术形式,他花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电影作为革命手段的合理性、优越性。但他在文中鲜少提到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对音乐概念的使用也不甚明了。从音乐学的视角重新梳理本雅明的艺术革命理论,一方面能对该理论起到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能借本雅明之眼分析、审视音乐活动,为音乐美学提供新视角。本文试图基于本雅明在《作品》中论述的艺术革命思想来进行探究:为何他认为电影比音乐更适合作为革命的艺术?从他的理论视角看待传统艺术音乐,将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传统艺术音乐是否具有革命性?
一、基本理论
本文将参照在本雅明《作品》②中谈到的艺术品存在形式理论来探讨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在第二节中,他对传统艺术(绘画)和机械复制艺术(摄影)的原作和复制品进行了区分,总结下来,一个艺术品可能会关联到的存在形式共有四层:原材料、艺术品、传统复制品、技术复制品。绘画的四层存在形式分别为描绘对象(自然、人或神话文本)、画作、通过雕版印刷等手段复制而得的印刷品、原作的相片或扫描件。而摄影仅有原材料、艺术品两层存在形式,分别为拍摄对象(现实、摄影棚场景)、影片;作为复制时代的作品,以传统复制手法复制影片的现象不属主流,偶见于二次创作,在此不做赘述;机械复制品在这里则是无意义的,它与艺术品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③。
同理可将这四层存在代入音乐艺术,可知音乐具有原材料、艺术品、技术复制品三层存在,分别为:原初内容材料(据创作者的不同理念,可能是情感,也可能是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原初技术形式、音乐作品(音乐作品包含创作者的创作结果和演奏者的表演结果,二者缺一不可,因此这里将演出音响包含在音乐作品中而不作为传统复制品单独列出)、留声机等机器记录或复制的作品录音。

表1
那么从这种划分方式来看,什么因素能够决定一种艺术形式是否革命呢?
二、革命与否的判定因素
(一)从四层存在形式看
一方面,从原作与复制品的关系来看,本雅明认为传统艺术作品(如绘画)的原作具有历史性、独一无二性、即时即地性,即“原真性”[1]④;而其复制品由于无法复制原作的这些特性,只能是影子一般的存在,地位天然劣于原作。拥有原真性的传统艺术原作带有更多的“膜拜价值”,也就是说,在传统艺术原作面前,审美活动仿佛是一种对美的仪式化的崇拜:由于原作相较于复制品具有特殊性,审美者便会将原作“神化”,在审美活动里沉浸于其中、被其征服而放弃自我。而机械复制技术的出现,使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如电影)再无原作与复制品之分,与传统艺术相比带有更多客观的、祛魅的“展示价值”。
另一方面,从艺术品和原材料的关系来看,艺术创作技术的有限性也限制了传统艺术的革命性:由于传统艺术无法完美复刻其原材料,故艺术品只能是一种“象征”。这意味着象征者(艺术品)与被象征者(原材料)之间存在一层神秘的联系,这层联系看似具有随机性,但从作为结果的艺术成品来看却是既定的、必然的。这种象征关系只能靠相信来把握,而不能靠理性把握(人不会因为A的肖像画看着更像B而硬说它是B的肖像画),故宗教性大于理性。机械复制技术一定程度上复刻了原材料(或至少是以充足的相似性证据让观众以为它复刻了原材料),摄影与电影仿佛将日常生活本身搬到了屏幕前,使观众无需用知觉层面的“相信”,而是用感觉层面的“直观”来相对客观地观照作品,艺术品那种“假定性真实”[2]⑤从而消弭。
在本雅明看来,具有原真性、象征性的传统艺术,就是带有“奥拉”(aura)的艺术。他没有对艺术作品的奥拉进行一个官方而严谨的定义,只是提到自然对象的奥拉类似于“远方的物体让你感觉它很近”而散发出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自然界物体或艺术品所拥有的、能对人产生迷惑作用的特质,它看似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经过知性运动才能产生的结果。不过从文中“在复制活动中被排除的东西可纳入奥拉概念之中”一句以及本雅明对复制技术的推崇可知,奥拉本身就带有“非革命”的意味,他对奥拉艺术抱有一种看待英雄迟暮的感情:承认其历史,否定其未来。他认为,所谓的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就是奥拉艺术发展到极端的结果。由此,本雅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判马拉美的诗歌、毕加索的绘画,认为他们对纯粹的、脱离具体内容的表现形式的追求会导致对艺术社会价值的忽略,而这些作品要求人们“凝神观照”、放弃自我,只拥有神学意义上的膜拜价值,是一种脱离大众的艺术。
(二)从观照方式看
本雅明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会影响感知方式,在文化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艺术作品的存在形式亦影响着人们对它的感知方式。因此他判断艺术作品革命与否的标准,除了创作角度的存在形式,还有接受角度的观照方式。传统的、拥有膜拜价值的奥拉艺术作品要求接受者的“静观冥想”,这意味着接受者被艺术作品散发的魅力所吸引,仅能将自己置于下位去全身心地欣赏、体验它,而无法以一个相对客观、平等的视角来审视它,因此这种观照方式是非革命、非解放的。传统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是一种较为纯粹的个体活动,艺术作品体现了艺术家即时即地的所思所想;而接受者的接受活动也同样是个体活动,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接受者虽然可以互相沟通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与看法,但审美过程以及审美判断终究是个体化的。
而机械复制技术将人们的感知方式从静观冥想转变到心神涣散。这种观照方式在布莱希特的叙事剧中已初露端倪,“间离-中断”技术将观众从戏剧的“假定性真实”中惊醒,同时也是从“静观冥想”的状态中惊醒,而作为新时代戏剧的电影则更彻底地完成了这个转变。如果说布莱希特叙事剧还需要依托于传统戏剧形式的象征性才能打破这种象征性、打破观众的膜拜状态,那么电影就是提供了一种比现实更现实的现实。摄影-放映的机械复制流程一方面将现实复刻进影院,而观众并不会膜拜自己日夜所要面对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则通过蒙太奇、升格、特写等将现实分割解剖的手法避免观众沉浸其中、产生共鸣,如围观者一般事不关己地观察事件、产生反应。此外,在影院这样一种集体观赏的环境中,观众们因同样的情节一同欢笑、惊呼,这样一种相互影响的接受状态也完全不同于人们观赏传统艺术时个体化的、与外界隔绝的接收状态。这便是心神涣散——人应对新型艺术形式甚至新型生活形式的新态度、新方式。机械复制时代、文化工业时代来势汹汹,人因此产生的感知方式变化,这些在本雅明看来都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他将这些改变与左翼理想相结合,看作是人从往昔的虚幻魅影中苏醒解放的契机。
三、传统音乐的非革命性
若从批评纯艺术的角度看,传统艺术音乐自然也在本雅明的批评对象之中。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诞生并逐渐成熟的德国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确立了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的概念,理论家们以贝多芬的器乐音乐为榜样,宣扬、赞美这种纯粹的、崇高的、以有限喻无限的音乐,影响了一批德奥浪漫主义音乐家,进而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音乐观甚至审美意识。绝对音乐的光辉一度笼罩世界,时至今日也没有消退。
如果以存在形式、观照方式为标准判断传统艺术音乐的革命价值,结果也是不尽如人意的。
(一)从四层存在形式看
1.技术风格与现场表演决定的原真性
传统艺术音乐与其他传统艺术有一个显著区别,那就是它本身就无须区分原作和传统复制品。没有人会把作曲家手稿或作品首演音响作为所谓的原作,而每一次音乐会上的“复制”都是一次再创作,是对原作的进一步完成。如此一来,传统艺术音乐仿佛与机械复制艺术一样,是没有原真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如果考虑到作曲家个人风格在音乐鉴赏活动中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发现,作曲家特有的创作技法,也就是使他形成个人风格的特殊形式,具有类似于原作的原真性。对这种特殊形式的模仿就是一种复制,而这种复制自然无法拥有原真性;此外,这些特殊形式是为了组织作曲家对内容材料即时即地的表达意图而被创造的,这种历史性也是无法被模仿复制的。
但是这样是否混淆了模仿与复制的概念呢?笔者认为,纯粹的模仿就是技术形式层面的复制。本雅明在原文中并未单独提及这种复制,这是因为他所讨论的文学、绘画、摄影、戏剧、电影等艺术形式往往都有一个明确的、与现实世界直接相关的表达内容,而他所重视的也正是这个内容,所以不会刻意论述脱离现实内容的技术形式。而音乐作为抽象艺术,一方面无法复刻现实世界,一方面更依赖于其技术形式而存在,也正因如此,音乐是较早讨论自律-他律、形式-内容的艺术,甚至可以说,其他艺术门类的抽象化、形式化多多少少都受到了音乐的影响。因此,形式上的模仿-复制对音乐来说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同时,音乐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也相对弱于其他艺术门类,这也是本雅明不愿过多讨论音乐的原因之一。
另外,传统艺术音乐是一种舞台艺术,依赖于即时即地的表演。由于奥拉正“来自即时即地性”[3]⑥,故本雅明认为表演者与接受者处于同一空间的舞台表演也是一种无法摆脱奥拉的艺术形式。他对比了传统舞台戏剧和电影两种表演艺术,认为舞台上的演员即时即地地、一气呵成地散发魅力,而电影演员则不连贯地在机械设备而非观众面前表演,一个几分钟的镜头可能需要演员在数小时内、数个场景、数个镜头中分别完成,于是电影演员成了表演的工具,个人的整体性魅力无处释放,奥拉从而消逝。将这一观点转移到传统艺术音乐上可知,音乐会音乐是具有即时即地性的,虽然它不代表作曲家的在场,但如前所述,表演也是原作的一部分,所以现场听众亦受到表演者奥拉的影响,难以抽离地、客观地寻找音乐作品的展示价值。
2.作为抽象艺术决定的象征性
从原作与原材料的关系即象征性问题看,音乐作为一种极度抽象的艺术,本就无法完全复刻原材料、使其直接呈现于受众面前。即使是所谓的绝对音乐、形式音乐,也不能说没有一种需要以“象征”联系的原材料,毕竟音乐不是凭空产生的,亦不是随机数列。由此可见,音乐可以说是天然带有象征性、天然带有奥拉的艺术形式。从象征-宗教性的角度看,如果说马拉美的象征主义诗歌是文学艺术膜拜价值的极端体现,那么以象征的方法联系作品和原材料的传统艺术音乐,可以说是艺术膜拜价值的极端体现。这么看来,音乐,至少是传统艺术音乐,似乎注定与革命无缘。
(二)从观照方式看
那么,接受者对传统音乐采取的观照方式是静观冥想还是心神涣散呢?从本雅明对电影画面流变性的肯定中,也许有人会联想到音乐的时间一维性:如果说影片因其画面的不固定而使人无法静观冥想,那同样在时间中不停变化的音乐是否也拥有这种能力呢?如前所述,电影使人无法进入审美的静观冥想状态,是因为它不断流变的画面和情节将人置于观察事态发展的围观者立场;而流变的传统艺术音乐并未脱离其象征性,它依旧要求接受者以一种教众的心态去感悟其奥拉。可见,内容的“流变”并非打破静观冥想状态的充分条件。除此之外,音乐厅虽然作为一个集体观照场所,却有其严格的规则:着装得体,不得饮食,演奏期间不得发出异响,乐章之间不得鼓掌……除了演出结束后的掌声或欢呼,音乐厅中的接受者在演出过程中不被允许也不需要互相感知,他者的存在非常多余,甚至只是会影响个体审美活动的杂音,这与本雅明所期望的具有统一“神经网”的、作为“革命的放电器”的、适应“集体身体”[4]⑦审美需要的场所是相悖的。
结论
综上,传统艺术音乐在本雅明眼中是缺乏革命潜力的。阿多诺在阅读《作品》一文后对该文进行了批判,认为本雅明夸大了大众的力量而贬低了奥拉艺术的力量。但实际上,本雅明所厌弃的向来不是某种客观意义上的艺术形式,而是擅自与新技术为敌的艺术工作者。如今,许多艺术音乐活动与技术复制的联系愈发紧密,散发着新的生机。但与此同时,技术复制这一在20世纪上半叶初出茅庐的技术,也在百年来逐渐发展成熟。本雅明曾十分看重的升格、特写、蒙太奇等电影技术也逐渐为艺术活动的参与者们所熟悉,滑入一种新的假定性真实。由此可见,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确是基于时代的理论,但其中的辩证在新的领域、新的时代背景下依旧能散发新的光彩。在新的技术环境下,艺术音乐何以推动人类解放?什么样的音乐具有革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音乐在人类精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思考这些问题的意义也愈发深重。知晓传统艺术音乐何故“非革命”,是为了探究何为革命的音乐,何为解放的音乐。
注释:
①译文有魅影、光晕、灵晕、灵韵、韵味等,为避免误解和歧义,后文均使用音译“奥拉”。
②本文参考的Das Kunstwerk in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rt译文来源为王才勇翻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二稿,2001年由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虽该译本采用“机械复制”这一译法,但近年学界对该翻译有所纠正,故文中均采用“技术复制”这一译法。
③在这里,本雅明把作为艺术品的画作和作为原材料的拍摄对象均视为“原作”,对应到四层存在形式中并不统一。笔者认为,将原材料视为原作是不严谨的,而界定清楚原作和复制品的概念不论对于《作品》一文还是对于本文来说都很重要,故后文将自作主张地将影片,即经艺术加工的原材料,作为摄影这种机械复制艺术的“原作”,而将原文中作为“原作”的拍摄对象划为“原材料”。
④[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85.
⑤[德]本雅明.单向街[M].陶林,译.西苑出版社,2018:177.
⑥[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104.
⑦赵勇.静观冥想与心神涣散——阿多诺-本雅明大众文化之争背后的美学分野[J].江西社会科学,2020(1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