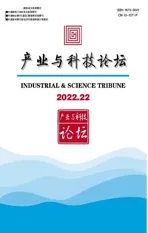后疫情时代全球化的发展及改进方向分析
2023-01-25□徐可
□徐 可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已逾三年,给各国经济发展和全球供应链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人类社会发展遭遇变数。同时,疫情也推动国际社会对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学界、政界对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势、改进措施有许多判断和主张。这些观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克服全球化弊端、挖掘其新动力,助力世界经济走出疫情泥淖,使后疫情时代的人类社会获得更加长足的、可持续的发展。
一、对全球化发展的一些担忧和判断
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国外学界和政界部分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将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根据一些学者对全球化历史的理解,冷战结束到近期是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是全球化“最伟大的时代”,这一阶段的主题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全球供应链建立、中产阶级形成壮大、极端贫困减轻、民主范围扩大,同时极大地增加了数字化通讯和全球流动性,整体上促进了国际社会的团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是类似9·11和大萧条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全球化进入了令人担忧的“2.0时代”:地球开始划分成各自拥有强大军力和独立供应链的大国集团,专制主义兴起,社会阶层分裂并引发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普遍焦虑,国际社会走向分裂[1]。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跨境旅行锐减、国际会议取消、全球停工和本土主义者的反应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全球化两个阶段的界线变得明晰,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时代开始了。
此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已严重破坏数十年来的开放经济贸易体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更加剧了体系的危机。即使经济活动随着疫情好转而重启,世界自由贸易和国际旅行也难以快速恢复:大流行使得旅行和移民政治化,并使各国倾向于自力更生。这种内向性限制了全球经济复苏,增加经济脆弱性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如此一来,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包括疫苗和经济复苏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全球化高峰回落,相应地是逆全球化势头渐趋强劲。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危机,各国普遍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世界正处在“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全球化高峰期”(peak globalization):以世界出口额占GDP比例衡量,全球化于2008年达到顶峰后遭受经济危机重创,之后虽逐渐复苏但一直步履蹒跚[2]。新冠大流行深刻影响了各国对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依赖性的看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内向性和逆全球化趋势。尽管这不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结束,但消除逆全球化带来的反作用力仍将十分困难。
二、疫情揭示全球化发展的严重问题
当前的全球化模式积弊已久,在疫情下充分暴露。有些问题在平时是“优势”,如对高效率的追求,但在重大传染性公共安全问题面前也成了负面因素。具体看,全球化自身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四方面。
(一)传统的全球化主导力量意愿不足。美国基于“美国优先”理念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愿再担当现行全球化的领导者,在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上无所作为,防疫不力及内部混乱和分裂也极大地削弱了其声望。疫情初期,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领导层就应对不利,其国内政治运转的系统性失灵更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过度反应”的风险,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留下了真空[3]。拜登上台后,在“重回多边主义”的旗号之下依旧行单边主义之实。美国不惜将贸易作为“战争”手段,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相等同,该国政客本就希望重建美国制造业,更是借疫情之机声称需要恢复制造能力和基本药物供应链,试图进一步逆转全球贸易。英、法、德、日等许多国家经济行为趋于内向,效仿美国限制重要物资的贸易,散布全球的生产基地有向各国国内转移的趋势。疫情之后,GDP之和占世界59%的国家一度收紧了对外资的规定[4]。
(二)国际矛盾拖累全球合作。此前,美国发动贸易战已严重破坏了全球开放经贸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又加剧了中美矛盾,成为导致联合国在应对疫情上“失灵”的诸多因素之一。此外,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历了美德等国争抢医疗物资,美欧涉华矛盾及经贸摩擦趋于严重,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日韩战时劳工征用问题持续发酵,美欧日等国纷纷拿产业链转移当“经济武器”大做文章等问题,2022年2月以来的乌克兰危机更是给本就脆弱的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严重打击。2022年8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国强烈反对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加剧了台海局势紧张,破坏了全球半导体等产业链的稳定。国际冲突矛盾的不断激化,严重影响了国际抗疫合作和正常生产活动。可见,共同的公共卫生利益未能很好地转化为国际合作的强大动力,一些大国、强国为了追求更广泛的地缘战略利益甚至不惜利用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凸显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
(三)全球治理无政府状态暴露。与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团结起来拯救金融体系免于崩溃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未能及时得到国际社会团结有效的应对,一些国家和泛民族组织暴露了它们官方声明掩盖下的“基本生存本能”。各国曾经为全球化而让渡部分主权,但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自主行为体,当危机降临,国家仍倾向于首先考虑自保。在一些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阴谋论相结合,街头冲突不断,甚至裹挟政府推行极端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政策,国际合作的水平和范围大为降低,对此国际机制也未能及时作出调整和应对。
在此背景下,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力、公信力遭到质疑和破坏,还频受“政治化”指责。美国一度暂停对其资助,并指责其没有及时分享疫情信息、提供防疫政策建议和宣布“全球大流行”等;德、印、日等国则纷纷借机质疑二战后奠定的联合国基本框架应对当下问题的能力,要求全面的特别是针对安理会的改革,其本质是希望提高本国在联合国体系内的地位;G20召开能源部长会议协商原油减产,但对减产措施与规模存在争议,特别是墨西哥与沙特意见相左;美国有意扩大G7架构并邀韩国参加2020年峰会但招致日方反对。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国际组织普遍面临失能问题。
(四)全球化存在系统性问题。尽管新冠大流行凸显出全球化存在的诸多漏洞,但新冠肺炎疫情显然不是全球化危机的根源性问题。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化模式自身所存在的系统性问题,而全球化论者所谓“世界是平的”的叙述掩盖了体系的脆弱性和国家的剥削行为[5]。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全球化局限于经贸领域,将其等同于“国际贸易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错误地认为自由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可以支撑一个“自我维持的国际秩序”,事实证明这种全球化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当前全球化功能的失调正是过分依赖市场力量所导致的,经济民族主义、市场自由主义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医疗物资供不应求,各国围绕医疗资源的竞争甚至不择手段,连欧盟内部都以邻为壑,一度限制口罩出口;而由于供应链过于分散,一国封闭引发环节中断,就有可能使整个产业的生产活动陷入瘫痪,这些本质上都是全球化模式存在系统性问题导致的。
三、疫情催生对全球化的反思与更新
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深刻反思,同时积极探索改良、更新全球化的方式。从长远看,全球化发展仍然危中有机。
(一)共同问题塑造共同记忆,解决问题需要国际合力。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而言,新冠肺炎疫情都是一件大事。疫情暴发三年来,狭隘民族主义与极端民粹主义所酿成的恶果,世人有目共睹,其对国际合作的破坏及对各国民众造成的不必要伤害正是一种自我揭露。而以中国、古巴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医疗援助,树立了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典范,更突出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大众传媒与数字通信的普及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各国人民形成了对于苦难的集体记忆和同理心,这将有助于各国同心协力应对接下来的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培养起某种“全球意识”。事实上,疫情所引发的学界、政界和民间关于全球化的反思,也正是疫情之下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各国有识之士提出的宏观、中观层面的改革倡议及论述,也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
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早已凸显全球合作对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疫情更使各国认识到,在全球性问题中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务必团结协作、共同应对。疫情暴露出全球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但病毒本身并非全球化的产物。一些国家借疫情之机“退群”“断链”“脱钩”,质疑全球化,试图对抗甚至破坏国际合作潮流,终究是行不通的。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全球合作是应对疫情的最好武器,国际社会有望以此为契机,在公共卫生、医学研究、科技发展、金融稳定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
(二)国际分工、区域合作等发展需求仍在全球化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轮全球化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征包括产业链、生产和管理技术的全球再分配,此后世界贸易经历数十年的繁荣,各种产业技术也在全球化框架下实现飞跃,各国逐渐适应了这一潮流下的全球分工,并探求经济制度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的稳步升级。尽管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不断,但全球化无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重要发展机遇,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发展需求,这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较为广泛的共识。未来一段时期内,技术发展、产业链分配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大趋势不会被轻易颠覆,全球化发展仍具有深厚的经济条件、技术需要和民意基础。
此外,区域化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和补充。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局部收缩,世界日益形成北美、欧洲和东亚三个经济和贸易体系,三个体系内部贸易均超过了其与区域外的贸易,区域内产业链的整合度也更强。大量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圈兴起,助推了世界经济的区域化。这是对WTO多边贸易谈判进展不力的回应,也是“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背景下国际经贸发展的一种有效形式。订立四年多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积极发挥作用,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区域一体化带动全球化的改良,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三)应超越经贸领域,面向问题建立“更好的全球化”。全球化理应更关注经济效率和全球市场以外的问题,将重点放在全球公共产品的共同治理上,使其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向。为摆脱全球化危机,需建立一种能有效减轻经济和政治依赖风险并支持全球社会新愿景的新体系。区别于基于市场规则的旧有全球化,新的全球化必须将公共安全和人民福祉放在首位,并辅以必要的矫正手段。
要面向问题建立“更好的全球化”,具体而言,一是需要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来共同解决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并重新评估供应链中的风险,建立一种新的“反托拉斯模式”。二是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建立保护机制,致力于消除国内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不平等。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巩固战略重要性商品(既包括芯片也包含食品等必需品)的区域价值链,变“适时反应”(just-in-time)生产为“以防万一”(just-in-case)模式,优先考虑供应的安全性而不是最优成本效率。三是新全球化模式要求广泛的信息共享,WHO等国际组织必须发挥更大作用并被赋予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多边主义代替单边主义。
四、结语
学术界较为主流的看法是,全球化肇始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按此观点来看,这一进程至今已历经了约六百年。毫无疑问,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全球范围的大规模交流活动,有着十分深远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整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本土主义、保护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各国经济政策内向性增强,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汹。但如同人类社会发展螺旋形上升的形式一样,全球化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同大航海时代相伴生的、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和掠夺,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黑历史”,早已被国际社会摒弃,成为历史的教训,时刻警醒着世人。而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等也都曾给全球化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但应该看到,无论是全球化自身曾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是人类社会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干扰全球化进程的各种因素,最终都没能阻挡这一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事实上,经受过考验的全球化浪潮每一次都更为强劲。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天性当中对于社会交往、互利合作的需求,更在于人类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与共的本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化,但也给人类社会提供了审视和反思的契机。改进和发展全球化,使之适应后疫情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需要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各个主体的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最终也将更好地造福全世界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