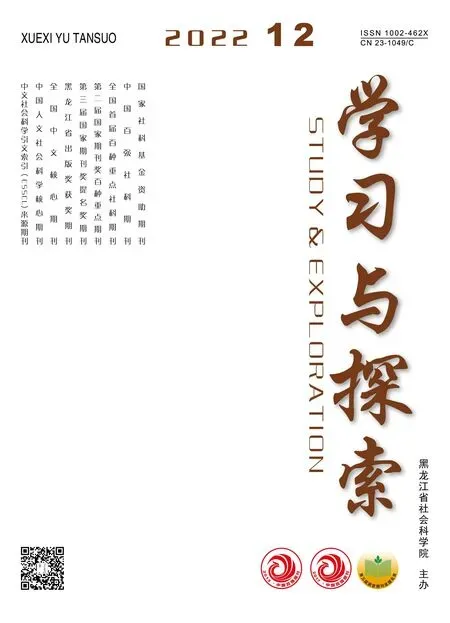权威与说服
——儒家化在汉代立法修辞上的体现
2023-01-24侯迎华
侯 迎 华
(华东政法大学 文伯书院,上海 201620)
一、问题的缘起
“法律儒家化”的说法最早出自于1948年瞿同祖所撰《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他认为:“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1]即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渗入法律、律令,使中国的封建法律兼具伦理法的性质。这一命题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中国法律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此后,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命题,如杨振红的《从出土秦汉律看中国古代的礼、法观念及其法律体现》[2]一文,提出纳礼入律的时间早在秦代就开始了;武树臣的《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 的法文化考察》[3],从法律文化的视角描述了中国古代法律实践活动的宏观状态;律璞的《汉代儒家思想法律化辨正》[4]对汉代儒家思想法律化给出了辩证思考;李勤通的《法律儒家化及其解释力》[5]对法律文本、司法制度、司法实践等解释力的限度做了深入研究;杜军强的《中国古代司法论证中儒家价值的理由类型及适用》[6],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儒家价值参与司法论证的模式进行了总结反思。但这些学者都是从这一命题本身出发讨论儒学对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或法律实践的影响等,没有从修辞的角度分析儒家化对立法语言和立法修辞的影响。
本文拟以汉代的立法诏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儒家化对汉代立法诏书语言的影响,从而进一步揭示儒家化在汉代立法修辞上的体现。之所以将年代限定在汉代,一方面因为儒家化是从汉代开始并逐渐形成的,汉代的诏书语言也是最早体现儒家化的地方。另一方面,汉代又是我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形成和法律制度初步发展的时代,汉律令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律的体系大体在唐律中得到了保存,而远承汉律的唐律,不仅为明清所沿袭,甚至影响了日、朝等国的律令制度。因此,研究汉代的立法修辞,探讨儒家化对该时期立法修辞的影响,或许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的整体修辞特征。
汉代的立法形式主要有律、令、科、比四种,法典主要由律典和令典构成。律典主要沿袭秦律,而且律典属于基本法典,有很强的稳定性,语言受儒家化的影响较小。而令来源于皇帝的诏令,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7]2659,可见令这种立法语言,具有随时可以阐述立法者对法律见解的功能。相比于律,诏令更带有立法者的主观意志与价值取向,其语言也更易受到时代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响。所以本文抛开律、科、比,单独选取汉代的立法诏令作为研究汉代立法修辞的切入点,所选诏书来自清代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诏令名称皆取自本书。笔者梳理了其中汉代的立法诏令,共有92篇。其中赦诏35篇,因即位、改元、祥瑞、灾异等原因,赦免罪行,赏赐百姓。因有赦罪减罪的条文,故将其算入立法诏令。减罪宽刑诏14篇,这是整体宏观上的减缓刑罚,如汉景帝的《减笞诏》、光武帝的《减罪诏》、汉章帝的《东作缓刑诏》,皆此类也。还有减免具体罪行的诏书19篇,如汉文帝的《除诽谤妖言法诏》《议除连坐诏》《除肉刑诏》、汉宣帝的《子匿父母等罪勿坐诏》等。另有有关司法制度的诏书若干,如汉高帝《疑狱诏》、汉景帝《谳狱诏》(2篇)、汉宣帝《置廷平诏》、汉元帝《议律令诏》等。有关法治公平的诏书若干,如汉宣帝《平法诏》、汉成帝《治冤狱诏》、汉章帝《纠举狱吏诏》、汉和帝《择良吏诏》《察苛吏诏》等。
二、儒家化在汉代立法语言上的体现
吴曾祺在《文体刍言》中说:“汉诏……其文词典雅,为历朝之所不及,亦其近古然也。”[8]所以“典雅”是汉代帝王诏令的语体特征,也是儒家化在汉代立法诏令语体风格上的体现。这里的“雅”,一方面是指内容上的“雅”,即援引儒家经义,博引经典,是儒家化在语言内容上的体现;另一方面,是指文体格式、篇章结构、语言艺术风格上也模仿儒家经典,化用古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儒家化在语言风格上的体现。
(一)立法语言直接引经据典
儒家化在汉代立法诏书语言上的体现之一,是在诏令文书中直接援引儒家经传。西汉的“经”指当时通行的今文经,六经中去除了《乐经》,只有“五经”,也即指《诗》《书》《礼》《易》《春秋》。其中《诗》指《诗经》,《书》指《尚书》,《礼》指《仪礼》(时称《士礼》),《易》指《易经》,也即《周易》,《春秋》通常指《公羊春秋》。“传”指《论语》《孝经》一类的准经以及对“五经”做解释说明的书。汉代立法诏书有92篇,其中引用儒家经传的共有22篇,而赦诏占一半,为11篇,其他有关宽刑减刑、律令改革、吏治改革的占另外一半。汉文帝开诏令引经风气之先,在其《除肉刑诏》中引《诗经·大雅·泂酌》之“恺弟君子,民之父母”[9]13,后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7]212,诏令中称引儒家经传的现象就屡见不鲜了。从此,汉代诏令中援引经传成为惯例,清代皮锡瑞对此评价说:“君之诏旨,臣之章奏,无不先引经义。”[10]现梳理如下。
汉文帝立法诏书中仅有一篇征引经书。其在十三年五月发布《除肉刑诏》,引《诗经·大雅·泂酌》之“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意为和蔼而平易近人的君子,为民之父母,应当爱民恤民,废除残酷的肉刑。
汉武帝有两篇《赦诏》征引经书。元朔元年三月的《赦诏》,引《易》的“通其变,使民不倦”和《诗经》逸诗“九变复贯,知言之选”,这是在引经义来支持自己的变政,同时大赦天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已前,皆勿听治”[9]27。元狩元年四月的《遣谒者巡行天下诏》,引《诗经·小雅·正月》“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表现自己爱民恤民,视民如伤,关注民生疾苦,于是大赦天下,“有冤失职,使者以闻”[9]29。
汉宣帝有三则立法诏令引用了经义。元康二年正月的《赦诏》,引用《尚书·康浩》“文王作罚,刑兹无赦”[9]52,作为“如果官吏不称职,那么百姓犯罪情有可原”的理论依据,特赦天下。五凤二年八月的《嫁娶不禁具酒食诏》引《诗经·小雅·伐木》“民之失德,乾糇以愆”[9]56,意思是不要行苛政,要让百姓有嫁娶时摆酒庆贺的仪礼和乐趣。五凤三年三月的《匈奴来降赦诏》中引用《尚书周书吕刑》“虽休勿休,祗事不怠”[9]56,意为虽然匈奴来降,一片祥和,但大家不要懈怠,同时因喜事赦“殊死以下”。
汉元帝建昭五年三月的《赦诏》引用了《论语》“百姓有过,在予一人”[9]69,自责罪己,大赦天下。
汉成帝有四则立法诏令引用了经义。建始元年二月《大赦诏》中引用《尚书·商书》“惟先假王正厥事”[9]73。河平元年四月《日蚀求言大赦诏》引传“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9]74。河平中《议减省律令诏》引《尚书》“惟刑之恤哉”,提出减省律令,尤其是死刑的相关律令,“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9]75。鸿嘉元年二月《治冤狱诏》引《尚书》“即我御事,罔克耆寿,咎在厥躬”[9]76,指出刑罚不中,百姓蒙辜,下诏要求治理冤狱。
汉哀帝建平二年六月《大赦改元诏》引《尚书》“五曰考终命”[9]86,改元大赦。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三月乙未颁布《赦诏》,引《论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指出“酷吏残贼,用刑深刻,狱多冤人”[11]3,所以要省刑罚,赦天下。
汉章帝是引经据典最多的一位皇帝,立法诏书中有六篇引用了经义。建初元年正月丙寅的《东作缓刑诏》,引了《尚书·尧典》的“五教在宽” 和《诗经·大雅》的“恺悌君子”,要求“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11]30,建立清明政治。五年三月甲寅的《纠举狱吏诏》,援引《论语》的“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1]32,令有司纠举冤狱。元和元年七月,引《尚书》的“鞭作官刑”[11]35,作为禁止酷刑的依据。同年十二月的《蠲除禁锢诏》,下诏引《尚书》的“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11]36,作为废除连坐制度的依据。元和二年二月丙子的《东巡大赦诏》引《诗经·小雅》“君子如祉,乱庶遄已”[11]38,君子如果多行好事,祸乱就会很快止息,故大赦天下。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的《择良吏诏》,引《诗经·大雅》“瞻仰昊天,何辜今人?”[11]49悲天悯人,怜民无辜,既有天灾,又有苛吏暴政,故下诏择良吏,同时赏赐天下贫弱。
顺帝四年正月丙寅《大赦诏》引《诗经·小雅》“君子如祉,乱庶遄已”,提出“务崇宽和,敬顺时令,遵典去苛”[11]59,行宽政,赦天下。
质帝本初元年正月丙申《宽罚诏》引《尚书·康诰》“明德慎罚”,行宽政,提出“罪非殊死,且勿案验,以崇在宽”[11]280。
(二)典雅弘奥语体风格的形成
汉代诏令典雅弘奥的语体风格,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时才逐渐形成。刘勰的《文心雕龙·诏策》曰:“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诫渊雅,垂范后代。”[12]179他指出文帝景帝之前,诏令还采用当时的语言,到了武帝时期,诏书有了“弘奥”“渊雅”的风格。班固在《汉书·元帝纪》的传赞中说:“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7]299其称赞元帝的诏令“温雅”,并在《儒林传》中再一次评论西汉诏书“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儒林传》)。《后汉书》载陈忠上疏说:“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13]1537其认为帝王的诏令应当“弘雅”“温丽”。所以,汉代自武帝开始,逐渐形成了典雅弘奥的语体风格。
汉初文景之前,诏令文风契合黄老之学,崇尚真朴、主张简质。如汉高祖刘邦的《疑狱诏》:“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9]3该诏令先指明当前现状,碰到疑难案件,官吏不敢决断,导致有罪的长久不判,无罪的长期关押不敢放;接着就是解决措施,不能判决的案件,就需要层层上报,由上级判决。其风格简易朴实,近乎口语,三言两语,语意明了,显示出开国君主的尚实风格。汉文帝的《议除连坐诏》亦是如此:“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9]11景帝的《减笞诏》《谳狱诏》等均为如此。
到汉武帝时,受时代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影响,儒学化表现在诏令文风上,即为崇雅尚典。典雅的文风不仅表现在引用儒家经典上,还表现在语言表达和形式结构上。如武帝的《遣谒者巡行天下诏》:“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二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9]29其风格从内在结构上,不同于汉初的诏令直述问题然后给出解决之道。武帝行文,先称述上古圣王,然后开列现世出现的若干社会问题,接着引用儒学古典,指称上古时代的解决之道,最后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并以法令形式下发,要求各地方严格执行[14]。可以看出,这篇诏书在行文表达和结构上全方位的模仿《尚书》。《尚书》是尧舜禹以及三代的政事事典,圣王治国的嘉言懿行尽在其中。刘勰曰“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12]30,认为《尚书》是诏令类文体的起源,并对武帝的诏令文书大加赞赏,认为它语言广博深奥,文辞跟《尚书》里的训典相同,意义深刻正确,可以垂范后世。
东汉时期因为受汉大赋文学风格以及社会整体向美之风的影响,典雅之外又增加骈俪,诏令向整齐华美的方向转化。比如《禁酷刑诏》:“《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已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9]35该诏令引经据典,四字一句,句式整齐,音韵和谐,典雅博奥。
三、儒家化对汉代立法修辞的影响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修辞就是说服,“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15]。关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修辞,当今学界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和研究,比如关于判词修辞,赵静认为其修辞蕴涵是说服与劝导[16];与赵静类似,彭中礼认为中国古代判决的“修辞论证方式,目的是要说服当事人、说服听众”,方式是注重语言表达和价值判断[17]。刘兵认为司法修辞的目的有两个,表达观点和说服他人。“以修辞方法调整语言至少有两个目的:其一,传情达意,准确地表达观点和立场;其二,以言行事、以言成事,说服他人或令他人信服,影响他人的行为和判断。”[18]关于立法修辞,武飞认为“立法修辞就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为获得人们对法律内容的认同而采取说服性手段的行为”[19]。不论是立法修辞还是判决修辞,诸位学者都认为“说服”是法律修辞的一个关键词。而且武飞还认为,“立法修辞过程至少包含三个关键要素,即权威、听众和修辞方法”,其中,“立法者权威是立法修辞的起点”[19]。在汉代立法诏书中,君主立法者一方面通过援引儒家经典来表达观点,所引经典成为确凿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立法者为君主帝王,君王本身就是政治权威,其权威身份不证自明。同时,汉代立法思想儒家化后,儒家思想成为道德权威,典雅弘奥的儒家经典成为知识权威,尤其在经学神学化之后,儒家经传里的每一句话都成为天意的表达。由此,君王的政治权威叠加了道德权威与知识权威。儒家化对立法者权威身份的加强,成为立法修辞中的积极因素,其更有利于达成说服的修辞目的。
(一)儒家化的价值判断:道德权威的说服力
自汉武帝表彰六经,尊崇儒学,儒学在汉代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价值观就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儒家价值融入司法,法律儒家化,儒家经典在包括法律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处于绝对真理的神圣地位,儒家的价值判断也成为汉代的道德权威。从修辞角度讲,本身即为政治权威的立法者,如果在道德层面也站在制高点,更有利于他取信臣民、发号施令。征引儒家经传的皇帝诏令也必然更具权威性,更加不容置疑,在说服性上取得了天然优势。
1.儒家思想成为道德权威
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经义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彰显着儒家学派的道德要求与政治主张。它“既体现儒家思想、又贯彻当代统治者思想学说,同时又兼具封建社会的行为准则”[20]。儒家经典被置于绝对真理的神圣地位,儒家思想也成为汉代的道德权威。“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21]。人们“以《洪范》察变、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三百篇当谏书为朝野认可,那么,征引经书无疑就增强了诏书的神圣性、权威性和不可置疑性,从而为之罩上了神秘的灵光”[22]。君王立法诏书与儒家经典的结合是一种双向的加持,诏令引经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有利于儒学的造神运动;反过来,儒学经典化,经学神圣化之后,诏令引经又进一步增加了君王立法的权威性。“根据这种理论,儒家经典的每句话,每个字,特别是《春秋公羊》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圣人表达天意的符号。”[23]以至于“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7]2336。
2.援引经典成为施政的理论依据
汉代帝王在立法诏令中援引经典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为施政提供理论依据。汉代君主也通过诏令引经,将儒学的道德权威成功的转移到自己身上。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4]汉代立法诏书援引的儒家经典,主要集中在五经(今文经)里的《春秋》《尚书》《诗经》《易经》里,还有部分引自《论语》。学者晋文在《论〈春秋〉〈诗〉〈孝经〉〈礼〉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一文中提出儒家各经典特别是《春秋》《诗》《孝经》《礼》的政治地位,在两汉各阶段有着微妙的差别和变化[25]。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社会问题,也对应着不同的政治需求,体现在立法诏书中,就是援引不同的经典来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
汉文帝《除肉刑诏》中征引《诗经》“恺弟君子,民之父母”,因为《诗经》是提倡“温柔敦厚”的,与汉初奉行的与民休息、宽法省刑的政策相合。汉武帝时尊《公羊春秋》,因为在当时《公羊春秋》最适合他的政治需要,“大一统”说为武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依据,“大复仇”理论,则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制造了借口[25]。汉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的《赦诏》,引《易》的“通其变,使民不倦”和《诗经》逸诗“九变复贯,知言之选”,这是在为自己的变政寻找理论支持,继而宣布“赦天下,与民更始”。汉宣帝元康二年正月的《赦诏》,引用《尚书·康浩》“文王作罚,刑兹无赦”作为“如果官吏不称职,那么百姓犯罪情有可原”的理论依据,特赦天下。汉元帝以后,诏令引经由独尊《春秋》转移到以《诗》为尊,因为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已解决,《春秋》就丧失了被独尊的意义。而汉元帝时期的流民问题与奴婢问题激化了阶级矛盾,政治需求转化为如何掩盖矛盾,麻醉人民,培养驯服的工具,“以柔销天下之气节也”[26],因而“温柔敦厚”的《诗》成为新的理论根据[25]。
东汉时期,汉章帝是引经据典最多的一位皇帝。建初元年正月丙寅的《东作缓刑诏》,援引《尚书·尧典》的“五教在宽” 和《诗经·大雅》的“恺悌君子”,要求“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建立清明政治。五年三月甲寅的《纠举狱吏诏》,援引《论语》的“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令有司纠举冤狱。元和元年七月,引《尚书》的“鞭作官刑”作为禁止酷刑的依据。同年十二月的《蠲除禁锢诏》,下诏引《尚书》的“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作为废除连坐制度的依据。光武帝、和帝、顺帝等的引经情况此处不一一列举。正如学者孟祥才所说,两汉皇帝在诏书中征引经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的一切活动寻求理论的支撑,诏书中征引儒家经典,突出表现了政治与学术的互动[22]。
(二)典雅弘奥的语言表达:知识权威的说服力
学者彭中礼论及法律论证中的修辞方法时,认为法律实践中修辞论证的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方式说服当事人,而说服的方式之一就是注重语言表达[17]。两汉君主习儒读经,通晓儒学,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储备。“亦君亦师”的文化形象、诏令中大量引用的儒家经义、典雅弘奥的语体风格,让两汉立法诏令在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之外,还呈现了知识权威的一面,其说服力也因之如苍穹压顶般令人难以抗拒。
1.君师兼资成为知识权威
君主教育三代以来即有之,但君主研习儒术、尊儒崇经,却是汉代的创造。根据学者王健的研究,汉代君主研习儒学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汉高祖刘邦固然以布衣创天下,早年有轻儒之语,文帝亦喜黄老,好道家之学,但也习儒学,其《除肉刑诏》中就引了《诗》,是汉代第一个征引经义的君主。景帝时期是帝王之学的转变阶段,表现出对儒学的好感和器重。汉武帝发起尊崇儒学的努力,开创了儒家政治格局,武、昭、宣时期是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东汉时期, 君主习经传统又有所发展。光武“以习经术而涉大位”,格外降意于儒经研习。光、明、章帝时期开创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和、安、顺帝也都依靠儒臣侍讲之制实施经学教育[27],历代君主自幼读经,能“以经学通朝野上下之志,立时代风尚之纲准,故能成一代之规模”[28]。
汉代君主对儒经不但秉持一种学习、接受的状态,还进一步参与到讲经、研讨中。如明帝中元元年行辟雍明堂之礼时,“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13]2545。明帝还亲自撰写了《五家要说章句》。由于通晓儒学,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汉代君主塑造了“儒学皇帝”的文化形象,具有“君师兼资”、政教合一的皇权职能,立法者于政治权威之外还具备了知识权威的光环,其立法诏令也就更有说服力了。对精英受众而言,儒学成为皇权与儒士阶层之间的文化纽带,让立法者与这类精英受众之间有了共同语言;对普罗受众而言,“亦君亦师”的形象更具有震慑力与说服力,即便听不懂,需要郡守“选择良吏,分部宣布诏令,令民咸知上意”[7]3629,但他们对知识权威的尊崇感,也为立法的说服提供了可能。
2.典雅语体带来的震慑力与说服力
学者吴承学认为,诏令“是‘王言’,为了表现出庄重与尊严,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威性,诏书必然在语言修辞上有特别的要求,必须有独特的文体体制与文体风味”[8]。这个独特的文体风味就是典雅弘奥。典雅弘奥的语体风格最大化地呈现出立法诏令的权威化、陌生化、高高在上、一言九鼎、凛然不可侵犯的效果。
从立法修辞的角度看,汉代诏令用语模仿《尚书》,或直接援引经义,或间接化用经典,岂非不利于立法文书的传播?为解决这个问题,宰相公孙弘建议增加通晓经艺的治礼掌故来宣讲诏令,挑选秩比二百石以上治礼掌故及通一艺以上的小吏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秩比百石以下的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选用诵习儒经最多的人充任,“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这个建议获得武帝批准,并著入《功令》[7]3594。这样一来,普法传播,以及被受众理解接受就不存在问题了。
一方面,立法法令的沟通可以依赖通晓经义的官吏宣讲;另一方面,典雅弘奥的诏令风格又树立了庄严肃穆的知识权威风范,故汉代立法诏令达到了很好的修辞效果。宋代楼昉编《东汉诏令》,其在《后序》中自述“幼嗜《西汉书》,每得一诏,辄讽味不忍释。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雍含咀,入人之深也”[8]。
四、结语
汉代立法在法治为本的同时,将儒家经义运用到了极致。法律儒家化是中华法系的基本格调,儒家化的立法思想对封建时代中国的政治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代的立法修辞同样受到儒家化的影响,“汉令语言恰好是儒家法律思想作用于立法的结果”[29],儒家化后的汉代立法修辞呈现出立法权威叠加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进路。正如学者武飞所说,立法过程的修辞目的在于使听众接受立法者所建构的法律规范,进而自觉地遵守这一规范。法律规范的建构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宣示权威的过程,而更应是一个倚赖权威进而追求说服效果的过程[19]。汉代立法修辞依赖三种权威的叠加,达到了“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的说服效果,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为我国当前的立法修辞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