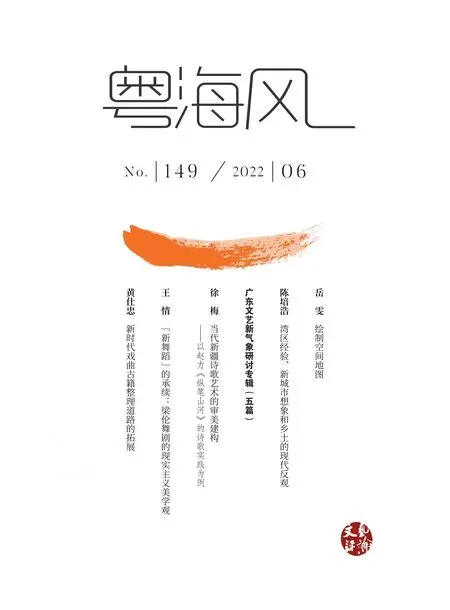遗产化与艺术化
——岭南民俗的价值转换与创新发展
2023-01-21刘晓春
文/刘晓春
岭南地区自然生态多样,多族群共生共存,历经漫长的历史发展,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之中蕴育着岭南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彰显岭南民俗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实现岭南民俗的价值转换和创新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服务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
遗产化
遗产化是实现岭南民俗价值转换的路径。遗产化是指各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民俗文化指定为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的系统性实践。“‘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及振兴”。而那些“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
中国自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以来,广东省与香港、澳门联合申报的“粤剧”,以及联合其他省市共同申报的“皮影”(陆丰皮影戏)、“古琴艺术”(岭南派)、“剪纸”(广东剪纸)等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另外还有165项、816项分别被列入国家级、省级名录。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之前,大多被命名为“民族民间文艺”,尽管20世纪80年代通过“十大文艺集成”的国家工程得以搜集、记录、整理、保存,但尚未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在法律层面予以合法的承认,得到合理的保护。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其中的表述看似耳熟能详、平淡无奇,但对于那些此前与主流、上层、精英群体相比较而存在的边缘、下层、民间群体而言,他们传承的文化第一次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法律层面被命名为“文化遗产”,被视为民族的、国家的瑰宝,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堪称革命性的观念与制度变革。如果说,此前对于“民族民间文艺”的重视尚且潜含“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特征,那么,在法律层面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予以承认与保护,则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转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生活文化传统,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构成了全民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这一变革,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持有者而言,带来的是文化自信,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遗产化的“民族民间文艺”是增强促进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于最大程度地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文化奠基作用。民俗的遗产化过程,实现了从“民族民间文艺”到“文化遗产”的现代价值转换和重新发明。
比如韶关市南雄市的“珠玑巷人南迁传说”,2021年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作为该传说系列之一的江门市蓬江区的“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珠玑巷移民落籍良溪传说)”,则于2022年列入第广东省第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语族群历代口耳相传的族群起源传说,活态传承于口传记忆,也广泛记载于家乘族谱之中。如果说此前更多的是强调岭南与中原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粤语族群迁徙到世界各地,这一族群的集体记忆,则跨越了地域、制度、国家的边界,成为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的象征之一。随着这一传说的遗产化过程,其价值也实现了从血缘的、族群的、地域的到民族的、国家的、全球的意义转换和发明。
艺术化
艺术化是实现岭南民俗创新发展的路径。民俗的艺术化,一方面是指结合声音、文字、视觉、博物馆展示等艺术手段,将民俗文化从生活语境中抽取出来进行提炼、加工、再创造的过程,如《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以及广东卫视的《老广的味道》等;另一方面是指将艺术化的手段植入日常生活之中,比如美化人居环境,增强仪式活动的表演性、观赏性、参与性、共享性,将文化、生态的“灵晕”(aura)赋予地方的生活、生计、山川以及物产等等,使之具有相对于他人的远方感、差异性与魅惑力,从而产生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与精英艺术家独立创作所追求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不同,民俗被认为是日常的、平凡的、琐碎的、重复的、保守的,具有群体化、模式化、程式化的特点,其传承方式是口传身授的,被精英艺术视为大忌的固守传统、因循守旧反而是民俗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民俗生活的艺术化,可以说既是阿瑟·丹托的“寻常物的嬗变”(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也是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过程。年复一年循环往复,传承者视之理所当然、毫无启迪意义的民俗生活,如何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微妙地、奇迹般地成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如何营造一种人们对于平凡事物的自我陶醉和诗意化的感觉?无论是丹托的“寻常物的嬗变”还是费瑟斯通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都强调“审美距离”的重要性。只不过前者还是强调将审美对象置于特定的审美距离之中[3],而后者则主张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消解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发展起来的非投入式审美(在审美过程中与审美客体保持审美距离),谋划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沉浸到凝神审视的对象之中获取审美愉悦,这种距离消解的(dedistantiation)的审美方式,特别适合于对那些被置于常规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与体验进行观察,比如示范性的生活方式的建构。[4]因此,“寻常物的嬗变”是如何创造审美对象的过程,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则是审美主体如何融入审美对象的过程。民俗文化作为“寻常物”和“日常生活”,审美主体既可以通过艺术化的手段使之成为审美对象,也可以通过沉浸其中,与当地人共享民俗文化,进而产生共情的审美体验。
上述民俗艺术化的两种方式,可以称之为“民俗主义”的运用和“地方感”的营造,这是两种相辅相成的观念与实践。
简单而言,民俗主义是指第三者对民俗的利用。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将民俗主义定义为“是在一个与其原初语境相异的语境中使用民俗的素材和风格元素”,并且指出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民俗通过文学、艺术和美术等形式,从底层文化上升到社会统治阶层的文化领域;旅游和大众传媒领域中原本简单的习俗改变为夸张的色彩斑斓的表现形式;经常被“中介”和“表演”的童话等“古典”叙事形式。以上三种现象,特别是第一种,其实并非20世纪所独有。法国启蒙运动、德国浪漫派或俄国民粹派,都曾经有过对民俗的跨语境移植和利用。[5]因此,首先将“民俗主义”这一概念从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论著中运用到民俗学领域的德国学者汉斯·莫泽也指出,“民俗主义自身并不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形成”,“民间习俗的传统和功能成分在它们原来的地区之外被利用,民间文化的主题在其他社会阶层被随意模仿,出于各种目的所发明和创造的带有民间印记的成分对于传统的越位,这一切正如它们所显现的,很久以来就存在于所有的早期文化之中”。[6]当然,汉斯·莫泽也特别强调,20世纪60年代那些紧密嵌入旅游业、休闲业的民俗主义,与以前的民俗主义大不相同。[7]美国学者古提斯·史密什则指出,教科书将民俗主义定义为“二手的传统”或“原初语境之外的民俗”似乎有些过于粗疏,以致于无力把握18世纪以来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民俗研究以及民俗主义建构民族国家传统的历史运动。如此看来,这一概念所定义的现象似乎遮蔽了文化传承变迁的复杂性。因此,基于田野经验,史密什认为民俗最大的特色是作为约定,而民俗主义则是一种过程。他更愿意从功能的角度定义“民俗主义”。在他看来,民俗主义在功能上显示了对民俗有目的的运用,使之成为族群、区域或民族(国家)文化的象征。民俗主义的历史恰恰触及了民俗学的学术根源。[8]而在这意义上而言,德国、芬兰、日本等国的民俗学历史可以说也是一部民俗主义的历史。[9]
在时空压缩时代,“地方感”既是扎根的,可以营造的,也是可以与他人共享的,可以进行意义再生产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认为,当人们对一个地方熟视无睹,感觉自然熨帖、无拘无束、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就拥有了自己的“地方感”。[10]而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认为,在时空压缩时代,应该以一种开放的、进步的、强调过程性和社会关系连贯性的“全球地方感”的观念感知和思考地方。[11]也就是说,在时空压缩时代,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具有扎根与真实性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与人有紧密而稳固关联的空间,而是一个事件,结合了身体、物体与流动的事件。“作为事件的地方,其特征是开放和改变,而不是界限与永恒”。[12]
笔者近几年在贵州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以自我的视角去发现、讲述和记录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通过将传统和日常生活神圣化、传奇化以及审美化的方式唤醒当地人的“地方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可以发现“前现代”的神圣叙事和消解审美距离、倡导简朴生活的后现代美学实践叠加在一起,共同奏响了融汇地方传统与外界想象的“全球地方感”。当地人还将日常转换为非常,采用非日常的艺术性庆典方式集中呈现村寨传统的日常生活,虽然也有程序化的设计,但这种庆典都是村民以主体身份参与实践,不是旅游公司设计的、非共情的表演性生活表象。村民与游客在美食、歌舞、仪式共同营造的热情和欢乐的氛围中共享“地方感”,这是一种开放的、共享的,与其他地方相互作用、与其他人群互动交流共同营造出来的“全球地方感”。
民俗遗产化与艺术化过程中的问题
1. 谁是主体:“非遗在社区”还是“社区的非遗”?
在民俗的遗产化过程中,“社区(communities)保护”是相关利益方强调的核心措施。然而,非遗与社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相关利益方却是暧昧不明。究竟是存在于社区还是为社区所属并持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保护理念及其生活实践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的区别在于谁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前者强调“非遗在社区”,后者则强调“社区的非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意义上的“社区”,是指生活在特定地区、国家,具有强烈的文化共享意识的人们,包含了地理空间、行政空间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群。“非遗在社区”强调作为项目的非遗在某个地域共同体的存在,这是将“社区”功利性地理解为行政单位和空间单位,至于谁是非遗项目的保护主体,并非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理念主导下的非遗保护往往是主体缺位、权责不明、主次失序,最终导致保护乏力。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很多情况下,有些地方政府、机构或者资本擅权越位,越过社区主体,在社区致力于各种非遗的展示、表演、传播活动,试图借此扩大非遗的影响,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对于非遗本体的保护与传承往往并不在意。久而久之,导致政府、机构、资本与社区主体之间的关系疏离,渐行渐远。社区主体即便参与到这些活动之中,也情非自愿,原因在于这是“要我做”,而非“我要做”。而“社区的非遗”则强调非遗属于社区,并为社区所持有,社区是非遗保护的主体,非遗是地域共同体中的所有人共享、实践的文化。他们所从事的非遗保护相关实践,出于自愿,知情且同意,并且投入极大的热情,执着地坚守社区的传统,是“我要做”,而非“要我做”。这种保护理念所带来的,是非遗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非遗保护的社区主体与政府、机构、资本的合作权责分明,相互尊重,惠益共享。
2. 民俗:艺术化乡村振兴路径的灵魂
乡村硬件环境的美化,只是乡村振兴的一部分。良风美俗的传承与弘扬,才是乡村振兴的灵魂。长期以来,人们在与自然、群体、祖先之间长期的互动交流过程之中,积淀了一整套稳定的观念和模式化的实践方式,其中与自然共生共存的技艺、智慧,与群体合作共享的习俗、惯制,与祖先神明之间形成的奉献、赐予的精神互惠机制,在今天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亟待发掘其蕴含的现代性价值。永续利用自然资源,与他人和谐共处,敬畏天地自然万物和孝敬父母等优良传统,这些乡村的良风美俗,都值得传承和弘扬。关键在于如何发掘,如何进行意义的再发明。这是一个涉及村民、政府、学者、机构、资本等力量共同协作才能实现的系统工程。在广东的乡村振兴和城市化过程中,有许多鲜活的案例值得深入调查,总结经验教训。
注释:
[1] 参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
[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http://www.gov.cn/flfg/2011-02/25/content_1857449.htm.
[3] [美] 阿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陈岸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4页。
[4] [英] M.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6-97页,第103-104页。
[5] [德] 赫尔曼·鲍辛格:《民俗主义》,载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上),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2-115页。
[6] [德] 汉斯·莫泽:《论当代民俗主义》,载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上),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3-44页。
[7] 同 [6],第52页。
[8] [美] 古提斯·史密什:《民俗主义再检省》,载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上),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80-188页。
[9] 刘晓春:《民俗与民族主义——基于民俗学的考察》,《学术研究》,2014年,第4期。
[10] [美]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页。
[11] Edited by Massey,Doreen,“A global Sense of Place”,Journal of Space,place and Gend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p146-156.
[12] Tim Cresswell:《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Place:A Short Introduction),徐苔玲、王志弘译,群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