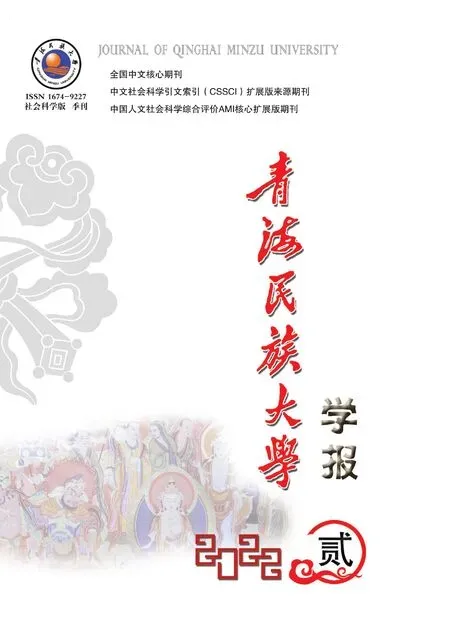近现代西方考察家对安多地理环境及藏族生态保护习惯规则的人类学观察
2023-01-21白佩君
白佩君 马 骅
(青海民族大学 西宁 810007;青海师范大学 西宁 810008)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学者寻找“香格里拉”神秘世界的时代背景使一些西方考察家始终怀有对青藏高原探究的悸动。考察家与传教士进入青藏高原考察和游历,可以说是近现代西方人展开藏族聚集区生态环境和人文风俗探索之旅的起点。[1]藏族聚集的安多地区,也吸引了一大批考察家,他们围绕生态环境和宗教人文,展开一系列的考察和游历,从人类学和民族志的角度进行了生动的书写。在字里行间,展现出了历史上安多地区秀丽的自然风光,人与动物、植物等生态要素和睦相处的图景。和谐环境的保有离不开藏、蒙古等当地民族的环保意识和行为习惯,行为习惯下派生出的习惯规则又表现在生活禁忌、宗教信仰、生计方式、村规民约等方方面面,这些生态环境保护习惯规则在考察家的考察和记述中也有一定的深描。
一、历史记述中安多地区的生态环境
藏文化语境中“安多”(Amdo)的地理空间,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在《安多政教史》中有如下记载:
“自通天河之色吾河谷(现青海玉树曲麻莱县),北逾巴颜喀拉山,其东麓有阿庆冈嘉(a chen gangs rgyab阿尼玛卿) 雪山与多拉山(mdola祁连山),据说以摘取这两座山峰之名的首字,合并起来把以下的区域称为安多云。此处之水,汇合起来流向玛云秀茂川,称为玛曲(rma chu黄河)。流经索罗玛(今果洛鄂陵湖之北地区)或称扎陵湖川,折向南流,自此河湾以下,才是安多区域。”[2]赛多·罗桑崔臣嘉措在《塔尔寺志》中讲:“所谓‘阿垛宗喀者’,是说‘阿钦岗日伊甲日’(意思为阿钦雪山的后面即积石山)和垛拉仁谟二者之名共合而起名‘阿垛’。”[3]
《塔尔寺志》和《安多政教史》中所记载的“阿钦岗日伊甲日”和“垛拉仁谟”二者之名共合而起名为“安多”区域。许多学者认为安多范围是从黄河上游以及青海湖以东的湟水流域、扩大至青海湖以北和以西地区,形成了西起柴达木、北抵祁连山、南达阿尼玛卿山南麓,东到四川阿坝黄河大转弯之间横跨甘青川三省的广袤地区。[4]
安多地区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山峰高度在4000米~6000米。总体地势西高东低,山脉大都由西北向东南伸展。这里雪山耸立、河流纵横,成为黄河、长江的发源地。安多南部的阿尼玛卿、北部多拉热毛(祁连山)主要为“雪山”,这使得两山之间的安多地区也成为“雪域”的一个重要标识。在东部地区,也就是汉语语境中的河湟地区,气候温和,适于灌溉,适合农作物生长,也是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安多政教史》中称谓的幸福宗喀(Tsong kha)城之所在地。色多·罗桑崔臣嘉措在《塔尔寺志》中描述到:“环顾‘宗喀德康’外围的‘安多’地境,南面为玛卿岗日神山,犹如雪山如同水晶塔,映衬着安多中心‘宗喀德康’散发光彩。西面库库淖尔(青海湖)留有莲花生密宗降魔手印痕迹,震服着此地魔怪不得作乱佛法,使此地得以祥和平安。北面垛拉仁谟神山护佑,使得这里免遭狂风飞沙,东有宗曲(tsong chu湟水河)自北向东南蜿蜒流经多个大川,资惠着这里五谷丰登。[5]松巴堪布·益西班觉在《松巴佛教史》中也描述到安多地区粮食果木丰饶,其地上部为雪山、石山,中间为草山、岩山,下面为森林和田园,其间镶嵌着湖泊、水池等景观。
从许多对安多生态环境描述的历史文献中看到,这里生长着柳树、桦树、松柏、沙棘、鞭蔴灌木等树木,雪山脚下的开阔地带及高山草场中,盛产冬虫夏草、大黄、黄芪、贝母、雪莲、党参等近百种珍贵药材,成为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药材供给地;还有蕨麻、黄蘑菇、发菜、松茸等营养价值很高的植物及食用菌类。这里野生动物种群丰富,在林地、草原上栖息着藏羚羊、野耗牛、藏野驴、雪豹、棕熊、羚牛、白唇鹿、盘羊、岩羊等动物;野生禽类有黑颈鹤、斑头雁、棕头欧、雪鸡、蓝马鸡、鹰、雕等数十种。夏季,各种珍惜鸟类成群结队迁徙到高山湖泊和河流湿地,觅食繁衍后代。高原河流湖泊有裸鲤、藏水獭繁衍栖息其中。安多地区高山地貌奇异,怪石嶙峋,无数涓涓细流直泻而下,汇集如同银河落地的细密织锦,在文山峡谷中湍急而落,各类珍禽异兽游走于草原山林。万顷草原丰美,农田富饶。[6]安多生机勃勃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青藏高原人类繁衍生息的适宜家园。
二、西方考察家对安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考察
(一)西方考察家对藏族聚集区生态环境的初次认知
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对伊莫顿斯(Emodus)山脉以北赛里斯(Sares)国家,有犬状大小蚂蚁掘金的故事有过记述,[7]到中世纪欧洲旅行家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k)等人的游记对青藏高原印象的描述,吸引了英国人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等人开展寻找“蚁金”的活动,藏族聚集区这一地理概念始进入西方人的眼帘。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考察家与传教士陆续进入青藏高原考察游历,他们对当地地理环境、动植物、族群、宗教人文以及习惯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可以说,对藏族聚集区近现代的人类学书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一批西方人入藏探险的传记中。瑞士米歇尔·泰勒(Michael Taylor)的《发现西藏》,印度萨拉特·钱德拉·达斯(Zarate Chandra Das)的《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失踪雪域 750天》,法国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的《勇闯无人区》,雅克玲·泰夫奈(Jacqueline Thevenet)《西来的喇嘛》,以及奥地利勒内·德·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NebeskyWojkowtz)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意大利朱塞佩·图齐(Giuseppe·Tucci)的《西藏宗教之旅》,等等,这些探险家记述了身临其境于藏族聚集区自然生态与神圣空间中的奇遇,而且深描了宗教场域周围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了深描。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考察家注意到建造寺院及宗教场选址时所观照的地理生境以及藏族聚集区生态繁盛的,其中民间习俗与寺规中保护环境的理念发挥着巨大作用。考察家亲历其境考察游历,甚至内心对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色产生了敬畏,就如邦瓦洛特在《勇闯无人区》“神灵的惩罚”一章中记述到:“我再也不敢去摘下那些神树上有经文的布条了,这是触犯神灵的亵渎行为啊!”[8]
(二)西方考察家对安多生态环境的人类学描述
在美国人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考察认知安多的基础上,许多西方学者以朝圣者的身份对安多地区山川地貌、河流湖泊等自然空间以及藏族风俗进行了考察,从“他者”的视角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记录。如芬兰前总统卡尔·曼妮海姆(Carl Gustav Mannerheim)在安多地区旅行时,对拉卜楞寺周围的生态环境描述到:“这样的山谷许多地方长着灌木和乔木,我们行程的头十二俄里路,山的北坡都有针叶林,大多数还延伸到河边,在高山逐渐远离河流的时候,树林也远离而去,只有个别时候看到附近山坡上密密麻麻的针叶林山顶。 ”[9]保罗·涅图普斯基 (Paul Kocot Nietupski)的《拉卜楞——处在四种文明十字路口的藏传佛教寺院》[10]一书中认为安多地区特别是拉卜楞寺的周边自然与人文环境是“西藏型神圣和世俗互动型”社会。近代后期探险家旅行传记如《在中国的边疆省份:植物学家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的颠沛生涯》《消失的王国——一个女探险家在唐古特、汉地和蒙古的游记》等,从考察探险中可以探视出安多地区自然环境与民众的生活习俗给他们带来的研究兴趣。1956年约瑟夫·洛克(Jeseph F.Rock)的《阿尼玛卿山及邻近地区的专题研究》[11],以安多阿尼玛卿神山自然与人文环境为主线,同时也包含了对近现代西方人探险阿尼玛卿山周围族群人类学的考述。另外,20世纪中叶卡西亚·布福特里耶(Katia Buffetrille)对安多神山阿尼玛前后考察两次,在她的论文《对于神圣圣湖修行岩洞‘朝圣’的反思》中开篇就指出:在藏族的空间概念中神山、圣湖和岩洞是一个整体[12]。她把神山确定为自然景观和神圣领域。同时在论文《安多的蓝色湖泊和它周围的岛屿:传说和朝圣指南》一文中强调了自然崇拜标的物对实际朝圣者行为的影响。尽量从藏族宗教信仰到生态理念探讨神圣与世俗,深度理解藏族聚集区对自然环境的神圣性认知和形成生态保护的行为习惯。
学者妥超群在其文章《汉藏交界地带的徘徊者——近现代在安多(Amdo)的西方人及其旅行书写》中详尽地梳理了西方考察家的入藏路线,其中强调安多地区是入藏东线的必经之地。此时,前来安多考察的法国人古伯察(Huc,Evariste Regis)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描述了宗喀(河湟地区)的田园景色:“一般来说,通往西宁府的道路都是平坦的,维护得也相当好,它蜿蜒地穿过一片肥沃的原野,田地被精心地耕耘,由于大树、丘陵和大量的小溪而被点缀得风景如画。”[13]美国考察家芮哈特(Lusie C Rijhunt)在《与西藏人同居记》中对安多的地貌地理和自然奇观有着生动的书写。俄国人崔比科夫(Gombojab Tsebekovitch Tsybikoff)的《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和科兹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的《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对安多考察较为详细。科兹洛夫对贵德黄河秋天的景色进行了诗情画意般的记述:“清澈的河水的温度在秋天来说是相对而言还算比较高,为13℃。天气晴好的时候还可以见到蝴蝶、苍蝇和甲虫。只有发黄的秋叶和忙于南飞的候鸟让人想起现在已是天气渐凉的秋日了……”[14]英国人威里璧(Wellby)在《穿越西藏无人区》第二十四章中记述游历安多时,对塔尔寺的神树、金瓦殿,与米纳佛爷会面以及当时匪患对寺院周围森林的焚烧、山地的破坏有着较详细的描述。[15]美国人麦贝·卡布特(Mabel H Cabot)在《消失的王国—— 一个女探险家在唐古特、汉地与蒙古》中采用大量的图片形式,记述了美国考察家珍妮特(Janet E Wulsin)从河北出发,游历阿拉善和安多地区,其间记录当时安多的生态和人文情况。在前往拉卜楞寺的旅行中记述到:我们穿过了许多藏族村落,大草原上长满了野花,一直延伸到汉地边界的古城洮州。[16]瑞典人斯文赫定(Seven Hedin)所著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法国人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 Neel)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以及俄国人波塔宁(Grigori Nikolaevich Potanin)、美国人安妮·泰勒(Annie RoyleTaylor)、 瑞德里(H.F.Ridley)、 李纳(Frank Doggett Leaner)、 珀尔希尔 (Cecil Henry Polhill)夫妇等考察纪实中多处对藏传佛教宗教场域的山川、地景所构成的生态和人文空间进行了描述。尤其关于安多地区河流湖泊资源、野生动物、草场森林等生态环境的内容,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 (Nikolay Mikhaylovich Przhevalsky)在《荒原的召唤》“从青海到柴达木”一章中进行过较详尽的记述,在柴达木和准格尔栖息的濒危珍惜动物野驴因他最早记录而被命名为普氏野驴。美国人鲍大可在20世纪80年代考察青海牧区途径西石峡(湟源峡)时被秀丽的山川所折服,他感慨道:“在我们的周围到处可见令人心动的壮丽景色,极目远眺让人心旷神怡,天空、草地、旖旎的景观无边无际,使人心情也开阔起来,空气清新,使人倍感振奋。”[17]从考察家对自然景观的描述中可以窥见,在上世纪前半期现代工业尚未进入安多地区时,这里的社会生活依然保持着以游牧和农耕生计方式为主的原生态图景。
三、西方考察家对藏族生态保护民间规则的观察
柏拉图(Plato)在他的《法律篇》中阐述到:“在古代,人们当时尚无立法……,最初连文字都没有,人们根据习惯和他们称之为他们祖先的法律而生活。”[18]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罗伯特·曼加贝拉·昂格尔(Roberto.Mangabeira Unger)教授认为,习惯法或民间规则只是“反复出现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因而是一种自发形成的相互作用的法律。”[19]这即是我们所认知的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并自觉遵循的社会规则。在广大藏族聚集区,由于特殊的生计方式和行为习惯,藏族逐渐形成了成文或不成文的习惯规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下自觉与不自觉逐渐规范而成。这些习惯规则在近现代西方考察家的考察记录中也有过深描,以他者的眼光观察到藏族生态保护习惯规则对安多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敬仰神山、山神的习惯规则
以神山为代表的高山峻岭被藏族人认为是神灵在人间的化身,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所以产生了许多禁忌。例如,禁止人们在神山上开挖动土和采集花草树木,不得在神山上打猎和伤害各类生物,不准污染神山以及将神山上的东西尤其是祭供器物带回家中。在西方考察家的笔墨中,就有着对阿尼玛卿神山丰富多彩的描述。如法国探险家多隆(Dollon)在黄河上游游历时记述到:“对于藏族地区的游牧民族来说,阿尼玛卿就是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标志。释迦牟尼只福荫有德行的人,而阿尼玛卿接受所有诚心向他祈祷的人。”[20]也有对安多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人对山神的禁忌的描述,不尊崇山神,在朝圣的路上将会降临厄运,如俄国探险家崔比科夫在藏北高原探险时描述蒙古人和唐古特人把一种超自然的神奇之力称作“苏尔”,他们相信“苏尔”的降临是由于人们不尊重山神,因而朝圣者在攀登山口时异常胆怯,口里总是念着不同的经文。[21]考察家在游记中描述藏族敬畏神山、山神的场景,或许也牵引出西方人信仰体系中对高山圣迹膜拜相同的场景心理,就如古伯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感悟到鞑靼地区山顶的祭拜敖包,使他无意间联想到《圣经》里所讲的犹太人违反先知的禁令而崇拜的“圣地”一样。但与之相比,藏族对神山、山神护卫的习惯规则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更具有意义可言。
(二)崇拜圣水河湖的习惯规则
藏族原始苯教遗留形成了对水的敬畏,保护水资源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约定俗成的规矩。安多地区湖泊众多,它们同样被当地藏族视为是神灵的化身成为藏族心目中的圣湖,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对圣湖的禁忌。如不得将污秽之物扔到湖中,禁止在湖水中捕捞生物。认为江河湖泊之中有叫做“鲁”的主宰神,就像汉族崇拜的龙,不可冒犯。又如青海湖,被藏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视为圣湖膜拜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隆重的“祭海”仪式。19世纪末,西方考察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等人专门对库库诺尔(青海湖)进行考察,对藏、蒙古等民族的圣湖崇拜进行过描述。美国传教士季维善(麦仑·格威特·格里布诺,藏文名:喜饶丹贝)在拉卜楞寺游历时,由于听说达尔宗湖的盛名,他意图到那里游览时,被当地部落头人警告休想动湖底的一草一木,等到达那里时他发现自己早已被尾随监视,他才知道达尔宗湖水下全是藏族人的敬奉。[22]藏族的环保理念中还有禁止在泉水、江河源头随意大小便,禁忌随意下水游泳嬉戏,不准在青苗出土和收割时间里下河洗浴、洗衣物等,以防因污染水源而触犯神灵,遭到处罚。这些习惯在英国探险家W.W·福格森的《青康藏藏区的冒险生涯》中也有多处的记述。
(三)敬畏土地的习惯规则
藏族深信草山、土地是富有生命和灵性的,一切生灵都栖息在它们之上,如果随意在草山、土地上乱挖乱掘,必然会破坏其所蕴含的生命气息。因此,在藏族农牧区,大家都恪守“不随意动土”的风俗习惯,严禁在草地上胡乱挖掘。由于地理环境对游牧民族生计方式的决定性,藏族非常注重合理利用草场农田。在牧区,往往有冬季和夏季分季节放牧的草场,按照游牧习惯,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转换草场,以便草场得到相应的休养生息。[23]在农区,人们形成了重视保护土地的风俗,如动土之前先要祈求土地神,举行严格的动土仪式仪轨,禁忌随意挖掘土地,不得在土地上焚烧破布、骨头等散发恶臭气味的东西。关于藏族对神灵和土地方面的禁忌及习惯规则,意大利学者图齐在《西藏宗教之旅》一书中从宗教教义的角度也进行过相应的阐述。
(四)尊重生灵的习惯规则
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Tylor)从泛神论的角度认为神灵与人是相通的,人的行为会引起神的高兴与不悦。佛陀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条龙不听燃灯佛的劝说,硬是去破坏草木,结果遭到了头上长树的恶报,每当风吹树摆的时候,龙就流血、流脓不止,头痛难忍。[24]我们从宗教故事的视角来看,保护生态也是佛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佛教看来,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人们向往适宜人类居住的美妙生态空间。藏传佛教教义中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使得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遵从教义,热爱赖以生存的土地及其山岭湖泊、草木生灵。可见,藏族的宗教信仰体系中蕴含了大量保护万物生灵的习惯规则内容。这些尊重生灵的理念和规则在考察家的观察中也进行过一定的深描。美国人芮哈特在《与西藏人同居记》中记述到,汉人在此攻猎者甚多,但西藏人(藏族)则反是,西藏人以为凡生物均有灵魂,其灵魂均由达于圣贤之境之可能,故伊等不敢攻猎恐伤生命,不但不敢杀生,并不敢食其肉。[25]美国传教士季维善在甘南旅行期间,他写道当地数不清的野生动物与美妙的大自然相映成趣,那些狐狸、野牦牛、蓝马鸡等栖息在藏族地区广阔的高原上,藏族人视这些动物为和人一样的有情众生,不随意猎杀。他讲到:“藏人的生活虽然依赖牛羊肉,但他们从不以滥杀动物取乐,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罪的,如果是寺院这样做了,那么寺院在藏人中的威信就会一落千丈。”[26]安多地区大多数藏传佛教寺院坐落在森林茂密、植被茂盛的地方,为了营造寺院周围良好的环境空间,寺院和僧侣向来有植树和守护林木的习惯。寺院建造之后,僧人们每年都必须种草植树,营造一幅极乐世界的境域。为此,就会告诫进入寺院的人们禁止毁坏寺院周围草木,不得随意在寺院周围狩猎。这种禁忌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笔下也有记述,他在《走向罗布泊》一文中描写到:“我们在榆树林近旁干爽的地面上搭起了帐篷,这里海拔2300米,树木周边就是奔流而下的大通河,河对岸的山上,有一片树木繁多的原始森林,可能已经历数百年,因为林中有一座天堂寺,禁止当地居民进去狩猎。”[27]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为了获得动物标本,在两边的关系融通下,才得到寺院活佛的特许在山上打猎。英国旅行家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hess)在《大西北的呼唤》中也描写到:“森林里有许多麝香鹿和雉鸡,因为是在喇嘛寺境内,所以是禁止猎杀的。”[28]除了在寺院周围严禁砍伐林木、狩猎外,藏传佛教寺院及僧众大都有放生的宗教仪轨,每年在特定的一天举行放生仪式,由僧侣念诵经文,再将“神水”洒在牧民和僧人们事先准备好的牛羊等牲畜身上,并在牲畜的耳朵、犄角上绑上毛线,再将这些牲畜牵引至牧区放生。这样,被放生的牲畜就成了神圣化身,人们不得捕捉和随意伤害。宗教背景下形成不轻易杀生和放生的习惯规则,在崔比科夫的藏北高原探险中有考察记述,一位蒙古喇嘛看到一只母绵羊,准备把它杀掉,但有一位安多虔诚的佛教徒用一两银子买下了这只羊,他在羊脖子上系上了用各种颜色的布条做成的“采塔尔”(护身符),重新把羊赶到了山中。”[29]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系列尊重生灵的习惯规则,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这些地区的生态平衡,安多地区也得以保有大片茂密的森林和丰美的草场。
从近现代西方考察家在安多地区的考察记述来看,无论是基于人类学的考察,还是出于传播西方宗教等目的的考察,他们在安多地区的游历,与其对当地民族、生态环境的认知关系极为密切。西方考察家所留存的关于安多地区的考察资料,不仅详尽实录了这里的地理空间、生态环境、民族宗教等内容,而且记述了当地民族的生态观,以“他者”的目光对当地民族在宗教、风俗习惯等背景下形成的生态环保习惯规则进行了较详尽的阐述和各自的解读。笔者对这些珍贵文献资料进行梳理,从人类学的角度透视近现代西方考察家对安多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这将有利于扩展区域环境保护法治研究的基础资料,在国家环境保护上位法的框架下,为探究历史上安多地区的生态状况,挖掘和研究安多地区保有较好生态环境和自然空间提供了积极因素,对民族生态保护习惯规则的践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更好地推进当代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