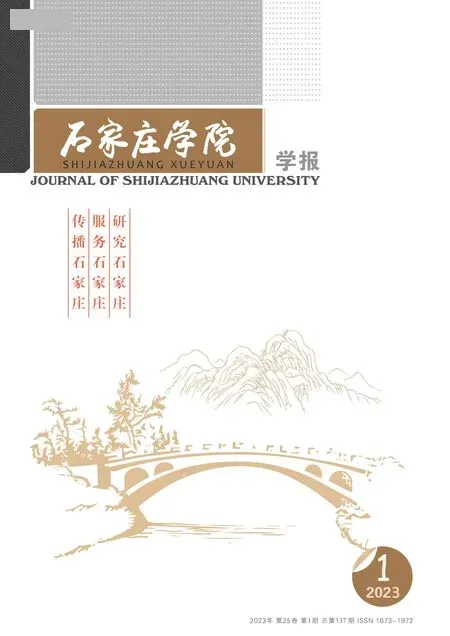《大众文艺丛刊》对延安文艺的延续
2023-01-16钟海林林嘉雯
钟海林,林嘉雯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大众文艺丛刊》(以下简称《丛刊》)于1948年在香港创刊,主编为邵荃麟,作家有丁玲、冯乃超、林默涵等人。《丛刊》共有六辑,各辑皆有独立的主题内容,分别是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第二辑《人民与文艺》、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第四辑《论批评》、第五辑《论主观问题》、第六辑《新形势与文艺》,前后历时一年。总体而言,《丛刊》的内容以文学理论批评为主,兼有译介外国的文学理论,同时还刊登一些作家作品。1946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共产党”)的文艺宣传事业难以在国统区展开,急需开辟一个新的文化战场。因此,国民党势力难以企及的香港显然成为文化战场的最优选择。[1]作为当时南下左翼文人在香港创办的机关刊物,《丛刊》在创刊时即承担起共产党在国统区和香港进行文艺宣传的责任,隶属“文委”(即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2]《丛刊》的编辑人员,邵荃麟、林默涵、冯乃超、夏衍等文人皆有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并且长期负责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他们南下香港,继续开拓共产党在南方的文化事业。[3]101-154
尽管《丛刊》的发行距离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过去5年,但《丛刊》仍然贯彻了《讲话》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解放区以外延安文艺精神延续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丛刊》的发布在文艺界曾掀起一阵波澜。洪子诚认为,《丛刊》“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进程”[4]9,是沟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桥梁之一。通过对该刊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窥探共产党如何将政治与文学意识形态融合,扩大延安文艺在解放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掌握南方地区的话语权;还可以发现在新环境之下延安文艺的延续情况,进而为延安文艺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一、作家、编辑与党性的确立
1936年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以后,大批的知识分子,包括丁玲、周扬等左翼文人随后追随党迁至延安。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创办学校,发行了大量的文艺期刊,使延安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194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将《讲话》定性为“党的文艺政策”[5]123-130。随着《讲话》的发表,延安文艺逐渐形成了以党报副刊为中心、富有解放区特色的文艺体系[6]。1948年在香港创刊的《丛刊》延续了这一文艺体系特点。
首先,《丛刊》通过作家与编辑者的身份确立刊物的共产党党性。“报纸是党的喉舌”[7],在党的领导阶层的观念中,文学不过是一种特殊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工具。刊物作为文学的载体,自然而然成为宣传党的思想与政策的媒介之一。[8]《丛刊》创刊即明确了其共产党的党性特征,无论是编辑,还是批评家、作家,都与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整理统计了六辑《丛刊》作家文章的发表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丛刊》六辑作家的发表情况
除表1所列的作家外,其余作家如葛琴、丁玲、周扬、夏衍等都是党员的身份,丁玲和周扬更是被延安整风运动影响显著的作家。还有在《丛刊》发表过文章的其他作家,如潘汉年、乔冠华、周而复、茅盾、田间等人,当时或在党内任职,或作为民主人士公开支持共产党。这些忠诚于共产党的作家、编辑,将1942年以来以《讲话》为中心构建起来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的编辑理念,将解放区的文艺思想移植至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和南方国统区,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扩大共产党在解放区以外文化界的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文艺与政治一体、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浪潮中,这些作家大部分被吸纳为党和国家文艺部门的工作人员,并在文化界担任一定的职务。由此可见,《丛刊》绝非只是普通的“同人”或“群众”刊物,其党性也正是由作家与编辑共同确立的。党员与干部的身份要求作家与编辑在进行文艺工作时必须“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17],这进一步佐证了《丛刊》实质上是为共产党服务的性质,并带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
其次,《丛刊》采用了带有延安文艺痕迹的编辑形式。抗战时期,延安文艺期刊以服务抗战、鼓舞大众士气为首要宗旨。在这一背景之下,解放区刊物中报告文学成绩显著,主要反映现实斗争中的重大事件,记录解放区真实的人物事迹。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期所设置的专栏包括聚焦前线战事、作家纪念日、特殊纪念日、探讨文学作品、普及与提高等,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报告文学相对活跃的专栏[18]。《丛刊》共六辑,前四辑为双月刊,后两辑出于形势要求改为季刊。在刊物栏目的设置上,《丛刊》第一辑至第四辑“实在的故事”有明确的栏目标题外,其余皆只列出了文章的标题。每一辑的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文艺批评、散文小说、“实在的故事”(报告文学)、诗歌,第五、六辑改为季刊后删掉“实在的故事”这一栏目。《丛刊》每辑的文艺批评不乏作家纪念与特殊纪念日的内容,如:第二辑的开篇文章夏衍的《“五四”二十九周年》是纪念五四运动,第四辑的《敬悼朱自清先生》是纪念突然因病去世的朱自清。“实在的故事”这一栏目的设立初衷是为了刊载一些短小的文学作品,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变体,栏目之下的作品发挥了报告文学的作用,如第一辑的《强渡黄河》和第三辑的《渡淮河》都讲述了解放军战士智勇过河的真实故事。这些编辑形式继承了延安文艺的理念,在形式上采用了更为亲近社会生活、亲近人民群众的方式,加强了共产党以文学为媒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输出党的文艺政策理念。简而言之,《丛刊》通过编辑形式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党性”。
《丛刊》通过采用党员担任刊物的编辑与作家,遵循延安整风运动后所树立起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党与无产阶级服务”等文艺观,同时继承了延安时期文艺刊物的办刊形式,明确了刊物的党性特征,表明共产党试图通过文学在香港和南方国统区扩大影响力的政治目的。《丛刊》对于延安文艺的继承还进一步体现在其文艺批评理论上。
二、文学理论批评对延安文艺的延续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逐渐流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观的“革命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末兴起,并成为稍后30年代左翼文学的先声。发展至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延安有所革新,1948年在香港更是走向了另一态势。“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17]延安时期,随着抗战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意识到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性,《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成熟阶段[19]。《讲话》中,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待文艺,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要实现大众化,必须始终要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不能只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象牙塔”,应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是具有革命功利主义的,要服从于政治[20]。
就此,以《讲话》为界限,延安文艺明显呈现出具有差异性的前后两个时期。1935年共产党中央抵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进驻延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意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毛泽东直接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1]618-620。在1937年至1942年整风运动前夕,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吸纳,共产党在陕北地区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文艺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团结新旧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自由创作、创办大量的报刊社团、保障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水平等等,以此形成当时延安文艺的繁荣。[22]74-84但是,由国统区到达解放区的延安文人也暴露出共产党所言及的“小资产阶级”毛病,毛泽东认为,来延安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经过整风运动来“洗澡”。整风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确立,延安知识分子将它奉为文学实践活动的圭臬。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延安文艺盛行的批评理论及其批评标准也由解放区走向了国统区以及受殖民统治的香港,最终在《丛刊》上呈现。
《丛刊》以延安文艺时期构建起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准绳,进行了大量不同的文艺批评实践。《丛刊》开篇名义的文章是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被视为该刊文艺批评实践的总纲。在这篇文章中,邵荃麟提出“今天的文艺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必须要“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以土地改革作为它主要内容,服务于工农兵”;文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以及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成为了文章的重点。[23]穆文的《略论文艺大众化》则详细论及了文艺大众化中,如何具体实现大众化、如何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等问题。[24]林默涵的《论文艺的人民性和大众化》中提出利用旧的文学形式来普及文艺,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加强文艺与人民的联系。[25]
《讲话》无疑是要求文人作家与小资产阶级决裂的宣言,虽然毛泽东同志在此提出“团结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但小资产阶级实质上已被视为是次于工农兵群众的“他者”,小资产阶级立场因而成为了负面的观点与标准。[5]
《丛刊》的文艺理论批评延续了整风后延安文艺的批评标准,对于小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地批评,把一切涉及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作品笼统地归纳到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内,在高举“批判小资产阶级文艺观”旗帜的同时,深化了文艺大众化的主题。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以“文艺是否为人民服务,联系现实生活”为尺度,以作家作品是否包含了小资产阶级气息、有无表现工农兵群众积极向上的一面为原则,进行批评实践。例如,在第二辑《人民与文艺》中,胡绳发表了《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分别对姚雪垠的《牛镕全德和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记卢轩》这几部作品的主人公进行批评。胡绳认为,作者即使写的是工农兵人物,但在他们身上,仍然无法摆脱浓厚的、令人难以忽略的小资产阶级气息,作者陶醉于自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遐想,使作品脱离真实的历史与生活。[26]第四辑中对于香港文学作品《虾球传》,周钢鸣发表了《评〈虾球传〉第一二部》,其核心思想是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虽然出身于底层,但身上所表现出的一些特质却不符合贫苦百姓应有的特点。归根到底,是由于作者本身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又未能深入群众、深入到具体生活中去,只能以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兵大众的幻想来创作作品。[27]相反,林默涵的《评臧克家的〈泥土的歌〉》则对臧克家十分赞扬,开篇即说“臧克家是一位有相当历史的诗人”。文章把臧克家称作是“农民诗人”,他的诗歌表现了“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看法与感情”,在描写农民群众贫苦一面的同时,又体现了底层百姓对生存的积极与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反叛。[28]六期《丛刊》中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并不多,有《论西欧文学的没落倾向》《罗曼罗兰的〈搏斗〉——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道路》《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等。这些文章都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存在观为准则,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文艺与政治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文艺应为现实斗争和为人民服务。
《丛刊》所践行的文艺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后的标准,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产物。作为具有共产党党性的文艺刊物,《丛刊》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政治宣传。在1948年的香港,《丛刊》作为延安文艺在解放区外的延续,通过大量的文艺批评理论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观在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和南方国统区传播,有利于共产党迅速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但潜藏在这些文艺观背后的是小资产阶级成为了假想的“敌人”,“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无话可说,也就没有仔细看”[29]299。《从刊》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也处处透露着不严谨,以草率的批判方式和先入为主的政治观念抹杀了作品的文学性。例如,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批判朱光潜时曾表明,他是未读过朱光潜的作品的,为了写批评文章才特意去读其一二篇作品。[30]此外,《丛刊》的批评面虽广,但批评套路大多相似,这也是刊物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三、文学作品对延安文艺的移植
除了在文学批评上坚持对《讲话》文艺标准的实践,《丛刊》在主题内容上也体现其学习并发扬《讲话》精神和对延安文艺的移植。《丛刊》刊载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故事与诗歌为主,数量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丛刊》刊载作品的数量
主题内容上,作品遵循了延安文艺所强调的文学贴近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等要求,几乎取材于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它们或是反映军旅生活和个人的先进事迹,如小说《人民英雄刘志丹》《真假李板头》《林湖大队》等;或是反映了在封建地主和反动派的压迫剥削之下农民群众的穷苦生活,如长诗《苦难的童年》、小说《富贵》《瞎老妈》等;或是反映了现实斗争中人民群众昂然向上的激情,如诗歌《中国学生颂歌》、长诗《反迫害进行曲》等。
赵树理作为延安文艺的代表文人,遵循了毛泽东文艺观要求,他在《丛刊》上共发表过两篇小说,分别是《富贵》与《催粮差》。前者叙述了一位贫苦农民在地主高利贷的压迫之下抛妻弃子远走他乡,直至共产党解放家乡后他归来并对地主控诉的故事[31];后者则描写封建官僚制之下,一个县上的催粮差对权贵谄媚、对贫苦百姓剥削的丑陋嘴脸[32]。这些作品构思巧妙、真实感强,在表达工农兵生活的同时,也向香港和南方国统区的大众展现了国民党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和解放区人民的幸福生活,通过国统区和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对比,意在宣扬共产党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宣传作用。
《丛刊》在主题内容上进一步体现“移植”的还包括街头诗。街头诗是延安文艺的产物,以短小精悍的形式、通俗明快的语言、极强的号召性和鼓动性为特点,通俗易懂,受众较广。作为延安时期兴起的一种新型传播媒介[33],街头诗响应《讲话》中文艺服务于现实斗争的要求,让诗歌有效发挥服务于战争的功能。此外,《丛刊》也刊登了不少由田间、柯蓝等人创作的街头诗,这些诗歌的取材与小说故事类似,主要以反抗压迫、与强权斗争、颂扬英雄事迹、发扬乐观精神为主。如田间的《坚壁》,“狗强盗/你要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来告诉你/枪,弹药,统埋在我的心里”[34]。
“实在的故事”这一栏目更是体现“移植”精神内核。“实在的故事”虽是一种新的文艺形式,参照了苏联文艺的“True story”和日本文学的“实录”形式创造,结合左翼报告文学的传统,试图通过这样的文艺形式迅速反映现实斗争;但栏目作品口语化的表达仍旧延续了延安文艺的表达方式。[35]“实在的故事”一共收录了20篇作品,作品短小精悍,语言夹杂着方言、俚语、俗语,多用语气词,多以口语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文章浅显易懂,从语言上体现了延安文艺的大众化要求。例如,第一辑华嘉的《好心肠的谢医生》以短句开头:“粤东XX县,有个姓谢的好医生。他医道好,做人好,替穷人看病仔细周到,又不肯收钱......”[36]这些故事造句简单、多用短句叙述,读罢朗朗上口而不晦涩难懂。还有些故事喜欢用对话进行表述,故事的情节在对话中递进,高潮也随之展开,如第二辑刘五的《王喜天的冤恨》,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王喜天的话语,通过个人对他人的回答揭示了国民党军队强抢民妇、殴打平民致使其家破人亡的暴徒行径[37]。口语化的表述也往往潜藏在人物的对话之中,如第四辑李平潮的《征实》,就在对话中采用“妈的,我老子是你们牛呀还是马……你们晓得一个屁”“喂!告诉你们……听清楚了吧”的表达方式。[38]这些口语化与粗鄙化的表达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知识分子迫切贴近“工农兵”、贴近“大众化”与“群众化”的成果。
理论先行,主题随后。《丛刊》在文艺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进一步深化了延安文艺中毛泽东的文艺观,维护了作品“党性”的特质。1942年整风运动以后,以《讲话》为方针的毛泽东文艺观逐渐成为延安文人的集体无意识。《丛刊》并非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设立的第一份报刊,在《丛刊》之前,1946年《华商报》复刊,随后又陆续出版《正报》《群众》等刊物[39]。可以说,经过这些刊物的实践,1948年创办的《丛刊》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运作模式,目的十分明确。但《丛刊》在内容主题上对延安文艺的移植,也正如移植其字面意义所指,只是极端地将已成型的延安文艺由解放区移植至香港。刊物所刊载的内容仍旧是解放区的那一套,表面上是对延安文艺的深刻继承,但究其内容与主题却是狭窄的单一复制,缺乏新意。
四、结语
五四运动以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无法以个体独立存在的形式前进,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被迫纳入政治与现实斗争的版图之中。一方面,知识分子需要通过政党获得自我生存的空间,发表个人主张;另一方面,政党需要吸纳知识分子,借助知识分子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1936-1949年,大量的文人为了追求心中的“理想国”来到延安,预示着他们个体的命运将与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整风运动以后,这种共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并具体体现在知识分子的文艺创作中。在政治功利性的驱动之下,解放区的文艺由延安文学窄化为工农兵文学,最后置换成党的文学。[40]延安整风运动最终将一套完整的、带有政治性的文艺观深深植入作家文人的脑海中,包含着自由主义、个体思想、温情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被清理,作家个性逐渐消亡,“为党与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大众化”等《讲话》所强调的观点成为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1948年,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接连取胜,迫切需要掌握解放区以外的意识形态战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思想基础;而整风运动以后,延安文艺的成果则为共产党提供了一条统一思想的可行之道。《丛刊》被视为解放区以外第一份全面阐释《讲话》的文艺刊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型的重要扭结之一[41]。在香港创办的《丛刊》委派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编辑,并且大部分作家拥有党员身份,他们自觉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立场去筹办刊物,在文艺批评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文艺观,在主题内容上贯彻了毛泽东《讲话》的要求,移植延安文艺,使《丛刊》由里至外体现了对整风运动以后延安文艺的延续。与延安整风时期相比,《丛刊》在政治的立场上采取更为苛刻的标准批判小资产阶级文艺,排斥“个体”的存在,提倡去个体的“集体”,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尊崇工农兵文学、党的文学等,从而突出了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而抹杀了文学的艺术性。这虽然有利于文化思想的统一,却也使文学逐步走向了越来越狭窄的局面。此外,《丛刊》中不少文艺主张也成为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前后制定中国文艺发展方针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该刊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走向“一体化”进程的先兆。在笔者看来,《丛刊》通过编辑和作家确立的党性,所进行的文艺理论批评、所刊登的作品主题内容都是对延安文艺的一脉相承,但也预示延安文艺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文学的窄化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