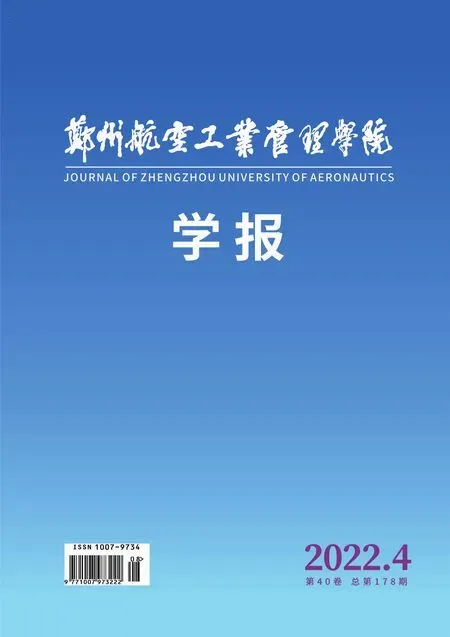“情报坚守”及其价值
2023-01-11周九常王红云
周九常,王红云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情报坚守”既是一个情报学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情报工作实践问题。从理论方面说,它关系情报学学术传统能否继承,关系情报学理论基础是否稳固;从实践方面看,它关系情报工作的“广、快、精、准”的要求和标准、“耳目、尖兵、参谋”的角色地位、决策支持和战略规划的功能定位是否改变,[1]关系情报领域能否“守土有责”。相关研究散见于情报学基本理论研究成果中,特别是情报及其相关概念辨析、情报学理论体系构建、知识管理和大数据等对情报学的影响(或者与情报学的关系)等方面,而直接、独立面对“情报坚守”问题的研究成果还较为少见。
1 “情报坚守”的含义及问题由来
“情报坚守”的含义是,情报学界(情报学人和学术组织)在学术活动中,情报业界(情报工作者和情报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维护“情报”传统,坚持“情报”立场,不为“时髦”所惑,不惧“新贵”打压,始终以“情报”之名行事,努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情报话语权”,保有基本稳定的情报话语体系,并使这一话语体系在理论研究、专业教育和工作实践的核心领域得到应用。
那么“情报坚守”问题从何而来呢?毫无疑问,它和“信息扩张”密切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信息”一词的应用一直处于扩张之中。究其根源,理论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三论”,即C.E.Shannon的信息论、N.Wiener的控制论和L.Bertalanffy的系统论。“三论”的提出为“信息扩张”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三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信息”概念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从而开启了“信息扩张”,甚至一统“近义词族”的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信息”一词的使用远不如今日之盛况,当时,它和“消息”“口信”“音讯”“讯息”等近义词的使用面、使用次数和使用频率并无显著差别)。另一方面,在“三论”的影响下,加上后来的“新三论”(Haken的协同论、Rene Thom的突变论和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论)的接续助力,社会信息化进程大大加快,“信息社会”加速到来,“信息”一词“身价”大增,“行情”看涨,迅速成了全社会各领域中的“热词”。在信息浪潮冲击下,“信息”一路攻城略地,有横扫千军之势。传统的“情报”领地一时山河色变,换了人间。“情报”节节败退,目前仅剩下几小块零零落落的核心地盘,到了退无可退便死守不退的地步。“信息扩张”与“情报坚守”之间是一对矛盾关系,前者代表了时代潮流,后者反映了历史传统,二者都具有存在的价值。拂去历史的尘埃和现实的泡沫,经过对“信息扩张”喧哗与骚动的沉淀,我们发现:第一,“信息扩张”与“情报坚守”并非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一对广的关系,即“信息扩张”是全领域、全社会的扩张,而“情报”的应用范围本来就是有限的;第二,“信息”在多领域、多方面蚕食、掠夺了“情报”的地盘,相当于对情报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但是,这种“改造”进行得并不彻底,因为在有些领域,“情报”拒绝改造,拒绝退场,坚守自己的“底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扩张”既是“情报坚守”不可脱离的时代背景,也是“情报坚守”的对立面。这样说来,“情报坚守”的真实含义是——部分情报学界、情报业界人士坚守“情报”立场,拒不接受“信息”带来的“改朝换代”。但总体上看,“情报”一词的使用面大大缩小,使用领域大大减少,呈现出一种由面状,到块状,再到点状的变化图景。这是长期以来身不由己、此消彼长的发展结果。
2 “信息扩张”的主要体现
如上所述,“信息扩张”是各领域的扩张,理论上应当“扫描”所有领域的“信息扩张”分别有哪些体现,但限于篇幅,这里仅仅聚焦于图书情报、信息管理和民用航空(以下简称“民航”)领域“信息扩张”的主要体现。
2.1 对Information的理解和翻译脱“情报”向“信息”
把Information一词越来越多地翻译为“信息”,“信息”逐渐成为Information的主要对应词。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学者,由于成长环境的原因,他们更多或经常地把Information与“信息”对应起来,从而“自然而然”地与其他多数领域对Information的通行理解与称谓——信息“达成一致”。这样一来,国内图书情报学界对Information的理解和称谓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会儿称“情报”,一会儿叫“信息”,或者你叫“信息”,他呼“情报”。比如对同一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现在有人翻译为“信息与图书馆学院”[2][3],而过去则一般翻译为“图书情报学院”[4]。翻译为“情报”者代表的是“传统”,翻译为“信息”者代表的是“当代”;中老年学者习惯于译为“情报”,年轻学者(因热烈拥抱“信息”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倾向于译为“信息”。近几年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种翻译的差别由开始时的泾渭分明逐渐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部分中老年学者不再完全排斥(往往也难以排斥)“信息”,甚至他们自己也时常把Information译为“信息”,少数青年学者也遵从图书情报的学术传统,开始在一些特定场合理解、接受Information的“情报”称谓或者自己也偶尔把Information翻译为“情报”。
民航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形,传统上视information为“情报”,几乎不存在什么争议,但现在也开始有人把它对应于“信息”,这是“Information”翻译脱“情报”向“信息”的另一个体现。比如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and Meteorological Data Link Services,有人翻译为“航空信息与气象数据链服务”[5]。甚至还出现同一个人在一个特定情景(比如一篇文章)中既把information看成“情报”,又把information当作“信息”的现象[6]。比如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一词,国内学者过去基本上翻译为“航空情报服务”,现在也有人翻译为“航空信息服务”[7]。美国的The National Air Pollution Technical Information Center,国内学者过去一般翻译为“国家大气污染技术情报中心”,现在也有人翻译为“国家大气污染技术信息中心”[8]。
2.2 出现一股“信息化”的改名潮
在国内,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信息泛在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叠加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情报”变“信息”为核心的改名潮。部分省地(市)级“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信息研究院”或“信息研究所”,比如浙江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杭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杭州市科技信息研究院”,河南省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河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在高校,绝大多数原来的图书情报学院(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院(系)”。
美国高校图书情报学院改名一方面显示出“Information化”,或更加突出“Information Science”,另一方面表现为“去Library化”,或者淡化学院的“Library Science”色彩,导致名称中含有“Library”一词的学院越来越少。1982年,肯塔基大学的College of Library Science 更名为 the Colleg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93年合并后改名为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2012年改名为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9]。另外,极个别的甚至把传统上“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的习惯顺序颠倒,变成“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比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图书情报学院的名称变成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 of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Chapel Hill)。跟中国图书情报学院的“信息”化改名明显不同的一点是,美国图书情报学院的改名还出现了另一个走向:“技术化”或“计算机化”。这个新的走向看似特别,其实依然内涵了“Information化”,因为“技术化”或“计算机化”跟“Information化”紧密相关。比如德雷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图书情报学院先更名为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后在2013年创建新的The College of Computing & Informatics[10]。匹兹堡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在1996年更名为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2017年再更名为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11]。
2.3 因“信息”而衍生的新词空前增加
“信息扩张”不仅蚕食“情报”的领地,而且又衍生出一系列形形色色的新词汇,表现在课程设置上就是出现了许多带“信息”字眼的新课程,这样的课程汇集起来,就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课程体系。比如,仅仅在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填补情报学退出本科教学所留下的空缺的专业——就增加了如下众多课程:信息管理学、信息组织与利用、信息服务与用户、信息经济学、经济信息学、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信息计量学、信息分类学、信息检索、信息咨询、信息检索语言、信息分析、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安全、信息网络(计算机网络),等等。此外,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还设置了层次不同、名目也略有不同的“信息技术”课。
3 “情报坚守”的主要内容
面对摧枯拉朽、席卷一切的“信息扩张”,在部分领域,因情报学界和情报业界的坚守,“情报”就不是浮萍,随波逐流;情报也不是流云,随风飘荡。它有根有魂,扎根在情报工作实践中,魂系于情报人(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员、情报工作人员、行业管理人员)的内心深处。“情报坚守”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3.1 与“library”关联时“Information就是情报”的译名主流没变
一直到现在,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如果Information一词的出现和使用是和library或library science等词语联系在一起,则一般遵循“旧制”,翻译为“情报”,比如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多翻译为“图书情报学”而非“图书信息学”。对国外比较有影响的图书情报学术刊物名称的翻译,其中涉及Information与library在一起的情形,也基本上把Information翻译为“情报”,比如《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译为《图书情报学研究》,《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译为《图书情报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tudies》译为《国际图书情报研究杂志》,等等。此外,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在我国一般也翻译为“图书情报学院”,比如美国的Simmons College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译为“西蒙斯大学图书情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译为“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情报学院”,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of University of Kentucky译为“肯塔基大学图书情报学院”,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of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译为“北得克萨斯大学图书情报学部”,等等。在图书情报领域,无论“信息扩张”如何高歌猛进,information的使用只要伴随library或library science,它基本上就被翻译或理解为“情报”,这是“情报坚守”在图书情报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也表明,其“情报坚守”存在着对于“library或library science”的“路径依赖”。
3.2 民航领域中的“情报立场”初心未改
图书情报以外,民航领域的“情报坚守”是另一个比较成功的典范,“信息扩张”几乎没有撼动其“情报”的主导性称谓。传统上,“Information”一词对应于“情报”,比如aeronautical information,几乎毫无疑问地翻译为“航空情报”,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翻译为“航空情报服务”,其他诸如“航空情报员”“航空情报专家”“航空情报资料”“航空情报专业”“航空情报系统”“航空情报(系统)平台”“航空情报技术”“航空情报规划”“航空情报研究”“航空情报学”“航空情报培训”“航空情报案例”“航空情报(资料)汇编”“航空科技情报研究所”“航空情报中心”“国际航空情报日”“航空情报工作”等专业词汇中的“情报”也统统是作为information的对应词。更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民航局管理全国空中交通服务、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航空气象、航行情报的职能机构,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下辖6个直属单位,其中包括“航行情报服务中心”(不叫“航行信息服务中心”)。
管理部门和机构出台的法规对“情报坚守”也功不可没,比如“航空情报服务”这一称谓被多个相关法规所“固定”。对于Aeronau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s来说,由于法规文本称它为“航空情报服务”而非“航空信息服务”,就具有权威性的指示意义,同时也把二者区分开来:前者是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内涵与外延,还是一门民航学院的课程名称;后者则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内容更加复杂,边界更加模糊,涵盖更加广泛。编号为IB-TM-2018-01的《中国民航航空情报管理(AIM实施指南》中明确规定:“航空情报(Aeronautical Information)包括航空法规、飞行规则、机场、空域、航路、飞行程序、通信导航设施、各种航空服务程序等资料和数据以及航空图,它是民用航空器飞行所依据的基本资料,也是航空公司航务部门组织飞行,民航空管单位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提供空中交通服务必需的情报资料。”围绕上述航空资料开展工作并提供服务就是“航空情报服务”。具体来说,航空情报服务是空中交通管理的重要一环,是对航空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后所生成的情报,包括文字资料、数据、航图和航行通告等不同形式的资料。航空情报(成果或产品)的发布与提供(即航空情报服务的落实)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航空情报服务产品,二是航行通告。航空情报服务产品主要用于发布有效期在半年以上和较为稳定的长期性航空资料。航行通告主要用于发布有效期在3个月以内和临时有变更的航空资料[12]。
不仅如此,《指南》还规定了由全国民用航空情报中心、地区民用航空情报中心、机场民用航空情报服务机构负责履行航空情报工作运行职责。以上种种,在法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航空情报服务”的内容范围、实施主体、服务方式,表明“航空情报服务”只能围绕这些方面开展“既定”“有限”的工作,自然也进一步明确了“航空情报服务”的边界。而“航空信息服务”的提法则比较随意,“专业性”色彩不足,服务深度不够,进入门槛不高,外延比较宽泛,内容比较复杂,比如航空公司网站提供的航班信息服务、票务信息服务等都可以纳入“航空信息服务”的范畴,但是对照《指南》的规定,它们显然无法成为“航空情报服务”的内容。另外,在比较严谨的学术论文中,Aeronautical Information较多地翻译为“航空情报”,这也显示了民航学界的“情报坚守”。
以上所述,充分表明,在图书情报和民航领域,“情报”一词的使用“粘性”较大,“传统烙印”明显,意味着“情报坚守”比较成功。其他领域的“情报坚守”,值得一提的还有气象、医药、农林渔业、金融、测绘,等等。
3.3 情报学学科对“情报”的细心呵护
无论“信息”如何铺天盖地,“情报”一词都是情报学永恒的关键词,情报概念都是情报学最基本的概念,是构建情报学体系的理论基点和逻辑起点。为此,情报学学科的“情报坚守”无疑就是对“情报”的细心呵护。反过来说,对“情报”的细心呵护就是情报学学科对“情报坚守”的落实。情报学学科担起了“呵护”责任,尽力抵挡或减轻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冲击,延续了“情报”的根脉,自然也保持了情报学的传统“纯粹性”。
第一,从科研项目立项来看,高层次科研项目立项中显示了“情报坚守”。比如,仅仅在图书情报学的立项项目中,除“竞争情报”(这里的“情报”是“intelligence”而非“information”)类的项目外,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多源数据的情报学新兴趋势探测研究”“情报学研究方法的知识图谱构建及其应用场景推荐研究”“产品化思维下的国内外开源情报开发与利用机制研究”“大数据环境下突发事件中多模态危机情报智能挖掘与推荐研究”;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产业技术情报分析方法体系研究”“情报刻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开放科学环境下图情机构与智库协同创新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多源数据融合驱动的智慧情报感知研究”“多源数据驱动的制造产业智慧情报服务研究”“情报视角下大国竞争中的信息迷雾成因与识别研究”“多链交互的新时期产业技术情报服务方法体系研究”等标题中依然存在“情报”字眼。
第二,从学术期刊来看,刊名中带有“情报”二字的还有不下50种,其中除了17种由传统图书情报机构创办的“情报”期刊外,还包括其他领域相关机构创办的“情报”期刊。如《农业图书情报学报》《林业科技情报》《渔业气象情报》《水产科技情报》《测绘科技情报》《国外医学情报》《预防医学情报杂志》《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中国医药情报》《医学情报》《能源情报研究》《建筑科技情报》《科技情报导刊》(通信)《轿车情报》《汽车情报》《地质科技情报》《国土资源情报》《租售情报》《艺术商情》《经济学情报》,等等。上述期刊,特别是其中影响较大的核心期刊,长期支持情报研究,支持情报学人成长,维护情报学学术传统,对“情报坚守”来说,贡献尤其突出。
第三,从人才培养来看,情报学专业虽然退出了本科教学,但是在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从学科名称、学位点名称、学位名称、课程名称、招生简章、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等多方面显示了“情报”的存在。比如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有生物情报学硕士点,设置“战略与学科情报”和“生物情报分析技术研究与情报源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培养具有生物学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专业情报人才。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2021年的专业介绍中显示,“空中交通管理学院”的“交通运输专业”包括三个专业方向:空中交通管制、飞行签派、航行情报。毕业生可在民航系统从事空中交通管制、飞行签派、航空情报服务和机场运行指挥等工作[13]。
第四,以学科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法中设有相关“情报”类目。比如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的G大类“文化、科学、教育、体育”下设二级类目“科学、科学研究”,二级类目下再设三级类目“情报学、情报工作”,最后展开以下四级类目:情报学,情报工作体制、组织,情报机构的建筑、设备,情报资料的搜集、保管,情报资料的处理,情报检索,机器翻译,情报过程自动化的方法和设备,文献复制方法和设备,情报资料的利用,世界各国情报事业等。
第五,科研项目分类中设置了“情报学”类。比如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学科分类表中,单独设置“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大类,代码为21,其中“情报学”代码为TQC。
第六,专业分类中设置情报专业。比如教育部普通本科专业目录中,在管理学一级学科门类下设置“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
第七,学科分类中含有“情报学”类,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简表中,设置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870),其中情报学的代码是87030。
3.4 机构、职业、网站(栏目)命名中对“情报”的不离不弃
尽管一些省级、副省级和地市级情报研究所的名称改为“信息研究院”或“信息研究所”,但仍有不少单位坚持“情报”立场。大部分省级、地市级科技情报学会的名称拒绝“信息化”改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曾经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后来又改回原来的名字。难能可贵的是,在河南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河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后,以它为依托单位的“河南省科技情报学会”却没有随之起舞。郑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立场坚定,没有跟风改名。当然也有个别地市级科技情报研究所,在它的上级科技情报研究所(院)没有把“情报”改名“信息”的情况下,仍然自作主张,擅自改名,令人侧目(比如河北某单位)。据我们的调查,除了拒绝以“信息”取代“情报”进行改名的省级、地市级科技情报研究所(院)外,还有如下一些情报机构拒绝改名,坚守“情报”底线,令人肃然起敬:农科院(科技)情报(研究)所、林业(科技)情报(研究)所、测绘科技情报研究所(站)、气象科技情报研究所(站)、冶金情报研究所、冶金情报标准研究所、工业信息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纺织情报研究所(东华大学)、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医学情报所(中心)、能源情报研究中心、汽车技术情报研究所、国防科工委情报研究所、310所北京海鹰科技情报研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航天科工集团情报信息研究中心(航天六院602所)、航空研究院航空情报研究所、煤炭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中船重工科技情报所(714所)、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中国中铁科技情报中心,等等。
招聘中涉及情报职业,也在不知不觉中坚持了“情报”立场,如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招聘新能源信息情报分析师。在“猎聘网”上,专门设置“情报分析师”专场栏目,广泛招聘涉及数据分析、市场分析、专利分析、投资分析等方面的情报分析师。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岚图汽车分公司招聘工厂情报中心综合质量解析工程师、工厂情报中心冲焊品质(解析)推进工程师、工厂情报中心总装品质(解析)推进工程师、工厂情报中心工程师等。此外,有的网站(及其栏目)名称也显示了自身的“情报坚守”,比如中商情报网、汽车情报网、多多情报通、市农牧业科技情报网、中国科技情报网,雷速体育网设置“情报中心”栏目、永安在线专门设置“黑灰产情报周报”(后改为“黑灰产团伙情报”)栏目。
4 “情报坚守”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4.1 实践意义
“情报坚守”的实践意义首先是提升信息工作的水准,使信息工作向情报尺度、情报标准看齐,即提升信息工作的成色。具体说来,第一,在信息搜集工作中,情报尺度能使信息工作以用户的需求为指针,坚持用户需求导向,在深入调查、研究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的搜集工作,使搜集的信息达到“情报”所要求的有用性(以真实、准确为基础)和有效性(以新颖、及时为前提),提升用户的满意度。第二,在信息监视(信息监测)工作中,情报尺度能使信息监视以“情报监视”为榜样,并借鉴竞争情报的某些做法,加强隐蔽性、刺探性、侦测性和监控性,为此,可以动用多方资源,通过所有关系(渠道),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凭借各类先进技术对监视对象及其环境进行长期、持续、实时的监视,并且不拘泥于“陈法”,不自缚手脚,甚至可以在“底线”边缘打擦边球,在合法与非法不甚分明的“灰色地带”行事。第三,在信息挖掘中,情报尺度能使信息挖掘工作以数据挖掘、大数据挖掘为取向,深度挖掘出其中隐含的新关联、新规律、新结论、新模式,等等。第四,在信息分析中,情报尺度能使信息分析向“情报研究”看齐,向“情报研究”靠拢,或直接以“情报研究”代之,促进信息分析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深入化发展,有利于把信息分析视为“脑力劳动”,把信息分析结果看作是“智慧产品”,提升信息分析产品中的智慧含量,从而提升信息分析产品的质量和应用层次,使信息分析产品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保证信息分析产品的战略性应用(支持战略决策)方向正确,成效长远。
其次,除了以上四点提升信息工作的水准以外,“情报坚守”的实践意义还体现在情报学学科发展和专业建设中,即“情报坚守”能够保持和发展情报学学科和情报学专业,使本来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萎缩的情报学学科(相比其他学科,情报学变成了“小学科”)和情报学专业(退出本科教学,使情报专业变成“无根基”专业,)能够赖以生存和发展。换言之,正是因为学界、业界长期的“情报坚守”,才消除了四十年来社会上对于情报学学科和情报学专业“行将消失”的担忧,也解除了部分情报学研究者、情报教育人员和情报工作者对于“无枝可栖”的生存顾虑。
其三,从思想意识上提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警觉性、敏感性,从而加强对数据、资料、隐私等有关信息的安全保护。人们通常有这样一种心理:获得“信息”感觉上稀松平常(分量不够),或者没有感觉,因为它无处不在,泛滥成灾,但是一旦听到“情报”就觉得事大,会警觉起来,全神贯注,其内心深处的保密意识马上被唤醒,甚至会立即行动起来。也就是说,“情报”将提示信息工作的敏感性和严肃性——对信息工作,尤其是高层次和涉密岗位的信息工作,必须充分重视起来,认真负责,慎重对待,不可轻忽马虎。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民航和交通运输领域(对安全有特殊关切),人们多不愿意以“信息”取代“情报”,不愿意用“信息分析研判”取代“情报分析研判”。因为这样的领域一旦出事便事关重大,人命关天,“信息”会让人误读为情况“轻而缓”,而“情报”才预示着情况“重且急”。
4.2 理论价值
“情报坚守”的理论价值主要是一种“本体价值”而非“他者价值”,即对情报学的存在与发展的“自我价值”,或“自证价值”,具体来说就是维护对情报学理论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的传统“情报话语体系”(当然要发展情报学理论,使之与时俱进,也需要融入“信息话语体系”)。情报学理论有无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既不能靠“外因”(指促进情报学产生与发展的其他相关学科,比如哲学、数学、军事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等等)来证明,也不能靠“利他”(比如与别的学科交叉产生新的交叉学科,或者情报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被别的学科吸收利用从而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等等)来证明,它主要依靠自己证明自己——依靠基于“情报”概念的情报话语体系的动态演进来证明情报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而情报学理论的存在与发展表现在各种情报学著作、期刊论文、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等研究成果上,它们可以看成是不同类型的情报话语体系的文本载体。这样,“情报”概念之于情报话语体系和情报学理论,就是“名”与“言”的关系——名正方能言顺;也是“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报坚守”关乎情报学理论的生死存亡。
5 结 语
“信息扩张”导致“情报”的使用领域不断萎缩。学界、业界的坚守让“情报基因”得以遗传下来。到目前为止,“信息扩张”的势头已经有所减弱,但还没有完全结束,这意味着“情报坚守”仍将持续,不过已经挺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在不同领域,“情报坚守”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有的彻底失守,有的基本盘稳定,有的有名无实或名不符实。现在,“情报坚守”主要存在于图书情报、民航、经济、医药卫生、农林渔业、测绘、气象等领域,这些领域成为动态复杂环境中“情报退守”的最后堡垒。鉴于“情报坚守”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作为学术传人,不必过于担心,因为我们明白,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情报学、情报教育、情报工作中所依赖和维护的情报话语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被“信息扩张”大潮完全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