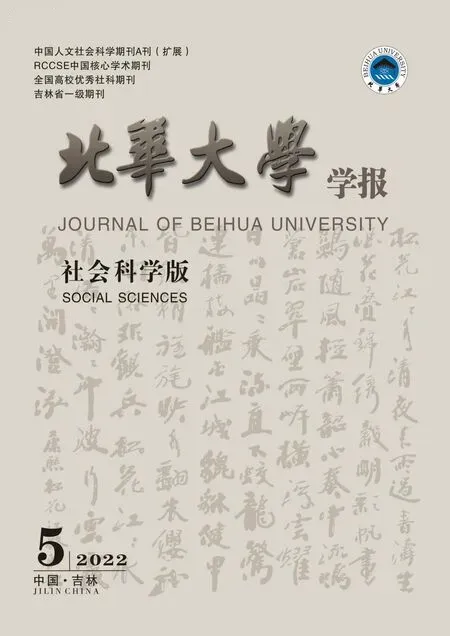一君万民
——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的互生共融
2023-01-09张东
张 东
引 言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王政复古,以国体标榜天皇统治的独自性,同时学习西方宪政,使民参政,历经大正德谟克拉西、政党政治,终在持续扩大的对外侵略中趋向法西斯统治。通常认为,近代日本政治是民众、政党、众议院等民主宪政势力与天皇、枢密院、贵族院、军队等封建保守势力并存与对抗的过程,宪政体制与国体精神作为异质的内容此消彼长。而且对于宪政的考察,通常在于民众参政、政党发展、宪法条文等方面,对于国体的考察,则常在于思想文化或社会史研究之中,如支撑天皇大权的精神力量、蒙蔽民众的教化宣传以及破坏宪政、对外侵略的精神根源。当然,亦有学者从西方政法理论去探讨近代日本的国体,但近代日本的国体并非单纯的政法概念,其包含着社会历史性与伦理道德等,且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表现,因此单以政法概念考察近代日本的国体,不免有脱离历史语境之倾向。
既然说近代日本是基于传统政治而导入宪政,在明确了传统政治与宪政并存的前提下,我们还应知二者何以并存,即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阐明二者的结合点以及结合后权力秩序的特质与趋向。本文认为,近代日本的所谓宪政,是指一君万民伦理道德在政治上得到体现,天皇总揽大权下,采取职能性分权,民众参与立法,大臣辅弼并承担政治责任。其所谓国体,即基于肇国神话与民族性,实现一君万民政治,万世一系天皇作为无上之尊与日常自然的道德表率,保全国利民福。基于此,通过考察明治立宪与国体的互生、大正德谟克拉西与“国体明征”间的关联,明确国体在民众参政中的推动力与界限,辨析天皇统治与民众参政间的吊诡之处,指出近代日本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下宪政与国体互生共融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一、明治立宪与国体的互生
立宪主义产生于西方文明,其思想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如法制、权力制衡、民主等。经过中世纪至17、18世纪启蒙思想兴起,限制王权与注重权力正当性等成为共识,在一切法律和政治之前的个人权利与社会契约说相结合,成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天赋人权、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说等遭遇批判,立宪主义的基础也从抽象的理性演绎转向具体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秩序。明治维新后,日本在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导入宪政,其关键即在于限权并标榜天皇统治的正当性。
1867年12月9日,在萨摩、土佐等五藩藩兵的支持下,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中山忠能、岩仓具视等在宫中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诸事回神武创业之始”[1]148,以复古行维新,废除幕府、京都守护、京都所司代等武家职位,以及摄关、议奏、武家传奏等朝廷旧职,设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翌年1月3日,幕府军与政府军在京都西南郊的鸟羽、伏见相遇,戊辰战争开始。
明治新政府在打破旧制、确立天皇权威的同时,需广泛争取支持、稳定秩序、与外交际。如大久保利通在1868年1月23日提出迁都计划时称:之前天皇只与少数公卿接触,这“有悖为民父母之天赋职责”,“上下隔绝之弊习,未尽敬上爱下之人伦大纲,有失君道、臣道”,因此借迁都之机,更始一新,“除数种大弊,行为民父母之天赋君道”。[2]3月14日,明治天皇率公卿、诸侯等在京都紫宸殿向天神地祇宣誓,发布《五条誓文》。随后在4月27日又公布了《政体书》,实施太政官体制。
1868年12月,明治天皇命令开设公议所:“保全万民,确定永世不朽之皇基,万机应出自公论”[3]。翌年1月25日,岩仓具视上奏称:“(公议所)看似模仿欧美诸国之风,实则不然,我皇国神代既有采取公论”,“施政法度有众议参与,经宸断后实施,即使有异论百出,亦不易变更”,“古之良法美制或不适于今日,则断然弃之”。[1]682-685他认为“君臣之道、上下之分”为建国之体,政体应基于国体并随时而变,明确了天皇亲裁与天下公论共存之意。
对于建国之体,岩仓具视在1870年详论:“天神使天孙降临,神胤统治国土,建万世一系天子统治之国体,亿兆各守其分,定君臣之义,此为天神虑亿万年后、使国土永久安全之意。因此,天子使亿兆各安其业、各得其所,以此为天神尽责。亿兆励行其业、各保其生,以此为天子尽责,是为上下通义。天子爱亿兆,为王者大宝,亿兆尊天子,称御一人,此为我建国之体。”[1]822-832在他看来,“人君体天意,惩恶劝善,不随意发挥威权。天将万民托付于人君,非君之私物”。指出历代勅语中“有‘朕为万人苦心’等残编断简之辞句,是为念苍生之心”,“陛下与他国人君不同,在于服从祖宗之名诫”。并引用池田光政之言:“人君自俭爱民,使国民服从”,若“以锻冶之甲胄、利刃护身,是为浅薄”。因此,“陛下上服祖宗名诫,下听光政之言,察古今治乱,于今政治定有裨益。”[4]
1871年11月12日,岩仓具视作为特命全权大使率团出访欧美。1873年5月,大久保利通提前回国,随后提出制宪意见书,认为君主以命令约束无智之民,只能达一时之治,“一旦暴君污吏擅权,生杀予夺随意而为,众怒国怨归于君主一人,动辄生废立篡夺之变”,应“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至公至正君民不得私”。他认为立宪并不是轻视天皇大权,“外在的天子大权越重,其实权越轻,将门均秉之日,天子在九重之内,威严堂堂,下民仰为神,天子无尺寸之权,一旦亲裁万机,下民拜天而知至尊所在,外在威严半损,人情时势逐渐开明,其势非物理自然人力所能为。今不察此,欲强行外在之大权,天子坐拥空器,不仅与昔时将门秉均之日无异,天位亦将危殆,上定君权下限民权,出自国家爱欲至情,使人君万世不朽之天位安泰”[5]。
可以看出,无论是说君民无隔、君臣之义、君主之天职责任,还是说天子“不重外在大权”,明治政府在树立和强化天皇权威时,亦知天皇“免责减负”方可长久安泰,其途径则是将一君万民伦理道德纳入国体叙述,而系统论述并将此融于宪法的则是井上毅。
对于近代政治,井上毅认为其中一个必然产物是政党:“文明之邦皆有政党,召开议院、分席而坐,相制以呈均势,各党争辩以发现真理”[6]。但他批判政党偏向私利、争夺政权,而且对议会政治表示疑虑:“通过阴险狡猾手段在众议院聚集多数,其议不能称做舆论,此非国会真正多数,非民望之舆论”[7]631。因此他认为政府应在一个全能君主的信任下,“调和社会各阶层利害,避免倾轧,否则国家不固。政府不基于议会、与政党无涉,这样才能增进永久生存之国运”[7]630-632。
当然,井上毅希望天皇成为这种“全能君主”。但问题是,如何使作为“全能君主”的天皇能够持久稳固。在他看来,若要使君主不易被人攻击、否定,就要避免宗教化崇拜。因为“宗教发展常与知识进步相反,随着知识发展,人们不再满足道义之先天空想,倾向于以人事推天道,注重考据,伦理学逐渐向哲理发展。最终社会中产生不信之念,豪杰起而另寻机轴,主张新说排击旧典,宗教遂成退缩之势”[8]。也就是说,如果假借神明来推广某种普世神教,虽可流传颇易、人心归一,但随着人们智识发展,所谓神教也会被质疑,其势不得不后退。因此,不能使“全能君主”与宗教相关联。他转而将目光投向孔孟儒学,称其“远鬼神,务民义,知生不知死,其言布帛菽粟,毫无神怪,没有祻胎,可谓千古卓见”,提出要“以古典国籍为父、儒教为师。”[9]
在他看来,“国法学源于各国古典,今日神学者之说可取之处少,但探立国之本、寻风俗之源,决不可将其束之高阁”[10],即保存国典是立国要务,“以古典国籍为父”。1888年他在皇典研究所演说时称:“国典是国家政治、国民教育之必要,而非宗教之必要,亦非某一政党之素材”,将国典作为宗教理论、或以之攻击其他宗教的话,是“有悖国道之本意”。“国学是属于我国所有人的,精通国典者将之作为自身或自身党派的专有物,将其他党派排除在国典之外,这不仅是量见狭小,且有悖国典本意。”[11]井上毅认为国典、国学有着超越政治与宗教的普遍化性格,试图在国民生活习惯、历史、文学中发现天皇权威与立国之本。
因此,井上毅着力研究国典,终“发现”了日本独特的天皇统治方式,即“皇祖以来的家法”、“皇道之本”。他认为天皇统治方式与中国或者欧洲的统治方式不同,不是把国土和国民作为物质上的私产,这种区别即公私之别,且为“不容歪曲之明文与事实,亦是两千五百年来历史之结果。”[12]133-136实际上,他这里所说的天皇统治方式,并非单纯复古的天皇统治,而是在他对近代宪法的认识基础上的。他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于限制君权、赋予人民立法权、定宰相责任,若宪法不明此义,“(民众)怨恨愤懑,结果或致法国大革命时民众拥立国宪之骚乱”[13]。也就是说,在对近代宪法原则有所认知的前提下,井上毅“发现”了独特的天皇统治方式,从而使西方宪政与日本传统相融合,进而标榜“我国宪法非欧洲宪法之临摹,而是皇祖之不文宪法在今日之发展”[12]133-136。
经过对外考察宪政、对内“发现”传统,1883年9月19日伊藤博文上奏制宪方针:“我国古来万世一系天皇总揽万机,以万邦无比之国体为基础,举经国大纲,明君民分义”[14]。一系列准备后,1886年6月,伊藤博文、井上毅、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等开始起草宪法。几经修改,1889年2月11日“纪元节”,明治天皇颁赐《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其勅语中表示:“我祖我宗赖臣民祖先之协力,肇造帝国,以垂无穷,乃神圣祖宗之威德,及臣民忠实勇武,爱国殉公,成就光辉国史”。“朕及朕子孙将来依循宪法条章而行,重臣民之权利、财产安全,并保护之。”[15]3-5伊藤博文对宪法第一条解释道:“祖宗重天职”,其统治非“一人一家之私事,此乃宪法之依据”[15]11,即君民共守立宪政治与伦理道德。
近代日本在树立天皇权威的同时,以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为其政治之义,皇权有所自制,避免随意发动与专断之失,宪政在此基础上展开。宪政与国体互生共融,宪政因国体而被历史化、正当化,国体亦因宪政而有了顺时进步的“近代化”色彩 ,如伊藤博文所言:“固有国体因宪法而愈益巩固”[15]10。
明治宪法颁布后,藩阀政府主张“超然政治”,以“至公至正”立于议会之外施政,但其“至公至正”在议会多数决议面前显得说服力不足,对议员的争取和笼络更显得切实可靠,政党人士开始入阁,甚至有短暂的隈板政党内阁(1898年6月—11月)。宪政趋向深化,民众要求扩大选举权范围、明确大臣辅弼的政治责任。随着宪政发展,“国体观念非单纯的法律观念,它有远超国法之价值”[16],国体亦愈显其价值。
二、大正德谟克拉西: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
虽然明治立宪与国体互生,但二者并非一开始就充分结合,亦非此消彼长。通常认为,明治末期的民众参政扩大、政党发展以及随后的大正德谟克拉西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同时削弱了保守专制势力,但事实上,此时在宪政发展的表象之下,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与国体精神却得到了强化。
大正德谟克拉西(即大正民主运动)是指贯穿整个大正期(1912—1926),涉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运动与思潮,以“打破阀族、拥护宪政”为口号,民本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一战之后,与世界革命风潮相呼应,普选成为其政治目标。大正德谟克拉西是民众对藩阀专制、政治特权的批判与反抗,要求确立责任政治、将民意更充分地反映在政治当中。如德富苏峰所说,“只有赖国民之力,得其奉戴,皇室才能安泰,其尊荣与天壤无穷”[17],此时,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为民众参政提供了正当性,宪政发展亦被视为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天皇统治。在打破藩阀专制、反对政治特权之后,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天皇统治与持续扩大的民众参政相协调,而这一过程则呈现出了其特质——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
大山郁夫认为,社会生活不是理性的产物或契约的结果,而是出自人类原始本能的社交性,注重伦理关系、同类意识与共同利害等心灵上的冲动以及家族与民族等血统意识,“物质需求应置于心灵需求之下,政治应服从于伦理”[18]。在他看来,反抗权威、否认特权之后,“如果没有东西来替代它们,社会则趋向解体”[19],希望德谟克拉西能够成为替代权威与特权的社会结合力、伦理之力。室伏高信亦认为:“现在应摆脱对法国大革命的憧憬之心、对英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赞美之情”,理想的德谟克拉西是“从个人到协同、从权利欲求到自我牺牲”[20],抛却个人的利己欲望,才能实现机会平等与真正自由。
相比个人价值,大正德谟克拉西更关注社会秩序,这反映在政治制度上,便是对代议政治的怀疑。如浮田和民提出:“我们必须尽快摆脱对议会的讴歌与空想,无意义的代议政治绝不能使德谟克拉西获得创造性发展”[21]331-332。通过对一战时各国的观察,他认为“即使是在民主主义国家,政治也是以国家为绝对目的”,“立宪君主制混合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长处,取舍了共和制的优缺点。我国体千秋万古如泰山之安、磐石之重,即在于国民养成立宪精神与宪政运用”[21]331-332,他以伦理道德、国家主义来牵制代议政治。
大正德谟克拉西论者是将国家作为内部没有利害对立、浑然一体的共同生活体,强调秩序、伦理道德与国家主义,山川均批判这是“在砂石上构建德谟克拉西”[22]。在普选与民本主义,大正德谟克拉西的这一特质表现得至为明显。
(一)普选与天皇统治的结合
一战爆发后,日本出现了“成金”风潮,物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1918年8月,富山县爆发“米骚动”,民众积极展开普选运动。而政党最初认为民众智识水平尚低,不宜过早实施普选。但随着一战后世界革命与民主化风潮的到来,以及日本民众对藩阀专制和政党腐败的不满等,政党转而支持普选。
在当时诸多普选理由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天皇统治中引申出的普选正当性,其代表人物便是国体论者上杉慎吉。上杉慎吉从1916秋开始鼓吹普选,他认为日本的选举制度造成了民众缺乏民族主义意识,应尽快开展普选,“使国民参与议员选举,保障国策运行,这也是举国一致的重要条件”[23]。而且,他认为政党“毫无节操,唯利是图,愚弄国民,失去了立宪政治的本质”,通过普选“扫除那些把政权作为私欲、阻碍国家发展、国民幸福之势力,实行公明政治,鬼魅魍魉无处容身”[24]53,使“亿兆国民之真心能够充分反映在天皇那里,国民之心日益同体”[24]125-126,普选被视为天皇统治的应有之意。
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两大旗手——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支持普选,但同时都反对以天赋人权作为普选的理由。吉野作造认为,“主权在民是绝对的或哲学上的民主主义,理论上将权力归于人民,它是对国家本质的抽象性思考”,也是“我国所不能容忍的危险思想”,其“缺点已被充分认知”。[25]他认为天赋人权论主张绝对自由平等下的生存权及劳动权,早已失去了理论根据,普选应有新的理由,即“国家乃个人集合体,我们在经营国家上要有积极责任,参政权就是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分担。”[26]
美浓部达吉亦毫不吝惜对普选的批判,认为国民间的精神联络构成了国家单一体,“同时代的国民有共通目的、单一体之自觉,不同时代者之间亦然”,“无论强弱,任何国家皆如此。”[27]而普选在“理论上并非正当、实际上亦非最优”,国民主权、天赋人权论已被认为是“根本错误的”,“人有天赋平等之权利,这是违反天赋性质的,个人天生的能力与见识极不平等”,“不应将哲学理论作为普选根据,今日各国的普选绝非基于此空论。”[28]
也就是说,近代日本的普选与天皇统治一致融合,而非对立。其普选不是指个人独立下的权利伸张和意志表达,而是基于共同生活体性质的政治职责,公务色彩浓厚。个人意志被消解在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之中,参政的民众越多,天皇统治则越显稳固。
(二)民本主义中民众的缺失
民本主义是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主要指导思想,其基本内涵即是施政为民。事实上,大正德谟克拉西论者在高唱民本主义的同时,普遍对民众智识表示怀疑。河上肇认为:“舆论政治绝不是众愚政治,国家方针不应由多数众愚决定,而应基于少数贤者的无私判断”[29]。大山郁夫亦认为:“自古以来,民众运动必须要有伟人指导,若没有强大组织力和统帅力的伟人指导,民众的希望终将落空,民众也会从乌合之众而走向骚乱”[30],即便是被视为最具立宪性的吉野作造,其民本主义亦是如此。
吉野作造认为,“政治上的绝对自由并非使君主真的自由,而是以君主大权之名行贵族政治跋扈之实,这会导致人们对贵族政治的不满累及皇室,危害国家前途”[31]57。他认为,国体“不只是法律上的主权在君,更是道德上君主与人民间微妙的情谊关系。尊崇皇室为民族之宗,使国民精神以皇室为中心实现团结,这是我国独有的、冠绝万国之特长,正因为此,我国君主作为主权者地位才最巩固”[31]57。因此在他看来,民众参政并不会根本上冲击到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民本主义与国体并不相悖,且更能强固国体观念。因为,“形式上说,立宪政治是国民舆论支配政治家,但实质精神上,它是少数贤者指导国民”。理想的立宪政治便是“少数贤者指导国民精神,君主立于之上,成为道德感化的中心,其地位、人格受国民尊崇”。“若(君主)滥用法律地位,干涉细微政治问题,卷入政治漩涡,决不能维持其尊严。君主不轻易使用法律地位,常事依于人民,则是一种趣意”。[31]55-56
也就是说,即便是立宪政治下,多数民众仍需要有见识和能力的少数贤者作指导,“若政界被众愚盲动所支配的话,国家就不可能健全发展”,“政治上的民本主义与精神上的英雄主义浑然一体,宪政之花才能绽放”,“缺乏指导的平民容易陷入盲动和革命暴虐,从而使国家涂炭苦难,如革命时期的法国,或者无节操的众愚被少数奸雄操纵利用,国民全体利益受到蹂躏,如现在的墨西哥”,[32]50-53“若国民接受伟大精神的指导,并且能够体会其精神的话,就可以实行有民众监督的政治,这才是健全的民众政治。”[33]而且,在吉野作造看来,民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民众对所有政治问题都要有积极的独立意见,直接参与国政的人向民众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政见,以征求民众支持,而民众在聆听各方主张后冷静判断,被动地判断各方政见就可以了。因为“只要具备了一定教育和普通常识,任何人都可以作出判断,民众不必就每个问题都有自己独自的积极政见”[32]49。吉野作造虽以舆论政治为重,但其舆论政治非在于民众自身。他强调多数民众与少数贤者的调和,以及少数贤者处于实质性的支配地位,民众处于被动位置。
表面上看,大正德谟克拉西要求扩大民众参政、确立责任政治,主张普选,这有助于政党发展、推动宪政深化,但在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下,民众参政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由此被导向天皇统治,造成了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山川均认为这是“德谟克拉西的烦闷”[34]。而正是这一烦闷,使大正德谟克拉西与随后的“国体明征”运动、法西斯统治有了连通之可能。
三、宪政危机的克服与“国体明征”的吊诡
在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参政并释放出政治能量,当有政党或其他政治势力疏导这些政治能量并承担其政治责任时,可使天皇统治趋于安泰、国体得到维持。但在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下,妨碍君民一体的政治势力会受到批判和质疑。当国体精神强化、宪政与国体充分结合,这种批判和质疑会更强烈。但是,若没有政治势力承担责任,一君直面万民,民众参政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会强烈冲击天皇统治,使宪政与国体遭遇危机。这一吊诡在大正德谟克拉西之后愈加明显,并在“国体明征”运动前后达到了高潮。
1924年6月,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组阁,近代日本终迎来政党政治期。翌年5月实现了普选,选民人数激增至1 240万人左右,约占总人口的20%。然而仅8年时间,以1932年“五一五事件”(1)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海军少壮派军人为主发动政变,袭击首相官邸、警视厅、内大臣邸、政友会总部以及东京周边变电所等,犬养毅首相被杀。为契机,政党政治便告结束,由于选举腐败,政党、议会受到强烈批判,宪政遭遇危机。随后5月26日,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举国一致”内阁。
面对“举国一致”的长期化趋势,曾支持政党内阁的美浓部达吉明确反对政党组阁,否定政党组阁的能力,主张强化内阁制度,避免行政决策受内阁频繁更迭的影响。1932年10月,他提出:“议会并不直接施政,而是通过支持或打倒内阁来间接影响政治。宪政中真正的中心势力是内阁而非议会,宪政是否良善在于内阁组织是否健全”,“将来宪政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内阁制度,净化议会、修改选举制度、保障官吏身份等都是次要问题”。[35]20
美浓部达吉把宪政分为政党内阁和非政党内阁两种形式,在政党政治结束后,他认为只能组成非政党内阁,但非政党内阁的最大弱点是缺乏议会的支持,因此内阁常以不正当手段与政党妥协,这会导致政界堕落。那么,“挽救其弊的唯一途径是政党抛却政权之念,基于批判地位而公正监视内阁施政。只要内阁无大局错误,政党即应给与援助”。因此,他希望此时“政党抛却政权之念,援助内阁,协力救国,这样才能使政治安定”[35]28-29,进而提出了由政党、军部、实业界、劳动者代表组成的“圆桌巨头会议”构想,以此确立财政政策。
美浓部达吉之所以提出“圆桌巨头会议”,这与他的明治宪法解释密切相关。他认为“国民不能构成统一意志,不能以自己意志将权利、权能委任给议员。选举仅止于选定何人为议员,而非委任权能之行为。议会权能是由宪法而获得的,非由他人授权”[36]347-348,议会依据其自身意志行使权能,独立决议,不受他者约束。在他看来,议会决议在国法上被视为国民意志,但这“并不是说已经存在的国民意志通过议会来表达,而是说议会决议在国法上被视为国民意志。国民本身没有意志能力,只有通过议会,国民才能成为国法上的意志主体”[36]348-349。因此,“选举与代表之间无任何法律上的直接关系,议会不只代表选民。即使议员不是由全体国民选出,仍无妨其代表国民”,“通过选举产生出代表关系,这只是政治理念而非法律观念”。[37]只要有议会存在,无论任何情况下,国民意志都会在国法上得到表达,从而使政治有了立宪性,内阁与议会内多数的关系如何,就不再是重要的了,这也就为“圆桌巨头会议”提供了正当性支持。
也就是说,为了克服政党政治结束后的宪政危机,美浓部达吉提出了“圆桌巨头会议”。然而,此时日本已实施普选,有更多的民众参政,“圆桌巨头会议”与议会内多数无关,其组阁的正当性仍会受到质疑。为强化和维持“圆桌巨头会议”的正当性,就需要强化推荐首相的人——即元老、重臣的责任,而这种强化政治特权的倾向与大正德谟克拉西精神有些相悖。而且,大正德谟克拉西要求民意充分反映在政治当中,实现君民一体,但美浓部达吉以法定权限解除来自于民众的政治压力,这无疑是对民众政治力的压抑和冷却,使天皇统治在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上的政治免责与担保受到削弱,有隔离君民之嫌。
1935年2月18日,陆军中将议员菊池武夫在贵族院会议上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为“叛逆思想”,“破坏了金瓯无缺之皇国国体”。[38]随后,民间右翼团体和在乡军人会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运动。4月23日,在乡军人会本部发布《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解释的见解》,强调“全体国民以天皇为中心,浑融一体,国家乃永久发展之生命体”[39]。为平息事态,冈田启介内阁在8月、10月先后两次发布“国体明征”声明。
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国体明征”运动,正是在承续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脉络中对美浓部达吉展开批判。例如,山崎又次郎批判美浓部达吉只看法律关系而忽视了政治性权力:“(国家法人说)作为脱离事实的概念论,从法与正义出发,但实际上却往往无视和破坏法与正义”[40]93-94。“国家内部有非常复杂的利益关系,它是多种利益团体相结合的复合体”,因此“政治性权力是必要的”,由此“从国家整体上增进个人或团体的安宁福祉”。[40]77-79
究其实质,“国体明征”运动欲使宪政与国体完全一致,以一君万民来克服宪政危机。里见岸雄认为:鉴于日本国体,“天皇大权不是游离于道德、民族、社会、国民精神的一纸法文、一条权力,只以法律不能全面完整地理解天皇大权”[41]363。因此,“在社会爱的基础上,基于日本国体的构造,天皇与臣民通过命令服从、统制扶翼、指导奉教、慈民归一、祈祷报恩等精神而一致实施政治行动,其中心便是天皇政治。从道的观念来说,即皇道政治,从国体上说,即国体政治”[41]363。亦如中谷武世所言:“国体是派生和发现一切法、制度、组织、法律、典章的原理与法源,因此,日本的宪法学、国法学及国家学都应是国体学”[42]。1938年12月,国体明征派召开时局协议会,标榜“纯正的护宪运动”:“宪政是天皇统治之大道,亦是皇运扶翼之臣道规范,显扬肇国本然之日本主义”,“帝国议会作为政治运行机关应恪遵于此,通过立法预算翼赞宏谟,作为臣道躬行之神圣殿堂”,“日本主义扫荡功利主义,充分发挥议会、行政、司法机能,政治与国体相合,才能实施国策、打开局面,谋得国民生活安定”,因此,“基于日本主义才能确立宪政”。[43]
可以看出,美浓部达吉与“国体明征”运动都欲克服宪政危机,也都反对政党政治,希望政府决策不受议会内政争及民众压力的影响,谋求强力内阁。但二者有根本区别,美浓部达吉主张强化内阁及元老、重臣的责任,将议会作为法定国民代表机关,仅止于监督地位。“国体明征”则欲通过国民对天皇的情感、一君万民伦理道德来解释宪法,强调全体国民的辅弼之责,议会成为连接君意民心的通道、实现国体精神的首要辅弼机关。如佐藤清胜所说:“天皇之心即臣民之心,臣民之心也就是天皇之心。天皇与臣民是同一生命,同心一体”[44]。
“国体明征”欲实现一君万民政治,积极恢复民众对议会的信心,实则是为强化天皇权威,为内阁提供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号召民众参政,最终也只是对民意的压抑与无视。然而,如上所说,随着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与国体精神的强化,君民更趋一体,二者不再是单纯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而是亲密无间的,天皇成为公平无私之存在,没有“私意私欲”。这样一来,任何个人、政治势力都可能成为妨碍君民一体的“幕府”“奸侧”,原本欲求广泛民众支持的强力内阁亦会受到批判,越多民众参政,对内阁的这种批判力就会越强。但如果缺少政治主体承担责任,“万民”参政(辅弼)所生发出的政治能量会冲击“一君”,“不逞之徒趁此间隙,虽口称‘万民翼赞’,实则违反宪法、紊乱朝宪,甚至有变革国体之可能”。[45]因此,实现一君万民政治,需有承担责任的政治主体。而无论任何人或团体作为这种政治主体,都有可能被批判为“幕府”“奸侧”,这一吊诡在随后的大政翼赞体制中充分表现了出来。
1940年8月28日,近卫文麿首相发表新体制构想:“超越自由主义下的多元性政党政治,其本质是举国性的、全体性的和公共性的”,是“公益优先的超政党国民运动”,“不允许部分的、对抗的和竞争性的政党运动”。[46]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近卫文麿首相出任总裁。由于《大政翼赞运动规约》规定其总裁与首相一致,议会及舆论批判大政翼赞会有“违宪嫌疑”。1941年1月的第76回议会(又称“翼赞议会”)上,议员对其人员构成、宪法地位及其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鉴于此,近卫文麿内阁不得不在1941年4月2日改组大政翼赞会机构,废止了政治性强的政策局、企划局及议会局。
1941年10月16日,现役陆军大将东条英机组阁。翌年2月,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成立了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实施“推荐选举制”。随着“东条独裁”的强化以及战局的走向,右翼团体批判东条英机内阁有悖君民一体国体精神,例如中野正刚表示:“天皇非以严法酷罚号令民众的专制国皇帝,而是长期苦心志、劳身骨、磨圣德、冒艰险,成为躬行实践的人格模范”;“以‘非常时’为借口,通过行政抹杀政治力,使社会丧失活力、民众沉沦,这决非日本传统的指导精神。”[47]10-121944年1月末,近卫文磨等重臣开始倒阁运动,7月22日,东条英机内阁辞职。
结 语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积极塑造天皇权威,同时为其“免责减负”,将一君万民伦理道德纳入国体叙述,国体与宪政互生共融,民众参政有了持续扩大之可能,并采取职能性分权与大臣辅弼。随着宪政的深化,大正德谟克拉西反对藩阀专制、政治特权,在天皇统治与普选、民本主义相融合的过程中,却造成民众的缺失与国体精神的强化。经过8年短暂的政党政治期,1935年“国体明征”运动承续大正德谟克拉西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使宪政与国体充分融合,强化议会沟通君意民心的机能,实现一君万民政治并欲克服宪政危机,但随后展开的大政翼赞体制充分显示出一君万民政治的吊诡之处。
从争取政党政治到反对政党组阁,近代日本的宪政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表现,其基本内涵则是皇权自制,使民意反映在政治之中。同时,从穗积八束到美浓部达吉、再到“国体明征”运动,近代日本的国体在不同阶段亦有不同表现,其基本趋势则是伦理道德与政治权力逐渐融合。其宪政与国体并非对立,而是在一君万民伦理道德下互相支撑。吊诡的是,欲达成宪政,需有政治主体来承担责任,但随着一君万民伦理道德的强化,任何政治主体都可能被批判为“幕府”“奸侧”,这就使宪政难以维持。如果没有宪政、缺乏政治主体连接君民,天皇将直面万民参政之冲击,被暴露在政争与决断面前,国体亦将处于危境。所谓一君万民伦理道德,它既是近代日本宪政与国体之基础,又在内部对二者有所破坏,一君万民之理想得到的却是无君无民之混迷,民众充分参政的结果却是权力对民众自身的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