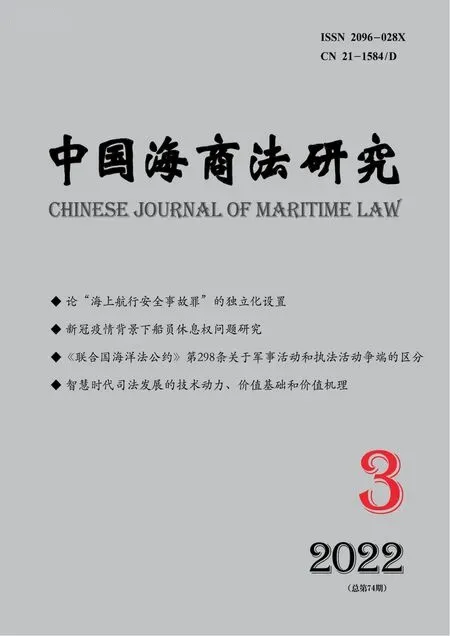中国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识别研究①
2023-01-09安寿志申钟秀
安寿志,申钟秀
(1.武汉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承运人的识别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确定关系重大。然而,海上货物运输中常存在光船租赁、融资租赁、定期租船(及其变种航次期租)和航次租船等复杂的租约链,装货港代理“为和代表”(for and on behalf of)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提单,提单内容的记载不规范等情形,导致对承运人的识别存在一定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第78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这些规定指明了对于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提单下的承运人的识别应依据提单的规定进行,但并未对承运人如何识别进行规定,这导致中国司法实践中对承运人的识别不一致。在《海商法》启动修改的背景下,笔者拟对中国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识别的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和分类,归纳分析不同的识别方法和识别路径,并对这些识别方法涉及的理论问题及其利弊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海商法》修改提出若干建议。
一、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的主要方法与识别路径
对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有助于减少价值论证的任意性,发挥法律的规范性与预测性作用(1)实证分析法属于法律实证主义类别,源自以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为奠基人的现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或者先验的思辨,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之内。但在法律实证主义中,又逐渐发展出分析(实证)法学、纯粹法学、语言学(实证)法学等各种具体方法与派别。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14-115页及第117-129页。。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为索引进行搜索,共查询到132个相关案件;一一筛选后得到11个案例(2)这些案例皆是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关于海上运输合同纠纷的二审和再审判决或裁定,由于这些判决中已提及原审法院的判决情况,故对于原审判决不再另行列出。。此外,天津海事法院在2021年12月作出的5个系列判决皆认定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这5个案例(3)具体案号为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414号民事判决书、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415号民事判决书、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416号民事判决书、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558号民事判决书。还未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笔者选取其中一个案例作为实证分析样本。这些案例表现了中国司法实务中对承运人的主要识别方法及识别结果,简要说明如下。
案例一:“上风国际有限公司与韩进海运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海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提单持有人签有航次租约,但有权依据提单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为由提起诉讼。提单由装港代理代表船长签发,船长由光船承租人雇佣并代表其行使职权,光船承租人应被识别为承运人。
案例二:“久鸿贸易会社与兴联(香港)海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在没有租约存在的情况下,提单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托运人有权依提单记载识别承运人。二审判决仅以涉案船舶已经被期租为由,认定光船承租人并非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提单由船长签发并加盖载有光船承租人英文名称的船章,承运人应首先推定为光船承租人。
案例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与广西鸿晨投资有限公司、SHL海运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民终6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提单为船长授权签发,可视为承运人签发。据《海商法》第7条“船舶所有权,是指船舶所有人依法对其船舶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登记所有人应认定为承运人。
案例四:“先锋出口公司等诉奥迪塞斯航运贸易公司等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11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期租合同约定,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和船员,负责船舶航行和内部管理事务。除出租人事先另有明确声明外,船长签发的提单,应当视为代表出租人签发。授权装港代理限于根据大副收据的记载签发提单,这是出租人与装港代理之间的内部协议,与对外签发的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无关。出租人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
案例五:“山东省新迈特五金矿产有限公司等诉天联运输有限公司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纠纷二审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民终64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提单经船长授权签发,提单记载有承运人名称,应据此识别承运人。
案例六:“运输商贸服务股份公司等诉卡蒙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93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定期租船合同约定承租人或其代理被船舶所有人授权代表船长和/或船舶所有人按大副收据签发提单,正本提单未及时到达卸货港时承租人可凭保函放货。提单系代表船长签发,船长系船舶所有人雇佣并代表其行使职权,船舶所有人应识别为承运人。
案例七:“西蒙航运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岚山支行等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694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对于定期承租人在没有实际授权情况下签发不正确的船舶所有人提单是否约束船舶所有人的问题,定期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和船员,并由船长直接控制船舶,船长通常应知晓提单签发情况,船舶所有人应承担承运人责任。
案例八:“徐州恒大食品有限公司、正利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424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提单抬头载明承运人名称,提单签发栏打印文字为“Signed for the Carrier XXX by...As Agents for the Carrier”,签单代理人中创物流签单章载明文字为“Signed as Agent for Carrier of B/L Title”。提单抬头载明的承运人为承运人。
案例九:“达顺航运有限公司、弘远控股有限公司海事海商纠纷二审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42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签署栏内容明确是以船长代理身份签发提单,非以定期承租人代理身份签发提单。船长授权装港代理代表本人签发提单,船舶所有人是提单下的承运人。
案例十:“旺程有限公司与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天津海事法院(2021)津72民初41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船舶所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订立航次期租合同时提单持有人明知航次期租承租人的存在,提单持有人并未参与航次期租合同的签订,无法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来识别承运人,承运人的识别应以提单本身记载为据。案涉提单由装港代理代表船长签发,船长系受雇于船舶所有人,船舶所有人应为承运人。
案例十一:“山东翔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北方航运有限公司等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530号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识别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需重点考察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首要法律依据是《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关于承运人的定义。期租合同通常约定承租人负责揽货经营货运业务并签订运输合同,相应地出租人同意承租人签发提单,船长签发提单又未载明承运人名称的,一般应将定期承租人识别为承运人。
案例十二:“申特钢铁(香港)有限公司、福建省海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二审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终92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提单载明“代表船长签发”即证明船舶所有人是承运人不符合《海商法》第72条的规定,《海商法》第42条规定承运人是指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船舶所有人未与提单持有人订立合同亦未签发提单,不是运输合同项下之承运人。
在上述12个案例中,有2个案例将定期承租人识别为提单所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10个案例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识别为提单所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这些司法实践形成了以下几种承运人识别方法。一是提单文义识别方法。二是特殊的识别方法,包括:从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识别承运人;从接受无单放货保函的主体识别承运人;从作出提货指令的权利主体识别承运人。在前述两种方法仍不能识别承运人时,则适用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识别承运人(4)司玉琢教授于2021年9月18日为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旺程有限公司的系列案件出具的关于承运人识别的法律意见将中国司法实践和航运业务中的承运人的识别方法归为三大类,即“通常的识别方法”“特殊的识别方法”和“推定的识别方法”。。
(一)提单文义识别方法及其识别路径
此方法也称通常的识别方法,其识别路径为:依提单记载事项的“文义性”(5)中国有学者认为这是提单有价证券的特性,并提出提单制度的独立性以及提单权利的证券化。参见李学兰:《论提单权利证券化》,发表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61-65页。,将该提单记载或签署内容中的承运人直接识别为承运人,具体包括以下方式。第一,依据提单抬头识别承运人,通常是根据提单正面是否有“承运人”名称记载,如有,以此来识别承运人。第二,依据提单的签发人识别承运人,由承运人签发或者船长、代理人代表记名的承运人签发,在这种情况下,承运人的身份是明确的,也很容易识别。第三,以提单背面承运人的定义或者相关规定加以识别,如“承运人识别条款”等约定(6)对于提单背面的承运人定义或“承运人识别条款”,中国学者将此类条款视为规避、减轻承运人责任的条款,不承认其效力。参见司玉琢:《海商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118-120页。。中国法院对提单文义识别方法下的识别路径,即按提单抬头记载、提单上的船章内容、提单签署内容识别承运人未存分歧。前述案例二、案例五、案例七以及案例八皆适用此路径进行识别。如在案例五中,虽然船舶所有人抗辩称,其未参与提单签发,对提单的签发过程及提单记载内容完全不知情,提单上记载其为承运人是货方和第三人强加的,对其没有约束力;但法院认为,只有在依据提单记载和签署的内容无法识别出承运人的情况下,才存在借助其他资料辅助识别承运人的必要性,因此将提单记载的承运人识别为承运人。在案例八中,法院同样是根据提单抬头载明的承运人以及提单签署的装港代理“作为提单抬头承运人的代理签发”,将提单抬头载明的承运人识别为承运人。
(二)特殊的识别方法及其识别路径
当采用提单文义识别方法不能识别谁是承运人时,法院常采用特殊的识别方法,结合运输合同的磋商、订立和履行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认定究竟谁是提单所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承运人。这些特殊的识别方法包括:从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识别承运人;从接受无单放货保函的主体识别承运人;从作出提货指令的权利主体识别承运人。具体分析如下。
1.从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识别承运人
《海商法》第72条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提单可以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承运人是签发提单的主体,对于托运人而言,签发提单是承运人的义务,签发提单义务是运输货物的对价之一(7)对于承租人而言,如果他向出租人交付了货物,要求出租人签发提单,出租人也有签发提单的义务,只是此提单不是运输合同的证明,但仍是货物收据和提货凭证。。对于托运人之外的人,如收货人或者提单持有人,签发提单则是承运人的法定权利,即只有承运人有签发提单的权利,因为他要对托运人之外的人承担法定义务(8)《海商法》第95条规定:“对按照航次租船合同运输的货物签发的提单,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的约定。但是,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据此,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签发了提单,对不是承租人的提单持有人也要依照提单的记载和约定承担责任。。
第二,承运人可以授权包括船长在内的他人签发提单,但不改变承运人作为签发提单主体的地位和义务,也即签发提单的权利源自承运人。在租船运输中,出租人应承租人的要求也会签发提单,此提单在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不是运输合同的证明,只是货物收据和提货凭证,即使提单中有并入租船合同的条款,也并不改变出租人和承运人之间的租船合同关系。但是,当提单流转到第三人手中,依据《海商法》第95条的规定,该持有人与签发提单的出租人(即承运人)便建立起提单合同关系,可见,对于承租人之外的第三人,有权签发提单的人就是承运人。因此,中国司法实践中常从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识别承运人,即看“谁授权签发提单”,并根据“代理说”“控制说”或“雇主责任说”,查明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于船舶所有人,据此认定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
此种方法的识别路径为:先根据《海商法》第72条第2款规定的“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得出船长或代表船长签发的提单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再根据载货船舶的船长是被授权签发提单,以及船长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雇佣或聘任并代表后者行使职权等,查明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于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并进而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认定为承运人。如在案例二中,法院认为,期租合同仅约束当事人,不能对第三人(提单持有人)产生效力。承运人的识别仍应根据提单签发的情况来进行。提单为运输合同的证明,若其由船长签发,则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交付货物的托运人(即实际托运人)有权依据提单记载识别承运人并向其主张权利。该提单由船长签发,并加盖了载有光船承租人英文名称的船章,光船承租人应当首先推定为承运人。在案例九中,船长根据定期租船合同的约定向定期承租人在装港的代理出具签发提单的授权书。后定期承租人要求定期出租人拆分原提单以换发两套新提单,并向定期出租人出具保函。装货港代理未征求船舶所有人及船长的意见,仅根据定期出租人的指示将原提单换签成案涉提单。法院认为,案涉两提单签署栏显示“装货港代理作为XX轮船长的代理”,并非以定期出租人的代理的身份签发提单。两套新提单系船长授权他人签发,船舶所有人是案涉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在案例七中,装货港代理提单签署栏载明“as Owner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of XX”。法院认为,提单签署栏的签署内容使用了“作为船舶所有人”(as Owner)而非“作为承运人”(as Carrier),船舶所有人作为定期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船员,并由船长直接控制船舶,船长通常应知晓装货港代理签发提单的情况,船舶所有人应承担承运人责任(9)此外,案例七的判决表明无论定期承租人有没有实际授权船长签发内容不正确的船舶所有人提单,都不影响船舶所有人的承运人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法院适用提单文义方法识别承运人。。
2.从接受无单放货保函的主体识别承运人
《海商法》第71条规定,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故在货物交付环节,承运人应是接受提单持有人(10)当提单持有人主张提货时,即成为有权提取货物的收货人。提交正本提单并据以交付货物的主体。承运人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承担着交付货物的风险。所以,接受无正本提单放货保函的主体应该是承运人,而提货人向承运人提交保函是承运人规避无正本提单放货风险的救济措施,与其利益息息相关。故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案涉相关运输合同下的放货(卸货)保函受益人作为识别承运人的途径。在航运实务中,接受无单放货保函的受益人又分为以下情形:提货人出具的无单放货保函中的受益人是船船所有人(或定期租船合同的出租方);保函虽然是针对卸货出具的,但保函所针对的风险仍是受益人在未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卸载至码头可能带来的风险。在部分码头(尤其是货主所有的码头),货物卸载后船舶所有人无法有效控制货物,该风险与“无正本提单放货”的风险是类似的。此外,此类保函通常还要求“当担保人获得正本提单后,应立即将正本提单提交受益人”,而有权收回正本提单的主体亦应是签发提单的承运人。在此种情况下,提单项下的承运人应是船舶所有人,而不是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承租人。换言之,如若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承租人是所涉提单项下的承运人,则应是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承租人负有向收货人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在此情形下,保函的受益人应指向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合同的承租人,而不是船舶所有人,保函中也无需约定保函出具人在收到正本提单后将提单交于船舶所有人。如在案例六中,定期租船合同约定定期承租人或其代理已获得船舶所有人授权,代表船长或船舶所有人严格按照大副收据签发提单以及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法院认为,定期租船合同约定无正本提单放货条款以及保函正本应交给船舶所有人,表明在卸货港放货环节,船舶所有人对无正本提单放货有控制权和决定权,定期承租人需听从船舶所有人的指示行事,并负责追回相应的正本提单,船舶所有人应被识别为承运人。
在航运业务操作中,中国港口的提货流程一般是由收货人在承运人指定的船舶代理处凭借正本提单换取提货单(Delivery Order,D/O)或“小提单”,而提货单或“小提单”则是由承运人指定的船舶代理签发。随后,收货人凭借上述提货单(且对进口货物而言,还需海关在提货单上加盖放行章)前往货物堆存的场站提货。这一提货流程实质上反映了承运人是作出提货指令的权利主体,与承运人是签发提单的权利主体相呼应,通过提单的签发和收回,完成了其履行运输合同的义务。换言之,当提货单是由船代公司在卸货港签发,由于在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下,只有签发提单的承运人才负有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义务,也应由该承运人发出指令签发提货单以完成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履约行为,即只有该承运人才有下达此项指令的权利。基于此,根据船代公司签发提货单这一事实可查明船舶所有人应是提单所涉海上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如若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承租人是所涉提单项下的承运人,则应是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期租承租人或者他们在卸货港的代理公司向收货人签发提货单和履行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义务,而不是船代公司向持有提单的收货人签发提货单。
(三)推定承运人识别方法及其识别路径
当依据提单文义识别方法和特殊的识别方法仍然不能识别谁是承运人时,法院适用推定原则,推定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除非船舶所有人提出相反的证据,即只要货物装在船上,便推定该船登记船舶所有人是承运人,推翻此种推定的举证责任即转移给该船舶所有人,除非该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该船已经光船出租,并指出光船承租人的名字与地址,或者直接证明谁是真正的承运人。光船承租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推翻此种推定。此种方法的识别路径为:在提单未记载任何承运人信息时,推定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如果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能证明定期承租人或其他第三人与提单持有人存在运输合同,则承运人应为定期承租人或其他第三人。在此方法下,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仅证明存在定期租船合同还不能达到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法律效果,其必须进一步证明定期承租人或其他第三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案例二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法院认为,光船承租人仅以其与定期承租人签订期租合同的事实证明其并非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并无证据证明定期承租人与涉案提单记载的托运人具有运输合同关系。在没有证据证明托运人(也即提单持有人)与他人存在运输合同的情况下,根据提单由船长签发并加盖载有兴联公司英文名称的“吉盛”轮船章的事实,应当认定提单持有人与光船承租人构成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二审判决仅以涉案船舶已经被期租为由,认定光船承租人并非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11)在案例二中,法院进一步认定光船承租人江苏兴联公司与青岛广亚公司签订的期租合同中有关提单签发的约定,仅在期租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并不能对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亦不能成为兴联公司免除其对外责任的依据。。
此外,案例十一推定定期承租人为承运人。法院认为,识别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的首要法律依据是《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关于承运人的定义。第72条第2款的立法主旨是原则性否定将有关船长签发的提单视为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的立场,其所针对的典型情形主要是定期租船经营方式下提单的签发。定期租船合同通常约定由定期承租人负责揽货经营货运业务并签订运输合同,相应地定期出租人同意定期承租人签发提单,因此,在船长签发提单而又未载明承运人名称时,一般应将定期承租人识别为承运人。但是,定期承租人的推定是错误的,该推定以船长签发提单代表承运人,排除代表船舶所有人和光船承租人为前提条件,实际上,船长代表承运人签发提单并不当然排除承运人就是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该推定方法的前提条件不成立,结论错误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方法涉及的理论问题分析
除天津海事法院的5个系列案件的判决为一审判决,是否生效仍待观察外,上述案例中的11个案例均为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生效判决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或审监生效判决,但目前都不属于中国的指导性案例或典型案例(12)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建立了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典型案例见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典型案例发布栏目,访问网址:www.court.gov.cn/zixun-gengduo-104.html。,是否具有类案作用需进一步分析。首先,类案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这些案例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相似性(13)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将待决案件与检索结果进行相似性识别和比对,确定是否属于类案。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案例七和案例九是两个典型例子,在这两个案件中船舶所有人皆向法院提交了案例十一的判决以支持其关于定期承租人才是承运人的主张,但法院认为该案例中所涉事实及争议法律问题与待决案件不完全一致而未予采纳。其次,案例二和案例十一明显存在法律适用分歧,虽然都采用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但推定的路径不同,导致得出的结论不同,未起到“确保法律正确统一适用”的效果(14)对于此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的实施办法》第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各业务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各专门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与执行过程中,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当向审管办提出法律适用分歧解决申请:(一)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之间存在法律适用分歧的;(二)在审案件作出的裁判结果可能与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或者标准存在分歧的。”。但是,对这些案例的比较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案例表明各法院在依提单文义的识别方法无法识别承运人的情况下,按照特殊的识别方法和推定承运人识别方法的路径不尽一致,并涉及以下两个理论方面的问题。
问题一:能否仅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规定的承运人的定义来识别承运人?这不仅涉及如何适用《海商法》第78条第1款规定的“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还涉及是否可仅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来识别承运人,以及《海商法》第72条第2款的立法主旨是否原则性否定将船长提单视为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
问题二:推定承运人识别方法和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识别方法,特别是后者下的雇主责任理论有何本质不同?这进一步呈现为对载货船舶船长签发提单的身份的认定问题,即船长签发的提单到底是船舶所有人的提单还是定期承租人的提单?与之相关联的问题是:是否需要进一步根据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识别承运人,即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最终源于船舶所有人对船长的雇主责任或控制,还是源于定期承租人的指示?定期承租人的指示的最终来源是来自船舶所有人和定期承租人之间的定期租船合同的约定,还是来自定期承租人自己作为承运人的意图?在定期承租人未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并在提单上载明其作为承运人的信息时,此种单方面的意图或指示能否约束对定期租船合同内容不知情的提单持有人?
(一)能否仅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规定的承运人的定义识别承运人
《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关于承运人的定义与《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简称《汉堡规则》)第1条第(一)项关于承运人的定义并无实质上的不同。根据该定义,“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据此,有学者认为中国采取的是“承运人提单制度”,提单签发人和承运人视为同一人。[1]亦有司法实践认为《海商法》试图通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来解决承运人识别问题,不同于英国法下的“船东提单主义”,而是借鉴《汉堡规则》下的“承运人提单主义”,并具体体现在案例十一中。但是,如果仅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或“承运人提单主义”来识别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并将《海商法》第72条第2款的规定视为具有“否定将船长签发的提单视为代表船舶所有人的立场”的立法目的,这不仅忽视了《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第71条“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单证”两种法律关系的区别,还会存在逻辑上、文义上和商业需要上的问题。
不可否认,我们在发展中也走过一些弯路,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无论成功的案例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值得我们总结的,都可以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逻辑上的问题。首先,按照《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定义,谁与提单持有人订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谁就是承运人。但是,对于通过贸易合同或银行流转获得提单,甚或是通过赠与等获得提单的人,其没有与任何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如果以是否订立海上运输合同作为承运人识别的首要法律依据,显然会存在逻辑前提上的错误,即按照此路径,无论是船舶所有人还是定期承租人,都无法被认定为承运人,因为这些人都没有与提单持有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院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此采取推定承运人方法,以“定期租船合同通常约定定期承租人负责揽货经营货运业务并签订运输合同”(案例十一)或者“船舶运输货物的行为与船舶所有人不必然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联系”(案例十二)为由,推定定期承租人为承运人。但这仍然无法解答定期承租人没有与提单持有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这一事实问题,并错误地排除了载货船舶的船长可能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提单的情形。其次,当提单项下货物的租约链中涉及多个定期租船合同时,《海商法》第136条规定了定期承租人有权就船舶的营运向船长发出指示,第137条规定了承租人可以将租用的船舶转租,转租后原租船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影响。因此,若定期租船合同没有相反约定,定期承租人都有权就船舶的营运向船长发出指示,在此种情形下,就会产生哪个定期承租人应被识别为承运人的问题。实际上,案例十一中,“相应地出租人同意承租人签发提单”透露了推定承运人在逻辑上的问题,即定期承租人签发提单的权利(包括授权船长签发提单)实际上来源于定期出租人(即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的同意。
第二,文义上的问题。从文义上看,《海商法》第72条第2款的两句内容分别有不同的含义。前一句明确规定“提单可以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承运人有自己签发提单的权利,非承运人的第三方签发提单须经承运人授权。二是承运人是谁没有明确,可能是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也可能是定期承租人。后一句内容为“提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其中“视为”一词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被当作一个通俗意义上的用语,具体含义为“认定为”。该词一般被认定为用来表达的是一种法律拟制,[2]其本质是立法者基于特定价值或政策考量并根据实际需要,将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事实予以相同的法律评价,使其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3]据此,对于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提单,立法者将其“认定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因此,后一句内容整体上有两层含义:一是解决实践中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提单的约束力问题,即认定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并约束承运人。二是当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授权船长签发提单时,船长签发的提单是代表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签发;当定期承租人授权船长签发(自己的)提单时,定期承租人是承运人。此外,拟制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即拟制中的两事实性质不同,立法者是处于明知状态的,[3]换言之,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提单和承运人签发提单这两个事实的性质是不同的。承运人签发提单的性质是明确的,即承运人自己签发提单;但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提单的性质可能是不明确的,因为载货船舶的船长可能是根据定期承租人的授权签发提单,也可能是根据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的授权签发提单,甚至是在没有人授权的情况下签发提单,但无论是何种情形,立法者仍基于法律经济性的考虑以及这些事实构成要件的相似性而“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因此,从《海商法》第72条第2款内容的文义上看不出该款的“立法主旨是原则性否定将有关船长签发的提单视为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的立场”,该款只解决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的提单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的问题,而不具有排除哪一方被认定为承运人的立法目的。
第三,商业需要上的问题。在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今天,在提单未载明任何承运人信息,以及在使用简式提单或康金1994格式提单(CONGENBILL 1994)的情况下,如果要求作为非托运人的提单持有人查找到提单项下的货物涉及的租约链中的每一个承租人,以及查找到船长或装货港代表的提单签发授权是由谁出具的,并非易事。甚至即使在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可能也无法查清所有的租约链关系或船长或装港代理的提单签发的授权来源。这显然不符合商业上的需要,还会导致提单持有人可能因无法找到承运人而无法行使提单相关权利,或者提单持有人不得不想方设法以侵权之诉起诉所有相关当事方并由此产生多个侵权之诉,并不可避免地增加提单持有人的举证责任。尽管法律确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相对独立性,但法律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及社会需要。商法以效益价值为首要价值目标,而无论是交易自由,还是交易公平、交易秩序等最终都是服务于效益价值之实现。[4]如果对于交易程序及方式的规定过于繁琐、僵化,势必会影响交易效率和增加交易成本。在国际贸易和航运活动中,正如杨良宜先生所述:“在一连串的买卖过程中,要最后买家查找原始托运人或原始卖家,有时是不可能的;……所以,1855年《提单法》第一节规定:‘提单中所载明的每一收货人和每一提单背书受让人,根据或通过这样的托付或背书获得提单中所述的货物的所有权的,应转移获得所有的诉讼权利’。”[5]此外,《德国商法典》第518条(缺乏承运人信息时船舶所有人的地位)规定:“如果由船长以及任何其他有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提单的一方,签发提单没有标明承运人,或在所述提单标注了某个并非承运人的人为承运人,那么提单中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应移交至船舶所有人而非承运人。”[6]
综上,不能仅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定义来解决复杂的承运人识别问题。承运人的识别需重视第78条第1款的价值,根据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仅为承运人和托运人;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是一种由第78条第1款规定的提单关系。这就使得对于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另一方,即承运人的识别,不能仅依据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进行,否则将混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这两种法律关系的区别;而且,即便是在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下,提单所证明的只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不能证明提单持有人是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当事人。此外,虽然《海商法》第72条第2款并未解决具体承运人是谁的问题,但也不能就此认为该款仅是对于定期租船合同下的提单签发方式的规定。该款对于承运人的识别同样具有指引意义,即在明确船长是代表承运人签发的同时,将承运人指向船长背后的人(船长代表的人或者给予船长授权的人),尤其在提单持有人不是托运人的情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二)推定承运人与签发提单权利来源下的雇主责任的本质有何不同
对于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中国法律并无关于推定的概念性规定,[7]在中国法理上存在“提证责任转移说”“证明责任转移说”“证明责任倒置说”“规范区分说”“权利区分说”“反驳区分说”“诉讼权利变动说”等学说。[8-14]通说认为推定分为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前者是指法律明文规定当某一事实被证明存在就应当据此推导出另一事实的存在,后者则是指法官在诉讼活动中依据一定的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的推定。[15]2019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10条较为粗略地概括了这一制度,即对于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以及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这一规定中的推定本身是一项证据制度,[16]而不是有关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制度。承运人的识别是要在有关事实的基础上查明和认定谁是提单下货物运输的承运人。而且,事实上的推定根源于经验法则,且其后果是转移完整的证明责任,[17]即需要在已知(或已被证明)的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法则推测另一事实。这其实也是一种“证据裁判规则”(15)中国有学者认为“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让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可以解决事实真伪不明困境,但其前提是当事人举证能力充分且均衡,这在司法实践中恐怕只是一种应然的理想状态。非以客观真实为依托的证明责任规则的冒然适用会冲撞社会实质公平正义的底线。”参见卞建林,李树真,钟得志:《从逻辑到法律——推定改变了什么》,发表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第35页。。[18]
此外,《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规定了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法条释义强调,法官在运用《民事证据规定》第9条(2019年修正的《民事证据规定》调整为第10条)进行推定时应当满足如下要件:仅当待证事实无法用其他证据规则予以证明、基础事实必须被证明是真实、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具有必然联系(也即所运用的经验法则真实可靠),以及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19]但是,实务中航运业务情形复杂多样,提单等运输单证签发和记载内容不规范,承运人规避风险的情形十分常见。同时,一些航运企业兼营货运代理和无船承运人业务,混淆货运代理人与承运人身份,一旦提单记载或签署内容没有承运人的名称信息时,提单持有人仅凭提单的记载内容来查找谁是承运人几乎不可能,其唯一能确定的信息是载运船舶的信息。因此,在提单未载明承运人的情况下,《鹿特丹规则》第37条第2款规定:“……货物已装上指定船舶的,推定该船舶的登记所有人为承运人,除非该登记所有人能够证明运输货物时该船舶处于光船租用之中,且能够指出该光船承租人及其地址,在这种情况下,推定该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或,船舶登记所有人可以通过指出承运人及其地址,推翻将其当作承运人的推定。光船承租人可以按照同样方式推翻将其当作承运人的任何推定。”在这种推定模式下,由推定为承运人的登记船舶所有人举证谁是承运人,要比托运人举证谁是承运人来得更公平、公正和容易,而且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也是基于各方对提单作为物权凭证以及承运人凭正本提单放货基本原则的合理信赖,这是提单票据性的基本要义。但是,从法律效果来看,采用推定承运人有一个明显的弊端,即对于同一船舶同一航次中不同票货物签发的不同提单,可能存在认定承运人结果不同的问题。
货物索赔的根本在于使承运人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对于推定承运人的识别路径而言,各国学界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依靠托运人寻找承运人,即“索赔人应当从托运人而不是注册船舶所有人入手,证明谁是真正承运人的责任应当施加于托运人一方,因为运输合同是经其处理的”。[20]但此种路径存在的问题是:托运人难以在复杂的租约链关系中找到承运人,最终持有提单的索赔人与原始的缔约托运人之间可能存在多个中间贸易方,作为FOB卖方可能根本无意牵涉运输合同中,等等。[21]19而且,认为承运人无法识别问题的源头在于托运人不审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这方面的例子是2007年生效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简称UCP600)中要求多式联运单证,海运单,空运单,公路、铁路和内陆水运单据必须表明承运人(indicate the name of the carrier)(16)参见UCP600第19a(i)条、第20a(i)条、第21a(i)条、第23a(i)条和第24a(i)条。,但由于租船合同提单下承运人的复杂性,UCP600将租船合同提单作为唯一的例外(17)参见UCP600第22a(i)条。。二是推定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船舶所有人与承运人直接或间接地打交道,几乎没有船舶所有人会在不知道谁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同意将货物装上自已的船舶进行运输,而且其往往从使用其船舶从事运输的承运人那里获得某种保证。这一路径是将本属于承运人的责任通过立法技术转嫁到船舶所有人身上,因此允许船舶所有人提供真正的承运人的信息或者证明船舶处于光船租赁状态以推翻该推定。这也是《鹿特丹规则》所构建的注册船舶所有人可反驳的推定责任的合理性,但学者也认为《鹿特丹规则》中的该制度尚新,需待司法实践进一步考察其合理性和可行性,[21]24且该公约能否生效,目前尚不可知,即使生效,其效果如何也还有待观察。[22]因此,如何确保中国各法院在相同的案件类型中适用相同的盖然性和经验法来推定承运人是个重大的命题。在《海商法》没有规定推定承运人的情况下,应限缩事实推定之适用,并将此概念限定在法律推定的框架内,[23]并且应当是在采用提单文义的识别方法和特殊的识别方法仍无法识别承运人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
对于签发提单权利来源识别方法下的雇主责任,在海上运输中,船长是受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雇佣或聘用,主管船上行政和技术事务的人。[24]船长作为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聘任的人员,基于公司的利益,对于货物的运输和交付负有妥善照看的义务,以及在装货后负有妥善签发提单的义务。同样,在海上运输期间,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也信赖于船长对船舶的管理和控制。即使在定期租船合同下,如果定期租船合同中有关于提单签发以及凭保函无正本提单放货的约定,船长需按照这些要求和指令行事。因此,在船长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船舶所有人被认定为承运人。[25]这是英美判例法发展出的“实际联系”标准,并被视为船舶所有人承担承运人责任的构成要件,[26]即:一是物权下的实际联系,即因船舶所有人占有控制船舶推定船舶所有人与货物运送之实际联系,这与案例三依据《海商法》第7条有关船舶所有权的规定认定登记所有人为承运人的识别路径相同。二是债权下的实际联系,即因船舶所有人签发运输单证、因代理人行为产生替代责任的债权标准推论船舶所有人与货物运送之实际联系。加拿大的泰特雷教授(William Tetley)亦认为,海上货物运输实际上是船舶所有人和船舶承租人之间的一种共同冒险行为,他们应同时作为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27]
中国的司法实践常采用雇主责任来查明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进而识别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在案例四中,法院根据期租合同约定的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和船员,负责船舶航行和内部管理事务,指出除非出租人事先另有明确声明外,船长签发的提单应当视为代表出租人签发。即使出租人一直声称授权装港代理限于根据大副收据的记载签发提单,但这是出租人与装港代理之间的内部协议,与对外签发的提单记载的托运人无关。因此,出租人(船舶所有人)是涉案海上货物运输的承运人,应当根据提单的记载对托运人承担承运人责任。在案例七中,法院认为,对于定期承租人在未实际授权情况下签发不正确的船舶所有人提单是否约束船舶所有人的问题,由于定期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和船员并由船长直接控制船舶,船长通常应知晓提单签发情况,船舶所有人应对案涉提单承担承运人责任。在案例六以及案例十中,法院皆认为船长系船舶所有人雇佣并代表其行使职权,船舶所有人应识别为承运人。需指出的是,雇主责任并不是法律上逻辑推理的产物,它是社会公共政策考虑的折衷物,是利益衡量与法律逻辑冲突协调的结果,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28]《海商法》第51条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十二)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但该条规定的是承运人雇主责任,并不当然是船舶所有人雇主责任。
由上述分析可知,推定承运人和签发提单权利来源识别方法下的雇主责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的前提条件和顺序不同。推定承运人是在采用提单文义的识别方法和特殊的识别方法仍无法识别承运人的情况下才考虑适用,并在已知(或已被证明)事实的基础上,运用经验法则推定另一事实,且分为事实上的推定和法律上的推定;雇主责任是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识别方法下的一种识别路径,在采用提单文义的识别方法无法查明承运人的情况下即可适用。
第二,法律本质不同。推定承运人是一种“证据裁判规则”;雇主责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海商法》第51条规定的一种替代责任,其归责基础有“支配说”“重大影响说”以及“控制理论说”。
第三,举证归责不同。推定承运人是一种推定的责任,允许推定的不利方提出反证证明其不是承运人;雇主责任则是一种法定的替代责任,不允许不利方提出反证证明其不是承运人,此外,《海商法》下的承运人雇主责任还是一种不完全过错责任,承运人可以援引《海商法》中规定的免责事由进行抗辩。
第四,法律效果不同。推定承运人受已知的事实和经验法则的影响,推定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在同一船舶同一航次中签发的不同票货物的提单下可能存在承运人结果不同的问题;雇主责任下的承运人是确定的,即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存在“类案不同判”的问题。
三、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方法的利弊分析及对《海商法》的修改建议
(一)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方法的利弊分析
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承运人识别方法是中国法院近三十年来逐渐积累的,它们丰富了中国承运人的识别路径,与此同时存在一些利弊。
案例三中依据《海商法》第7条船舶所有权规定的识别路径的实质是将船舶所有人推定为承运人。《海商法》第7条的船舶所有权的规定是对船舶物权下的所有权的定义,在中国的民事法律关系下,一方对于物的所有关系或者占有关系并不能当然地使其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根据《民法典》,只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主体为才能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18)《民法典》第13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第13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因此,《海商法》第7条的规定不能作为承运人识别的法理依据,否则将导致“以物识人”。
案例一、案例六、案例七中的雇主责任识别路径对承运人的识别具有直接的法律效果,适用了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识别方法,即船长签发提单的权利来源于聘任或雇佣他的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但是,《海商法》第51条只规定了承运人雇主责任,没有解决船舶所有人的雇主责任问题。
案例二、案例十一和案例十二运用了推定承运人识别方法,案例二的价值在于明确了被推定为承运人的光船承租人仅举证证明存在定期租船合同是不够的,还需证明提单持有人和定期承租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案例十一和案例十二以定期承租人通常负责货物运输的经验法则推定其为承运人是错误的:一方面,忽视了“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之间的区别,即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是《海商法》第78条第1款规定的提单关系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不能用《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来识别提单关系下的承运人;另一方面,排除了船长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发提单的情形,事实上,当承运人就是船舶所有人时,船长签发提单代表的承运人就是船舶所有人(19)前文述及的天津海事法院在2021年12月作出的五个系列案件的判决中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这五个案件中,船舶所有人皆向法院提交了案例十一以支持其关于船舶所有人不应被识别为承运人的主张,法院指出虽然船舶所有人主张案外人航次期租承租人与船舶所有人之间存在航次期租合同,但船舶所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在订立该租次期租合同时提单持有人明知航次期租承租人的存在,不能仅依据国际贸易合同中约定的价格条款为FOB就必然认定提单持有人与航次期租承运人签订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在提单持有人未参与船舶所有人主张的海上货物运输航次期租合同的签订的情况下,无法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来识别承运人,案涉提单为船长签发的提单,船舶所有人应识别为承运人。。
(二)对《海商法》下的承运人识别的修改建议
交通运输部2020年1月7日向国务院呈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送审稿)》(简称《修改送审稿》)。《修改送审稿》新增了第89条,专门制定了承运人识别规则(20)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对承运人有不同记载的,以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的记载为准,除非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的持有人为托运人。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未明确记载承运人的,依照下列情形认定承运人:(一)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或者明确记载货物已装上船舶的,推定该船舶的所有人为承运人,但是船舶所有人证明船舶已经以光船租赁、光船租购或者融资租赁形式出租以及承租人的名称和地址的,推定该承租人为承运人;(二)前项船舶所有人或者承租人证明第三人为承运人及其地址的,该第三人为承运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人证明承运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基本上是吸收借鉴《鹿特丹规则》第37条的规定,采用“单证载明—推定(船舶所有人)—证明—再推定(光船租赁、光船租购或者融资租赁人)—再证明(第三人)……”的多重推定模式。但是,该模式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起草《鹿特丹规则》时,对于“推定”这一立法模式本身就存在不同意见,最大争议在于推定承运人条款如何构建。[29]第二,未明确推定承运人的证明程度,根据法理上的“举证责任转移说”,推定的过程是举证责任的转换过程,当推定的结果对甲方当事人有利时,法院应允许乙方当事人举证反驳,直至原推定结果不成立。[8]换言之,推定的承运人若想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推定,除了提供光船租赁合同或者定期租船合同及承运人的地址外,还需证明该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21)例如案例二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二审判决仅以涉案船舶已经被期租为由,认定光船承租人兴联公司并非涉案货物运输的承运人,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三,推定和再推定的多重推定方式不符合法律上的效率(efficacy)原则,这种多重推定方式将明显加重提单下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造成提单权利行使的困难,影响提单在国际贸易中的票据性功能。第四,无法解决审判实务中的“类案不同判”问题,即对于同一船舶同一航次多票货物签发多份类似提单时,如果推定的承运人在一案中选择承认推定事实但在另案中选择反驳推定事实,则可能产生承运人识别结果的不一致。
无论是《汉堡规则》中的“承运人提单主义”还是英美法中的“船东提单主义”(22)英美普通法下存在对物诉讼制度,在对物诉讼制度下,不需要区分谁是运输合同的承运人,因为载运的船舶本身就可被视为责任主体。参见郭瑜:《海商法的精神——中国的实践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00-107页。,承运人识别问题归根结底是提单持有人如何识别提单下的货物运输的承运人问题。托运人如果与承运人签订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则不存在承运人的识别问题,无需依赖提单的规定来识别承运人。而对于未签订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提单持有人则不同,其必须依赖提单的规定来识别承运人,即“以单识人”;而签发提单又是承运人的义务,所以以提单出自谁手或者提单是经谁的授权而签发来识别承运人是最有效的路径。如果拘泥于“以人识人”或者“以物识人”,即按照《海商法》第42条第(一)项的承运人的定义或者第7条的船舶所有权来识别承运人,则会存在逻辑上的不自洽或者法理错误,其根本问题是脱离了提单的生成这一基本事实问题。因此,单纯的“以人识人”或“以物识人”无法解决承运人的识别问题。只有在“以单识人”仍不能识别承运人,或者没有签发任何单证的情况下,方可采用推定承运人,但应该推定登记船舶所有人或者已登记的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再则,推定承运人是对承运人采取一种对特定事实的拟制,即当民事关系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或事件而处于不确定或不完全确定的状态,而从已知事实又无法确定时,根据已知事实或经验法则拟制一定的事实,从而使民事法律关系得以确定。此种拟制实际上造成了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的法律效果,应允许被推定为承运人的人举证反驳,直至原推定结果不成立。但是,推定的目的是为了使民事法律关系得以确定,按照《修改送审稿》第89条的多重推定模式,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民事法律关系是难以确定的,这阻碍了提单权利的行使,影响了法律的效率价值。应限定推定的次数或明确推定不利方的反证程度,即推定不利方仅证明存在定期租船合同还不能达到推翻其为承运人的法律效果,须进一步证明定期承租人或其他第三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存在运输合同方可达到推翻推定的法律效果。而且,应当是在采用提单文义的识别方法和特殊的识别方法仍无法识别承运人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
此外,从各国立法例的比较来看,德国法采用法定的方式,直接规定提单必须载明承运人的信息,如果没有载明或者载明的“承运人”不是承运人,则船舶所有人应承担承运人责任(23)参见《德国商法典》第518条。。英国法则采取“雇主理论为原则,定期承租人明确表示为例外”的方式,除非提单“有效、清楚”地载明定期承租人为承运人,否则,船长和为船长签发的提单下船舶所有人(如存在光船租赁,则为光船承租人)应为承运人。提单由船长签署的,由于船长为船舶所有人的雇员,船舶所有人应为承运人(24)参见Turner v. Haji Goolam [1904] A.C. 826,Wehner v. Dene [1905] 2 K.B. 92,Limerick v. Coker (1916) 33 T.L.R. 103。;船舶为光船租赁时亦是如此(25)参见Baumwoll v. Gilchrest [1892] 1 Q.B. 253,[1893] A.C. 8,Sotrade Denizcilik v. Amadou Lo (The Duden) [2009] 1 Lloyd’s Rep. 145。。这同样适用于尽管提单不是由船长亲自签署,而是在租船合同或其他合同中授权代理“为船长”签署的情况(26)在The Rewia案中,Leggatt L法官认为:“为船长签署的提单不能成为租船人的提单,除非合同是单独与租船人签订的,而且签提单的人有权代表租船人而不是船舶所有人签署。”参见The Rewia [1991] 2 Lloyd’s Rep. 325,另见Tillmanns v. Knutsford [1908] 1 K.B. 185,Wilston v. Andrew Weir (1925) 22 Ll. L. Rep. 521。在The Starsin案中,英国上议院认为提单背面的“承运人条款”甚至“光船条款”不能超过提单正面记载的承运人。即关于承运人识别的问题应该在提单正面找,而不是在背面的小字上,应更重视当事各方特别选择的字句,特别注意构成签名的一部分的措词,而不是重视印刷表格的规定。参见Homburg Houtimport B.V. v. Agrosin (The Starsin) [2004] A.C. 715,[2003] 1 Lloyd’s Rep. 571,reversing [2001] 1 Lloyd’s Rep. 437,restoring [2000] 1 Lloyd’s Rep. 85,The Flecha [1999] 1 Lloyd’s Rep. 612。有些提单未载明“光租条款”或者“承运人条款”,是由定期承租人授权明确代表定期承租人签署,或者定期承租人本人无条件代表自已签署,则定期承租人是承运人。参见Harrison v. Huddersfield SS. Co. (1903) 19 T.L.R. 386,另见The Okehampton [1913] P. 173。Paterson,Zochonis & Co.v. Elder Dempster案和Samuel v. West Hartlepool案中也有类似的裁决,即提单上有定期承租人的名字,由船长签字,这时定期承租人为承运人。如果提单持有人实际收到了船长无权代表船舶所有人签字的通知,则提单下承运人的一般原则不适用于提单持有人。参见The Paterson,Zochonis & Co.v. Elder Dempster [1924] A.C. 522,The Samuel v. West Hartlepool (1906) 11 Com. Cas. 111,Manchester Trust v. Furness [1895] 2 Q.B. 282,539,The Hector [1998] 2 Lloyd’s Rep. 287。。也即,在英国法下,如果提单由船长签署,则认定提单是船长作为雇员签发的,对船舶所有人有约束力;提单即使是由代理人“为船长”签发,不论该代理人是依租约授权还是依据其他授权,承运人仍为船舶所有人。对于视为定期承租人提单的情况,必须是在提单中“有效、清楚”地标明定期承租人为承运人。而对于何为“有效、清楚”,应依据提单抬头的“名称”、提单签署的内容、手写打印的优于印刷的基础事实进行识别。英国法和德国法虽然采用不同的识别模式,但以异曲同工的方式解决了承运人的识别问题。
中国多式联运的快速发展使海上货物运输方式、主体、责任期间变得更加精细复杂;船舶建造及交易与金融相融合,使船舶物权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都要求法律制度具有更强的针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27)参见交通运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说明》,访问网址:https://xxgk.mot.gov.cn/jigou/fgs/201811/P020181106615908705167.docx。。中国法院已有提单文义识别方法、特殊的识别方法和推定承运人的识别方法等司法实践,对中国的贸易和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商法》修改应在这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扬弃,明确几种承运人识别方法的顺序,并避免《修改送审稿》第89条的多重推定模式下的提单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基于上述分析,建议将《修改送审稿》第89条第2款修改为:“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未明确记载承运人的,依照下列情形认定承运人:(一)按照提单签发的权利来源、接受无单放货保函的主体以及做出提货指令的权利主体认定承运人;(二)在适用本条第一款和本款第一项仍无法认定承运人的情况下,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由载货船舶的船长签发或者明确记载货物已装上船舶的,推定船长作为船舶所有人的雇员签发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船舶所有人为承运人;但是船舶已经以光船租赁、光船租购或者融资租赁形式出租并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登记的,推定船长作为光船承租人的雇员签发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光船承租人为承运人;(三)前项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证明定期承租人或者第三人与运输单证或者电子运输记录持有人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该定期承租人或者第三人为承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