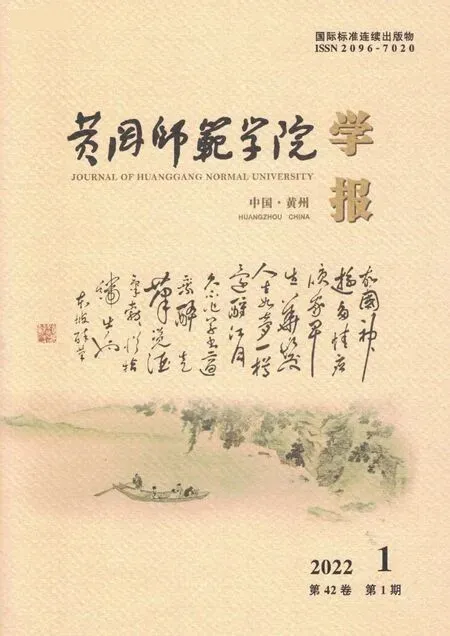从《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看黑塞对中国文化的转向
2023-01-06李玉箫
李玉箫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审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十九世纪末,德语文坛掀起一股“李白热”的风潮,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纷纷改写李白诗,或从其中寻求灵感,这一热潮直到二十世纪初仍未衰退。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作为一名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德语作家,其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东方元素,其小说《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①,既是世纪之交“李白热”催生的产物,也反过来丰富和拓展了“李白热”。
张佩芬在《黑塞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中收录的节译版《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的题解中指出,“一些德国学者认为克林格梭尔-李白的原型为梵高,而诗人-杜甫②正是黑塞自己”,并强调“‘下沉’是全书象征性主题”[1]140。莫亚萍在论文《“李白热”中的狄奥尼索斯——黑塞之传承与转型》则将克林格梭尔和李白的形象割裂开,认为前者作为“替罪羊”代替黑塞死去,后者代表黑塞的理想[2]。
在小说中,“李太白”既是克林格梭尔醉酒时的自称,也是其幻想中的化身之一。倘若对比现实中的黑塞和李白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亦可以看到克林格梭尔之死的情节与李白之死的传说构成了巧妙的互文关系。这些都表明,克林格梭尔这一形象既与作为其化身的“李太白”不可分割,也同在当时备受德语作家追捧并为黑塞所景仰的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赫尔曼,其形象中寄托着黑塞对未来的思考。在这篇“带有虚拟精神自传性质”[3]6的小说中,“克林格梭尔-李太白”代表了黑塞对欧洲传统的幻灭,“赫尔曼-杜甫”则预示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皈依。
一、世纪之交的“李白热”:李白印象的形成
1862年,法国汉学家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翻译出版了《唐代诗歌选》,这是欧洲首个唐诗选集[4]。1867年,诗人戈蒂耶(Judith Gautier)出版了带有强烈再创作倾向的中国诗歌选集《玉书》(LeLivredeJade)③,1873年,伯姆(Gottfried Boehm)据此出版了德语改译本[5]283。首部直接从中文翻译为德文的中国诗歌选集是福尔克(Alfred Forke)选译的《中国诗歌盛期佳作》,迟至1899年才面世[6]。在德理文与戈蒂耶的译本中,李白的诗歌都占有突出的地位,随着这两个译本的广泛流传,李白也为欧洲文坛所发现。
在德国,当时的大部分读者不通中文,多是借助法译本或其德语转译本来认识中国诗歌。对于他们而言,“中国诗歌”中的“中国”二字所提供的仅仅是由异域身份而带来的神秘色彩,实际上他们所面对的是经过了再创作而产生的法文诗或德文诗,即德语读者在阅读中始终处在自身熟悉的欧洲文化里,并未真正直面另一种文化。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反作用于译者与作者,对其在翻译与创作中的倾向发生影响。1905年,海尔曼(Hans Heilmann)发表了翻译中国诗歌集《中国抒情诗:从公元前12 世纪到当代》(ChinesischeLyrik:vom12.Jahrhundertv.Chr.biszurGegenwart),这一在德语文坛引发轰动的译本仍然是转译本[4]。而当德语作家试图改写中国诗歌或从中寻求灵感时,也完全是从欧洲文化出发的。
由于德语文学中有“颂酒诗”的传统,李白诗中关于狂歌痛饮的内容自然地吸引了作家们。德默尔(Richard Dehmel)1893年发表的诗作《中国饮酒诗》,名为改写自李白《悲歌行》的前半部分,实则依据的是德理文的法译本《悲伤的歌》,次年,他又创作了应和此诗的《我的饮酒歌》。1906年,德默尔又发表了三首改写而成的诗作:《遥远的琉特》《同盟中的第三者》和《春醉》[5]295,分别对应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月下独酌》和《春夜洛城闻笛》,所依据的是此前海尔曼(Hans Heilmann)的转译本。霍尔茨(Arno Holz)在1898年的诗集《幻想者》中提及李白时这样写道:
圆碗中酒在打转。
琉特鸣响。
从我们心中
欢呼出一支不朽的歌
属于李太白![5]284
直至1916年,他仍对李白念念不忘,在这一年的《幻想者》中,不但再一次称颂李白,而且将《春日醉起言志》改写为诗集中的一个部分。李白常常描写的月亮也为德语诗人所喜爱,尤利乌斯·哈特(Julius Hart)与德默尔都对《静夜思》做过改写[5]289,294-295。在改写中,德语诗人有意识地取消原诗中的中国文化特征,向其中增添欧洲的文化元素,并舍弃了中国诗歌的形式。
于是,在世纪之交的德语文坛,“李白热”以矛盾的状态出现:一方面,李白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被一代作家视为精神偶像,另一方面,在这一热潮中,李白及其诗歌呈现为“欧化”的面目,其中国文化的含义被抹去。读者对中国文化浅尝辄止的猎奇心理的确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但究其根本,“李白热”的出现与当时欧洲的整体社会氛围密切相关。身处在工业文明的阴影下的人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出口,而孕育了工业文明的欧洲文化是难以提供这一渠道的,这就迫使欧洲作家转向外部,在异域文化中寻找新的话语。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工业文明为欧洲社会带去的物质上的进步,令人们忽视其文化中的缺陷,无法平等地看待当时在物质上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的文化,更不可能主动地借助东方文化反思自身。
李白在一部分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洒脱不羁、放浪形骸、藐视权威的姿态,恰好契合了德语作家内心所渴盼的慰藉和理想,从而引发了再创作的风潮。而这些德语作家只是借李白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无意去认识中国古代诗歌的全貌,也无意去了解李白及其诗歌中的其他方面。德默尔在书信中坦言:“众所周知,中国诗歌的结构样式根本不能用任何欧洲语言来复现。……我把李白不同诗歌中的母题并作一处,同时,意义和感情内容也大大改变。”[5]297在另一封信中,德默尔又说“李太白的诗,我知道的有几十首,不想再多了解了”,并表示“要把这个古代中国人改造成新人”[5]298。
克拉朋特(Klabund)于1916年出版了诗集《李太白》,在后记中,他将李白形容为“永恒的醉汉”“永恒的神圣浪子”和“神圣的流浪者”,并将李白之死的传说重述为一个通往仙境的梦幻故事[4]。这种描述可以被视作对世纪之交的“李白热”中李白形象的总结。在这一热潮中,李白纵酒、纵歌、纵游的一面被放大、夸张,受到追捧和崇拜,而其任侠、隐逸、求仙、求仕和苦闷等方面则被忽视,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也被淡化。
二、《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黑塞对李白形象的深化与拓展
小说《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写作于1919年夏季,收录于192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中。黑塞在其中对李白的化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化用意象,化用诗句,化用形象。三种化用都紧扣“下沉”这一主题。
“酒”与“月”这两个意象,在李白诗中极为常见,在“李白热”风潮中备受青睐,在这篇小说中也随处可见。“酒”的意象贯穿整篇小说,可以被视作克林格梭尔的生命源泉。他对艺术、情感乃至整个生活的体悟都是借助与酒相关的活动来表达的。美好的诗句于他而言等同于美酒,读诗犹如饮酒。游乐时的醉酒象征着他享受生命的欢乐,迷狂时的醉酒象征着他痛苦时的挣扎,小说的最后,克林格梭尔“洗澡,刮脸,穿上新衬衫和外衣”[7]515,一反平日里醉汉的形象,预示着他的生命即将终结。
月的意象在小说中与生命的欢愉相联系,和死亡形成对抗:
不要把我抛弃在黑夜,别让我痛苦,我的月亮脸![7]468
夜已深了,月亮已在山顶。生命在笑,死亡在哭呢![7]492
克林格梭尔也将曾经的爱人比作月亮:
噢,往日的月亮啊,欢乐之夜的月亮啊,照着芦苇塘上陋屋的月亮啊![7]489
然而,停滞在往昔的欢乐,不能掩盖当下的痛苦,占星术士向克林格梭尔指出,酒与月都无法抑制其对“下沉”——即死亡——的渴望。
小说所化用的李白诗句,也同酒或月、生与死有关。成段化用李白诗的地方有两处,一处为赫尔曼主动吟诵的:
生命匆匆消逝有如闪电,
光华乍露便难觅踪影。
但见天空大地常驻不变,
人的容颜匆匆随时流逝。
噢,斟满酒杯因何不饮,
你还在等待谁人光临?[7]477-478
另一处为赫尔曼在克林格梭尔的要求下重新吟诵的:
今晨你的头发还乌亮似黑绸,
夜晚时便已像白雪覆盖,
谁若不愿活生生被折磨至死,
请举起酒杯邀明月共饮![7]478
分别对应李白诗中《对酒行》的后半段和《将进酒》的开头。两处化用都有意放大原诗中对生命流逝的慨叹,第二处中甚至将之推衍为生死之间的对立感,而且从中生发出生存之痛苦,酒则是用于麻醉这一痛苦的工具。舍弃第一首诗而要求听第二首诗,暴露了克林格梭尔的痛苦心理,也暗示了他最终死亡的结局。
在“下沉之歌”一节中,克林格梭尔-李太白呼喊的“今天我要痛饮三百杯”[7]495“今天要饮干三百杯”[7]497,化用自《襄阳歌》中的“一日须倾三百杯”[8]369,也继承了《襄阳歌》一诗本身所带有的强烈的借酒浇愁之感。克林格梭尔在幻想中一分为三——“李太白”、亚美尼亚占星术士和影子,应和了《月下独酌》中“对影成三人”[8]1063一句。“李太白”作为三个化身中为主的那一个,其言行反映出克林格梭尔的矛盾的思想中占上风的方面,他与占星术士之间的对话,反映了克林格梭尔的内心斗争,全文中随同游乐却不发一语的影子则是克林格梭尔内心中残存并渐渐消耗殆尽的生存欲的象征。
相比起“李白热”中的其他作品,黑塞在《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中的一个特点便是直接引入了李白的形象,令“李太白”成为主人公的化身之一。而在克林格梭尔陷入幻想之前,他在聚会中主动提及李白之死:“他就是在今天这样日子的美丽傍晚死的,在一条静静河流的小船上。”[7]478关于李白之死的讨论旋即被艾茜丽亚打断,少女对死亡的抗拒和克林格梭尔对死亡的期待形成鲜明对照。临近死亡的克林格梭尔与正值青春的少女之间存在着隔阂,这一隔阂又令他进一步远离生命的欢乐,走向死亡。此外,和克拉朋特的描述相比,黑塞对李白之死的重述剥离了超脱尘世、升入仙境的梦幻想象,更为朴素自然,也更接近这一故事原本的面貌。
在克林格梭尔陷入幻想之后,黑塞还将杜甫作为赫尔曼的唯一化身引入情节中,杜甫的引入使得李白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也令之前“李白热”作品中被淡化的历史背景得以浮现。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任何与李白相关的历史事实,但却准确地把握住了李白的生命历程与唐王朝盛极而衰的过程相伴随这一特征,从而将“克林格梭尔-李太白”对死亡的渴盼和欧洲传统的崩溃相联系,指向现实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的“下沉”。在与占星术士的对话中,“克林格梭尔-李太白”坦言“两千年来一直自认为是世界的头脑”的“欧洲正在下沉”,并认为“我们是乐意往下走的”“我们乐意死亡”[7]496。在整个社会的崩溃面前,酒与月作为往昔生活欢乐的象征,逐渐失去效力,与这些意象共生的“李太白”在享尽欢愉之后,终于坦然面对死神。
黑塞在引用李白诗歌时,采用的是经过改写的版本,在对“克林格梭尔-李太白”的塑造上,侧重于纵酒狂欢的一面,他笔下的李白仍然带有“欧化”的特征。但黑塞并未落入此前德语诗人一味神化李白的窠臼,而是挖掘出李白对当时欧洲社会的意义,为“李白热”注入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在“下沉”的主题之下,狂歌痛饮的行为被深化为生与死的角力,李白不再因这些行为而成为被人崇拜的永恒的偶像,而被还原成一个处于特定时代下的困境中的人。
三、自比“李太白”:黑塞与李白的精神共鸣
《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中的李白以不同于以往“李白热”作品中的固定形象的面目出现,与黑塞当时的心理状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德国学者基尔希霍夫曾指出:“在黑塞一生所遭逢的无数危机中,有一个危机对于作家整个一生和著作的成功或失败具有决定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危机。”④写作于这一时期的《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反映了黑塞复杂的内心世界。克林格梭尔这一角色与黑塞生日相同⑤,显然是黑塞本人的投射。之所以选择李白作为克林格梭尔的化身之一,是因为黑塞与李白发生了跨文化跨时空的精神共鸣。这种精神共鸣得以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成长环境令黑塞对东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黑塞的外祖父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名传教士,曾在印度居住长达24年之久,黑塞的母亲就出生在印度。少年时代与外祖父一同生活的经历,令黑塞早早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他在《魔术师的童年》一文中自述:“我不仅从父母亲和老师们,还从一些秘不现身的、更高明、更神秘的力量那里受到教育,……早在我能读书写字之前,……在我的小脑袋里装满了东方的古老图像和想法,日后每当接触到印度和中国的哲人时,都有一种重逢之乐,一种回到家的感觉。”[9]167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家庭环境使黑塞比起一般的德语作家对东方文化持有更为客观、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年幼时接触的印度文化后来成为黑塞思想与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也是引导黑塞转向中国文化的桥梁。
第二,共有的诗人身份和共通的赤子之心使得黑塞能够在思想上亲近李白,并更深一层地理解李白。两人都于少年时期便投身于文学,黑塞曾自述“从十三岁上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10]187,李白也曾于诗中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8]599黑塞一生做出过无数反抗世俗规则的举动,与李白的恃才傲物之态不谋而合。从成名作《彼得·卡门青特》开始,黑塞的诗文小说中始终弥漫着的对自然的向往之情,也和李白诗中崇尚自然的感情相似。在1907年的一篇书评中,他如此评价李白:“这忧郁的诗人是一位酒中仙,又是一位多情人,他的诗表面上轻松愉快光彩照人,内涵则无比忧伤。”[11]115此时的黑塞就已经领会到李白苦闷的一面。
第三,黑塞与李白都经历了一个社会盛极而衰的剧变,相似的经历为精神共鸣提供了契机。黑塞生于1877年,当时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正因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并进一步向亚非扩张势力,由此黑塞的祖辈才得以远赴并长居印度。和见证了开元盛世的李白类似,黑塞也见证了欧洲的繁荣。虽然工业文明为他向往的田园牧歌蒙上了阴影,但他也的确在物质上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福利,正如同李白虽然鄙弃长安的权臣贵戚,却并不会憎恶开元盛世本身。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下沉”,对于黑塞而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李白而言则是“安史之乱”,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中,但是艺术家(作家/诗人)在“盛世”崩溃时陷入生存危机的境遇却是相似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塞在业已崩塌的欧洲文明中无法寻找到思想的出路,面对强烈的精神危机,死亡也就成为了一种解脱之道。结合李白死于安史之乱末期的历史背景,醉后捉月、沉水而死的传说便带有象征的色彩,即一个“盛世”中极为出色的诗人,在“盛世”崩溃之后,最后一次极享“盛世”之欢并从容死去。这一传说恰好暗合了黑塞的人生走向的一种可能。
二十年后,回顾小说创作的过程,黑塞写道:“战争年月的动荡与伤害几乎完全摧毁我的人生,如果我要重新振作,为人生赋予意义,就必须通过激烈的内省与转变,向迄今为止的一切告别。”[12]85他通过将克林格梭尔一分为三,剖析并割舍了自身对过去的欧洲的繁华假象的留恋,并借助这一角色实践了狂歌痛饮之后的从容死亡,为自身的精神危机找到一个出口。
通过克林格梭尔对“李太白”的自比与幻化等情节,黑塞使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下沉”呈现出互文的关系,将两个时空的历史压缩进这部篇幅不很长的小说中,令其不仅仅是一幅精神自画像,而且成为一部时代的精神图谱。他后来这样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生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的命运的问题。”[10]193这种将自身与全人类相联系的思考使他能够由己出发,向另一种文化、另一层时空中探求可能,从而重新发现李白并与之共鸣,且不止步于此,而是深入地向中国文化中寻求启迪。
四、向往“杜甫”与重识“李白”:黑塞的自我治愈及转向中国文化
黑塞在小说创作中常常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寄寓在形成互补对照的一对朋友形象中,以这种手法创作的作品有《德米安》(1919年)、《悉达多》(1922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1930年)等等,《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也属于此类。小说中,与黑塞生日相同的画家克林格梭尔和与黑塞名字相同的诗人赫尔曼这一对形象反映了处于精神危机状态下的黑塞在思想上的左右互搏。
通过克林格梭尔这一角色,黑塞完成了“向迄今为止的一切告别”,但要真正走出精神危机,还需要重新建立新的足以面对未来的思想观念。小说中占星人模棱两可的劝说和影子无声的游乐的确流露出黑塞对生活和时代的希望,却远远不足以令他说服自己。他对未来的人生之路的思索是借助赫尔曼这一角色来完成的。
在同李白之死传说的对照中,杜甫的人生经历显现出与之相呼应的象征意义:心系苍生,忍受、见证并记录时代的种种变迁,这些都代表着“较为接近生活的肯定态度”[13]105。这一态度也是黑塞后来回顾自己思想转变历程时对中国文化的一个总结。在小说中,赫尔曼就呈现为更勇于且乐于投入生活的形象。相比起克林格梭尔期待听到的描述生死对立的《将进酒》的改写本,赫尔曼首先朗诵的《对酒行》的改写本在情绪上显然要缓和得多,也更有“合情合理地把握生活”[7]477的意味。当“克林格梭尔-李太白”因痛苦而酣饮沉醉时,“赫尔曼-杜甫”在带领孩子们玩耍、跳舞,没有徒然地为时代的“下沉”而苦闷,这一情节虽然没有被大肆渲染,却暗示着赫尔曼将和杜甫一样“顺从生命法则”[7]498,投入时代,经历“下沉”之后,又走入“新生”。
在1919年12月的书信中,黑塞解释了自己对“下沉”的理解:“在我眼中它也完全就是新生。‘欧洲的下沉’对我而言是一种发展过程,是我的亲身体验……并没有突如其来的崩溃,而是人们灵魂中一种缓慢的日益增长的转变。”⑥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黑塞已经走出了创作克林格梭尔的迷狂分裂的精神状态,并吸取了道家思想中“福祸相依”的观念。在小说中,占星人曾试图劝导对时代失望的“克林格梭尔-李太白”:“在你看来是下沉,在我眼中也许却是新生呢。”[7]496这一未能为“李太白”所听取的占星人的劝说,在现实里被黑塞以积极的方式采纳并继续思考着。
对于黑塞而言,从中国文化中探索生存之道,并不是从写作《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才开始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黑塞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1911年,黑塞前往亚洲旅行,途中遇见的中国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黑塞虽然未能到达中国,但却领略了中国文化并为之倾倒。他在文章中向欧美社会强调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认为“我们应当乐于见到在地球的另一半存在着一个坚固而值得尊敬的反极”,“我们应当学习这外来的思想,把东亚也看为我们的老师”[14]93。这次旅行也成为他在思想上转向中国文化的起点⑦。1914年,回忆起这次旅行,黑塞如此形容中国人:“这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知道自己的文化并不后顾,而是在行动中向前看。”[15]97在现实中,黑塞身体力行,实践着他从中国文化中习得的生存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黑塞与罗曼·罗兰结成反战联盟,亲身投入救济战俘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反对不义之战。写作《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也是他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矛盾,寻求通往未来之道的行动。从之后黑塞的生活与创作经历来看,这一行动是有效的。
“在行动中向前看”的精神在此后也一直支撑着黑塞。他的最后一部长篇作品《玻璃球游戏》于1931年开始构思,直至1943年问世。面对欧洲社会的又一次崩溃和席卷世界的又一次大战,黑塞却以沉着冷静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未来世界的故事。在《玻璃球游戏》里,黑塞不断地写到中国,大量引用中国文化中的格言、典故,并在结尾回溯了李白“沉水而死”的传说:主人公克乃西特死于水中。但与克林格梭尔不同,克乃西特不是因为对时代的失望或与青春的隔阂而投向死亡,而是为了年轻的学生去自发地同死亡对抗:“他在为赢得孩子的尊重和友谊而斗争,他在为孩子的灵魂而奋斗,——他现在正与已把他摔倒,并已将他紧紧扭住的死神搏斗,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将竭尽全力赶走死神。”[16]420对“沉水而死”传说的这一重写,回应了1919年的旧作以及世纪之交的“李白热”,反映出黑塞在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之后,对李白的全新的理解,对生命的深刻的感悟,和对人类的坚定的信心。
通过小说《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黑塞将自身的思考注入到“克林格梭尔-李太白”身上,重塑了十九世纪末以来德语文坛对李白形成的固定印象,并借助中国文化完成了精神上的自我治愈。他不仅在小说、诗歌中融入中国元素,还在游记、论文中呼吁欧美社会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重视中国“丰富的生活、丰富的精神、古老的思想”[17]101。黑塞的呼声不是孤立的,当布莱希特因纳粹统治而被迫流亡时,也在遥隔时空的唐朝找到了共鸣,他在诗中写道:
李白和杜甫,在吞噬了
三千万生命的内战中颠沛漂泊[6]
在二十世纪后期的美国,后垮掉派的诗人也借助李白来书写内心的苦闷⑧。“李白热”的风潮虽然早已淡去,李白的形象却在经过了黑塞等人的深化之后,在欧美文坛不断引起新的共鸣,中国文化也渐渐成为欧美社会反思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本文所依据的小说版本为张佩芬所译的《克林格梭尔的最后夏天》(《婚约——中短篇小说选》,张佩芬、王克澄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克林格梭尔”,也有的版本译作“克林索尔”。
②此处的“诗人”指小说中克林格梭尔的朋友赫尔曼,他在克林格梭尔的幻想中化身为“杜甫”。
③《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参考文献[5])第283页译为“《玉笛》”。按参考文献[4]与[6],应为“《玉书》”。
④转引自张佩芬:《黑塞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96。
⑤黑塞生于1877年7月2日。小说中克林格梭尔自叙“出生在七月的第二天”,见参考文献[7],第494页。
⑥转引自张佩芬:《黑塞研究》,第82页。
⑦旅途中遇见的一位中国留学生成为日后黑塞作品中诸多重要角色的原型,有学者评价此次旅行为“走进和走出印度”,见张佩芬:《黑塞研究》,第60-61页。
⑧相关诗歌有:鲍勃·霍尔曼《步李白》《在杜甫之后的一千年想起李白》,米克哈伊·霍洛威茨《唐代断忆》《中国王朝的一件珍宝》。见弗雷泽主编,文楚安,雷丽敏译:《后垮掉派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