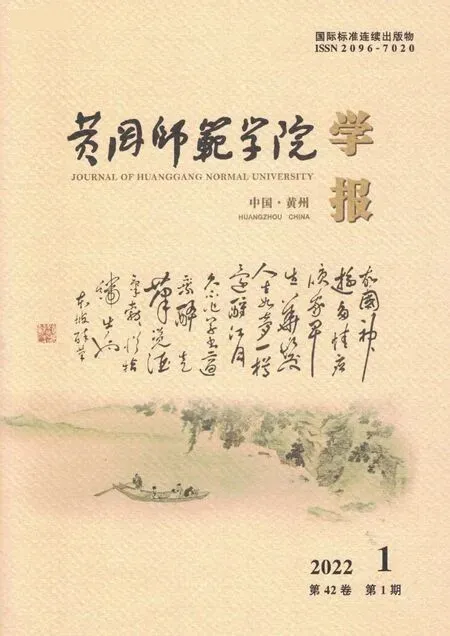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四维:历史、时代、人性和社会
——樊星教授访谈
2023-01-06孟庆奇
樊 星,孟庆奇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8000)
孟庆奇:樊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近年来,“非虚构”写作从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上都得到了广泛认可,这种鼓舞对新闻工作者和非虚构写作者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您长期从事文学研究,今天想请您来谈谈“非虚构”写作问题。
樊星:很高兴有这么一次交流分享的机会。“非虚构”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2015年白俄罗斯的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无疑是给“非虚构”的发展势头又添了一把新柴火。从国内来说,《人民文学》现在有个专栏就叫“非虚构”,而且它把“非虚构”常常放在头条,由此可见其对“非虚构”的重视。有些时评认为现在虚构文学的影响力还赶不上非虚构文学,这与大家对“真实”的关注大于“虚构”显然有关。大家在网上、报纸上读到的那些国际新闻、社会奇闻,那种离奇、那种惊悚的冲击力,远远地超过了文学的虚构。
当我们真正地着眼于阅读作品,尤其是关注全国范围内比较前卫的“非虚构”作品时就不难发现,现在的“非虚构”文学一般都在“描述”上下功夫,比如说关于“社会底层”的非虚构,展示各种人间生态,那种逼真、匪夷所思,具有足够的震撼力。而作家们也总是在寻求着突破。报告文学曾经号称文学的“轻骑兵”,指的就是这种文体感应现实之快。
孟庆奇:“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研究难以像小说、散文那样展开。目前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的是归纳思潮、点评作品,而在理论探讨方面似乎少有经典之作。您认为对“非虚构”写作展开研究的过程中,有哪些要素是必须具备的?
樊星:对于“非虚构”文学现象的关注,首先要建立在对相关作家的深入了解以及对有关作品广泛阅读的基础之上,通过这个过程知晓他们是如何深入生活、面对现实挑战的;其次,“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研究似乎一直很难展开。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它们的呈现方式往往都是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并且在表述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些“添油加醋”,语言形式上则又常常不拘一格,这就造成想要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和量化分析考察的难度极大。
说到“非虚构”文学研究,这里推荐一位美国学者Morris Dickstein写的书,名叫《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所谓“伊甸园”的典故——由于偷食禁果,人类被放逐出伊甸园。作者前不久刚去世。书中就有研究“非虚构”(即“新新闻写作”)的内容,它的副标题是:“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描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各种社会潮流风起云涌,从“垮掉的一代”到“女权主义”“反战运动”“黑色幽默”等等。“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就是在六十年代产生的,以前叫报告文学(reportage),报告文学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对现实发生的事件进行即时的、深入的呈现、剖析。不仅如此。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这些作品具有“离经叛道倾向。这包括种类广泛的地下作品——政治的、对抗文化的、女权主义的、色情的等等。它们描写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地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动荡使得“非虚构文学”崛起。我在美国的书店就注意到,“非虚构文学”(包括人物传记)的专柜明显多于“虚构文学”。
一、历史:发掘深度的事实
孟庆奇:“非虚构”写作,在20世纪初的发轫期也被称之为“叙事新闻”(narrative journalism),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一些美国的杂志上迎来繁荣,即使是在碎片化新闻和实时传播等快速消费成为风尚的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深度阅读、耐人寻味的写作精品的需求从未衰减,甚至可以说更加迫切。仅从“对事实的深度发掘”这一点,是否可以说是被作为“非虚构”写作的历史使命来贯彻的呢?
樊星:传记文学属于“非虚构”,它本身就是所谓历史主题写作的典型代表。我们的当代传记文学就产生了很优秀的作品,比如吴晗的《朱元璋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就是其中的代表。传记文学都是选择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这就和注重虚构的小说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小说往往具有批判现实的精神。虽然也有歌颂的作品,如“红色经典”。但古往今来,批判现实的小说是主流。但是传记类作品中,讴歌不平凡人生的作品居多。像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欧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梵高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冯至的《杜甫传》、李辉的《黄苗子与郁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等等代表作品,多在弘扬一种伟大的人格。虽然也有关于恶魔的传记,但比较起来,小说中的“颂歌”(如《三国演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等)还是少了许多。而传记文学,则自带真真切切的人格光芒。因此我常常对同学们说,要多读传记。这样既可以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知道成功的不易;也可以了解历史的曲折、社会的变化、人生的多变,从而超越许多简单化的偏颇之见。
举个例子吧,这些年网上对郭沫若贬得厉害,从政治上到私生活,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他曾经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写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样的文章,是显示了文人的风骨的。“文革”中,他的儿子受到迫害,自杀以后,他内心的痛苦也有披露。
这里推荐大家去读一读王晓明教授写的《鲁迅传》,它的正标题叫《无法直面的人生》。因为鲁迅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是在王晓明的笔下,却写出了鲁迅在许多时候实际上也无法直面太惨淡的人生。在有关鲁迅的传记中,这一本我认为写得最凝重。王晓明的阅读体验是“为什么鲁迅的文章读起来总是让人觉得那么苦涩、那么沉重、那么绝望呢?”
首先,鲁迅本人对经济收入是特别看重的,常常在日记里面记下稿费收入,请客吃饭花了多少钱,买书花了多少钱等等。为什么?考虑到鲁迅的成长环境,从小吃过苦,所以他会比较注重记账。鲁迅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顾,他的母亲包括他的原配夫人,他都要去供养。所以鲁迅常常批判社会,却一直不点名攻击像章士钊这样的高官?因为鲁迅在教育部供职,而章士钊就是当时鲁迅的顶头上司。他的批判会不会导致丢掉饭碗?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生活中,人们常常把“钱不是问题”这样的话挂在嘴边,实际上大家内心里常常还是得计较钱的问题。因为钱是经济基础。现在的年轻人在谈收入时直截了当,就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纠葛。所以谈知识分子就要这样直接切入到做人的根本——要先挣了钱才能有生活的来源。所以这本传记里面还原了鲁迅看重经济收入的历史,鲁迅经常跟书商就版税交涉,就很接地气。
再者,作者也写到鲁迅的婚姻悲剧。鲁迅不爱朱安女士。而朱安也十分痛苦,痛苦到曾经说鲁迅完全可以娶个小老婆,生个孩子由她来带。可见她已经自卑到了尘埃里,可鲁迅就是不喜欢她。但是鲁迅还是始终在承担养家的责任,所以鲁迅搬家的时候还是一直带她走,从绍兴到北平,然后跟周作人闹翻了以后,又带她去新家。鲁迅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婚姻不幸、兄弟失和等等,这一切都使得他非常痛苦。连他最敬爱的母亲都给他痛苦的婚姻,他怎么可能不感到绝望?
因此,“鲁迅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吗?”就成为书中提出的问题。一般都认为鲁迅是现代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批判的精神。但是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以后,许广平作为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想出去参加活动,鲁迅说:“你走了谁来做家务?”这样有没有传统的夫权意味?鲁迅跟许广平怄气了,许广平认为作为老师的鲁迅应该让着自己。而鲁迅呢,就到外面的阳台上往地上一躺,那时天已经很凉了,小儿子也就跟着默默地躺下了,许广平就吓坏了,因为鲁迅身体很不好,她只好隐忍退让。由此可见,鲁迅甚至跟自己最爱的人也赌气。所以这本书里提出的关于“鲁迅是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问题耐人寻味。从他的眼光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从他的学识层面上看也没有问题。但是他的为人,他性格中恪守孝道、多疑、易怒,则明显带有传统士大夫气。
孟庆奇:关于“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点这个问题,似乎也已经有了不少的讨论。说来说去倒像是两者的安身立命之本的区别,也就是所谓的“道统”跟“学养”方面的差异:说到传统士大夫,当然首先应该具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同时还要学识渊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则要有世界眼光、学贯中西,还要有现代批判意识。您认为是这样吗?
樊星:这样去归纳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士大夫就没有批判意识吗?从王充、李贽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有质疑传统、批判传统的著述。所以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其实常常不那么泾渭分明——士大夫有人格,也有学问,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现代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吧。如果说真要说有什么差别的话,也许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士大夫很不一样,他们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背景,还有了更广阔的世界眼光。
好多传记把鲁迅捧得很高,突出“偶像”“斗士”“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而王晓明这部鲁迅传记就不一样。钱理群在《心灵的探寻》一书中已经是将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进行审视。但是王晓明写出了鲁迅的传统士大夫意味,这就很耐人寻味了。
现代文学三十年,而当代文学已经七十年了。改革开放都四十多年了,虽然没有产生鲁迅这样的大师,甚至戏剧界也一直没有产生曹禺那样的大家,但是当代有没有超越现代的成就?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吧,比如现代就没有产生长篇历史小说,而当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则名篇多多,像姚雪垠的《李自成》,就曾被茅盾认为是填补了现代文学一个空白的力作。还有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少年天子》等等这样的作品,五四那一代人就没有写出来。
孟庆奇:您写过文章专门讨论“新中国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①,其中特别谈及历史长篇和非虚构文学,表示这些作品体现出当代人的英雄崇拜情感与深厚的“寻根”情结,那么当代文学在传记文学方面超过了现代同类文学没有?
樊星: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已经有那么多作品,而且还产生了重要的经典。当代传记文学成果多多,朱东润的《陆游传》《梅尧臣传》《张居正传》、李辉的《浪迹天涯——萧乾传》《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韩石山的《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季红真的《萧红传》等等都广受好评。包括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虽然是在美国写的,也算当代作品,被称为是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一部经典。
还有吴晗的《朱元璋传》,他笔下的朱元璋性格复杂,这本书是1940年代末写的,所以关于朱元璋残暴一面的刻画描写据说也有影射蒋介石的意味。但没想到建国后毛泽东很喜欢,还亲自批阅,最后作者又修改为后来的新版《朱元璋传》。已经有人指出毛泽东为什么很少谈到汉文帝、唐太宗?而经常会谈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这样的帝王?这些人物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来自底层,在激烈、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成就了霸业。由此可见,传记文学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版本研究。
再比如像朱东润先生的《陆游传》也是非常有名的传记文学作品。还有像邓广铭先生的《岳飞》,虽然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写的传记寄托了深厚的民族情感。还有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其中关于李白的那一部分写得很有看头。这本书写于“文革”中,有“扬李抑杜”的倾向。但其中写李白的复杂性格就不同于那个年代僵化的“阶级”观点。而且,书写得很有才气,也不同于那个年代的刻板文风。所以,我有一种感觉,郭沫若在写李白时是有所寄托的。至于书中对杜甫的批判,则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而且多有苛求之意,则另当别论。
朱东润、邓广铭、郭沫若都是很有名的学者,由他们来写的传记文学,就自然带有了学术的色彩。所以传记写作有的文学性突出,有的学术色彩鲜明,这就有了不同的风格,值得研究。可以说从50年代到现在,“非虚构”文学在传记文学上已经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
关于当代传记文学的热潮,可以看出传统传记文学(如《史记》中的“世家”“列传”)的影响,也有对西方传记文学冲击的回应(西方传记文学作家安德烈·莫洛亚、罗曼·罗兰、茨威格、欧文·斯通的作品在中国读书界都很有影响),还有传记作者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以及,尽管时代变化太快,大家仍然频频回首往事的心态,通过对往事进行回顾、反思,从中感悟世道玄机、成功的奥秘。再者,见贤思齐,邓广铭当年写《岳飞》,就因为岳飞是民族英雄,作者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扬岳飞的精神,团结起来去抵抗日本,这就是一种现实的紧迫感。
此外,传记式的“非虚构”文学对于作者的文学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传记写作得对传主的事业有深入的了解,同时涉及很多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恩恩怨怨。这就需要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所以林语堂就很了不起,他的《苏东坡传》就显示了深厚的历史、文学修养,以及妙语连珠的才华。
二、时代:呈现流畅的内容
孟庆奇:讲述、聆听和分享是人类基于社会交往的本能需求,无论身处哪一个时代,深度的思考、本质的揭示、精彩的故事和流畅的呈现都是作品的统一标准。只是呈现的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传记文学的写作就需要学养和研究,要想写的好,就得备受煎熬,要有勇气和耐心、博学和见识、执着和感受力,同时怀有一颗谦卑之心。相对而言,虚构的作品则不一定有对于学养方面的严格要求。虚构,更多需要的是想象。
樊星:现当代传记文学中有不少是写现代文化人的坎坷历程的。这些文化人对现实的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奋斗都体现了对救国之路的上下求索。同时,在为这些文化人作传的过程中也表达了当代传记作家对那一代人的复杂情感——既有敬仰,也有对他们生不逢时的感慨——天纵英才,却生活在动荡的年代。
这里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作家是如何把“非虚构”作品写出中国特色的?在这里我介绍一位代表作家——李辉,他跟陈思和是同学,本科毕业论文就是和陈思和合著的《巴金论稿》,大学毕业后去了北京当记者。他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与许多老一代文化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经常的登门拜访、约稿、信件往来中,发掘出许多珍贵史料。关于巴金、萧乾、冰心、沈从文、周扬等等,这些“在场感”极强的材料保留下来,规模相当于一个小型的“现代文学馆”。在这个基础之上,他的传记写作就显得独具特色:既有当事人对现代文学史的回忆,也凝聚了作家对那一段历史、对那一代文化人命运的思考。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思想意味。他关于那一代文化人的纪实写作受到美国非虚构作家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如《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还有在《收获》杂志开辟的专栏“沧桑看云”,都包含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在欧文·斯通那里就是不可能有的。欧文·斯通的传记写作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对生活的热情、对人心的探讨。传主的经历风云激荡,作家的文笔也扣人心弦。这就是中国传记文学和西方非虚构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
说到传记文学,应该包括自传,作家自己写自己,也值得研究。作家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既有助于深入研究作家的文学创造,也为研究作家的个性、经历,包括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提供了特有的视角。例如《王蒙自传》,作为当代作家自传里的代表作品,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值得重视的历史资料。其中就回忆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荒唐和去新疆后经历的充实人生,就与好些在底层挣扎的“右派”(例如张贤亮、从维熙等等)很不一样。获得平反以后,作者对文坛风云的观察与思考,对一些曾经的朋友的看法,对一些争鸣问题的意见,都写出了传主对自己的剖析。其中有生存智慧,也有独特个性。关于王蒙,评论界也曾经有过不同的说法。《王蒙自传》保留了这些原汁原味的个人经历,可以与王蒙的许多作品对照着读。
孟庆奇:“非虚构”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努力还原着属于一个人的“真实”。重现那些后人看来已经十分陌生的历史情境,但那些生动的细节、珍藏的史料,都足以将过来人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再次唤醒,也为当代文化史留下了宝贵的一笔。未来的历史书写,应该离不开“非虚构”文学的逼真、生动与光怪陆离。
樊星:再来看看“口述实录”文学,也是“非虚构”的一支,它诞生于1940年代的美国,最初只是搜集史料的一种手段。后来,一些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提着录音机走向社会,开始倾听、记录百姓的各种话语,并如实记录下来,稍微加工,发表出来。它的特点在个人的现场感,可以还原各种当事人、亲历者原汁原味的见闻。尽管,口述的也未必就是十分可靠的。而口述者在陈述时其中又难免会牵涉到他们的自尊或者隐私,因此不可能百分之百真真切切,但是作为“非虚构”文学,它还是会保存下来很多珍贵的史料。“口述实录”的代表作有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的名著《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还有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The Chernobyl Prayer: the Chronicles of the Future)一书,都是深入普通人中间,采访、追问、思考的力作。
早在1980年代,作家张辛欣、桑晔合作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就通过对一百个北京人的自述实录还原了普通人的各种欲望、各种经历,为他们写下了一部光怪陆离的生活史。这本厚重的书显然受到了《美国梦寻》的影响。后来,冯骥才写出了《一百个人的十年》,也是以口述实录的文体记录了许多普通人在政治风暴中的各种体验与记忆。《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则通过许多当事人对自己情感隐私的披露打开了人们倾诉内心情感的一扇门,也引出许多电视台和报刊的“情感口述”的传播甚广。这些“口述实录”让普通人讲述他们的生活、情感(包括隐私),是民间生活史的宝贵记录,也像“万花筒”一般开人眼界,使人眼花缭乱。
有一位在武汉大学任教多年、研究美国历史的老先生刘绪贻,与杨生茂共同主编了六卷本《美国通史》,被誉为“美国通”。刘老先生也有一部回忆录叫做《箫声剑影》,就是一部口述历史作品,主要采用访谈的方式展开,是百岁老教授对他前半生的深情回忆,其中既有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也有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而贯穿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刘绪贻先生作为武大文脉的一位典型代表,他所留下的口述历史,是武汉大学,也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一个亮点。这种个人色彩浓厚的回忆,也与那些自传一起,填补了历史的一些空白,而且更加口语化,更富有生活气息。
孟庆奇:“非虚构”写作对作者提出了历史学养和研究背景等的要求,相应地作为研究者,在对“非虚构”文学现象的考察过程中,除了对相关作家作品进行必要的深入了解外,在研究路径和理论学习方面是否也应当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樊星:关于你说的这点已经涉及写作学科建设的范畴了,从学理上来说,写作学和现当代文学其实是相通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主攻方向表现为研究诗歌、小说和散文、戏剧等等方面。现在大学本科阶段基本上不会讲“非虚构”了,因为课时安排紧,没有时间可供分配。这就形成一种很错位的现象,一方面“非虚构”文学在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大学里面又缺少必要的“非虚构”文学的传授,这是当代“非虚构”文学面临的突出尴尬处境。久而久之,也就导致了现在研究“非虚构”文学的学者后劲不足。而这也许只有在写作学的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与研究中可以得到弥补。
研究当代文学,一定要建立起“1980年代”的知识背景。因为那个年代离今天的青年学子已经显然相当陌生了。而1980年代,“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曾经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的一大使命就是反映社会问题,而且常常是社会新闻没有关注的深层次问题。1970年代末,随着思想解放浪潮的高涨,已经产生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小木屋》这些讴歌科学家在困难年代里刻苦钻研、不计回报的名篇,其实就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待遇低的普遍问题。而陈禹山暴露张志新冤案的报告文学《一份血写的报告》和王晨、张天来披露“文革冤案”的名篇《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产生的轰动效应,也催生了反思政治问题的浪潮。后来,写历史和现实冤案的报告文学作品一直绵绵不绝,就是证明。这样,终于汇成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浪潮,到1980年代中期,涌现出以麦天枢的《天地与土皇帝》、乔迈的《希望在燃烧》那样呼唤民主与法制的力作,和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那样揭示改革困境的作品。到1980年代末,100多家期刊联合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声势空前浩大,产生了好些发人深思的好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奇观,至今令人缅怀。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潮流的主要特点在于:反映了那一代作家对现实的关切,特别是披露的很多问题,都是当时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好些还都是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小说中看不到的。这样的文学具有强烈的冲击力,总是致力于发现现实的隐患,同时去深化人们对现实的思考。例如贾鲁生就以一系列报告文学揭示了“商品经济封建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一部分暴富起来的人们很容易“倒退到地主式的消费方式”?
三、人性:揭露真相的本质
孟庆奇:“非虚构”的体裁混合了人情世故、学术理论和从观察者角度出发的事实呈现,其生成过程是通过对日常事件带有专项理解的剖析,对来源复杂的各项信息进行归纳整理。这种肇始于作者走进真实世界去了解某种新信息的写作模式,对读者和作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写作者是否从找选题、采访设计、文本编辑,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反复打磨,才有可能实现理想的“还原”?
樊星:关于这个问题,有一部美国“非虚构”文学经典可以作为案例,书名叫《冷血》(In Cold Blood),写两个少年杀人犯,作品聚焦于他们为什么会犯罪?这本书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专门去采访这两个罪犯,帮他们买东西,最后打开他们懵懵懂懂的心结,披露了冷血的隐秘。这种“非虚构”作品就是把对犯罪现象的书写深入到罪犯的心灵深处,写出他们犯罪的家庭原因和偶然因素。中国人历来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西方人则比较主张人性本恶,当然中国也有人说人性恶比如荀子,但是这个“恶”的根源在哪里?常常有人认为它是家庭教育的缺失,但事实上有的家庭条件很好、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为什么也犯罪?这样的思考就指向了人生的复杂与神秘。这种对人性的追问,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来说就是:是否存在天生的“坏种(bad seed)”?“非虚构”文学中不少写犯罪的就是在尝试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探讨。包括对犯罪者心理的分析,有一些人犯罪就是一念之间的冲动。所以“非虚构”文学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体,还具有相当的社会学意义,体现在聚焦某种特别的社会现象,并进行深入挖掘,揭示其复杂性。
“非虚构”文学代表了一种求真的精神。因为小说常常是虚构的。但其实我们常常还是会有这样一种阅读体验,例如看《红楼梦》,很容易就会想到贾宝玉是不是就是曹雪芹本人?“假作真时真亦假”,这就是文学欣赏与批评当中对“真”的诉求,而“非虚构”就很好地满足了的这种求真的期待。而且,这种“求真”并非是作为小说的填补而存在的。有些小说真的是虚构的吗?郁达夫就说过“小说就是作家的自传”②,郁达夫小说里面的“我”,就是郁达夫本人添油加醋之后的艺术效果:那样一个多情的、冲动的、喜欢自怨自艾的形象。另一方面,历史的真实中有没有传说的成分?《史记》是真实的吧,但“项羽本纪”显然就有小说笔法——霸王别姬的场景描写显然很有文学性。司马迁写史,不少内容来自传说,而传说就难免会有添油加醋、真假掺杂。所以《史记》也是一本文学著作,绝不仅仅是原汁原味的历史。也不可能有原汁原味的历史吧!
王安忆有一本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它有个副标题,叫“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这个作品写“寻根”,寻母亲家族的源头。王安忆的母亲是茹志鹃,但是,王安忆关注到“茹”不是一个汉族的姓,王安忆就去查史料,结果发现此姓来自柔然,柔然是北方少数民族,可是她的母亲是江苏人。那么,它的迁徙中有过多少往事已经失传!这段历史不可能被真实的“还原”,因此王安忆一边到图书馆去查阅了大量的史料,一边回到她母亲的老家,去调查,当然也只能采集到一些口口相传的传说,再把这些传说加上自己的虚构与想象,最后写成了这部小说。这样的故事其实相当典型,因为很多的历史都是掺合了虚构与想象,甚至别有用心的编造的。因此,“非虚构”作品中也难免掺进了作家的一些想象、虚构,比如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就需要作家设身处地地去想象。所以有没有绝对的“非虚构”,“非虚构”中有多少虚构与想象?很难说清楚。
四、社会:讲述精彩的故事
孟庆奇: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非虚构”文学是暴露了生活的阴暗面的。这就同小说的批判精神一致了。发现“非虚构”中不能够被小说所替代的部分,最真实、最纠结的那些问题。是否能给“非虚构”写作和研究可以提供一些很好的参考呢?
樊星:仍然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为例,这种写作本身首先要求作家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还得有相当的思想力和知识储备。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能够给人以振聋发聩的震撼力,所带来的阅读体验与上述这些因素很有关系。例如夏衍的《包身工》、还有1980年代的许多“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像麦天枢的《土地与土皇帝》暴露农村的政治问题,还有贾鲁生的《性别悲剧》写当代富人纳妾、元配的屈辱等等。麦天枢、贾鲁生的作品中常常燃烧着现实的忧患,与他们善于通过社会问题深入到对传统文化(包括“国民性”)问题、对体制问题的思考密切相关。因此,需要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关于社会学的、思想史的,然后才能在写作的时候,把学养糅合进去,使得这种“非虚构”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新闻报道,这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一个典型特色,思想厚重、有学术背景。
也有作家为了深入到生活当中去,追求切身的“体验”。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就是“体验派”报告文学的代表。这个“体验派”是“非虚构”文学的很重要的一支。有一位德国作家叫瓦尔拉夫,他的笔下就描写了德国的另一面,德国是一个现代化发达的国家。但是瓦尔拉夫就注意到德国社会的底层有很多来自土耳其的苦力,他就去进行调查研究,深入他们中间,写成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最底层》,暴露了发达社会底层的苦难。这本书对许多中国作家影响很大。所以前面谈到了“非虚构”文学需要学养、需要思想,现在还可以加一点——需要体验。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就是作家混入乞丐群体,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经历的力作。对于记录“底层”、“边缘群体”的生活形态,影响很大。
孟庆奇:传记文学竭力还原历史人物的多面性,或者致力于构筑个人视角下的时代记忆。那么作为报告文学这一种“非虚构”的重要呈现形式,除了披露社会问题、曝光阴暗角落之外,是否存在正向的、有温度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意义?
樊星:说到报告文学的使命感,有没有“正能量”的作品?也有很多。军旅作家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就写得十分感人,这部作品深入了解了许许多多贫困孩子渴望上学的生存状况,很多真真切切的描写感动了许多读者。大家主动捐资助学,改变了许多贫困学生的命运。
尽管如此,最近有一部有影响的“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值得关注,作者是武大文学院毕业的“79后”作家黄灯。根据《中国青年报》的统计,截至2020年6月底,全国共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只有1258所,并且在这一千多所高校里,人们所熟悉的“211”“985”高校所占的比例,甚至还不到十分之一。中国在校大学生当中的90%都集中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一本院校只占全部高校的13%。可以说,二本院校的学生身上能够体现出中国最为多数的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活法、他们的命运因此值得关注,“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对久居“象牙塔”的名校学生和教授来说,她笔下所描写对象的校园生活及生存状态显然比较陌生。黄灯自己也说,“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年轻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只有少数学生能进入几十所全国重点大学,更多的人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像黄灯这样,关心普通学生,为他们代言,体现了关注普通人的可贵情怀。可见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至今还在延续。
这就是“非虚构”写作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展现社会群像生命姿态的多样性,并引起社会的关注与理解。而且,通过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依然有不可忽略的沉重与感伤。社会的弱势群体永远期待有人为他们发声。
注释:
①樊星:《七十年风云激荡——漫谈“新中国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当代文坛》,2020(05):17-24.
②郁达夫在1927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至于我的对于创作的态度,说出来,或者人家要笑我,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后经日本的自传文学研究专家川合康三严密考证,“所有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来源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阿·法郎士的名言“所有的小说,细想起来都是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