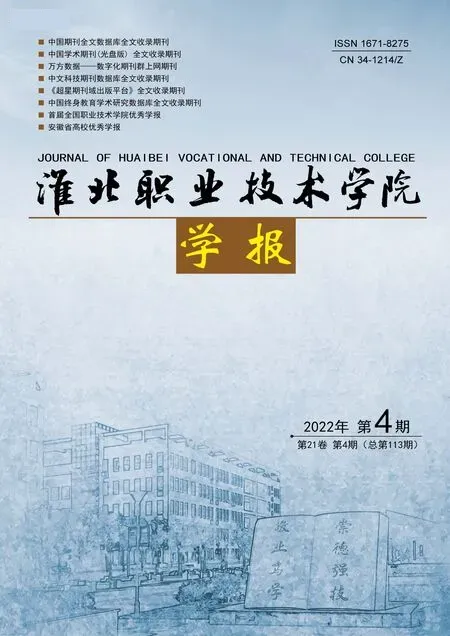新文科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安徽地域文化的适度融入
2023-01-06邓祥龙
邓祥龙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在山东大学(威海)召开,《新文科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布,该《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宣言》强调,我们需要走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根据各学科专业特点,结合行业领域特定问题,坚持分类推进。其中,文科建设要实现“促人、修身、铸魂”的目标。根据新文科建设要求,安徽省本科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适度融入地域文化将能更好地实施课程改革,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古代汉语”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也是学生在基本掌握了现代汉语知识基础上的语言类进修课程。因此,该课程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有一定的理论难度。“古代汉语”课程自设立以来,众多一线教师不断开展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探索,逐渐形成自有的一套教学模式。但在课堂教学中仍存在授课内容脱离实际的问题。因此,能否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适度融入安徽地域文化,实现新知识与学生固有文化背景的联系,值得探究。
1 安徽地域文化适度融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安徽地域文化适度融入“古代汉语”课程,具体体现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适度融入一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资源,以期更好地完成课程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教学目的。新形势下,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1.1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强国”“文化自信”等时代课题的提出,为我们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政策指引;“新文科”建设又为高校推进学科发展布置了重要的建设任务。新时代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学科建设也要建立在传统文化厚实的基础之上。
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实际上就是在挖掘地域文化的价值。高校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场所和文化继承和创新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地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高校需要在文化建设政策的指引下,结合不同学科特色,将地域文化适度融入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中去,从而实现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发展,发挥文化传承创新的优势,增强文化育人的功能。
1.2 课程教学实践的需要
首先,“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内容以“古”为主,重点在于比较古今汉语之异,其中:不仅需要纵向的历时研究,而且还需要共时的区域横向对比。中国幅员辽阔,古今区域划分不同,各地汉语状况可以说是“各有土风”。因此,从历时角度来看,古今汉语总体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从共时角度来看,各区域汉语表现不同,继承程度不同,发展情况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代汉语”教学离不开对地域文化的阐释。其次,任何课程的教学都需要结合具体的学情。“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强,容易出现脱离实际的问题,一方面,脱离学生固有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脱离实践需要。安徽本科高校学生主要来自省内各地,拥有相似的文化大背景,他们也深谙各自家乡的地域特色文化。因此,将学生原有认知结构中的知识经验与地域新知识建立联系,使之成为“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这就需要适度融入安徽地域文化。
1.3 安徽地域文化与“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结合点多
安徽所辖区域文化起源早、历时长、文化资源多样,并且依托其特定的地理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涡淮文化、皖江文化、新安文化(或曰徽州文化)三大文化圈。[1]三大文化圈有各自的文化代表,不同地域又有丰富且独特的方言、民俗等文化资源。“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通论和文选两个部分。通论部分主要讲授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和必备的文化常识,包括但不限于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等专题。文选部分则侧重于文献阅读,主要以经典传世文献为主,具体篇目的选择因教材、教师的不同,差异很大。“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呈现出“框架清晰、内容灵活”的特点。“框架清晰”为课程融入安徽地域文化划定了明确的范围,实际操作也将更有针对性;“内容灵活”为选取更适合课程教学的内容提供更多可能性。因此,安徽地域文化与“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结合灵活多样,如:可以选取安徽出土文献字形作为文字通论的补充;选取各地方言口语作为音韵通论的补充;选取安徽学人的古汉语理论著作和地方文化名人相关的经典作品作为文选部分的补充等。
另外,前辈学者已经有在具体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的探索实践。蔡正发、熊兴主编的《古代汉语》在编写说明中就强调:“(本书)文选部分与云南地方少数民族相关的篇章为总篇章的大半数,包括写滇人,记滇事,咏滇物,评滇文以及滇人记、写、吟、咏的各类作品。”[2]尉迟治平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左传》文选部分共十篇,有关楚地文献三篇,并且开篇选读《楚武王侵随》,想必也是有意为之。这都为“古代汉语”教学融入安徽地域文化提供了借鉴。
2 安徽地域文化适度融入“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主要文化资源
安徽省地跨南北,历史底蕴浓厚,地域文化多样,拥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都可以作为“古代汉语”教学中的材料补充。
2.1 通论部分
2.1.1 安徽学术史
有人认为“古代汉语”大致相当于古代的“小学”,“古代汉语”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小学”附属于经学,两者之间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包含文字、音韵、训诂内容的“小学”,经常被提及和使用。讲到“小学”,不得不提清代的考证学,清代考证学顶峰在乾嘉时期,乾嘉学派又以戴震为高峰,戴震即为皖派汉学的代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皖派以戴中原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3]而后受业或私淑于戴震者甚多,《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4]他们都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治经,成绩斐然。可见,安徽拥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和治学特色,在教学中,可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利用导读课对具有安徽学术特色的乾嘉皖派学人进行梳理介绍,让学生了解前贤的治学方法和成果,从而加深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后续通论和文选等内容的教学打下基础。
2.1.2 出土材料
新中国成立后,安徽省考古工作突飞猛进,研究成果丰硕,涵盖各个历史阶段,涉及古代社会诸多方面。考古方面的新发现,对“古代汉语”的教学,尤其对文字通论的教学有着重要作用。如:蚌埠钟离国春秋青铜铭文、安庆战国越王亓北古铜剑鸟虫书、寿县战国卾君启金节铭文、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阜阳汉简、亳州曹操宗族墓砖刻文字,再结合安徽出土的汉魏之后的今文字材料,基本勾画了古今汉字书体演变的脉络,丰富了课堂教学中的文字案例。尤其是亳州曹操宗族墓砖刻文字古今字体多样,学生通过观察,认识到文字演变的渐变性和复杂性,避免形成篆隶草行楷依次相因相承的简单认识。同时,学生也能看到东汉时期,就已出现“书、东、寿”等字的简化写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古今字、繁简字、异体字等字际关系的理解。
2.1.3 地名及方言材料
音韵部分通论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专业性强、术语繁杂,囿于课程性质,所占课时并不多,因此,学习难度较大。加之安徽省官话区人口众多,声韵调较之古音变化很大,如:中原官话入声消失,江淮官话存在不同程度的入声舒化现象,因此,多数本省学生缺少对入声概念的把握。但各地方言或地名中存在或多或少的存古现象,这都是音韵通论教学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如:“阜”,《广韵》中属上声並母字,根据声调演变规律,全浊上声变去声,普通话读为[fu]51,阜阳地名中的“阜”在当地仍读为上声;蚌埠地名中“埠”从阜得声,普通话读为[pu]51,可以引出“古无轻唇”的知识点;皖南多地保留入声,更是课堂教学的生动实例。
2.2 文选部分
2.2.1 经典文学作品
历代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性可以从当地的作品和反映当地情况的作品两方面入手。今安徽所辖各市,在历代分属不同方国或行政区域管辖,直到清代,疆域格局才基本定型。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地区涌现了众多的历史人物,也出现了众多反映当地情况的作品。如:《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5]4697杜预注曰“(涂山)在寿春东北”[5]4697,即今蚌埠市怀远县之当涂山。后代学者多从此说,因此,可选取对应文献作为选读作品;亳州老子道家文化、华佗康养文化兴盛,可选读《道德经》《三国志》等经典作品作为地域文化的体现。另外,具有完整性与代表性的安徽地区出土文献也可以作为选读作品,如:寿县鄂君启金节铭文记载了贩运活动的种种规定、安大简记载了战国《诗经》的原貌,这些材料都可以作为文选的补充。
2.2.2 语言理论文献
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文献主要选择能体现古代汉语言文字、词汇以及语法特点的作品,授课文选时代多以先秦为主,选取诸子散文和《诗经》等韵文材料,这些都属于直接的感性材料。同时,文选也可以增加一些理性材料,如涉及语言理论的相关文章。一些教材已经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汤可敬主编的《新编古代汉语》节选《说文叙》《切韵序》等,王世贤主编的《新型古代汉语》选入《说文叙》《答刘歆书》《颜氏家训·音辞篇》等,毛远明、陈志明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文选部分单列语言文字学文选一章,收入《说文解字·叙》《助字辨略·自序》《马氏文通·序》三篇,这些都是语言理论文章,是对文选部分的重要补充,也是对“古代汉语”学科特点的凸显。因此,文选部分可以结合安徽学术史,选读皖派汉学代表作品,尤其是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有关文字训诂经典论述,提高学生的学术视野;在经典文选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学习前贤的考证方法,提高阅读文言理论著作的能力。
3 安徽地域文化适度融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意义
安徽地域文化融入“古代汉语”教学主要通过教师与学生主体的互动,在完成教学环节的基础上实现文化知识的传承与实践,这一过程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3.1 实现高效的课程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教学中体现地域文化,目的是教师提炼各地语言资源,通过课堂教学观照学生已有的语言知识基础,进而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更好地完成教学环节,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高校学生地域分布广,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掌握学情的基础上,结合各地特色资源,提炼出本课程相关的理论知识,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环节之中,更能接受、理解新的教学内容。同时,通过地域文化因素与课程理论知识的结合,学生认识到“古代汉语”并非晦涩且无用,让学生有意识地观察并分析日常所见所闻的感性材料,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的目的。
3.2 培育教师的地域文化素养
安徽省南北差异大,各地文化各异,将地域文化融入“古代汉语”教学中,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地域文化素养,了解各地历史、名人、地名等文化状况和资源,尤其是与“古代汉语”结合密切的方言分布情况。安徽方言类型多样,包括皖北中原官话,皖中江淮官话,皖西赣语,皖南宣城吴语、徽语、客籍话等。[6]在音韵通论的教学中,教师需要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阅读方言志等相关资料,结合“古代汉语”教学知识点,针对性、多方面地掌握各方言片区的相关特点。只有这样,才能针对不同地区的学生,恰当地选取合适的教学资源。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教师的地域文化素养也在不断得到培育和提高。
3.3 搭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教科研平台
各地高校都努力依托当地特有的文化资源,挖掘办学亮点,形成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教科研平台。“古代汉语”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虽然体现在教学环节之中,却是在提炼地域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个过程就是寻找地域特色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特色的教科研平台,以教促研,教研相辅。如:安徽大学的古文字研究与文字通论结合、安徽师范大学的诗学研究与诗律结合、黄山学院的徽文化研究与学术史结合、亳州学院的中医药文化与秦汉文献结合,这既体现了“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地域性,又在教学研究过程中为相应的教科研平台提供支持。
3.4 拓宽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模式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于年轻一代,高校学生拥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也有独立的创新精神。因此,他们是地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体。“古代汉语”课程比其他课程能更好地展现地域特色文化,一方面,地域文化进入课堂教学,学生能科学、准确地获取其中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古代汉语”课程的理论知识也为地域文化的挖掘与分析提供方法借鉴。高校学生在学习“古代汉语”理论知识之后,自觉将其运用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现象分析的实践中,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在此过程中,学生真正体会到地域文化的内涵,在增强文化认同的同时,成为文化传承的主体,并在今后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中,更好发挥自己的文化创新能力,进一步拓宽文化创新的模式。
4 结语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中文专业的核心基础课,教学内容模块清晰但内容庞杂,重点突出但难度较大。安徽省拥有丰富的“古代汉语”教学资源,将其适当融入日常教学之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而且,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地域文化资源,进而学以致用,将“古代汉语”理论知识用诸实践,增强学生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育人的效果,也体现了新文科背景下,该课程的特色育人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文化资源只是“古代汉语”教学中的辅助材料,王力本《古代汉语》强调通论、文选和常用词的系统性,三者的选择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即便后来的一些教材删减了常用词部分,至少通论与文选仍是需要相互配合的。地域文化因素的过度增加,可能会割裂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因此,要遵循地域文化融入教学的适度原则,明确地域文化因素要以服务“古代汉语”基本教学内容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