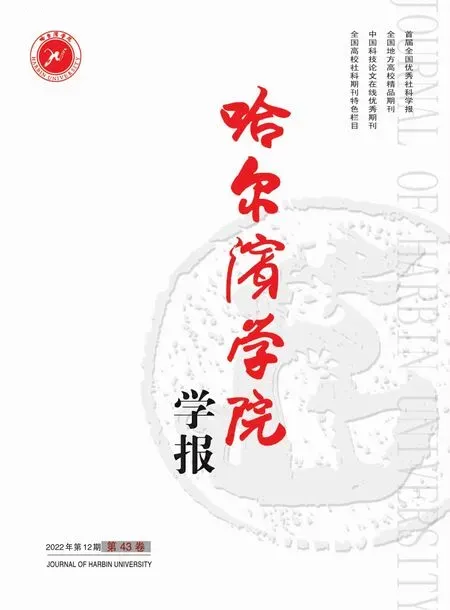论大卫·米切尔作品中的历史和女性
2023-01-04王忠霞
王忠霞
(1.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基础教学部,安徽 芜湖 241000;2.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一、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英国《泰晤士报》曾经对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1969—)的小说《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给予高度的评价:“与当今几乎所有作品相比,这部作品的雄心和才气令人炫目……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部以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贯穿其间的惊险小说;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部华丽的历史小说,讲述了发生在历史重要关口的文化冲突。”[1](P51)历史小说的创作通常“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2](P193)历史小说这一界定之于《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还是十分准确的。小说以真实的日本历史事件为蓝本,以一个荷兰商官职员雅各布·德佐特的视角,讲述了荷兰人在日本长崎从事贸易活动时的见闻,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日本闭关锁国时期,幕府统治下的社会形态和文化风貌,为读者再现了东西方文化冲撞下的出岛众生相。事实上,当我们仔细阅读大卫·米切尔的其他作品,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作品都包含了历史元素,“历史”的影子一直若隐若现地浮现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读《骨钟》,作家用明确的年代勾勒出整本书六个故事发生的时间线:1984—1991—2004—2015—2025—2043;[3]读《幽灵代笔》,会不时读到这样的语句:“说到一个叫孙逸仙的人,一个叫俄罗斯的人,还有一个叫欧罗巴的人。”[4]读《云图》中第二个故事“西德海姆的来信”,作家借由主人公,落魄的音乐天才罗伯特·弗罗比舍推测出第一个故事“亚当·尤因的太平洋日记”所发生的年代:“从我努力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这是一本编辑好的旅行日记……书中提到了淘金热,所以我猜故事发生在1849年或1850年。”[5](P132)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作家在叙事中运用如此清晰的年代、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一方面,意在通过历史书写暗示出故事发生的历史场域,同时结合女性书写,作家尝试证明,女性的命运与历史紧密相连,女性在复杂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挣扎求生,暗示了女性人生悲剧发生的成因之一是无法摆脱的历史力量。另一方面,作家对于作品中历史场域的设置,从文本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与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视角的个人化”[6](P222)是一致的。作家并未正面叙述历史事件,而是以女性的视角切入,让女性来还原、反思历史。女性面对历史困境和命运压迫所表现出的非凡的坚韧,不为命运所打到,努力求生,完成自我的救赎。这种表面消极被动实则积极主动的反抗消解了以男性为主导的宏大历史叙事。本文将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观照下,通过文本细读,对米切尔几部代表作中的女性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评析蓝场川织斗、圣山老妇等独特的女性形象所负载的历史的、时代的思想内涵。
二、历史困境——女性无法摆脱的宿命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有关场域的理论,社会空间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场域,在这些场域中,个体“被抛入这个空间之中,如同力量场中的粒子,他们的轨迹将由‘场’的力量和他们自身的惯性来决定”。[7](P15)可见,个体的轨迹即其生存和发展无不受到他们周围的历史场域的巨大影响。在米切尔的多部作品中,展示了历史力量如何影响个体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的命运走向。在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他的创作是否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时,米切尔回答:“我希望能表现历史如果塑造一个人物,同样在这样的历史塑造下一个人会如何改头换面……历史很重要,因为历史同样创造和影响了现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记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共同创造了这个国家的记忆。”[8]在米切尔看来,历史书写不仅仅意在对历史进行想象性建构,其深层目的在于描绘历史语境下个体的生存状态,以及探讨历史如何影响个体的命运、如何使人性得以彰显。这与新历史主义有关新历史小说家反顾历史的目的不谋而合。蔡翔教授认为,区别于编年史料在时间维度上再现真实发生的历史,“重新关注个人在历史践踏中的悲剧性命运”才是新历史小说家关注历史的真实目的。因此,每一位新历史小说家都应以“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人性,个人在此在的幸福价值,明显的人道主义特征,尤其是对个人、终极价值的深深眷注”为己任。[9](P63)
米切尔笔下的历史书写和女性书写是以一种胶着的状态来呈现的,作家将“浓缩”的历史在一个个女性人物的身上铺陈开,借由女性的个人视角透视历史。《幽灵代笔》中“圣山”篇以“我”——一个四川腹地大山里的女孩的视角,再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跨越了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的时间线。“我”是圣山上一个普通卖茶小店人家的女儿,当“我”还是个女娃儿的时候,就被大烟鬼父亲以一只银碗的要价出卖给军阀之子,之后惨遭强暴蹂躏,“我”失去了贞操,并因此怀孕生下私生女。为了掩盖这个私生女给家族带来的耻辱,“我”的女儿被偷偷送给一个大户人家收养,“我”在对女儿的无限思念中度过了残破的一生,直到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之时仍然没能和女儿见上一面。圣山老妇的悲惨遭遇并未引起他人的同情,相反地,少女时代惨遭凌辱的经历像个幽灵一样如影随形,成为她背负一生的耻辱。她的亲人和家族以她为耻,她每天活在世俗的冷漠、白眼甚至是谩骂中,歧视和辱骂不仅来自于男性,“妓女”“婊子”这类不堪入耳的词汇时不时从那些同为女性身份的女人们恶毒的嘴里吼出来。
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长崎,社会等级森严,各阶层被严格划分为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等级。伴随着18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幕府的统治岌岌可危,由于害怕统治受到威胁,幕府决定对外实行锁国政策,严禁与外国贸易,只许同中国、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政府为此专门建造了一个供外国商馆办公和生活的扇形人工岛——出岛。此地是锁国时期日本唯一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对于日本后来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雅各布·德佐特的千秋》的故事正发生于此背景下。作家抛弃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而是借助蓝场川织斗和不知火神社众尼僧为代表的一群特殊女性群体之视角,揭示了这一时期女性群体,尤其是残疾女性群体的边缘地位和悲惨命运。助产士织斗年少时因烫伤导致永久的面部缺陷,其后父亲离世,家道中落,失去了庇护的织斗被伪善的继母抵债卖给峡河藩藩主榎本,之后被送入榎本掌管的不知火神社。这个神社以收容身体有缺陷的女子为名,从妓院和畸形人表演场所诱骗女性至此,强迫这些女性出家。表面上,道貌岸然的榎本大人是受人尊敬的芝兰堂学者和乐善好施的药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名人,却是阴鸷邪恶的。他迷信长生不老之术,在他的授意下,不知火神社的僧众定期与尼僧发生关系,迫使她们受孕并生下婴孩。再按照所谓的身怀六甲、塑过金身的女神的指示,溺毙婴孩后炼制丹药,再将它们装入瓶中服用,以期能够长生不老。为了长期控制这些女性,神社对她们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奴役。精神上她们被训诫崇拜女神,背诵《感谢经》,理由是,女神能保佑峡河藩河水丰盈,五谷丰登;生理上她们被施以慰神汤这种毒品,导致她们对药物产生依赖,由于毒药在她们体内日积月累,这些可怜的尼僧一直以一种病态的状态苟延残喘,身心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更加令人恐惧的是,由于神社缺乏专业的助产士和医疗设施,这些可怜的尼僧分娩时难产率非常高,许多尼僧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命。即便她们幸运地熬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劳役,也终究逃不过一死,在下山前神社的法师会残忍地下毒,当她们对神社和主持大人千恩万谢后重返凡尘俗世,等待她们的将是被埋葬在春林客栈后的那片竹林。
历史在个体的命运走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导致这些女性悲剧命运的成因中,历史的力量无处不在。圣山老妇、织斗和不知火神社众尼僧之所以被压迫,表面上是因为她们的女性身份,然而,剥开这层表象,其内核依然是历史场域强加给她们的苦难。作为女性,“我”,一个无名的、卑微的小人物,生于一个女性处境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年代,经历了物质匮乏的少女时代,经历了被唾弃和被凌辱的青春岁月,“我”无法抗拒地被裹挟进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舞台。在这里,各种政治势力角力,而所有政治势力的杀伐争斗,带给“我”的是被毁的一生。“我”承受和容纳一切的苦难:饥饿、病痛、颠沛流离、痛失自己的女儿、孤独终老。同样,作家将织斗的生命轨迹作为一个点,映射的正是当时日本女性的艰难的生存状况。日本女性极低的社会地位可以追溯到大化改新(公元645年)之前,到江户时期更是发展到极致。在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结构、儒家和佛教三股势力施压下,女性被要求“三从四德”,要努力成为武士的贤妻、顺妾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在此意识形态下,女性背上了沉重的枷锁,被歧视、禁锢,人格尊严丧失殆尽,即便是出身名门的蓝场川织斗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父亲去世之后,她从尊贵的小姐沦为仆人,被虐待,甚至差点被继母的儿子强暴。因为父亲生前留下的债务和自己容貌的缺陷,她和青梅竹马的恋人绪川宇左卫门的爱情无疾而终,眼睁睁看着恋人遵从养父的指示,娶了一名商人的女儿阿绢为妻,而婚礼之前二人甚至从未谋面,这场婚姻就是一场交易,各取所需。宇左卫门口中的妻子也是个可怜人,因多次流产无子嗣,在绪川家受尽白眼,即便是同为女性的婆婆也不待见她。宇左卫门善良、正直,可他无法忤逆养父的命令,尽管阿绢对他百依百顺,但完全不爱妻子的他,如何真心待她。圣山老妇、织斗、不知火神社众尼僧这群女性污秽、龌龊的生存状态,唤起读者的无限唏嘘和一种令人压抑的内心感受:希冀却求而不得,渴望却无法摆脱历史的困境。
三、救赎——夹缝中坚韧地求生
新历史小说中,人占据了全部的文本,小说家致力于表现人对生命、对劳作、对生存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其中,对生命的关注是第一位的,在他们看来,一个人生存价值的体现就在于活着本身。因此,大多数新历史小说家会致力于描述个体在困境中如何坚韧地求生,米切尔曾经在专访中谈到小说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他表示,尽管他作品中所有的角色发生在不同的年代,但他们的性格,或者说人性是不变的,“人性是广谱的不以时代或者社会改变而改变。”[8]小说家应关注这些人性如何表达以及以何种方式来表现自我。小说家的责任在于探究人性和提出问题,优秀的小说家并不负责解决问题,而是向人类提出新的问题。细读他的作品之后发现,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具备一定的共性,即她们依靠女性的力量,穷尽一切方式,在历史困境和女性困境的夹缝中走出了一条救赎之路。
战争带给人类尤其是女性的创伤是无法被忘记的。《幽灵代笔》“圣山”篇中作家借“我”之口,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娓娓道来。在“我”的注视下,历史风云变幻,社会更迭交替,各色人物悉数登场,所有的军队和政治势力都是不请自来,赶也赶不走:“日本人拆了我们的茶社”“国民党来了,有两千人”“国民党比日本人还凶,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狼”。[4]女性承受历史的苦难却不懂历史,她们是历史被动的承受者,正如“我”所说,“总是穷人来承担这一切。而且,总是穷人中的女人承担得最多。”[4]面对他人的欺压,我在内心一次次地告诉自己,“如果我是个男人,我会冲下楼梯,一刀捅进他背上”[4]“如果我是个男人,我早就把他丢到粪坑里头去了,管他是不是当官的”。[4]然而,我的愤怒终究没有付诸实施,“在圣山上,愤怒是没有意义的”。[4]为了卑微的生存,“我”收藏起愤怒,“我”隐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历史对女性的压榨和命运对女性的戏弄。每天,“我”带着最深的悲哀醒来,“我”的避风港——我赖以维持生计的茶社一次次地被摧毁,而“我”在废墟上又一次次地重建。“我”只不过是圣山上一个不起眼的老太太,“我”缺乏历史理性,一切形而上的东西与“我”无关,只能用宗教来解释和容纳这一切。“佛主经常告诉我,宽恕对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不是为了被宽恕者的幸福,而是为了宽恕者的幸福。”[4]“我”需要反复地用对他乡的女儿的思念化解创伤,这是“我”唯一的权利。没有政治虚荣心的“我”本能地疏远政治,当时代迈入改革开放,一位记者上山找到“我”,想以“我”为原型写一篇题为“70年代的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的报道。这位记者认为老太太目光远大,具有前瞻性和远见,在70年代人人关注政治远离生产的时候,唯独她头脑清醒,一直坚持做茶水生意,于是便出现了荒诞的一幕。关于“我”的描述与“我”本人的自叙构成一对极端矛盾体,记者笔下的“我”:“您是一个真正的先行者……您是‘下金蛋的奶奶’。”而真实的“我”:“我不是啥子先行者,我住在这儿,是因为我没得其他选择。”尽管记者一再坚持,“我”依然婉拒:“我的工作不是让你的读者感兴趣!我的工作是下面条,泡茶!”[4]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风云变幻,老妇人选择坚守在圣山,圣山接纳了她,这使她得以保持性格的率真、质朴,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在苦难中练就了一身的生存智慧,她挺过了所有的灾难活了下来。即使命运对她施加了很多痛苦,但是她依然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寻得一条出路,并且义无反顾地作出决定并勇敢表达。
如果说圣山老妇的救赎是通过宽恕历史和施暴者来实现,那么,织斗的救赎则是通过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身份的重构两个步骤完成。织斗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她坚持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追求学识,和面对历史懵懂无知的“我”不同的是,织斗这一女性形象似乎得到了作家的偏爱,作家赋予她过人的才华、胆识和高洁的品德。她出生于书香世家,对于医学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父亲蓝场川静庵是一位开明的武士和学者,热衷于翻译荷兰语典籍。他尊重织斗渴望求学的愿望,拜托好友荷兰医生马里纳斯收女儿为学生,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正是得益于她的求学经历,作家在小说开场用一个完整篇章详细描绘了助产士织斗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冷静果敢,拯救了城山奉行的儿子。这是一场紧张、困难重重的助产,长崎奉行的小妾川蝉由于骨盆狭窄,胎位不正导致难产,一向保守的城山奉行不得不请来在出岛办学的荷兰医生马里纳斯,由于分娩时间过长,几乎所有人都认定新生儿已无救活的可能,但作为助产士的织斗沉着、冷静,按照标准助产操作步骤一丝不苟地对新生儿进行急救,奇迹般拯救了婴儿。织斗的女性主体意识还表现在她对自己容貌的坦然接受上,面对他人异样、猎奇的目光,她从不刻意隐藏自己烫伤的面孔,甚至敢掀开头巾,“呶,看个够吧!”[1](P196)可见,她对外貌之于女性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女性生命的全部价值绝不是为了用一副姣好的容貌为自己挣得一份好姻缘,女性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都应当是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个体。因此,当荷兰人雅各布·德佐特向她表达爱意之时,织斗并不打算接受这位年轻人的求爱,因为那样的话,无异于承认自己和其他的出岛商馆官员豢养的情妇并无二致。
新历史小说认为,在生存不具备最低限度的条件时,人的本能生命是如何被吞噬和毁灭的,只有在极端艰难的历史语境中,个体的全部人性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那些在困境中坚韧不拔,始终保持人性中善良和光明的一面的个体无疑是真正的英雄。米切尔笔下的织斗是一个十分真实、丰满的形象,作家毫不避讳对于她人性深处进行描写,写出了她的恐惧、懦弱。在未被出卖前,织斗的人生轨迹虽称不上圆满,但总体保持上升趋势,然而,绑架强行改变了这一轨迹,一同改变的还有她的身份。她陷入了空前的身份危机,此时,人性的弱点才逐渐显现出来。在不知火神社被囚禁的日子,作家运用大量的心理描写,写出她由高贵跌落至尘埃的复杂心境和由此带来的身份困惑:“我已经不再是谁的女儿了”[1](P198)“我本不该在这儿的”“我不属于这儿”[1](P204)“你能找来这么多女人,干嘛偏偏夺走我的生活”[1](P220)“就算做出岛夫人,让外国人用钱来保住自己,也好过授礼周会发生的事”。[1](P302)与其他尼僧相比,“我失去的比她们要多”“我……接受不了他们对其他女人做的那种事。我不行”[1](P219)“在揭晓授礼之日的大‘喜’日子,她害怕极了,难以忍受与神社僧人‘交合’这种令人作呕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地祈祷:‘可别是我’‘可别是我’……”[1](P274)尽管说出此话的织斗为自己的话感到羞愧,但人性使然,她的恐惧、柔弱在作家笔下惟妙惟肖,使得这个人物形象立刻跃然纸上,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读者一下子被她真实的内心紧紧抓住。有了这层铺垫,其后织斗侥幸获得了一次逃生的机会,读者不禁期盼着她一定要逃出神社。囚禁、慰神汤和女神崇拜加重了织斗的身份危机,她知道自己必须逃离压迫她、禁锢她的神社,才能实现主体的自我救赎。于是,她偷偷拒绝服用慰神汤(防止生理上受控制),坚持穿自己的衣服(杜绝被其他尼僧同化),假装配合神社的规定(消除寺僧的戒心),直至最终找到了一条逃生通道(发现神社的邪恶秘密),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神社的高亢、急迫的钟声从远处传来,她的好友弥生即将分娩,由于骨盆异常狭窄,且是双胎妊娠,弥生发生难产的几率几乎毋庸置疑。助产士织斗在激烈地思索着,“蓝场川的自由要比弥生和她的双胞胎的性命更重要”“但我还是助产士……”[1](P196)她放弃了出逃,回到神社,拯救了弥生和她的孩子。织斗的顿悟象征着她身份的重建,她不再是名门之后,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从犹豫不决、质疑到坚定地牺牲自由为代价,以拯救其他更弱势群体的性命,她的选择隐喻着生存以及欲望本能驱使下逐渐凸显与被关注的全部人性,使得这位女性身上流露出一股侠骨与正气。
四、结语
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评析大卫·米切尔作品中的历史和女性的双重书写,对于人性剖析和时代再现有着深刻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米切尔的作品中有厚重的历史气息,书中字里行间溢出的是一群特别的女性对于历史场域的观感和思悟。它不是正统历史教科书或者传统史书对于史实的重述,而是作家对历史进行的大胆的想象和虚构。米切尔作为一名男性作家,选择女性的叙述视角,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的身份来讲述历史,将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沉默的女性推到台前,通过女性的生命历程来建立和体现历史段落。这种立足于女性个体本位的艺术手法,既反映了作家的女性观,即女性依靠女性自己的力量完成自我和他人的救赎,同时又表明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处在最底层的苦难人民的悲悯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