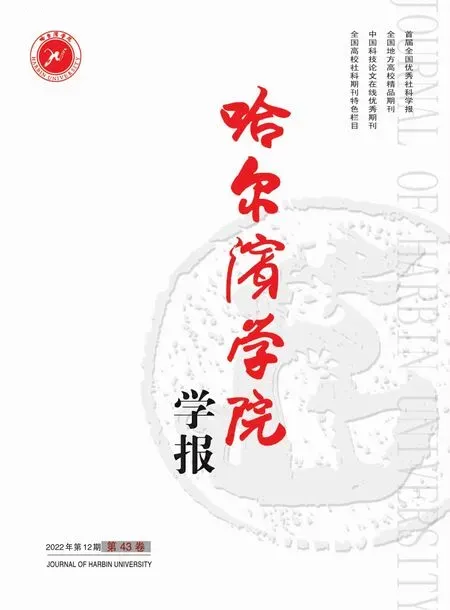凝视与被凝视间:《神秘的河流》中索尼尔主体身份建构
2023-01-04王秋雨
王秋雨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神秘的河流》是澳大利亚文学中一部著名的和解小说,讲述了被流放到澳洲的英国人索尼尔携家带口在澳洲建立新家园的故事。索尼尔作为从英国移民到澳洲的典型代表,他的心路历程是不少澳洲新移民的共同心声,而作者格伦维尔借助索尼尔一家的经历为澳洲新移民发出声音,澳洲土著的形象也在澳洲新移民的视野中跃然纸上。在书中作者有成功地复原了澳洲移民的悲伤和痛苦记忆,对澳大利亚历史叙事作出补充和修正。
《神秘的河流》因讲述的是白人对土著居民进行殖民的历史,所以被认为是翻版《鲁滨逊漂流记》,但事实上,两个主人公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鲁滨逊在小说中被丹尼尔·笛福描写为典型的英勇殖民者形象,而格伦维尔摒弃把白人描写为纯粹理性文明者的惯例,她打破传统的黑白二元对立,试图还原白人殖民者的真实样貌。作为格伦维尔笔下的澳洲新移民,索尼尔的身份建构之路坎坷崎岖,在他者凝视下,他的主体身份经历了从建构到被解构再重构的艰难历程。关于主体性和凝视的关系,萨特认为注视在建构人的主体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P347)而拉康却认为人一直追逐的主体性是流动的、不稳定的;[2](P354)福柯则认为凝视中蕴含着话语和权力。[3](P52-53)结合这三种观点,可将索尼尔的一生看作是以寻求稳定的主体身份为目的,在他者凝视中不断构建自身主体性,并通过凝视创造自身权力场从而巩固主体身份的逐梦旅程。下文将从萨特、拉康和福柯等的凝视理论出发,探究索尼尔的主体身份是如何在凝视中建立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异化,再又是怎样重构起来的。
一、在他者凝视中主体身份的建构:索尼尔对命运的成功抵抗
《西方文论关键词》对“凝视”作出解释,认为:凝视是携带着权力运作或者欲望纠结的观看方法……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2](P349)索尼尔的一生就处于凝视与被凝视间,在观者与被观者的身份之间来回转换,既感受过当被观者时被压迫的无助感,也体验过当观者时居高临下的主宰感。拉康的凝视理论认为,眼睛和凝视分裂,凝视无处不在,主体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已,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处在流动之中。那在凝视与被凝视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保持主体性?索尼尔在英国的寻家旅程中给出答案,他向具有权力压迫和侵犯的凝视目光投去具有对抗性的反凝视目光,不断消解他者凝视的权力性,也在他者凝视之下获得身份认同从而建构起主体身份。
索尼尔在家乡英国伦敦时,多半处于被观者的位置,承担着观者目光的权力压迫。索尼尔自幼家境贫寒,童年生活饥寒交迫,生活的地方“可以看到下层人的房屋屋顶”,“附近是制革厂、屠宰场、制胶厂和麦芽作坊,空气里弥漫着臭味儿”。[4](P9)随后贫穷的种子种进索尼尔心里,在上帝的住所——尖塔下面他甚至会“感到眩晕、迷惑、燥热而且有点惊恐不安”,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显得冰冷无比,找不到一个令人愉悦的可以栖身的角落”,[4](P10)上帝宅邸给索尼尔的压迫感成为他之后漫长寻家旅程或者说寻找主体身份之路的激发点。在激发他寻找主体身份之前,这有着“无情的光亮”的来自上帝的凝视对索尼尔来说首先是具有权力压迫性的,这种权力将他置于可见性的空间,在上帝无处不在、无所不见的凝视下,索尼尔感觉自己在上帝的完全可见下弱小无助、无能为力。在索尼尔的童年时期,他者的凝视不仅来自于上帝,也来自于他的家人和社会文化制度。在母亲的眼光中,他被定义为“贪婪的小家伙”,在兄弟姐妹中,他也是处境尴尬、总是被排挤的那个。用拉康的“镜像理论”解释,他身边的家人就像是一面镜子,在他们对索尼尔的印象反馈中他知道自己是贪婪的、庸俗的、不值得被爱的,索尼尔也由此不自觉地把这些标签内化。萨特的一句关于“注视”理论的描写能很好地概括童年索尼尔的心理状况:“我的真实,我的性格,我的名字,它们无不操在成年人的手里。我学会了用他们的眼睛来看我自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它们不无遗憾地创造出来的怪物。”[5](P58)索尼尔由此在家人的凝视下被塑造成一个“怪物”。另外,社会文化制度的凝视力量也不容小觑,无形却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在上等人的眼里,“索尼尔不过是一个系船柱而已”,[4](P31)他几乎是不可见的。这种对他可见性的否定直接剥夺了他作为对象——他者而存在的权利,而人的自我和他者身份本就交叠。也就是说,除了家人之外,社会文化制度对他的主体身份也进行了否定。家人、社会文化制度、上帝等凝视的力量把他捆绑在被“看”的位置,让他对自己的认识也被束缚在这些“他者”的眼中,使他困扰痛苦。
然而,他者的凝视并没有完全束缚住他对自我的探寻,他也在努力冲破他人的目光,打破对他者的镜像性身份认同,向他人投去反凝视目光。在反凝视的目光中,索尼尔由往常的被观看者角色转变为观者,这种身份的自我主动性逆转使他的主体性逐渐确定起来,他者凝视的权力性也由此得以消解。在面对姐姐的恶语“你的名字像污垢一样庸俗,威廉·索尼尔”时,[4](P11)他径直回击,“威廉·索尼尔会占满全世界的”;[4](P11)在被上等人亨利夫妻低看时,他内心也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竞争比赛中,他都能战胜那个叫亨利的男人,尽管他只是一个船夫”;[4](P30)在面对教堂门口两头得意洋洋的狮子时,“他从怀里掏出烂泥,朝最近的那头猛掷过去”。[4](P19)索尼尔通过自己方式向那些消解他主体身份的他者们投去反抗性的凝视目光,这种对抗性的策略使他在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建立起自身主体性。索尼尔主体性的建立不仅得益于自恋式认同,也获益于他人的认同。根据萨特的凝视理论,他者的注视能让人的主体性消解,也能确立主体身份。这“确认”的力量主要来自于他妻子萨尔的凝视,在萨尔的凝视下索尼尔的理想自我形象得到确认和肯定。在萨尔眼里,索尼尔对她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威尔”,而不是大众化的“威廉·索尼尔”;他是在教导下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很棒的威尔;他是能给与她幸福和未来的威尔。索尼尔在反注视萨尔的目光中能感受到萨尔对他的爱与支持,索尼尔正是在凝视—被凝视的过程中认识到别人眼中的自己,他在被凝视时由观看主体变为客体并不意味着他主体地位丢失,相反,他的主体地位在他人对他的认同性凝视下得到加固。
在英国,童年时期的索尼尔的主体身份在家人、社会文化制度、上帝等具有压迫性的他者凝视下是支离破碎、不完整的。然而,他有强大的自我身份建构意识,他深知在他者这面镜子面前,他看到的始终是幻象,是虚幻的存在,并不一定真实。所以,虽然他活在他者的凝视下痛苦、混乱与不安,但他能主动去对他者的凝视进行辨别取舍,在想象中逃避一直被权力凝视的事实,否定他者对自己的消极凝视,然后发起内视,即自我观看,他者凝视的权力性由此得以消解。同时,索尼尔在他人对自己的认同凝视目光中主体身份得以建构和巩固。
二、在他者凝视下主体身份的异化:索尼尔在欲望中堕落
作为意识形态,凝视是携带着权力和欲望的运作模式。凝视理论的基础和核心要义就是:自我与他者(作为主体的他者和作为对象的他者)是一种凝视关系,凝视始终与权力和欲望联系在一起,与主体性联系在一起,凝视暗示了存在之可能和权力之行动。[6]在英国时,索尼尔最强烈的欲望就是娶萨尔,和她组建家庭,可当家的居所失去后,他再次陷入不安,机缘巧合下他们一家被流放到澳洲——一片充满希望的处女地,索尼尔的欲望被再次强烈激发出来,土地和黑人成为他凝视下的欲望客体,是他在澳洲寻家过程中一直寻找的用来再次确立自身主体身份的他者。在确立欲望客体的过程中,索尼尔试图通过凝视创造自己的权力场,将黑人和土地都纳入权力监视范围,最终结果是土地如期获得,黑人却在索尼尔凝视的权力场中消失。虽然后期澳洲新移民的到来代替黑人作为索尼尔凝视的客体对象,黑人这个凝视客体的丢失不会使索尼尔的主体身份建构从此停滞不前,但如果考虑到索尼尔到澳洲后的夙愿——征服黑人,争做“殖民者”这个事实,黑人这个历史上由来已久的被殖民者的缺失或不在场使得索尼尔的主体身份建构始终是不完整的。同时,作为造成澳洲土著黑人消失的凶手之一,他的道德已经在欲望中沦丧,道德的缺失是索尼尔主体身份建构中永远的缺憾。
首先,在索尼尔和黑人的凝视与被凝视间,索尼尔的主体建构逐渐崩塌。索尼尔自从知晓澳洲土地上有澳洲黑土著的存在后,就立志要征服他们,成为和鲁滨逊一样的“殖民者”。
正是在凝视与被凝视者的相互运动中,人类原初的主客体关系即“主—奴”关系才开始建立起来。[7]为实现这种“主—奴”关系,索尼尔先是从知识—权力入手。根据福柯的权力观——凝视背后是知识和权力的运作,索尼尔就试图借助知识实现对澳洲土著的权力压制。在索尼尔朝思暮想的土地被土著翻过之后,他大放厥词:“那些可怜的黑家伙们什么都不会种。”[4](P135)即使这时黑土著并不在场,但此话能表现出索尼尔在知识层面上对黑土著的权力凝视。之后,索尼尔决定从视觉上否认黑土著的存在,在黑土著的领地上缕缕青烟升起来时,“父子二人都看在眼里,但不约而同地对其视而不见。”[4](P143)索尼尔通过漠视黑人的方式试图否定他们作为客体/主体的存在。最后,索尼尔试图通过建立话语,创建自身权力场。福柯的凝视观认为,话语的建立有助于自我形成对他人的凝视,“掌握了话语,就能拥有权力,而拥有了权力,也就生产出更多的话语。”[6]在和黑土著对峙时,索尼尔总是努力掌握话语权,“怎么不吭声啊,你们这些黑鬼?”[4](P190)他还总是强迫自己打断土著的讲话,让自己在话语上拥有优先权。通过这些策略,索尼尔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凝视者——主体,把土著定位在被凝视者——客体的位置,由此保证想象中自己的光辉殖民者形象,证明威廉·索尼尔是最先到达霍克斯布里的人,是最先征服黑土著和土地的人。
然而,这些策略都以失败告终,黑土著并没有在索尼尔的强制策略下成为权力凝视下“被规训的肉体”。相反,他们在自己反凝视索尼尔中逆转主客体位置,争夺凝视者的话语权:“对于眼前这个带着帽子穿着裤子的男人,她没有一丝畏惧,她说每句话的时候都不容质疑。”[4](P189)通过建立自身话语漠视索尼尔话语的方式,黑土著让索尼尔的权力凝视得以消解。黑土著们的凝视在格伦维尔的描述下更是无处不在、神秘未知:“索尼尔会不时地瞥见有人在盯着他们,但正当他要起身之时,那人便不见了踪影,只留下一些相互交错的枝枝丫丫”,[4](P146)他们隐匿的、如影随形的目光中体现着他们类似于全景敞式监狱的权力运作机制,像一张无形之网笼罩在索尼尔领地上空,监视着索尼尔一家以及其他澳洲移民们,而移民们却无法确知监视者——黑土著的真实状况。在这种常态化的监视目光下,索尼尔已经成为凝视的客体,成为无主体性的对象——他人。主体性的丢失助长他焦急愤怒的情绪,因为对黑土著的权力掌控已不再可能,他消灭黑土著夺回土地权和话语权的欲望由此愈加强烈,索尼尔人性的异化也由此开始。
在索尼尔与白人同胞的凝视与被凝视间,索尼尔异化的主体身份被确认并逐渐加深。索尼尔作为澳洲新移民中的一员,生活离不开和白人同胞的相处。首先,家人是他最为亲密的凝视者。因为索尼尔受欲望驱使,一次次辜负妻子萨尔和孩子的信任,甚至有想要打妻子和儿子的行为,所以在妻子萨尔不断质疑的眼神、儿子迪克反抗的眼神里他变得不再值得信任。索尼尔在家人的眼里逐渐异化为野人形象,野蛮好斗,脾气易怒暴躁。根据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观点,“他人的注视对我的存在产生摧毁效果的作用,这种注视使我‘异化’。”[6]家人——主体的目光成为逼视索尼尔——他者的地狱,他如照镜子一般看到家人眼中自己的动物性行为,从而将家人对自己的注视当做自己的可能性,并将其意识化。虽然他在家人这面镜子前发现了自我分裂和异化,但耐不住欲望驱使,他在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同为澳洲移民的白人邻居对索尼尔的看法也会加深索尼尔的主体异化。老赫林太太对小说中的男性处于无时无刻的监视中,索尼尔也在她的凝视之下。她的凝视类似于上帝对他的凝视,是一种不在场但又永恒的存在,将索尼尔置于完全可见的状态下。他参与黑土著大屠杀的秘密在她的凝视下昭然若揭,他的罪恶和主体异化的事实在赫林太太的凝视下被确认。
在英国时,土地和殖民者的权力在索尼尔那里就是不足、匮乏,但在澳洲,这里有新的处女地和黑土著,于是他对他者(不足、匮乏)的欲望被唤醒,踏上对能证明自己主体身份的他者的追寻之路。索尼尔在澳洲的寻梦过程中其主体性就在不断地被他者否定、去中心化。首先是在黑土著——他者的凝视下他看到自己的无能、欲望和愤怒,他的主体性也在黑土著的否定下开始瓦解。后来在家人的凝视下他感受到家人对他的不信任和不认可,他的罪恶行径也接着越来越多。在赫林太太的凝视下他的罪恶仿佛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步步地,他人性的异化加深,异化主体被逐渐确认。索尼尔在他者的镜像性认同中,良知渐失、道德沦丧的异化主体在叠加的想像中逐渐确立。
三、用他者眼光重构主体身份:索尼尔在想象中重生
“凝视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是一种与想象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但凝视本身所印证的只是欲望对象的缺席和匮乏。……凝视所诱发,携带的幻象,是欲望的投射,观看主体希望沿着缺席(欲望对象的匮乏)到达在场(欲望的满足),但我们所能达到的只是欲望本身——那个掏空了的现实的填充物。”[6]索尼尔的凝视中蕴含的对土地和权力的欲望使得他逐渐迷失自我,从欲望对象的匮乏到欲望满足,他获得欲望客体,但同时其主体身份也在对欲望的盲目追逐中异化。为抹去罪恶的历史印迹和难以摆脱的历史记忆,索尼尔决定在他者凝视中重塑自我,建立一个全新没有污点的自我新形象。要建立起这种全新形象,索尼尔使用两种方式:一是选择性接受他者凝视,主动接受他人的积极凝视,获得自我认同感,有意识逃避忽视他人的消极凝视,这与索尼尔在英国时对他者的消极凝视投去对抗性的反凝视有所不同;二是自我,即作为主体的他者,对自己进行积极凝视,对自己进行自我赞扬鼓励式的自我暗示。
首先,索尼尔试图在他人的肯定、积极的凝视目光中重建主体身份。“在那些新来的居民看来,威廉·索尼尔有几分像国王”“他的妻子则有几分像皇后”“索尼尔非常乐意别人称呼他先生,每次听到有人这么叫他,他都觉得非常愉快”。[4](P308)在新来的移民的凝视中,他光鲜亮丽,生活富足幸福,值得尊敬,他也欣然认同这面镜子前的自己,潜移默化地将新移民对他的凝视内化,重新构建自身主体。当然,在旧移民的眼里,索尼尔在他们眼中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但他们选择沉默不语。索尼尔在向外人吹嘘自己精心编造的关于自己过去的故事时,萨尔默不作声;在索尼尔探望布莱克伍德并试图跟他讲话时,布莱克伍德也只是聆听。纵使在他们的凝视中,索尼尔能回忆起过去不堪的自己,但索尼尔在他们的静默中能选择回避这种凝视,努力忘记过去,用新编造的美好回忆代替丑陋的过去。索尼尔一面迎合他者的镜像性认同,在积极凝视下重获自信,重建主体身份;一面化被动为主动,打破他者的镜像性认同,有意逃避他人的消极凝视以实现主体的顺利重构。
另外,索尼尔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观看模式“看到自己观看自己”。索尼尔在镜像前制造出一个虚幻美好的自己,并努力让自己相信眼前的这个自己,例如他让画家给自己画一幅肖像画并把它摆在客厅,“这幅肖像时刻提醒着索尼尔他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人物了。”[4](P314)他还把自己的过去美化一番,在他精心编造的故事里,他“并不是出生在肮脏的柏孟塞,而是石灰崖旁边干净整洁的肯特州。……他并没有因此而被判刑绞刑,因为他的这次行程是为英国君主效力的,目的是往法国运送英国间谍。”[4](P315)通过这些方式索尼尔把自己想象中的幻像——一个体面干净、较为光辉的间谍形象强加在自己身上,而这种想象的关系作用于主体,参与了索尼尔的主体建构。索尼尔在自己编织的理想形象中确立主体身份,获得满足感。另外,他还在门柱旁边放狮子宣示自己的领地归属权,雇负责做饭洗衣、帮忙梳洗的女佣,通过这些方式他试图在澳洲复制英国社会下的等级关系,在这里他成功把自己过去的被雇佣者、被凝视者的身份逆转为雇佣者、凝视者。索尼尔充分运用自己的眼睛,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自己塑造的幻像下,顺利完成从对欲望的追求者到他者欲望的对象的转变。
索尼尔在这两种方式下自身的主体性被建构起来,但建构起来的主体始终是不稳定的,在变化的。在黑土著几乎被全部消灭后,澳洲新移民步入了平静安宁的生活,索尼尔表面上过上了富足有尊严的生活,但其内心的愧疚感、自责感一直挥之不去,“他经常感到这只是一个精心编织的美梦罢了。”[4](P310)他深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制造的幻象,这里像英国又不是英国,像家却又不是家,他看上去仁善慷慨却又内心丑陋不堪,他知道自己好似占有了这片土地但又知道这片土地从根上并不属于自己,他活在虚荣自满与自责愧疚的深深矛盾之中。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如果把照镜子的索尼尔看作“能指”,那么索尼尔在镜子中的成像则是“所指”。索尼尔看到的镜像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意义”,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结合并不是稳固的。也就是说,索尼尔所看的镜子中的成像始终是幻像,他在向幻像靠近,却无法和幻像完全贴合,索尼尔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始终是有缝隙的。在结尾处,作者特意描绘了索尼尔望着山崖缅怀黑土著的场景,“他说不出自己为什么要一直坐在这里。他只知道凝视着望远镜中的事物是唯一能给他内心带来平静的方法。”[4](P328)所以,因为索尼尔过去犯下的无法弥补的过错,他与他的理想形象始终是有差距的,他的主体建构虽然表面上完成,但始终是不完全的、不稳定的。
四、结语
索尼尔个人主体身份的困境不仅仅是个人困境,也是整个澳大利亚非土著移民群体的困境。他们的主体性在凝视与被凝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又逐渐异化,再又重建,他们在权力的欲望和道德的谴责中徘徊前进。格伦维尔的笔下索尼尔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对黑土著残忍无情,时而又对黑土著仁善慷慨;时而想要抹去历史重塑自我新形象,时而又想缅怀历史警醒自己。索尼尔内心的矛盾也折射出白人作者格伦维尔的内心所想,作者实际上也深陷在力图反殖民和不自觉陷入种族二元对立的矛盾中,这也是有些学者认为《神秘的河流》是反殖民的,而又有些学者却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为种族主义行为辩护的原因。通过凝视理论的新路径解读这部小说,以索尼尔为代表的澳大利亚非土著移民的主体身份建构之路和作者创作这部作品时的矛盾心理会更清晰直观化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对澳洲移民史和白人殖民史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