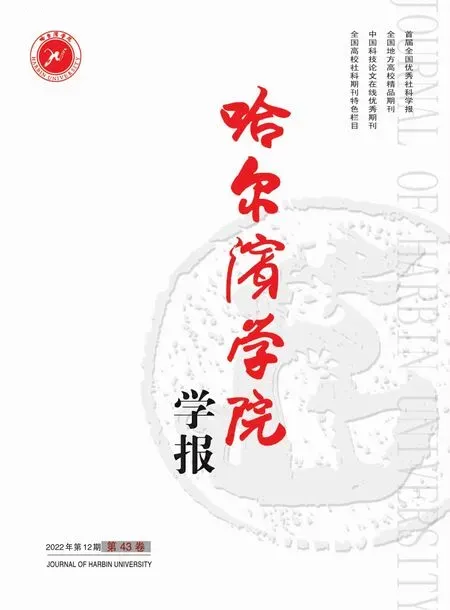西方政治生态的民粹主义转向
——兼议疫情之下的政治危机
2023-01-04陈子雄
陈子雄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自现代性发轫以来,“否定元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形塑了当代西方世界图景,社会、信仰与文化的异质和冲突难以弥和,一时间各种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甚嚣尘上。从英国脱欧公投,到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从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到抗疫期间令世人震惊的美国社会暴乱,这些民粹主义政治的典型极化现象表明,西方世界正面临着政治与社会生态的重大变革与开裂,“集体右转”的民粹主义倾向正重新塑造着西方所谓“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态。在疫情期间西方社会中政治精英的缺位与不作为、各政党间的相互倾轧与抵牾、社会救治的无序,都在显现着民生制度的失效,实质上昭示着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端倪。
一、西方民粹主义的发轫与泛滥
近年来西方民粹主义政治运动频频上演,冲击着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成为西方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奇观。疫情期间,美国多数城市陷入了大规模冲突和骚乱之中,人们走上街头抗议,作出大量反建制的举动,由此可以窥见新自由主义的整体式微。毋庸讳言,西方的政治危机无情地打破了“历史终结论”的迷梦。“政治混乱、经济凋敝、文化冲突、社会断裂的现代性危机,催化了哲学范式的重大嬗变,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1]后现代主义盛行下,民众的反建制、反理性、反精英的趋向愈发显现,从宏大叙事到普世价值、从政治结构到社会体系、从传统建制到精英主义,人们质疑一切、解构一切。后现代主义裹挟西方政治生态转向民粹主义。
所谓“民粹主义”即“大众主义”或“平民主义”,从词源上说它源于“人民”一词。“民”即作为草根阶级的平民大众,“民粹”则象征着平民大众与精英阶层之间的互动关系,民粹主义强调“人民优先”,具有平民化与极端化倾向。民粹主义“其本性上的特点便是易变性”,[2](P16)其形态可以是政治思潮、政治逻辑、政治策略(工具、运动)、政治话语、政治风格等。作为社会政治思潮的民粹主义缺乏逻辑严密的内在理论体系,因此理解它的关键不在于它主张建构什么,而在于弄清它批判与反对什么。民粹主义诉诸“人民”反对的对象包括政治精英、现存建制、非本共同体的“他者”等。
近代民粹主义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大体经历了三波浪潮,现渐已成为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生态重构的主导性力量。民粹主义运用其独特的“人民观”将“沉默的大多数”组织起来,这里的“人民”被视作同质的、良善的共同体,在此他们获得了共同的身份认同与集体性意识。自我意识的膨胀化、情绪感染的共通化、政治诉求的理想化、政治行为的极端化形塑了同质的共同体,或者说形塑了共同体的同质;现代信息网络传播的私人性、便利性与蛊惑性,促使被忽视的民意以共同体的形式迅速扩张。民粹主义者往往会在共同体之外设立假想敌,借以鼓动民众联合起来抵御精英与体制的外部腐蚀。民粹主义的非理性与极端性,既与精英主义不相容,更与多元主义相对立。
二、民粹主义转向下的西方政治危机
(一)民粹主义与西方政治合法性危机
西方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的盛行,将民众固有的“政治冷漠”与无政府主义畸形结合起来,导致的结果便是选民对固有建制的普遍质疑与消极批判。此乃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内在危机的外在显现,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正在被消解和侵蚀殆尽。
西方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于近代的人民主权学说,洛克以社会契约论的形式确认了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主权在民实际上内嵌着民粹主义的种子。伴随着启蒙之门的开启与理性的广泛殖民,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具象的身份关系被奠基于市民社会中的理性抽象的假设所替代,个人被设想成同质的、抽象的、原子化的个体。基于理性假设的平等个人观必然引申出人们享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将政治共同体的理论根基建构于由各个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组成的人民想象之中,进而以人民共同意志为政治合法性辩护。
代议制民主,作为调节人民与政府、大众与精英之间关系的委托代理机制,为西方政治运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然而,这一民主形式是消极意义上的民主,其与卢梭将政治权力直接授予具有道德内涵的共同体——人民的做法相抵牾。卢梭指出,“唯有当人民集合起来的时候,主权者才能行动。”[3](P118)这种积极民主观使群众觉察到“我们受着代表们的统治而不是自己统治自己”,[4](P282)即大多数人是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民粹主义要求大众直接行使权利;而现实的精英主义民主强调的是候选人对民意的塑造,即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精英权力与大众权利的悖谬构成了西方民主的内在诉求困境。现代性进程中,西方政治合法性偏离政治价值而聚焦于政治事实,要解决当前的困境,必须重新调适民主的合法性基础。
(二)民粹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冲撞
近年来,欧洲社会极右翼政治势力崛起,右翼政党在选举中频频获胜,以英国脱欧公投为标识,右翼民粹主义概念与现象受到极大关注。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彰显了西方国家试图以多元文化主义整合社会不同群体、挽救政治合法性危机意图的失败。
福柯运用后现代主义对自启蒙以来理性主义构建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秩序予以颠覆和解构,从微观视角出发强调文化的异质与多元,借此打破总体权力对多元主体的宰制。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承认异质的多元文化群体同等地位的身份政治,它是对“平等主义”政治规范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也瓦解了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共识,个人主义的权利政治走向多元群体平等的身份政治。实际上,“身份政治的极端平等主义价值观恰恰是在用政治伦理的相对主义为多元文化价值至上的极端主张作哲学背书。”[5]
在美国反种族歧视浪潮中,身份政治的平等要求极端化、民粹化,抗议者将“哥伦布雕像”“丘吉尔雕像”推倒并砍头,反对和摧毁公共领域中存在“歧视性”的一切事物。所谓的“差异政治”“生活政治”似乎是将文化批判以及平等诉求深入到生活的各个细微的角落,但这并未触及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政治经济平等。多元文化主义对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的片面追求,实际上是对阶级分析及政治经济批判等现代“宏大叙事”的遮蔽,这是使西方左翼政治趋于弱化与右倾的重要原因。
根据群体身份特征寻求区别对待的做法与自由主义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的理念相违背,以公民身份建构的民族国家政治认同面临被小群体文化解构的危险。西方身份群体的分裂引发民主政治面临无政府主义的危机,致使政治生态民粹主义倾向日益明显。
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倾向及其应对
全球化是现代性进程的衍生物,西方现代性困境致使全球化遭受重挫。当前西方各国正处于民粹主义的第三波浪潮之中,其中反建制和反全球化是这一潮流的突出特征。依附于民族主体的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议题上的政策失败的反抗。民族民粹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化,其孕育的分离主义倾向尤其值得关注与警惕。
(一)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分离主义倾向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西方社会是“无世界性”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对作为意义境域的世界的遮蔽,使人在世界中没有任何位置,被他者所承认和担保。民粹主义作为否定性与敌对性的话语政治,即通过设立和拒斥“他者”完成对自我主体意识与共同体身份的认同。民粹主义话语秉持二元对立思维,通过划定同质统一的“人民”与异质多元的“他者”身份,构筑起具有排他性的反抗性政治。正如施密特对“政治”所作的界定:促发政治动机和行动的特别的政治区分就是分清敌友。西方社会对抗性政治风格的回流,裹挟着民族、种族、宗教、地区的分歧冲突,酝酿出新一轮的分离主义潮流。
在政治实践中,民粹主义的二元对立政治观在纵向上体现为草根大众与政治精英的抗争,其通常具有激进的反权贵与平等主义的左翼倾向;在横向上则表现为本民族或本国人民对外来种族移民的拒斥,其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的动向奠定了其右翼保守立场的底色。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施政纲领聚焦于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通过区分本土人民与外来移民构建本国、本民族群体身份的认同;强调区分民族群体和国家实体的敌人与朋友,而其敌人即外国移民、穆斯林群体、多元文化及全球化等。右翼民粹主义依附于民族主义并与之合流,“而分离主义也意图通过自治或独立的形式求得所谓‘民族’的统一,巩固‘民族’的认同”,[6]“分离的民族民粹主义”随之生成。
由于在“民族”“人民”等维度上的重叠,分离主义得以弥补民粹主义的价值缺失,同时得以将民粹主义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政治动员工具。近几年西方国家与社会屡见不鲜的分离公投与街头政治折射了二者互动耦合的共振关系,而这无疑会给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权威与分离地区的自治权利带来威胁与挫伤。
(二)世界的分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构
面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困局,阿甘本从生命政治的视角出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共同体的分裂,处于分隔性结构的西方主权国家,无力解决赤裸生命问题。他将人民划分为“大写人民”,即归属于主权国家的整体性概念的人民;以及共同体中被排斥的、边缘的、底层的人民,即“小写人民”,也即“赤裸生命”,这一划分是对施密特“敌友政治”的新发挥。透过阿甘本理论的后现代视角,从中可以窥探到民粹主义是对人类共同体分割性状态的应激反应,西方的政治危机就是人民主权危机。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从政治构序的层次上理解西方主权危机,并未深入到政治危机生成的根源层面,惟有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才能真正厘清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症结。西方民主危机离不开“资本”的逻辑,人类共同体的分裂正是拜“资本逻辑”所赐。首先,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被资本所异化。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人权,尤其是私有财产权被封闭于利己主义的个人手中,市民社会无疑成为个人私利的战场,其结果无法逃脱共同体内部个人的对立与分裂。其次,资本逻辑在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一方面引起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冲突;另一方面各国资本在放任的市场逻辑下展开激烈竞争,势必引起人类共同体内部的各主权国家间的对抗与分裂。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真正主体,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生产活动,发挥人民的主体性智慧和创造性实践的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容纳并协调个体特殊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使现实的人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7](P90)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彰显的“类思维”超越了民族、种族、宗教、地区的分歧与偏见,不失为应对喧嚣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对抗性极化政治的一剂良药。
四、结语
“现代性祛魅”的现代西方社会,充满魅力的完备的道德学说已经不复存在,价值观念遁入到私人领域并变得日益私人化、多元化。“当价值多元主义被应用于自由或任何其他核心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时,它并不支持自由主义原则。相反,自由主义原则为价值多元主义所颠覆。”[8](P97)个人理性共识一旦被群体身份政治的差异认同所打破,那么身份政治在文化层面的平等要求必然走向极端化,并进而演变成民粹化的无政府主义骚乱。同时,民族民粹主义开始兴起,西方国家右翼保守的政治风向正成为主流。随着民族民粹主义的分离主义倾向日益显现,西方政治生态逐渐民粹化、分裂化、极端化。唯有立足于人类整体,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着眼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国际合作的最大公约数,超越狭隘的群体身份认同政治、单一的民族国家利益、傲慢的意识形态偏见,实现人民内部各群体与各国之间多元利益与文化的相容共生、互利共赢,才能重构民粹化的西方政治生态与分裂的人类共同体,从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