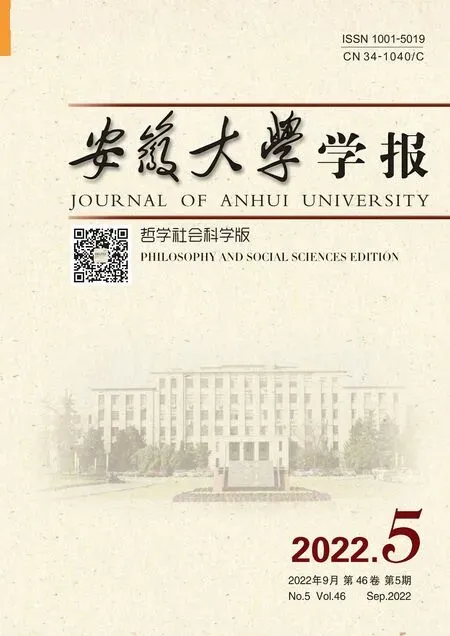从“学说”到“思潮”的知识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1917—1921)
2023-01-03蒋含平汪娜娜
蒋含平,汪娜娜
一、引 言
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截然两分,由“早期译介阶段”跨入到“广泛传播阶段”(1)参见齐卫平《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阶段比较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这是学界已形成的共识。前一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众多舶来学说中的一种,零散地被译介、解读,影响力有限。五四前后各类“主义”涌动,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种种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流行一时却大多很快湮灭,而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却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完成了从一种“学说”到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潮”的跃进。
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历史描述的研究早已异常丰沛,但关于从“学说”到“思潮”的传播阶段跨越背后内在理路的书写,却相对不足。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五四时期多元思想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当前的研究多归因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国内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等等原因,概言之,即马克思主义初期传播的阶段式跨越是种种“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解释的路径将马克思主义固化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触发革命行为的“开关”,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套成熟的知识体系,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多元面相。
本文从知识成长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知识”的基本内涵是洞见、观念、话语、思想,是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区别于相对原始的、特殊的和实际的“信息”(2)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陈志宏、王婉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页。。知识社会学研究者认为,知识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秩序的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秩序创造和传播的关键力量(3)E.D. McCarthy, Knowledge as Culture: 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12.。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从“学说”到“思潮”的飞跃,背后蕴含着一种新的知识类型建立与更新的知识演进史脉络。通过关注“知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4)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李步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32页。,回到知识群体、知识资源、知识媒介所构成的知识传播系统中,本文试图探究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界,马克思主义如何形成了知识演进中的阶段式跨越,并进而讨论建立这种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所拓展的研究进路与价值。
二、知识群体的成长:扩大的理论“承载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等陆续介绍过马克思主义,他们基于各自的立场和价值取向而征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部分内容,但尚未围绕这种知识类型形成群体认同和系统的知识传播。五四时期,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遽然增多,“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是罕见的”(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 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7页。。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聚拢形成“认识论共同体”(epistemological communities),即建构知识和通过特定渠道引导知识传播的最基本单位(6)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第9页。。以五四前后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共产党》《劳动界》5份刊物中发表言论的30多位中共党员为例(7)参见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29~30页。这批知识分子中,有曾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李大钊、沈泽民等人,曾留学法德的袁振英、张申府、马哲民、李季、蔡和森等人,曾访苏或驻苏俄采访的瞿秋白、张太雷、柯庆施、刘仁静等人。,其中绝大多数为青年人,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约三分之二的人有过留学日本、欧美等国或访问苏俄的经历。他们会通中西,多数都精通一门或多门外语,具有“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语言优势,基本构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军。
当然,知识群体并非处于一种固化的状态。正如曼海姆所指出的,“自由的漂浮的知识阶层”的观点“取决于包含了各种矛盾观点的知识媒介”,“他们能够适应任何一种观点,也只有他们处于一种能够选择从属于谁的地位”(8)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第197页。。因此在各类“主义”喷涌、思想争鸣的场域下,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的成长必然伴随着思想和队伍的纯化。他们在获取知识之后,通过吸收与转化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表达与认知结构。
首先,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透过日本译介和欧美布尔什维克文献,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综合知识体系的特点,并建立起清晰的思考与阐释模式。在当时涌入中国的众多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共产主义世界的预言,“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9)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1921年人民出版社曾计划出版15种“马克思全书”、14种“列宁全书”、11种“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等共计59种书籍,旨在“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10)《人民出版社通告》,《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号。。虽然后来未能全部成型,但这些出版信息透露出传播者构筑马克思主义知识版图的计划。除译介外,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系统来宣传。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分别对应着过去、现在与未来,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从根本上联络起这三大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11)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19页。。此外杨匏安总结“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的历史观为经,以革命的思想为纬”(12)杨匏安:《马克思主义浅说》,见《杨匏安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年,第152页。;李汉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13)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第1版。;李达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概括为“唯物史观、资本集中说、资本主义崩坏说、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说”(14)李达:《马克思还原》,《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号。等。这些论述均体现出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已有较为全面的理解。
这种综合知识体系下的思考模式在论战中显现出优势。如蔡和森提出唯物史观、资本论、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完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而“社会革命与染有中产阶级色彩的思想家和被中产阶级学说、教育、势力熏坏的改造家全无干涉”(15)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号。,由此大力驳斥基尔特派人士;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运用剩余价值说、阶级斗争等理论分析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国家社会主义“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16)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7~350页。,进而强调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正当性的大厦建立在语言之上,以语言为主要媒介。”(17)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吴肃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3页。上述这些论战中的言论体现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以体系完整的“语言”陈述改革的方向、国家的出路,从而在各派思想争锋中获得话语正当性,使“马克思主义站稳了脚,在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界里边有了它的地位”(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编:《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08页。。
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也在知识传播格局中探索自身的角色定位,展现出明确的向内维度的“规制”与向外维度的“联合”意识。
一方面,通过汲取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等理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极其重视组织内部的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早期“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会员组织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19)《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1月17日第4版。。随着李大钊等人对于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20)李大钊:《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见《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79页。认识的深化,知识群体内部成员的集合和运作愈发注重规制,新民学会、觉悟社、励新学会等团体不仅以成员之间的知识学习与共享为目标,同时以知识交流作为强化组织纪律与凝聚力的途径。如新民学会逐渐在宗旨性质、指导原则和成员组成方面具备自觉的高度一致性,即便出现分歧,也通过会员之间的反复讨论和通信使之达成一致(21)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3页。,形成集体的意志。五四之后李大钊与陈独秀在酝酿建党问题时,通过前期这些社团组织的运作,他们的周围已经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对建党的步骤和方法也有了初步的考虑(2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6页。。1920年下半年起各地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组织机构更趋周密,知识表达与流动更为规整有序。对比之下,曾活跃一时的无政府主义群体因反对组织纪律而缺乏统一性,“他们就无法限制阐释的自由,其思想活动也仍是以自我为中心并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改变的”(23)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6页。,其知识传播活动因此呈现出散漫和无常的印象,不可避免走向衰微。
另一方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满足于“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24)《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1920年第1期。,他们对建立更大范围的“联合”报以期待。毛泽东曾呼唤“民众的大联合”,需让农夫、工人、学生、女子、教师等等小的联合,进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大联合(25)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二)》,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年十一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2~346页。。李大钊也提出过“联人社会”的设想(26)李大钊:《联人社会》,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91页。,从他的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联人社会”指的是不同阶层之间的联合,重在处理知识阶层与民众如何建立关系、如何联合的问题。他“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27)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70页。。为此,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实践中围绕“劳动”等具体观念,推动建立民众与知识阶层团结一致的阵线。1919年2月,李大钊提出“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28)李大钊:《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87页。。5月,渊泉在《晨报》号召“身的劳动者”与“心的劳动者”要联合起来,做社会的“中坚”(29)渊泉:《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晨报》1919年5月1日第7版。。10月,李汉俊在《星期评论》上主张“应该从精神上打破‘智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30)先进:《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星期评论》1919年第21号。。1921年,陈独秀进一步阐释了劳动者联合的观念,认为“脑力和体力,是同在一个阶级”,脑力劳动者要和体力劳动者“结合团体,共同进行”,“便可做成社会上种种改造的事业”(31)陈独秀:《在工业学校演说词》,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355~356页。。上述这些观点都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框架内阐发,把民众与知识阶级融汇在“劳动者”的共同身份节点上,从而使知识群体具备联合更多社会角色、推进实际运动的功能。
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在吸收与转化中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综合知识体系的脉络,开展较为完整的而非零敲碎打式的学习;二是将知识目标与现实目标统一,通过强化组织规制、联合外界社会阶层,知识群体扮演着勾连理论传播与群众实践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角色,“和群众组成为一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32)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页。。这样一来,民众就成为理论的共同“承载者”(carriers)(33)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第148页。,即接纳理论并形成社会利益一致的群体集合。不同知识群体之间的理论之争演化为各自连接着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由此不局限于以文字为中心的学习与阐释活动,更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实践主体,向着“一种能够作战的新势力”(34)李达:《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见《李达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6页。迈进。
三、知识的构造:与“实境”相呼应
陈独秀等人对于知识的价值有着清晰的认知与判断。他认为,“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是“跟着需要来的,不是跟着时新来的”(35)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74页。。李大钊也表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要“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认为把“主义”拿来运用到实际的运动时,“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见《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页。。这些论述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现实社会需要为标准去判断知识的价值,追求与“实境”相呼应的知识资源。
当时环绕着各类理想与主义的“实境”是什么呢?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同时一战的爆发使得欧洲诸国作为现代国家楷模的形象大为受损,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开始寻找新的学习标杆。其间,1917年开始的俄国政权变动让“社会改造”作为一种革命形式逐渐被国人所认识,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改造概念开始渗透进知识界(37)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本部分将围绕这种重要的经验型知识——“俄国革命”,探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构造与本土“实境”相呼应的知识资源时所呈现的独特形态。
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后,国内知识界即有所关注,且多持以赞赏态度,认为革命起因在于“自由民权之说,渐浸润于俄民脑中”(38)高劳:《俄国大革命之经过》,《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5号。,“经此壮快的革命之风云……自由政治之基础,必缘兹而确立”(39)李大钊:《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1页。,暗合了当时中国社会追求民主自由的心理。几个月后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布尔什维克派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面对这样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政权,知识界的反应却不如此前二月革命热烈。盖因一方面《晨钟报》《民国日报》《申报》等媒体虽有报道,但消息源多来自英、美、日等国通讯社的间接信息,“极端派常白昼杀人,肆无忌惮”“今后流血必多”(40)《俄国大局之恍惚》,《民国日报》1917年11月15日第6版。等恐怖情形的描述和充斥着偏见的唱衰之声见诸报端,令“看报的人堕在云里雾里”(41)季陶:《俄国两政府的对华政策》,《星期评论》1919年第15号。,生出谨慎或抵触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知识界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政府还很陌生,也就是说,对于发起十月革命的内在理论依据知之甚少,尚欠缺理解这场革命运动的知识基础。
五四前后国内对十月革命以及俄国问题的传播迎来转折,特别是1920年初“苏俄对华宣言”在国内大量报道后,相关的讨论更为密集且态度趋于乐观明朗。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5月至1920年5月期间,国内各种报纸上登载俄国革命相关的译介文章约在110篇以上,其中态度客观及报以同情的文章达95篇之多(42)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在其中扮演着积极解释宣传的角色,开设多种集中讨论的专栏。1919年2月,《晨报》新增“革命实话”栏目,连载由日文转译的《地底的俄罗斯》近3个月;11月12日又专设“俄国研究”栏目,当日登载兰塞姆(Ransome)著、兼声翻译的《1919年旅俄六周见闻记》。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刊登来自苏俄的资料。《共产党》所刊文章中,与苏俄、共产国际有关的内容约占一半以上。相比其他知识群体,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问题的关注在频次、深度、议题多元性等方面更为突出,尤为重要的是,逐渐将十月革命作为一种被成功验证的“实践知识”纳入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中,力图展示马克思主义知识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层面上的丰富图景。
解释这种新的“实践知识”的构造生成逻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知识流动格局的转向,为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并理解俄国革命经验开启了源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最早借由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介辗转摄取。随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欧美的布尔什维克文献开始大量传入中国,逐渐构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支柱。通过从“师资”到“师俄”的改变,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产生了浓厚兴趣。1920年代初始,就有不少人赴俄访问。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派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前往俄国考察,旨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一次推动”(43)瞿秋白:《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待》,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旅苏两年间瞿秋白在《晨报》发表48篇通讯,通过报道俄国真实情况为中国的社会变革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出路,“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44)瞿秋白:《瞿秋白游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7页。。同时,留俄学生人数也在上升。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出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此外,苏俄也主动对华传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在以建立中苏无产阶级同盟为目标的对华传播格局中,魏金斯基等来华代表成为承载知识流动的重要“媒介”,帮助出版《新潮》《劳动界》等刊物,改组《新青年》,并于1922年前后在中国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22种(45)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第283页。。
随着较为通畅的知识流动体系的搭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加深了对俄国革命所蕴含的理论依据的理解,从此前“观察”的姿态演进为“学习”“借鉴”。1917年3月李大钊分析“俄国革命之气运”的远因近因,仍处于一种基于“十余年来世界革命之怒潮”(46)李大钊:《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见《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1~2页。视野下的观望。到了1921年,在为《新青年》撰写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李大钊综观俄国革命的往迹,分析革命中心势力的组成与派别,并细数了列宁、托罗茨基等核心人物的主张与事迹,已有认清其价值、“供留心俄事者的参考”(47)李大钊:《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见《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98~122页。之意。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党知识分子从俄国经验中探察到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现实革命道路的可行性,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核心思想,逐渐认同了“刚性化”的列宁主义(48)许纪霖:《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这一过程也带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思想与队伍的进一步纯化,与此前有一定认知交集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其他知识群体分歧渐深。围绕俄国革命经验的“知识学习”促使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获得了建设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指导经验,他们的理想与主义也寻得了落入现实的基本方向。
其次,知识受社会存在影响,苏俄革命作为一种“实践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必然地与社会背景相关联。五四前后各类社会主义学说“你方唱罢我登场”,知识市场看似蓬勃却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意义纷乱。究其原因,在于理论假说与经验现实之间仍存在着明显的割裂。诸如新村主义也曾在中国开展了一些实验,但局限于狭小社会空间中的浪漫主义设想,不久即宣告失败。从这些社会背景来看,一种能够连接理论依据与成功实践的“实践知识”显得尤为需要。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6页。,同时在传播中将之构造为“取之即用”的、能够整体全面地解释现实的“实践知识”。一方面,从国情相近的角度宣传俄国经验的参照价值。俄国与中国一样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列宁领导的阶级斗争的经验“也可以适用于中国”(50)无懈:《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共产党》1920年11月创刊号。。李汉俊号召国人关注俄国发生的种种剧变,“由这些环境产生出来的学说,人家都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只待我们拿来求了解”(51)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2年6月6日第1版。。湖南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立时提出,“劳农政府既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么不研究他的内情,安排应付的方法呢?”(52)《俄罗斯研究会成立》,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4页。苏俄被视为社会主义生产方法“最大的最新的试验场”(53)《短言》,《共产党》1920年11月创刊号。。另一方面,扩展“实践知识”的内容范畴,以应对“从根本上谋全体”(54)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1920年第48号。的中国社会改造。以《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为例,自创办至1921年底登出的35篇文章中,虽大多为译作,但内容涉及劳工联合、农业制度、经济政策、教育、妇女解放、文学文艺等众多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足见其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全面性。
上述可知,受知识流动格局、社会现实需求的作用,俄国革命等新的知识资源被不断融入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中。梁启超言:“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之要求也。”(5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可见能成为“思潮”的知识,既需要具备自身价值,更需要与时代环境同频。对应这两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结合的知识特征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即得以展现,同时,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持续兼容新理论、新实践,不断呼应“实境”的需求,从而以新的话语表达突破了旧有知识世界的认知束缚,引发了一场“知识革命”。
四、知识的落地:构建“制度性媒介”
知识的扩张不是来自知识本身,真正造成一个知识世界变动的,一定与一种知识生产组织方式相关(56)黄旦:《媒介变革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格尔茨认为,观念或思想“必须由强大的社会集团来承担,才能发挥强大的社会作用。必须有人尊崇、赞美、维护、贯彻它们。为了在社会中找到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它们必须被体制化”(57)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72页。。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学说”林立的五四时期突围而出,也缘于其知识传播活动最终抵达了“物质的存在”,即借由书报、教科书、学会、学校等多元、交错的“制度性媒介”(58)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4期。,在制度层面形成一套从知识走到现实的机制,实现了“知识的落地”。
首先是书报、教科书等文本所架构的制度体系。前文中已论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报在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出版和宣传,其中分属不同媒介的“书”与“刊”所面对的知识传播对象有所不同。如《社会主义史》《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讨论集》等“新青年丛书”、 《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新时代丛书”,这一系列“丛书”有体系地出版马恩、列宁及相关研究,旨在以“知识”凝聚知识分子们的价值共识;而报刊中既有《共产党》这类理论月刊,也有《劳动界》这类面向劳动大众的启蒙刊物,以不同的语言体系去解释、呈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观点。此外,作为“现代社会文化记忆中重要一环”的教科书,也在形成“族群叙述的认同”(59)沙培德:《知识传播与集体认同之载体:历史、记忆、教科书》,见张寿安主编《晚清民初的知识转型与知识传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0页。中发挥作用。例如1919年编写的教材《白话书信》,以书信体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本教材的编写者是《新青年》作者群中的高语罕。以上这些书、报、教科书等制度文本一方面在建党工作中发挥出“有力的出版物”(60)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见《新民学会资料》,第161页。的组织认同功能,一方面连接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以及面向民众的知识启蒙,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从少数知识分子掌握的“真理”扩散为可共享的公共知识,由精英走向大众。
其次是各种学会、研究会等社群组织的制度维系。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实验的失败,让参与者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在中国难以成型。社会革命的成功不可以仅凭思想争辩,而必须是以个人网络的联系为基础,最终要超越个体层面,进入到高度组织的程序之中。五四前后众多的社团尤为注重制度机制。“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上海、武汉、济南、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同样性质的团体,连接起城市之间的学术活动与社会革命实践。一个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会“为具体的行为方式提供凝聚的原则”(61)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社会组织的诞生》,第252页。,将所有成员整合统一到组织中去。
最后是学校等场所延伸的制度空间。学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阵地,一方面促进了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一方面辐射带动社会民众的思想教育。以1920年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为例,该校主要进行俄语教育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研读,团员由各地进步组织介绍入学,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党团活动。该校培养了刘少奇、罗亦农等多位中共领导干部,“组织动员了一批批青年到莫斯科去取经……这种气势是前所未有的”(62)张羽:《难忘渔阳里》,见张羽、岳凤麟主编《一束洁白的花——缅怀曹靖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234 页。。同年北京大学也在史学系、政治学系等系开设了几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例如由李大钊主讲的《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唤起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以北大为中心,马克思主义传播形成了向全国辐射的传输网络,这些新的接收站和传播点的设立,大多以各大学的青年团为依托。例如张太雷等人在天津北洋大学成立的社青团小组,董必武在武昌高师等学校发展学生组织,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大学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深入工农群体、劳动者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业余学校,如平民学校、劳动补习学校、识字班等。1921年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创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授课内容包含工人阶级政党、工会组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劳动周刊》《劳动音》《共产党》也都在这个学校里出现了(63)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编:《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64~69页。。另外,设在一些学校内外的书报贩卖部也成为制度化体系下人与人的连接场域。书报贩卖部不仅销售书刊,还可以根据订阅情况把握阅读者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供阅读者们沟通联系,以“书”为媒,将散落于各处的读者串联在同一个知识场景中,推动建构制度化的知识传播体系。学校、书报贩卖部等知识的多重场所推动了知识与人的生产性实践,形成向社会延伸的制度空间。
彼得·L.伯格等人认为,制度化是建构客观化的现实社会的过程,当制度秩序的客体化被传递到下一层级时,正当化(legitimation)的问题必然会出现,即需要对制度进行解释和证明(64)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第116页。。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构建出从观念到现实的制度世界,实现这一过程必须依赖于“制度性媒介”发挥“解释和证明”的功能,建立起不断传承的制度秩序,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从思想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并逐渐进化为全民族的革命运动。
五、结论与讨论
从“知识”的视角重新回望并审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完整图景不仅包括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阐释知识的过程,还包括这种知识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从知识群体、知识资源、知识媒介三个维度出发,基于对知识的获取、构造到最终落地的进程的分析,本文有如下认识:
首先,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兼具学习者、传播者、生产者、组织者等多元身份,对于其历史形象的勾勒不应局限于“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6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9页。。与同时代其他进入中国的新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经过文字阅读而获得。在获取知识和社会行动之间,知识群体成为一种贯穿全局的结构性因素。通过构筑体系完整的“知识地图”、向内强化组织规制、向外联合大众,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力图使知识阶级、劳工阶级等更多的社会阶层共同成为理论的“承载者”。“当所有社会阶层都成为它的‘承载者’时,这种现实就表现得庞大无比了。”(66)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第157页。知识群体由此走出了“沙龙”式的知识交流,成长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关键力量。
其次,围绕马克思主义所形成的知识资源的集合,具有不断回应中国本土“实境”的特点。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不应当对它“食古不化”(67)存统:《马克思底共产主义》,《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4号。。苏俄革命经验就是当时所构造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知识”,是先进知识分子在变动的知识流动格局中寻找实践参考体系的成果。不断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为国内革命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的双重依据,以改造世界为目标的新型理论与实践知识逐渐席卷传统的知识世界。
此外,知识的落地必须依托于“物质的存在”。经由书报、社团、学校等“制度性媒介”,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文本层面形成了凝聚政党意识形态的理论语言以及面向大众的社会公共知识;在组织层面形成了政治性团体的制度交流机制;在空间层面形成了以学校为代表的知识传播中枢,联结多元的场所、不同的人群开展知识动员。通过多进路的制度化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构建起超越个体、到达组织的知识生产模式,促进了从观念到现实的变迁。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曲折而至的“学说”演进为与中国社会变革同频共振的“思潮”,并建立起政党意识形态体系,一种知识类型崛起的背后,涌动着知识与社会交织作用的三重表征:一是知识群体的成长与理论“承载者”的进一步扩大;二是不断回应现实的知识资源的集合所带来的知识体系的革新;三是知识媒介连接起人与人、人与组织的新型社会网络。三者融汇,推动了这种知识类型在“百家争鸣”中胜出并取得有效的社会行动,也导致了传统知识世界的解构与重建。因此,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在五四前后的阶段式跨越绝不能仅仅归因于客观环境、传播者思想变化等“外力”的作用,而是一种“知识”与中国“合适的土壤”相遇且互构的结果。
进而言之,建立知识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叙述,将可以打开以往较为静态的、阶段性的传播分析模式,在知识与社会环境交互的背景中看待传播各要素与过程,即不是回答“谁在传播”,而是关注理论“承载者”的聚拢和扩大的过程;不是回答“传播什么”,而是关注知识资源如何在本土环境下适应与调适;不是回答“通过什么传播”,而是关注知识媒介的社会连接与动员。知识一直处于不断累积、不断更新的轨迹中,依循着知识成长的脉络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就是建立以贯通历史的知识变迁为主线,以知识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变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时代关联域为场景的历史叙述。受限于篇幅,本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分析起止于五四前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中所产生的知识的“新地图”,仍留待做进一步的探讨分析。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68)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求是》2021年第7期。。沿着知识生长的脉络回到创党前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即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识基础发轫阶段,也是回到理论最初的历史起点。从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演进的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理论创新与创造的动力之源在于理论依据以及“承载者”群体的确立,在于理论表达话语体系的创新,在于理论传播媒介的扎根与连接。处于当前舆论生态与媒介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变革的形势和背景下,面对“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更强大、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一时代命题,如何进一步凝聚全民族的“认识论共同体”、形成有力回应现实的话语体系、构建与新的媒介技术相适配的知识媒介,也是新时代传媒实践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