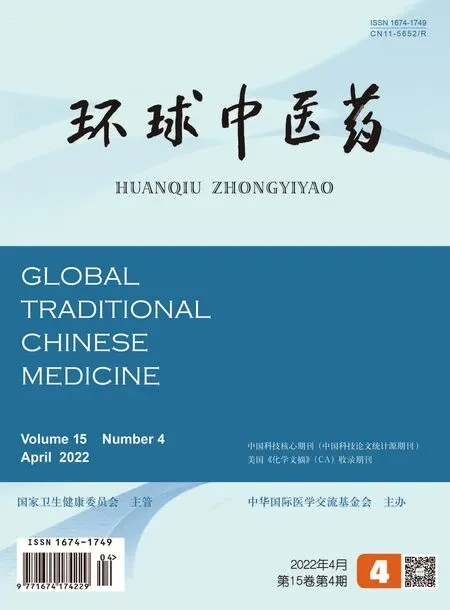丁甘仁中风病辨治方药探赜及医案举隅
2023-01-02朱思行顾博丁尚力严世芸陈丽云
朱思行 顾博丁 尚力 严世芸 陈丽云
中风病是由于正气亏虚、饮食、情志、劳倦内伤等引起气血逆乱,产生风、火、痰、瘀等病理产物,以脑脉痹阻或血溢脑脉之外为基本病机,以突然昏仆、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语謇涩或不语、偏身麻木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病证[1]。《内经》虽没有明确提出中风病名,但所记述的“大厥”“薄厥”“仆击”“偏枯”“风痱”等病证,与中风病的临床表现相似。至仲景《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则正式采用“中风”的病名。丁泽周,字甘仁,江苏武进孟河人,清末民初孟河医派四大家之一,海派中医丁氏内科的创始人,同时亦创立了现今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前身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医学家、教育家。其治学熔伤寒温病于一炉,内外妇儿皆有所研,声名海内外。丁甘仁对中风病的辨治,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值得研究。
1 对真中风的认识与方药运用
1.1 重视内虚,以阴阳为辨证纲领
丁甘仁先生对真中风的认识,实承袭唐代孙思邈关于中风病即外风及内虚外风的病因病机学说而来,但丁甘仁认为真中风是以脏腑内虚为主,以外风为诱因,与内风互结为其发病机理。与孙思邈论真中风比较,丁甘仁在思想上更加重视内虚,故其在所著《证治论要·论治中风》中自述曰:“盖谓真中风虽因风从外来,实由脏腑内虚,外风引动内风,贼风入中脏腑、经络、营卫,致以痹塞不行,陡然跌仆成中,此之谓真中风也。”又具体言其病因病机为“阳气本虚”和“高年营阴亏耗”[2]。笔者认为,丁甘仁侧重内虚,以阴阳为真中风内虚病机之辨证纲领。
丁甘仁重视真中风以内虚为主的思想极有可能是受到孙思邈和李东垣的影响。金元时期对于中风病从内虚而论者,当属李东垣“正气自虚”的病机学说,其在所著《医学发明》中曰:“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多有此疾。壮岁之际,无有也。若肥盛,则间有之,亦形盛气衰如此。”更有“口眼斜,亦有贼风袭虚伤之”之语[3]。由此看来,李东垣着眼于人体内虚之病因。丁甘仁精勉勤训,临床上博采众家,用药常顾护脾胃正气,对李东垣补土益气的学说自有心得体会。
对于真中风的辨证,丁甘仁在《证治论要·论治中风》中明确指出以本虚为主,痰热蒙蔽清窍或痰浊堵塞灵机为邪实阻塞,故以阴阳为纲,把真中风的病机分为以阳气本虚、痰湿稽留和营阴亏耗、痰热蒙蔽两种类型,这在其中风病医案中也常有体现。对真中风的认识,丁甘仁未舍弃前贤关于外风入中为因的宝贵学术经验和对应方药,更是结合自己的经验,从临床出发,以内虚为发病之本,执阴阳虚损两端而辨治,笔者认为此可视为丁甘仁的独创,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对于把握真中风的辨证思路提供了捷径。
1.2 治虚为主,标本缓急兼顾
针对真中风以虚为主、以风痰为患的病机,丁甘仁治虚以阴阳分论之,标本、缓急兼顾。对阳气本虚、痰湿稽留、灵机堵塞者,采用小续命汤助阳祛风、开其寒痹以急治,并配合苏合香丸疏通络道,同时加竹沥、姜汁等涤痰开窍。对营阴亏耗、外风引动内风、兼见痰热蒙蔽清窍者,采用刘河间地黄饮子育阴息风,配合至宝丹化痰清神。在此基础上,丁甘仁常用生地、麦冬、石斛、山萸肉、牡蛎、羚羊角滋阴息风,天竺黄、胆星、川贝、远志、菖蒲化痰开窍。
如丁甘仁治胡左案:“中风已久,舌强言语謇涩,右手足无力,形寒身热,胸闷不思饮食,神识时清时寐,舌苔腻布,脉象沉细而滑。阳虚外风乘隙而入,痰湿上阻濂泉。”丁甘仁辨为真中风之急症,方以小续命汤加减[4]。药用熟附块、川桂枝助阳祛风,云茯苓、制半夏、陈广皮、大砂仁化痰,全当归、大川芎、光杏仁、嫩桑枝活血通经,炒谷麦芽健脾开胃。此案患者形寒身热、神识时清时寐,显然是阳虚外风直中,导致风痰阻滞清窍,当属真中风之急症,故用小续命汤加减治疗无误,体现了丁甘仁治虚为主,急则治标的真中风治疗思想。
2 对类中风的认识与方药运用
2.1 重视内风,以肝肾阴虚为本、风痰火为标
金元以降,医家对中风病的病机逐渐由“外风”转向了“内风”立论。其中,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首先提出了“肾水不足,心火暴甚”的中风病机,并由重视内虚转为重视内因在中风病病因中的地位。此后,李东垣认为“正气自虚,形盛气衰”所致的脾胃虚损是引发中风的关键,而朱丹溪则把“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归结为中风病的病机。直至元代王履从病因学角度将中风病分为“真中”“类中”,始开类中名称的先河[5]。明代缪希雍称类中为“内虚喑中”,张景岳又提出“非风”之说,认为“内伤积损”是导致本病的根本原因。明代李中梓又将中风病明确分为闭、脱二证,在临床急救上给予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清代叶天士的“水不涵木,肝阳化风”说更是被丁甘仁先生推崇备至。基于上述中风病重视内因及类中的病机发展,笔者认为丁甘仁实是宗王履真中、类中之说,以朱丹溪、叶天士之论为据,把类中风的病因病机归结为风痰火三者为实,肝肾气阴本亏为虚,且虚实同见。
具体而言,丁甘仁把半体不用、足痿不行、舌强言謇、口角流涎之症归结为痰湿或痰热阻于廉泉之窍,认为是风痱重症;把神识不清者,归结于肝火内炽、风阳上僭、痰热阻窍所致。总之,丁甘仁把类中的病机概括为肝肾阴亏为本,风阳痰热为标,并提出标急于本,先治其标,标由本生,缓图其本的治疗法度。
2.2 泻实为主,兼顾肝肾阴虚
对于痰湿或痰热阻于廉泉之窍者,丁甘仁治宜扶正养阴、熄风和络,方用《古今验录》续命汤或地黄饮子加减,方中石膏清热泻火,确是治疗热证的良药。对于肝火内炽、神识不清者,方用羚羊角、牛黄清心丸、至宝丹涤痰开窍,石决明、青龙齿镇肝潜阳,天麻平肝熄风,僵蚕、蝎尾、钩藤和络。对于阳明热盛者,用石膏与知母相配;痰阻舌根者,用竹沥半夏、川贝、天竺黄、胆南星、蛇胆陈皮、远志、菖蒲化痰开窍;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项强不能转侧者,用牵正散加当归、丹参活血和血,秦艽、木瓜祛风转筋,地龙、丝瓜络、嫩桑枝通络,更用虎潜丸、大活络丹强筋骨、祛风活络;痰盛气逆者,丁甘仁认为此证较急,故用礞石滚痰丸、竹沥、姜汁化服以涤痰;而对正虚导致的手足麻木无力者,用人参再造丸、指迷茯苓丸扶正祛痰。《丁甘仁用药一百十三法·杂病门·中风类》系丁甘仁当年门诊处方记录,由其门生归纳整理而成,将丁甘仁治类中风经验总结为养阴熄风、熄风涤痰、豁痰开窍三法,可供参考。
如丁甘仁治钱左案:“类中偏左,半体不用,神识虽清,舌强言謇,咬牙嚼齿,牙缝渗血,呃逆频作,舌绛,脉弦小而数。”丁甘仁诊为“阴分大伤,肝阳化风上扰,肝风鼓火内煽,痰热阻于廉泉之窍。”因呃逆之症见于危重病症过程中,属于胃气将绝、生命垂危之恶兆,故肺胃肃绛之令不行,是为危症险关[4]79。方以地黄饮子、竹沥饮合方加减挽堕拯危。其中地黄饮子去附子、肉桂、巴戟天等阳热之药,以防更伤阴液,甚则助阳化风,而加西洋参养阴清热,瓜蒌皮、生蛤壳、枇杷叶、贝母、鲜竹茹等祛风化痰,柿蒂止呃逆。竹沥饮方出吴仪洛《成方切用》,由竹沥、生葛汁、生姜汁组成,再加真珍珠粉、真猴枣散另服,增强涤痰醒神之功效。两方合用,肝风息而痰热清,阴液渐复而诸症得解。
3 浅析丁甘仁对于真中与类中的辨析
有研究者认为,丁甘仁对中风病的辨证处理,并不着重于“外风”或“内风”,而在于“脏腑内虚”[6]。从丁甘仁临床医案的记录来看,似有混淆二者之意。如治董左案:“右半身不遂已久,近来舌强不能言语,苔薄腻,脉弦小而滑。”丁甘仁辨为“外风引动内风,挟湿痰阻于廉泉,横窜络道,为类中风之重症。”治以熄风涤痰,和营通络,药用左牡蛎、花龙骨、煨天麻、嫩钩钩潜阳熄风,西秦艽、炙僵蚕祛风通络,枳实炭行气通滞,淡竹沥、生姜汁、炙远志、陈胆星、川象贝、仙半夏等化痰开窍[4]80。又如治金左案:“陡然右手足不用,舌强不能言语,神识时明时昧,口干欲饮,舌质红苔薄腻,脉虚弦而滑。”丁甘仁同样辨为“气阴本亏,外风引动内风,挟湿痰阻于廉泉,横窜络道,为类中风之重症”。不同的是,此为急症,急予熄风潜阳、清神涤痰,药用西洋参、川石斛、大麦冬滋养气阴,生石决明、煨天麻、嫩钩钩潜阳熄风,炙僵蚕通络,朱茯神、竹沥半夏、炙远志、川贝母、鲜石菖蒲、淡竹沥清心涤痰,真猴枣散冲服加强化痰开窍的作用[4]79-80。
以上两案虽同为外风引动内风,但一为湿痰阻遏,一为气阴本亏,丁甘仁反而均辨为类中风之重症,其辨治并非以病情的急缓或病因的不同而各异,故丁甘仁传人沈仲理对此两医案的按语中亦认为丁甘仁对真中与类中的区别不甚严格[2]89-90。但从丁甘仁中风病医案及医论中可知,丁甘仁在学术认知上,对真中、类中仍是有所区分,尤其丁甘仁对外风入中的真中风,如外风入中而身发寒热,或阳虚邪中者,采用续命汤驱散外风,并且收效显著。通过对其中风病医案的整理和分析,笔者认为丁甘仁对中风病的认识是在区分真中、类中的基础上,即区分两者不同的病因病机,但在临床上,丁甘仁统外风与内风于辨证,把握虚实两端为要,这体现了丁甘仁灵活把握辨证,执简驭繁的临床思维。这与王琳等[7]从虚实的病机角度来研究丁甘仁中风病不谋而合,但其未从学术认知的角度对丁甘仁学术思想及方药形成的脉络和渊源进行梳理研究和总结,笔者认为是其不足。另有一些学者从中经络和中脏腑两方面对丁甘仁中风病辨治进行归纳整理[8-9],这是属于中风病的内因部分,与丁甘仁基于真中、类中的病因病机认识尚有偏差,不能全面地反映丁甘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如仅从丁甘仁治疗中风的处方分析,简单地把内虚为主、邪实为患的中风病病机归结为气虚、阳虚、阴虚,间夹风痰火瘀等邪实的结论似是而非,实是欠妥,是未明丁甘仁对中风病认识的本意。
综上,笔者认为丁甘仁对真中、类中的辨治区别在于,两者都有症状轻重急缓之分,但真中风是以外风为诱因,引动内风,以内虚为主,内虚以阴阳为纲分而论之,故治疗以助阳祛风或育阴息风为主,兼化痰清窍。而类中风是以风痰火为标、肝肾阴虚为本,常采用脏腑虚实为辨证手段,治疗上采用标本先后、虚实兼顾之法。但丁甘仁在临床上统外风与内风于辨证,把握虚实两端为要,淡化了学术上的区分,这从其医案中可以见到。治疗上,丁甘仁对续命汤和地黄饮子的运用颇具心得,常随证加减,但均辨证以施治,不囿于真中、类中。
4 丁甘仁运用仲景小续命汤心得
丁甘仁治罗左案:“年甫半百,阳气早亏,贼风入中经腧,营卫痹塞不行,陡然跌仆成中,舌强不语,神识似明似昧,嗜卧不醒,右手足不用……脉象尺部沉细、寸关弦紧而滑,苔白腻。”丁甘仁辨为“风性上升,痰湿随之,阻于廉泉,堵塞神明……阴霾弥漫,阳不用事之证……急拟小续命汤加减以助阳祛风,开其痹塞,运中涤痰,而通经络。”丁甘仁处方用麻黄、川桂枝、制附子助阳祛风,杏仁、姜半夏、生姜汁、淡竹沥宣肺化痰,川芎、当归活血行气,甘草调和诸药,另用再造丸扶正祛邪[4]75-76。服两剂后,患者神识稍清、嗜寐渐减,是药证相符的佳兆,故在原方基础上去麻黄,加茯苓、枳实炭化痰行气,炙僵蚕通络。三剂后,患者神识较清,嗜寐大减,略能言语,惟右手足依然不用,腑气六七日不行,苔腻。治以助阳益气,以驱邪风,通胃涤痰,下浊垢而通腑气。于上方中加入生黄芪益气,风化硝、全瓜蒌、淡苁蓉、半硫丸化痰通便。服上药后,患者腑气已通,神识已清,但舌强,言语未能自如,右手足依然不用,脉弦紧转和,尺部沉细。仍助阳气以祛邪风,化痰湿而通络道,药加秦艽、嫩桑枝祛风通络,怀牛膝补肝肾。后患者诸恙见轻,属于中风恢复期的范畴,故丁甘仁守方六十余贴,加用大量生黄芪祛风,鹿茸养血,大活络丹通络,最终使患者舌能言、手能握、足能履,并用膏滋方善后[10]。此案属阳气早亏、贼风入中经腧的真中风,所致跌仆、舌强甚至神识不清,故用小续命汤助阳祛风以通经络为急,待病情稳定后,祛风通络和补养肝肾精血兼顾,是急则治标、缓图其本之法。
此案例详尽,且效如桴鼓,但笔者认为,丁甘仁在其治疗中风医案中用仲景小续命汤的说法当属有误。小续命汤由麻黄、附子、甘草、桂心、防风、川芎、白芍、人参等药物组成,方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有备急之用。而张仲景《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病治》中确实也有续命汤治疗中风病的记录,不过此续命汤出自《古今验录》,且由麻黄、桂枝、杏仁、当归、干姜、石膏、人参、甘草、川芎九味药物组成,两者虽有部分药物一致,且都治疗中风病,但其功效实与《备急千金要方》之小续命汤不同。从组成来看,该方近似《备急千金要方》之大续命汤,为治疗外风入中、内有郁热之中风风痱,肢体缓纵不收,皮肤不知痛痒,口不能言,不省人事,产妇出血较多,及老人、小儿见上述症者。据此,笔者认为丁甘仁所用的小续命汤应当是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小续命汤。
5 丁甘仁运用地黄饮子心得
地黄饮子最早出自于《备急千金要方》,原名内补散,经前人略作加减后,以地黄饮之名收录于《圣济总录》,被用于治疗舌强不能言、足废不能用之喑痱证,直至刘完素《宣明论方》以地黄饮子刊行于世后,才引起后世的广泛关注。地黄饮子具有滋肾阴、补肾阳、化痰开窍的作用,方由熟地黄、巴戟天、山茱萸、石斛、肉苁蓉、制附子、五味子、肉桂、茯苓、麦门冬、菖蒲、远志组成。
笔者认为,在丁甘仁的中风病医案中,不管是真中还是类中,常选用地黄饮子中的补阴药,而舍阳药不用,可能跟他承袭叶天士的“水不涵木,肝阳化风”之说有关,恐阳药伤阴,使风愈炽。其组方常用生地、麦冬、川石斛三者养阴为主药,间或加入西洋参、南沙参等物。如辨为气阴两虚、肝阳上亢者,则从肝之体用角度论治,以生地、生白芍养阴柔肝为主,穞豆衣、左牡蛎、煨天麻、滁菊花、钩藤镇肝熄风,陈皮、茯苓、陈胆星、竹沥半夏、淡竹沥、川象贝化痰,石菖蒲、炙远志开窍。由此可见,丁甘仁虽未用地黄饮子全方,甚至只取其滋养肝阴之药,但这与其治从肝肾阴虚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而用药加减的变化也体现了其据证而灵活制方的思路。
如丁甘仁治沈左案:“年逾古稀,气阴早衰,旧有头痛目疾,今日陡然跌仆成中,舌强不语,人事不醒,左手足不用。舌质灰红,脉象尺部沉弱,寸关弦滑而数,按之而劲。”丁甘仁辨为“水亏不能涵木,内风上旋,挟素蕴之痰热,蒙蔽清窍,堵塞神明出入治路,致不省人事……中经兼中腑之重症。”[4]76-77急以育阴息风,开窍涤痰。方以羚羊角片、至宝丹开窍为主急以治标,辅以麦冬、玄参养阴清热,仙半夏、川贝、天竺黄、陈胆星、竹茹、枳实、全瓜蒌、淡竹沥、生姜汁涤痰,天麻、嫩钩钩祛风除眩。两剂后,患者人事渐知,但仍舌强不能言语,左手足不用,脉尺部细弱,寸关弦滑而数,舌灰红。急症已解除,丁甘仁考虑痰涎为营阴亏耗,内风扰胃,变化津液而成,故以地黄饮子加减缓缓图之以治其本,认为“草木功能,非易骤生有情之精血也”。该案以虚实缓急为辨,治疗上先标后本,虚实并治。值得注意的是,后方加减时以患者神情舌和,然手足仍不用为辨治的要点,用药上减少化痰开窍药而增加祛风通络药。
6 小结
与后世中风病的辨证不同,丁甘仁对中风病的认识是在精研历代医家学术和用药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其临床体会产生的,对中风病的辨治,既有继承亦有创新。其首辨真中、类中,真中以内虚为主,由外风引动,与内风互结,故重视内虚为病,在此基础上,内因以阴阳为辨证纲领,分为阳虚和阴虚,以治虚为主,标本、缓急、虚实兼顾。类中则以风、痰、火等内因标实为患,兼见肝肾阴液亏虚,虚实夹杂,故重视内因为患,以泻实为主,兼顾肝肾。丁甘仁临床上统外风与内风于辨证,要在把握虚实,注重标本缓急,灵活运用补泻。治疗上,丁甘仁对续命汤和地黄饮子的运用颇具心得,常随证加减,但均辨证以施治,不囿于真中、类中。在用药上,丁甘仁撷采众家,辅以丸膏,特色鲜明。丁甘仁对中风病的辨治可谓执简驭繁,无有偏废,临床上易于掌握。因此,对于学术的发展,不能泥于教材之辨证分型,而应广泛继承先辈经验,重新挖掘经典方药,发扬学术之争鸣,丰富辨证思路与手段,才能有利于中医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