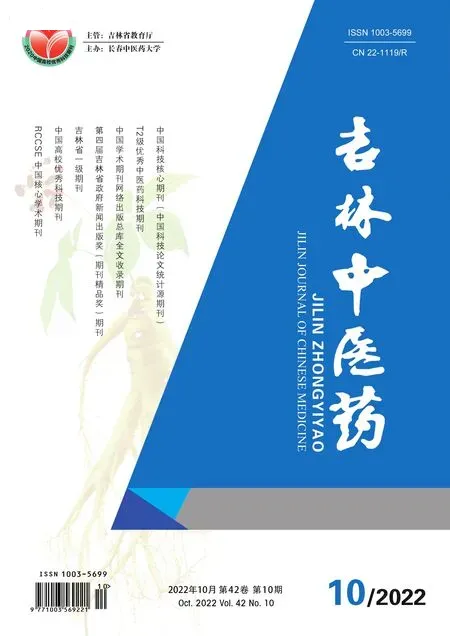运用“不温则痛”理论辨治痛证探析
2022-12-31孙西庆张风霞
许 倩,孙西庆,张风霞
(1.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济南 250014;2.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济南 250014)
疼痛是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所引起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感体验[1],属临床疑难病之一。凡具有“疼痛” 临床表现的病症,中医学均将其纳入“痛证”范畴[2]。对于痛证的发生,古代文献中常以“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加以论述。吾师孙西庆教授对痛证有独到见解及治法,在临证中受“阳气主导论”“气一元论”“元气主宰论”思想的启发,结合现代社会发病因素,提出了“不温则痛”理论[3],机体阳气不足,或为阳虚或为阳郁,在表不能为卫温煦四肢,在里不能入营温养气血,导致机体阴阳反作,气血逆乱,经络痹阻,引发疼痛。不温是痛证发病的始动因素。“不温则痛”理论既丰富了中医疼痛病机理论体系,又为临床痛证的诊疗提供了指导。本文试作探析。
1 重阳之学术源流
关于阳气重要性的论述,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有言:“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又道“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充分说明了阳气的重要作用。阳气不仅维持着人体各脏腑组织的功能活动,生命物质的代谢,还发挥着护卫机体、抗御邪气的作用,阳气主持着生命活动的全过程。《伤寒论》中“阳复者生,阳亡者死”“以阳为本,时时固护阳气”的论述也处处体现着重阳思想。“重阳”理念根源于《内经》,贯穿发展于《伤寒论》,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类经附翼·大宝论》言:“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医理真传》 中提出了“人生所侍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有阳则生,无阳则死”的观点[4]。《扶阳讲记》言:“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5]。纵观历代医家所言,阳为人体之根本的言论朗若星河,阳气盛衰关系到生命的强弱与存亡[6]。
2 “不温则痛”理论发微
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导致今人古病不相同,根据现代疾病谱系的变化以及对新的病因学的重新认识[7],孙西庆提出了“不温则痛”理论。阳气是人生身立命的根本,若阳气温煦、推动的作用减弱,导致阴阳失调,影响气血运行,或气血运行不畅,痹阻经络,或使其失于荣养,从而引发疼痛,看似“不通”与“不荣”,根本在于“不温”,本质为阳气不足,或为阳虚,或为阳郁。
2.1 不温之当代病因 在现代社会,痛证病因虽多,阳气不足乃致病之主因。当世之人不晓顺应天时以养生,不知固护阳气以保真,以致气损阳折,从而使得今时之人“阳不足者十之八九”[8],为痛证的形成构建了病理基础。1)环境因素:现代社会对自然界地过度破坏和污染,引起气候季节异常变化,冷暖无常,昼夜阴晴不定,天运无以日光明,种种变化导致人们直接或间接与自然界阳气接触减少,人体阳气得不到自然界阳气的补充。2)生活方式:现代人起居无时,久坐少动,纵欲过度,过用空调,过度防晒的生活方式违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导致阳气的升浮降沉紊乱,造成阳气耗损或被郁于内,影响健康。3)饮食不节:现代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世人饮食不分季节,不加节制,过食辛辣肥甘厚味及寒凉冷冻饮食成为常态,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过食寒凉,直中脏腑,阳气受损,邪气丛生。4)情志因素:高强度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导致人们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情志抑郁焦虑的状态,困遏阳气,影响气机升降,阳郁于内,久又耗伤,如此反复,百病丛生。
2.2 五脏相通,不温则痛
2.2.1 痛之不温,首责于肾 “疼”者,病“冬”也,“冬”者,北方也,寒也。北方生寒,寒生水,“疼”取决于寒与水[9]。“痛”者,病“甬”也,天寒地坼,道路干裂,就是不通,不通则痛。圣人悬象以示人,立象以尽意,所谓“疼痛”,是以寒为象也,乃借自然之寒以表述人体内在的病理变化。“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寒与肾密切相关,故因“寒”而“疼痛”,与肾关系密切。如《素问·逆调论》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气也,寒从中生者何? 岐伯对曰:是人多痹气也,阳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肾为先天之本,内育元阴元阳,是一身阴阳之基,正如《景岳全书》曰:“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肾阳充足则全身阳气皆足,肾阳亏虚则全身阳气皆虚[10]。内寒之本在于肾阳不足,温煦气化失职;外寒之基在于肾阳不足,易招致外寒侵袭,外寒虽属于外感邪气,但其致病与人体肾阳虚关系密切。肾阳不足,寒从中生,导致血脉失于温煦,血行迟缓,瘀滞不畅,“不通则痛”;感受外邪,寒客于血脉,泣而不流,新血不生,血液不能正常濡养脏腑经络,导致“不荣则痛”。根本原因均在于肾阳不足,机体失温,“不温则痛”。治疗上当以温扶下焦真元,倡用温润之品,如精羊肉、生晒参、肉苁蓉、巴戟天、覆盆子、沙苑子、桑寄生、杜仲等药物,对于阳虚甚者,可选用桂附等温燥之品,常用方剂为真武汤、右归丸、封髓丹、潜阳丹、附子汤等。而对于肾阳不足复感外邪者,酌情配伍解表散寒药,使外邪散之,阳气才可通。
2.2.2 痛之不温,与心肝脾肺相关 《天人解·气血原本》云:“肾水温升而化木者……脾为生血之本;心火清降而化金者……胃为化气之原。”《素问·刺禁论》曰:“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心部于表,肾治于里,脾为之使,胃为之市。”五脏相通,牵一发而动全身,皆可令人“痛”。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气机升降之枢,居中央以灌四傍,中土健则精气化生无穷,脏腑形体官窍得养而邪不可干。如《金匮要略》云:“四季脾旺不受邪。”时代变迁导致人们生活方式随之改变,平素或过食肥甘厚腻,或饮冷贪凉,或久坐少动,或忧虑过度,则易致脾病,易伤脾阳[8]。脾病运化失司,升清降浊功能受累,水谷精微失于布散,一则不能上输下达荣养脏腑经络;二则变生痰湿等病理产物阻遏气机,或聚于血脉影响气血运行而成血浊,日久造成络脉不通,引发疼痛。再者,如《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载:“大抵脾胃虚弱,阳气不能生长,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脏之气不生。脾病则下流乘肾,土克水……”,脾病则先天之本无以为养,日久则肾虚。而命门火衰,火不暖土,反过来又影响脾胃运化。如此反复,脾肾之阳气衰减益甚,不温机体,经脉失却濡养或痹阻不通,引发疼痛。治疗上当温中益气,清除内邪,常选用白术、茯神、炒麦芽、豆蔻、砂仁等益气健脾化湿之品,常用方剂为平胃散、四君子汤、理中汤、参苓白术散等,使药直达病所或间接补益其他脏腑,同时也可防止长期口服药物损伤脾胃,以取“未病先防”之义[11]。
《素问·痿论》云:“心主身之血脉”,不通与不荣者,经络血脉也,故而病机十九条言“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主血脉的功能依赖于心阳的温煦和心气的推动作用。若环境变化,污染、辐射等外在有毒物质损伤机体,入血化浊,日久就会耗伤心气心阳;若起居无常,情志不畅,导致机体明显的昼夜节律变化,由营卫之气传达于心,心之气化随之而变,在上不能生血行血,在下不能温肾助阳,或发为气血亏虚,周环失休;或血行迟缓,瘀滞不畅,均可引发疼痛。治疗上可予桂枝法以温通心阳,常选用桂枝、防风、川芎、檀香、酸枣仁、川牛膝等药物,选用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桂枝去芍药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等方剂加减,以振奋温通心阳。
《素问·六微旨大论》云:“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即谓升降出入是阳气布运流行的方式。肺主一身之气,调节全身气机;肺朝百脉,主治节,可助心行血;肺主行水,治理调节全身气血津液,使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现代诸多病因导致肺阳气亏虚,或郁闭于内,则在外不能固肌表、抗外邪,外邪侵袭注于肌腠经络、筋骨关节,导致气血运行不畅;在内不能温分肉、肥腠理,易变生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阻碍气机,影响营血生成,导致脏腑经络失养,痛证由生。治疗上阳郁在表者,常以麻黄、桂枝、柴胡、升麻等药散之以通;肺阳亏虚、腠理开泄者,常以山药、杏仁、白芥子、桑白皮、紫菀等药补之以温。
黄元御有言:“凡病之起,无不因于木气之郁。以肝木主生,而人之生气不足者,十常八九,木气抑郁而不生,是以病也。”肝体阴而用阳,主升主动,疏泄和畅达全身的气机。肝中阳气充沛则气机运行畅达,若肝阳气虚或郁,失于升发敷布、推动,气结不畅,一则不能助生君火,心火不生,不能下潜温肾水,则北方愈寒;二则不能克中央脾土,影响气血的生成与运行,变生诸邪;三则肝木生于肾水,乙癸同源,精血为一,子病及母,肝肾不能凿分也。肝阳亏虚或阳郁不得发,终致痛证形成。治疗上常选用桂枝、柴胡、薄荷、吴茱萸、天麻等药,常用方剂为桂枝汤、小柴胡汤、逍遥散、左金丸等,以枢转气机,疏肝通阳。
3 病案举例
患者,男,56 岁,2021 年1 月6 日初诊。主因“右下肢截肢处过电样疼痛反复发作30 余年,加重1 月”来诊。患者1985 年参战时右下肢受伤,于越南前线给予膝关节及以下截肢手术,并安放假肢治疗,手术后遗留截肢处疼痛,平素口服“普瑞巴林”“吗啡”“路盖克”等药物止痛,剂量逐渐加大,效果日益下降。1月前因受凉疼痛加重故来诊。现症见:患者右下肢截肢处过电样疼痛,呈阵发性,常于夜间发作,每次持续数分钟,冬季、阴雨天、受凉后加重,时有头昏沉,下午发作较频繁,偶有左侧胸部隐痛(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腰酸痛,平素畏寒热,阵汗出,心烦易急躁,无口干苦,纳一般,眠差,大便2日一行,夜尿2~3次。舌淡白,苔略黄,脉沉紧。既往史:高血压病病史20年,血压最高达140/95 mm Hg(1 mm Hg ≈0.133 kPa),平素口服降压西药,血压控制尚平稳。慢性胃炎病史30年。西医诊断:截肢后神经痛、高血压病I级(低危)、下肢截肢术后(右)、慢性胃炎。中医诊断:痛证,证属阳虚寒凝。治以温阳散寒,予桂枝汤加减:桂枝18 g,白芍15 g,枳实12 g,覆盆子18 g,沙苑子18 g,肉苁蓉18 g,桑寄生18 g,川芎12 g,川牛膝12 g,薤白9 g,白术15 g,淡豆豉15 g,栀子9 g,葛根18 g,炙甘草6 g。上方7剂,每日1剂,清水煎400 mL,分早、晚2 次空腹温服。
2021 年1 月13 日二诊:病人诉右下肢截肢处疼痛程度较前减轻,头昏沉、眠差等症状减轻,血压控制在130/90 mm Hg,心烦好转,舌淡红,苔薄白,脉沉细。遂于原方中去栀子、淡豆豉,加杜仲18 g,菟丝子18 g。7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
2021 年1 月13 日三诊:病人诉右下肢截肢处疼痛明显减轻,胸部隐痛未再发作,夜尿次数减少,头昏沉好转,血压控制在125/90 mm Hg,近日患者劳累过度,腰痛加重,舌淡红,苔薄白,脉沉。遂于上方中去薤白,加狗脊20 g,14 剂,水煎服,每日 1 剂。
后经间断治疗至 2021 年 6 月,病人右下肢截肢处疼痛症状已明显缓解(ⅤAS 评分初诊为9,2021 年3月6 日降至2,同年5 月12 日降至1),余症状均较前明显改善。2021 年8 月电话随访得知病人右下肢截肢处疼痛一直未再发作,平素血压稳定在110/80 mm Hg,已停服降压药。
按:该患者初诊时,孙西庆认为阳虚致病是主因,尚有七情内伤和外邪致病因素。患者截肢术后,骨断筋伤,正气受损,精血俱虚,阴阳皆不足,然以阳气受损为主,术后药物的攻伐,阳气再损,其正更虚。因此,阳虚不温是发病的始动因素。阳虚则风寒湿邪侵而客之,痹阻经脉,发为疼痛,治以温阳散寒法。方中桂枝乃通阳之良药,助卫阳、通经络;芍药酸能收敛,益阴敛营。覆盆子、沙苑子补肾扶正、固精缩尿;淫羊藿、桑寄生补肾壮阳、祛风除湿;川芎入心,活血行气止痛;川牛膝引血下行,直达病所;枳实调腑降浊,“长肌肉,利五脏”。孙西庆于温补之品中佐以通降药,正如《医方集解》中说:“古人用补药必兼泻药,泻去则补药得力,一阖一辟,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必致偏盛之害矣。”薤白行气通阳,解心胸之痛,白术斡旋中州、顾护脾胃;栀子、淡豆豉宣发郁热;葛根轻扬发散荣头目。甘草合桂以辛甘化阳,配白芍以苦甘化阴,亦奏调和诸药,缓急止痛之功。纵观全方,紧扣病机,灵机活法,用药精当,富于变化。二诊时病人诉右下肢截肢处疼痛程度较前减轻,头昏沉、心烦、眠差等症状减轻,血压得降,考虑患者阳气得充、郁热得解,遂于原方中去寒凉之栀子、淡豆豉以防伤正,加杜仲、菟丝子增强补肾温阳之功。三诊时病人诉右下肢截肢处疼痛程度明显减轻,胸痛好转,因劳累过度腰痛加重,遂于上方中去薤白,加狗脊,以取《本经》“主腰背强,机关缓急,周痹寒湿,膝痛”之义。后以此思路守方平调,随证监测,终获良效。
4 结语
张景岳说:“凡欲保生重命者,尤当爱惜阳气,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扁鹊心书》云:“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阳气不足,是引起临床很多疑难杂症的病因,激发阳气可以增强人体正气、提高人体抗邪能力。“不温则痛”是痛证的全新病机理论,“不温”所以“不通”和“不荣”,阳气不足是主要病因。扶阳是保持“五脏元真通畅”的第一要务,在治疗上阳虚者应温养之,阳郁者宜宣通之;复感表邪者,散之以通;邪气滞里者,和之以通,使邪去而阳气通达。如是才能疏其血气,令其温通,使其通则不痛,荣则不痛。此即“不温则痛”临床之具体应用,可推广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