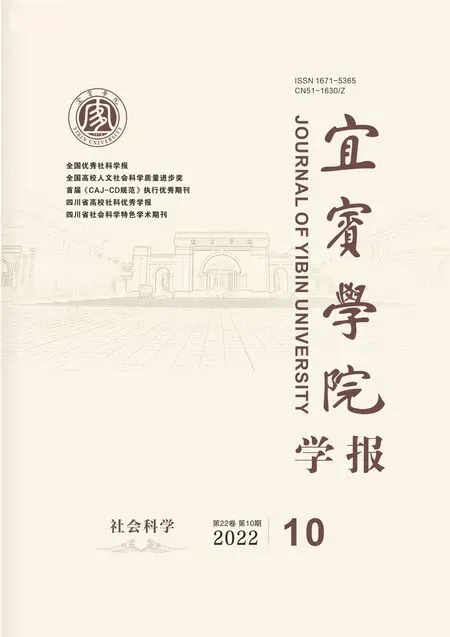学科化与工艺性: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源起的两个传统
2022-12-30万平杨靖雪
万平,杨靖雪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施瓦布是美国著名的课程理论家,一直致力于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他犀利批判美国课程领域盲目地依赖理论,导致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课程领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之时,现有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维持其研究,也难以对教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课程领域达到如此地步,其原因在于习惯性地、不假思索地、错误地依赖理论”[1]。该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一阵轰动,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其他三篇“实践”论文的系列篇,建构了系统的实践课程理论,标志着课程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施瓦布的思想对于当今的课程研究与实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然而,我们当前关于施瓦布的研究,主要是对其思想的译介和诠释,对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形成的来源缺乏详细的考察。理解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楚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是如何解决并形成不同于传统的实践课程思想?这是理解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形成的根本问题。面对当时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实状况,施瓦布将问题的根源追溯于影响课程研究的两个传统的分裂,之后施瓦布基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想,探讨了将“两个传统”相弥合的方法,这对反思我们当前的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一、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分化
美国的课程研究有两个传统: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学科化传统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的综合性大学与师范学校之间针对教师教育的管辖权问题产生竞争,在这场政治性的斗争中,综合性大学认为基于教育科学的重要性,他们在教师教育中应占有绝对的核心地位和优先性,必须以科研为主要的依据,理论的地位优先于实践,课程开发由课程知识驱动。正如美国第一位教育学教授格雷斯·比布(Grace Bibb)声称,只有教育的科学才能给教师提供掌握所有教育问题的条件,而师范学校提供的教学艺术仅仅局限于经验层面,基于情境的工艺性传统难以满足教师的发展需要[3]。在这样的背景下,基于艺术的、技艺的对于课程工作的理解便渐渐失去了话语,综合性大学赢得了教师教育的管辖权。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学科结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学科结构运动的代表人物布鲁纳看来,学科结构就是一门给定学科中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而对于教学和学习而言,学科结构具有广泛又有力的普适性,因为学科结构是教学和学习的核心,适用于各个不同的学科。而工艺性传统起源于中世纪的学徒制,最早出现在手工业领域,是一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以口传手授为主要形式的技术、技能传授方式,以师带徒和“做中学”为主要特征。如一个人通过实际去做课程开发的事情从而学会从事课程开发。1934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开展了一项为时八年的调查研究活动,被称为“八年研究”,强调课程开发的当地性和具体性,以实践来滋养理论。正是在“八年研究”课程改革的影响下,美国中学的课程脱离了传统的学术性束缚,增加了很多富有实践性与生活性的课程,如保健、家政、体育等,同时还在传统的学术性科目中增加了一些关于人文发展的课程。泰勒曾在访谈中表示他从“八年研究”中认识到,“工作与行动所在的地方、真实的思考和行动发生的地方、孩子们所在的地方、父母们所在的地方、教师和校长所在的地方是多么的重要”[4]。
可见,学科化传统依赖理论与知识,基于学科化传统的课程开发试图寻求一种理论应用的普遍程序,具有客观性、普适性。因此,即使教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学校教学经验,但在学科化传统的课程开发中依旧没有其位置。而工艺性传统是强调实践情境和工作本位的,工艺性传统的课程开发是植根于真实的教育情境与经验的,以及从工艺、艺术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课程工作。学科化传统是关于理论的问题,工艺性传统是关于实践的问题,二者的分化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别,而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之间的分歧就是理论与实践关系分离的问题。但是,理论与实践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关系同样如此。19世纪比布与其他教育先驱引导我们走向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理论的方法不自觉会受到原理的控制,更显抽象与概括化,导致了理论泛滥而问题不断的局面,教育理论和研究攻击错了目标。施瓦布的实践课程思想就是针对以理论模式为代表的传统课程理论而提出的,传统模式基于理论的学科化传统,在理论与目标的导向下,课程从开发、实施到评价的全过程具有较强的一般性与普适性,注重最终的学习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课程并没有被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与课程的情境性背道而驰,忽视了基于实践的工艺性传统。施瓦布认为,课程必须深入到学校实践。但施瓦布的实践观念不同于激进派的观点,传统主义的学校改进方法忽略了施瓦布“实践”的复杂性,其“实践”可以说是对19世纪遗留问题的一个回应。基于课程开发工作的经验,施瓦布陷入了对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关系的深深反思之中,他希望教育研究能重新重视工艺性传统,力图重新寻找到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方式。
二、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弥合的思想基础
施瓦布试图解决课程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以此增强课程的实践适应性,将课程从“濒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施瓦布并非是基于实践而实践的,而是基于传统又超越传统的,他提出了实践课程论,寻求弥合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方法。施瓦布吸收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一)从亚里士多德到施瓦布:实践观的继承
亚里士多德是施瓦布的主要知识来源之一,也是施瓦布课程阅读材料的必然来源[5]。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思想引发了施瓦布对课程“实践”概念的思考,即是一种关于课程中工艺性传统知识的思考。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不同于理论原则运用的“创制”,是以实践生活本身为目的,用一种实践之知对实践生活的境地、行为等作出判断和选择,这是一种实践理性智慧,反映在施瓦布的实践观中,即是教育的实践理性智慧,一种工艺性传统的知识,“它不是一套操作技能,不是教育技艺,它是植根于教育实践的知道怎样去做(Knowhow)的知识,是选择教育活动进行教育判断所必需的智慧,是深思熟虑的明智的推断”[6]。因此,施瓦布课程中的“实践”是以课程实践本身为目的,是实践情境中知道与行动的统一,“实践”与理论并不相对,但也不是简单地基于理论的“创制”行为。这蕴含着对课程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不断探究以及对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思考。加之,近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传统逐渐衰弱,实践逐步成为机械的理论运用,教育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也出现分离。这与施瓦布所面对的课程领域危机是一致的,为此,施瓦布强调回归实践而又不忽视理论,重申工艺性传统而又不拒绝学科化传统。
(二)从杜威到施瓦布: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界定
康纳利指出,杜威和他的思维的辩证模式是理解施瓦布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重要思想来源[5]。这其中便包含了杜威的经验思想。从杜威的经验哲学出发,理论与实践是必然联系的,经验是连结理论和实践的方式。经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之产物,交互是具有连续性的。杜威认为教育即生长,即经验持续不断的生长,这就是一种交互,通过做中学的方式达到“做”与“受”的统一,个体经验便在此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生长,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二者不间断的关系。从此出发,施瓦布看到了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经验”方式。经验思想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是将进步教育与传统教育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是杜威倡导工艺性传统在进步主义改革服务中的系统化,以实现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辩证统一。这引发了施瓦布对课程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思考与界定,以及对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辩证关系的深思。在杜威之后,施瓦布想要做的就是在教育中进一步推动工艺性传统恢复生机与再度合法化,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并将其与学科化传统结合起来。
(三)从麦基翁(Richard Mckeon)到施瓦布:理论与实践的多样联系
施瓦布关于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的多种方式的观点,为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多种方式的结合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源自麦基翁在其哲学思想中论述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四种模式,包括逻辑、问题、辩证法和操作模式:逻辑模式是理论的应用,问题模式是探究以实践为中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辩证法模式是理论与实践不断相互作用的,操作模式始于实际并始终伴随着实际的进展。麦基翁以此四种模式,点明了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多样性。因此,当施瓦布借鉴麦基翁该观点时,他将实践和理论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一方面认为课程实践是多元的、依赖于情境独特性的灵活构成;另一方面认为实践的理论世界也是多样的,在多样的理论框架中,有多种实践安排的方式。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关系由此是辩证的、多样的、植根于实践情境的。正如康纳利谈到,施瓦布之所以借鉴麦基翁的思想,目的在于将理论、实践以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复杂化,以彻底推翻当时流行的关于实践进步和学校改革的认识,深刻地挑战学术界认为的理论优先于实践的看法[5]。
除此之外,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布洛克则将施瓦布的课程思想与犹太文化相联系,认为施瓦布的“实践”来源于犹太教学习《塔木德》(Talmud)的学校的实践以及各种文本实践。因为《塔木德》所表征的正是一种由理论导向实践,再由实践完善理论的方式[7]。而无论如何,施瓦布对其实践课程思想思考的出发点是学科化传统和工艺性传统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种种前人的伟大思想首先是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相统一的思想启发和思想基础,而后通过学科化传统和工艺性传统的辩证统一关系扩展成为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的整个实体。学科化传统和工艺性传统的统一成为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的源起之思,贯彻在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的各个方面。
三、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弥合方法
施瓦布将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其极具影响力的实践课程理论构想。施瓦布的实践课程思想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将课程领域作为理论和实践努力的综合性框架,二是关于课程审议或者说以实践智慧为中心的实践。第一层面蕴含着施瓦布的愿景,即弥合课程领域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需实现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统一。由此,施瓦布提出课程领域应该把精力从用于追求理论转向实践—准实践—折中的运作方式。就第二个层面而言,施瓦布提出课程审议的实践方法,以此在现实的课程运作层面统一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
(一)实践—准实践—折中
施瓦布提出课程作为实践的基本主张,强调课程要回归真实的实践情境,重新恢复工艺性传统在课程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因为理论定向的学科化传统是当时课程领域的主流,凌驾于实践定向的工艺性传统之上。当时的课程领域应用单一的课程理论来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等问题,学习是儿童接受既定的观念的过程,课程开发仅仅是学科专家的事情。在这样严格的学科化传统遵循下,真实的实践情境与实践问题反而被忽视了,“实践”成为文本,“实践”的概念也被简单化了。但施瓦布所谓的“实践”是区分了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学科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实践的特殊性,而这一点可以从工艺性传统中找回。韦斯特伯里认为,施瓦布并不是拒绝理论,而是拥抱它们,将其转到一个新的方向——准理论[3]。施瓦布的“准实践”正是在识别实践多样性的基础上,与多样的理论相结合,实现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统一。“准实践”的目的就在于识别实践情境以及实践问题的多样性,课程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课程实践问题,而是由多样的、相互关联的个别情境所组成。简言之,理论的情境与实践的情境在“准实践”的过程中交相汇合,既遵循工艺性传统,同时也没有忽视学科化传统。“折中”则是探求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结合的多种方式。它辩证看待和识别关于实践问题的所有课程理论的缺陷,并且要在各理论中有实践意义的部分之间架一座尝试性的桥梁。与以单一理论为基础的学科化传统不同,“折中”以更加宽阔的理论视角面对复杂的实践情境,即理论与实践在多种关系形式中相遇,使得理论复归于实践情境,从而实现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统一。
(二)课程集体审议
施瓦布为了实现课程领域的复兴,转向了“实践—准实践—折中”的运作方式,而这种运作方式的探究方式就是课程集体审议。课程集体审议是施瓦布在实际的课程运作层面,寻找广泛的视角来探讨课程问题,进而统一学科化传统和工艺性传统的方式。课程审议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审议要形成与选择多种备选方案,也就是基于对理论多样性和实践多样性的认识,探索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结合的多种可能的、潜在的方式;二是审议始终遵循的是实践的逻辑,审议的过程不是演绎和归纳,而是就实践情境而发声和行动,这代表着学科化传统要着眼于实践,与工艺性传统相结合;三是经由审议形成一个共同体,打破研究人员(如学科专家)与学校工作人员(如教师)的屏障,为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统一提供一个现实的“论坛”。因此,课程集体审议是指课程开发的主体对具体教育实践情景中的问题反复讨论权衡,以获得一致性的理解和解释,最终作出恰当的、最优化的课程变革的决定及其提出相应的策略,是“择宜”的艺术。课程集体审议的重点是四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包括学科内容、学生、环境、教师,这极大地增强了工艺性传统知识的力量,即使是单一的理论应用,也必须得考虑实践中的教师如何教学的情况。因为教师是最熟悉课堂与教学、学生特性的人,所以关于“做”课程的事情,他们同样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作为学科化传统代表的课程教授也应当被纳入其中。施瓦布于1983年在《课程探究》期刊上发表《实践4:课程教授要做的事》一文以专门探讨课程教授在课程开发实践中的参与,提出基于学校层面建立课程审议小组的全面构想[8]。至此,学科化传统的拥护者与工艺性传统的主张者,通过“审议”暂时形成一个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为更好地解决课程实践问题而努力。
四、对我国课程改革与课程研究的启示
施瓦布实践课程思想源起的“两个传统”之弥合达成了课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向建构,体现了一种融合的、中介的思维与方式,这与我国的中庸思想相契合。而在我国的新课程改革中,“大破大立”“另起炉灶”等观点却受到推崇,有人主张我国也有必要进行一场类似于西方的概念重建运动,但很少有学者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思考中国的课程改革。这是一种与传统相对立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施瓦布的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与启发。教育改革应以中庸之为实现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辩证统一,遵循课程研究的实践逻辑,以理论上的中西互动引导实现实践中学科与经验的育人融合。
(一)走渐进式的课程改革之路
回望中国教育现实,传统教育尤重学科化传统,但自新课改以来,提倡工艺性传统似乎又走向极端。新课改刚一施行,学科知识就被推上改革的“风口浪尖”,经验成为这场改革高扬的旗帜。以知识为中心的学科课程开始被以兴趣和经验为中心的综合课程所取代,成为学校改革的重心。学校强调课程的综合性、活动性与研究性,力求通过以学生经验和兴趣的综合性研究活动等来实现学生的发展。学生的经验与兴趣得到重视,但学科知识似乎又被“弃之如敝屣”。回归现实,课程实施要么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仍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要么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形式多样的活动导致学生难以掌握基本知识与技能,呈现学科与经验间的“钟摆运动”轨迹。那么学科与经验如何达成统一呢?可从施瓦布“两个传统”相弥合的思想中得到启发。施瓦布认为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和分化的,而是可以在实践中得到统一,这也正是理论沟通实践的方法。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是相通的。中庸之“中”不是“折中”,而是“致中和”,其蕴含着两个重要的方法论原理,即通权达变与和合创生[9]。因此,基于我国这种融合式文化所催生的现代课程改革本就应当具备渐进性、继承性的性质,学科与经验也并不是相对的。正如王策三先生所讲的,“非此即彼,是没有出路的。出路(转型、改革)只能是超越彼此对立,另辟蹊径,真正根据实际情况(教育阶段、年级、学科、教材、具体情境条件),实行有主有从的多样综合”[10]。超越二元对立的改革思维,走渐进式的课程改革之路,这是施瓦布“两个传统”弥合的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
(二)遵循课程研究的实践逻辑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都是以一种对立的视角来看待学科化传统和工艺性传统的,课程研究也是如此。审视我国当前的课程研究,理论并没有很好地与实践形成融合互动的机制。张华等学者大力批判传统课程理论,认为其是技术性的教育生产模式,课程研究的基本课题由课程开发逐渐转向课程理解[11]29,这忽视了传统课程理论的价值,也没有看到开发与理解之间的课程实践、课程批判的过程,是二元对立思维的体现。课程理论若离开了实践情境,就成为了自说自话的言说者,失去了倾听的对象。另外,将视线转向现实场域,课程实践中存在着许多生搬硬套、拾人牙慧等现象,很多学校在不考虑自身实际的前提下,套用一些课程专家包装好的课程理论,以追求短期的利益,导致课程的质量堪忧,忽视了长远的发展。回溯施瓦布“两个传统”弥合的思想,这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课程理论与课程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施瓦布“两个传统”弥合的思想为我们指明了一条中和之路:遵循课程研究的实践逻辑。具体做法是增进对具体实践情境的理解,追求课程的实践价值,课程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改造才能更好地适用,反对对理论不假思索地依赖。有学科专家在基础教育新课程设计中说:“做义务教育课标的时候,对于学教育学与心理学的那些人,一开始还觉得很别扭,他们提出的东西有时候不着边际。后来一想还挺有道理,两方面结合还能互相促进”[12]。这也恰恰体现了施瓦布“两个传统”弥合的思想的科学性,有利于我国课程决策的合理化与民主化,对我国课程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结语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在《庖丁解牛》一文中,厨工对于解牛是“游刃有余”自然“目无全牛”。技艺极其纯熟,解牛轻而易举。庄子言“庖丁解牛,技近乎道也。”这是一种超越艺术的道,而道是从多次的实践中萌生的。学科化传统与工艺性传统的融合便是超越艺术的道,根源于教育实践,而叩其两端以致中和。理想的课程教学是实现学科与经验的和合创生,最终走向人的和合。走渐进式的课程改革之路和遵循课程研究的实践逻辑为解决当前课程领域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方向。教育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选好改革的“发”,来引导教育实践智慧的达成。聆听传统与时代的教育之声是未来教育改革的应有之义,我们需要认识到施瓦布教育思想的遗产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