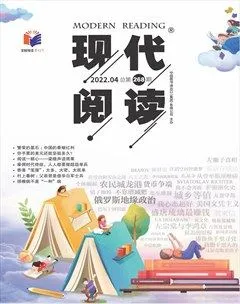为何我国独有“新闻采访权”一说?
2022-12-29彭桂兵

“新闻采访权”一词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经常被使用,在官方文书中也经常出现。例如,新闻出版总署200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闻采访活动保障工作的通知》中就提到,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事件依法享有知情权、采访权、发表权、批评权、监督权。
在英美等国,公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与限制,新闻记者理应包括在内。因此,在英美有关新闻学和传播法学的著作中,从未看到过与中文“采访权”这一表述相对应的说法。我们所见到的是“寻求、获取和传递信息的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采集信息或新闻的自由”这一类说法,而不存在“采访权”这样的用语。
虽然美国并未通过立法的方式区分出新闻工作者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差异。但是相关部门曾考虑通过建构专属特权的“新闻记者保护法(盾法)”的联邦立法方式,赋予记者某些特权和豁免记者某些法律事务,尤其是在诉讼程序中拒绝透露消息来源(拒证)的特权。在州一级,“记者拒证权”已经得到了某些州法律的承认。
我国之所以会有“新闻采访权”一说,有3个原因:
第一,在英美国家,媒体是与立法机构、司法机构、行政机构并列的“第四权力”机构;我国的媒体则有所不同,在领导权上,我国坚持党对新闻媒体的绝对领导。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因此,在媒体工作的新闻记者就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从事新闻采访活动。这种国家利益原则把作为一种职业活动的新闻采访与普通的个人采访活动相区别。因此,从“实然”的角度说,认为新闻采访权是权利而非权力,是有待商榷的。
第二,从事新闻采访活动要经过行政许可,持有新闻记者证才可以从事新闻采访活动。我国新闻出版总署2005年1月10日发布《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并于2009年对此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2014年,我国又把新闻网站的记者证核发纳入了《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新闻记者的从业资格和采访行为就这样被纳入了行政许可的范畴。行政许可是有排他性的,某项行为只有政府许可才可以做,否则就不可以做,这就把采访权的特权性质法律化了。
第三,在我国,公众普遍对新闻媒体寄予很高的期望,往往把新闻媒体看作社会正义的化身。很多人遇到不平之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寻求规则、法律的保护,而是新闻媒体的曝光,所谓“十年上告,不如一次上报”。正因为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的普遍过高期待,才使得部分新闻记者过分地夸大自己从事的新闻采访活动,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无所不能”,从而寻求和呼吁对新闻采访权的特殊保护。在西方,虽然把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是社会的共识,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并没有把新闻媒体的采访活动作为特殊对象予以保护,只是经常会在司法判例中对媒体基于公共利益的表达自由予以倾斜性保护,这是为了充分捍卫表达自由所作的司法保护措施。当然,我国从司法方面捍卫新闻采访权,并不能成为部分记者用来寻租的借口。有人可能打着捍卫公共利益的幌子来侵犯国家、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以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有学者所说,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也可能成为一个侵犯人权的幌子,德国法西斯的统治已经证明,“过度滥用公共利益以剥夺私人之自由,则后果不堪设想”。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新闻采集与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