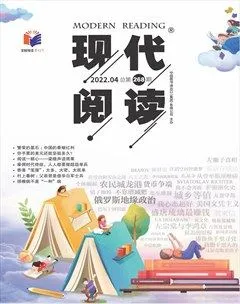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
2022-12-29喻航

由自然人创作完成是构成作品的必要条件,并非具备了独创性就可以认定相关内容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2018年9月9日,某律所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一文。次日,该文章被上传至某互联网公司经营的网络平台,而其中的署名以及引言、检索概况和“注”等内容均被作删除处理。该律所发现后,以该互联网公司侵害了其对《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一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权利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该互联网公司向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560元。
该互联网公司辩称,《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是通过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获得,其中的数据并非来源于该律所,相关图表也是由相关数据库自动生成,因此,该报告并非由律所创作,不构成作品。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报告中的相关图形是律所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不构成图形作品。其次,从分析报告生成的过程看,选定相应关键词,使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和软件使用者均不能以作者身份进行署名。但是,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诚实信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应添加相应计算机软件的标识,标明相关内容系软件智能生成。同时,软件使用者可采用合理方式在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上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最后,报告中的文字内容并非软件“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而是该律所独立创作完成,具有独创性,构成文字作品。最终,法院判决互联网公司向律所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共计1560元。
本案是我国首例对于计算机软件生成内容是否构成作品进行认定的司法案例。
思考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内容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作品构成要件有4项:一是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二是具有独创性;三是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四是智力成果。其中“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和“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作为事实,相对容易判断,而“具有独创性”和“智力成果”则是价值判断。相较而言,“智力成果”因其有人的参与、反映出人对相关内容或表达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容易判断,“具有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更加抽象,往往是判断的难点。
所谓独创性,分为“独”和“创”,“独”是指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是作品从无到有,从原来形态到现在形态的一个发生、转变的过程,是作者自己构思的产物而不是抄袭自他人已有成果的结果。而“创”则是体现作者智力活动的过程,体现了作者某种程度的取舍、选择、安排、设计,是作者内在思想的外化形式,体现作者一定程度的个性或创造性表达。而从作者个性的表述来看,没有程度高低、多少的问题,只需判断是否有创作空间、有作者个性发挥的余地,而非唯一表达或极其有限的表达,就能成立创作性。所以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作品的要件之一,对独创性的判断只涉及有或是没有。而且,独创性是需要根据具体事实加以判断的问题,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需要在个案中具体判断。
在理解什么是作品独创性的基础上,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前述案例中法院作出裁判结论的依据和逻辑。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为查明报告生成的过程,进行了现场勘验,过程为:登录相关智能软件,设置相应检索条件,并使用数据库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了两份大数据报告。法院将两份大数据报告与涉案文章的内容进行对比后发现:涉案文章与两份大数据报告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图形分析维度和文字分析内容等方面均不相同;涉案文章中有大数据报告中不涉及的内容。在此基础上,法院对于分析报告中的图形、文字以及涉案作品中的图形文字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以及某律所是否对涉案作品享有著作权进行了分析:
1.相关图形部分是否构成作品?
通过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图形是对相关数据内容的直接呈现,数据直接决定了图形的表达,数据相同则表达相同,且由于数据特定,利用常规图形类别处理这些数据,表达十分有限,著作权法对有限的表达不给予保护。再者,虽然数据选择、软件选择或图形类别选择不同可使得计算机软件生成的分析报告中图形的表达不同,但并未体现该律所的创造性劳动。综上,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图形与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不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不构成作品,不在《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内。
2.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报告是否构成作品?
分析报告系相关软件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某种意义上讲可认定智能软件“创作”了该分析报告。报告中基于可视化分析图形数据进行的文字分析,涉及对电影娱乐行业的司法分析,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其内容体现出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而针对相同的数据和统计图,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比对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并不相同,亦表达不同。因此,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报告的文字部分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本案判决中指出,“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就本案智能软件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而言,虽然软件开发者和软件使用者对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报告有投入和贡献,但并未传递两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所以相关分析报告并非由两者创作。其“创作”实际上是由计算机软件完成的,智能软件的开发者只是提供软件,软件使用者只是提供关键词进行检索,均未直接参与“创作”过程,没有“创作”行为。所以本案中由计算机软件,而非软件开发者或软件使用者“创作”产生的分析报告,虽然满足独创性的要求,但仍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3.涉案文章是否构成作品?
涉案文章系选定与创作目的相契合的关键词,并利用上述关键词对相关智能软件中的数据进行搜索、筛选,再对搜索结果涉及的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判断、分析后最终形成的。经勘验比对,涉案文章与两份大数据报告的文字内容及表达存在较大的差异。据此,涉案文章的文字内容并非智能软件“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而是律所在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报告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整理、加工和创作形成的,是律所通过智力活动所创作的智力成果。所以涉案文章是律所独立创作完成,具有独创性,构成文字作品。因此法院认为,从律所提交的证据能够体现原告对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涉案文章是律所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
(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网络著作权纠纷典型案例解析》 编者:北京互联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