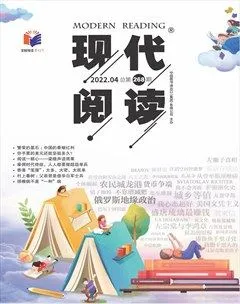区隔与自我
2022-12-29段义孚\\文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



个体的崛起是所有复杂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在西方达到顶峰。作者转向中世纪至19世纪晚期的欧洲,向读者展示个体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在3个社会文化领域中不断增加的隐私需求。
房子和家庭空间
在中世纪的欧洲,庄园主的宅邸基本上只是一个大的未隔开的房间或大厅。所有的活动都在这里举办,就像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市场上。室内和室外的差别极小。冬天,人们进入室内,只是觉得躲避了风雨,事实上房子是透风的,尽管生着火,也不真的暖和。为此,他们不会脱下披风和帽子;因为屋内没有凳子可以坐下,他们只好站着。
一些人站着谈论商业和政治,一些人活动腿脚或跳舞,还有一些人吃东西或试图在某个角落睡觉。音乐家弹奏的乐曲,几乎没人留心欣赏,因为孩子们在到处乱跑乱叫,狗也在追逐狂吠。室内和室外一样紧张忙碌,哪里都没有隐私,当然人们也不需要隐私。
第一次真正的改变是在大厅两旁添加了房间。一个最终成了需要回避的地方,即卧室;另一个成了厨房。
久而久之,家庭空间越来越多地被分割,尤其在欧洲的上层家庭,这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了顶峰。
屋内除了卧室和厨房,还有画室、餐厅、起居室、音乐室、婴儿室、女士的闺房、吸烟室和先生的书房,以及楼下仆人的住处。当然,以往的大厅,变成了一条狭窄的过道,人们依旧站着,就像中世纪的先辈们一样,只是现在他们会脱下外套和帽子。
隐私的理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得以最大化地实现。孩子有自己的房间,照顾孩子的保姆也有自己的住处。男女主人通常在各自的房间里睡觉。女人可以在闺房里涂脂抹粉、调整心情,男人可以在书房里抽支雪茄、吐个烟圈。
对隐私的需求带来了对内心生活的渴望,而较强的自我意识历经约三百年才普及开来。
到16世纪中叶,公共长凳被单人椅所取代,后来又改成坐垫椅。坐垫椅的优点是可以让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悠闲自在。17世纪末之前,壁镜一直很流行,表明人们喜欢从上到下地审视欣赏自己。到18世纪,图书馆成为上层阶级和贵族家庭经常光顾的场所。男人可以只身一人去那里放松、学习、反思,进入他人的世界和时代。
书填满了书架,这些书是否会被认为过于私密而不宜曝露于众?不论什么原因,曾经有一段时间,它们被隐藏在玻璃板和幕帘之后。当主人发现这些书能显示他的好品味时,便移走了这些遮掩物。因此,对社会赞许的渴望与发展内在自我的需求产生了矛盾。
饮食和餐桌礼仪
饮食和餐桌礼仪的故事与家庭内部空间及其摆设的故事有共通之处:两者都取决于分隔(区隔)和专门化。
在中世纪,数量比质量更重要。富人吃得多,穷人吃得少:真正的区别不在于食物是否美味,而取决于数量的多寡。
富人常吃的两种食物都不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一种是烤什锦,里面有多种非常不新鲜的肉和蔬菜(甚至是花)。另一种就是整只动物——野猪、家猪或鹿。烹饪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使用更少的食材,更欣赏其独特的风味,比如将肉类分离,使之一道道上桌而不是混在一起;将蔬菜和肉切开,避免整只动物或一大块肉出现在餐桌上。
餐桌礼仪的进步被视为自我意识及个人尊严感提升的另一标志,这也是一个人远离动物状态的体现。
在中世纪,即使是出身高贵的欧洲人也用手抓东西吃。到了16世纪,优雅的用餐者用3根手指来拿取公共盘子里的食物。
意大利最早使用叉子,随后是德国和英国。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餐桌上为用餐者提供叉子这一新奇的餐具,被批评家视为装腔作势。
之后,餐桌器具的数量持续增加。1800年之后,一个精心布置的餐桌上会有水果刀、叉子以及鱼刀和汤匙,这些餐具表层镀着银,因为人们认为直接与钢铁接触会影响食物的味道。
17世纪后期,即使餐桌上供应几种酒,客人也只能用一个酒杯。到19世纪末,人们用超过6个杯子盛酒,如雪利酒、波尔多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摩泽尔葡萄酒、匈牙利葡萄酒、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拉白葡萄酒。
客人进入餐厅时,一列闪闪发光的水晶和镀银餐具便映入眼帘。在第一道菜上桌前,桌上已摆满代表着高雅文化的器具。
如前所述,中世纪的大厅陈设极少。用餐期间,桌子才会摆好,长凳才被搬进来。长凳是最常见的坐具。人们在吃饭时共用一个凳子,仿佛他们无权要求成为分离的个体。
重要的人才有椅子坐。只有他们是个体——具有权威,“权威”意味着有能力成为发起人或代理人。
从我的自身经历而言,因为我和我的同学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大厅吃饭的时候,我们会被指引坐在长凳上,很显然,我们并未被视为成年人。在贵宾席上,导师坐在椅子上,拥有他们自己的空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成为首席教授,具有发言的权威。
戏剧世界
英国剧作家、诗人威廉·莎士比亚曾写道,“世界是一个舞台”。借此,他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舞台代表着世界,它不仅仅是世界的一个模型,更是世界的一面镜子。
不同于文学或建筑的成就,戏剧从两个方面——戏剧情节和剧场布局——反映着世界,两者相互强化。
简言之,戏剧的历史是从宇宙到陆地,从广场到客厅,从参与到旁观,从着眼于罪和救赎的公共仪式——经由反映社会交往的悲喜剧——到沟通交往的无能、自我孤独及绝望。
现代戏剧起源于中世纪教堂的宗教仪式。12世纪,向世俗戏剧的重大转变首次出现:把教堂外的仪式转移到普通的公共空间;在直接反映基督教教义和仪式的戏剧中,更多使用演员参演,而非神职人员;把演员和观众分开;如果我们把观众看作教堂会众,那这一行为代表了进步性的分离,即普通人与神职人员分离、日常生活与神圣仪式分离。
1300年到1600年,基督圣体节戏剧一直很流行,它们展现了某些时空范围以及那段时期戏剧表演的宗教特色。戏剧在空间上上至天下至地,在时间上也同样囊括了一切,从人类的堕落直至最后的审判日。
显然,没有一个戏剧的舞台布景能近乎包罗整个时空。但是,有一些单独的道具,比如诺亚方舟的工作台,一幅着色的红海油画,以及画有十字的树桩。演员们用完一个道具,再换另一个。
后来,宗教剧逐渐让位于伦理剧,尽管伦理剧依旧以《圣经》为主题,但包含了世俗元素,以幽默甚至不雅的形式呈现。神职人员不再完全参与其中。演员都是近乎专业的表演人士。
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戏剧中不再只是寓言里的人物,日常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也开始出现。伦理剧已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但其说教意味依旧存留。此外,尽管故事情节不再从人类堕落贯穿至最后的审判,但仍涵盖了全球范围:莎士比亚的露天剧场堪称环球剧院(建于1599年),因为他的戏剧里大小人物掺杂,王国与市场共存,园圃与自然同在——这是一个宇宙,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陆地风景,也绝不是个人的家庭空间。
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只能在近乎空旷的舞台上表演。这类舞台布景出现在18世纪,当时,戏剧主题倾向从政治和战争转向个人生活。19世纪下半叶,戏剧中发生在客厅的家庭矛盾标志着这种倾向达到了顶峰。
戏剧的主题转向个人生活,剧场空间的格局布置的间隔和界限也愈发清晰明确。
在伦理剧中,演员和观众自由地融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舞台与观众席没有明确划分界限。即使有既定的界限,随着18世纪舞台台口的出现,有特权的观众观看戏剧时,仍会心安理得地坐在舞台上或靠近舞台。
直到19世纪,随着使用幕布、变暗大厅等措施的相继实施以及戏剧的私密性不断增加,观众和演员被强制分隔开来。
观众自身的举止表现也更正式了。中世纪,观众在剧场里随意站立,到处乱走,喋喋不休,只是偶尔看一下表演。
莎士比亚时期,观众们坐着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舞台表演内容多么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付钱买了座位,不愿花钱的观众只得站着观看表演。坐板凳还是椅子,取决于观众的地位。最后,所有观众都获得了尊严,可以坐在椅子上,虽然很拥挤,但是观众们有了自己的专属空间。
与此同时,19世纪末期,黑暗的剧场氛围成为时尚,观众可以认为只有自己在观看演出。观看什么呢?不是天和地,也不是王国和公国,而是私人住宅和私人生活。在亨利克·易卜生1879年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离开丈夫和孩子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在易卜生1876年的戏剧《培尔·金特》中,培尔被驱使着不论付出多少代价也要找寻自我。旅程即将结束,他在剥洋葱的时候发现洋葱没有心,非常惊恐——原来自我是没有核心的。在俄国作家、剧作家安东·契诃夫1896年的戏剧《海鸥》中,特里波列夫悲伤地问:“我是谁?我是谁?”
直到19世纪,西方开始觉得个人主义太过了,以至于人们觉得孤独和焦虑,所有的物质所得都无法弥补彼此间交往热情的缺失。如何能使人的生活更有意义?人们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诸如“共同体”“邻居”这样的词受到了社会改革者和规划者的青睐,因为这类词能唤起前现代的归属感及合作意识。今天这些词以及其他温暖的词汇与“社会、文明和个人主义”等所有暗示孤独、冷漠和客观的词形成了对比。
空间的再整合是最终答案吗?规划者和建筑师似乎这么认为,因为20世纪后半叶之后的建筑趋势就是把客厅和餐厅合二为一,并最小限度地将家里的厨房与餐厅区域分开。
剧院里,撤掉舞台的台口和幕布已成为时尚,这使得舞台前端成为观众席,观众和演员可以同在一个世界里。社会改革家通过将前现代的共同体浪漫化来满足他们的怀旧情结。
最后,“个人主义”一词不再是个人潜能(包括智慧与优秀)的体现,而是单纯的利己主义。数百年的历史进程允许人类成为更加真实的自我,但人们将其视为消极的。尤其是现代的国际化都市,通常都被视为自我意识的完全释放之地,有碍于公共联结。
(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