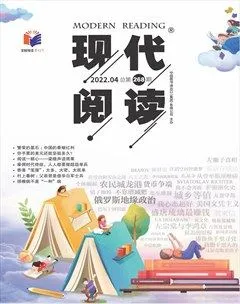龙港靠什么造出了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2022-12-29朱晓军


这是一份来自中国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报告,记录了中国行政改革先行者的发展奇迹,书写下敢闯敢试、创新创业、开明开放的龙港精神。
中国城建史上有两大奇迹。一是广东深圳。二是浙江龙港。
20世纪80年代初,位于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南岸的方岩下不过是几爿“灯不亮,水不清,地不平”的渔村,人口不足六千,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连一寸公路都没有。民谣凄然唱道:“方岩下,方岩下,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
1981年,平阳分成两个县,方岩下隶属苍南县。1983年,龙港设镇,镇政府选择在方岩下。3年后,龙港镇初具规模,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前往视察,给予肯定。
201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苍南县龙港镇,设立县级龙港市。龙港市由浙江省直辖,温州市代管。龙港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首个“镇改市”。
有人说,深圳是举国之力建成的。深圳在发展初期得到国家的支持,一是1.35亿的资金;二是特区优惠政策;三是工程兵先遣团的人力支持。深圳的发展还得益于香港与澳门的投资和信息以及贸易等各方面的促进……
《新华时评》说:“在基层首创和改革推动、市场先发与政策红利等混合动力驱动下的龙港,率先推出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三大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行政体制改革、城市治理创新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为中国小城镇综合改革提供了样板。”
龙港最了不起之处是在没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情况下,依靠改革开放政策和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独辟蹊径,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农民集资建城。这座“城”也改变了几十万农民的命运,使他们在20年前就实现了共同富裕。
龙港是个奇迹。如果创造奇迹的人可称为奇人,那么龙港的奇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奇人群体。
1984年,深圳初具规模。1月26日,邓小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4月30日,53层的“中华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提前一个月封顶,3天1层楼的“深圳速度”传遍全国。
这时,距深圳千里之外的龙港还是一片滩涂,五爿渔村犹如散落在青龙江边的几枚卵石,水边的芦苇继续摇曳着几个世纪的荒凉。龙港是浙江省苍南县的一个镇,确切地说是一座要建还没建起来的镇,除两三条新建的走上去沙沙作响的砂石路,还有几处在建的码头,以及远远近近的几处建筑工地。作为一座城镇该有的学校、医院、商场、影院、住宅小区都还在图纸上,有的图纸上也没有。它的建设速度跟深圳相反,犹如从青龙江爬到岸上晒太阳的乌龟,爬爬停停,说不上爬到哪儿就不动弹了,照这架势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建成。
6月15日早晨,端午节刚过的方岩下内河码头,船像从天边赶过来的一群群鸭子。它们被拴在一起,由前边的机动船牵着,三五条、七八条串在一起,浩浩荡荡,有点儿壮观。
船靠上码头仿佛列车进站,车厢打开,旅客下车。一位穿着像农民工似的瘦瘦小小的男人背起行李卷儿,拎着装有洗漱用具的网兜下了船。他穿过方岩下的那条条石铺的老街,蹚着江滨路砂石道上的尘埃,走进面江矗立的江滨饭店,熟门熟路地上了二楼。
江滨饭店距方岩下内河渡口不远,距新建码头亦不远。它是龙港的地标,也是唯一看上去像个城镇的建筑。在一片黑乎乎、矮趴趴、破烂烂的渔家农舍中,这幢4层建筑有鹤立鸡群之气势。
江滨饭店自有骄傲的资本,在青龙江对岸的古镇——鳌江也难以找到这种规格的饭店,何况饭店门外还挂着两块不同寻常的牌子,一块白底红字——“中共龙港镇委员会”;一块白底黑字——“龙港镇人民政府”。
“你找谁?”镇政府的文书朱照喜问道。
朱照喜24岁,个头一米六,看上去像个半大孩子。镇政府牌子挂出去后,从来没进过乡镇政府的农民和渔民纷纷跑来看新奇。朱照喜见来者不像当地农民,倒像投宿找错地方的打工人。
“我不找谁。”
“不找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到这里工作。”来者环视后说。
哎呀,这人口气不小,想来这儿工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朱照喜上下打量对方一下,他头发浓密,脸儿白净,眉目紧凑,单薄瘦弱,个头恐怕还没有自己高,身穿旧衬衫、草绿色军裤和一双落满灰尘的黄胶鞋,这身板就是在工地上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
“这是镇政府,你想来这儿工作就能来这儿工作?”
“你都能来这儿工作,我为什么不能?”来者笑了。
朱照喜看了他一眼,也许心想你怎好跟我比?我要不是高考没发挥好,差了28分,现在已大学毕业,没准进了县政府呢。
朱照喜赶上全省招考农村青年干部的机会,省里给新分出来的苍南县33个名额。作为“大学漏”的朱照喜一举中第,在温州市培训一年多。两个多月前,他被分配到龙港镇政府。作为农家子弟,他深为自己能进镇政府工作而自豪。
朱照喜来龙港报到时,镇委、镇政府刚成立,仅有两个人,一个书记,一个镇长。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方岩下的水流也太急了,还不到3个月,书记和镇长就被“冲”跑了。
这个镇政府也远远称不上“铁打的”,倒像个皮包公司,除两枚公章和饭店门口的牌子之外一无所有。书记、镇长走了,朱照喜成了 “元老”,那两枚公章是他上灵溪镇取回来的,牌子也是他找人制作的。
“你想找什么工作?”
“组织上让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你是哪位?”
“陈定模。”
这几天县委县政府连续下发两次任命,先是县政府提名陈萃元为龙港镇代镇长,陈林光、林昌元代副镇长,接着县委下文任命陈定模为镇委书记,陈萃元等3人为副书记,还有3位镇委委员,朱照喜都没搞清楚谁是谁。
那个年代没人把领导当老板,也没有什么张局、李副、王助之类的称谓,误把新来的领导当成清洁工或修车师傅的绝不新奇。
朱照喜没有从陈定模那温和的目光里发现威严,也没感觉到他身上不易察觉的书卷气,甚至没把他当成顶头上司,起码没表现出如今官场中部下对上司的谦卑与恭敬。朱照喜也许觉得既然他也是来工作的,那就是自家人了。他是公仆,我也是公仆,公仆与公仆分工不同,没有高低,同志之间又何必客套呢。
镇政府租的是一层楼,10个标准间和一个中型会议室。一步之宽的走廊静悄悄的,一扇扇门紧闭,脚步声是陈定模自己的。新任命的干部有的还没报到,报到的也许下基层调研了。镇委书记的办公室位于最西边,窗对青龙江。陈定模走进去,把行李放下,擦一把汗,环视一下房间:有办公桌椅和床铺,还有卫生间。住宿办公一体化,吃喝拉撒睡和办公都可以在房间解决。
下午,陈定模与上一任书记办理了交接。其实也没什么好交接的,镇委、镇政府刚运转两个多月,也就热热身,办公室是江滨饭店的,两枚公章揣在朱照喜的口袋里,他视如生命,放办公桌里怕被偷,放在宿舍怕丢了,只好随身携带,不时还用手摸摸。龙港镇4.1平方公里辖区,5个渔村,近六千人口,这是谁也偷不上抢不走的。
在龙江乡仅有的一家照相馆——望江楼留影,大家欢送上一任书记、镇长调任,没有提“欢迎陈定模、陈萃元履新”。照片上的12个人,都穿着白衬衫,一派团结紧张的感觉,好像立刻要赴战场杀敌立功。
陈定模就这么走马上任了。他45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要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了。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农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