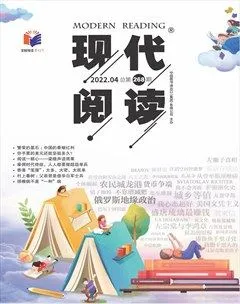你手里的美元还能坚挺多久?
2022-12-29李晓



为何美国大量印钞,美元却一直坚挺?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美国一改对外战略的传统做法,不仅频繁“退群”,引发中美贸易争端,更是对其传统盟友肆意敲打,甚至在全球四处点火,挑起争端。
这些做法看起来令人困惑不解,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美国的鲁莽之举是其衰落的自然表现。
实际上,美国到处挑起争端、四面树敌并非衰落的表现,恰恰是其依旧强大或者说是它凭借这种强大恣意妄为的结果。总的来看,美国如此作为主要有以下3个目的。
第一个是远期的:搞乱世界,甚至导致世界大乱、极度动荡不安,到那时再出手,证明这个世界需要美国,美国还是“老大”。
第二个是中期的,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重塑全球经济贸易规则,二是重构全球产业链或价值链,二者目标高度集中,即“去中国化”。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欧日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打压同其发动与中国贸易争端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以打促谈”,形成对中国的遏制,构建“去中国化”的市场经济的规则同盟,“毒丸条款”(《美墨加协定》)即是如此。因此,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危险问题不是所谓的“逆全球化”(全球化本质上不可逆),而是主要大国之间有关“全球化共识”的破裂,这种不可弥合的共识破裂,必定导致规则重塑。
第三个是近期的:促使美元资金回流。
美国一方面通过减税等方式促使实业资本回流,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另一方面则利用全球动荡时期美元的避险功能促使美元资金回流,试图以此压低长期利率,确保国内资金成本低廉,实现金融市场膨胀,经济繁荣。
显然,美国现阶段与他国特别是与中国贸易争端的背后,不仅有其强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背景,也有着强大的金融和货币优势支撑。这是我们思考、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时不应忽视的。
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20世纪世界经济最为核心的变化,使得美国构建了一个与以往霸权国家全然不同的世界控制体系,对世界的剥削与控制更加隐秘,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金融逻辑,这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与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十分巨大。
美国是如何篡改金融逻辑的?
欠债还钱,曾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金融逻辑。它使得人类社会即便在文明未现的丛林时代也能实现社会经济的缓慢进步。
当今世界,每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财政、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各种全球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其实行救助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受救助国财政紧缩,即通过节约开支、增强经济再循环机能,提升偿还贷款的能力,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五国”概莫能外。
但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所欠外债屡创新高,达到天文数字,却可以继续实现经济扩张,而且除了该国国会有关于“债务上限”的内部限制外,并无外在的强制性约束。
这个国家就是美国。
美国为什么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关键就在于,美国在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债权债务关系上偷天换日般地更改了人类的金融逻辑,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建立的美元体系予以实施。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美元体系或者美元霸权的金融逻辑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将美元体系的行为逻辑归结为美国现有的硬实力、软实力,而没有看到其本质是人类金融逻辑的变化,即从“债权人逻辑”转化为“债务人逻辑”。
6a99be2e17df116578cb5a4d49e2d8ff众所周知,在1943年下半年至1944年7月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曾有过一段著名的“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之争。
一般认为,两者之争的关键在于英国作为衰落帝国试图保证自身的地位及利益,而美国作为新兴霸权国家需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即两者分歧的焦点在于老牌帝国与新兴帝国的利益纷争。
当时“凯恩斯计划42f43343c5c47b9192c65e5bad5a0aca”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恢复多边清算,盈余国家应该负有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与此相反,“怀特计划”则坚持以美元为中心,赤字国家必须承担调整国际收支的责任。
幸运的是,虽然美国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使“怀特计划”胜出,但依其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旧秉持了“债权人逻辑”,即以债权人利益为核心要求赤字国家调整国际收支失衡,并做出紧缩等调整措施,进而为二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以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流动性与信用之间的矛盾即“特里芬难题”开始逐渐显露。
美国人曾经极度担忧美国国债的过度扩张及其政治后果,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将1985年国债总额达到1.8万亿美元视为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表现,并悲观地认为:“历史上除了美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发国债的大国仅有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它的财政危机也导致了国内的政治危机。”
但后来的经验证明,在“债权人逻辑”下如此之大的债务扩张的确是危险的,然而在“债务人逻辑”下这种担忧则是多余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特里芬难题”,而是美国不愿意像当年英国在一战后表现的那样遵守欠债还钱的“债权人逻辑”,即美国不再遵守规则。
伴随着黄金外流问题日益严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开始探讨如何摆脱“黄金魔咒”,实现美元无约束扩张的路径。1968年3月,“黄金总库”的解体、黄金市场的分割,使得世界进入了“美元本位制”。直至“保罗·沃尔克(美国经济学家)工作小组报告”的提出和时任总统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美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违约行动。
可见,美国对金融逻辑的改变并非突然,而是“蓄谋已久”。
美元体系的本质及其权力
美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改变了敦促赤字国家恢复、强化政策约束的原则,使其可以无视债务规模及其合理水平而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度则使得赤字国如美国的经常账户得以持续扩大,且导致无约束政策从赤字国传播至盈余国,破坏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与效率。
与黄金脱钩的结果,表面上看是使得美元从一种资产货币转变为债务货币,即纯粹的信用纸币制度,其实质则是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美元开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并成为其他货币的定价标准和锚定对象。
因此,与以往依靠殖民地掠夺世界的帝国主义不同,美元体系的形成及其金融逻辑的变化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规模更大、控制力更强也更为隐秘的剥削体系,这是一个超级帝国主义体系,相关政策与行为更加具有自利性,可以“合法地”放弃其应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并具有横行无敌的全球性金融权力。其核心利益在于,维护一个允许它坚守“债务人逻辑”、大量举债而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约束的世界货币秩序。
中国如何应对“挑战国陷阱”
就中国自身而言,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到,中美贸易争端不过是大国博弈的开始,是一场持久战的“序幕”,即便一时有所缓和,绝不意味着争端消弭,而是酝酿着更高层次的冲突。
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自由贸易大多是在体制、制度相近的国家间得以长期开展,而在那些规则、体制和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结果往往是冲突甚至是战争。
这场贸易争端的本质,是大国间制度的较量。
因此,应对中美贸易争端,不能将全部精力用于计算一城一池的得失,计较眼前的输赢,而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超越贸易争端本身,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顺势而为,以这场空前的外部压力为契机和动力,促进国内的体制、制度改革,以实现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针对现阶段的中美贸易争端,有3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就国内层面而言,有关中美贸易争端的损益及其度量,不能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
经验证明,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遏制对手的途径往往是多元、系统和综合的。这其中,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压制对手的可能性极大。
迄今为止,在美元体系下有关大国间贸易争端的唯一经验,来自美日贸易摩擦。其中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教训,不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崩溃,而是美国利用美元体系对对手货币的操控或打击能力,这幕戏剧的高潮就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
因此,作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中国应尽全力将中美贸易争端控制在贸易范围内,避免“货币争端”“金融争端”,即便迫不得已,也应尽力拖延时间,减小冲突规模。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逐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之举,但在资本项目开放领域仍需谨慎对待。对今天的中国而言,货币金融安全面临着比传统安全更为严峻的挑战。
与此同时,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针对现行美元体系日益增强的自利性乃至可能的金融制裁压力,中国有必要在两个领域中有所作为:一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计价原油期货市场的发展;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建设与发展。
第二,在区域层面,中国应在新形势下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
实际上,在当今美元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在其中如鱼得水,欧盟国家因为有统一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而作为世界经济第二、第三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不得不独自应对。
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心置于东亚地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更多的是增强双边抵御金融风险的信心,而非增加贸易结算功能。只有在中国处于区域生产网络中心的东亚地区,人民币贸易计价与结算功能的提升才真正具有坚实的基础与巨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中国应有恒久而非善变的地缘战略意识,高度重视周边、区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安排。鉴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历来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中国应顺势而为,以中日关系“破冰”为契机,积极推进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和经济贸易合作走向新的阶段,为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奠定坚实的区域合作基础,这应该是今后中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在国际层面,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作为美元体系的系统内国家,中国应努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秉持“债权人逻辑”或者增强对“债务人逻辑”的约束功能。
一方面,推进其朝着对美国自利的动力与行为能力加强约束的方向进展;另一方面,则应高度重视与日本、德国等对美债权国家一道,循序渐进地形成一个“债权人同盟”,共同致力于恢复以“债权人逻辑”为核心的国际货币秩序。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与安排。
(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双重冲击:大国博弈的未来与未来的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