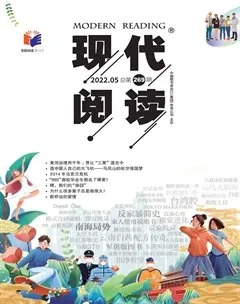黄河治理两千年:贾让“三策”通古今
2022-12-29张真宇蔺生睿


西汉末年,黄河下游淤积严重,决口频繁。据《汉书·成帝纪》记载,“四年……秋,桃李实,大水,河决东郡金堤。”《汉书·沟洫志》记载,“后三岁(建始四年,公元前28年),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这时候出了一位治河理论家,他叫贾让,因为“治河三策”而名垂青史,但他的生平简历却鲜有记载,家族渊源更无从可考。
“西汉哀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贾让应诏上书。”绥和是西汉时期皇帝汉成帝刘骜的第七个年号,公元前8年至公元前7年,汉哀帝即位沿用至年末,次年改元建平。由此可知,汉哀帝上任第一年就接见了贾让,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黄河形势严峻,连他的皇帝年号都没来得及定夺,就把治理黄河提上了议事日程,正应了“欲治国,先治河”的道理;二是说明贾让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阅历和资历。
据班固著《汉书·沟洫志》记载,哀帝初年,河官有奏:“九河今皆置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黄河问题迫在眉睫,需要皇帝选派专家协助治河,于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们举吏民能者,但没有人来应聘。只有“待诏”贾让对治河有见解,于是史无前例的“治河三策”火热出炉。贾让当时没有什么正式官衔,“待诏”身份相当于现在国家智库里的人才。
贾让的“治河三策”都有些什么内容?
所谓三策,并非平行的3个方案,而是解决黄河疑难杂症的上策、中策、下策。《汉书·沟洫志》对此有详细记载。贾让奏言,先是将黄河现状、存在问题如实奏报,接着便提出3个治河方案以及可行性分析,供皇帝拍板,而且奏明此3个方案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说还是有轻重,属于上、中、下3种选择。
贾让的“治河三策”,其实很有针对性,是针对两千多年以前西汉王朝以及天下百姓所面对的那条黄河;很有实操性,对黄河下游怎么治理、怎么修整、什么流路都有论述,而且对采用不同思路治河将取得的结果、优劣性都有明确说辞。现在所言“三策”,是后人将其理论化了的,概括为:上策是不与水争地。这是直到如今依然先进的治水理念,具体措施是“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这是针对当时黄河已成悬河不可挽回,提出人工改道,避高趋下。他认为,实行这一方案,虽要付出重大代价,“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但是可以使“河定民安,千载无患”。
中策是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运等目的。贾让认为这一方案不能一劳永逸,但可兴利除害,造福于民,而且能维持数百年。
接下来就是下策了,贾让认为如果固守旧堤,年年修补,劳费无穷,属于三策中的最下策,可以勉强维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这便是贾让“治河三策”的核心内容。到底汉哀帝采用了哪一策,终究无据可查。而在贾让之后约80年(公元69年),历史的车轮驶向东汉时代,水利专家王景登上了治理黄河的历史舞台,尽管史书没有记载他的治河理论,但他的治河实践却昭然于世,而且显然对贾让的“治河三策”很有研究,看其结果,大概用的是“中策”。贾让认为中策不能一劳永逸,但可兴利除害,维持数百年黄河安澜。贾让幸而言中。
从贾让到王景的近80年,是大汉王朝一个动荡的年代。西汉末年出了个王莽,改朝换代;接着南阳郡的“奉天命者”刘秀来了,东汉拉开了历史大幕。贾让“治河三策”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而王景遇上了大汉王朝再度兴盛的时代,仅仅用了贾让的中策,就一举成名,至今传为美谈。
贾让虽然生不逢时,但他的“治河三策”,经《汉书·沟洫志》详细记载而流传后世,对于后来的治黄方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站在今天,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审视先贤的“治河三策”,会发现贾让从尊重自然、尊重黄河本性出发,追求人水和谐,其治河理念不仅不过时,而且依然闪耀着超越时代的光辉。
1933年,民国时代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依据我国人口分布图与人口密度图,划出一条著名的“胡焕庸线”,并撰文《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文章称:“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千万,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这就是著名的胡氏“瑷珲—腾冲线”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不是一条简单的45°斜线,而是一条具有丰富的人口地理学、人口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内涵的线。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大西北的人口增加了,经济总量也大了许多,但这条虚拟的线仍然是中国东南、西北部的人口地理分布界线,东南多西北少的格局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一条虚拟的线告诉我们,我国适宜人类生存的国土主要在东南地区,而黄河下游正在这条线的东南区。因而不难理解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农耕文明的主要标志就是有足够的耕地,就是现在也有一个最通俗、最实在、最重要的词,这就是“口粮田”。
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确保粮食安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黄河下游25万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土质肥沃,地势平坦,正是耕地红线重点地区之一。如果按照贾让的上策:主张不与水争地。实行这一移民方案,虽要付出重大代价,“败坏城郭、田庐”,却可以使“河定民安,千载无患”。这基本就是“人工改道”说了,但实施起来一定是千难万难,因为人往哪里去的问题不仅当时难以解决,就是现在也困难重重。早在20世纪90年代,河南、山东两省就开始尝试实施黄河滩区向外移民,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有100多万居民在高滩和中滩区生活、生产。
我们拿“瑷珲—腾冲线”说事,是因为我们发现,贾让当年的中策,才是今天的上策。“开渠引水,达到分洪、灌溉和发展航运”等目的,除了航运没实现,其他不仅实现了,而且早已超越了古人的想象力。
自1946年黄河回归1855年故道以来,人民治黄总结了历代治黄经验与教训,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调水调沙,综合治理,实现了七十多年黄河安澜。在2020年黄河下游洪水实战演练中,5020立方米/秒的人造洪峰顺利汇入大海,而黄河下游河道全线没有出现出槽漫滩,说明通过多年连续利用水库汛前泄洪排沙,调水调沙,减游刷槽,黄河河道过流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黄河下游悬河形势正在得到缓解。
(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天下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