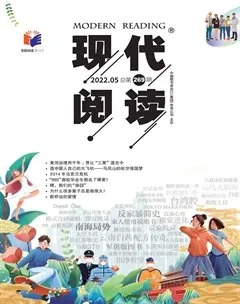如果悟净是个哲学家\t
2022-12-29章远阳


日本小说家中岛敦善于“重塑”经典故事,他的短篇小说集《山月记》取材于中国古代典籍,重新演绎李征、子路、李陵、苏武、悟净等人物的故事。我正是因为看了《山月记》,才会想聊一聊悟净。
悟净的自缚与自救
流沙河底住着的约一万三千个妖怪里,只有悟净最心神不宁。那时,河底的活物都相信他是由天上的卷帘大将转世,只有悟净自己深表怀疑。他想不通自己与卷帘大将有什么身体或灵魂上的联系,想不通为什么自己没有相关记忆,想不通灵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不能像其他妖怪一样直接相信转世投胎说,又自苦于解释不了自己提出的众多问题。他意气消沉且自我厌恶,甚至不知道“到底明白了什么,自己才能从不安中解脱出来”。
在妖怪的世界里,心病会直接转化为肉体痛苦。悟净已疼痛难忍,必须立刻上路寻医。
他花了五年多的时间遍访河底的贤者、名医、占星师,在千奇百怪的世界观里遨游。他遇到过招摇撞骗的道人,遇到过将幸福等同于万事皆空的隐士,遇到过以个人感受定义时间的禅修者,遇到过宣扬慈悲为怀却食子充饥的圣人,遇到过以极尽偶然之生追求“无上法悦”的女妖……五年多过去,他才意识到重复奔波于不同“医生”之间并不会治好自己的心病。如果说以往的自己想不通许多问题是愚蠢,那现在的自己就是看似见识广阔,实则愚蠢且内心空洞了。他意识到,“除了通过思考来探索意义外,也应该有更为直接的解答”。
与此同时,他来到了女偊氏的居所。
女偊氏是个极其平凡的仙人,她在悟净开始感觉到仅仅依靠思考只会在泥沼中越陷越深的节点出现,用几句话就点通了悟净。她讲道:
非要将所有的事情全都浸在意识的毒汁之中,其实是可怜且痛苦的。因为所有决定我们命运的重大变化,全都是无关乎我们的意识而进行的。
溪流流到断崖附近,打一个漩涡而后化作一道瀑布掉落下去。你胆战心惊、无限怜悯地在一旁望着如同溪流一般打着旋、飞流直下的人们,自己却为跳与不跳而踌躇不前,你明明知道自己迟早也会掉落谷底的,你明明知道不被卷入漩涡也绝非什么幸福。即便这样你还是恋恋不舍于旁观者的地位吗?
在生之漩涡中喘息的人们,事实上并不如旁观者所以为的那般不幸,至少要比持怀疑论的旁观者幸福得多啊。
其实故事并没有多么不凡,只是终究还是人贵自救,他人不过是恰到好处的助力罢了。
悟净突然明白自己无意探寻世界的意义,而所谓的追寻因果不过是自己逃避现实的一个幌子。因为被卑劣的功利主义倾向影响,害怕历尽艰险后一无所得而不敢上路,又必须找些什么充实自己,所以假装自己是个持续思考的哲学家。他有点想不论结局地去追寻一下世俗定义里的某些幸福了。正如在某个似梦非梦的情境里,观音菩萨在青白色的月光下告诉他:“正观得而净业立成,而你因心相羸劣如今才陷入了三途无量之苦恼。想来,你已不能由观想而得救,只能靠勤勉劳作而自救。”
这年秋天,悟净遇到了大唐的玄奘法师,便随他取经去了。
悟净西行
唐三藏、悟空、八戒和悟净都是截然不同的人。在悟净心里,三藏法师非常不可思议。他柔弱得毫无自卫能力,却“忍受着此种悲剧性,勇敢地追求着正确、美好的东西”。悟空是个魅力无限的天才。他聪慧又炽热,对命运满怀信心,一世神通广大,永远游戏人生。八戒热衷享乐。他总跟悟净列数这个现世的种种赏心乐事,譬如月夜吹笛、在溪流中洗澡、冬夜围炉畅谈。在悟净看来,八戒好吃懒做的背后,其实是怀揣着一种如履薄冰的绝望感在西行,他也因为某种原因将取经看作唯一的救赎,他也怀疑那个极力奔赴的“极乐世界”是否真的“极乐”。
于悟净而言,此次西行不过是试图在某个新角色里寻找自己,试图通过接近悟空那团火,理解八戒的享乐主义,或是在团队中发挥作用,以一种实践的、不假装自己是个哲学家的方式。
矛盾或均衡
我想起幼时看《西游记》,觉得悟空威风凛凛,八戒好吃懒做,唐僧坚定又刻板,唯独会忽略沙僧的人物特征。
一种感觉变得刻板,主要原因在于人从不主动思考如何推翻一种已经存在的感觉。近来我翻《西游记》原文,想到如果取经是一条必经路,沙僧的特征也许就在于不显。
唐僧,个性显著却难以评判。盲目慈悲到不能自控,常一叶障目好坏不分,他迂腐。取经路上,悟空冲动、八戒懒惰、沙僧缺少主见,大家对这条路都有过动摇,似乎只有唐僧始终如一,他坚定得近乎刻板。我欣赏坚定这种具有磅礴力量的品质,通常也欣赏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可对于唐僧我是矛盾的,因为他的坚定来得太过盲目,他一心要走的是菩萨早就安排好过程和结果的取经路,可敬也可笑。
悟空,汲取天地灵气生于石中,天赋异禀又了无牵挂。世俗里任何一种遥不可及的成就,对他来说都太易于达成了。什么金丹蟠桃定海神针,大圣想要的东西哪样不是手到擒来;什么取经大业,不过一个筋斗云的距离。可对于一出生就在罗马的人而言罗马是没有吸引力的,脱离某些界限引起的快乐,在世人持续艳羡或嫉妒的眼光里变得无趣。我想悟空若一直是大圣,当然会因为不可控而被拍死。让他戴上紧箍咒保护唐僧取经听来可惜,后来我想,那些人为的敲打与设限,在借用他神力的同时说不定也在帮他找到一些生存意义。
凡事确有两面性,不论这两面看起来多么的不平等。
八戒,懒惰放纵总想半途而废的个性相当显著,但他境遇不差且常遇贵人。他深知“自小生来心性拙,贪闲爱懒无休歇。不曾养性与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即便如此,他还能有缘拜师真仙,得传九转大还丹后飞升成仙;即便他在蟠桃宴调戏嫦娥依律当斩,却有太白金星殿上求情使其免死,还有观音劝善给他还得正果的机会。转意修行是他与混沌迷心抗争的起点,被封为享八方香火的净坛使者,似乎也暗示了他在修行与贪闲的博弈中达到了相对均衡的状态。
沙僧,特征不显著。比起八戒来,沙僧的路走得曲折太多。他“自小生来神气壮,乾坤万里曾游荡”,比起八戒的偶遇真仙,沙僧的寻师之路是“沿地云游数十遭,到处闲行百余趟”;比起八戒得传九转大还丹,他是“明堂肾水入华池,重楼肝火投心脏”,三千功满才得以拜天颜,曲折得近乎真实,这才是众生常态啊。沙僧的命运转折点也发生在蟠桃宴,他因失手打破玉玻璃遭贬至流沙河,同时被罚每七日承一次飞剑穿刺胸胁之苦,直至被观音点化取经。
到这里,我在想是不是沙僧的性格里也有一点不被看好的执拗,即便曾云游多年无果,即便修行漫长且曲折,即便长期苦刑加身,当遇观音点化时,他还是即刻道出一句“愿皈正果”,他还是相信自己可以修得正果的吧。
是不是所有像沙僧一样特征不那么显著又不那么幸运的众生,心里都有些不显的执拗;要是有选择的余地,是不是大家都更愿意走那条不那么舒服的路。我们总是忽略沙僧,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承认如果真的去取经,自己也是个沙僧。
我们费尽心思地评价他人,却想不到,唯一该被评判的只有自己。
(本刊原创文章)